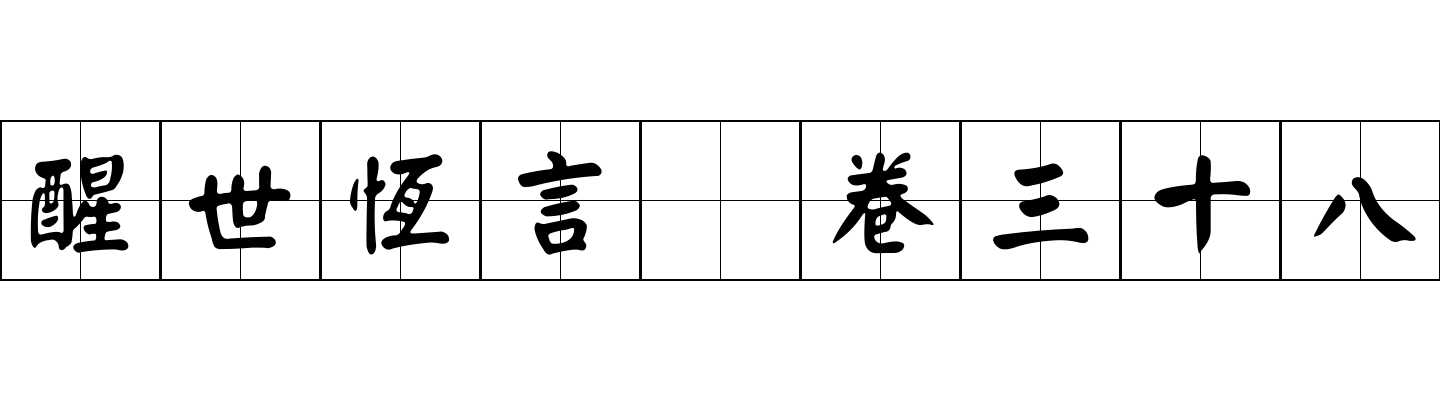醒世恆言-卷三十八-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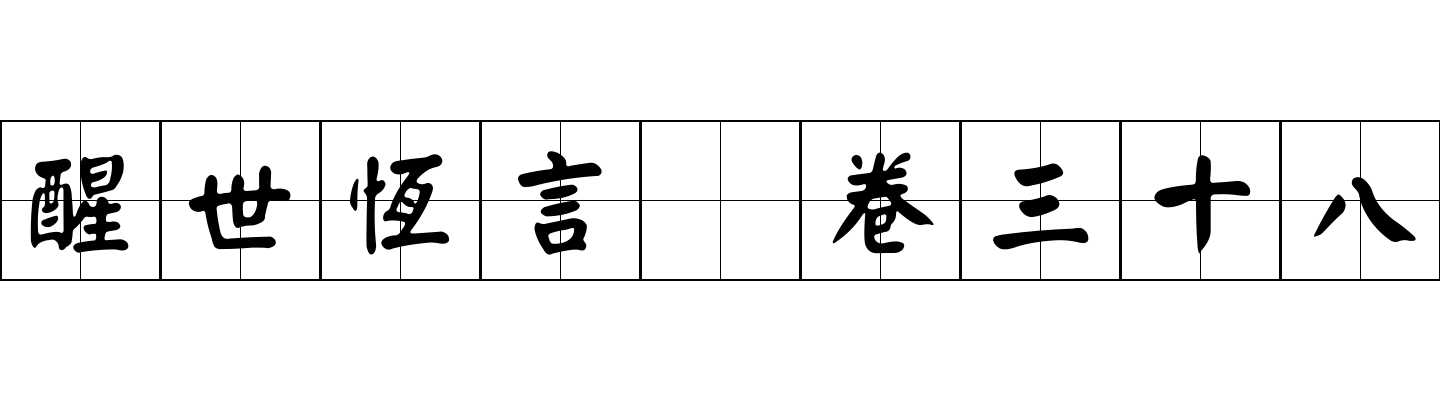
《醒世恆言》,白話短篇筆記集。明末馮夢龍纂輯。始刊於1627年(明天啓七年)。其題材或來自民間事實,或來自史傳和唐、宋故事。除少數宋元舊作外,絕大多數是明人作品,部分是馮氏擬作。形象鮮明,結構充實完整,描寫細膩,不同程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和市民思想感情。但有些作品帶有封建說教、因果報應宣傳和色情渲染。《醒世恆言》同作者之前刊行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一起,合稱《三言》,是最重要的中國古代白話短篇筆記集之一。通常亦與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並稱,稱爲“三言二拍”。
李道人獨步雲門
盡說神仙事渺茫,誰人能脫利名繮? 今朝偶讀雲門傳,陣陣薰風透體涼。
話說昔日隋文帝開皇初年,有個富翁,姓李名清,家住青州城裏,世代開染坊爲業。雖則經紀人家,宗族倒也蕃盛,合來共有五六千丁,都是有本事,光著手賺得錢的。因此家家饒裕,遠近俱稱爲李半州。一族之中,惟李清年齒最尊,推爲族長。那李清天性仁厚,族中不論親疏遠近,個個親熱,一般看待,再無兩樣心腸。爲這件上,合族長幼男女,沒一個不把他敬重。每年生日,都去置辦禮物,與他續壽。宗族已是大了,卻又好勝,各自搜覓異樣古物器玩、錦繡綾羅饋送。
他生平省儉惜福,不肯過費,俱將來藏置土庫中,逐年堆積上去,也不計其數。只有一件事,再不吝惜。你道是那一件?
他自幼行善,利人濟物,兼之慕仙好道,整千貫價佈施。若遇個雲遊道士,方外全真,叩留至家中供養,學些丹術,講些內養。誰想那班人都是走方光棍,一味說騙錢財,何曾有真實學問。枉自費過若干東西,便是戲法討不得一個。然雖如此,他這點精誠終是不改,每日焚香打坐,養性存心,有出世之念。
其年恰好齊頭七十,那些子孫們,兩月前便在那裏商議,說道:“七十古稀之年,是人生顯難得的,須不比平常誕日,各要尋幾件希奇禮物上壽,祝他個長春不老。”李清也料道子孫輩必然如此,預先設下酒席,分著一支一支的,次第請來赴宴。因對衆人說:“賴得你等勤力,各能生活,每年送我禮物,積至近萬,衣裝器具,華侈極矣!只是我平生好道,布衣蔬食垂五十年,要這般華侈的東西,也無用處;我因不好拂你等盛情,所以有受無卻。然而一向貯在土庫,未嘗檢閱,多分已皆朽壞了。費你等錢帛,做我的糞土,豈不可惜!今日幸得天曹尚未錄我魂氣,生日將到,料你等必然經營慶生之禮,甚非我的本意。所以先期相告,切莫爲此!”子孫輩皆道:“慶生的禮,自古叫做續壽。況兼七十歲,人生能有幾次,若不慶賀,何以以展卑下孝順之心?這可是少得的!”李清道:“既你等主意難奪,只憑我所要的將來送我何如?”子孫輩欣然道:“願聞尊命!”李清道:“我要生日前十日,各將手指大麻繩百尺送我,總算起來約有五六萬丈,以此續壽,豈不更爲長遠!”衆人聞聲,暗暗稱怪,齊問道:“太公吩咐,敢不奉命!但不知要他做甚?”李清笑道:“且待你等都送齊了,然後使你等知之,今猶未可輕言也。”衆子孫領了李清吩咐之後,真個一傳十,十傳百,都將麻繩百尺,趕在生日前交納,地上疊得滿高的,竟成一座繩山。只是不知他要這許多繩何用。
原來離著青州城南十里,有一座山叫做雲門山,山頂上分做兩個,儼如斧劈開的。青州城裏人家,但是向南的,無不看見這山飛雲度鳥,窩兒內經過,皆歷歷可數。俗人又稱爲劈山。那山頂中間,卻有個大穴,澒澒洞洞的,不知多少深。也有好事的,把大石塊投下,從不曾聽見些聲響,以此,人都道是沒底的。只見李清受了麻繩之後,便差人到那山上緊靠著穴口,豎起兩個大橛子,架上轆轤。家裏又喚打竹家火的,做一個結結實實的大竹籃,又到銅鋪裏買上大小銅鈴好幾百個,也不知道弄出甚麼勾當?子孫輩一齊的都來請問,李清方纔答道:“我原說終使你等知之,難道我就瞞著去了。我自幼好道,今經五十餘年,一無所得,常見《圖經》載那雲門山是神仙第七個洞府。我年已七十,便活在世上,也不過兩三年了,趁今手足尚還強建,欲於生日這一日,借你等所送的麻繩,用著四根,懸住大竹籃四角,中間另是一根,繫上銅鈴,待我坐於籃內,卻慢慢的絞下。若有些不虞去處,見我搖動中間這繩,或聽見鈴響,便好將我依舊盤上。萬一有緣,得與神仙相遇,也少不得回來,報知你等。”
說猶未畢,只見子孫輩都叩頭諫道:“不可,不可!這個大穴裏面,且莫說山精木魅、毒蛇怪獸藏著多少,只是那一道烏黑的臭氣,也把人薰死了。高年之人,怎麼禁得這股利害?”李清道:“我意已決,便死無悔!你等若不容我,必然私自逃去,從空投下。不得麻繩竹籃,永無出來的日子。”內中也有老成的,曉得他生平是個執性的人,便道:“恭敬不如從命。只是這等天大的事,豈可悄然便去,須要遍告親戚,同赴雲門山相送。也使四海流傳,做個美談,不亦可乎!”李清道:“這卻使得。”
那李家一姓子孫,原有五六千,又去通知親眷,同來拜送。只算一人一個,卻不就是上萬的人了。到得李清生辰這一日,無不陳了鼓樂,攜了酒饌,一齊的捧著李清,竟往雲門山去。隨著去看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幾乎把青州城都出空了。不一時,到了雲門山頂。衆人舉目四下一望,果然好景。但見:衆峯朝拱,列嶂環圍。響泠泠流泉幽咽,密葺葺亂草迷離。崖邊怪樹參天,巖上奇花映日。山徑煙深,野色過橋青靄近;岡形勢遠,鬆聲隔水白雲連。淅淅但聞林墜露,蕭蕭只聽葉吟風。
那竹籃繩索等件,俱已整備停當。衆親眷們,都更遞的上前奉酒。內中也有一樣高年的說道:“老親家,你好道之心這般決烈,必然是神仙路上人,此去保無他慮,但我等做事也要老成,方無後悔。我想這等黑洞洞深穴,從來沒人下去,怎把千金之體,輕投不測?今日既有竹籃繩索,不若先取一個狗來,放下去看。若是這狗無事,再把一個伶俐些家人下去,看道有甚麼仙蹟在那裏,待他上來說了,方纔送老親家下去,豈不萬全?”李清笑道:“承教,承教!只是要求道的,長拚個死,才得神仙可憐,或肯收爲弟子。這個穴內,相傳是神仙第七洞府,又不比砒霜毒藥,怎麼要試他利害?似此疑惑,便是退悔道心,怎能勾超凡脫濁?我主意已定,好歹自下去走遭。不消列位高親擔憂。老漢信口謅得四句俚言,在此留別,望勿見笑!”衆親眷齊道:“願聞珠玉。”李清隨念出一首詩來,詩云:
久拚殘命已如無,揮手開門願不孤。 翻笑壺公曾得道,猶煩市上有懸壺。
衆人聽了這詩,無不點頭嗟嘆,勉強解慰道:“老親家道心恁般堅固,但願一下去,便得逢仙。”李清道:“多謝列位祈祝,且看老漢緣法何如。”遂起來向空拜了兩拜,便去坐在竹籃內,揮手與衆親眷子孫輩作別,再也不說甚話,一逕的把麻繩轣轣轢轢放將下去。莫說衆親眷子孫輩,都一個個面色如土,連那看的人也驚呆了,搖頭咋舌道:“這老兒好端端在家受用倒不好,卻癡心妄想,往恁樣深穴中去求仙!可不是討死喫麼?”噫!李清這番下去了,不知幾時纔出世哩?正是:
神仙本是凡人做,只爲凡人不肯修。
卻說李清放下也不知有幾千多丈,覺得到了底上,便爬出竹籃,去看那裏面有何仙蹟。豈知穴底黑洞洞的,已是不見一些高低,況是地下有水一般,又滑又爛。還不曾走得一步,早跌上一交。那七十歲老人家,有甚氣力,才掙得起。又閃上一跌。只兩交,就把李清跌得昏暈了去。那上面親眷子孫輩,看看日色傍晚,又不見中間的麻繩曳動,又不聽得銅鈴響,都猜著道:“這老人家被那股陰溼的臭氣相觸,多分不保了。”且把轆轤絞上竹籃看時,只見一個空籃,不見了李清。
其時就著了忙,只得又把竹籃放下。守了一會,再絞上來,依舊是個空籃。那夥看的人,也有嗟嘆的,也有發笑的,都一鬨走了。
子孫輩只是向著穴中放聲大哭,埋怨道:“我們苦苦諫阻,只不肯聽,偏要下去。七十之人,不爲壽夭,只是死便死了,也留個骸骨,等我們好辦棺槨葬他。如今弄得屍首都沒了,這事怎處?”那親眷們人人哀感,無不灑淚。內中也有達者說道:“人之生死,無非大數。今日生辰,就是他數盡之日,便留在家裏,也少不得是死的。況他志向如此,縱死已遂其志,當無所悔。雖然沒了屍首,他衣冠是有的,不若今晚且回去,明早請幾個有法力的道士,重到這裏,招他魂去。只將衣冠埋葬,也是古人一個葬法。我聞軒轅皇帝得了大道,已在鼎湖昇天去了,還留下一把劍、兩隻履,裝在棺內,葬於橋山。又安知這老翁不做了神仙,也要教我們與他做個空冢。只管對看穴口啼啼哭哭,豈不惑哉!”子孫輩只得依允,拭了眼淚,收拾回家。到明日重來山頂,招魂回去。一般的設座停棺,少不得諸親衆眷都來祭奠。過了七七四十九日,造墳不葬,不在話下。
且說李清被這兩跌,暈去好幾時,方纔醒得轉來,又去細細的摸看。原來這穴底,也不多大,只有一丈來闊,周圍都是石壁,別無甚奇異之處。況且腳下爛泥,又滑得緊,不能舉步,只得仍舊去尋那竹籃坐下,思量曳動繩索,搖響銅鈴,待他們再絞上去。伸手遍地摸著,已不見了竹籃,叫又叫不應,飛又飛不出,真個來時有路,去日無門,教李清怎麼處置?只得盤膝兒,坐在地下。也不知捱了幾日,但覺飢渴得緊,一時難過,想道古人齧雪吞氈,尚且救了性命,這裏無雪無氈,只有爛泥在手頭,便去抓一把來嚥下。豈知神仙窟宅,每遇三千年才一開,底裏迸出泥來,叫做“青泥”,專是把與仙人做飯喫的,盡也有些味道,可解飢渴。吃了幾口,覺得精神好些。卻又去細細摸看,只見石壁擦底下,又有個小穴,高不上二尺。心下想道:“只管坐在泥中,有何了期!左右沒命的人了,便這裏面有甚麼毒蛇妖怪,也顧不得,且是爬將進去,看個下落。”只因這番,直教黑茫茫斷頭之路,另見個境界風光;活喇喇拚命之夫,重開個鋪行生理。正是:
閻王未注今朝死,山穴寧無別道通?
李清不顧性命,鑽進小穴裏去,約莫的爬了六七裏,覺得裏面漸漸高了二尺來多,左右是立不直的,只是爬著地走。
那老人家也不知天曉日暗,倦時就睡上一覺,飢時就把青泥喫上幾口。又爬了二十餘裏,只見前面透出星也似一點亮光,想道:“且喜已有出路了。”再把青泥喫些,打起精神,一鑽鑽向前去。出了穴口,但見青的山,綠的樹,又是一個境界。
李清起來伸一伸腰,站一站腳,整衣拂履,望空謝道:“慚愧!
今朝脫得這一場大難!”依著大路,走上十四五里,腹中漸漸飢餒,路上又沒一個人家賣得飯喫。總有得買,腰邊也沒錢鈔,穴裏的青泥,又不曾帶得些出來,看看走不動了。只見路旁碧靛青的流水,兩岸覆著菊花,且去捧些水喫。豈知這水也不是容易喫的,仙家叫做“菊泉”,最能延年卻病。那李清才喫得幾口,便覺神清氣爽,手腳都輕快了。
又走上十多裏,忽望見樹頂露出琉璃瓦蓋造的屋脊,金碧閃爍,不知甚麼所在?飛捻的趕到那裏去看,卻是座血紅的觀門,周圍都是白玉石砌就臺基。共有九層,每一層約有一丈多高,又沒個階坡,只得攀藤捫葛,拚命吊將上去。那門兒又閉著,不敢擅自去叩,只得屏氣而待。直等到一佛出世,二佛昇天,方纔有個青衣童子開門出來,喝道:“李清,你來此怎麼?”李清連忙的伏地叩頭,稱道:“青州染匠李清不揣凡庸,冒叩洞府,伏乞收爲弟子,生死難忘!”那童子笑道:“我怎好收留得你?且引你進去懇求我主人便了。”那青衣童子入去不久,便出來引李清進去。到玉墀之下,仰看壁上華麗如天宮一般,端的好去處。但見:
朱甍耀日,碧瓦標霞。起百尺琉璃寶殿,甃九層白玉瑤臺。隱隱雕樑鐫玳瑁,行行繡柱嵌珊瑚。琳宮貝闕,飛檐長接彩雲浮;玉宇瓊樓,畫棟每含蒼霧宿。曲曲欄杆圍瑪瑙,深深簾幕掛珍珠。青鸞玄鶴雙雙舞,白鹿丹麟對對遊。野外千花開爛熳,林間百鳥囀清幽。
李清去那殿中看時,只見正居中坐著一位仙長,頭戴碧玉蓮冠,身披縷金羽衣,腰繫黃縧,足穿朱舄,手中執著如意,有神遊八極之表。東西兩傍,每邊又坐著四位,一個個仙風道骨,服色不一。滿殿祥雲繚繞,香氣氤氳,真個萬籟無聲,一塵不到,好生嚴肅。李清上前,逐位叩了頭,依舊將這冒死投見的情節,表訴一遍。只見中間的仙長說道:“李清,你未該來此,怎麼就擅自投到?我這裏沒有你的坐位,快回去罷!”李清便涕泣稟道:“我李清一生好道,不曾有些兒效驗。今日幸得到了仙宮,面見仙長,豈肯空手回去?我已是七十歲的人,左右回去,也沒多幾時活,難道還再來得成?
情願死便死在階下,斷然不回去了。”那仙長只是搖頭不允。
卻得旁邊的替他稟道:“雖則李清未該到此,但他一片虔誠,亦自可憐!我今若不留他,只道神仙到底修不得的了。況我法門中,本以度人爲第一功德,姑且收留門下,若是不堪受教,再遣他回去,亦未遲也!”那仙長才點著頭道:“也罷!也罷!姑容他在西邊耳房暫住。”李清連忙拜謝。一頭走到耳房裏去,一頭想道:“我若沒有些道氣,怎得做仙家弟子?只是當初曾與子孫們約道,遇得仙時,少不得給假回去,報知你等。今我再三哀稟,又得傍邊這幾位仙長相勸,才許收留,怎麼又請回去?萬一觸忤了他,嗔責我塵緣未淨,如何是好?且自安心靜坐,再過幾時,另作區處。”那李清走到西邊耳房下,尚未坐定,只見一個老者,從門外進來,稟道:“蓬萊山露明觀丁尊師初到,西王母特啓瑤池大宴,請羣真同赴。”並不見有人陳設,早已幾乘鶴駕鸞車,齊齊整整,擺列殿下。其時中間的仙長在前,兩傍的八位在後,次第步出殿來。那李清也免不得隨著那夥青衣童子,在丹墀裏候送。只見仙長覷著李清吩咐道:“你在此,若要觀山玩水,任意無拘;惟有北窗,最是輕易開不得的,謹記,謹記!”說罷,各各跨上鸞鶴,騰空而起。自然有云霞擁護,簫管喧闐,這也不能備述。
豈知李清在耳房下憑窗眺望,看見三面景緻。幽禽怪鳥,四時有不絕之音;異草奇花,八節有長春之色。真個觀之不足,玩之有餘。漸漸轉過身來,只見北窗斜掩,想道:“既是三面都好看得,怎麼偏生一個北窗卻看不得?必定有甚奇異之處,故不把與我看。如今仙長已去赴會,不知多少程途,未必就回,且待我悄悄的開來看看,仙長哪裏便知道了?”走上前輕輕把手一推,呀的一聲,那窗早已開了。舉目仔細一觀,有恁般作怪的事!一座青州城正臨在北窗之下。見州里人家,歷歷在目。又見所住高大屋宅,漸已殘毀,近族傍支,漸已零落,不勝慨嘆道:“怎麼我出來得這幾日,家裏便是這等一個模樣了?俗語道得好:‘家無主,屋倒柱。’我若早知如此,就不到得這裏也罷!何苦使我子孫恁般不成器,壞了我的門風。”不覺歸心頓然而起。豈知嘆聲未畢,衆仙長已早回來了,只聽得殿上大叫:“李清!李清!”
那李清連忙掩上北窗,走到階下。中間的仙長大怒道:“我吩咐你不許偷開北窗,你怎麼違命,擅自開了?又嗟嘆懊悔,思量回去。我所以不肯收留者,正爲你塵心不斷故也。今日如何還容得你在此,便可速回,無得溷我洞府!”那李清無言可答,只是叩頭請罪,哀告道:“我來時不知吃了多少苦楚,真個性命是毫釐絲忽上掙來的。如今回去,休說竹籃繩索,已被家裏人絞上;就是這三十多裏小小穴道中,我老人家怎麼還爬得過?”仙長笑道:“這不必憂慮,我另有個路徑,教人指引你出去。”那李清方纔放下了這條肚腸,起來拜謝出門。
只見東手頭一位,向著仙長不知說甚話。仙長便喚李清:“你且轉來。”李清想道:“一定的又似前番相勸,收留我了。”不勝欣然。急急走轉去跪下,聽候法旨。
你道那仙長喚李清回來,說些甚麼?說道:“我遣便遣你回去,只是你沒個生理,何以度日?我書架上有的是書,你可隨意取一本去,若是要覓衣飯,只看這書上,自然有了。”
李清口裏答應,心裏想道:“原來仙長也只曉得這裏的事,不曉得我青州郡裏的事。我本有萬金家計,就是子孫輩連年送的生日禮物,也有好幾千,怎麼剛出來得這兩日,便回去沒有飯吃了?”只是難得他一片好意,不免走近書架上,取了一本最薄的,過去拜謝。那仙長問道:“書有了麼?”李清道:“有了。”仙長道:“既有了書,去罷!”
李清正待出門,只見西手頭一位,向著仙長也不知說甚話。那仙長把頭一點,又叫道:“李清你且轉來。”李清想道:“難道這一番不是勸他收留我的?”豈知仍舊不是。只見仙長道:“你回去,也要走好些路,纔到得家裏。便到了家裏,也不能勾就有飯喫,你可喫飽了去。”早有童子,拿出兩個大芋頭來,遞與李清喫。原來是煮熟的鵝卵石,就似芋頭一般,軟軟的,嫩嫩的,又香又甜,比著雲門穴底的青泥,越加好喫。
再走過去拜謝。那仙長道:“李清,你此去,也只消七十多年,還該到這裏的。但是青州一郡,多少小兒的性命,都還在你身上!你可廣行方便,休得墮落。我有四句偈語,把與你一生受用,你緊記著!”偈語云:
見石而行,聽簡而問。傍金而居,先裴而遁。
李清再拜受了這偈語,卻教初來時原引進的童子送他回去。竟不知又走出個甚的路徑來,總便不消得萬丈麻繩,難道也沒有一些險處?原來那童子指引的路徑,全不是舊時來的去處,卻繞著這一所仙院,倒轉向背後山坡上去。只見一個所在,出得好白石頭,有許多人在那裏打他。李清問道:“仙家要這石頭何用?”童子道:“這個是白玉,因爲早晚又有一個尊師該來,故此差人打去,要做第十把交椅。”李清便問道:“這個尊師是甚麼名姓?”童子道:“連我們也只聽得是這等說,怎麼知道?便知道,也不好說得,恐怕泄漏天機,被主人見罪。”一頭說,一頭走,也行了十四五里,都是龜背大路,兩傍參天的古樹,間著奇花異卉,看不盡的景緻,便再走兩裏,也不覺的。
又走過一座高山,這路徑漸漸僻小,童子把手指道:“此去不上十里,就是青州北門了。”李清道:“我前日來時,是出南門的,怎麼今日卻進北門?我生長在青州已七十歲了,那曉得這座雲門山是環著州城的。可知道開了北窗,便直看見青州城裏。但不知那一邊是前路,那一邊是後路,可指示我,等我日後再來叩見仙長,只打這條路上來,卻不省費許多麻繩吊去雲門穴裏去?”問未絕口,豈知颼颼的一陣風起,托地跳出一個大蟲來,向著李清便撲,驚得李清魂膽俱喪,叫聲:“苦也!”望後便倒,嚇死在地。可憐:身名未得登仙府,支體先歸虎腹中。
說話的,我且問你:嘗聞得古老傳說,那青泥白石,乃仙家糧糗,凡人急切難遇,若有緣的嘗一嘗,便疾病不能侵,妖怪不能近,虎狼不能傷;這李清兩件既已都曾飽食,況又在洞府中住過,雖則道心不堅,打發回去,卻又原許他七十年後,還歸洞府,分明是個神仙了,如何卻送在大蟲口裏?看官們莫要性急,待在下慢慢表白出來。那大蟲不是平常喫人的虎,乃是個神虎,專與仙家看山守門的,是那童子故意差來把李清驚嚇,只教他迷了來路,原非傷他性命。
那李清死去半晌,漸漸的醒轉來,口裏只叫:“救命,救命!”慢慢掙扎坐起看時,大蟲已是不見,連青衣童子也不知去向,跌足道:“罷了,罷了!這童子一定被大蟲馱去吃了。
可憐,可憐!”卻又想道:“那童子是侍從仙長的,料必也有些仙氣,大蟲如何敢去傷他?決無此理。只是因甚不送我到家,半路就撇了去?”心下好生疑惑,爬將起來,把衣服整頓好了,忽地回頭觀看,又喫一驚:怎麼那來路一剗都是高山陡壁,全無路徑?連稱:“奇怪!奇怪!”口裏便說,心中只怕又跳出一個大蟲來,卻不喪了這條老命。且自負命跑去。約莫走上四五里,卻是三叉路口,又沒一個行人來往,可以問信。看看日色傍晚,萬一走差路頭怎了!正在沒擺佈處,猛然看見一條路上,卻有塊老大的石頭,支出在那裏,因而悟道:“仙長傳授我的偈語,有句道:‘見石而行。’卻不是教我往這條路去?”果然又走上四五里,早是青州北門了。
進了城門,覺得街道還略略可認,只是兩邊的屋宇,全比往時不同,莫測其故,欲要問人,偏生又不遇著一個熟的。
漸漸天色又黑,只得趕回家去。豈知家裏房子,也都改換,卻另起了大門樓,兩邊八字牆,好不雄壯!李清暗道:“莫非錯走到州前來了?”仔細再看:“像便像個衙門,端只是我家裏。
難道這等改換了,我便認不得。想我離家去,只在雲門穴裏,不知擔擱了幾日,也是有數的。後面鑽出小穴來,總是今日這一日,怎麼便有這許多差異的事?莫非州里見我不在,就把我家房子白白的佔做衙門?可道凡事也不問個主。只可惜今日晚了,拚到明日,打進狀詞,與他理會。隨你官府,也少不得給官價還我。”只得尋個客店安歇,爭奈身邊一個錢也沒有,不免解件衣服下來,換了一貫錢。還覺腹中是飽的,只買一角酒來吃了。便待去睡,終久心下旁徨,這夜如何睡得著。李清在牀上翻來覆去,自嗟自嘆,悔道:“我怎麼倒去抱怨仙長?他明明說我回去將何度日?教我取書一本,別做生理。又道是我回去,就也未有飯喫,把兩個煮熟的石子與我,豈不是預知已有今日了。”便去袖裏把書一摸,且喜得尚在,只如今未有工夫去看。
待到天明,還了房錢,便遍著青州大街上都走轉來,莫說衆親眷子孫沒有一個,連那染坊鋪面,也沒一間留下的。只得陪個小心,逢人便問。豈知個個搖頭,人人努嘴,都說道:“我們並不知道有甚李清,也並不曾見說雲門山穴裏有人下去得的?”只教李清茫然莫知所以。看看天晚,只得又向客店中安歇。到第二日,又向小巷兒裏東抄西轉,也不曾遇著一個。
但是問人,都與大街上說話一般,一發把李清弄呆了,想道:“我也怪前日出來的路徑,有些差異,莫非這座青州城是新建的,不是我舊青州?故此沒個熟人相遇。天下雲門山只有一個,絕無兩個。我何不出了南門,逕到雲門山上一看,若雲門山無異,這便是我舊青州了,再慢慢的訪問,好歹究出甚的緣故來。”忙忙的奔出南門,逕往雲門山去。
將至山頂,早見一座亭子,想道:“這路徑明明是雲門山的,幾時有個亭子在這裏?且待我看是甚麼亭?”原來題著:“爛繩亭。開皇四年立。”李清道:“是了!昔日樵夫曾遇見仙人下棋,他看得一局棋完,不知已過了多少年歲,這斧柄坐在身下,已爛壞了,至今世人傳說爛柯的故事。多分是我衆子孫,道我將這麻繩吊下雲門穴底,也去遇了神仙,把繩都爛掉在山上,故建立這座亭子,名爲爛繩亭。無非要四方流傳,做個美談的意思。看他後面寫著‘開皇四年立’,卻不仍是今年的日月,怎麼城裏人家就是這等改換了?且再到上邊去看。”只見當著穴口,豎個碑石,題道:“李清招魂處。”李清嚇了一跳道:“我現今活活的在此,又不曾死,要招我的魂做甚麼?”又想了一想道:“是了,是了!是我下到這般險處,提起竹籃上來,又不見了我,疑心道死了,故在此招我的魂回去。”又想一想道:“咦!莫非是我真個死了,今日是魂靈到此?”心下反旁徨起來,不能自決,想道:“既是招魂,必有個葬處;若是葬,必在祖墳左右,人家雖有改換之日,祖宗墳墓,卻千年不改換的,何不再去祖墳上一看,或者倒有個明白。”
下了雲門山,一逕的轉過東門,遠遠望見祖墳上,山勢活似一條青龍,從天上飛將下來的。想起:“《葬經》上面有云:‘山如鳳舉,或似龍蟠,一千年後當出仙官。’看我祖墳有這等風水,怎麼剛出得我一個!才遇見仙人,又被趕逐回家,焉能勾昇天日子?卻不知這風水,畢竟應在那個身上?”
到了祖墳,不免拜了兩拜。只見許多合抱的青松白楊,盡被人伐去,墳上的碑石,也有推倒的,也有打斷的,全不似舊時模樣,不勝悽感,嘆道:“我家衆子孫,真個都死斷了,就沒一個來到墳上照管?”單有一個碑,倒還是豎著的,碑上字跡,彷佛可認,乃是“故道士李清之墓”七個字。李清道:“既是招魂葬,無過把些衣冠埋在裏面,料必是個空冢。只是碑石已被苔蘚駁蝕幾盡,須不是開皇四年立的,可知我死已多時了。今日來家的,一定是我魂靈,故此幽明間隔,衆親眷子孫都不得與我相見。不然,這上千上萬的人,怎麼就沒一個在的?”那李清滿肚子疑心:“只當青天白日,做夢一般。
又不知是生,又不知是死,教我哪裏去問個明白?”
正在旁徨之際,忽聽得隱隱的漁鼓簡響,走去看時,卻是東嶽廟前一個瞎老兒,在那裏唱道情,聚著人掠錢,方纔想起:“臨出山時,仙長傳授我的偈語第二句道:‘聽簡而問。’這個不是漁鼓簡?我該問他的。且自站在一邊,待衆人散後,過去問他便了。”只見那瞎老兒,止掠得十來文錢,便沒人肯出。內中一個道:“先生,你且說唱起來,待我們斂足與你。”
瞽者道:“不成不成!我是個瞎子,倘說完了,都一溜走開,那思來尋討?”衆人道:“豈有此理!你是個殘疾人,哄了你也不當人子。”那瞽者聽信衆人,遂敲動漁鼓簡板,先念出四句詩來道: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橋下水東流。
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
唸了這四句詩,次第敷演正傳,乃是“莊子嘆骷髏”一段話文,又是道家故事,正合了李清之意。李清擠近一步,側耳而聽,只見那瞽者說一回,唱一回,正嘆到骷髏皮生肉長,覆命回陽,在地下直跳將起來。那些人也有笑的,也有嗟嘆的。卻好是個半本,瞽者就住了鼓簡,待掠錢足了,方纔又說,此乃是說平話的常規。誰知衆人聽話時一團高興,到出錢時,面面相覷,都不肯出手。又有身邊沒錢的,假意說幾句冷話,佯佯的走開去了。剛剛又只掠得五文錢。那掠錢的人,心中焦躁,發起喉急,將衆人亂罵。內中有一後生出尖攬事,就與那掠錢的爭嚷起來。一遞一句,你不讓,我不讓,便要上交廝打,把前後掠的十五文錢,撇做一地。衆人發聲喊,都走了。有幾個不走的,且去勸廝打,單撇著瞽者一人。
李清動了個惻隱之心,一頭在地上撿起那十五文錢,交付與瞽者,一頭口裏嘆道:“世情如此磽薄,錢財恁般珍重!”
瞽者接錢在手,聞其嘆語,問道:“你是兀誰?”李清道:“老漢是問信的,你若曉得些根由,倒送你幾十文酒錢。”瞽者道:“問甚麼信?”李清道:“這青州城內,有個做染匠的李家,你可曉得麼?”瞽者道:“在下正姓李,敢問老翁高姓大名?”李清道:“我叫做李清,今年七十歲了。”瞽者笑道:“你怎麼欺我瞎子,就要討我的便宜。我也不是個小夥子,年紀倒比你長些,今年七十六歲了。只我嫡堂的叔曾祖,叫做李清,你怎麼也叫做李清?”李清見他說話有些來歷,便改著口道:“天下盡有同名同姓的,豈敢討你的便宜?我且問你,那令曾叔祖,如今到哪裏去了?”
瞽者道:“這說話長哩。直在隋文帝開皇四年,我那叔曾祖也是七十歲,要到雲門山穴裏,訪甚麼神仙洞府,備下了許多麻繩,一吊吊將下去。你道這個穴裏,可是下去得的?自然死了。原來我家合族全仗他一個的福力。自他死後,家事都就零落;況又遭著兵火,遂把我合族子孫都滅盡了,單留得我一個現世報還在這裏,卻又無男無女,靠唱道情度日。”
李清暗忖道:“原來錯認我死在雲門穴裏了。”又問道:“他吊下雲門穴去,也只一年裏面,怎麼家事就這等零落得快?合族的人也這等死滅得盡?”瞽者道:“哎呀!敢是你老翁說夢哩。如今須不是開皇四年,是大唐朝高宗皇帝永徽五年了。隋文帝坐了二十四年天下,傳與煬帝,也做了十四年,被宇文化及謀殺了,因此天下大亂。卻是唐太宗打了天下,又讓與父親做皇帝,叫做高祖,坐了九年。太宗自家坐了二十三年。
如今皇帝就是太宗的太子,又登基五年了。從開皇四年算起,共是七十二年。我那叔曾祖去世時節,我只有得五歲,如今現活七十六歲了,你還說道快哩。”
李清又道:“聞得李家族裏,有五六千丁,便隔得七十三年,也不該就都死滅,只剩得你一個。”瞽者道:“老翁你怎知這個緣故?只因我族裏人,都也有些本事,會光著手賺得錢的。不料隋煬帝死後,有個王世充造反,到我青州,看見我家族裏人丁精壯,盡皆拿去當軍。那王世充又十分不濟,屢戰屢敗,遂把手下軍馬都消折了。我那時若不虧著是個帶殘疾的,也留不到今日。”李清聽了這一篇說話,如夢初覺,如醉方醒,把一肚子疑心,才得明白。身邊只有三四十文錢,盡數送與瞽者,也不與他說明這些緣故,便作別轉身,再進青州城來。
一路想道:“古詩有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果然有這等異事!我從開皇四年吊下雲門穴去,往還能得幾日,豈知又是唐高宗永徽五年,相隔七十二年了。人世光陰,這樣容易過的!若是我在裏面多住幾時,卻不連這青州城也沒有了。如今我的子孫已都做故人,自己住的高房大屋,又皆屬了別姓,這也不必說起。只是我身邊沒有半分錢鈔,眼前又別無熟識可以挪借,教我把甚麼度日?左右也是個死,那仙長何苦定要趕我回來怎的?”嘆了幾聲,想了一會,猛然省道:“我李清這般懵懂,怎麼思量還要做仙哩?我臨出門時,仙長明明說我回家來,怕沒飯喫,曾教我到他書架上拿本書去,如今現在袖裏,何不取出書來,看道另做甚麼生意?”
你道這本書,是甚麼書?原來是本醫書,專治小兒的病症,也不多幾個方子在上面。那李清看見,方纔悟道:“仙長曾對我說,此去不消七十多年,依舊容我來到那裏。我想這七十年,非比雲門穴底下,須在人世上好幾時,不是容易過的。況我老人家,從來藥材行裏不曾著腳,怎便莽莽廣廣的要去行醫;且又沒些本錢,置辦藥料;不如到藥鋪裏尋個老成人,與他商量,好做理會。”剛剛走得三百餘步,就有一個白粉招牌,上寫著道:積祖金鋪出賣川廣道地生熟藥材。
當下李清看見便大喜道:“仙長傳授我的第三句偈語說道:‘傍金而居。’這不是姓金的了?世稱神仙未卜先知,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只見鋪中坐的,還不上二十多歲,叫做金大郎。李清連忙向前,與他唱個喏,問道:“你這藥材,還是現賣,也肯賒賣?”金大郎道:“別人家買藥的,都要現錢才賣;只有行醫開鋪的,是長久主顧,但要藥料,只上個帳簿取去,或一季或一月一算,總數還錢,叫做半賒半現。”李清便扯個謊道:“我原是個幼科醫人,一向背著包沿村走的,如今年紀老了,也要開個鋪面,坐地行醫,不知哪裏有空房,可以賃住?乞賜指引,也好與貴鋪做個主顧。”金大郎道:“就是我家隔壁,有一間空房,不見門上貼著‘招賃’兩字麼?只怕窄狹,不夠居住。”李清道:“我老身別無家小,便一間也儘夠了。只是鋪前須要豎面招牌,鋪內須要藥箱藥刀,各色傢伙,方纔像個行醫的。這幾件,都在哪裏去置辦?不知可也賒得否?”金大郎道:“我鋪裏盡有現成餘下的在此,我一發都借了你去。待生意興旺時,連那藥帳,一總算還與我,豈不兩得其便?”
那李清虧得金大郎一力周旋,就在他藥鋪間壁住下,想起:“當初在雲門山上與親族告別之時,曾有詩云:‘翻笑壺公曾得道,猶煩市上有懸壺。’不意今日回來,又要行醫,卻不應了兩句讖語。”遂在門前,橫吊起一面小牌,寫著“縣壺處”三個字。直豎起一面大牌,寫著“李氏專醫小兒疑難雜症”十個字。鋪內一應什物傢伙,無不完備。真個裝一佛像一佛,自然像個專門的太醫起來。
恰好這一年青州城裏,不論大小人家,都害時行天氣,叫做小兒瘟,但沾著的便死。那幼科就沒請處,連大方脈的,也請了去。豈知這病偏生利害,隨你有名先生下的藥,只當投在水裏,眼睜睜都看他死了。只有李清這老兒古怪,不消自到病人家裏切脈看病,只要說個症候,怎生模樣,便信手撮上一帖藥,也不論這藥料,有貴有賤,也不論見效不見效,但是一帖,要一百個錢。若討他兩帖的,便道:“我的藥,怎麼還用兩帖?”情願退還了錢,連這一帖也不發了。那討藥的人,都也半信半不信,無奈病勢危急,只得也贖一帖,回去喫看。
你道有這等妙藥?纔到得小兒口裏,病就好一半,一咽嚥下肚裏去,便全然好了。還有拿得藥回去,小兒已是死了的,但要煎的藥香,衝在那小兒鼻孔內,就醒將轉來。這名頭就滿城傳遍,都稱他做李一帖。
從此後,也不知醫好了多少小兒,也不知賺過了多少錢鈔。我想李清是個單身子,日逐用度有限,除算還了房錢藥錢,和那什物傢伙錢以外,贏餘的難道似平時積攢生日禮一般,都爛掉在家裏?畢竟有個來處,也有個去處。原來李清這一次回來,大不似當初性子,有積無散。除還了金大郎鋪內賒下各色傢伙,並生熟藥料的錢,其餘只勾了日逐用度,盡數將來賑濟貧乏,略不留難。這叫做廣行方便,無量功德。以此聲名,越加傳播。莫說青州一郡,遍齊魯地方,但是要做醫的,聞得李一帖名頭,那一個不來拜從門下,希圖學些方術!只見李清再不看甚醫書,又不親到病人家裏診脈,凡遇討藥人來,收了銅錢便撮上一帖藥,又不多幾樣藥味。也有說來病症是一樣的,倒與他各樣的藥;也有說來病症是各樣的,倒與他一樣藥。但見拿藥去喫的,無有不效。衆皆茫然,莫測其故,只得覓個空間,小心請教。李清道:“你等疑我不曾看脈,就要下藥,不知醫道中,本以望聞問切目爲神聖工巧,可見看脈是醫家第四等,不是上等。況小兒科與大方脈不同,他氣血未全,有何脈息可以看得?總之,醫者,意也。
無過要心下明,指下明,把一個意思揣摩將去。怎麼靠得死方子,就好療病?你等但看我的下藥,便當想我所以下藥的意思。那《大觀本草》這部書,卻不出在我山東的,你等熟讀《本草》,先知了藥性,纔好用藥。上者要看本年是甚司天,就與他分個溫涼;二者看害病的是那地方人,或近山或近水,就與他分個燥溼;三者看是甚等樣人家,富貴的人,多分柔脆,貧賤的人,多分堅強,就與他分個消補:細細的問了症候,該用何等藥味,然後出些巧思,按著君臣佐使,加減成方,自然藥與病合,病隨藥去。所以古人將用藥比之用兵,全在用得藥當,不在藥多。趙恬徒讀父書,終致敗滅,此其鑑也!”衆等皆拜謝教而退。豈知李清身邊,自有薄薄的一本仙書,怎肯輕易泄漏?正是:
小兒有命終須救,老子無書把甚看。
李清自唐高宗永徽五年,行醫開鋪起,真個光陰迅速,不覺過了第六年,又是顯慶五年,龍朔三年,麟德二年,乾封二年,總章二年,咸亨四年,上元二年,儀鳳三年,調露一年,永隆一年,開耀一年,一總共是二十七年了。這一年卻是永淳元年,忽然有個詔書下來,說御駕親倖泰山,要修漢武帝封禪的故事。你道如何叫做封禪?只爲天下五座名山,稱爲五嶽。五嶽之中無如泰山,尤爲靈秀,上通於天,雲雨皆從此出。故有得道的皇帝,遇著天下太平,風調雨順,親到泰山頂上祭祀嶽神,刻下一篇紀功德的頌,告成天地。那碑上刻的字,都是赤金填的,叫做金書。碑外又有個白玉石的套子,叫做玉檢。最是朝廷盛舉。那天帝是不好欺的,頌上略有些不實,便起怪風暴雨,不能終事。這也不是漢武帝一個創起的,直從大禹以前,就有七十九代,都曾封禪。後來只有秦始皇和漢武帝兩個,這怎叫得有道之君?無非要粉飾太平,侈人觀聽。畢竟秦始皇遇著大雨,只得躲避松樹底下;漢武帝下山,也被傷了左足。故此武帝之後,再沒有敢去封禪的。那唐高宗這次詔書,已是第三次了。青州地方,正是上泰山的必由去處,刺史官接了詔,不免點起排門夫,填街砌路,迎候聖駕。那李清既有鋪面,便也編在人夫數內,催去著役。
其時青州自有了李清行醫,羞得那幼科先生都關了鋪門,再沒個敢出頭的。若教他去做夫砌路,萬一小兒們有個急病,一時怎麼就請得他到,討得藥喫?因此合郡的人,都到州里去替他稟脫。少不得推幾個能言會語的做頭,向前稟道:“現今行醫的李清已是九十七歲近百的人,有甚麼氣力當夫?我們情願替他出錢,另顧精壯少年應役,仍留他在鋪裏,也好保全我一州的小兒性命。”原來李清開鋪這一年,依還說是七十歲,因此人只認他九十七歲,那知他已是一百六十八歲了。
從來律上凡七十以上的,即系是年老,準免差役。所以合郡的人,借這個名色,要與他顧工替役,仍留他在鋪行醫。
豈知州刺史是嶺南人,他那地方最是信巫不信醫的,說道:“雖然李清已有九十七歲,想他筋力強健,盡好做工,怎麼手裏撮得藥,偏修不得路?不見姜太公八十二歲還要輔佐周武王,興兵上陣。既做了朝廷的百姓,死也則索要做,躲避到哪裏去?總便他會醫小兒,難道偌大一坐青州,只有他幼科一個?查他開鋪以來,只得二十七年,以前的青州人家小兒,也不曾見都死絕了。怎麼獨獨除下他一個名字,何以服衆?”隨他含郡的人再三苦稟,只是不聽。急得那許多人,就沒個處置。都走到李清鋪前商議,要央個緊要的分上,再去與州官說。李清道:“多謝列位盛情!以我老朽看來,倒不去說也罷。你道一些小事,有何難聽。那州官這等拘執,無過慮著聖駕親來,非尋常上司之比。少有不當,便是砍頭的罪過。故此只要正身著役,恐怕顧工的做出事來,以後不好查究。做官的肚腸,大概如此,斷然不肯再聽人說。但我揣度事勢,這詔書也多分要停止的。在麟德二年一次,調露元年又一次。如今卻是第三次。既是前兩次不來,難道這一次又來得成?包你五日裏面,就有決裂。不若且放下膽,憑他怎生樣差撥便了!”
衆人聽了這篇說話,都怪道:“眼見得州里早晚就要僉了牌,分了路數,押夫著役,如火急一般,那老兒倒說得冰也似冷。若是詔書一日不停止,怕你一日不做夫!我們倒思量與他央個分上,保求頂替,他偏生自要去當。想是在鋪裏收錢不迭,只要到州里去領他二分一日的工食哩。”都冷笑一聲,各自散去。豈知高宗皇帝這一次已是決意要到泰山封禪,詔下禮部官,草定了一應儀注,只待擇個黃道吉日,御駕啓行;忽然患了個痿痹的症候,兩隻腳都站不起來,怎麼還去行得這等大禮?因此青州上司,隔不得三日之內,移文下來,將前詔停止。那合郡的人,方信李清神見,越加歎服。
原來山東地面,方術之士最多,自秦始皇好道,遣徐福載了五百個童男童女到蓬萊山,採不死之藥。那徐福就是齊人。後來漢武帝也好道,拜李少君爲文成將軍,欒大爲五利將軍,日逐在通天台、竹宮、桂館祈求神仙下降。那少君、欒大也是齊人。所以世代相傳,常有此輩。一向看見李清自七十歲開醫鋪起,過了二十七年,已是近百的人,再不見他添了一些兒老態,反覺得精神顏色,越越強壯,都猜是有內養的。如今又見他預知過往未來之事,一定是得道之人,與董奉、韓康一般,隱名賣藥。因此那些方士,紛紛然都來拜從門下,參玄訪道,希圖窺他底蘊。屢屢叩問李清,求傳大道。李清只推著老朽,原沒甚知覺,唯有三十歲起,便絕了欲,萬事都不營心,圖個靜養而已,所以一向沒病沒痛,或者在此。
方士們疑他隱諱,不肯輕泄,卻又問道:“壽便養得,那過去未來之事,須不是容易曉得的。不知老師有何法術,就預期五日內當有停止詔書消息?”李清道:“我哪裏真是活神仙,能未卜先知的人?豈不知孔夫子萍實商羊故事!只是平日裏聽得童謠,揣度將去,偶然符合。蓋因童謠出於無心,最是天地間一點靈機,所以有心的試他,無有不驗。我從永徽五年在此開醫鋪起,聽見龍朔年間,就有個童謠,料你等也該記得的。那童謠上說道:‘上泰山高,高几層?不怕上不得,倒怕不得登。三度徵兵馬,旁道打騰騰。▉▉▉▉▉▉▉▉▉▉▉▉▉▉。三度去,登不得。’果然前兩度已驗,故知此回必無登理。大抵老人家聞見多,經驗多,也無過因此識彼,難道有甚的法術不成!”這方士們見他不肯說,又常是收錢撮藥,忙忙的沒個閒暇,還有那夥要賑濟的來打攪,以此漸漸的也散去了。
明年高宗皇帝晏駕,卻是武則天皇后臨朝,坐了二十一年,纔是太子中宗皇帝,坐了六年,又被韋皇后謀亂。卻是睿宗皇帝除了韋后,也坐了六年,傳位玄宗皇帝,初年叫做開元,不覺又過了九年,總共四十三年。滿青州城都曉得李清,已是一百四十歲。一來見他醫藥神效如舊,二來容顏不老,也如舊日,雖或不是得道神仙,也是個高年人瑞。因此學醫的、學道的、還有真實信他的,只在門下不肯散去。正是:
神仙原在閻浮界,骨肉還須夙世成。
話分兩頭,卻說玄宗天子也志慕神仙,尊崇道教,拜著兩個天師,一個葉法善,一個邢和璞,皆是得道的,專爲天子訪求異人,傳授玄素赤黃,及還嬰溯流之事。這一年卻是開元九年,邢、葉二天師奏道:現有三個真仙在世:一個叫做張果,是恆州條山人;一個叫做羅公遠,是鄂州人;一個叫做李清,是北海人。雖然在煙霞之外,無意世上榮華,若是朝廷虔心遣使聘他,或者肯降體而來,也未可知。”因此玄宗天子,差中書舍人徐嶠去聘張果,太常博士崔仲芳去聘羅公遠,通事舍人裴晤聘李清。三個使臣辭朝別聖,捧著璽書,各自去徵聘不題。
原來李清塵世限滿,功行已圓,自然神性靈通,早已知裴舍人早晚將到,省起昔日仙長吩咐的偈語:“第四句說道:‘先裴而遁。’這個‘遁’字,是逃遁之遁,難道叫我逃走不成?明明是該尸解去了。”你道怎麼叫做尸解?從來仙家成道之日,少不得要離人世,有一樣白日飛昇的謂之羽化,有一樣也似世人一般死了的,只是棺中到底沒有屍骸,這爲之尸解。惟有尸解這門,最是不同。隨他五行,皆可解去。以此世人都有不知道他是神仙的。
且說李清一個早起,教門生等休掛牌面,說道:“我今日不賣藥了,只在午時,就要與汝等告別。”衆門生齊喫一驚,道:“師父好端端的,如何說出這般沒正經話來?況弟子輩久侍門下,都不曾傳授得師父一毫心法,怎的就去了?還是再留幾時,把玄妙與弟子們細講一講,那時師父總然仙去,道統流傳,使後世也知師父是個有道之人。”李清笑道:“我也沒甚玄祕可傳,也不必後人曉得。今大限已至,豈可強留。只是隔壁金大郎又不在此,可煩汝等爲我買具現成棺木,待我氣絕之後,即便下棺,把釘釘上,切不可停到明日。我鋪裏一應傢伙什物,都將來送與金大郎,也見得我與他七十年老鄰老舍,做主顧的意思。”衆門生一一領命,流水去買辦棺木等件,頃刻都完。那金大郎也年八十九歲了,筋骨亦甚強健,步履如飛,掙了老大家業,兒孫滿堂,人都叫他是金阿公。只有李清還在少年時看他老起來的,所以原呼他爲大郎。那日起五更往鄉間去了,所以不在。
李清到了午時,香湯沐浴,換了新衣,走入房中。那些門生,都緊緊跟著。李清道:“你們且到門首去,待我靜坐片時,將心境清一清,庶使臨期不亂。問金大郎回了,請來面別,也不枉一向相處之情。”衆門生依言,齊走出門,就問金大郎,卻還未回。隔了片時,進房觀看李清,已是死了。衆門生中,也有相從久的,一般痛哭流涕;也有不長俊的,只顧東尋西覓,搜索財物。亂了一回,依他吩咐,即便入棺。原來這屍,也有好些異處。但見他一雙手,兩隻腳,都交在胸前,如龍蟠一般。怎好便放下去?待要與他扯一扯直,豈知是個殭屍,就如一塊生鐵打成,動也動不得。只得將就擡入棺中,釘上材蓋,停在鋪裏。李清是久名向知的,頃刻便傳遍了半個青州城,主顧人家都來吊探。衆門生迎來送往,一個個弄得口苦舌乾,腰駝背曲。有詩爲證:
百年蹤跡混風塵,一旦辭歸御白雲。 羽蓋霓旌何處在,空留藥臼付門人。
卻說通事舍人裴晤,一路乘傳而來,早到青州境上。那刺史官已是知得,帥著合郡父老香燭迎接。直到州堂開讀詔書,卻是徵聘仙人李清。刺史官茫然無知,遂問衆父老。父老們稟道:“青州地方,但有個行小兒科的李清,他今年一百四十歲,昨日午時,無病而死,此外並不曾聞有甚仙人李清在那裏。”裴舍人見說,倒吃了一驚,嘆道:“下官受了多少跋涉,齎詔到此,正聘行醫的仙人李清,指望敦請得入朝,也叫做不辱君命。偏生不湊巧,剛剛的不先不後,昨日死了,連面也不曾得見。這等無緣,豈不可惜!我想漢武帝時,曾聞得有人修得神仙不死之藥,特差中大夫去求他藥方,這中大夫也是未到前,適值那人死了。武帝怪他去遲,不曾求得藥方,要殺這大夫。虧著東方朔諫道:‘那人既有不死之藥,定然自己喫過,不該死了;既死了,藥便不驗,要這方也沒用。’武帝方悟。今幸我天子神明,勝於漢武,縱無東方朔之諫,必不至有中大夫之恐。但邢、葉二天師既稱他是仙人,自當後天不老,怎麼會死?若果死,就不是仙人了。雖然如此,一百四十歲的人,無病而死,便不是仙人,卻也難得。”即便吩咐州官,取左右鄰不扶結狀,見得李清平日有何行誼,怎地修行的,於某年月某日時,已經身死,方好覆命。
刺史不敢怠慢,即喚李清左近鄰佑,責令具結前來,好送天使起身。那些鄰舍領命出去,內中一個道:“我們盡是後生,不曉得他當初來歷詳細,如何具結?聞說止有金阿公是他起頭相處的,必然知他始末根由。昨日往鄉間去了,少不得只在今日明早便歸,待他斟酌寫一張同去呈遞,也好回答。”
衆人齊稱有理,同回家去。恰好金老兒從鄉間歸來,一個人背著一大包草頭跟著,劈面遇見。衆人迎住道:“好了,金阿公回也!你昨日不到鄉間去,也好與你老友李太醫作別。”金老兒道:“他往哪裏去,要作別?”衆人道:他昨日午時已辭世了。”金老兒道:“罪過,罪過!我昨日在南門遇見的,怎說恁樣話咒他?”衆人反喫一驚道:“死也死了,怎麼你又看見?想是他的魂靈了。”金老兒也驚道:“不信有這等奇事!”
也不回家,一逕奔到李清鋪裏,只見擺著靈柩,衆門生一片都帶著白,好些人在那裏弔問。金老兒只管搖首道:“怪哉!怪哉!”衆門生向前道:“我師父昨日午時歸天了,因爲你老人家不在,這靈柩還停在此。”又遞過一張單來道:“鋪內一應什物傢伙,遺命送與你做遺念的。”
金老兒接了單,也不觀看,只叫道:“難道真個死了!我卻不信。”衆鄰舍問道:“金阿公,你且說昨日怎的看見他來?”
金老兒道:“昨日我出門雖早,未出南門,就遇了一個親戚,苦留回去喫飯,直弄到將晚,方纔別得。走到雲門山下,已是午牌時分。因見了幾種好草藥,方在那裏收採,撞見一個青衣童子,捧個香爐前走,我也不在其意。不上六七十步,便是你師父來,不知何故,左腳穿著鞋子,右腳卻是赤的。我問他到哪裏去,他說道:‘我因雲門山上爛繩亭子裏,有九位師父師兄專等我說話,還有好幾日未得回來哩。’他又在袖裏取出一封書,一個錦囊,囊裏像是個如意一般,遞與我,教帶到州里;好好的送甚裴舍人,不要誤了他事。即今書與錦囊現在我處,如何卻是死了?”便向袖中摸出來看。
衆門生起初疑心金老搗鬼,還不肯信,直待見了所寄東西,方纔信道:“且莫論午時不午時,只是我師父從不見出鋪門,怎有這東西寄送?豈不古怪!”衆鄰舍也道:“真也是希見的事!他已死了,如何又會寄東西?卻又先曉得裴舍人來聘他,便做道魂靈出現,也沒恁般顯然!一定是真仙了。”金老兒問道:“甚麼裴舍人聘他?”衆鄰舍將朝廷差裴舍人徵聘,州官知得已死,著令結狀之事說出。金老兒道:“原來如此。
如今他既有信物,何必又要結狀?我同你們去叩見州官,轉達天使。”衆人依著金老兒說話,一齊跟來。金老兒持了書與錦囊,直至州中,將李清昨日遇見寄書的話稟知。州官也道奇異,即帶一干人同去回覆天使。那裴舍人正道此行沒趣,連催州里結狀,就要起身。只見州官引衆人捧著書禮,稟是李清昨日午時,轉託鄰佑金老兒送上天使的,請自啓看。裴舍人就教拆開書來,卻是一通謝表。表上說道:陛下玉書金格,已簡於九清矣。真人降化,保世安民,但當法唐、虞之無爲,守文、景之儉約。恭候運數之極,便登蓬閬之庭。何必木食草衣,刳心滅智,與區區山澤之流學習方術者哉!無論臣初窺大道,尚未證入仙班;即張果仙尊、羅公遠道友,亦將告還方外,皆不能久侍清朝,而共佐至理者也。昔秦始皇遠聘安期生於東海之上,安期不赴,因附使者回獻赤玉舄一雙。臣雖不才,敢忘答效?謹以綠玉如意一枚,聊布鄙忱,願陛下鑑納。
裴舍人看罷,不勝嘆異,說道:“我聞神仙不死,死者必尸解也。何不啓他棺看?若果系空的,定爲神仙無疑。卻不我回朝去,好覆聖上,連衆等亦解了無窮之惑。”合州官民皆以爲然。即便同赴鋪中,將棺蓋打開看時,棺中止有青竹杖一根,鞋一隻,竟不知昨日屍首在哪裏去了。倒是不開看也罷,既是開看之後,更加奇異:但見一道青煙,沖天而起,連那一具棺木,都飛向空中,杳無蹤影。唯聞得五樣香氣,遍滿青州,約莫三百里內外,無不觸鼻。裴舍人和合州官民,盡皆望空禮拜。少不得將謝表錦囊,好好封裹,送天使還朝去訖。到得明年,普天下疫癘大作,只有青州但聞的這香氣的,便不沾染,方知李清死後,爲著故里,猶留下這段功果。至今雲門山上立祠,春秋祭祀不絕。詩云:
觀棋曾說爛柯亭,今日雲門見爛繩。 塵世百年如旦暮,癡人猶把利名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