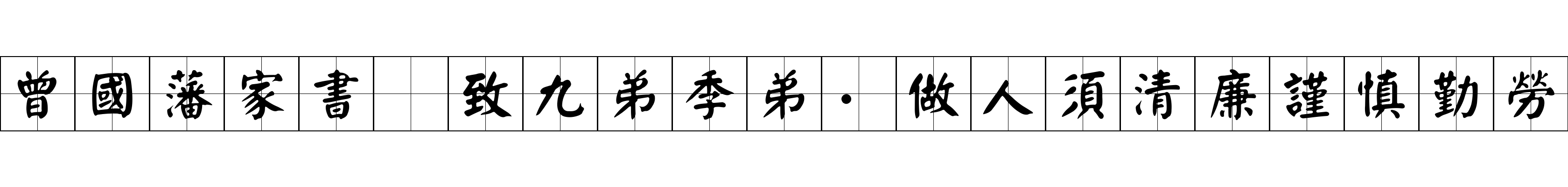曾國藩家書-致九弟季弟·做人須清廉謹慎勤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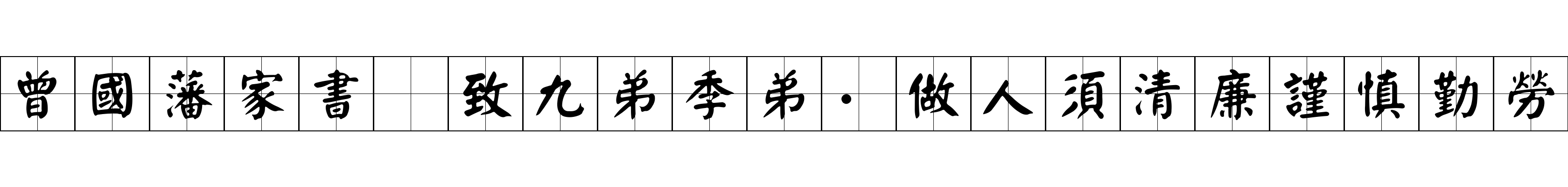
《曾國藩家書》是曾國藩的書信集,成書於清19世紀中葉。該書信集記錄了曾國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後達30年的翰苑和從武生涯,近1500封。曾氏家書行文從容鎮定,形式自由,隨想而到,揮筆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蘊育真知良言,具有極強的說服力和感召力。曾國藩作爲清代著名的理學家、文學家,對書信格式極爲講究,顯示了他恭肅、嚴謹的作風。
季沅弟左右:
帳棚即日趕辦,大約五月可解六營,六月再解六營,使新勇略得卻署也。小臺槍之藥,與大炮之藥,此問並無分別,亦未製造兩種藥,以後定每月解藥三萬斤至弟處,當不致更有缺乏。王可升十四日回省,其老營十六可到,到即派往蕪湖,免致南岸中段空虛。
雪琴與沅弟嫌隙已深,難遽期其水乳。沅弟所批雪信稿,有是處;亦有未當處。弟謂雪聲色懼厲,凡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聲音笑貌之拒人,每苦於不自見,若不自知。雪之厲,雪不自知,沅之聲色,恐亦未始不厲,特不自知耳。
曾記咸豐七年冬,餘咎駱文耆待我之薄,溫甫則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難堪。”又記十一年春,樹堂深咎張伴山簡傲不敬,餘則謂樹堂面色亦拒人於千里之外。觀此二者,則沅弟面色之厲,得毋似餘與樹堂之不自覺乎?
餘家目下鼎盛之際,餘吞竊將相,沅所統近二萬人,季所統四五千人,近世假此者,曾有幾家?沅弟半年以來,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吾家亦盈時矣。管子云:“鬥斜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餘謂天概之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將清字改爲廉字,慎字改爲謙字,勤字改爲勞字,尢爲明淺,確有可下手之處。
沅弟昔年於銀錢取與之際,不甚斟酌,朋輩之譏議菲薄,其根實在於此。去冬之買犁頭嘴栗子山,餘亦大不謂然。以後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銀回家,不多贈親族,此廉字工夫也。謙字存諸中者不可知,其著於外者,約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語,曰書函,曰僕從屬員。沅弟一次舔招六千人,季弟並未稟明,徑招三千人,此在他統領斷做不到者,在弟尚能集事,亦算順手。而弟等每次來信索取帳棚子藥等件,常多譏諷之詞,不平之語,在兄處書函如此,則與別處書函更可知已。
沅弟之僕從隨員,頗有氣焰,面色言語,與人酬按時,吾未及見,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對渠之詞氣,至今餘憾!以後宜於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謙字工夫也。每日臨睡之時,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幾件,則知宣勒王事之處無多,更竭誠以圖之,此勞字工夫也。餘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始之福,自我一人享盡,故將勞謙廉三字,時時自惕,亦願兩賢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湖州於初三日失守,可憐可儆!(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