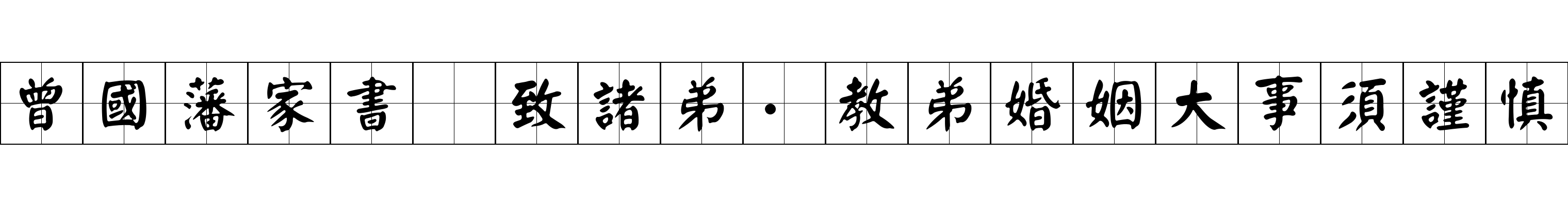曾國藩家書-致諸弟·教弟婚姻大事須謹慎-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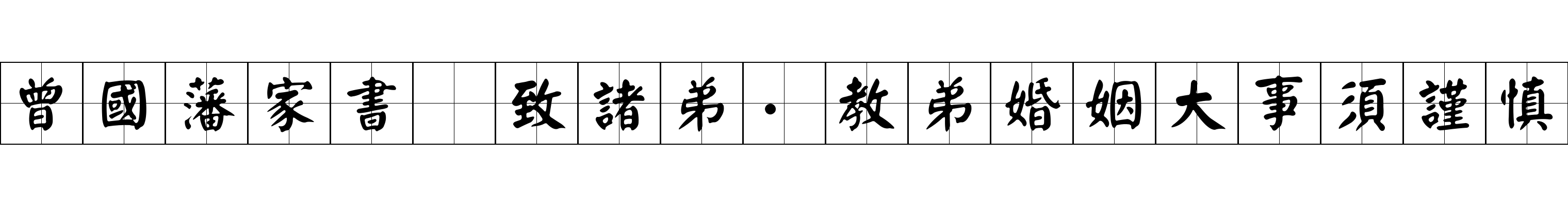
《曾國藩家書》是曾國藩的書信集,成書於清19世紀中葉。該書信集記錄了曾國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後達30年的翰苑和從武生涯,近1500封。曾氏家書行文從容鎮定,形式自由,隨想而到,揮筆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蘊育真知良言,具有極強的說服力和感召力。曾國藩作爲清代著名的理學家、文學家,對書信格式極爲講究,顯示了他恭肅、嚴謹的作風。
諸位老弟足下:
十六早,接到十一月十二日發信,內父親一信,四位老弟各一件,具悉一切,不勝次喜!四弟之詩,又有長進,第命意不甚高超,聲調不甚響亮。命意之高,須要透過一層,如說考試,則須說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懷,則詩意高矣。若說必以得科名爲榮,則意淺矣。舉此一端,餘可類推。腔調則以多讀詩爲主,熟則響矣。
去年樹立堂所寄之筆,亦我親手買者,春光醉目前每支大錢五百文,實不能再寄。漢壁尚可寄,然必須明年會武后,乃有便人回南,春間不能寄也。
五十讀書固好,然不宜以此耽擱自己功課;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不誣也。
家常欲與我結婚,我所以不願意者,因聞常世兄最好恃父勢,作威福,衣服鮮明,僕從恆赫,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驕奢習氣亂我家規,誘我子弟好奢耳。今渫再三要結婚,發甲五八字去,恐渫家是要與我爲親家,非欲與弟爲親家。此語不可不明告之。
賢弟婚事,我不敢作主,但親家爲人如何?亦須向汪三處查明。若吸鴉片煙,則萬不可對。若無此事,則聽堂上各大人與弟自主之可也。所謂翰堂秀才者,其父子皆不宜親近,我曾見過,想衡陽人亦有知之者,若要對親,或另請媒人亦可。
六弟九月之信,於自己近來弊病,頗能自知,正好用功自醫。而猶曰終日泄泄,此則我所不解者也。
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媧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輩則宜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至於宗族姻黨,無論他與我有隙無隙,在弟輩只宜一要概愛之敬之。孔子曰:“汛愛衆,而親仁。”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將來當家立業,豈不個個都是仇人,古來無與宗族、鄉黨爲仇之聖賢,弟輩萬不可專責他人也。
十一月信言:觀看《莊子》並《史記》,甚善!但作事必須有恆,不可謂考試在即便將之書丟下,必須從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將《史記》看完,則以後看書不可限量,不必問進學與否也。賢弟論袁詩,論作字,亦皆有所見;然空言無益,須多做詩,多臨帖乃可談耳。譬如人慾進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進京程途,亦向益哉?即言之津津,人誰得而信之哉?
九弟之信,所以規勸我者甚切,餘覽之,不覺毛骨悚然!然我用功,實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着如此做去,不作外官,將來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諸弟與兒侄。而省城之聞望日隆,即我亦不知其所自來。我在京師惟恐名浮於實,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詡一言,深以過情之聞爲恥耳。
來書寫大場題及榜信,此間九月早已知之,惟縣考案首前列及進學之人,則至今不知。諸弟以後寫信,於此等小事,及近處戚族家光景,務必一一詳載。
季弟信亦謙虛可愛,然徒謙亦不好,總要努力前進,此全在爲兄者倡率之,餘他無所取,惟近來日日不恆,可爲諸弟倡率。四弟六弟,總不欲以有恆自立,獨不泊壞季弟之樣子乎?餘不盡宣,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