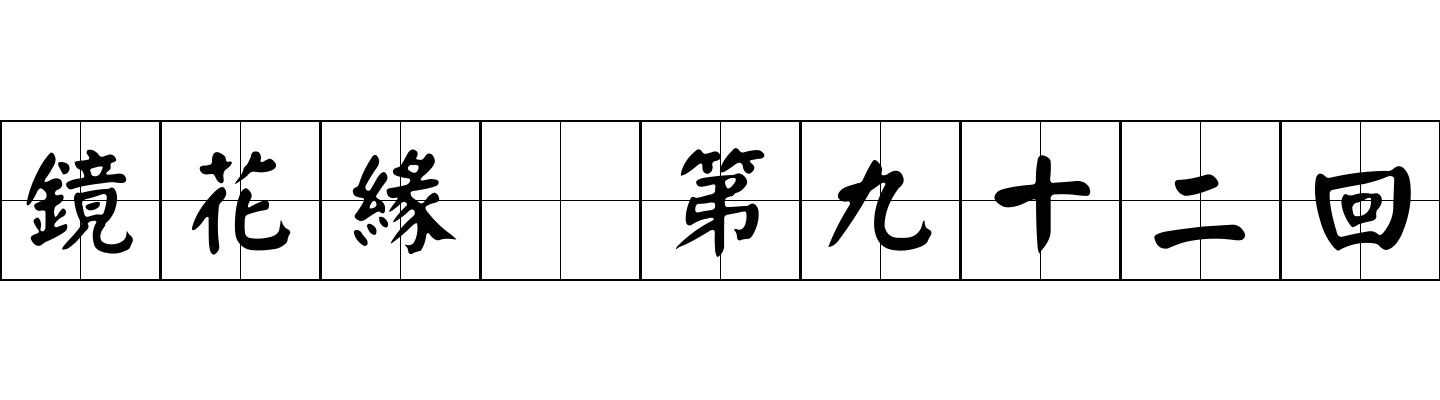鏡花緣-第九十二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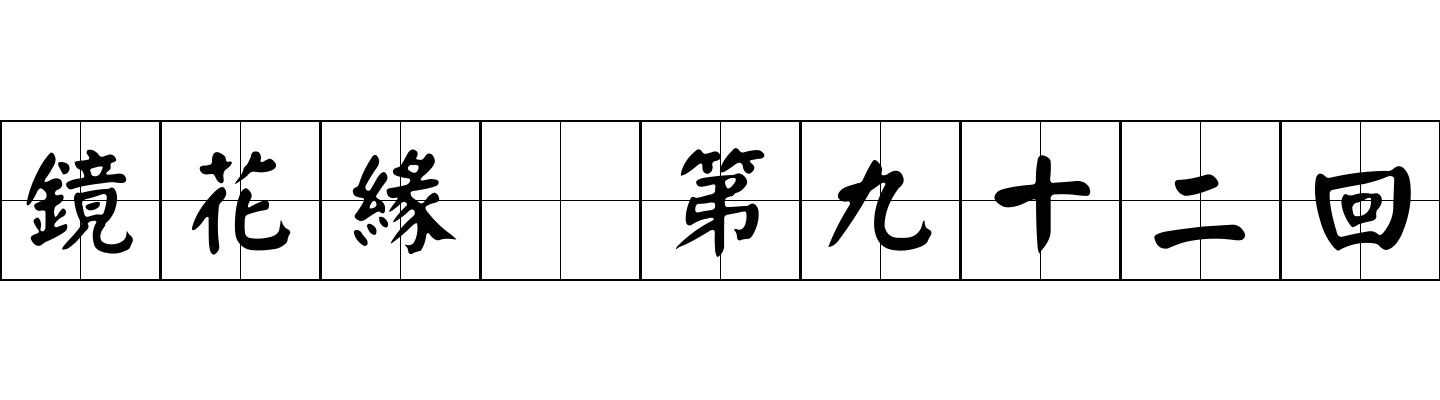
《鏡花緣》是清代文人李汝珍創作的長篇小說。小說前半部分描寫了唐敖、多九公等人乘船在海外遊歷的故事,包括他們在女兒國、君子國、無腸國等國的經歷史。後半部寫了武則天科舉選才女,由百花仙子託生的唐小山及其他各花仙子託生的一百位才女考中,並在朝中有所作爲的故事。其神幻詼諧的創作手法數經據典,奇妙地勾畫出一幅絢麗斑斕的天輪彩圖。
論果贏佳人施慧性 辯壺盧婢子具靈心
話說亭亭點頭道:“還是‘五行’哩。”紫芝道:“不必說,我喫一杯。”
春輝道:“我也曉得了,上面還有‘卯金刀’哩。”衆人不憧。春輝道:“《漢書·五行志》曾有‘爲蟲臭惡’之句,卻是班固引劉向的話,所以他說“五行’篇,我說‘卯金刀’了。”
衆人道:“請教臭蟲主人可能也說一個?”紫芝道:“你們可曉得本朝有個喜喫臭蟲的?”衆人道:“又說本朝了,罰一杯。”紫芝道:“我說晉朝郭璞,可使得?他注《爾雅》,曾言‘負盤臭蟲’,難道你們還不該喫……”略停一停,又接著道:“一杯麼?”春輝道:“你把一句話分做兩截說,這個意思,也教我們喫臭蟲了。”紫芝道:“話雖如此,但喜臭蟲之人,乃喫的是負盤,其形似蜂;
若認做咬人的臭蟲,那就錯了。”春輝道:“喫到這些臭東西,還要替他考正,你也忒愛引經據典了。”紫芝道:“若不替他辯明,將來都要亂喫,姐姐還當得住麼?”春輝道:“他喫臭蟲,爲何我當不住?看這光景,我又變做臭蟲了。你可曉得我這臭蟲是愛咬人的?”說著,走了過來。紫芝道:“好姐姐!莫咬!算我說錯,罰一杯。”蘭言道:“二位姐姐莫鬧臭蟲了,天已不早,快接令罷。”
瓊英掣了宮室雙聲道:
“承塵幹寶《搜神記》飛上承塵。
本題雙聲,敬芷馨姐姐一杯。”蘭言聽了,望了一望,不住搖頭。竇耕煙暗暗問道:“姐姐爲何搖頭?”蘭言道:“此書原是‘鳩來爲我禍也飛上承塵’一連十個字,纔是一句。今瓊英姐姐因上半句話語不好,只飛下半句。我細細把他一看,那知此句竟是他的讖語,也是一位不得其死的。”耕煙道:“待我問他一聲。”
因叫道:“姐姐要飛‘塵’字,書中甚多,即如劉峻《辨命論》、班彪《北征賦》,以及《晉紀·總論》、屈原《漁父》之類,都可用得,必定要用《搜神記》,這是何意?”瓊英道:“妹子原想用《何水部集》‘尋玉塵於萬里,守金龜於千年’。
誰知不因不由,忽把此句飛了出來。”
姚芷馨掣了財寶雙聲道:
“真珠陸賈《新語》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
‘玉於’雙聲,敬秀英姐姐一杯。”
閨臣道:“適因此珠,偶然想起昨託寶雲姐姐請問師母之話,可曾問過?”
寶雲道:“昨日姐姐去後,妹子細問家母,據說姐姐之珠,乃無價之寶,務須好好收藏。家父真珠雖多,類如此等的,也只得兩顆。但各珠名號不同,其類有龍、蛟、蛇、魚、鱉、蚌之分,龍珠在額,蛟珠在皮,蛇珠在口,魚珠在目,鱉珠在足,蚌珠在腹,姐姐之珠,乃大蚌所產,名‘合浦珠’。”廉錦楓道:“師母這雙慧眼,真是神乎其神。此珠果是大蚌腹中之物。”寶雲道:“姐姐何以曉得?”
閨臣就把錦楓取參殺蚌各話說了,衆人聽了,莫不讚嘆錦楓之孝。春輝道:“剛纔我們說王休徵臥冰求魚,已是奇孝,誰知錦楓姐姐入海取參,竟將性命置之度外,如此奇孝,曾席也該立飲一杯,大家也好略略學個樣子。”衆人飲畢。
秀英掣了列女雙聲,想了多時,忽然垂下淚來道:“此時我們只顧在此飲酒。
只怕家中都是:
朝姝《戰國策》汝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
玉芝道:“‘汝暮去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閨臣同錦楓、亭亭聽了,都淚落如雨。座中凡有老親而在異鄉的,聽了此句,又見秀英、閨臣這個樣子,登時無不墮淚。蘭芝道:“姐姐:這是何苦!甚麼飛不得,單要飛這兩句?究竟那位接令?真鬧糊塗了。”司徒嫵兒道:“他在那裏傷心,我替盟姐說罷:‘而晚’、‘而望’俱雙聲,敬嫵兒妹妹一杯。此係時音,不敢替主人轉敬。”題花道:“時音還是其次;至《戰國策》正令雖未飛過,寶塔詞卻用的不少,只怕要罰一杯。”
秀英道:“我用玫乘《七發》‘麥秀囗[上氵下斬]兮雉朝飛’。”紫芝道:“姐姐何不用《齊書》‘蝨有諺言,朝生暮孫’;或用徐幹《中論》‘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普席豈不都有酒麼?”蘭言道:“秀英姐姐不必另飛,省得接令換人又要爭論,好在《戰國策》與正令還不重複,也可用得。”
司徒嫵兒掣了蟲名疊韻道:
“蒲盧《爾雅》果蠃蒲盧。
‘果蠃’,本題俱疊韻,敬玉蟾姐姐一杯。”春輝道:“《詩經》是‘螟嶺有子,蜾蠃負之’;《爾雅》又是‘果蠃蒲盧’。一物而兼三名,原不爲奇,最難得都是疊韻。古人命名之巧,無出其右,這可算得千古絕唱了。”題花道:“此中還有幾個奇的:若把‘蠃’之當中‘蟲’字換個‘鳥’字,《博雅》謂之‘果鸁桑飛’,卻又變成鳥名;再把‘鳥’字換做‘果’字,《詩經》謂之‘果臝之實’,忽又變成瓜名。三個都是同音。這個不但命名甚巧,並且造字也巧。”玉兒道:
“祝才女把‘蟲’字讀做‘蟲’音,不知有何出處?只怕錯了。”題花道:“我願知‘蟲’是古‘虺’字,應當讀‘毀’,只因一時匆忙說錯,罰一杯。你這玉老先生,我實在怕了!”
蘭言道:“玉兒,你既這樣聰明,我再考你一考:請教店鋪之‘鋪’,應做何寫?”玉兒道:“應寫金旁之‘鋪’。”蘭言道:“帳目之‘帳’呢?”玉兒道:“此字才女只好考那鄉村未曾讀書之人。我記得古人字書於帳字之下都注‘計簿’二字,誰知後人妄作聰明,忽然改作貝旁,其實並無出處。這是鄉村俗子所寫之字,今才女忽然考我,未免把我玉兒看的過於不知文了。”蘭言道:“玉老先生莫動氣,是我唐突,罰一杯!”
玉蟾掣了花卉疊韻道:“我們連日在老師府上,妹子有個比語,說來求教:
芄蘭《家語》人善人之室,加入芝蘭之室。
‘加入’雙聲,敬香雲姐姐一環。”蘭言道:“此句飛的乃‘言道其實’,萬不可少,恰恰飛到香雲姐姐,尤其湊巧。明日老師看見這個單子,見了此句,必說我們這些門生雖然年輕,還是識得好歹的。”小春道:“獨贊寶雲姐姐,豈不把今日的主人落空麼?”春輝道:“何嘗落空!你把飛的‘芝蘭’二字翻個筋斗,豈不是今日的主人麼。”衆人聽了,不覺大笑,都道:“這句飛的原巧,也難得春輝姐姐這副錦心,這張繡口。”
香雲掣了蟲名疊韻道:
“螳螂《吳越春秋》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
本題疊韻,敬再芳姐姐一杯。”蘭言道:“每見世人惟利是趨,至於害在眼前,那裏還去管他。所以俗語說的:‘人見利而不見害,魚見食而不見鉤。’就如黃雀一心要捕螳螂,那知還來到口,而自己卻命喪王孫公子之手,豈非爲螳螂所害?
古人因貪利之輩不顧禍患,故設此語以爲警戒;無如世人雖知其語之妙,及至利到跟前,就把‘害’字忘了。所謂‘利令志昏’,能不浩嘆!”
青鈿道:“再芳姐姐接令了。”花再芳因紫芝臭蟲之令又多飲幾杯,正在打盹,忽聽此言,連忙接過籤桶,掣了一枝,高聲念道:“身體雙聲。”衆人聽了,想起蘭蓀的腳筋,由不得又要發笑;因再芳性情不好,大家也不敢多言。紫芝卻暗暗寫了一個紙條拿在手裏。只見再芳在那裏一面搖著身子尋思,一面拿著牙杖剔牙。紫芝趁勢過去道:“姐姐只怕也是肉圓子塞在牙縫裏,我替你剔出來。”
再芳仰首張口。紫芝朝裏望一望道:“這個好剔,只有豆大,是個紅的。”接過牙籤,放入口內,朝外一剔,看了一看,撂在地下道:“我說爲何通紅,原來是個臭蟲。”再芳道:“左邊也塞的狠,你也替我剔出來。”紫芝又剔出,朝地下一丟道:“我只當是些脂麻,原來是幾張蝨子皮。”就勢把紙條遞過,隨即歸位。
再芳看了,樂不可支,慌忙說道:
“禿頭《穀梁傳》季孫行父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
重字雙聲,敬瓊芳姐姐一杯。”引的衆人由不得好笑。春輝道:“這都是紫芝妹妹造的孽。我同你賭個東道:除前書之外,如再飛個禿字,或雙聲,或疊韻,我喫一杯。並且聽飛之句仍要歸到形體,至於蘇武禿節效貞,孔融禿巾微行之類,那都不算。”紫芝想一想道:“有了:《東觀漢記》:‘竇後少小頭禿,不爲家人所齒。’這是本題雙聲。又《許氏說文》:‘倉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這是‘因以’雙聲。還有《風俗通》:‘五月忌翻蓋屋瓦,令人發禿。’這是‘屋瓦’雙聲。別的雖有,大家用過之書我都忘了,必須查查單子去。”春輝道:“查出不算。”紫芝道:“既如此,就喫三杯饒你罷!”春輝道:“我記得他們議論‘菽水’,《風俗通》倒象有人用過。”紫芝道:“呸!我也喫一杯。”
青鈿道:“剛纔玉兒替紫芝姐姐掣的實系天文,我因題目過寬,所以改個蟲名,那知還是教他灌了好幾杯。”紫芝道:“並且亭亭姐姐說的那句《漢書》,還多謝你們把笑話也免了。”春輝道:“這個虧喫的不小。怎麼九十多人都被他鬧臭蟲攪糊塗了?少刻這笑話一定要補的。”
葉瓊芳掣了獸名雙聲道:
“騊駼《司馬文園集》軼野馬,騊駼。
‘野馬’疊韻,本題雙聲,敬銀蟾姐姐一杯。”題花道:“這兩句竟是套車要走了。”衆丫環道:“車都套齊,久已伺候了。”玉芝道:“祝才女說的是書,何嘗問你們套車。看這光景,你們倒想家了。”史幽探道:“正是。天已不早,此令不知還有幾人。”玉兒道:“還有八位才女。”衆人齊催拿飯。蘭芝只說:“天時尚早,儘可從容。”
宰銀蟾掣了蔬菜疊韻道:
“壺盧劉義慶《世說》東吳有長柄葫蘆,卿得種來否?
本題雙聲,敬蘭芳姐姐一杯。”蘭言道:“玉兒,我考你一考:此句怎講?”玉兒道:“這是當日陸士衡弟兄初見劉道真,以爲道真不知問些甚麼大學問的話,誰知他只問壺盧種可曾帶來。”紫芝道:“我也學劉道真了,請問婉春姐姐:你們會稽山的老虎最多,你來時可曾把虎鬚帶來?”婉春道:“姐姐要他何用?”
紫芝道:“我要兩根送蘭蓀、再芳二位姐姐做剔牙杖。”蘭言道:“玉兒:你把單子拿來我看。”玉兒送過,蘭言看了道:“這‘壺盧’二字,爲何寫做兩樣?
究竟用那個爲是?”玉兒道:“歷來寫草頭雖多,但據我的意思:壺是飲器,盧的飯器,北邊此物極大,大都做爲器用,古人命名,必是因此。《詩》有‘八月斷壺’之句,並非草頭。至於草頭二字,葫是大蒜,蘆是蒲葦,會義指事,迥然不同,不如無草頭最切。當日崔豹雖未言其所以,卻已用過。”蘭言道:“玉老先生請罷!將來我們再寫這兩上字,斷不‘依樣葫蘆’一定要改‘新樣壺盧’的。”
蔡蘭芳掣了地理雙聲,忖一忖道:“妹子雖想了兩句,但一有普席之酒,一無普席之酒,若取吉利,卻無普席之酒。”蘭言道:“且把吉利的交了卷再講。”
蘭芳道:
“黃河王嘉《拾遺記》黃河千年一清,聖人之大瑞也。
本題雙聲,‘千年’疊韻,敬錦心姐姐一杯。”蘭言道:“普席之酒卻是何句?”
青鈿道:“我猜著了:莫非虞荔《鼎録》‘寇盜平,黃河清’麼?”蘭芳道:“並非《鼎録》。是《呂氏春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蘭言道:“這句卻有‘呂梁’、‘孟門’兩個雙聲,既如此,我們普席各位半杯。”
言錦心掣了花卉雙聲道:“妹子並無好句,不過搪塞完卷。至於以上所飛之句,處處入妙,卻有一比:
荷花李延壽《南史》此步步生蓮花也。
重字雙聲,敬閨臣姐姐一杯。”青鈿道:“且慢斟酒!這部《南史》,正令雖未用過,我記得剛纔紅英、堯春二位姐姐以琴棋二字打賭,曾用李延壽《南史》;
並且紅英姐姐曾借‘李’字說過元元皇帝一個笑話。姐姐誤用重書,只怕要罰一杯。”井堯春道:“春鈿姐姐記錯了!我用的是李延壽的《北史》,並非《南史》。”
青鈿只得飲了一環道:“我今日鬧的糊里糊塗多吃了許多酒,總是‘湖州老兒’把我氣的。”
閨臣掣了時令雙聲道:“蘭芝姐姐:天已黃昏,所謂‘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請賜飯罷。妹子就用‘黃昏’三字交卷,以記是日歡聚幾至以日繼夜之意。”青鈿道:“‘黃昏’二字,雖是對景掛畫,就只可惜是個俗語。”閨臣道:“‘日至虞淵,是謂黃昏。’見《淮南鴻烈》,豈是俗語。”春輝道:“他才把酒乾了,倒又想喫,真是好量。”
忽聞遠遠的一片音樂之聲,只見丫環向寶雲道:“各燈都在小鰲山樓上樓下分兩層掛了,請小姐先去看看,如有不妥,趁此好改。夫人恐衆才女過去看燈,未備花炮,覺得冷淡,現命府中女清音在彼伺候。”衆人道:“即已掛齊,我們就同去走走,少刻再來接令。”一齊出席,離了凝翠館。
寶雲道:“蘭芬姐姐如把這些燈球算的不錯,我才服哩。”蘭芬聽了,甚覺不懂,只得含糊應道:“妹子只能算算天文、地理、勾股之類,何能會算燈球。”
董花鈿道:“我們今年正月在小鰲山看燈,那知轉眼又交夏令了。”只聞音樂之聲漸漸相近,不多時,來到小鰲山,原來三面串連大樓二十七間,只南面一帶是低廊,樓上樓下俱掛燈球,各種花樣,五色鮮明,高低疏密,位置甚佳。蘭芬道:
“怪不得姐姐說這燈球難算哩。”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