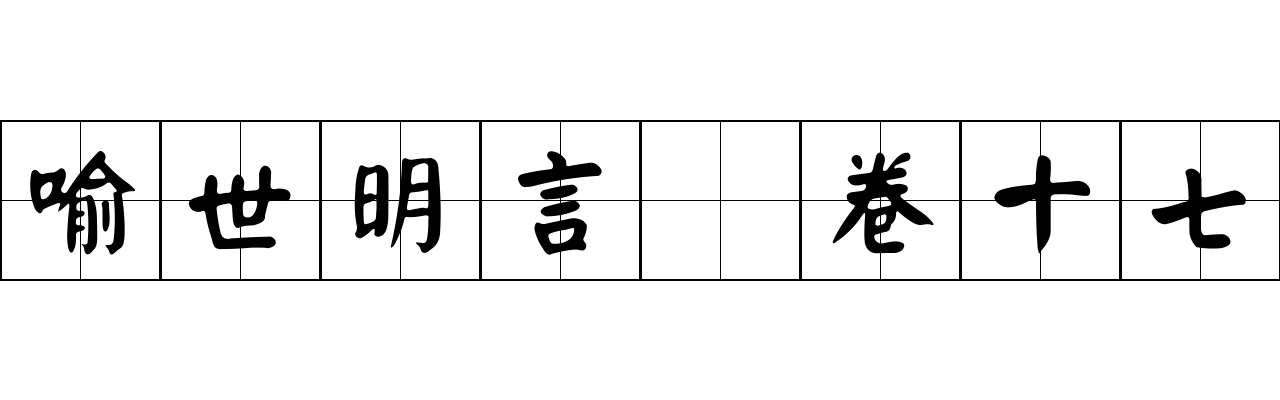喻世明言-卷十七-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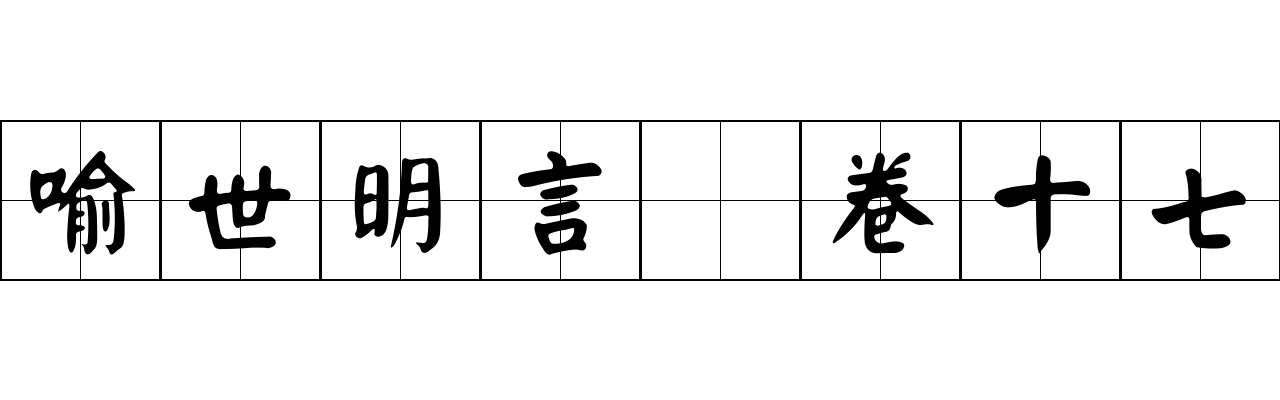
《喻世明言》是明末馮夢龍纂輯的白話短篇小說集。《喻世明言》最初版本名爲《古今小說》,全稱《全像古今小說》。後重印改名爲《喻世明言》,以與“三言”其他作品書名相配。全書40卷,每卷1篇,共計40篇。它和《通言》《恆言》一樣,爲宋元明話本小說。《喻世明言》中故事產生的時代,包括宋、元、明三代,其中多數爲宋元舊作話本,另外有些是明人對宋元舊作的改編加工,還收錄和改編了一些歷史傳奇故事。此外,《喻世明言》各篇小說多取材於現實生活,主題涵蓋愛情、婚姻、朋友情義等,展現了當其時的社會百態。
單符郎全州佳偶
郟鄏門開城倚天,周公拮構尚依然。 休言道德無關鎖,一閉乾坤八百年。
這首詩,單說西京是帝王之都,左成皋,右澠池,前伊闕,後大河;真個形勢無雙,繁華第一;宋朝九代建都於此。今日說一樁故事,乃是西京人氏,一個是邢知縣,一個是單推官。他兩個都在孝感坊下,並門而居。兩家宅眷,又是嫡親姊妹,姨丈相稱。所以往來甚密,雖爲各姓,無異一家。先前,兩家未做官時節,姊妹同時懷孕,私下相約道:“若生下一男一女,當爲婚姻。”後來單家生男,小名符郎;邢家生女,小名春娘。姊妹各對丈夫說通了,從此親家往來,非止一日。符郎和春娘幼時常在一處遊戲,兩家都稱他爲小夫婦。以後漸漸長成,符郎改名飛英,字騰實,進館讀書;春娘深居繡閣,各不相見。
其時宋徽宗宣和七年,春三月,邢公選了鄧州順陽縣知縣,單公選了揚州府推官,各要挈家上任。相約任滿之日,歸家成親。單推官帶了夫人和兒子符郎,自往揚州去做官,不題。卻說邢知縣到了鄧州順陽縣,未及半載,值金韃子分道入寇。金將斡離不攻破了順陽,邢知縣一門遇害。春娘年十二歲,爲亂兵所掠,轉賣在全州樂戶楊家,得錢十七千而去。春娘從小讀過經書及唐詩千首,頗通文墨,尤善應對。鴇母愛之如寶,改名楊玉,教以樂器及歌舞,無不精絕。正是:
三千粉黛輸顏色,十二朱樓讓舞歌。
只是一件,他終是宦家出身,舉止端詳。每詣公庭侍宴,呈藝畢,諸妓調笑謔浪,無所不至;楊玉嘿然獨立,不妄言笑,有良人風度。爲這個上,前後官府,莫不愛之重之。
話分兩頭。卻說單推官在任三年,時金虜陷了汴京,徽宗、欽宗兩朝天子,都被他擄去。虧殺呂好問說下了僞帝張邦昌,迎康王嗣統。康王渡江而南,即位於應天府,是爲高宗。高宗懼怕金虜,不敢還西京,乃駕幸揚州。單推官率民兵護駕有功,累遷郎官之職,又隨駕至杭州。高宗愛杭州風景,駐蹕建都,改爲臨安府。有詩爲證:
山外青山樓外摟,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卻把杭州作汴州。
話說西北一路地方,被金虜殘害,百姓從高宗南渡者,不計其數,皆散處吳下。聞臨安建都,多有搬到杭州入籍安插。單公時在戶部,閱看戶籍冊子,見有一“邢祥”名字,乃西京人。自思:“邢知縣名禎,此人名祥,敢是同行兄弟?”從遊宦以後,邢家全無音耗相通,正在懸念。乃遣人密訪之,果邢知縣之弟,號爲“四承務”者。急忙請來相見,問其消息。四承務答道:“自鄧州破後,傳聞家兄舉家受禍,未知的否。”因流淚不止。單公亦愀然不樂。念兒子年齒已長,意欲別圖親事;猶恐傳言未的,媳婦尚在,且待干戈寧息,再行探聽。從此單公與四承務仍認做親戚,往來不絕。
再說高宗皇帝初即位,改元建炎。過了四年,又改元紹興。此時紹興元年,朝廷追敘南渡之功,單飛英受父蔭,得授全州司戶。謝恩過了,擇日拜別父母起程,往全州到任。時年十八歲,一州官屬,只有單司戶年少,且是儀容俊秀,見者無不稱羨。上任之日,州守設公堂酒會飲,大集聲妓。原來宋朝有這個規矩:凡在籍娼戶,謂之官妓,官府有公私筵宴,聽憑點名喚來祗應。這一日,楊玉也在數內。單司戶於衆妓中,只看得他上眼,大有眷愛之意。詩曰:
曾綰紅繩到處隨,佳人才子兩相宜。 風流的是張京兆,何日臨窗試畫眉?
司理姓鄭,名安,滎陽舊族,也是個少年才子。一見單司戶,便意氣相投,看他顧盼楊玉,已知其意。一日,鄭司理去拜單司戶,問道:“足下清年名族,爲何單車赴仕,不攜宅眷?”單司戶答道:“實不相瞞,幼時曾定下妻室,因遭虜亂,存亡未卜,至今中饋尚虛。”司理笑道:“離索之感,人孰無之?此間歌妓楊玉,頗饒雅緻,且作望梅止渴,何如?”司戶初時遜謝不敢,被司理言之再三,說到相知的分際,司戶隱瞞不得,只得吐露心腹。司理道:“既才子有意佳人,僕當爲曲成之耳。”自此每遇宴會,司戶見了楊玉,反覺有些避嫌,不敢注目;然心中思慕愈甚。司理有心要玉成其事,但懼怕太守嚴毅,做不得手腳。
如此二年。舊太守任滿升去。新太守姓陳,爲人忠厚至誠,且與鄭司理是同鄉故舊。所以鄭司理屢次在太守面前,稱薦單司戶之才品,太守十分敬重。一日,鄭司理置酒,專請單司戶到私衙清話,只點楊玉一名祗候。這一日,比公堂筵宴不同,只有賓主二人,單司戶才得飽看楊玉,果然美麗!有詞名《憶秦娥》,詞雲:
香馥馥,樽前有個人如玉。人如玉,翠翹金鳳,內家妝束。嬌羞慣把眉兒蹙,逢客人只唱傷心曲。傷心曲,一聲聲是怨紅愁綠。
鄭司理開言道:“今日之會,並無他客,勿拘禮法,當開懷暢飲,務取盡歡。”遂斟巨觥來勸單司戶,楊玉清歌侑酒。酒至半酣,單司戶看著楊玉,神魂飄蕩,不能自持,假裝醉態不飲。鄭司理已知其意,便道:“且請到書齋散步,再容奉勸。”那書齋是司理自家看書的所在,擺設著書、畫、琴、棋,也有些古玩之類。單司戶那有心情去看,向竹榻上倒身便睡。鄭司理道:“既然仁兄困酒,暫請安息片時。”忙轉身而出,卻教楊玉斟下香茶一甌送去。單司戶素知司理有玉成之美,今番見楊玉獨自一個送茶,情知是放鬆了,忙起身把門掩上,雙手抱住楊玉求歡。楊玉佯推不允,單司戶道:“相慕小娘子,已非一日,難得今番機會。司理公平昔見愛,就使知覺,必不嗔怪。”楊玉也識破三分關竅,不敢固卻,只得順情。兩個遂在榻上,草草的雲雨一場。有詩爲證:
相慕相憐二載餘,今朝且喜兩情舒。 雖然未得通宵樂,猶勝陽臺夢是虛。
單司戶私問楊玉道:“你雖然才藝出色,偏覺雅緻,不似青樓習氣,必是一個名公苗裔。今日休要瞞我,可從實說與我知道,果是何人?”楊玉滿面羞慚,答道:“實不相瞞,妾本宦族,流落在此,非楊嫗所生也。”司戶大驚,問道:“既系宦族,汝父何官何姓?”楊玉不覺雙淚交流,答道:“妾本姓邢,在東京孝感坊居住,幼年曾許與母姨之子結婚。妾之父授鄧州順陽縣知縣,不幸胡寇猖獗,父母皆遭兵刃,妾被人掠賣至此。”司戶又問道:“汝夫家姓甚?作何官職?所許嫁之子,又是何名?”楊玉道:“夫家姓單,那時爲揚州推官。其子小名符郎,今亦不知存亡如何。”說罷,哭泣不止。司戶心中已知其爲春娘了,且不說破,只安慰道:“汝今日鮮衣美食,花朝月夕,勾你受用。官府都另眼看覷,誰人輕賤你?況宗族遠離,夫家存亡未卜,隨緣快活,亦足了一生矣。何乃自生悲泣耶?”楊玉蹙頞答道:“妾聞‘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雖不幸風塵,實出無奈。夫家宦族,即使無恙,妾亦不作團圓之望。若得嫁一小民,荊釵布裙,啜菽飲水,亦是良人家媳婦。比在此中迎新送舊,勝卻千萬倍矣。”司戶點頭道:“你所見亦是。果有此心,我當與汝作主。”楊玉叩頭道:“恩官若能拔妾於苦海之中,真乃萬代陰德也。”
說未畢,只見司理推門進來道:“陽臺夢醒也未?如今無事,可飲酒矣。”司戶道:“酒已過醉,不能復飲。”司理道:“一分酒醉,十分心醉。”司戶道:“一分醉酒,十分醉德。”大家都笑起來。重來筵上,洗盞更酌,是日盡歡而散。
過了數日,單司戶置酒,專請鄭司理答席,也喚楊玉一名答應。楊玉先到,單司戶不復與狎呢,遂正色問曰:“汝前日有言,爲小民婦亦所甘心;我今喪偶,未有正室,汝肯相隨我乎?”楊玉含淚答道:“枳棘豈堪鳳凰所棲,若恩官可憐,得蒙收錄,使得備巾櫛之列,豐衣足食,不用送往迎來,固妾所願也。但恐他日新孺人性嚴,不能相容。然妾自當含忍,萬一徵色發聲,妾情願持齋佞佛,終身獨宿,以報恩官之德耳。”司戶聞言,不覺傪然,方知其厭惡風塵,出於至誠,非誑語也。
少停,鄭司理到來,見楊玉淚痕未乾,戲道:“古人云‘樂極生悲’,信有之乎?”楊玉斂容答道:“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耳!”單司戶將楊玉立志從良說話,向鄭司理說了。鄭司理道:“足下若有此心,下官亦願效一臂。”這一日,飲酒無話。
席散後,單司戶在燈下修成家書一封,書中備言岳丈邢知縣全家受禍,春娘流落爲娼,厭惡風塵,志向可憫。男情願復聯舊約,不以良賤爲嫌。單公拆書親看,大驚,隨即請邢四承務到來,商議此事,兩家各傷感不已。四承務要親往全州主張親事,教單公致書於太守,求爲春娘脫籍。單公寫書,付與四承務收訖,四承務作別而行。不一日,來到全州,逕入司戶衙中相見,道其來歷。單司戶先與鄭司理說知其事,司理一力攛掇,道:“諺雲:‘貴易交,富易妻。’今足下甘娶風塵之女,不以存亡易心,雖古人高義,不是過也。”遂同司戶到太守處,將情節告訴。單司戶把父親書札呈上,太守看了,道:“此美事也,敢不奉命?”次日,四承務具狀告府,求爲釋賤歸良,以續舊婚事,太守當面批准了。
候至日中,還不見發下文牒。單司戶疑有他變,密使人打探消息。見廚司正在忙亂,安排筵席。司戶猜道:“此酒爲何而設?豈欲與楊玉舉離別觴耶?事已至此,只索聽之。”少頃,果召楊玉祗候,席間只請通判一人。酒至三巡,食供兩套,太守喚楊玉近前,將司戶願續舊婚,及邢祥所告脫籍之事,一一說了。楊玉拜謝道:“妾一身生死榮辱,全賴恩官提拔。”太守道:“汝今日尚在樂籍,明日即爲縣君,將何以報我之德?”楊玉答道:“恩官拔人於火宅之中,陰德如山,妾惟有日夕籲天,願恩官子孫富貴而已。”太守嘆道:“麗色佳音,不可復得。”不覺前起抱持楊玉,說道:“汝必有以報我。”那通判是個正直之人,見太守發狂,便離席起立,正色發作道:“既司戶有宿約,便是孺人,我等俱有同僚叔嫂之誼。君子進退當以禮,不可苟且,以傷雅道。”太守踧踖,謝道:“老夫不能忘情,非判府之言,不知其爲過也。今得罪於司戶,當謝過以質耳。”乃令楊玉入內宅,與自己女眷相見。卻教人召司理、司戶二人,到後堂同席,直喫到天明方散。
太守也不進衙,逕坐早堂,便下文書與楊家翁、媼,教除去楊玉名字。楊翁、楊媼出其不意,號哭而來,拜著太守,訴道:“養女十餘年,費盡心力。今既蒙明判,不敢抗拒。但願一見而別,亦所甘心。”太守遣人傳語楊玉。楊玉立在後堂,隔屏對翁、嫗說道:“我夫妻重會,也是好事。我雖承汝十年撫養之恩,然所得金帛已多,亦足爲汝養老之計。從此永訣,休得相念。”嫗兀自號哭不止。太守喝退了楊翁、楊嫗。當時差州司人從,自宅堂中擡出楊玉,逕送至司戶衙中;取出私財十萬錢,權佐資奩之費。司戶再三推辭,太守定教受了。是日,鄭司理爲媒,四承務爲主婚,如法成親,做起洞房花燭。有詩爲證:
風流司戶心如渴,文雅嬌娘意似狂。 今夜官衙尋舊約,不教人話負心郎。
次日,太守同一府官員都來慶賀,司戶置酒相待。四承務自歸臨安,回覆單公去訖。司戶夫妻相愛,自不必說。
光陰似箭,不覺三年任滿。春娘對司戶說道:“妾失身風塵,亦荷翁嫗愛育;其他姊妹中相處,也有情分契厚的。今將遠去,終身不復相見。欲具少酒食,與之話別,不識官人肯容否?”司戶道:“汝之事,合州莫不聞之,何可隱諱?便治酒話別,何礙大體?”春娘乃設筵於會勝寺中,教人請楊翁、楊嫗,及舊時同行姊妹相厚者十餘人,都來會飲。至期,司戶先差人在會勝寺等候衆人到齊,方纔來稟。楊翁、楊嫗先到,以後衆妓陸續而來。從人點客已齊,方敢稟知司戶,請孺人登輿。僕從如雲,前呼後擁,到會勝寺中,與衆人相見。略敘寒喧,便上了筵席。飲至數巡,春娘自出席送酒。內中一妓,姓李名英,原與楊嫗家連居,其音樂技藝,皆是春娘教導,常呼春娘爲姊,情似同胞,極相敬愛。自從春娘脫籍,李英好生思想,常有鬰鬰之意。是日,春娘送酒到他面前,李英忽然執春娘之手,說道:“姊今超脫污泥之中,高翔青雲之上,似妹於沉淪糞土,無有出期,相去不啻天堂、地獄之隔,姊今何以救我?”說罷,遂放聲大哭。春娘不勝悽慘,流淚不止。原來李英有一件出色的本事:第一手好針線,能於暗中縫紉,分際不差。正是:
織發夫人昔擅奇,神針娘子古來稀。誰人乞得天孫巧?十二樓中一李姬。
春娘道:“我司戶正少一針線人,吾妹肯來與我作伴否?”李英道:“若得阿姊爲我方便,得脫此門路,是一段大陰德事。若司戶左右要覓針線人,得我爲之,素知阿姊心性,強似尋生分人也。”春娘道:“雖然如此,但吾妹平日與我同行同輩,今日豈能居我之下乎?”李英道:“我在風塵中,每自退姊一步。況今日雲泥回隔,又有嫡庶之異,即使朝夕奉侍阿姊,比於侍婢,亦所甘心。況敢與阿姊比肩耶?”春娘道:“妹既有此心,奴當與司戶商之。”
當晚席散,春娘回衙,將李英之事對司戶說了。司戶笑道:“一之爲甚,豈可再乎!”春娘再三攛掇,司戶只是不允,春娘悶悶不悅。一連幾日,李英遣人以問安奶奶爲名,就催促那事。春娘對司戶說道:“李家妹情性溫雅,針線又是第一,內助得如此人,誠所罕有。且官人能終身不納姬侍則已,若納他人,不如納李家妹,與我少小相處,兩不見笑。官人何不向守公求之?萬一不從,不過𢬵一沒趣而已,妾亦有詞以回絕李氏。倘僥倖相從,豈非全美!”司戶被孺人強逼數次,不得已,先去與鄭司理說知了,捉了他同去見太守,委曲道其緣故。太守笑道:“君欲一箭射雙鵰乎?敬當奉命,以贖前此通判所責之罪。”當下太守再下文牒,與李英脫籍,送歸司戶。司戶將太守所贈十萬錢,一半給與李嫗,以爲贖身之費;一半給與楊嫗,以酬其養育之勞。自此春娘與李英姊妹相稱,極其和睦。當初單飛英隻身上任,今日一妻一妾,又都是才色雙全,意外良緣,歡喜無限。後人有詩云:
官舍孤居思黯然,今朝綵線喜雙牽。 符郎不念當時舊,邢氏徒懷再世緣。 空手忽擎雙塊玉,污泥挺出並頭蓮。 姻緣不論良和賤,婚牒書來五百年。
單司戶選吉起程,別了一府官僚,挈帶妻妾,還歸臨安宅院。單飛英率春娘拜見舅姑,彼此不覺傷感,痛哭了一場。哭罷,飛英又率李英拜見。單公問是何人,飛英述其來歷。單公大怒,說道:“吾至親骨肉,流落失所,理當收拾,此乃萬不得已之事。又旁及外人,是何道理?”飛英皇恐謝罪,單公怒氣不息。老夫人從中勸解,遂引去李英於自己房中,要將改嫁。李英那裏肯依允,只是苦苦哀求。老夫人見其至誠,且留作伴。過了數日,看見李氏小心婉順,又愛他一手針線,遂勸單公收留與兒子爲妾。
單飛英遷授令丞。上司官每聞飛英娶娼之事,皆以爲有義氣;互相傳說,無不加意欽敬,累薦至太常卿。春娘無子,李英生一子,春娘抱之,愛如己出。後讀書登第,遂爲臨安名族。至今青樓傳爲佳話。有詩爲證:
山盟海誓忽更遷,誰向青樓認舊緣? 仁義還收仁義報,宦途無梗子孫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