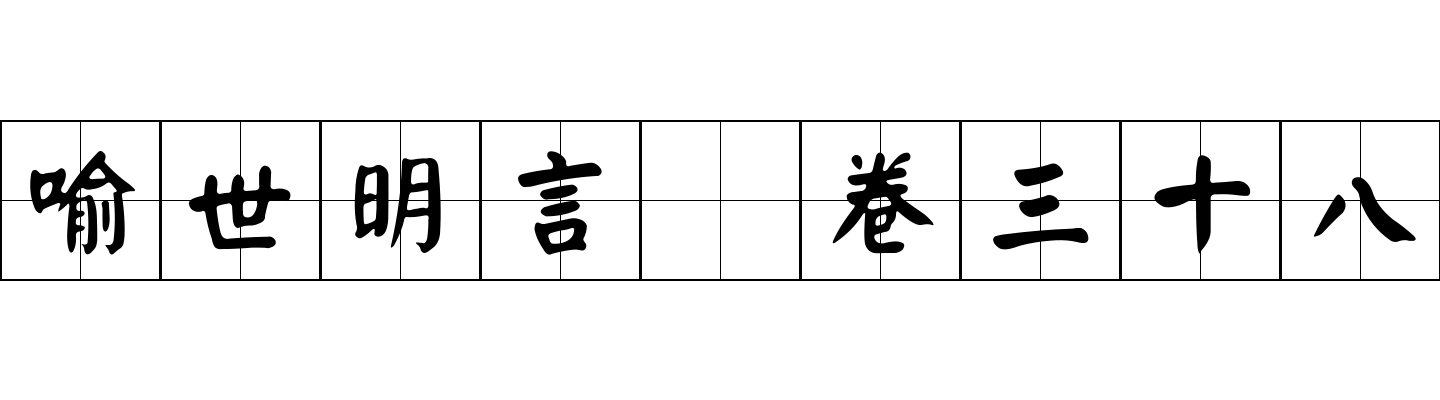喻世明言-卷三十八-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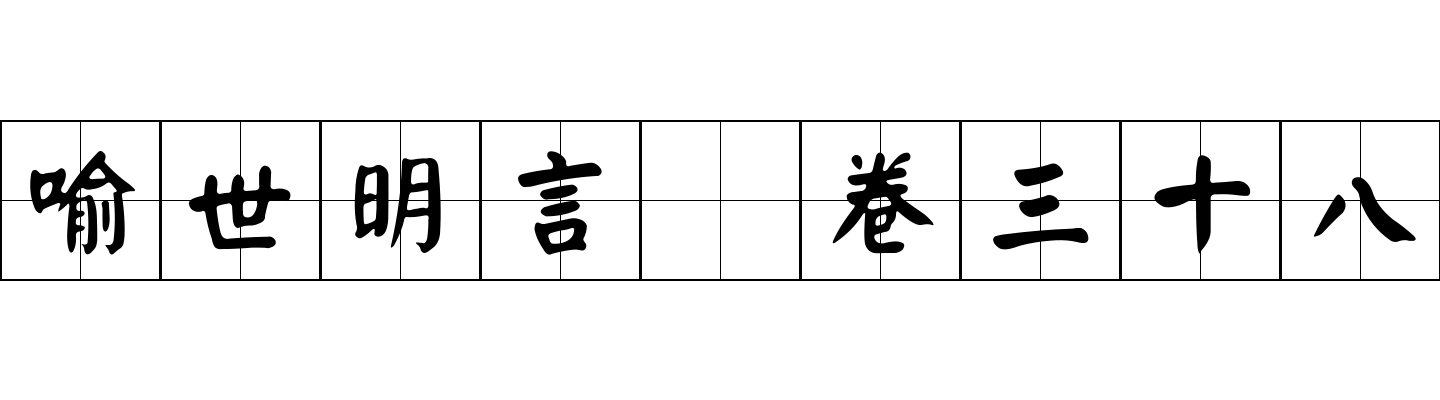
《喻世明言》是明末馮夢龍纂輯的白話短篇小說集。《喻世明言》最初版本名爲《古今小說》,全稱《全像古今小說》。後重印改名爲《喻世明言》,以與“三言”其他作品書名相配。全書40卷,每卷1篇,共計40篇。它和《通言》《恆言》一樣,爲宋元明話本小說。《喻世明言》中故事產生的時代,包括宋、元、明三代,其中多數爲宋元舊作話本,另外有些是明人對宋元舊作的改編加工,還收錄和改編了一些歷史傳奇故事。此外,《喻世明言》各篇小說多取材於現實生活,主題涵蓋愛情、婚姻、朋友情義等,展現了當其時的社會百態。
任孝子烈性爲神
參透風流二字禪,好姻緣作惡姻緣。 癡心做處人人愛,冷眼觀時個個嫌。 閒花野草且休拈,贏得身安心自然。 山妻本是家常飯,不害相思不費錢。
這首詞,單道著色慾乃忘身之本,爲人不可茍且。
話說南宋光宗朝紹熙元年,臨安府在城清河坊南首昇陽庫前有個張員外,家中鉅富,門首開個川廣生藥鋪。年紀有六旬,媽媽已故。止生一子,喚著張秀一郎,年二十歲,聰明標緻。每日不出大門,只務買賣。父母見子年幼,抑且買賣其門如市,打發不開。
鋪中有個主管,姓任名圭,年二十五歲。母親早喪,止有老父,雙目不明,端坐在家。任圭大孝,每日辭父出,到晚才歸參父,如此孝道。祖居在江干牛皮街上。是年冬間,憑媒說合,娶得一妻,年二十歲,生得大有顏色,系在城內日新橋河下做涼傘的梁公之女兒,小名叫做聖金。自從嫁與任圭,見他篤實本分,只是心中不樂,怨恨父母,千不嫁萬不嫁,把我嫁在江干,路又遠,早晚要歸家不便。終日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妝飾皆廢。這任圭又向早出晚歸,因此不滿婦人之意。
原來這婦人未嫁之時,先與對門周待詔之子名周得有奸。
此人生得丰姿俊雅,專在三街兩巷貪花戀酒,趨奉得婦人中意。年紀三十歲,不要娶妻,只愛偷婆娘。周得與梁姐姐暗約偷期,街坊鄰里那一個不曉得。因此梁公、梁婆又無兒子,沒奈何只得把女兒嫁在江干,省得人是非。這任圭是個樸實之人,不曾打聽仔細,胡亂娶了。不想這婦人身雖嫁了任圭,一心只想周得,兩人餘情不斷。
荏苒光陰,正是:
看見垂楊柳,回頭麥又黃。 蟬聲猶未斷,孤雁早成行。
忽一日,正值八月十八日潮生日。滿城的佳人才子,皆出城看潮。這周得同兩個弟兄,俱打扮出候潮門。只見車馬往來,人如聚蟻。周得在人叢中丟撇了兩個弟兄,潮也不看,一徑投到牛皮街那任圭家中來。原來任公每日只閉著大門,坐在樓檐下唸佛。周得將扇子柄敲門,任公只道兒子回家,一步步摸出來,把門開了。周得知道是任公,便叫聲:“老親家,小子施禮了。”任公聽著不是兒子聲音,便問:“足下何人?有何事到舍下?”周得道:“老親家,小子是梁涼傘姐姐之子。有我姑表妹嫁在宅上,因看潮特來相訪。令郎姐夫在家麼?”任公雙目雖不明,見說是媳婦的親,便邀他請坐。就望裏面叫一聲:“娘子,有你阿舅在此相訪。”
這婦人在樓上正納悶,聽得任公叫,連忙濃添脂粉,插戴釵環,穿幾件色服,三步那做兩步,走下樓來,布簾內瞧一瞧:“正是我的心肝情人,多時不曾相見!”走出布簾外,笑容可掬,向前相見。這周得一見婦人,正是:
分明久旱逢甘雨,賽過他鄉遇故知。 只想洞房歡會日,那知公府獻頭時?
兩個並肩坐下。這婦人見了周得,神魂飄蕩,不能禁止。遂攜周得手揭起布簾,口裏胡說道:“阿舅,上樓去說話。”這任公依舊坐在樓檐下板凳上唸佛。
這兩個上得樓來,就抱做一團。婦人罵道:“短命的!教我思量得你成玻因何一向不來看我?負心的賊!”周得笑道:“姐姐,我爲你嫁上江頭來,早晚不得見面,害了相思病,爭些兒不得見你。我如常要來,只怕你老公知道,因此不敢來望你。”一頭說,一頭摟抱上牀,解帶卸衣,敘舊日海誓山盟,雲情雨意。正是:
情興兩和諧,摟定香肩臉貼腮。手捻著香酥奶,綿軟實奇哉。退了褲兒脫繡鞋。
玉體靠郎懷,舌送丁香口便開。倒鳳顛鸞雲雨罷,囑多才,明朝千萬早些來。
這詞名《南鄉子》,單道其日間雲雨之事,這兩個霎時雲收雨散,各整衣巾。婦人摟住周得在懷裏道:“我的老公早出晚歸,你若不負我心,時常只說相訪。老子又瞎,他曉得什麼!只顧上樓和你快活,切不可做負心的。”周得答道:“好姐姐,心肝肉,你既有心於我,我決不負於你。我若負心,教我墮阿鼻地獄,萬劫不得人身。”這婦人見他設咒,連忙捧過周得臉來,舌送丁香,放在他口裏道:“我心肝,我不枉了有心愛你。從今後頻頻走來相會,切不可使我倚門而望。”道罷,兩人不忍分別。只得下樓別了任公,一直去了。
婦人對任公道:“這個是我姑娘的兒子,且是本分淳善,話也不會說,老實的人。”任公答道:“好,好。”婦人去竈前安排中飯與任公吃了,自上樓去了,直睡到晚。任圭回來,參了父親,上樓去了。夫妻無話,睡到天明。辭了父親,又入城而去。俱各不題。
這周得自那日走了這遭,日夜不安,一心想念。歇不得兩日,又去相會,正是情濃似火。此時牛皮街人煙稀少,因此走動,只有數家鄰舍,都不知此事。不想周得爲了一場官司,有兩個月不去相望。這婦人淫心似火,巴不得他來。只因周得不來,懨懨成病,如醉如癡。正是:
烏飛兔劫,朝來暮往何時歇?女媧只會煉石補青天,豈會熬膠粘日月?
倏忽又經元宵,臨安府居民門首扎縛燈棚,懸掛花燈,慶賀元宵。不期這周得官事已了,打扮衣巾,其日巳牌時分,徑來相望。卻好任公在門首唸佛,與他施禮罷,徑上樓來。袖中取出燒鵝熟肉,兩人吃了,解帶脫衣上牀。如糖似蜜,如膠似漆,恁意顛鸞倒鳳,出於分外綢繆。日久不曾相會,兩個摟做一團,不捨分開。耽閣長久了,直到申牌時分,不下樓來。
這任公肚中又飢,心下又氣,想道:“這阿舅今日如何在樓上這一日?”便在樓下叫道:“我肚飢了,要飯喫!”婦人應道:“我肚裏疼痛,等我便來。”任公忍氣吞聲,自去門前坐了,心中暗想:“必有蹺蹊,今晚孩兒回來問他。”這兩人只得分散,輕輕移步下樓,款款開門,放了周得去了。那婦人假意叫肚痛,安排些飯與任公吃了,自去樓上思想情人,不在話下。
卻說任圭到晚回來,參見父親。任公道:“我兒且休要上樓去,有一句話要問你。”任圭立住腳聽。任公道:“你丈人丈母家,有個甚麼姑舅的阿舅,自從舊年八月十八日看潮來了這遭,以後不時來望,徑直上樓去說話,也不打緊。今日早間上樓,直到下午,中飯也不安排我喫。我忍不住叫你老婆,那阿舅聽見我叫,慌忙去了。我心中十分疑惑,往日常要問你,只是你早出晚回,因此忘了。我想男子漢與婦人家在樓上一日,必有姦情之事。我自年老,眼又瞎,管不得,我兒自己慢慢訪問則個。”
任圭聽罷,心中大怒,火急上樓。端的是:
口是禍之門,舌爲斬身刀。 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
當時任圭大怒上樓,口中不說,心下思量:“我且忍住,看這婦人分豁。”只見這婦人坐在樓上,便問道:“父親喫飯也未?”
答應道:“吃了。”便上樓點燈來,鋪開被,脫了衣裳,先上牀睡了。任圭也上牀來,卻不倒身睡去,坐在枕邊問那婦人道:“我問你家那有個姑長阿舅,時常來望你?你且說是那個。”
婦人見說,爬將起來,穿起衣裳,坐在牀上。柳眉剔豎,嬌眼圓睜,應道:“他便是我爹爹結義的妹子養的兒子。我的爹孃記掛我,時常教他來望我,有什麼半絲麻線!”便焦躁發作道:“兀誰在你面前說長道短來?老孃不是善良君子,不裹頭巾的婆婆!洋塊磚兒也要落地,你且說是誰說黃道黑,我要和你會同問得明白。” 任圭道:“你不要嚷!卻纔父親與我說,今日甚麼阿舅在樓上一日,因此問你則個。沒事便罷休,不消得便焦躁。”一頭說,一頭便脫衣裳自睡了。那婦人氣喘氣促,做神做鬼,假意兒裝妖作勢,哭哭啼啼道:“我的父母沒眼睛,把我嫁在這裏。沒來由教他來望,卻教別人說是道非。”
又哭又說。任圭睡不著,只得爬起來,那婦人頭邊摟住了,撫卹道:“便罷休,是我不是。看往日夫妻之面,與你陪話便了。”
那婦人倒在任圭懷裏,兩個雲情雨意,狂了半夜,俱不題了。
任圭天明起來,辭了父親入城去了。每日巴巴結結,早出晚回。那癡婆一心只想要偷漢子,轉轉尋思:“要待何計脫身?只除尋事回到孃家,方纔和周得做一塊兒,耍個滿意。”
日夜掛心,捻指又過了半月。
忽一日飯後,周得又來,拽開門兒徑入,也不與任公相見,一直上樓。那婦人向前摟住,低聲說道:“叵耐這瞎老驢,與兒子說道你常來樓上坐定說話,教我分說得口皮都破,被我葫蘆提瞞過了。你從今不要來,怎地教我捨得你?可尋思計策,除非回家去與你方纔快活。”周得聽了,眉頭一簇,計上心來:“如今屋上貓兒正狂,叫來叫去。你可漏屋處抱得一個來,安在懷裏,必然抓碎你胸前。卻放了貓兒,睡在牀上啼哭。等你老公回來,必然問你。你說:‘你的好爺,卻來調戲我。我不肯順他,他將我胸前抓碎了。’你放聲哭起來,你的丈夫必然打發你歸家去。我每日得和你同歡同樂,卻強如偷雞吊狗,暫時相會。且在家中住了半年三個月,卻又再處,此計大妙。”婦人伏道:“我不枉了有心向你,好心腸,有見識!”二人和衣倒在牀上調戲了。雲雨罷,周得慌忙下樓去了。
正是:
老龜烹不爛,移禍於枯桑。
那婦人伺候了幾日。忽一日,捉得一個貓兒,解開胸膛,包在懷裏。這貓兒見衣服包籠,舒腳亂抓。婦人忍著疼痛,由他抓得胸前兩奶粉碎。解開衣服,放他自去。此是申牌時分,不做晚飯,和衣倒在牀上,把眼揉得緋紅,哭了叫,叫了哭。
將近黃昏,任圭回來,參了父親。到裏面不見婦人,叫道:“娘子,怎麼不下樓來?”那婦人聽得回了,越哭起來。任圭徑上樓,不知何意,問道:“喫晚飯也未?怎地又哭?”連問數聲不應,那淫婦巧生言語,一頭哭,一頭叫道:“問什麼!
說起來妝你孃的謊子。快寫休書,打發我回去,做不得這等豬狗樣人!你若不打發我回家去,我明日尋個死休!”說了又哭。任圭道:“你且不要哭,有甚事對我說。”這婦人爬將起來,抹了眼淚,擗開胸前,兩奶抓得粉碎,有七八條血路,教丈夫看了道:“這是你好親爺幹下的事!今早我送你出門,回身便上樓來。不想你這老驢老畜生,輕手輕腳跟我上樓,一把雙手摟住,摸我胸前,定要行奸。喫我不肯,他便將手把我胸前抓得粉碎,那裏肯放!我慌忙叫起來,他沒意思,方纔摸下樓去了。教我眼巴巴地望你回來。”說罷,大哭起來,道:“我家不見這般沒人倫畜生驢馬的事。”任圭道:“娘子低聲!鄰舍聽得,不好看相。”婦人道:“你怕別人得知,明日討乘轎子,擡我回去便罷休。”任圭雖是大孝之人,聽了這篇妖言,不由得: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
“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罷罷,原來如此!可知道前日說你與什麼阿舅有奸,眼見得沒巴鼻,在我面前胡說。今後眼也不要看這老禽獸!娘子休哭,且安排飯來吃了睡。”這婦人見丈夫聽他虛說,心中暗喜,下樓做飯,喫罷去睡了。正是:嬌妻喚做枕邊靈,十事商量九事成。
這任圭被這婦人情色昏迷,也不問爺卻有此事也無。過了一夜,次早起來,喫飯罷,叫了一乘轎子,買了一隻燒鵝,兩瓶好酒,送那婦人回去。婦人收拾衣包,也不與任公說知,上轎去了。擡得到家,便上樓去。周得知道便過來,也上樓去,就摟做一團,倒在梁婆牀上,雲情雨意。周得道:“好計麼?”婦人道:“端的你好計策!今夜和你放心快活一夜,以遂兩下相思之願。”兩個狂罷,周得下樓去要買辦些酒饌之類。
婦人道:“我帶得有燒鵝美酒,與你同吃。你要買時,只覓些魚菜時果足矣。”周得一霎時買得一尾魚,一隻豬蹄。四色時新果兒,又買下一大瓶五加皮酒。拿來家裏,教使女春梅安排完備,已是申牌時分。婦人擺開桌子,梁公梁婆在上坐了,周得與婦人對席坐了,使女篩酒,四人飲酒,直至初更。吃了晚飯,梁公梁婆二人下樓去睡了。這兩個在樓上。正是:歡來不似今日,喜來更勝當初。
正要稱意停眠整宿,只聽得有人敲門。正是:日間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喫驚。
這兩個指望做一夜快活夫妻,誰想有人敲門。春梅在竈前收拾未了,聽得敲門,執燈去開門。見了任圭,驚得呆了,立住腳頭,高聲叫道:“任姐夫來了!”周得聽叫,連忙穿衣徑走下樓。思量無處躲避,想空地裏有個東廁,且去東廁躲閃。這婦人慢慢下樓道:“你今日如何這等晚來?”任圭道:“便是出城得晚,關了城門。欲去張員外家歇,又夜深了,因此來這裏歇一夜。”婦人道:“喫晚飯了未?”任圭道:“吃了,只要些湯洗腳。”春梅連忙掇腳盆來,教任圭洗了腳。婦人先上樓,任圭卻去東廁裏淨手。時下有人攔住,不與他去便好。
只因來上廁,爭些兒死於非命。正是:
恩義廣施,人生何處不相逢?
冤仇莫結,路逢狹處難迴避。
任圭剛跨上東廁,被周得劈頭揪住,叫道:“有賊!”梁公、梁婆、婦人、使女各拿一根柴來亂打。任圭大叫道:“是我,不是賊!”衆人不由分說,將任圭痛打一頓。周得就在鬧裏一徑走了。任圭叫得喉嚨破了,衆人方纔放手。點燈來看,見了任圭,各人都呆了。任圭道:“我被這賊揪住,你們顛倒打我,被這賊走了。” 衆人假意埋冤道:“你不早說!只道是賊,賊到卻走了。”說罷,各人自去。任圭忍氣吞聲道:“莫不是藏什麼人在裏面,被我衝破,到打我這一頓?且不要慌,慢慢地察訪。”聽那更鼓已是三更,去梁公牀上睡了。心中胡思亂想,只睡不著。捱到五更,不等天明,起來穿了衣服便走。梁公道:“待天明吃了早飯去。”任圭被打得渾身疼痛,那有好氣?也不應他,開了大門,拽上了,趁星光之下,直望候潮門來。卻忒早了些,城門未開。城邊無數經紀行販,挑著鹽擔,坐在門下等開門。也有唱曲兒的,也有說閒話的,也有做小買賣的。任圭混在人叢中,坐下納悶。
你道事有湊巧,物有偶然,正所謂:
喫食少添鹽醋,不是去處休去。
要人知重勤學,怕人知事莫做。
當時任圭心下鬱鬱不樂,與決不下。內中忽有一人說道:“我那裏有一鄰居梁涼傘家,有一件好笑的事。”這人道:“有什麼事?”那人道:“梁家有一個女兒,小名聖金,年二十餘歲。
未曾嫁時,先與對門周待詔之子周得通姦。舊年嫁在城外牛皮街賣生藥的主管叫做任圭。這周得一向去那裏來往,被瞎阿公識破,去那裏不得了。昨日歸在家裏,昨晚周得買了嗄飯好酒,喫到更荊兩個正在樓上快活,有這等的巧事,不想那女婿更深夜靜,趕不出城,徑來丈人家投宿。姦夫驚得沒躲避處,走去東廁裏躲了。任圭卻去東廁淨手,你道好笑麼?那周得好手段,走將起來劈頭將任圭揪住,到叫:‘有賊!’丈人、丈母、女兒,一齊把任圭爛醬打了一頓,姦夫逃走了。
世上有這樣的異事!”衆人聽說了,一齊拍手笑起來,道:“有這等沒用之人!被姦夫淫婦安排,難道不曉得?”這人道:“若是我,便打一把尖刀,殺做兩段!那人必定不是好漢,必是個煨膿爛板烏龜。”又一個道:“想那人不曉得老婆有奸,以致如此。”說了又笑一常正是:
情知語是鉤和線,從頭釣出是非來。
當時任圭卻好聽得備細,城門正開,一齊出城,各分路去了。此時任圭不出城,復身來到張員外家裏來,取了三五錢銀子,到鐵鋪裏買了一柄解腕尖刀,和鞘插在腰間。思量錢塘門晏公廟神明最靈,買了一隻白公雞,香燭紙馬,提來廟裏,燒香拜告:“神聖顯靈,任圭妻梁氏,與鄰人周得通姦,夜來如此如此。”前話一一禱告罷,將刀出鞘,提雞在手,問天買卦:“如若殺得一個人,殺下的雞在地下跳一跳,殺他兩個人,跳兩跳。”說罷,一刀剁下雞頭,那雞在地下一連跳了四跳,重複從地跳起,直從樑上穿過,墜將下來,卻好共是五跳。當時任圭將刀入鞘,再拜,望神明助力報仇。化紙出廟上街,東行西走,無計可施。到晚回張員外家歇了。沒情沒緒,買賣也無心去管。
次日早起,將刀插在腰間,沒做理會處。欲要去梁家幹事,又恐撞不著周得,只殺得老婆也無用,又不了事。轉轉尋思,恨不得咬他一口。徑投一個去處,有分教:任圭小膽番爲大膽,善心改作惡心;大鬧了日新橋,鼎沸了臨安府。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這任圭東撞西撞,徑到美政橋姐姐家裏。見了姐姐說道:“你兄弟這兩日有些事故,爹在家沒人照管,要寄託姐姐家中住幾時,休得推故。”姐姐道:“老人家多住些時也不妨。”姐姐果然教兒去接任公,扶著來家。
這日任圭又在街坊上串了一回,走到姐姐家,見了父親,將從前事,一一說過,道:“兒子被這潑淫婦虛言巧語,反說父親如何如何,兒子一時被惑,險些墮他計中。這口氣如何消得?”任公道:“你不要這淫婦便了,何須嘔氣?”任圭道:“有一日撞在我手裏,決無干休!”任公道:“不可造次。從今不要上他門,休了他,別討個賢會的便罷。”任圭道:“兒子自有道理。”辭了父親並姐姐,氣忿忿的入城。
恰好是黃昏時候,走到張員外家,將上件事一一告訴:“只有父親在姐姐家,我也放得心下。”張員外道:“你且忍耐,此事須要三思而行。自古道:‘捉姦見雙,捉賊見贓。’倘或不了事,枉受了苦楚。若下在死囚牢中,無人管你。你若依我說話,不強如殺害人性命?冤家只可解,不可結。”任圭聽得勸他,低了頭,只不言語。員外教養娘安排酒飯相待,教去房裏睡,明日再作計較。任圭謝了。到房中寸心如割,和衣倒在牀上,番來覆去,延捱到四更盡了,越想越惱,心頭火按捺不祝起來抓扎身體急捷,將刀插在腰間,摸到廚下,輕輕開了門,靠在後牆。那牆苦不甚高,一步爬上牆頭。其時夏末秋初,其夜月色正明如晝。將身望下一跳,跳在地上。
道:“好了!”一直望丈人家來。
隔十數家,黑地裏立在屋檐下,思量道:“好卻好了,怎地得他門開?”躊躇不決。只見賣燒餅的王公,挑著燒餅擔兒,手裏敲著小小竹筒過來。忽然丈人家門開,走出春梅,叫住王公,將錢買燒餅。任圭自道:“那廝當死!”三步作一步,奔入門裏,徑投胡梯邊梁公房裏來。掇開房門,拔刀在手,見丈人、丈母俱睡著。心裏想道:“周得那廝必然在樓上了。”按住一刀一個,割下頭來,丟在牀前。正要上樓,卻好春梅關了門,走到胡梯邊。被任圭劈頭揪住,道:“不要高聲!若高聲,便殺了你。你且說,周得在那裏?”那女子認得是任圭聲音,情知不好了,見他手中拿刀,大叫:“任姐夫來了!”任圭氣起,一刀砍下頭來,倒在地下,慌忙大踏步上樓去殺姦夫淫婦。正是: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當時任圭跨上樓來。原來這兩個正在牀上狂蕩,聽得王公敲竹筒,喚起春梅買燒餅,房門都不閉,卓上燈尚明。徑到牀邊,婦人已知,聽得春梅叫,假做睡著,任圭一手按頭,一手將刀去咽喉下切下頭來,丟在樓板上。口裏道:“這口怒氣出了,只恨周得那廝不曾殺得,不滿我意。”猛想:“神前殺雞五跳,殺了丈人、丈母、婆娘、使女,只應得四跳。那雞從樑上跳下來,必有緣故。”擡頭一看,卻見周得赤條條的伏在樑上。任圭叫道:“快下來,饒你性命!”那時周得心慌,爬上去了,一見任圭,戰戰兢兢,慌了手腳,禁了爬不動。任圭性起,從牀上直爬上去,將刀亂砍,可憐周得從樑上倒撞下來。任圭隨勢跳下,踏住胸脯,搠了十數刀。將頭割下,解開頭髮,與婦人頭結做一處。將刀入鞘,提頭下樓。到胡梯邊,提了使女頭,來尋丈人、丈母頭,解開頭髮,五個頭結做一塊,放在地上。此時東方大亮,心中思忖:“我今殺得快活,稱心滿意。逃走被人捉住,不爲好漢。不如挺身首官,便吃了一剮,也得名揚於後世。”
遂開了門,叫兩邊鄰舍,對衆人道:“婆娘無禮,人所共知。我今殺了他一家,並姦夫周得。我若走了,連累高鄰喫官司,如今起煩和你們同去出首。”衆人見說未信,慌忙到梁公房裏看時,老夫妻兩口俱沒了頭。胡梯邊使女屍倒在那裏。
上樓看時,周得被殺死在樓上,遍身刀搠傷痕數處,尚在血裏,婦人殺在牀上。衆人吃了一驚,走下樓來。只見五顆頭結做一處,都道:“真好漢子!我們到官,依直與他講就是。”
道猶未了,嚷動鄰舍、街坊、里正、緝捕人等,都來縛住任圭。任圭道:“不必縛我,我自做自當,並不連累你們。”說罷,兩手提了五顆頭,出門便走。衆鄰舍一齊跟定,滿街男子婦人,不計其數來看,鬨動滿城人。只因此起,有分教任圭,正是:
生爲孝子肝腸烈,死作明神姓字香。
衆鄰舍同任圭到臨安府。大尹聽得殺人公事,大驚,慌忙升廳。兩下公吏人等排立左右,任圭將五個人頭,行兇刀一把,放在面前,跪下告道:“小人姓任名圭,年二十八歲,系本府百姓,祖居江頭牛皮街上。母親早喪,止有老父,雙目不明。前年冬間,憑媒說合,娶到在城日新橋河下樑公女兒爲妻,一向到今。小人因無本生理,在賣生藥張員外家做主管。早去晚回,日常間這婦人只是不喜。至去年八月十八日,父親在樓下坐定唸佛。原來梁氏未嫁小人之先,與鄰人周得有奸。其日本人來家,稱是姑舅哥哥來訪,徑自上樓說話。日常來往,痛父眼瞎不明。忽日父與小人說道:‘什麼阿舅常常來樓上坐,必有姦情之事。’小人聽得說,便罵婆娘。
一時小人見不到,被這婆娘巧語虛言,說道老父上樓調戲。因此三日前,小人打發婦人回孃家去了。至日,小人回家晚了,關了城門,轉到妻家投宿。不想姦夫見我去,逃躲東廁裏。小人臨睡,去東廁淨手,被他劈頭揪住,喊叫有賊。當時丈人、丈母、婆娘、使女,一齊執柴亂打小人,此時姦夫走了。小人忍痛歸家,思想這口氣沒出處。不合夜來提刀入門,先殺丈人、丈母,次殺使女,後來上樓殺了淫婦。猛擡頭,見姦夫伏在樑上,小人爬上去,亂刀砍死。今提五個首級首告,望相公老爺明鏡。”大尹聽罷,呆了半晌。遂問排鄰,委果供認是實。所供明白,大尹鈞旨,令任圭親筆供招。隨即差個縣尉,並公吏仵作人等,押著任圭到屍邊檢驗明白。其日人山人海來看。
險道神脫了衣裳,這場話非同小可。
當日一齊同到梁公家,將五個屍首一一檢驗訖,封了大門。縣尉帶了一干人犯,來府堂上回話道:“檢得五個屍,並是凶身自認殺死。”大尹道:“雖是自首,難以免責。”交打二十下,取具長枷枷了,上了鐵鐐手肘,令獄卒押下死囚牢裏去。一干排鄰回家。教地方公同作眼,將梁公家家財什物變賣了,買下五具棺材,盛下屍首,聽候官府發落。
且說任圭在牢內,衆人見他是個好男子,都愛敬他。早晚飯食,有人管顧,不在話下。
臨安府大尹與該吏商量:任圭是個烈性好漢,只可惜下手忒狠了,周旋他不得。只得將文書做過,申呈刑部。刑部官奏過天子,令勘官勘得本犯奸夫淫婦,理合殺死,不合殺了丈人、丈母、使女,一家非死三人。著令本府待六十日限滿,將犯人就本地方凌遲示衆。梁公等屍首燒化,財產入官。
文書到府數日,大尹差縣尉率領仵詐、公吏、軍兵人等,當日去牢中取出任圭。大尹將朝廷發落文書,教任圭看了。任圭自知罪重,低頭伏死。大尹教去了鎖枷鐐肘,上了木驢。只見:
四道長釘釘,三條麻素縛。
兩把刀子舉,一朵紙花遙
縣尉人等,兩棒鼓,一聲鑼,簇擁推著任圭,前往牛皮街示衆。但見犯由牌前引,棍棒後隨。當時來到牛皮街,圍住法場,只等午時三刻。其日看的人,兩行如堵。將次午時,真可作怪,一時間天昏地黑,日色無光,狂風大作,飛沙走石,播土揚泥,你我不能相顧。看的人驚得四分五落,魄散魂飄。
少頃,風息天明,縣尉並劊子衆人看任圭時,擲索長釘俱已脫落,端然坐化在木驢之上。衆人一齊發聲道:“自古至今,不曾見有這般奇異的怪事。”監斬官驚得木麻,慌忙令仵作、公吏人等,看守任圭屍首,自己忙拍馬到臨安府,稟知大尹。大尹見說大驚,連忙上轎,一同到法場看時,果然任圭坐化了。大尹徑來刑部稟知此事,著令排鄰地方人等,看守過夜。明早奏過朝廷,憑聖旨發落。次日巳牌時分,刑部文書到府,隨將犯人任圭屍首,即時燒化,以免凌遲。縣尉領旨,就當街燒化。城裏城外人,有千千萬萬來看,都說:“這樣異事,何曾得見!何曾得見!”
卻說任公與女兒得知任圭死了,安排些羹飯。外甥挽了瞎公公,女兒拾著轎子,一齊徑到當街祭祀了,痛哭一常任圭的姐姐,教兒子挽扶著公公,同回家奉親過世。
話休絮煩,過了兩月餘,每遇黃昏,常時出來顯靈。來往行人看見者,回去便患病,備下羹飯紙錢當街祭獻,其病即痊。忽一日,有一小兒來牛皮街閒耍,被任圭附體起來。衆人一齊來看,小兒說道:“玉帝憐吾是忠烈孝義之人,各坊城隍、土地保奏,令做牛皮街土地。汝等善人可就我屋基立廟,春秋祭祀,保國安民。”說罷,小兒遂醒。當坊鄰佑,看見如此顯靈,那敢不信?即日斂出財物,買下木植,將任圭基地蓋造一所廟宇。連忙請一個塑佛高手,塑起任圭神像,坐於中間,虔備三牲福禮祭獻。自此香火不絕,祈求必應,其廟至今尚存。後人有詩題於廟壁,贊任圭坐化爲神之事,詩云:
鐵銷石朽變更多,只有精神永不磨。 除卻姦淫拚自死,剛腸一片賽閻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