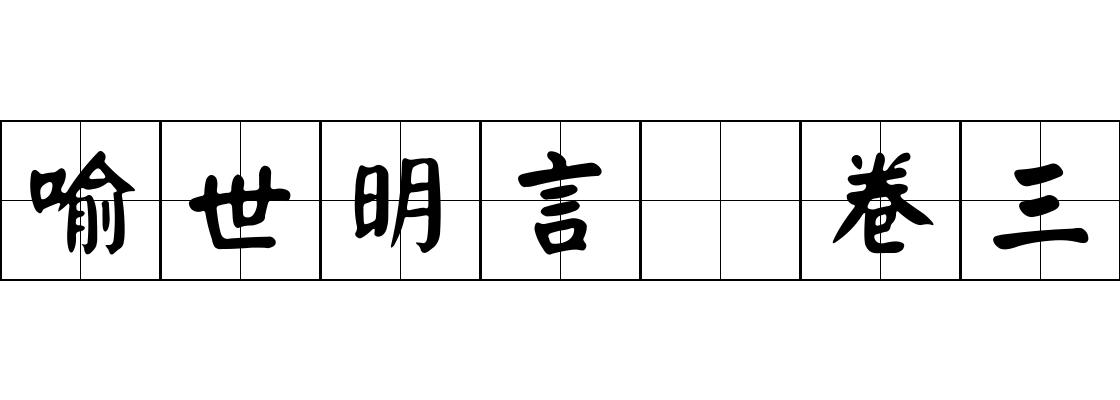喻世明言-卷三-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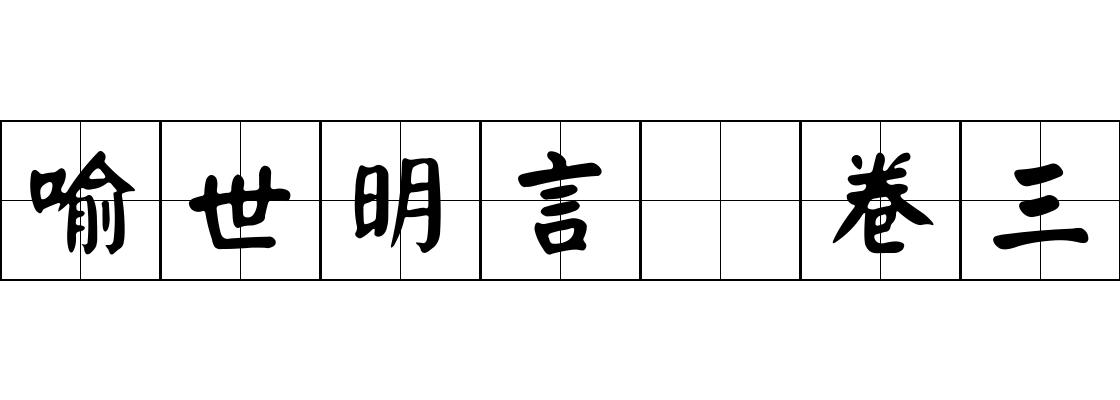
《喻世明言》是明末馮夢龍纂輯的白話短篇小說集。《喻世明言》最初版本名爲《古今小說》,全稱《全像古今小說》。後重印改名爲《喻世明言》,以與“三言”其他作品書名相配。全書40卷,每卷1篇,共計40篇。它和《通言》《恆言》一樣,爲宋元明話本小說。《喻世明言》中故事產生的時代,包括宋、元、明三代,其中多數爲宋元舊作話本,另外有些是明人對宋元舊作的改編加工,還收錄和改編了一些歷史傳奇故事。此外,《喻世明言》各篇小說多取材於現實生活,主題涵蓋愛情、婚姻、朋友情義等,展現了當其時的社會百態。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情寵嬌多不自由,驪山舉火戲諸候。 祇知一笑傾人國,不覺胡塵滿玉樓。
這四句詩,是胡曾《詠史詩》。專道著昔日周幽王寵一個妃子,名曰褒姒,千方百計的媚他。因要取褒姒一笑,向驪山之上,把與諸侯爲號的烽火燒起來。諸侯只道幽王有難,都舉兵來救。及到幽王殿下,寂然無事。褒姒呵呵大笑。後來犬戎起兵來攻,諸侯皆不來救,犬戎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又春秋時,有個陳靈公,私通於夏徵舒之母夏姬。與其臣孔寧、儀行父日夜往其家,飲酒作樂。徵舒心懷愧恨,射殺靈公。後來六朝時,陳後主寵愛張麗華、孔貴嬪,自制《後庭花》曲,姱美其色,沉湎淫逸,不理國事。被隋兵所追,無處躲藏,遂同二妃投入井中,爲隋將韓擒虎所獲,遂亡其國。詩云:
歡娛夏廄忽興戈,眢井猶聞《玉樹》歌。 試看二陳同一律,從來亡國女戎多。
當時,隋煬帝也寵蕭妃之色。要看揚州景,用麻叔度爲帥,起天下民夫百萬,開汴河一千餘裏,役死人夫無數。造鳳艦龍舟,使宮女牽之,兩岸樂聲聞於百里。後被宇文化及造反江都,斬煬帝於吳公臺下,其國亦傾。有詩爲證:
千里長河一旦開,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更不回。
至於唐明皇寵愛楊貴妃之色,春縱春遊,夜專夜寵。誰想楊妃與安祿山私通,卻抱祿山做孩兒。一日,雲雨方罷,楊妃釵橫鬢亂,被明皇撞見,支吾過了。明皇從此疑心,將祿山除出在漁陽地面做節度使。那祿山思戀楊妃,舉兵反叛。正是: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那明皇無計奈何,只得帶取百官逃難。馬嵬山下兵變,逼死了楊妃。明皇直走到西蜀。虧了郭令公血戰數年,才恢復得兩京。
且如說這幾個官家,都只爲貪愛女色,致於亡國捐軀。如今愚民小子,怎生不把色慾警戒!說話的,你說那戒色慾則甚?自家今日說一個青年子弟,只因不把色慾警戒,去戀著一個婦人,險些兒壞了堂堂六尺之軀,丟了潑天的家計,驚動新橋市上,變成一本風流說話。正是:
好將前事錯,傳與後人知。
說這宋朝臨安府,去城十里,地名湖墅;出城五里,地名新橋。那市上有個富戶吳防禦,媽媽潘氏,止生一子,名喚吳山,娶妻餘氏,生得四歲一個孩兒。防禦門首開個絲綿鋪,家中放債積穀。果然是金銀滿筐,米穀成倉。去新橋五里,地名灰橋市上,新造一所房屋,令子吳山,再撥主管幫扶,也好開一個鋪。家中收下的絲綿,發到鋪中賣與在城機戶。吳山生來聰俊,粗知禮義,幹事樸實,不好花鬨。因此防禦不慮他在外邊閒理會。
且說吳山每日早晨到鋪中賣貨,天晚回家。這鋪中房屋,只佔得門面,裏頭房屋都是空的。忽一日,吳山在家有事,至晌午纔到鋪中。走進看時,只見屋後河邊泊著兩隻剝船,船上許多箱籠、桌、凳、家火,四五個人盡搬入空屋裏來。船上走起三個婦人:一箇中年胖婦人、一個老婆子、一個小婦人,盡走入屋裏來。只因這婦人入屋,有分教吳山:
身如五鼓銜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燈。
吳山問主管道:“甚麼人不問事由,擅自搬入我屋來?”主管道:“在城人家。爲因裏役,一時間無處尋屋,央此間鄰居範老來說,暫住兩一日便去。正欲報知,恰好官人自來。”吳山正欲發怒,見那小娘子斂袂向前深深的道個萬福:“告官人息怒,非幹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膽,一時事急,出於無奈,不及先來宅上稟知,望乞恕罪。容住三四日,尋了屋就搬去,房金依例拜納。”吳山便放下臉來道:“既如此,便多住些時也不妨,請自穩便。”婦人說罷,就去搬箱運籠。吳山看得心癢,也替他搬了幾件家火。
說話的,你說吳山平生鯁直,不好花鬨,因何見了這個婦人,回嗔作喜,又替他搬家火?你不知道,吳山在家時,被父母拘管得緊,不容他閒走。他是個聰明俊俏的人,幹事活動,又不是一個木頭的老實。況且青春年少,正是他的時節。父母又不在面前,浮鋪中見了這個美貌的婦人,如何不動心?
那胖婦人與小婦人都道:“不勞官人用力。”吳山道:“在此間住,就是自家一般,何必見外?”彼此俱各歡喜。天晚,吳山回家,吩咐主管與裏面新搬來的說,“寫紙房契來與我。”主管答應了,不在話下。
且說吳山回到家中,並不把搬來一事說與父母知覺。當夜心心念念,想著那小婦人。次日早起,換身好衣服,打扮齊整,叫個小廝壽童跟著,搖擺到店中來。正是:
沒興店中賒得酒,命衰撞著有情人。
吳山來到鋪中,賣了一回貨。裏面走動的八老來接喫茶,要納房狀。吳山心下正要進去,恰好得八老來接,便起身入去。只見那小婦人笑容可掬,接將出來萬福:“官人請裏面坐。”吳山到中間軒子內坐下。那老婆子和胖婦人都來相見陪坐,坐間只有三個婦人。吳山動問道:“娘子高姓?怎麼你家男兒漢不見一個?”胖婦道:“拙夫姓韓,與小兒在衙門跟官,早去晚回,官身不得相會。”坐了一回,吳山低著頭睃那小婦人。這小婦人一雙俊俏眼覷著吳山道:“敢問官人青春多少?”吳山道:“虛度二十四歲,拜問娘子青春?”小婦人道:“與官人一緣一會,奴家也是二十四歲。城中搬下來,偶輳遇官人,又是同歲,正是有緣千里能相會。”
那老婦人和胖婦人看見關目,推個事故起身去了,只有二人對坐。小婦人到把些風流話兒挑引吳山。吳山初然只道好人家,容他住,不過砑光而已。誰想見面,到來刮涎,才曉得是不停當的。欲待轉身出去,那小婦人又走過來挨在身邊坐定,作嬌作癡,說道:“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來借我看一看。”吳山除下帽子,正欲拔時,被小婦人一手按住吳山頭髻,一手拔了金簪,就便起身道:“官人,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一頭說,逕走上樓去了。吳山隨後跟上樓來討簪子。正是:
由你奸似鬼,也喫洗腳水。
吳山走上樓來,叫道:“娘子!還我簪子。家中有事,就要回去。”婦人道:“我與你是宿世姻緣,你不要裝假,願諧枕蓆之歡。”吳山道:“行不得!倘被人知覺,卻不好看。況此間耳目較近。”待要下樓。怎奈那婦人放出那萬種妖嬈,摟住吳山,倒在懷中,將尖尖玉手,扯下吳山裙褲。情興如火,按撩不住,攜手上牀,成其雲雨。霎時雲收雨散,兩個起來偎倚而坐。吳山且驚且喜,問道:“姐姐,你叫做甚麼名字?”婦人道:“奴家排行第五,小字賽金。長大,父母順口叫道金奴。敢問官人排行第幾?宅上做甚行業?”吳山道:“父母止生得我一身,家中收絲放債,新橋市上出名的財主。此間門前鋪子,是我自家開的。”金奴暗喜道:“今番纏得這個有錢的男兒,也不枉了。”
原來這人家是隱名的娼妓,又叫做“私窠子”,是不當官喫衣飯的。家中別無生意,只靠這一本帳。那老婦人是胖婦人的娘,金奴是胖婦人的女兒。在先,胖婦人也是好人家出來的。因爲丈夫無用掙圍,不得已幹這般勾當。金奴自小生得標緻,又識幾個字,當時已自嫁與人去了,只因在夫家不坐疊,做出來,發回孃家。事有湊巧,物有偶然。此時胖婦人年紀約近五旬,孤老來得少了,恰好得女兒來接代,也不當斷這樣行業,索性大做了。原在城中住,只爲這樣事被人告發,慌了,搬下來躲避。卻恨吳山偶然撞在他手裏,圈套都安排停當,漏將入來,不由你不落水。怎地男兒漢不見一個?但看有人來,父子們都回避過了,做成的規矩。這個婦人,但貪他的,便著他的手,不止陪了一個漢子。
當時金奴道:“一時慌促搬來,缺少盤費。告官人,有銀子乞借應五兩,不可推故。”吳山應允了。起身整了衣冠,金奴依先還了金簪。兩個下樓,依舊坐在軒子內。吳山自思道:“我在此擔閣了半晌,慮恐鄰舍們談論。”又吃了一杯茶。金奴留喫午飯,吳山道:“我擔閣長久,不喫飯了。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金奴道:“午後特備一杯菜酒,官人不要見卻。”說罷,吳山自出鋪中。
原來外邊近鄰見吳山進去。那房屋卻是兩間六椽的樓屋,金奴只佔得一間做房,這邊一間就是絲鋪,上面卻是空的。有好事哥哥,見吳山半晌不出來,伏在這間空樓壁邊,入馬之時,都張見明白。比及吳山出來,坐在鋪中,只見幾個鄰人都來和哄道:“吳小官人,恭喜恭喜!”吳山初時已自心疑他們知覺,次後見衆人來取笑,他通紅了臉皮,說道:“好沒來由!有甚喜賀!”內中有原張見的,是對門開雜貨鋪的沈二郎,叫道:“你兀自賴哩,拔了金簪子,走上樓去做甚麼?”吳山被他一句說著了,頓口無言,推個事故,起身要走。衆人攔住道:“我們鬥分銀子,與你作賀。”
吳山也不顧衆說,使性子往西走了。去到孃舅潘家,討午飯吃了。踱到門前,向一個店家借過等子,將身邊買絲銀子秤了二兩,放在袖中。又閒坐了一回,捱到半晚,復到鋪中來。主管道:“裏面住的正在此請官人喫酒。”恰好八老出來道:“官人,你那裏閒耍?教老子沒處尋。家中特備菜酒,止請主管相陪,再無他客。”吳山就同主管走到軒子下。已安排齊整,無非魚、肉、酒、果之類。吳山正席,金奴對坐,主管在旁。三人坐定,八老篩酒。喫過幾杯,主管會意,只推要收鋪中,脫身出來。吳山平日酒量淺,主管去了,開懷與金奴吃了十數杯,便覺有些醉來。將袖中銀子送與金奴,便起身挽了金奴手道:“我有一句話和你說:這樁事,卻有些不諧當。鄰舍們都知了,來打和哄。倘或傳到我家去,父母知道,怎生是好?此間人眼又緊,口嘴又歹,容不得人。倘有人不愜氣,在此飛磚擲瓦,安身不穩。姐姐,依著我口,尋個僻靜所在去住,我自常來看顧你。”金奴道:“說得是!奴家就與母親商議。”說罷,那老子又將兩杯茶來。喫罷,免不得又做些乾生活。吳山辭別動身,囑咐道:“我此去未來哩,省得衆人口舌。待你尋得所在,八老來說知,我來送你起身。”說罷,吳山出來鋪中,吩咐主管說話,一逕自回,不在話下。
且說金奴送吳山去後,天色已晚。上樓卸了濃妝。下樓來吃了晚飯。將吳山所言移屋一節,備細說與父母知道。當夜各自安歇。次早起來,胖婦人吩咐八老悄地打聽鄰舍消息。八老到門前站了一回,踅到間壁糶米張大郎門前,閒坐了一回。只聽得這幾家鄰舍指指搠搠,只說這事。八老回家,對這胖婦人說道:“街坊上嘴舌不是養人的去處。”胖婦人道:“因爲在城中被人打攪,無奈搬來,指望尋個好處安身,久遠居住,誰想又撞這般的鄰舍!”說罷嘆了口氣。一面教老公去尋房子,一面看鄰舍動靜計較。
卻說吳山自那日回家,怕人嘴舌,瞞著父母,只推身子不快,一向不到店中來。主管自行賣貨。金奴在家清閒不慣,八老又去招引舊時主顧,一般來走動。那幾家鄰舍初然只曉得吳山行踏,次後見往來不絕,方曉得是個大做的。內中有生事的道:“我這裏都是好人家,如何容得這等鏖糟的在此住?常言道:‘近奸近殺。’倘若爭鋒起來,致傷人命,也要帶累鄰舍。”說罷,卻早被那八老聽得,進去說:“今日鄰舍們又如此如此說。”胖婦人聽得八老說了,沒出氣處,碾那老婆子道:“你七老八老,怕兀誰?不出去門前叫罵這短命多嘴的鴨黃兒!”婆子聽了,果然就起身走到門前叫罵道:“那個多嘴賊鴨黃兒,在這裏學放屁!若還敢來應我的,做這條老性命結識他。那個人家沒親眷來往?”鄰舍們聽得,道:“這個賊做大的出精老狗,不說自家幹這般沒理的事,到來欺鄰罵舍!”開雜貨店沈二郎正要應那婆子,中間又有守本分的勸道:“且由他!不要與這半死的爭好歹,趕他起身便了。”婆子罵了幾聲,見無人來睬他,也自入去。
卻說衆鄰舍都來與主管說:“是你沒分曉,容這等不明不白的人在這裏住。不說自家理短,反教老婆子叫罵鄰舍,你耳內須聽得。我們都到你主家說與防禦知道,你身上也不好看。”主管道:“列位高鄰息怒,不必說得,早晚就著他搬去。”衆人說罷,自去了。主管當時到裏面對胖婦人說道:“你們可快快尋個所在搬去,不要帶累我。看這般模樣,住也不秀氣。”胖婦人道:“不勞吩咐,拙夫已尋屋在城,只在早晚就搬。”說罷,主管出來。胖婦人與金奴說道:“我們明早搬入城。今日可著八老悄地與吳小官說知,只莫教他父母知覺。”
八老領語,走到新橋市上吳防禦絲綿大鋪。不敢逕進,只得站在對門人家檐下踅去,一眼只看著鋪裏。不多時,只見吳山踱將出來。看見八老,慌忙走過來,引那老子離了自家門首,借一個織熟絹人家坐下,問道:“八老有甚話說?”八老道:“家中五姐領官人尊命,明日搬入城去居住,特著老漢來與官人說知。”吳山道:“如此最好,不知搬在城中何處?”八老道:“搬在遊羿營羊毛寨南橫橋街上。”吳山就身邊取出一塊銀子,約有二錢,送與八老道:“你自將去買杯酒喫。明日晌午,我自來送你家起身。”八老收了銀子,作謝了,一逕自回。
且說吳山到次日巳牌時分,喚壽童跟隨出門,走到歸錦橋邊南貨店裏,買了兩包乾果,與小廝拿著,來到灰橋市上鋪裏。主管相叫罷,將日逐賣終的銀子帳來算了一回。吳山起身,入到裏面與金奴母子敘了寒溫,將壽童手中果子,身邊取出一封銀子,說道:“這兩包粗果,送與姐姐泡茶;銀子三兩,權助搬屋之費。待你家過屋後,再來看你。”金奴接了果子並銀兩,母子兩個起身謝道:“重蒙見惠,何以克當!”吳山道:“不必謝,日後正要往來哩。”說罷,起身看時,箱籠家火已自都搬下船了。金奴道:“官人,去後幾時來看我?”吳山道:“只在三五日間,便來相望。”金奴一家別了吳山,當日搬人城去了。正是: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且說吳山原有害夏的病:每過炎天時節,身體便覺疲倦,形容清減。此時正值六月初旬,因此請個鍼灸醫人,背後灸了幾穴火,在家調養,不到店內。心下常常思念金奴,爭奈灸瘡疼,出門不得。
卻說金奴從五月十七搬移在橫橋街上居住。那條街上俱是營裏軍家,不好此事,路又僻拗,一向沒人走動。胖婦人向金奴道:“那日吳小官許下我們三五日間就來,到今一月,緣何不見來走一遍?若是他來,必然也看覷我們。”金奴道:“可著八老去灰橋市上鋪中探望他。”當時八老去,就出艮山門到灰橋市上絲鋪裏見主管。八老相見罷,主管道:“阿公來,有甚事?”八老道:“特來望吳小官。”主管道:“官人灸火在家未痊,向不到此。”八老道:“主管若是回宅,煩寄個信,說老漢到此不遇。”八老也不擔閣,辭了主管便回家中,回覆了金奴。金奴道:“可知不來,原來灸火在家。”
當日金奴與母親商議,教八老買兩個豬肚磨淨,把糯米蓮肉灌在裏面,安排爛熟。次早,金奴在房中磨墨揮筆,拂開鸞箋,寫封簡道:“賤妾賽金再拜,謹啓情郎吳小官人:自別尊顏,思慕之心,未嘗少怠,懸懸不忘於心。向蒙期約,妾倚門凝望,不見降臨。昨遣八老探拜,不遇而回。妾移居在此,甚是荒涼。聽聞貴恙灸火疼痛,使妾坐臥不安。空懷思憶,不能代替。謹具豬肚二枚,少申問安之意,幸希笑納。情照不宣。仲夏二十一日,賤妾賽金再拜。”寫罷,摺成簡子,將紙封了。豬肚裝在盒裏,又用帕子包了。都交付八老,叮囑道:“你到他家,尋見吳小官,須索與他親收。”
八老提了盒子,懷中揣著簡帖,出門逕往大街。走出武林門,直到新橋市上吳防禦門首,坐在街檐石上。只見小廝壽童走出,看見叫道:“阿公,你那裏來,坐在這裏?”八老扯壽童到人靜去處說:“我特來見你官人說話。我只在此等,你可與我報與官人知道。”壽童隨即轉身,去不多時,只見吳山踱將出來。八老慌忙作揖:“官人,且喜貴體康安!”吳山道:“好!阿公,你盒子裏甚麼東西?”八老道:“五姐記掛官人灸火,沒甚好物,只安排得兩個豬肚,送來與官人喫。”吳山遂引那老子到個酒店樓上坐定,問道:“你家搬在那裏好麼?”八老道:“甚是消索。”懷中將柬帖子遞與吳山。吳山接柬在手,拆開看畢,依先摺了,藏在袖中。揭開盒子拿一個肚子,教酒博士切做一盤,吩咐燙兩壺酒來。吳山道:“阿公,你自在這裏喫,我家去寫回字與你。”八老道:“官人請穩便。”吳山來到家裏臥房中,悄悄的寫了回簡。又秤五兩白銀。復到酒店樓上,又陪八老吃了幾杯酒。八老道:“多謝官人好酒,老漢喫不得了。”起身回去。吳山遂取銀子並回柬說道:“這五兩銀子,送與你家盤纏。多多拜覆五姐:過一兩日,定來相望。”八老收了銀、簡,起身下樓,吳山送出酒店。
卻說八老走到家中,天晚入門,將銀、簡都付與金奴收了。將簡拆開燈下看時,寫道:“山頓首,字覆愛卿韓五娘妝次:向前會間,多蒙厚款。又且雲情雨意,枕蓆鍾情,無時少忘。所期正欲趨會,生因賤軀灸火,有失卿之盼望。又蒙遣人垂顧,兼惠可口佳餚,不勝感感。二三日間,容當面會。白金五兩,權表微情,伏乞收入。吳山再拜。”看簡畢,金奴母子得了五兩銀子,千歡萬喜,不在話下。
且說吳山在酒店裏,捱到天晚,拿了一個豬肚,悄地裏到自臥房,對渾家說:“難得一個識熟機戶,聞我灸火,今日送兩個熟肚與我。在外和朋友吃了一個,拿一個回來與你喫。”渾家道:“你明日也用作謝他。”當晚吳山將肚子與妻在房吃了,全不教父母知覺。過了兩日,第三日,是六月二十四日。吳山起早,告父母道:“孩兒一向不到鋪中,喜得今日好了,去走一遭。況在城神堂巷有幾家機戶賒帳要討,入城便回。”防禦道:“你去不可勞碌。”吳山辭父,討一乘兜轎擡了,小廝壽童打傘跟隨。只因吳山要進城,有分教金奴險送他性命。正是: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
吳山上轎,不覺早到灰橋市上。下轎進鋪,主管相見。吳山一心只在金奴身上,少坐,便起身吩咐主管:“我入城收拾機戶賒帳,回來算你日逐賣帳。”主管明知到此處去,只不敢阻,但勸:“官人貴體新痊,不可別處閒走,空受疼痛。”吳山不聽,上轎預先吩咐轎伕,逕進艮山門,迤邐到羊毛寨南橫橋,尋問湖市搬來韓家。旁人指說:“藥鋪間壁就是。”吳山來到門首下轎,壽童敲門。裏面八老出來開門,見了吳山,慌入去說知。吳山進門,金奴母子兩個堆下笑來迎接,說道:“貴人難見面。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吳山與金奴母子相喚罷,到裏面坐定喫茶。金奴道:“官人認認奴家房裏。”吳山同金奴到樓上房中。正所謂:
合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至話相投。
金奴與吳山在樓上,如魚得水,似漆投膠,兩個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少不得安排酒餚,八老搬上樓來,掇過鏡架,就擺在梳妝桌上。八老下來,金奴討酒,纔敢上去。兩個並坐,金奴篩酒一杯,雙手敬與吳山道:“官人灸火,妾心無時不念。”吳山接酒在手道:“小生爲因灸火,有失期約。”酒盡,也篩一杯回敬與金奴。喫過十數杯,二人情興如火,免不得再把舊情一敘。交歡之際,無限恩情。事畢起來,洗手更酌。又飲數杯,醉眼朦朧,餘興未盡。吳山因灸火在家,一月不曾行事。見了金奴,如何這一次便罷?吳山合當死,魂靈都被金奴引散亂了,情興復發,又弄一火。正是:
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
吳山重複,自覺神思散亂,身體睏倦,打熬不過,飯也不喫,倒身在牀上睡了。金奴見吳山睡著,走下樓到外邊,說與轎伕道:“官人吃了幾杯酒,睡在樓上。二位太保寬坐等一等,不要催促。”轎伕道:“小人不敢來催。”金奴吩咐畢,走上樓來,也睡在吳山身邊。
且說吳山在牀上方閤眼,只聽得有人叫:“吳小官好睡!”連叫數聲。吳山醉眼看見一個胖大和尚,身披一領舊褊衫,赤腳穿雙僧鞋,腰繫著一條黃絲縧,對著吳山打個問訊。吳山跳起來還禮道:“師父上剎何處?因甚喚我?”和尚道:“貧僧是桑萊園水月寺住持,因爲死了徒弟,特來勸化官人。貧僧看官人相貌,生得福薄,無緣受享榮華,只好受些清淡,棄俗出家,與我做個徒弟。”吳山道:“和尚好沒分曉!我父母半百之年,止生得我一人,成家接代,創立門風,如何出家?”和尚道:“你只好出家,若還貪享榮華,即當命夭。依貧僧口,跟我去罷。”吳山道:“亂話!此間是婦人臥房,你是出家人,到此何干?”那和尚睜著兩眼,叫道:“你跟我去也不?”吳山道:“你這禿驢,好沒道理!只顧來纏我做甚?”和尚大怒,扯了吳山便走。到樓梯邊,吳山叫起屈來,被和尚盡力一推,望樓梯下面倒撞下來。撒然驚覺,一身冷汗。開眼時,金奴還睡未醒,原來做一場夢。覺得有些恍惚,爬起坐在牀上,呆了半晌。金奴也醒來,道:“官人好睡。難得你來,且歇了,明早去罷。”吳山道:“家中父母記掛,我要回去,別日再來望你。”金奴起身,吩咐安排點心。吳山道:“我身子不快,不要點心。”金奴見吳山臉色不好,不敢強留。吳山整了衣冠,下樓辭了金奴母子,急急上轎。
天色已晚,吳山在轎思量:白日裏做場夢,甚是作怪。又驚又憂,肚裏漸覺疼起來。在轎過活不得,巴不得到家,吩咐轎伕快走。捱到自家門首,肚疼不可忍,跳下轎來,走入裏面,逕奔樓上。坐在馬桶上,疼一陣,撒一陣,撒出來都是血水。半晌,方上牀。頭眩眼花,倒在牀上,四肢倦怠,百骨痠疼。大底是本身元氣微薄,況又色慾過度。
防禦見吳山面青失色,奔上樓來,吃了一驚,道:“孩兒因甚這般模樣?”吳山應道:“因在機戶人家多吃了幾杯酒,就在他家睡。一覺醒來熱渴,又吃了一碗冷水,身體便覺拘急,如今作起瀉來。”說未了,咬牙寒噤,渾身冷汗如雨,身如炭火一般。防禦慌急下樓請醫來看,道:“脈氣將絕,此病難醫。”再三哀懇太醫,乞用心救取。醫人道:“此病非幹泄瀉之事,乃是色慾過度,耗散元氣,爲脫陽之症,多是不好。我用一帖藥,與他扶助元氣。若是服藥後,熱退脈起,則有生意。”醫人撮了藥自去。父母再三盤問,吳山但搖頭不語。
將及初更,吳山服了藥,伏枕而臥。忽見日間和尚又來,立在牀邊,叫道:“吳山,你強熬做甚?不如早隨我去。”吳山道:“你快去,休來纏我!”那和尚不由分說,將身上黃絲縧縛在吳山項上,扯了便走。吳山攀住牀櫺,大叫一聲,驚醒,又是一夢。開眼看時,父母、渾家皆在面前。父母問道:“我兒因甚驚覺?”吳山自覺神思散亂,料捱不過,只得將金奴之事,並夢見和尚,都說與父母知道。說罷,哽哽咽咽哭將起來。父母、渾家盡皆淚下。防禦見吳山病勢危篤,不敢埋怨他,但把言語來寬解。
吳山與父母說罷,昏暈數次。復甦,泣謂渾家道:“你可善侍公姑,好看幼子。絲行資本,儘夠盤費。”渾家哭道:“且寬心調理,不要多慮。”吳山嘆了氣一口,喚丫鬟扶起,對父母說道:“孩兒不能復生矣,爹孃空養了我這個忤逆子。也是年災命厄,逢著這個冤家。今日雖悔,噬臍何及!傳與少年子弟,不要學我幹這等非爲的事,害了自己性命。男子六尺之軀,實是難得!要貪花戀色的,將我來做個樣。孩兒死後,將身屍丟在水中,方可謝拋妻棄子、不養父母之罪。”言訖,方纔閤眼,和尚又在面前。吳山哀告:“我師,我與你有甚冤仇,不肯放舍我?”和尚道:“貧僧只因犯了色戒,死在彼處,久滯幽冥,不得脫離鬼道。向日偶見官人白晝交歡,貧僧一時心動,欲要官人做個陰魂之伴。”言罷而去。
吳山醒來,將這話對父母說知。吳防禦道:“原來被冤魂來纏。”慌忙在門外街上,焚香點燭,擺列羹飯,望空拜告:“慈悲放舍我兒生命,親到彼處設醮追拔。”祝畢,燒化紙錢。
防禦回到樓上,天晚,只見吳山朝著裏牀睡著。猛然翻身坐將起來,睜著眼道:“防禦,我犯如來色戒,在羊毛寨裏尋了自盡。你兒子也來那裏淫慾,不免把我前日的事,陡然想起,要你兒子做個替頭,不然求他超度。適才承你羹飯紙錢,許我薦拔,我放舍了你的兒子,不在此作祟。我還去羊毛寨裏等你超拔,若得脫生,永不來了。”說話方畢,吳山雙手合掌作禮,灑然而覺,顏色復舊。渾家摸他身上,已住了熱。起身下牀解手,又不瀉了。一家歡喜。復請原日醫者來看,說道:“六脈已復,有可救生路。”撮下了藥,調理數日,漸漸好了。
防禦請了幾衆僧人,在金奴家做了一晝夜道場。只見金奴一家做夢,見個胖和尚拿了一條拄杖去了。
吳山將息半年,依舊在新橋市上生理。一日,與主管說起舊事,不覺追悔道:“人生在世,切莫爲昧己勾當。真個明有人非,幽有鬼責,險些兒丟了一條性命。”從此改過前非,再不在金奴家去。親鄰有知道的,無不欽敬。正是:
癡心做處人人愛,冷眼觀時個個嫌。 覷破關頭邪念息,一生出處自安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