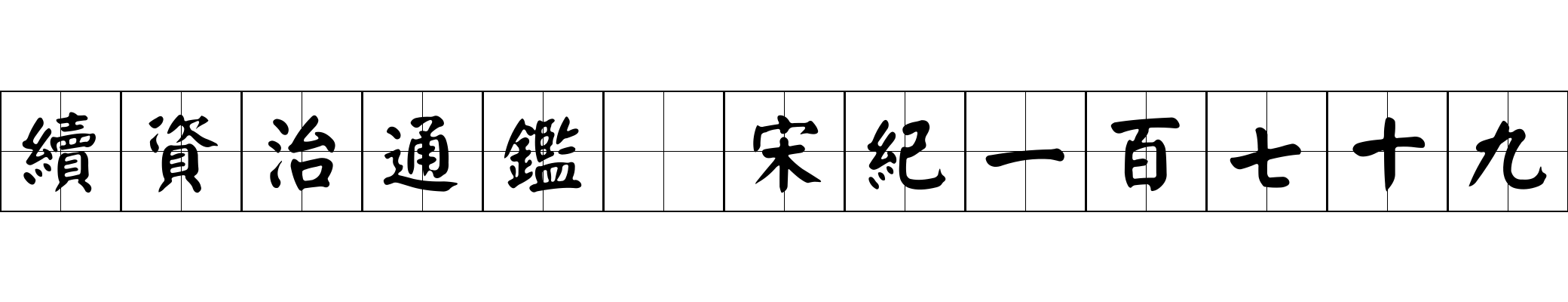續資治通鑑-宋紀一百七十九-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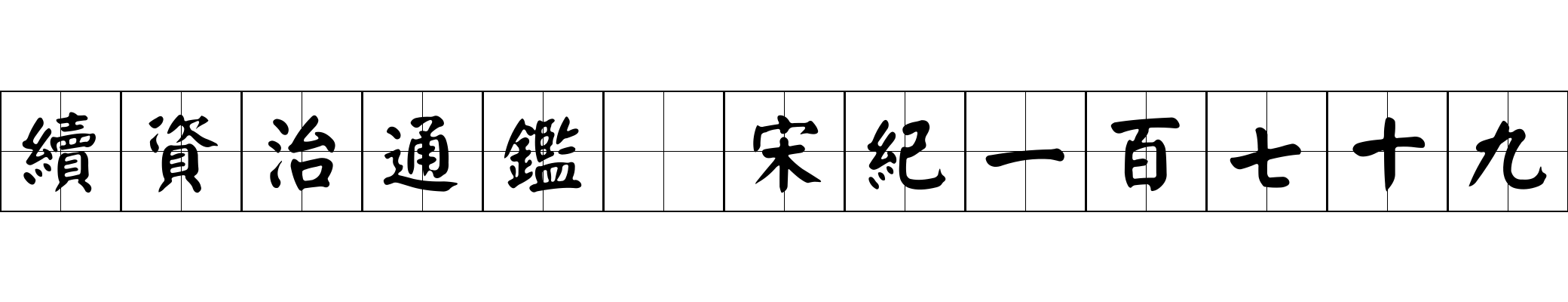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清畢沅撰。此書付刻未及半,畢沅生前僅初刻一○三卷,畢家因貪污遭籍沒而止,書稿散佚,桐鄉馮集梧買得全稿補刻成二百二十卷。《續資治通鑑》跟《資治通鑑》有不少出入,續通鑑大量引用舊史原文,敘事詳而不蕪;僅有取捨剪裁,而無類似溫公的改寫熔鍊,亦無“畢沅曰”等各家史論。《續資治通鑑》作者雖掛名畢沅,然名家錢大昕、邵晉涵、章學誠、洪亮吉、黃仲則等均參預其事,此書實成於衆人之手。梁啓超對該書評價極高,認爲“有畢《鑑》則各家續《鑑》皆可廢也”。
起著雍執徐十月,盡玄黓涒灘七月,凡四年有奇。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鹹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
冬,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皇子憲生。
參知政事常挺罷,尋卒。
蒙古以中書、樞密事多壅滯,言者請置督事官各二人。離鳴上言曰:“官得人,自無滯政。臣職在奉憲,願舉察之,毋爲員外置人也。”己卯,詔:“中書省、樞密院,凡有事民御史臺同奏。”
蒙古立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以參知政事阿哩行中書省事。庚辰,以御史中丞阿哩爲參知政事。
庚寅,蒙古命從臣錄《毛詩》、《論語》、《孟子》。
乙未,蒙古享於太廟。
蒙古中書省言前朝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遣失;詔即以和爾果斯、通呼喇充翰林待制兼起居注。
戊戌,蒙古宮城成。劉秉忠辭領中書省事,許之,爲太保如故。
己亥,詔:“四川州縣鹽酒課再免徵三年。”
十一月,癸丑,樞密院言:“南平鎮撫使韓宣,築城於渝、嘉、開、達、常、武諸州縣,峽州至江陵,水陸有備。宣盡瘁以死,宜視歿於王事加恩。”詔任其子承節郎。
戊午,皇子鍠生。
庚申,襄陽軍攻沿山諸寨,爲阿珠所敗,被殺甚衆。
丙寅,福建安撫使湯漢再辭免,乞祠祿,詔別授職。
辛未,以文武官在選,困於部吏,隆寒旅瑣可閔,命吏部長、貳、郎官日趣銓注,小有未備,特與放行,違者有刑。自是隆寒盛暑,申嚴戒飭。
壬申,行義役法。
癸酉,蒙古御史臺言:“立臺數月,發摘甚多,追理侵欺糧粟近二萬石,錢物稱是。”詔褒諭之。
蒙古朝儀未立,凡遇稱賀,臣庶雜至帳殿前。執法者患其喧擾,不能禁。太常少卿王磐上疏曰:“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入闌入;闌入之罪,由第一門至第三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院籍兩省而下百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進。其越次者,殿中司糾察定罰。不應入而入者,準闌入罪。庶朝廷之禮漸可整肅。”於是議定朝儀。
十二月,戊寅,蒙古以中都、南京、北京州郡大水,免田科。
丙戌,籤書樞密院事包恢罷。
辛卯,以夏貴爲沿江制置使兼知黃州。
戊戌,以汪立信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鹹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
春,正月,丁未,以李庭芝爲兩淮制置大使兼知揚州。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歲鹽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芝築大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銳軍。修學賑饑,民德之如父母。
甲寅,蒙古劉秉忠、博囉,奉詔命趙秉溫、史槓訪前代知禮儀者肄習朝儀。秉忠曰:“二人習之,雖知之莫能行也。”詔許用十人。乃訪問於金故老烏庫哩居貞等,遂偕許衡、徐世隆,稽古典,參時宜,沿情定製而肄習之。秉忠又曰:“無樂以相須,則禮不備。”詔搜訪樂工,依律運譜,被諸樂歌。
戊午,蒙古阿珠率衆侵復州、德安府、京山等處,掠萬人而去。
右丞相葉夢鼎,扼於賈似道,不得行其志,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癸亥,詔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辭不拜。以馬廷鸞參知政事。甲戌,以江萬里參知政事。
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遣史天澤與樞密副使呼喇楚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吏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爲一字城,聯亙諸堡,爲久駐計。
蒙古阿哈瑪特專總財賦,以新立憲臺,言於蒙古主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事何由辦?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廉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者。如阿哈瑪特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事豈可集耶?”阿哈瑪特語塞,乃止。
二月,己丑,蒙古頒行新字,詔曰:“國家創業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輝和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合有字。今文治寢興,字書尚缺,特命國師帕克斯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更號帕克斯巴爲“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爲宗。尋詔諸路蒙古字學各置教授。
三月,丙午,蒙古阿珠自白河率兵圍樊城,遂築堡鹿門山。
己未,詔浙西六郡公田設官督租有差。
辛酉,京湖都統制張世傑,將兵拒蒙古圍樊之軍,戰於赤灘浦,敗績。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賈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嘆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呂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會獲哨騎數人,文煥即以大捷奏,然朝廷實未嘗急於援襄也。
戊辰,以江萬里爲左丞相,馬廷鸞爲右丞相。廷鸞每見文法太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閫,升闢稍越拘攣。賈似道頗疑異己,黥堂吏以泄其憤。
己巳,以馬光祖知樞密院事。
夏,四月,辛巳,蒙古制玉璽大小十紐。
高郵夏世賢,七世義居,癸巳,詔署其門。
甲午,蒙古遣使祀嶽、瀆。
五月,己酉,知樞密院事馬光祖罷,提舉洞霄宮。
乙卯,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程元鳳卒。元鳳之在政府也,一仕者求遷,元鳳謝之。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元鳳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元鳳所不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帝聞訃,震悼,贈少師,諡文清。
蒙古洧川縣達嚕噶齊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逆,置極刑者七人,連坐者五十餘人。開封判官袁裕曰:“達嚕噶齊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罪於民?”議誅首惡一人,餘各杖之有差。部使者錄囚至縣,疑其太寬,裕辨之益力,遂陳其事於中書,刑曹竟從裕議。
六月,庚辰,皇子昰生。
高麗國王禃遣其世子愖朝於蒙古。
秋,七月,辛酉,蒙古制太常寺祭服。
癸酉,蒙古立國子學。降詔,諭宋官民以不欲用兵之意。
蒙古主命諸路決滯獄,釋輕罪。
沿江制置副使夏貴襲蒙古阿珠於新郢,敗績。初,貴率衆援襄、樊,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虛行,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果趣新城,至虎尾州,爲蒙古萬戶解汝楫等舟師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戰艦五十艘皆沒。范文虎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亦爲蒙古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八月,丙申,蒙古詔:“諸路勸課農桑,命中書省採農桑事,列爲條目,仍令提刑按察司與州縣官相風土之所宜,講究可否,別頒行之。”
九月,丙寅,明堂禮成,加上皇太后尊號曰壽和聖福。
辛未,蒙古以呼喇楚、史天澤並平章政事,阿哩爲中書右丞、行河南等路中書省事,賽喜諤德齊行陝西五路、西蜀、四川中書省事。
蒙古主歸自上都。
高麗權臣林衍廢其主禃而立禃弟安慶公淐。八月,己卯,蒙古遣使往其國詳問,條具以聞。
冬,十月,蒙古劉秉忠等奏朝儀已定,請備執禮員;詔丞相安圖擇蒙古宿衛士可習容止者百餘人肄之。己卯,定朝儀服色。
蒙古鄂爾多布哈、李諤還自高麗,以其臣金方慶至,奉權國王淐表,訴國王王禃遘疾,令弟淐權國事。丁亥,詔遣兵部侍郎赫迪、淄萊總管判官徐世雄召禃、淐及林衍俱赴闕,命國王特默格以兵壓其境,趙璧行中書省於東京。仍降詔諭高麗國軍民。
十一月,癸卯,高麗都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城附於蒙古。丁未,發兵往定。高麗國王禃遣其臣樸烋從赫迪入朝,表稱受詔已復位,尋當入覲。乃命止誅林衍,餘無所問。
庚午,蒙古敕:“諸路鰥寡廢疾之人,月給米二斗。”
先是蒙古主以安南入貢不時,以同籤土番經略使張庭珍爲朝列大夫、安南國達嚕噶齊,由吐蕃、大理至安南。世子光昺立受詔,庭珍責之曰:“皇帝不欲以汝土地爲郡縣,而聽汝稱籓,遣使喻旨,德至厚也。王猶與宋爲脣齒,妄自尊大!今百萬之師圍襄陽,拔在旦夕,席捲渡江,則宋亡矣,王將何恃?且雲南之兵,不兩月可至汝境,覆汝宗祀有不難者,其審謀之!”光昺惶恐,下拜受詔。既而語庭珍曰:“天子憐我,而使者多無禮。汝官朝列,我王也,相與抗禮,古有之乎?”庭珍曰:“有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光昺曰:“汝過益州,見雲南王,拜否?”庭珍曰:“雲南王,天子之子;汝蠻夷小邦,特假以王號,豈得比雲南王?況天子命我爲安南之長,位居汝上耶?”光昺曰:“大國何索我犀象?”庭珍曰:“貢獻方物,籓臣職也。”光昺無以對,益慚憤,使衛兵露刃環立以恐庭珍,庭珍解所佩刀,坦臥室中,曰:“聽汝所爲。”光昺及其臣皆服。至是遣使隨庭珍入貢。
蒙古築新城於漢水西。
十二月,癸酉,少師、衛國公呂文德卒。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爲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致仕。卒,諡武忠。賈似道以其婿范文虎爲殿前副都指揮使,總禁兵。
是歲,蒙古益都、淄、萊大水,河南、河北、山東諸郡蝗,恩州、曹州、開元、東昌、大名、東平、濟南、高唐、固安飢,賑之。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鹹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
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爲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聞庭芝至,文虎遺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於京閫,事成則功歸於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爲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以取旨未至爲辭。
初,蒙古主命劉秉忠、張文謙、許衡定官制,衡考古今分並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籓、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至是奏上之。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定爲諮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於蒙古主前,蒙古主曰:“衡言是也。”
丙午,蒙古左丞相耶律鑄、右丞相廉希憲並罷。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伊贊瑪鼎,爲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爲言,蒙古主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伊贊瑪鼎耶?”對曰:“不釋伊贊瑪鼎,臣等亦未聞此詔。”蒙古主怒曰:“汝等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忝爲宰相,有罪當罷退。”蒙古主曰:“但從汝言。”即與鑄同罷。
蒙古立尚書省,罷制國用使司,以平章政事呼圖達爾爲中書左丞相,國子祭酒許衡爲中書左丞,制國用使阿哈瑪特平章尚書省事。
阿哈瑪特多智巧,以功利自負。蒙古主急於富國,試以事,頗有成績,又見其與史天澤爭辨,屢有以詘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專愎益甚。尚書省既立,詔:“凡銓選各官,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尚書諮中書,中書聞奏。”阿哈瑪特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諮中書。安圖以爲言,蒙古主令問阿哈瑪特,阿哈瑪特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圖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哈瑪特。”蒙古主從之。阿哈瑪特遂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爲常額。
庚戌,以高達爲湖北安撫使、知鄂州,孫虎臣起復淮東安撫副使、知淮安州。賈似道迫於人言,故起用達;達懷宿憾,不爲似道用。
甲寅,高麗國王禃遣使詣蒙古言:“臣已復位,今從七百人入覲。”詔令從四百人來,餘留之西京。詔改西京曰東寧府,畫慈悲嶺爲界,以莽賚扣爲安撫高麗使,率兵戍其西境。
辛西,頒《成天曆》。
丙寅,以廣東經略安撫使陳宗禮籤書樞密院事,吏部尚書趙順孫同籤書樞密院事。
故事,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爲之,遇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爲之。宗禮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秋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丁卯,帝制《字民》、《牧民》二訓,以戒百官。
戊辰,左丞相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爲優,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時王應麟起爲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上言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議不容緩。朝廷方從容如常時,事幾一失,豈能自安?”賈似道謀復逐之,會應麟以憂去。
二月,辛未朔,蒙古前中書右丞相巴延爲樞密副使。
甲戌,蒙古築昭應宮於高梁河。
丙子,蒙古主御行宮,觀劉秉忠、博囉、許衡及太常卿徐世隆所起朝儀,大悅,舉酒賜之。
丁丑,蒙古以歲飢,罷修築宮城役夫。
壬辰,蒙古立司農司,以參知政事張文謙爲卿,設四道巡行勸農司。文謙請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等禮。阿哈瑪特議拘民間鐵,官鑄農器,高其價以配民,創立行戶部於東平、大名以造鈔,及諸路轉運使干政害民;文謙悉極論罷之。
乙未,襄陽出步騎萬餘人,兵船百餘艘,攻蒙古萬山堡,爲萬戶張弘範等所敗。
高麗國王禃朝於蒙古。蒙古令國王特默裕舉軍入高麗舊京,以托克托多勒、焦天翼爲其國達嚕噶齊,護送禃歸國。仍下詔:“林衍廢立,罪不可赦;安慶公淐,本非得已,在所寬宥。有能執送衍者,雖其黨,亦必重增官秩。”
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蒙古改諸路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
癸丑,詔曰:“吏以廉稱,自古有之。今絕不聞,豈不自章顯而壅於上聞歟?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將顯擢焉。”
甲寅,蒙古主如上都。
戊午,蒙古阿珠與劉整上言:“圍守襄陽,必當以教水軍、造戰艦爲先務。”詔許之。於是造戰艦五千艘,日練水軍七萬人,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
蒙古平章尚書省事阿哈瑪特,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中書左丞許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呼遜有同籤樞密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慮其反耶?”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阿哈瑪特,阿哈瑪特由是怨衡,欲以事中之。衡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
四川制置司遣將修合州城,蒙古立武勝軍以拒之。總帥汪惟正,臨嘉陵江作柵,扼其水道,夜懸燈柵間,編竹爲籠,中置火炬,順地勢轉走,照百步外,以防不虞。南師知有備,不敢逼。
廉希憲既罷,蒙古主念之,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侍臣以讀書對。蒙古主曰:“讀書固朕所教,然讀之而不肯用,多讀何爲?”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阿哈瑪特因讒之曰:“希憲日與妻怒宴樂爾。”蒙古主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飲!”阿哈瑪特慚而退。希憲有疾,醫言須用沙糖,家人求於外,阿哈瑪特與之二斤,希憲卻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受奸人所與求活也。”蒙古主聞而遣賜之。
夏,四月,戊寅,以文天祥兼崇政殿說書、真學士院,尋罷。
賈似道以去要君,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製,相承必先呈稿於宰相,天祥獨不循此例。似道見制,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億故事,亟求解職,遷祕書監,似道又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數被斥,乃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
壬午,蒙古檀州隕黑霜二夕。
己丑,蒙古高麗行省奏言:“高麗林衍死,其子惟茂擅襲令公位,爲尚書宋宗禮所殺。島中民皆出降,已還之舊京。衍黨裴仲孫等復集餘衆,立王禃庶族承化侯爲王,竄入珍島。”
五月,辛丑,以吳革爲沿江制置宣撫使。
癸卯,四川制置司遣都統牛宣,與蒙古陝西籤省伊蘇岱爾、嚴忠範等戰於嘉定、重慶、釣魚山、馬湖江,皆敗,宣爲蒙古所獲,遂破三寨。
丁未,蒙古以同知樞密院事哈達爲平章政事。
丙辰,蒙古尚書省言:“諸王遣使取索諸物及鋪馬等事,請自今並以文移,毋得口傳教令。”從之。
蒙古改宣徽院爲光祿司,仍以烏珍充使。
六月,庚午,詔:“《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天下士子宜肄其文。”
庚辰,皇子憲薨。
丙申,蒙古立籍田於大都之東南郊,從張文謙之言也。
蒙古禁民擅入宋境剽掠。
秋,七月,復開州,更鑄印給之。
蒙古都元帥伊蘇岱爾侵光州。
八月,戊辰朔,蒙古築環城以逼襄陽。
壬辰,詔:“郡縣行推排法,虛加寡弱戶租,害民爲甚。其令各路監司詢訪,亟除其弊。”
詔賈似道入朝不拜。每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庭始坐。癸巳,詔十日一朝。
時蒙古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倡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據地鬥蟋蟀,所押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餘玠有玉帶,已殉葬,發冢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圍已三年,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它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蘭溪處士金履祥,以襄、樊之師日急,進“牽制搗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不攻而自解,聞者以爲迂闊。然履祥所敘海舶經由之郡縣,以及巨洋、別塢,難易遠近,後驗之無或爽者。
九月,庚戌,以黃萬石爲沿海制置使。
冬,十月,丁丑,詔:“范文虎總統殿前司兩淮諸軍,往襄、樊備禦,賜犒師錢一百五十萬。”
台州大水;己卯,詔發倉米賑之。
甲申,以陳宗禮、趙順孫兼權參知政事。
乙酉,蒙古享於太廟。
己丑,蒙古主歸自上都,議立三省。侍御史高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改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於一堂,速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不如一省便。”蒙古主深然之。
閏月,己酉,以安吉州水,免公田租。
十一月,丁丑,以嘉興、華亭兩縣水,免公田、民田租。
陳宗禮疏言:“國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也。”
庚辰,詔犒賞襄、郢屯戍將士。
癸未,蒙古命西夏管民官禁僧徒冒據民田。
壬辰,蒙古申明勸課農桑賞罰之法。
乙未,陳宗禮罷,尋卒。
十二月,丙申朔,蒙古改司農司爲大司農司,添設巡行勸農使、副各四員,以御史中丞博囉兼大司農卿。安圖言博囉以臺臣兼領,前無此例,蒙古主曰:“司農非細事,朕深喻此,故令博囉總之。”尋以都水監隸大司農司。
蒙古以趙良弼爲祕書監、充國信使,使日本。
丁未,金齒、驃國二部酋長內附於蒙古。
蒙古以董文炳爲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接壤,鎮兵仰內郡餉運。有詔和糴本部,文炳命收州縣所移文。衆懼違詔旨,文炳曰:“第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者,三不可。”蒙古主大悟,罷之。
蒙古張弘範言於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御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者相繼,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速斃之道也。”天澤從之,遂城萬山,徙弘範於鹿門。自是襄、樊道絕,糧援不繼。
是歲,蒙古以應昌府及山東、淄、萊路飢,賑之。南京、河南兩路旱,減其賦。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鹹淳七年(元至元八年)
春,正月,乙丑朔,封皇子昰爲建國公。
召湯漢、洪天賜,不至。
詔戒貪吏。
己卯,蒙古以同籤河南行省事阿爾哈雅參知尚書省事。丙戌,蒙古高麗安撫阿哈等略地珍島,與林衍餘黨遇,多所亡失。中書省臣言,諜知珍島餘糧將竭,宜乘弱攻之;詔不許,令巡視險要,常爲之備。
壬辰,蒙古敕:“諸鰥寡孤獨疾病不能自薦者,官給廬舍、薪米。”
二月,丁酉,蒙古發中都、真定、順天、河間、平、灤民二萬八千餘人築宮城。
己亥,蒙古罷諸路轉運司入總管府,移陝蜀行中書省於興元。
癸卯,蒙古以東京行省事趙璧爲中書右丞。
蒙古四川行省伊蘇岱爾言:“比因饑饉,盜賊滋多。若不顯戮一二,無以示懲。”敕中書詳議。安圖奏曰:“強竊盜賊,一皆處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
甲辰,蒙古命呼圖達爾持詔招諭高麗林衍餘黨裴仲孫。
乙巳,蒙古大理等處宣慰都元帥保赫鼎、王傅庫庫岱等,謀毒殺皇子云南王呼格齊,事覺,並伏誅。
辛酉,蒙古敕:“凡訟而自匿及誣告人罪者,以其罪罪之。”
三月,乙丑,蒙古增置河東、山西道按察司,改河東、陝西道爲陝西、四川道,山北東、西道爲山北、遼東道。
甲申,蒙古主如上都。
蒙古中書左丞許衡上疏論阿哈瑪特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以老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乙酉,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以爲得師。
蒙古侍講學士圖克坦公履欲奏行科舉,知蒙古主於釋氏重教而輕禪,乃言懦亦有之;科舉類教,道學類禪。蒙古主怒,召姚樞、許衡與宰臣廷辨。董文忠自外入,蒙古主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文忠對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爲詩賦,何關修身,何益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謂道學!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欲行其說,故以是上惑聖聽。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國之本也。”事遂止。
是月,以和州、吉州、無爲、鎮巢、安慶諸州、平江府飢,賑之。
夏,四月,壬寅,蒙古經略司實都言:“高麗逆黨裴仲孫,稽留使命,負固不服,請與浩爾齊、王國昌分道進討。”蒙古主從之,命高麗籤軍徵珍島。
戊午,范文虎與蒙古阿珠等戰於湍灘,軍敗,統制硃勝等百餘人爲蒙古所獲。
五月,乙丑,蒙古以東道兵圍守襄陽,命賽音諤德齊、鄭鼎率諸將水陸並進,以趣嘉定;汪良臣、彭天祥出重慶,扎拉布哈出瀘州,立吉思出汝州,以牽制之。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辛未,蒙古分大理國三十七部爲三路,以大理八部蠻新附,降詔撫諭。
壬申,蒙古造內外儀仗。
己卯,蒙古以史天澤平章軍國重事。
蒙古實都言:“珍島賊徒敗散,餘黨竄入耽羅。”
乙酉,賜禮部進士張鎮孫以下五百二人及第、出身。
六月,甲午,蒙古敕樞密院:“凡軍事徑奏,不必經由尚書省;其幹錢糧者議之。”
丙申,以諸暨大雨、暴風,發米賑被水之家。
癸卯,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珠夾漢東、西爲陣,別令一軍趣會丹灘,擊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是月,淮東制置使印應雷城五河口,命鎮江轉米十萬石貯新城,賜名安淮軍。蒙古統軍司庫春、董文炳來爭,不能得。
秋,七月,壬戌朔,蒙古設回回司天臺官屬。
壬午,四川制置使硃禩孫言:“五月以來,江水凡三泛溢,自嘉而渝,漂盪城壁,樓櫓圮壞。又,嘉定地震者再,被災害爲甚。乞賜黜罷,上答天譴。”詔不允。
乙酉,襄陽遣將來興國攻蒙古百丈山營,爲阿珠所敗,追至湍灘,殺傷二千餘人。
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壬子,蒙古主歸自上都。
蒙古遷成都統軍司於眉州。
己未,蒙古聖誕節,初立內外儀仗及雲和署樂位。
蒙古東川統軍司攻銅鈸寨,守寨官李慶降。蒙古以慶知梁山軍事。
九月,甲戌,蒙古太廟柱壞,御史劾都水劉晸監造不敬,晸以憂卒。張易請先期告廟,然後完葺;從之。
乙亥,以湯漢、洪天錫屢辭召命,並權華文閣學士,仍予祠祿。
壬午,統制範廣攻膠州,爲蒙古千戶蔣德所敗,廣被擒。
癸未,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敝,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敕有司:“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己丑,皇子生。
冬,十月,癸巳,蒙古大司農司言高唐州達嚕噶齊呼圖納、州尹張庭瑞、同知陳思濟勸課有效,陝縣尹王仔怠於勸課,宜加黜陟以示勸懲;從之。
丙申,嗣秀王與澤卒,追封臨海郡王。
丁酉,蒙古享於太廟。
十一月,壬戌,蒙古罷諸路交鈔都提舉司。
己巳,湯漢以端明殿學士致仕。
乙亥,蒙古建國號曰大元,取《易》“大哉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丙戌,元置四川行省於成都。
元萬安閣成。
十二月,辛卯朔,元宣徽院請以闌遺戶淘金,元主曰:“姑止,毋重勞吾民也。”
辛亥,初置士籍。
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籍士人,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跡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鈁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其謬至此。
初,陳仲微爲江西提刑,忤似道,罷去,至是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諷言者論罷其官。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鹹淳八年(元至元九年)
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惟崇儉必自宮禁始,自今宮禁敢以珠翠、銷金爲首飾服用,必罰無赦。臣庶之家,咸宜體恤工匠,犯者亦如景祐制,必從重典。”
又詔曰:“有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之爲吏者長子孫,則其遺意也。比年吏習偷薄,人懷一切,計日待遷,事未克究,又望而之它。吏胥狎玩,竊弄官政,吾民莫敕焉!繼自今,內之郎曹,外之牧守以上,更不數易。其有治狀昭著,自宜大擢。”時有識者皆以襄、樊爲憂,而詔書徒託空言,泄泄如平時。
甲子,元井尚書省入中書省,平章尚書阿哈瑪特、張易併爲中書平章政事,參知尚書省事張惠爲中書左丞,參知尚書省事李堯諮、敏珠爾丹併爲參知中書政事。罷給事中、中書舍人、檢正等官,仍設左右司。省六部爲四,改稱中書。
辛未,皇子昺生。
庚辰,元改北京、中興、四川、河南四路行尚書省爲行中書省,京兆復立行省。
壬午,元改山東東路都元帥府統軍司爲行樞密院,以伊蘇爾岱、庫春併爲副使。
己丑,端明殿學士、致仕湯漢卒,諡文清。
二月,庚寅朔,元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同日本二十六人,至中都求見。
壬辰,元改中都爲大都。
癸巳,故左丞相謝方叔卒。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玩好、丹劑壽其君,爲時論所鄙。
前知台州趙子寅,死無所歸,詔:“特贈直祕閣,給沒官宅一區、田三百畝,養其遺孤,以旌廉吏。”
甲元,元命阿珠典蒙古軍,劉整、阿爾哈雅典漢軍。
庚子,元建中書省署於大都。
戊申,元始祭先農,如祭社之儀。
元詔諸路開浚水利。
元主如上都。
三月,乙丑,元主諭中書省,日本使人速議遣還。安圖言:“趙良弼請移金州戍兵,勿使日本妄生疑懼。臣等以爲金州戍兵,彼國所知,若復移戍,恐非所宜。但開諭來使,此戍乃爲耽羅暫設,爾等不須疑畏也。”元主稱善。
甲戌,元阿珠、劉整、阿爾哈雅破樊城外郛,守將堅閉內城,阿珠等增築重圍以困之。
元賑濟南路飢。
夏,四月,戊子,利路安撫張珏創築宜勝山城。
元庫春侵漣州,破射龍溝、五港口、鹽場、白頭、河城堡。
甲寅,元賑大都路飢。
五月,辛巳,元敕修築都城,凡費悉從官給。
乙酉,元宮城初建東、西華、左、右掖門。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城中稍有積粟,乏鹽、薪、布帛。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置蠟書於髻,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荊、郢援救。”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鉤爲薪,泅者被獲,郢、鄧之路亦絕。
至是詔京湖制置使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闖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每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溯流發舟。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槍、火砲、熾炭、巨斧、勁弓,夜漏下三刻,起碇行,以紅燈爲號,貴率先,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元舟師蔽水,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陽。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逆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樑。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埋之。
六月,甲午,高麗告飢,元命轉東京米以賑之。
丙申,徙皮龍榮于衡州。龍榮,舊宮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爲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龍榮少有智略,性伉直,故卒爲似道所擯死。
丁酉,以吏部尚書章鑑同籤書樞密院事。
發錢十萬緡,命京湖制置司糴米百萬石,轉輸襄陽積貯。
乙巳,以家鉉翁兼權知紹興府、浙東安撫提舉司事,以唐震爲浙西提點刑獄。鉉翁,眉州人;震,餘姚人也。
辛亥,臺臣言江西推排田結局已久,舊設都官團長等虛名尚在,佔B138常役,爲害無窮;又言廣東運司銀場病民;詔俱罷之。
高麗國王禃請元討耽羅餘寇。
秋,七月,丁巳朔,元河南省臣言:“往歲徙民實邊屯耕,以貧苦悉散還家。今唐、鄧、察、息、徐、邳之民,愛其田廬,仍守故屯,願以絲銀准折輸糧,而內地州縣轉粟餉軍者,反厭苦之。臣議今歲沿邊州郡,驗其戶數,俾折鈔就沿邊和糴,庶幾交便。”從之。
壬午,元和爾果斯言蒙古字設國子學,而漢官子弟未有學者,及官府文移猶有輝和爾字。詔:“自今凡詔令並以蒙古字行,仍遣百官子弟入學。”
元董文炳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於淮西,築正陽兩城,夾淮相望,以綴襄陽。
元大司農司以安肅州被徐水之害,議奪大故道,決使東入清苑。然地勢不便,徒使害及清苑而故道必不可奪,清苑縣尹耶律伯堅陳其形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遂得已。清苑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爲磑,民以失利訴,伯堅命毀磑;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磑;仍以事聞於省部,著爲定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