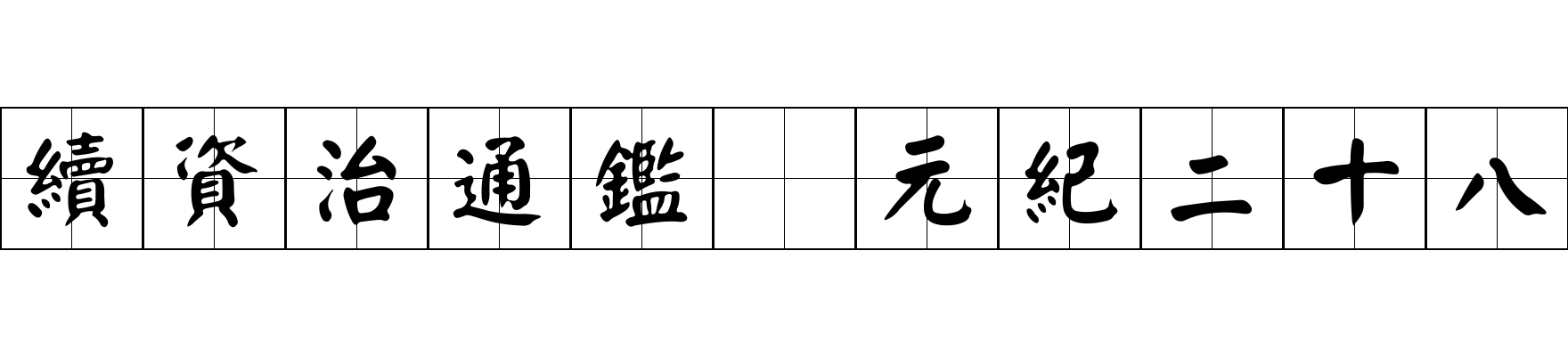續資治通鑑-元紀二十八-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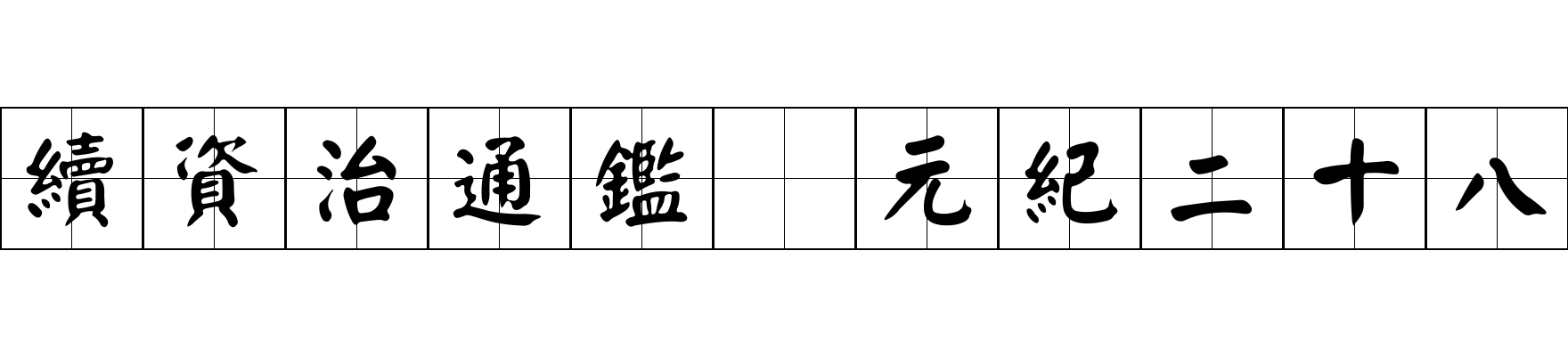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清畢沅撰。此書付刻未及半,畢沅生前僅初刻一○三卷,畢家因貪污遭籍沒而止,書稿散佚,桐鄉馮集梧買得全稿補刻成二百二十卷。《續資治通鑑》跟《資治通鑑》有不少出入,續通鑑大量引用舊史原文,敘事詳而不蕪;僅有取捨剪裁,而無類似溫公的改寫熔鍊,亦無“畢沅曰”等各家史論。《續資治通鑑》作者雖掛名畢沅,然名家錢大昕、邵晉涵、章學誠、洪亮吉、黃仲則等均參預其事,此書實成於衆人之手。梁啓超對該書評價極高,認爲“有畢《鑑》則各家續《鑑》皆可廢也”。
起重光單閼正月,盡玄黓執徐六月,凡一年有奇。
◎至正十一年
春,正月,庚申,命江浙行省左丞博囉特穆爾討方國珍。
丁卯,蘭陽縣有紅星大如鬥,自東南墜西北,其聲如雷。
己卯,命綽斯戩提調大都留守司。
是月,清寧殿火,焚寶玩萬計,由宦官薰鼠故也。
二月,命遊皇城。
初,世祖至無七年,以帝師帕克斯巴之言,於大明殿御座上置白傘蓋一頂,用素緞泥金書梵字於其上,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利。自後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殿啓建白傘蓋佛事,與衆祓除不祥。中書移文諸司,撥人舁監壇漢關羽神轎及供應三百六十壇幢幡、寶蓋等,以至大樂鼓吹,番部細樂,男女雜扮隊戲;凡執役者萬餘人,皆官給鎧甲、袍服、器仗,俱以鮮麗整齊爲尚,珠玉錦繡,裝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餘裏,都城士女聚觀。先二日,於西鎮國寺迎太子游四門,舁高塑像,具儀仗入城。十四日,帝師率梵僧五百人,於大明殿內建佛事,至十五日,請傘蓋於御座,奉置寶輿,諸儀衛導引出宮,至慶壽寺,具素食;食罷,起行,從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載紅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於玉德殿門外搭金脊吾殿綵樓以觀覽焉。事畢,送傘蓋,復置御座上。帝師、僧衆作佛事,至十六日罷散,謂之遊皇城,歲以爲常。至是命下,中書省臣以其非禮,諫止之,不聽。
立湖南元帥分府於寶慶路。
三月,庚戌,立山東元帥分府於登州。
丙辰,親策進士八十三人,賜多勒圖、文允中等及第、出身。
壬戌,徵建寧處士彭炳爲端本堂說書,不至。
是月,遣使賑湖南、北被寇人民,死者鈔五錠,傷者三錠,毀所居屋者一錠。
是春,成遵與圖嚕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裏,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遍閱史籍,博採輿論,以爲河之故首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其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托克托先入賈魯之言,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挽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爲河間鹽運使。
夏,四月,壬午,詔開黃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尚書爲總治河防使,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十五萬,廬州等戍十八翼軍二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齊等口,又自黃陵西至楊青村,合於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仍命中書右丞玉樞呼爾圖哈、同知樞密院事哈斯以兵鎮之。
冀寧路屬縣多地震,半月乃止。
乙酉,詔加封河瀆神爲靈源神祐靈濟王,乃重建河瀆及西海神廟。
丁酉,孟州地震,有聲如雷,圮民屋,壓死者甚衆。
乙巳,彰德府雨雹,形如斧,傷人畜。
是月,罷沂州分元帥府,改立兵馬指揮使司,復分司於膠州。
帝如上都。
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辛亥,潁州妖人劉福通爲亂,以紅巾爲號,陷潁州。初,欒城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徒廣平永年縣。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鬱、王顯忠、韓雅爾復鼓妖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福通等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爲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時謂之“紅軍”,亦曰“香軍”。
壬申,命同樞密院事圖克齊領阿蘇軍六千並各支漢軍討之,授以分樞密院印。圖克齊者,回回部人也,素號精悍,善騎射,至是與河南行省徐左丞俱進軍。二將皆耽酒色,軍士但以剽掠爲事,剿捕之方,漫不加省。圖克齊望見紅軍陣大,揚鞭曰:“阿布,阿布。”阿布者,譯言走也,於是所部皆走,淮人傳以爲笑。其後圖克齊死於上蔡,徐左丞爲朝廷所誅,阿蘇軍不習水土,病死者過半。
先是庚寅歲,河南、北童謠雲:“石人一隻眼,挑運黃河天下反。”及賈魯治河,果於黃陵岡掘得石人一眼,而汝、潁盜起,竟如所言。
六月,發軍一千,從直沽到通州,疏浚河道。
是月,劉福通據硃皋,攻破羅山、真陽、確山,遂犯舞陽、葉縣。
前監察御史藁城張桓,避亂之確山,賊久知桓名,襲獲之,羅拜,請爲帥,弗聽。囚六日,擁至渠魁前,桓直趨據榻坐,與之抗論逆順。其徒捽桓起跪,桓仰天大呼,詈叱彌厲,且屢唾賊面。賊猶不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怒汝死。”桓真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殺之,年四十八。賊後語人曰:“張御史真鐵漢,害之可惜。”事聞,贈禮部尚書,諡忠潔。
丞相托克託議軍事,每回避漢人、南人;方入奏事,目顧同列韓伯高、韓大雅隨後來,遽令門者勿納,入言曰:“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勿令詿誤。”於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軍者矣。
方國珍兄弟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博囉特穆爾兵至大閭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博囉特穆爾被執,反爲國珍飾辭上聞。朝廷覆命大司農達實特穆爾、江浙參政樊執敬、浙東廉訪使董守愨同招諭國珍,至黃岩,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小樓。紹興總官臺哈布哈欲命壯士襲殺之,達實特穆爾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耶?”乃止。仍檄臺哈布哈親至海濱,散其徒衆,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八月,丁丑朔,中興路地震。
丙戌,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陷徐州。
李二號“芝麻李”,以歲飢,其家惟有芝麻一倉,盡以濟人,故得此名。時江工大興,人心不安,芝麻李與其社長趙君用謀曰:“潁上兵起,官軍無如之何,此男子取富貴之秋也。”君用曰:“我所知,惟城南老彭,其人勇悍有膽略,不得其人,不可舉大事,我當爲汝致之。”即訪其家,見老彭,諷以起事,老彭曰:“其中有芝麻李乎?”曰:“有。”老彭即欣然從之,與俱見芝麻李,共得八人,歃血而盟。是夕,僞爲挑河夫,倉皇投徐州城宿,四人在內,四人在外。夜四更,城內火發,城外亦舉火應之,奪守門軍仗,斬關而入,內外呼噪。民久不見兵革,一時驚懼,皆束手聽命。天明,豎大旗,募人爲軍,從之者十餘萬人,四出略地,徐州屬縣皆下。
是月,帝至自上都。
蘄州羅田人徐壽輝舉兵爲亂,亦以紅巾爲號。壽輝體貌魁岸,木強無他能,以販布爲業,往來蘄、黃間,因燒香聚衆。
初,袁州慈化寺僧彭瑩玉,以妖術惑人;其徒周子旺,因聚衆欲作亂,事覺,江西行省發兵捕誅子旺等。瑩玉走至淮西,匿民家,捕不獲。既而黃州麻城人鄒普勝,復以其術鼓妖言,遂起兵爲亂。以壽輝貌異於衆,乃推以爲主。沔陽陳友諒往從之。友諒,漁家子,略通文義,嘗爲縣小吏,非其好也。有術者相其祖墓當大貴,友諒心竊喜,至是欲從亂,其父普才曰:“奈何爲滅族事?”友諒曰:“術者之言驗矣。”遂從壽輝。
九月,壬子,丞相托克託奏以其弟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知樞密院事,及衛王庫春格爾總率大軍,出征河南妖寇;詔從之。
壬戌,詔以高麗國王布答實裏之弟巴延特穆爾襲其王封。布答實裏本名禎,巴延特穆爾本名祺。時國王王昕無道,禎之庶子也,立三年,遇鴆卒,國人請立禎弟祺,遂從之。
是月,劉福通陷汝寧府及息州、光州,衆至十萬。
徐春輝陷蘄水縣及黃州路,衛王庫春格爾與其二子帥師擊之,爲壽輝將倪文俊所敗,二子被獲。文俊,沔陽漁家子也。
冬,十月,癸未,命知樞密院事老章以兵同額森特穆爾討河南妖寇。
辛卯,立中書分省於濟寧。
癸卯,以宗王神保克復睢寧、虹縣有功,賜金帶一,從徵者賞銀有差。
是月,天雨黑子於饒州,大如黍菽。
徐壽輝據蘄水爲都,國號天完,僭稱皇帝,建無曰治平,以鄒普勝爲太師。
十一月,己酉,有星孛於西方,見於婁、胃、昴、畢之間。
壬子,中書省言:“河南、陝西腹裏諸路,供給繁重,調兵討賊,正當春首耕作之時,恐農民不能安於田畝,守令有失勸課。宜委通曉農事官員,分道巡視,督勒守令,親詣鄉村,省諭農民,依時播種,務要人盡其力,地盡其利。其有曾經盜賊、水患、供給之處,貧民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之。仍命總兵官禁止屯駐軍馬,毋得踏踐,以致農事廢弛。”從之。
以資政院使多爾濟巴勒爲中書平章政事。
多爾濟巴勒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仗節死義,不污於寇,宜首旌之以勸來者;又言宜守荊襄、湖廣以絕後患。又數論祖宗用之兵,非專於殺人,蓋必有其道焉,今倡亂者止數人,顧乃盡坐中華之民爲叛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忤丞相托克託意。時托克托倚信左司郎中汝中柏、員外郎拜特穆爾兩人,因擅權用事。而多爾濟巴勒正色立朝,無所附麗,適陝州危急,因出爲陝西行臺御史大夫。
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賈魯,以四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是月,水土工畢,河復故道,南匯於淮,又東入於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魯以《河平圖》獻,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賞賚金帛;都水監及宣力諸臣三十七人,皆予遷秩。敕翰林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以旌托克托勞績,具載魯功,宣付史館。並贈魯先臣三世,賜托克托世襲達爾罕之號,仍賜淮安路爲其食邑。
玄既撰《河平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
其略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浚,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浚;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浚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御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治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堤,有截河堤,有護岸堤,有縷水堤,有石船堤。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藐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河塞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嘗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堤,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得,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氵衆也。”
又曰:“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涌入決河,困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樁,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將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經鐵錨於上流硾之水中,又以竹絙絕七八百尺者,系兩岸大橛上,每絙硾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佈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楮拄,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捶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沈,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以草木等物,隨宜填垛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址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
“魯嘗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並,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居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十二月,己卯,立河防提舉司,隸行都水監。
丁酉,命托克托於淮安立諸路打捕鷹房、民匠、錢糧總管府。
辛丑,額森特穆爾覆上蔡縣,擒韓雅爾等送京師,誅之。
是歲,盜蔓延於江浙;江西之饒、信、徽、宣、鉛山、廣德,浙西之常、湖、建德,所在不守。江浙行省平章慶通分遣僚佐往督師,以次克復。既乃令長吏按視民數,詿誤者悉置不問;招徠流離,發官粟以賑之。
蘄、黃賊造船北岸,銳意南攻。九江、江州路總管李黼,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不報。黼嘆曰:“吾不知死所矣!”乃椎牛享士,激忠義以作其氣,數日之間,紀綱初立。
廬州盜起,淮西廉訪使陳思廉言於宣讓王特穆爾布哈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胄,鎮撫淮甸,豈得坐視!思謙願與王戮力殄滅之。且王府屬集賽人等,數亦不少,必有能摧鋒陷陣者。”王曰:“此吾責也。但鞍馬、器械未備,奈何?”思謙括官民馬,置兵甲,不日而集,分道並進,遂擒渠賊,廬州平。既而潁寇將渡淮,思謙又言於王曰:“潁寇東侵,亟調芍陂屯卒用之。”王曰:“非奉詔不敢調。”思謙言:“非常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思謙坐之。”王感其言,從之。
其侄立本,爲屯田萬戶,召語曰:“吾祖宗以忠義傳家,汝之職,乃我先人力戰所致。今國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以圖報效,庶無負朝廷也。”尋召入爲集賢侍講學士,修定《國律》。
濟寧路總管董摶霄,奉詔從江浙平章嘉琿進徵安豐,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
時硃皋、固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名寨及芍陂屯田軍,摶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硃皋。官軍屯硃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基虛實。夜,縛浮橋於淝水,既渡,賊始覺。賊數萬據磵南,官軍渡者,輒爲其所敗;摶霄乃麾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敵。摶霄忽躍馬渡磵,揚言於衆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復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遂復安豐。摶霄,磁州人也。
方國珍兵起,江浙行省檄前沿海上副萬戶舒穆嚕宜遜守溫州,宜遜即起任其事。已而閩寇犯處州,復檄宜遜以兵平之,以功升浙東宣慰使,復分府於台州。頃之,處之屬縣,山寇並起,宜遜復奉省檄往討之,至則築處州城爲禦敵計。宜遜,其先遼人也。
太傅阿嚕圖出守和林,尋卒。
◎至正十二年
春,正月,丙午朔,詔印造中統元寶交鈔一百九十萬錠,至元鈔十萬錠。
戊申,竹山縣賊陷襄陽路,同知額森布哈等驚潰。達魯噶齊博羅特穆爾領義兵二百人,且戰且引,至監利縣,遇沔陽府達嚕噶齊耀珠等軍。時濱江有船千餘,乃糾合諸義兵、丁壯、水工五千餘人,畀以軍號,給刀槊,具哨馬五十,水陸繼進。比至石首縣,聞中興路亦陷,乃議趣嶽州就元帥特克嘉,而道阻不得前,仍趨襄陽,賊方駐楊湖港,乘其不虞擊之,獲其船二十七艘,生擒賊黨劉雅爾,訊得其情。進次潛江縣,又斬賊數百級,獲三十餘船,梟賊將劉萬戶、許堂主等。甫止兵未食,而賊大至,與戰,抵暮,耀珠等軍各當一面,不能救。博羅特穆爾被重創,麾從子瑪哈實勒使去,曰:“吾以死報國,汝無留此。”瑪哈實勒泣曰:“死生從叔父。”既而博羅特穆爾被執,賊請同爲逆,博羅特穆爾怒罵之,遂遇害。瑪哈實勒帥家奴求其屍,復與賊戰,俱沒於陣,舉家死者凡二十六人。博羅特穆爾,高昌人也。是日,荊門州亦陷。
初,妖賊起,陷鄧州,人情恟恟。俄而賊鋒自鄧抵南陽境,南陽縣達嚕噶齊喜同,以計獲數賊,詰之,雲賊將大至,喜同乃悉斬之以安衆心,晝夜督丁壯巡邏守備。時大司農錢木爾以兵駐於諸葛庵,爲賊所襲,死之,賊遂乘銳取南陽,喜同守西門,望見賊勢盛,即與家人訣曰:“吾與汝等不能相顧矣!但各逃生,吾分死此,以報國也。”已而城中皆哭。喜同策厲義兵,奮力與賊搏,賊退去,明日復至,與戰甚力,殺賊凡數百。賊知無援,戰愈急,南陽遂陷。喜同突圍將自拔,賊橫刺其馬,馬蹶,喜同鞭馬躍而起,手斬刺馬者,他賊追之,身被數創,不能鬥,遂爲所殺。妻邢氏,罵賊見殺,一家死者二十餘人。事聞,贈南陽路判官。喜同,河西人也。
時富珠哩遠調襄陽縣尹,須次居南陽,賊起,遠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遠被害。遠妻雷氏爲賊所執,賊欲妻之,雷曰:“我參政冢婦,縣令嫡妻,肯從汝狗彘以生乎!”賊將污之,雷號哭大罵不從,乃見殺,舉家皆被害。遠,翀之子也。
丙辰,徐壽輝遣其將丁普郎、徐明遠陷漢陽;丁巳,陷興國府。
己未,徐壽輝將鄒普勝陷武昌。
先是賊氛日熾,湖廣行省平章桑節會僚屬議之。或曰:“有鄭萬戶,老將也,宜起而用之。”桑節乃命募土兵,完城池,修器械,嚴巡警,悉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二千來約降,桑節與鄭謀曰:“此詐也,然降而卻之,於事爲不宜,受而審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殲之,械其渠魁數十人以俟命。適召入爲大司農,桑節去,同僚受賊賂,且嫉其功,乃誣鄭罪,釋其所械者。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威順王庫春布哈、行省平章和尚,皆棄城走,城遂陷。武昌之人駢首夜泣曰:“大夫不去,吾豈爲俘囚乎!”
有馮三者,湖廣省公使也,素不知書;武昌陷,皁隸輩拉三共爲盜,三固辭曰:“賊名惡,我等豈可爲!”衆怒,將殺之,三遂唾罵,衆乃縛諸十字木,舁以行而刲其肉,三益罵不止,抵江上,斷其喉,委之去。其妻隨三號泣,俯拾刲肉納布裙中,伺賊遠,收三血骸,脫衣裹之,大哭,投江而死。
命刑部尚書阿嚕收捕山東賊,給敕牒十一道,使分賞有功者。
辛酉,徐壽輝將魯法興陷安陸府,知府綽嚕死之。
法興之來攻也,綽嚕募兵得數百人,帥以拒賊,敗賊前隊,乘勝追之。而賊自他門入,亟還兵,則城中火起,軍民潰亂,計不可遏而歸,服朝服,出坐公堂。賊脅以白刃,綽嚕猶喻以逆順,一賊排綽嚕下使拜,不屈,且怒罵,賊渠不忍害,拘之。明日,又逼其從亂,綽嚕疾叱曰:“吾守土臣,寧從汝賊乎!”賊怒,以刀斫綽嚕,左脅斷而死。賊憤其不降,復以布囊纏其屍,舁置其家,綽嚕妻侯氏出,大哭,且列酒肉滿前,渴者令飲酒,飢者令食肉,以紿賊使不防己,至夜自經死。事聞,贈綽嚕河南行省參知政事,侯氏寧夏郡夫人,表其門曰雙節。
丙寅,以河復故道,大赦天下。
辛未,徐壽輝兵陷沔陽府,壬申,陷中興路。沔陽推官象山俞述祖,領民兵守綠水洪,城陷,被執,械至壽輝所,述祖罵不輟,壽輝怒,支解之。其犯中興也,山南宣慰司同知伊古輪實出戰,衆潰,宣慰使錦州布哈棄城走。山南廉訪使濟爾克敦以兵與抗,射賊多死,明日,賊益兵來,襲東門,力戰,被執,不屈而死。
武昌既陷,江西大震,賊舳艫蔽江而下,行省右丞博羅特穆爾方駐兵江州,聞之,亦遁去。總管李黼,雖孤立,辭氣愈奮厲。時黃梅縣主簿伊蘇特穆勻願出擊賊,黼大喜,向天瀝酒與之誓。言始脫口,賊遊兵已至境,急檄諸鄉落聚木石於險塞處,遏賊歸路,倉卒無號,乃墨士卒面,統之出戰;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伊蘇特穆爾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石,橫屍蔽路,殺獲二萬餘。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以舟薄我。”乃以長木數千,冒鐵錐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樁”。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遇樁不得動,進退無措,黼帥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舟散走。行省上黼勁,拜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
二月,乙亥朔,定遠人郭子興,集少年數千人,自稱節制元帥。子興兄弟三人,皆善殖貲產,由是豪裏中。子興知天下有變,元乃散家財,椎牛釃酒,與壯士結納,至是與孫德崖及俞某、魯某、潘某等以衆攻城。
甲申,鄒平縣馬子昭爲亂,官軍捕斬之。
乙酉,徐壽輝兵陷江州,總管李黼死之,遂陷南康路。
時賊勢愈盛,西自荊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黼中外援絕。賊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圖沁布哈自北門遁。黼引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甘棠湖,焚西門,乃張弩射之。賊轉攻東門,黼救之,而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刺黼墮馬,黼與兄冕之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郡民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於東門外。黼死逾月,參政之命始下。冕居潁,亦死於賊。事聞,贈黼淮南、江北行省左丞,追封隴西郡公,諡忠文,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
丙戌,霍州靈石縣地震。
房州賊陷歸州。
戊子,詔:“徐州內外羣聚之衆,限二十日,不分首從,並與赦原。”
置安東、安豐分元帥府。
巳醜,遊皇城。
庚子,郭子興陷濠州,據之。
辛丑,鄧州賊王權、張椿陷澧州,龍鎮衛指揮使諳都喇哈曼等帥師復之。
褒贈仗節死義者宣徽使特穆爾等二十七人。
是月,賊侵滑、濬,命德珠爲河南右丞,守東明。德珠時致仕於家,聞命,即馳至東明,浚城隍,嚴備禦,賊不敢犯。
徐壽輝將歐普祥陷袁州。普祥,黃岡人,以燒香聚衆,從壽輝起兵爲元帥,人稱“歐道人”。至是引兵掠江西諸郡縣,攻破袁州,焚室廬,掠人民以去,令別將守之。
三月,乙巳朔,追封太師、忠王滿濟勒噶臺爲德王。
丁未,徐壽輝將許甲攻衡州,洞官黃安撫敗之。
壬子,河南左丞相臺哈布哈,克復南陽等處。
癸丑,中書省請行納粟補官之令:“凡士庶爲國宣力,自備糧米供給軍儲者,照依定擬地方實授常選流官,依例升轉、封廕;及已除茶鹽錢穀官有能再備錢糧供給軍儲者,驗見授品級,改授常流。”從之。
甲子,徐壽輝將項普略陷饒州路,遂陷徽州、信州。
時官軍多疲懦不能拒,所在無賴子乘間竊發,不旬日衆輒數萬,皆短衣草屨,齒木爲杷,削竹爲槍,截緋帛爲巾襦,彌野皆赤。饒州守臣魏中立,率丁壯分塞險要,戒守備,俄而賊至,達嚕噶齊馬來出戰,不能發矢,賊愈逼,中立以義兵擊卻之。已而賊複合,遂爲所執,以紅衣被其身,中立叱之,鬚髯盡張。信州總管於大本以土兵備禦,賊又陷其城而執之,並送蘄水。壽輝欲使從己,二人皆大罵不屈,遂被害。中立,濟南人;大本,密州人也。
丁卯,以出征馬少,出幣帛各二十萬匹,於迤北萬戶、千戶所易馬。
戊辰,詔:“南人有才學者,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皆用之。”於是吏部郎中宣城貢師泰,翰林直學士饒州周伯琦,同擢監察御史。南士復居省臺自此始。
中書省臣言:“張理獻言,饒州、德興二處,膽水浸鐵,可以成銅,宜即其地各立銅冶場,直隸寶泉提舉司,以張理就爲銅冶場官。”從之。
是月,方國珍復劫其黨下海,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臺哈布哈發兵扼黃岩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抵國珍示約信,使之來歸。國珍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寫鞍諸山,臺哈布哈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甫招徠,又復爲變。君輩助我擊之,其克,則汝衆功也,不克,則我盡死以報國耳。”衆皆踊躍願行。時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降伏,臺哈布哈率部衆張受降旗乘潮,而船觸沙不能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臺哈布哈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一人,賊舉槊來刺,輒斫折之。賊羣至,欲抱持過國珍船,臺哈布哈瞋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僕,投其屍海中,年四十九。僮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戶赤盞,義士張君璧,皆死之。後追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諡忠介,立廟臺州,賜額曰崇節。臺哈布哈尚氣節,不隨俗浮沉。泰費音爲臺臣劾去相位,臺哈布哈獨餞送都門外,泰費音曰:“公且止,勿以我累公!”臺哈布哈曰:“士爲知己者死,寧畏禍耶!”
詔定軍民官不守城池之罪。
隴西地震百餘日,城郭頹移,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莊浪尤甚。會州公宇中牆崩,獲弩五百餘張,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改定西爲安定州,會州爲會寧州。
閏月,甲戌朔,鍾離人硃元璋從郭子興於濠州。
元璋先世家沛,後自句容、泗州徙鍾離。昆弟四人,元璋其季也。少苦疾,比長,姿貌雄傑,既就學,聰明英武,沈幾大度,人莫能測也。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飢疫,父母兄相繼歿,遂入皇覺寺爲僧,逾月,西至合肥,又適六安,歷光、固、汝、潁諸州,凡三年,復還皇覺寺。久之,寺爲亂兵所焚,僧皆逃散,元璋亦出避兵,不知所向,人有招以起事者,元璋意不決。是時徹爾布哈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徼賞,民皆恟懼。元璋恐不免於難,乃詣伽藍卜珓,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欲予從羣雄倡義乎?”果“大吉。”復自念從羣雄非易事,祝曰:“盍許我以避兵!”投之,交躍而立,意乃決。抵濠城,門者疑爲諜,執之,以告子興,子興奇其貌,問所以來,具告之故,子興喜,遂留置左右。尋命長九夫,常召與謀事,久之,甚見親愛,凡有攻討,即命以往,往輒勝,子興由是兵益盛。
初,宿州人馬公,與子興爲刎頸交,馬公卒,以季女屬子興,子興因撫爲己女。至是欲以妻元璋,與其妾張氏謀,張氏曰:“吾意亦如此。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豪傑,一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共功業者!”子興意遂決,乃以女妻元璋。
乙酉,徐壽輝將陳普文陷吉安路,鄉民羅明遠起義兵復之。
立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治揚州。
丁酉,湖廣行省參政鐵傑以湖南兵復嶽州。
是月,詔:“江西行省左丞相策琳沁班,淮南行省平章政事鴻和爾布哈,江浙行省左丞遵達特哩,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額森特穆爾,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巴實呼圖,及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納琳與江浙行省官,並以便宜行事。”
陝西行臺御史大夫多爾濟巴勒,行至中途,聞商州陷,武關不守,即輕騎晝夜兼程至奉元,而賊已至鴻門。吏白涓日署事,不許,曰:“賊勢若此,尚顧陰陽拘忌哉!”即就署。省、臺素以舉措爲嫌,不相聚論事,多爾濟巴勒曰:“多事如此,毋得以常例論。”乃與行省平章託多約五日一會集。尋有旨命與託多同討賊,即督諸軍復商州。乃修築奉元城壘,募民爲兵,出庫所藏銀爲大錢,射而中的者賞之,由是人皆爲精兵。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狀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列其功以聞,賜敕書褒獎之,由是其軍遂盛。金州由興元、鳳翔達奉元,道里回遠,乃開義谷,創置七驛,路近以便。
時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駐兵沙河,軍中夜驚,額森特穆爾盡棄軍資、器械,收散卒,北奔汴梁。時文濟王在城頭,遙謂之曰:“汝爲大將,見賊不殺而自潰,吾將劾汝,此城必不容汝也。”遂離城南四十里硃仙鎮屯焉。朝廷以其不習兵,詔別將代之。額森特穆爾徑歸,昏夜入城,明日仍爲御史大夫。西臺監察院御史蒙古魯哈雅、範文等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之罪,多爾濟巴勒當署字,顧謂左右曰:“吾其爲平章湖廣矣。”奏上,丞相托克託怒,果左遷多爾濟巴勒,而御史十二人皆謫爲各路添設佐貳官。
多爾濟巴勒赴湖廣,關中人遮路涕泣曰:“生我者公也,何遽去我而不留乎!”多爾濟巴勒慰遣之,不聽,乃從間道得出。
夏,四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江西臨川賊鄧忠陷建昌路。
乙卯,鐵傑及萬戶陶夢禎復武昌、漢陽,尋再陷。
丙辰,江西宜黃賊塗佑與邵武、建寧賊應必達等攻陷邵武路,總管吳按攤布哈以兵討之,千戶魏淳用計擒佑、必達,復其城。
賊自邵武間道逼福寧州,知州霑化王巴延乃與監州阿薩都喇,募壯兵五萬,分扼險阻,賊至楊梅嶺立柵,巴延與其子相馳破之。賊帥王善,俄擁衆直壓州西門,胥隸皆解散,巴延麾下唯白梃市兒數百人。巴延射賊,不復反顧,賊以長槍舂馬,馬僕,遂見執。善說巴延從己,仍領州,巴延呵善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守,義當死,肯從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扼以跪,弗屈,遂毆之,巴延嚼舌出血噀善面,罵曰:“反賊,殺即殺,何以毆爲!吾民,天民也,汝不可害。大丞相統百萬之師親討叛逆,汝輩將無遺種矣。”賊又執阿薩都喇至,善厲聲責其拒鬥,噤不能對,巴延復唾善曰:“我殺賊,何言拒耶?我死,當爲神以殺汝。”言訖,挺頸受刃,頸斷,涌白液如乳,暴屍數日,色不變,州人哭聲連巷,賊並殺阿薩都喇,欲釋相官之,相罵曰:“吾與汝不共戴天,恨不寸斬汝,我受汝官耶!”賊殺之。相妻潘氏挈二女,爲賊所獲,亦罵賊,母子同死。
甲子,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賜玉帶及鈔一百錠,給全俸終其身。
是月,帝如上都。
永懷縣賊陷桂陽。
四川行省平章耀珠以兵復歸州,進攻峽州,與峽州總管趙餘褫大破賊兵,誅賊將李太素等,遂平這。
詔天下完城郭,築堤防。
五月,戊寅,命龍虎山張嗣德爲三十九代天師,給印章。
命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納琳給宣敕與台州民陳子由、楊恕卿、趙士正、戴甲,令其集民丁夾攻方國珍。
己卯,四川行平省章耀珠復中興路,參政達實巴都魯請自攻襄陽,許之,進次荊門。時賊十萬,官軍止三千餘,遂用宋廷傑計,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義丁二萬,遍排部伍,申其約束。行至蠻河,賊守要害,兵不得渡,即令屈萬戶率奇兵間道出其後,首尾夾攻,賊大敗。追至襄陽城南,大戰,生擒其僞將三十人,要斬之,賊自是閉門不敢出。達實巴都魯乃相視形勢,內列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營,軍峴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軍四十據虎頭山以瞰城中,署從徵人李復爲南漳縣尹,黎可舉爲宜城縣尹,拊循其民。城中之民,受圍日久,夜半,二人縋城叩營門,具告虛實,願爲內應,達實巴都魯與之定約,以五月朔日四更攻城,授之密號而去,至期,民垂繩以引官軍,先登者近十人。時賊船百餘艘在城北,陰募善水者鑿其底。天將明,城破,賊巷戰不勝,走就船,船壞,皆溺水死;僞將王權領千騎而走,遇伏兵,被擒,襄陽遂平。
庚辰,監察御史徹徹特穆爾等言:“河南諸處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宜以瀛國公子和尚趙完普及親屬徒沙州安置,禁勿與人交通。”從之。
癸未,建昌民戴良起鄉兵,克復建昌路。
六月,丙寅,紅巾周伯顏陷道州。
是月,大名路旱蝗,饑民七十餘萬口,給鈔十萬錠賑之。
中興路鬆滋縣雨水暴漲,漂民舍千餘家,溺死七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