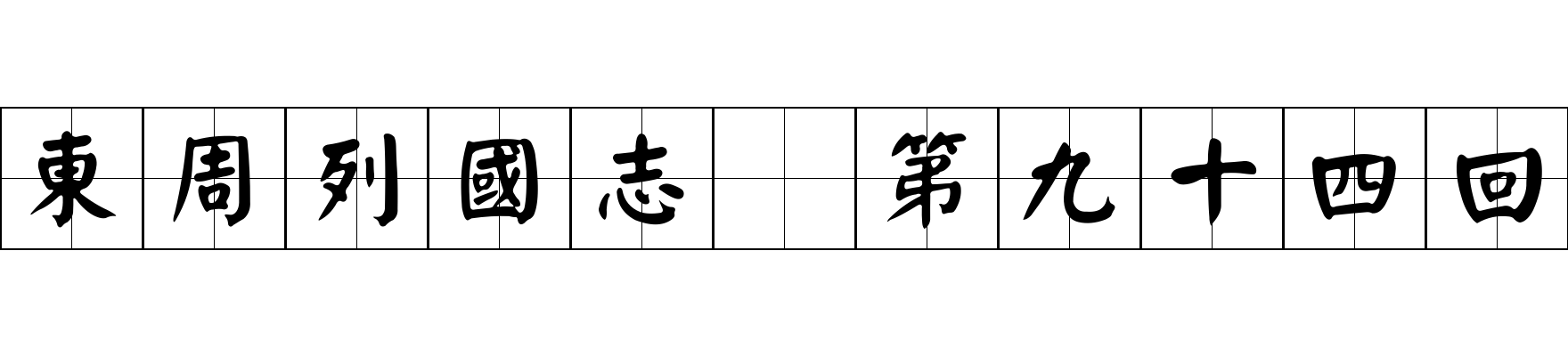東周列國志-第九十四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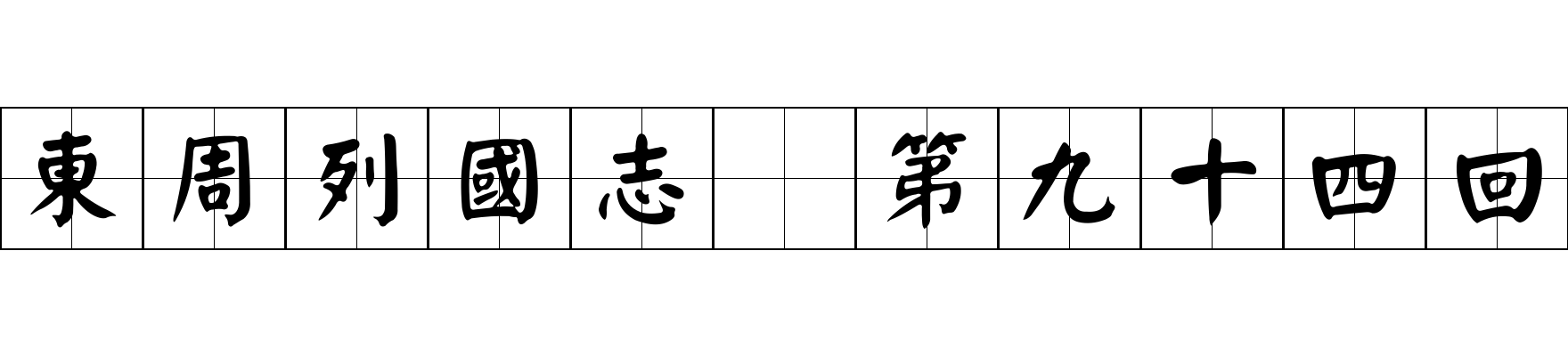
《東周列國志》是中國古代的一部歷史演義小說,作者是明末小說家馮夢龍。這部小說由古白話寫成,主要描寫了從西周宣王時期直到秦始皇統一六國這五百多年的歷史。早在元代就有一些有關“列國”故事的白話本,明代嘉靖、隆慶時期,餘邵魚撰輯了一部《列國志傳》,明末馮夢龍依據史傳對《列國志傳》加以修改訂正,潤色加工,成爲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國志》。清代乾隆年間,蔡元放對此書又作了修改,定名爲《東周列國志》。
馮諼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
話說孟嘗君自秦逃歸,道經於趙,平原君趙勝出迎於三十里外,極其恭敬。趙人素聞人傳說孟嘗之名,未見其貌,至是爭出觀之,孟嘗君身材短小,不逾中人,觀者或笑曰:“始吾慕孟嘗君,以爲天人,必魁然有異,今觀之,但渺小丈夫耳。”和而笑者複數人,是夜,凡笑孟嘗君者皆失頭,平原君心知孟嘗門客所爲,不敢問也。
再說齊湣王既遣孟嘗君往秦,如失左右手,恐其遂爲秦用,深以爲憂。乃聞其逃歸,大喜,仍用爲相國,賓客歸者益衆,乃置爲客舍三等,上等曰“代舍”,中等曰“幸舍”,下等曰”傳舍”。代舍者,言其人可以自代也,上客居之,食肉乘輿;幸舍者,言其人可任用也,中客居之,但食肉不乘輿;傳舍者,脫粟之飯,免其飢餒,出入聽其自便,下客居之。前番雞鳴狗盜及僞券有功之人,皆列於代舍,所收薛邑俸入,不足以給賓客,乃出錢行債於薛,歲收利息,以助日用。
一日,有一漢子,狀貌修偉,衣敝褐,躡草屨,自言姓馮,名諼,齊人,求見孟嘗君。孟嘗君揖之與坐,問曰:“先生下辱,有以教文乎?”諼曰:“無也,竊聞君好士,不擇貴賤,故不揣以貧身自歸耳。”孟嘗君命置傳舍。
十餘日,孟嘗君問於傳舍長曰:“新來客何所事?”傳舍長答曰:“馮先生貧甚,身無別物,止存一劍,又無劍囊,以蒯緱系之於腰間,食畢,輒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孟嘗君笑曰:“是嫌吾食儉也。”乃遷之於幸舍,食魚肉,仍使幸舍長候其舉動:“五日後來告我。”居五日,幸舍長報曰:“馮先生彈劍而歌如故,但其辭不同矣,曰:“長鋏歸來兮,出無車。”孟嘗君驚曰:“彼欲爲我上客乎?其人必有異也。”又遷之代舍,復使代舍長伺其歌否。
諼乘車日出夜歸,又歌曰:“長鋏歸來兮,無以爲家。”代舍長詣孟嘗君言之,孟嘗君蹙額曰:“客何無饜之甚乎?”更使伺之,諼不復歌矣。
居一年有餘,主家者來告孟嘗君。”錢穀只勾一月之需。孟嘗君查貸券,民間所負甚多,乃問左右曰:“客中誰能爲我收債於薛者。代舍長進曰:“馮先生不聞他長,然其人似忠實可任,曏者自請爲上客,君其試之!”孟嘗君請馮諼與言收債之事,馮諼一諾無辭,遂乘車至薛,坐於公府,薛民萬戶,多有貸者,聞薛公使上客來徵息,時輸納甚衆,計之得息錢十萬。
馮諼將錢多市牛酒,預出示:“凡負孟嘗君息錢者,勿論能償不能償,來日悉會府中驗券。”百姓聞有牛酒之犒,皆如期而來,馮諼一一勞以酒食,勸使酣飽,因而旁觀,審其中貧富之狀,盡得其實,食畢,乃出券與合之,度其力饒,雖一時不能,後可相償者,與爲要約,載於券上;其貧不能償者,皆羅拜哀乞寬期,馮諼命左右取火,將貧券一笥。悉投火中燒之,謂衆人曰:“孟嘗君所以貸錢於民者,恐爾民無錢以爲生計,非爲利也;然君之食客數千,俸食不足,故不得已而徵息以奉賓客,今有力者更爲期約,無力者焚券蠲免,君之施德於爾薛人,可謂厚矣。”
百姓皆叩頭歡呼曰:“孟嘗君真吾父母也!”早有人將焚券事報知孟嘗君,孟嘗君大怒,使人催召諼,諼空手來見,孟嘗君假意問曰:“客勞苦,收債畢乎?”
諼曰:“不但爲君收債,且爲君收德!”
孟嘗君色變,讓之曰:“文食客三千人,俸食不足,故貸錢於薛,冀收餘息,以助公費,聞客得息錢,多具牛酒,與衆樂飲,復焚券之半,猶曰:‘收德',不知所收何德也?”
諼對曰:“君請息怒,容備陳之。負債者多,不具牛酒爲歡,衆疑,不肯齊赴,無以驗其力之饒乏,力饒者爲期約,其乏者雖嚴責之,亦不能償,久而息多,則逃亡耳,區區之薛,君之世封,其民乃君所與共安危者也,今焚無用之券,以明君之輕財而愛民,仁義之名,流於無窮,此臣所謂爲君收德者矣。”
孟嘗君迫於客費,心中殊不以爲然,然已焚券,無可奈何,勉爲放顏,揖而謝之。
史臣有詩云:
逢迎言利號佳賓,焚券先虞觸主嗔。 空手但收仁義返,方知彈鋏有高人。
卻說秦昭襄王悔失孟嘗君,又見其作用可駭,想道:“此人用於齊國,終爲秦害!”乃廣佈謠言,流於齊國,言:“孟嘗君名高天下,天下知有孟嘗君,不知有齊王,不日孟嘗君且代齊矣!”
又使人說楚頃襄王曰:“曏者六國伐秦,齊兵獨後,因楚王自爲縱約長,孟嘗君不服,故不肯同兵;及懷王在秦,寡君欲歸之,孟嘗君使人勸寡君勿歸懷王,以太子見質於齊,欲秦殺懷王,彼得留太子以要地於齊,故太子幾不得歸,而懷王竟死於秦。寡君之得罪於楚,皆孟嘗君之故也。寡君以楚之故,欲得孟嘗君而殺之,會逃歸不獲,今復爲齊相專權,旦暮篡齊,秦、楚自此多事矣,寡君願悔前之禍,與楚結好,以女爲楚王婦,共備孟嘗君之變,幸大王裁聽。”
楚王惑其言,竟通和於秦,迎秦王之女爲夫人,亦使人布流言於齊。
齊湣王疑之,遂收孟嘗君相印,黜歸於薛,賓客聞孟嘗君罷相,紛紛散去。惟馮諼在側,爲孟嘗君御車,未至薛,薛百姓扶老攜幼相迎,爭獻酒食,問起居。孟嘗君謂諼曰:“此先生所謂爲文收德者也!”馮諼曰:“臣意不止於此,倘借臣以一乘之車,必令君益重於國,而俸邑益廣。”孟嘗君曰:“惟先生命。”
過數日,孟嘗君具車馬及金幣,謂馮諼曰:“聽先生所往。”馮諼駕車,西入咸陽,求見昭襄王,說曰:“士之遊秦者,皆欲強秦而弱齊;其遊齊者,皆欲強齊而弱秦。秦與齊勢不兩雄,其雄者,乃得天下。”
秦王曰:“先生何策可使秦爲雄而不爲雌乎?”
馮諼曰:“大王知齊之廢孟嘗君否?”
秦王曰:“寡人曾聞之,而未信也。”
馮諼曰:“齊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有孟嘗君之賢也,今齊王惑於讒毀,一旦收其相印,以功爲罪,孟嘗君怨齊必深,乘其懷怨之時,而秦收之以爲用,則齊國之陰事,以將盡輸於秦,用以謀齊,齊可得也,豈特爲雄而已哉?大王急遣使,載重幣,陰迎孟嘗君於薛,時不可失,萬一齊王悔悟而複用之,則兩國之雌雄未可定矣。”時樗裏疾方卒,秦王急欲得賢相,聞諼言大喜,乃飾良車十乘,黃金百鎰,命使者以丞相之儀從迎孟嘗君。
馮諼曰:“臣請爲大王先行報孟嘗君,使之束裝,毋淹來使。”
馮諼疾驅至齊,未暇見孟嘗君,先見齊王,說曰:“齊、秦之互爲雌雄,王所知也,得人者爲雄,失人者爲雌。今臣聞道路之言,秦王幸孟嘗君之廢,陰遣良車十乘,黃金百鎰,迎孟嘗君爲相,倘孟嘗君西入相秦,反其爲齊謀者以爲秦謀,則雄在秦,而臨淄、即墨危矣!”
湣王色動,問曰:“然則如何?”
馮諼曰:“秦使旦暮且至薛,大王乘其未至,先復孟嘗君相位,更廣其邑封,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使者雖強,豈能不告於王,而擅迎人之相國哉?”
湣王曰:“善。”然口雖答應,意未深信,使人至境上,探其虛實,只見車騎紛紛而至,詢之果秦使也,使者連夜奔告湣王,湣湣王即命馮諼持節迎孟嘗君,復其相位,益封孟嘗君千戶,秦使者至薛,聞孟嘗君已復相齊,乃轉轅而西。
孟嘗君既復相位,前賓客去者復歸,孟嘗君謂馮諼曰:“文好客無敢失禮,一日罷相,客皆棄文而去。今賴先生之力,得復其位,諸客有何面目復見文乎?”馮諼答曰:“夫榮辱盛衰,物之常理。君不見大都之市乎?旦則側肩爭門而入,日暮爲墟矣,爲所求不在焉。夫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常也,君又何怪乎?”孟嘗君再拜曰:“敬聞命矣。”乃待客如初。
是時,魏昭王與韓釐王奉周王之命,“合縱”伐秦,秦使白起將兵迎之,大戰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韓將公孫喜,取武遂地二百里;遂伐魏,取河東地四百里。昭襄王大喜,以七國皆稱王,不足爲異,欲別立帝號,以示貴重,而嫌於獨尊,乃使人言於齊湣王曰:“今天下相王,莫知所歸,寡人意欲稱西帝,以主西方,尊齊爲東帝,以主東方,平分天下,大王以爲何如?”湣王意未決,問於孟嘗君,孟嘗君曰:“秦以強橫見惡於諸侯,王勿效之。”
逾一月,秦復遣使至齊,約共伐趙,適蘇代自燕復至,湣王先以並帝之事,請教於代,代對曰:“秦不致帝於他國,而獨致於齊,所以尊齊也。卻之,則拂秦之意;直受之,則取惡於諸侯。願王受之而勿稱,使秦稱之,而西方之諸侯奉之;王乃稱帝,以王東方未晚也。使秦稱之,而諸侯惡之,王因以爲秦罪。”
湣王曰:“敬受教。”
又問:“秦約伐趙,其事何如?”
蘇代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趙無罪而伐之,得地則爲秦利,齊無與焉;今宋方無道,天下號爲桀宋,王與其伐趙,不如伐宋,得其地可守,得其民可臣,而又有誅暴之名,此湯武之舉也。”
湣王大悅,乃受帝號而不稱,厚待秦使,而辭其伐趙之請。
秦昭襄王稱帝才二月,聞齊仍稱王,亦去帝號不敢稱。
話分兩頭,卻說宋康王乃宋闢公闢兵之子,剔成之弟。其母夢徐偃王來託生,因名曰偃。生有異相,身長九尺四寸,面闊一尺三寸,目如巨星,面有神光,力能屈伸鐵鉤,於周顯王四十一年,逐其兄剔成而自立。
立十一年,國人探雀巢,得蛻卵,中有小鸇,以爲異事,獻於君偃。偃召太史佔之,太史布卦奏曰:“小而生大,此反弱爲強,崛起霸王之象。”偃喜曰:“宋弱甚矣,寡人不興之,更望何人?”乃多檢壯丁,親自訓練,得勁兵十萬餘,東伐齊,取五城;南敗楚,拓地三百餘里;西又敗魏軍,取二城;滅滕,有其地。
因遣使通好於秦,秦亦遣使報之,自是宋號強國,與齊、楚、三晉相併,偃遂稱爲宋王,自謂天下英雄,無與爲比。欲速就霸王之業,每臨朝,輒令羣臣齊呼萬歲,堂上一呼,堂下應之,門外侍衛亦俱應之,聲聞數裏。
又以革囊盛牛血,懸於高竿,挽弓射之,弓強矢勁,射透革囊,血雨從空亂灑,使人傳言於市曰:“我王射天得勝。”欲以恐嚇遠人。
又爲長夜之飲,以酒強灌羣臣,而陰使左右以熱水代酒自飲,羣臣量素洪者,皆潦倒大醉,不能成禮;惟康王惺然,左右獻諛者,皆曰:“君王酒量如海,飲千石不醉也。”
又多取婦人爲淫樂,一夜御數十女,使人傳言:“宋王精神兼數百人,從不倦怠。”以此自炫。
一日,遊封父之墟,遇見採桑婦甚美,築青陵之臺以望之,訪其家,乃舍人韓憑之妻息氏也。王使人喻憑以意,使獻其妻,憑與妻言之,問其願否,息氏作詩以對曰:“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 鳥自高飛,羅當奈何?”
宋王慕息氏不已,使人即其家奪之,韓憑見息氏升車而去,心中不忍,遂自殺。宋王召息氏共登青陵臺,謂之曰:“我宋王也,能富貴人,亦能生殺人,況汝夫已死,汝何所歸,若從寡人,當立爲王后。”息氏復作詩以對曰:“
鳥有雌雄,不逐鳳凰; 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宋王曰:“卿今已至此,雖欲不從寡人,不可得也!”息氏曰:“容妾沐浴更衣,拜辭故夫之魂,然後侍大王巾櫛耳。”宋王許之,息氏沐浴更衣訖,望空再拜,遂從臺上自投於地,宋王急使人攬其衣不及,視之氣已絕矣,簡其身畔,於裙帶得書一幅,書雲:“死後,乞賜遺骨與韓憑合葬一冢,黃泉感德!”
宋王大怒,故爲二冢,隔絕埋之,使其東西相望,而不相親。埋後三日,宋王還國,忽一夜,有文梓木生於二冢之傍,旬日間木長三丈許,其枝自相附結成連理,有鴛鴦一對飛集於枝上,交頸悲鳴,里人哀之曰:“此韓憑夫婦之魂所化也!”遂名其樹曰:“相思樹。”髯仙有詩嘆雲:
相思樹上兩鴛鴦,千古情魂事可傷! 莫道威強能奪志,婦人執性抗君王。
羣臣見宋王暴虐,多有諫者,宋王不勝其瀆,乃置弓矢於座側,凡進諫者,輒引弓射之,嘗一日間射殺景成、戴烏、公子勃等三人,自是舉朝莫敢開口,諸侯號曰桀宋。
時齊湣王用蘇代之說,遣使於楚、魏,約共攻宋,三分其地。兵既發,秦昭王聞之,怒曰:“宋新與秦歡,而齊伐之,寡人必救宋,無再計。”齊湣王恐秦兵救宋,求於蘇代。代曰:“臣請西止秦兵,以遂王伐宋之功。”乃西見秦王曰:“齊今伐宋矣,臣敢爲大王賀。”秦王曰:“齊伐宋,先生何以賀寡人乎?。”蘇代曰:“齊王之強暴,無異於宋,今約楚、魏攻宋,其勢必欺楚、魏,楚、魏受其欺必向西而事秦,是秦損一宋以餌齊,而坐收楚、魏之二國也,王何不利焉,敢不賀乎?”
秦王曰:“寡人慾救宋何如?”代答曰:“桀宋犯天下之公怒,天下皆幸其亡,而秦獨救之,衆怒且移於秦矣。”秦王乃罷兵不救宋。
齊師先至宋郊,楚、魏之兵亦陸續來會,齊將韓聶、楚將唐昧、魏將芒卯,三人做一處商議,唐昧曰:“宋王志大氣驕,宜示弱以誘之。”芒卯曰:“宋王淫虐,人心離怨,我三國皆有喪師失地之恥,宣傳檄文,布其罪惡,以招故地之民,必有反戈而向宋者。”韓聶曰:“二君之言皆是也。”
乃爲檄數桀宋十大罪:
一、 逐兄篡位,得國不正;
二、 滅滕兼地,恃強凌弱;
三、 好攻樂戰,侵犯大國;
四、 革囊射天,得罪上帝;
五、 長夜酣飲,不恤國政;
六、 奪人妻女,淫蕩無恥;
七、 射殺諫臣,忠良結舌;
八、 僭擬王號,妄自尊大;
九、 獨媚強秦,結怨鄰國;
十、 慢神虐民,全無君道。
檄文到處,人心聳懼,三國所失之地,其民不樂附宋,皆逐其官吏,登城自守,以待來兵。於是所向皆捷,直逼睢陽,宋王偃大閱車徒,親領中軍,離城十里結營,以防攻突。
韓聶先遣部下將閭丘儉,以五千人挑戰,宋兵不出,閭丘儉使軍士聲洪者數人,登車巢車朗誦桀宋十罪,宋王偃大怒,命將軍盧曼出敵,略戰數合,閭丘儉敗走,盧曼追之,儉盡棄其車馬器械,狼狽而奔,宋王偃登壘,望見齊師已敗,喜曰:“敗齊一軍,則楚、魏俱喪氣矣!”乃悉師出戰,直逼齊營,韓聶又讓一陣,退二十里下寨,卻教唐昧、芒卯二軍左右取路,抄出宋王大營之後。
次日,宋王偃只道齊兵已不能戰,拔寨都進,直攻齊營,閭丘儉打著韓聶旗號,列陣相持,自辰至午,合戰三十餘次,宋王果然英勇,手斬齊將二十餘員,兵士死者百餘人,宋將盧曼亦死於陣,閭丘儉復大敗而奔,委棄車仗器械無數,宋兵爭先掠取,忽有探子報道:“敵兵襲攻睢陽城甚急,探是楚、魏二國軍馬。”宋王大怒,忙教整隊回軍。
行不上五里,刺斜裏一軍突出,大叫:“齊國上將韓聶在此,無道昏君,還不速降?”宋王左右將戴直、屈志高,雙車齊出,韓聶大展神威,先將屈志高斬於車下,戴直不敢交鋒,保護宋王,且戰且走,回至睢陽城下,守將公孫拔認得自家軍馬,開門放入,三國合兵攻打,晝夜不息。
忽見塵頭起處,又有大軍到來,乃是齊湣王恐韓聶不能成功,親帥大將王蠋、太史敫等,引生軍三萬前來,軍勢益壯。宋軍知齊王親自領兵,人人喪膽,個個灰心,又兼宋王不恤士卒,晝夜驅率男女守瞭,絕無恩賞,怨聲籍籍。戴直言於王偃曰:“敵勢猖狂,人心已變,大王不如棄城,權避河南,更圖恢復。”
宋王此時一片圖王定霸之心,化爲秋水,嘆息了一回,與戴直半夜棄城而遁,公孫拔遂豎起降旗,迎湣王入城。湣王安撫百姓,一面令諸軍追逐宋王。
宋王走至溫邑,爲追兵所及,先擒戴直斬之,宋王自投於神農澗中不死,被軍士牽出斬首,傳送睢陽。齊、楚、魏遂共滅宋國,三分其地。
楚、魏之兵既散,湣王曰:“伐宋之役,齊力爲多,楚、魏安得受地!”遂引兵銜枚尾唐昧之後,襲敗楚師於重丘,乘勝逐北,盡收取淮北之地,又西侵三晉,屢敗其軍。楚、魏恨湣王之負約,果皆遣使附秦,秦反以爲蘇代之功矣。
湣王既兼有宋地,氣益驕恣,使嬖臣夷維往合衛、魯、鄒三國之君,要他稱臣入朝。三國懼其侵伐,不敢不從,湣王曰:“寡人殘燕滅宋,闢地千里,敗梁割楚,威加諸侯。魯、衛盡已稱臣,泗上無不恐懼,旦晚提一旅兼併二週,遷九鼎於臨淄,正號天子,以令天下,誰敢違者?”
孟嘗君田文諫曰:“宋王偃惟驕,故齊得而乘之;願大王以宋爲戒。夫周雖微弱,然號爲共主,七國攻戰,不敢及周,畏其名也。大王前去帝號不稱,天下以此多齊之讓。今忽萌代周之志,恐非齊福。”
湣王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桀、紂非其主乎?寡人何不如湯、武?惜子非伊尹、太公耳!”於是復收孟嘗君相印,孟嘗君懼誅,乃與其賓客走大梁,依公子無忌以居。
那公子無忌乃是魏昭王之少子,爲人謙恭好士,接人惟恐不及。
嘗朝膳,有一鳩爲鷂所逐,急投案下,無忌蔽之,視鷂去,乃縱鳩,誰知鷂隱於屋脊,見鳩飛出,逐而食之,無忌自咎曰:“此鳩避患而投我,乃竟爲鷂所殺,是我負此鳩也。”竟日不進膳,令左右捕鷂。共得百餘頭,各置一籠以獻,無忌曰:“殺鳩者止一鷂,吾何可累及他禽。”乃按劍於籠上,祝曰:“不食鳩者,向我悲鳴,我則放汝。”羣鷂皆悲鳴,獨至一籠,其鷂低頭不敢仰視,乃取而殺之,遂開籠放其餘鷂,聞者嘆曰:“魏公子不忍負一鳩,忍負人乎?”
由是士無賢愚,歸之如市,食客亦三千餘人,與孟嘗君、平原君相亞。
魏有隱士,姓侯名贏,年七十餘,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無忌聞其素行修潔,且好奇計,裏中尊敬之,號爲侯生,於是駕車往拜,以黃金二十鎰爲贄。侯生謝曰:“贏安貧自守,不妄受人一錢,今且老矣,寧爲公子而改節乎?”無忌不能強,欲尊禮之,以示賓客,乃置酒大會。
是日,魏宗室將相諸貴客畢集堂中,坐定,獨虛左第一席,無忌命駕親往夷門,迎侯生赴會,侯生登車,無忌揖之上坐,生略不謙遜,無忌執轡在傍,意甚恭敬。侯生又謂無忌曰:“臣有客朱亥,在市屠中,欲往看之,公子能枉駕同一往否?”無忌曰:“願與先生偕往。”即命引車枉道入市,及屠門,侯生曰:“公子暫止車中,老漢將下看吾客。”侯生下車,入亥家,與亥對坐肉案前,絮語移時,侯生時時睨視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略無倦怠。時從騎數十餘,見侯生絮語不休,厭之,多有竊罵者,侯生亦聞之,獨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與朱亥別,復登車,上坐如故。無忌以午牌出門,比回府已申未矣。
諸貴客見公子親往迎客,虛左以待,正不知甚處有名的遊士,何方大國的使臣,俱辦下一片敬心伺候,及久不見到,各各心煩意懶,忽聞報說:“公子迎客已至。”衆貴客敬心復萌,俱起坐出迎,睜眼相看,及客到,乃一白鬚老者,衣冠敝陋,無不駭然。
無忌引侯生遍告賓客,諸貴客聞是夷門監者,意殊不以爲然,無忌揖侯生就首席,侯生亦不謙讓,酒至半酣,無忌手捧金卮爲壽於侯生之前,侯生接卮在手,謂無忌曰:“臣乃夷門抱關吏也,公子枉駕下辱,久立市中,毫無怠色,又尊臣於諸貴之上,於臣似爲過分,然所以爲此,欲成公子下士之名耳。”諸貴賓皆竊笑。
席散,侯生遂爲公子上客,侯生因薦朱亥之賢,無忌數往候見,朱亥絕不答拜,無忌亦不以爲怪。
其折節下士如此。
今日孟嘗君至魏,獨依無忌,正合著古語:“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八個字,自然情投意合。孟嘗君原與趙平原君公子勝交厚,因使無忌結交於趙勝,無忌將親姊嫁於平原君爲夫人,於是魏、趙通好,而孟嘗君居間爲重。
齊湣王自孟嘗君去後,益自驕矜,日夜謀代周爲天子。
時齊境多怪異:天雨血,方數百里,沾人衣,腥臭難當;又地坼數丈,泉水涌出;又有人當關而哭,但聞其聲,不見其形。由是百姓惶惶,朝不保夕,大夫狐咺、陳舉先後進諫,且請召還孟嘗君。湣王怒而殺之,陳屍於通衢,以杜諫者,於是王蠋、太史敫等,皆謝病棄職,歸隱鄉里。不知湣王如何結果?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