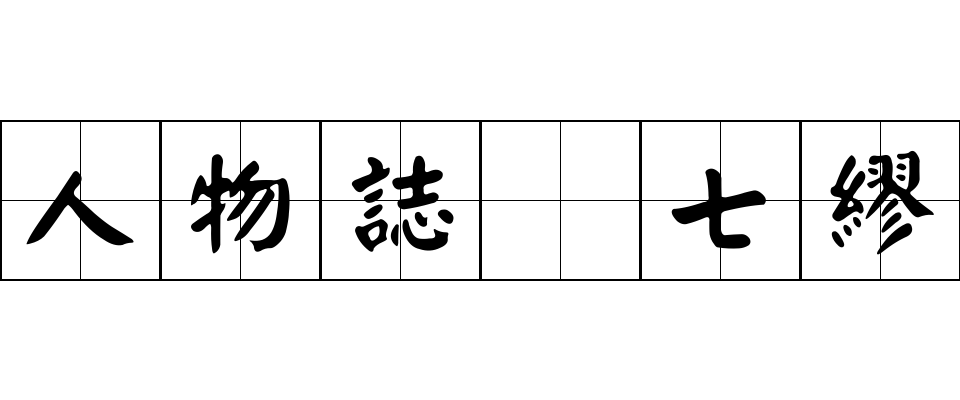人物誌-七繆-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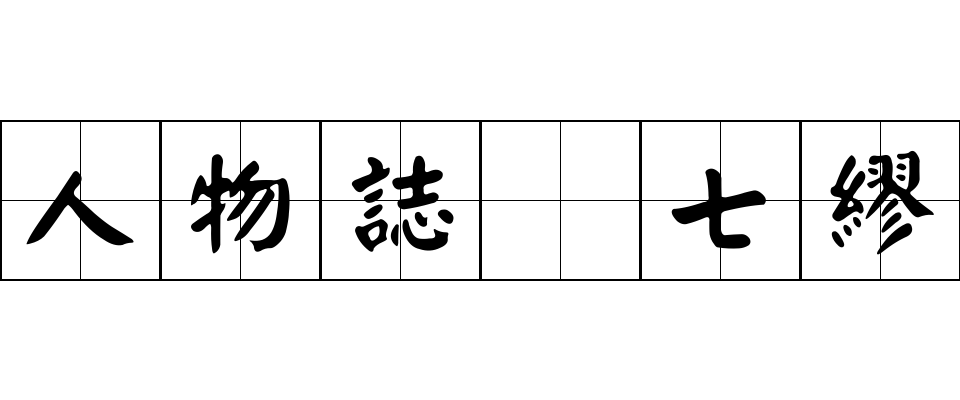
《人物誌》是一部系統品鑑人物才性的玄學著作,也是一部研究魏晉學術思想的重要參考書。全書共三卷十二篇,三國魏劉劭所作,南北朝時西涼劉炳曾爲之作注。書中講述的識鑑人才之術、量能用人之方及對人性的剖析。
七繆:
一曰察譽有偏頗之繆,二曰接物有愛惡之惑,三曰度心有大小之誤,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六曰論材有申壓之詭,七曰觀奇有二尤之失。
夫採訪之要,不在多少。然徵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故:人以爲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爲非,則意轉而化之;雖無所嫌,意若不疑。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萬原;不暢其本,胡可必信。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敗目。故州閭之士,皆譽皆毀,未可爲正也;交遊之人,譽不三週,未必信是也。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間,必每所在肩稱;上等援之,下等推之,苟不能周,必有咎毀。故偏上失下,則其終有毀;偏下失上,則其進不傑。故誠能三週,則爲國所利,此正直之交也。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皆合而非,或在其中。若有奇異之材,則非衆所見。而耳所聽採,以多爲信,是繆於察譽者也。
夫愛善疾惡,人情所常;苟不明賢,或疏善善非。何以論之?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以其所是,順己所長,則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善人雖善,猶有所乏。以其所乏,不明己長;以其所長,輕己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其善。是惑於愛惡者也。
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戡物任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王赫斯怒,以對於天下。”志大也。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大志大者,豪傑之雋也;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志小者,拘懦之人也。衆人之察,或陋其心小,或壯其志大,是誤於小大者也。
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有少有令材遂爲雋器者:四者之理,不可不察。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故文本辭繁,辯始給口,仁出慈恤,施發過與,慎生畏懼,廉起不取。早智者淺惠而見速,晚成者奇識而舒遲,終暗者並困於不足,遂務者周達而有餘。而衆人之察,不慮其變,是疑於早晚者也。
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損害之源,在於非失。故人無賢愚,皆欲使是得在己。能明己是,莫過同體;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親愛同體而譽之,憎惡對反而毀之,序異雜而不尚也。推而論之,無他故焉;夫譽同體、毀對反,所以證彼非而着己是也。至於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己無害,則序而不尚。是故,同體之人,常患於過譽;及其名敵,則鮮能相下。是故,直者性奮,好人行直於人,而不能受人之訐;盡者情露,好人行盡於人,而不能納人之徑;務名者樂人之進趨過人,而不能出陵己之後。是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也;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此又同體之變也。故或助直而毀直,或與明而毀明。而衆人之察,不辨其律理,是嫌於體同也。
夫人所處異勢,勢有申壓:富貴遂達,勢之申也;貧賤窮匱,勢之壓也。
上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是故,達有勞謙之稱,窮有着明之節。
中材之人,則隨世損益,是故,藉富貴則貨財克於內,施惠周於外;見贍者求可稱而譽之,見援者闡小美而大之,雖無異材,猶行成而名立。處貧賤則欲施而無財,欲援而無勢,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分義不復立,恩愛浸以離,怨望者並至,歸非者日多;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故世有侈儉,名由進退:天下皆富,則清貧者雖苦,必無委頓之憂,且有辭施之高,以獲榮名之利;皆貧,則求假無所告,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是故:鈞材而進,有與之者,則體益而茂遂;私理卑抑,有累之者,則微降而稍退。而衆人之觀,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是疑於申壓者也。
夫清雅之美,着乎形質,察之寡失;失繆之由,恆在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列:故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測其玄機,明異希;或以貌少爲不足,或以瑰姿爲巨偉,或以直露爲虛華,或以巧飭爲真實。是以早拔多誤,不如順次;夫順次,常度也。苟不察其實,亦焉往而不失。故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不早拔;拔奇而奇有敗,則患在不素別;任意而獨繆,則悔在不廣問;廣問而誤己,則怨己不自信。是以驥子發足,衆士乃誤;韓信立功,淮陰乃震。夫豈惡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奇逸美異也。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彊,爲衆智之雋也;荊叔色平而神勇,爲衆勇之傑也。然則,雋傑者,衆人之尤也;聖人者,衆尤之尤也。其尤彌出者,其道彌遠。故一國之雋,於州爲輩,未得爲第也;一州之第,於天下爲椳;天下之椳,世有憂劣。是故,衆人之所貴,各貴其出己之尤,而不貴尤之所尤。是故,衆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而不能知第目之度;輩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不能識出尤之良也;出尤之人,能知聖人之教,不能究之入室之奧也。由是論之,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窮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