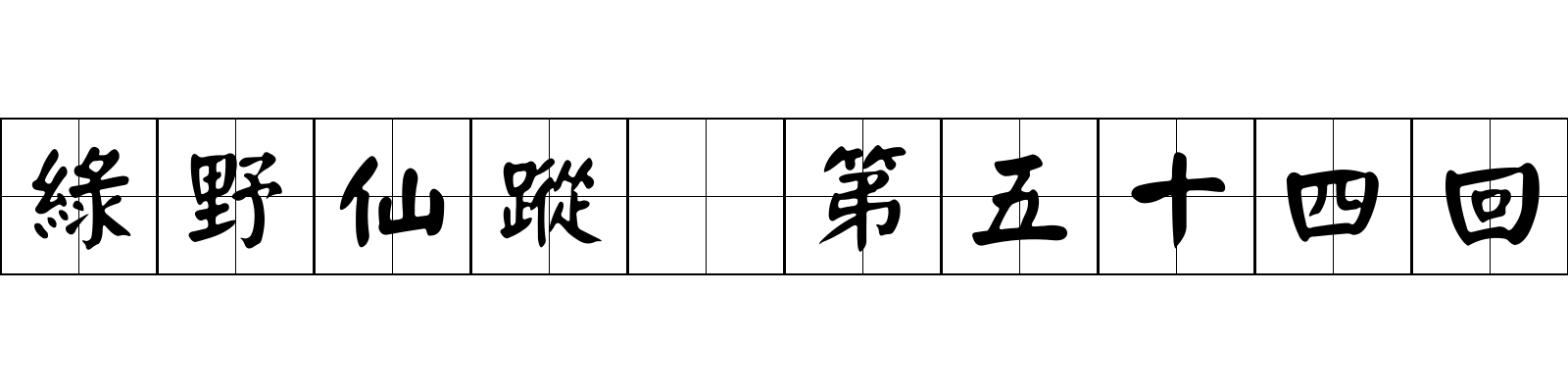綠野仙蹤-第五十四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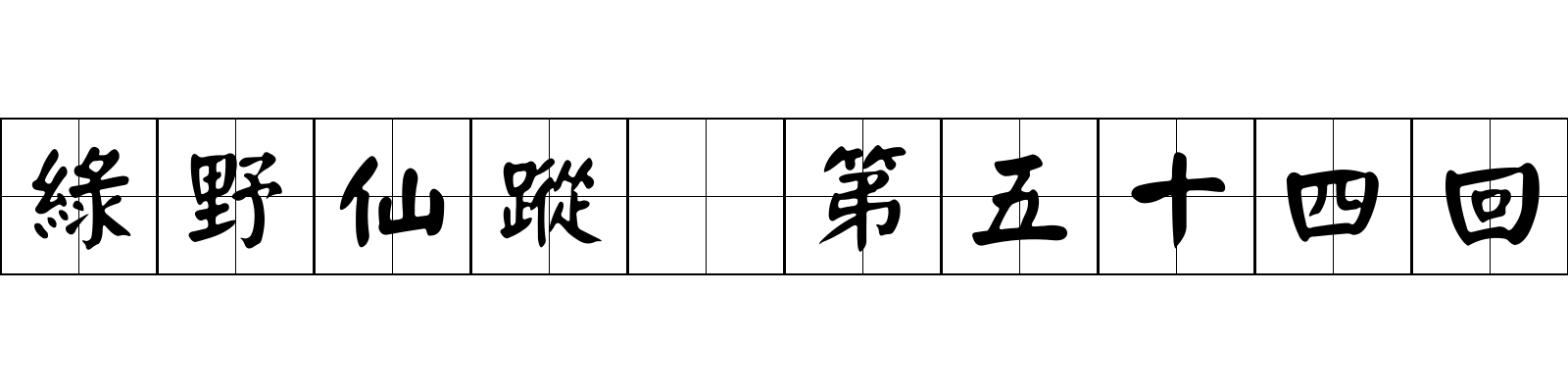
《綠野仙蹤》是一本世情小說更多於志怪小說。冷於冰在其成仙的道路上,收徒並且幫助其親人弟子誅殺爲禍世間的妖怪。人情關係很多時候影響了原本屬於志怪小說的天馬行空的特點。從文筆和批註來看,本書也很能反映古代小說的特點,也是明清小說的一個代表。
過生辰受盡龜婆氣 交借銀立見小人情
詞曰: 情郎妓女兩心諧,豪奢暗減裁。虔婆朝暮恨無財,友情也擬猜。 一過生辰情態見,幫閒龜子罷春臺。陡遇送銀人至,小人側目來。 ——右調《煉石天》。
且說溫如玉在鄭三家嫖的頭昏眼花,辨不出晝明夜暗,止知道埋頭上情。金鐘兒教與他的法兒,雖然支撐了幾個月,少花了幾兩銀子;無如樂戶人家,比老鼠還奸,早已識破他們的調度。鄭三還念如玉在他家花過幾個大錢,怎當鄭婆子剔尖拔毛,一尺一寸,都要打算在如玉身上。這些時,見如玉用錢有斟酌,蕭麻子三兩、五兩到叨點實惠;自己貼上個女兒,夜夜陪睡;又要日日支應飲食;每夜連五錢銀都合不來,心上甚是不平。又見金鐘兒一味與如玉打熱,不和他一心一意的弄錢,這婆子那裏放得過去?起先不過在房裏院外,吐些掂斤播兩的話說,譏刺幾句,使如玉知道;後來見如玉裝聾推啞,是個心裏有了主見,就知是他女兒指教的,便日日罵起金鐘兒來。不是嫌起的遲,就是嫌睡的早;走一步,也有個不是在內;連飲食都消減了。金鐘兒心愛如玉,只要與他省幾個錢,任憑他媽大罵小罵,總付之不見不聞。如玉又氣不過,到要按一夜一兩找還他。金鐘兒又不肯。
昔日苗禿子嫖錢,通是如玉全與;再不然,墊一半。自從金鐘兒教唆後,苗禿子來來往往好幾回,如玉一兩不幫,借也不應。苗禿雖然不如意,知如玉錢亦無多,心上到也罷了。只是這玉磬兒深惱如玉待他涼薄,又恨金鐘兒那一番痛罵,怨深切骨,因此上每逢苗禿子來,就批評他無才無能,連個憨小廝也牢籠不住。自己在嫖賭場中養大的人,還要掏生本兒當嫖客,難道那蕭麻子長着三頭六臂不成?怎麼他就會用憨小廝的錢兒?日日用這些半調唆、半關切的話咶唣。
苗禿子也就有些氣惱在心,想了些時,想出個最妙的道路:每逢鄭婆子與金鐘兒攔嘴,或譏刺如玉,他便搶在頭前,虛說虛笑,替如玉哭窮。這卻有個大作用在內。譬如一人欠債,一人要錢,從中有個人替那欠債的哭窮,十分中就有七八分安頓的下來。
這樂戶人家,講到“銀錢”二字,比蒼蠅見血還甜,任憑他女兒接下瘋子、瞎子、毛賊、強盜,再甚至接了他同行亡八,只要有錢,通不以此爲恥,只是見不得這一個“窮”字聽到耳朵裏,真是錐心刺骨,勢不兩立的勾當。每逢苗禿子替如玉哭一遍窮,便更與如玉加一番口舌。如玉識破他的作用,彼此交情越發淡了。當日每飯必有酒肉、並好果品,不是蕭麻子相陪,就是苗禿子打趣;如今是各喫各飯;各人在各人嫖房內,同坐的時候甚少。如玉的茶飯,午間止有一樣肉,至多也不過四兩;早間通是豆腐、白菜之類;油鹽醬醋等物,也不肯多加些,反不如苗禿子和玉磬兒的飲食還局面些。金鐘兒知如玉不能過甘淡薄,常買些肉食點心,暗中貼補。也有割斤肥肉,拿去廚房中收拾,鄭婆子就罵起打雜的來,說他落的是瞎毛,必着他調和的沒一點滋味,半生不熟的方送上來。
如玉雖說是行樂,究竟是受罪,不但從良的話不敢題,每日除大小便之外,連院中也不敢多走動,恐怕被鄭婆子咶唣。蕭麻子也不管誰厚誰薄,總是月兒錢,到要常使用三五兩。不與他,就有人來鬧是非。饒這般忍氣節用,這幾個月還用去六七十兩;又兼有張華、韓思敬兩家老小,沒的用度,便着如玉寫帖子,向王掌櫃鋪中去取。
取的那王掌櫃不耐煩起來,又知如玉經年家在試馬坡嫖賭,大料這幾百銀子,也不過是一二年的行情,沒有什麼長壽數在他鋪子中存放,好幾次向張華說,着回稟如玉,將銀子收回。張華恐銀子到手,怕如玉浪費起來,作何過度?自己又不敢規諫。止存了個多支架一年是一年的見識,因此總不肯替他說。
一日六月初四日,是如玉的壽日,早間苗禿子和蕭麻子每人湊了二錢半銀子,他們也自覺禮薄,不好與如玉送,暗中與鄭三相商,將這五錢銀子買些酒肉,算與鄭三夥請;第二日不怕如玉不還席。鄭三滿口應允,說道:“溫大爺在我們身上,也用過情。二位爺既有此舉動,我用此銀買些酒肉;不夠了,我再添上些,算二位爺與溫大爺備席。明日我另辦。”
話未說完,鄭婆子從傍問道:“是多少銀子?”
蕭麻子道:“共是五錢,委曲你們辦辦罷。”
鄭婆子道:“那溫大爺也不是知道什麼人情世故的人,我拙手鈍腳的也做不來。不如大家裝個不知道,豈不是兩便?”
蕭麻子道:“生日的話,素常彼此都問過,裝不知道也罷,只是看的冷冷的。”說罷,又看苗禿子。
苗禿子道:“與他做什麼壽?拉倒罷。”
於是兩人將銀子各分開,抽起去了。金鐘兒這日絕早的起來,到廚房中打聽,沒有與如玉收拾着席,自己拿出錢來,買了些面,又着打雜的做了四樣菜喫早飯。午間又託與他備辦一桌酒席。回房裏來,從新妝束,穿一件大紅氅兒,銀紅紗襯衣,鸚哥綠遍地錦裙兒,與如玉上壽。若是素常,苗禿子看見這樣妝束,就有許多的話說;今日看見,只裝不看見。到了午間,金鐘兒去廚房裏看打雜的做席,他媽走來罵道:“你這臭淫婦,平白裏又不赴席,又不拜年,披紅掛綠是爲什麼?閒常家中缺了錢,和你借件衣服典當,千難萬難;今日怎麼就上下一新了?真是死不知好歹的浪貨!”
金鐘兒道:“今日是溫大爺的壽日,他自到這姓鄭的家,前前後後也花費八九百兩銀子。就是這幾個月,手頭索些,也未嘗欠下一百五十。若將借他的八十兩銀子本本利利詳算起來,只怕除了嫖錢,還得倒找他幾兩。我雖然是個亡八羔子娼婦養的,也還頗有些人性、人心,並不是驢馬豬狗,恩怨不分,以錢爲命的人。就是這幾件衣服,也是姑老們替我做的,又不是你替我做的。我愛穿就穿,不愛穿就燒了,誰也管不得我。若害眼氣,也學我把渾身的骨頭和肉,都捨出來,教人家夜夜揉擦,總弄不上綢子、緞子,粗布衣服也騙兩件,喫這些淡醋怎麼?”
鄭婆子聽了,氣的渾身亂戰,將牙齒咬的怪響;拿起個瓦盆來在炕沿上一墩,立刻成了三半個,口裏說道:“反了!氣殺我,氣殺我!”
金鐘兒也撾起兩個盤來往地下一摔,打了個粉碎,說道:“氣殺你!氣殺你,我將來還有個出頭的日子。”
打雜的胡六道:“費上錢,治辦上酒席,嚷鬧的教溫大爺聽見,一總是個不領情。”
鄭婆子道:“誰教他領情哩?”
金鐘兒道:“你一毛兒不拔,他爲什麼領你的情?”
胡六道:“罷喲,老奶奶老翻了,二姑娘又沒老翻了,休教有空聽見笑話。席面我自收拾妥當,二姑娘也不用再來,請回去罷。”
孃兒兩個聽了,都不言語;四隻眼彼此瞅了一會。金鐘兒往前邊去了。
到了午間,打雜的走入金鐘兒房內,問道:“菜放到廳上了,可用請蕭大爺不用?”
金鐘兒道:“平白的又放到廳上怎麼?還照素日一樣打發就是了。”
如玉道:“你真是費心多事,我不說麼,如今是甚麼光景?還過生日?你既然預備下,苗老三他們想來也知道,還是在一處坐爲是。”
金鐘兒道:“我不。我嫌他們太涼薄。那一個沒受過你的好處?就來與你作個揖,也是人情,怎麼都裝起不知道來了?蕭麻子還可,這苗老三他怎麼該是這樣待你?”
如玉聽了,也就不言語了。打雜的把小菜兒搬入來,放在炕桌上;又拿入酒來。金鐘兒滿斟起一杯,奉與如玉,笑盈盈的說道:“我拜拜你罷。”
如玉連忙站起來,拉住道:“這都是沒要緊的想頭。”
兩人方纔對面坐下,共敘心田。直喫到未牌時分,方纔將杯盤收去。
沒有兩杯茶時,只見打雜的入來說道:“有泰安州一個姓王的坐着車來,要尋溫大爺說話,現在門前等候。”
如玉道:“泰安有甚麼姓王的尋我?想是他錯尋了。”
金鐘兒道:“是不是,你出去看看何妨?”
如玉走到門前一看,原來是他的舊夥契王國士。如玉連忙相讓。見國士從車內取出個大皮褡褳來,趕車的後生抱在懷內,跟將入來。鄭三迎着盤問。如玉道:“是我的一位舊朋友,到這裏看望我。”
鄭三見那後生懷中抱的褡褳,走的有些沉重費力,心上不住的猜疑。如玉將王夥計讓在金鐘兒房內。金鐘兒問明,方知是如玉的舊夥計,上前萬福。
慌的那王夥計還禮不迭。彼此揖讓坐下。金鐘兒看那夥計,年約五十多歲,生的肥肥胖胖,穿着一件繭綢單道袍,內襯着細白布大衫,坐下敦敦篤篤,像個忠厚不少飯喫的人。那後生將皮褡褳往炕頭上一放,把腰直了一直,出了一口氣,站在門傍邊,眼上眼下的看金鐘兒。金鐘兒向那後生道:“客人且請到我這院內南房裏坐。”
那後生走將出來,鄭三接住,問了原由,才知道是送銀子來,慌的連忙讓到南房裏坐。鄭婆子催着送茶。
再說王夥計向如玉道:“晚生去年賃了在爺的七百銀子,原欲託大爺的洪福,多賺幾個錢,不意新財東手腳大,將本銀亂用。晚生恐怕他花用盡了,今日與大爺送來。除大爺零碎使用外,淨存本銀五百二十兩。”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本清賬來,裏面夾着如玉屢次取銀帖子,雙手遞與如玉看。如玉道:“你替我使着罷了,何苦又送來?”
王夥計道:“晚生適才不說麼,實實的不敢在鋪中存放了。也曾和張總管說過幾次,總不見他的回信,所以親自來交。”
如玉道:“你送來不打緊,我又該何處安放?”
王夥計道:“任憑大爺。”
金鐘兒取了四百錢,走出來向胡六道:“你快買些酒肉,收拾起來,好打發客人喫飯。那個趕車的,也要與他些酒肉喫。”
鄭婆子連忙跑來,笑說道:“你這孩子好胡鬧!我家裏的客人,和你拿出錢?快拿回去,我自有妥當安排。”
胡六卻待將錢遞迴,金鐘兒道:“你少在我跟前浪,買你的東西去罷。”說畢,回房裏坐下。罵的胡六把手一拍道:“這是那裏的晦氣!”
鄭婆子道:“你還不知道他的性兒,從小兒就是個有火性的孩子。你只快快的買去罷。我在廚房裏,替你架火安鍋滾水等你。”
胡六去了。
這邊王夥計將褡褳打開,將銀子一封封搬出來擺在炕上,着如玉看成色,稱分兩;又要算盤,與如玉當面清算。如玉笑道:“我還有什麼不憑信你處麼?何用清算?你說該多少就是了。”
王夥計道:“大爺若不算算,晚生也不放心。”
講說了半晌,纔不算了。又一定着如玉稱稱分兩。金鐘兒道:“這銀子不但溫大爺,就是我也信的過,是絲毫不錯的。就是每封短上一頭半錢,難道還教添補不成?”
王夥計拂然道:“你這婊姐就不是了,虧你還相與過幾千百個人,連我王老茂都不曉得。不但一錢二錢,便是一兩二兩,我也從不短人家的,怎麼才說起添補的話來?”
金鐘兒笑道:“是我過於老實,不會說話。”又向如玉:“你就稱稱分兩罷。”說罷,將戥子取過來。
如玉見他過於小心,隨即稱兌了幾封,都是白銀子,每一封不過短五六分,也就算是生意人中的大賢了。兌完銀子,便立刻要抽借約。如玉道:“你的借約,還在家中,等我回家時揀還。你若信不過,我此刻與你立個收帖何如?”
王夥計道:“大爺明日與晚生同回去罷。五六百銀子,不是頑的。”
如玉道:“我親筆寫收帖,就是大憑據。我和你財東、夥計一場,難道會將來賴你未還不成?”
王夥計甚是作難,不得已,着如玉寫了收帖,自己看了又看,用紙包好,揣在貼肉處,才略放心些了,就要起身辭去。如玉道:“你好容易到此,我還要留你歇息幾天。”
王夥計道:“晚生手下還管着許多小夥計,如何敢在婊兒家停留?”
如玉笑道:“怎麼你這樣腐板?也罷。這裏也有客店,你吃了飯,我送你安歇。”
王夥計纔不推辭了。金鐘兒將銀子都搬入地下大櫃內。胡六端入菜來。兩人對面坐下。金鐘兒在下面斟酒坐陪。不意鄭婆子又添了許多菜數。那王夥計到好杯兒,酒到便幹。如玉見他有幾分酒態,指着金鐘兒問道:“你看他人物好不好?”
王夥計看了金鐘兒一眼,就將頭低下了。少刻,喫完酒飯,王夥計連茶也不喫,拿出褡褳,又叮嚀如玉回城時抽約,如玉送出院來。慌的鄭三急來相留。如玉說明絕意不在的話,同鄭三領他到店中去了;又與了趕車的幾錢銀子。須臾如玉回來,小女廝將燈送入。
沒有半頓飯時,忽聽得後面高一聲,低一聲叫吵,到像有人拌嘴的光景。忽小女廝跑來說道:“二姑娘,還不快去勸解勸解!老奶奶和老爺子打架哩!”
金鐘兒道:“爲什麼?”
小女廝道:“老爺子同大爺送了那姓王的客人回來,纔打聽出今日是溫大爺的壽日,午間沒有預備下酒席,數說了老奶奶幾句。老奶奶說:‘你是當家人,你單管的是甚麼?’老爺子又不服這話。就一遞一句的拌起口來。老奶奶打了老爺子一個嘴巴,老爺子惱了。如今兩個都打哩。苗三爺和大姑娘都去了;二姑娘還不快去!”
金鐘兒鼻子裏笑了一聲,向如玉道:“這般伎倆,虧他們也想算的出來,真是無恥!”
如玉也笑了。小女廝急的了不得,一定要金鐘兒去。金鐘兒道:“我沒功夫,任憑他們打去,不拘誰打殺一個到好。”
小女廝催了幾遍,見金鐘兒不去,也就去了。待了半晌,不聽得吵鬧了,猛見苗禿子掀簾入來,望着如玉連揖帶頭的就叩拜下去。如玉還禮不迭。苗禿子扒起來說道:“我真是天地間要不得的人!不知怎麼就死昏過去,連老哥的壽日都忘記了。若不是勸他老兩口兒打架,還想不起來。”
又指着金鐘兒道:“你好人兒,一句兒不說破。”
金鐘兒道:“誰理論他的生日、壽日哩?今日若不是人家送着幾兩銀子來,連我也想不起是他的壽日。”
苗禿道:“沒的說,明日是正生日,我們大家補祝也不遲。”
如玉道:“我的生日,是五月初四日,已經過了。”
苗禿子笑道:“你休混我,我記得千真萬真,是這兩日。昨年在東書房,不是我和你喫酒麼?”於是虛說虛道,親熱了半晌;又極力的奉承了金鐘兒幾句,方纔歸房去安歇。
次日鄭三家殺雞宰鴨,先與如玉收拾了一桌茶食;又整備着極好的早飯。苗禿子知會了蕭麻子,在廳內坐着,等候如玉起來補送壽禮。等到巳牌時分,白不見動靜,各有些餓的慌;又不肯先喫些東西,都是打掃着空肚子,要喫鄭三家的茶食和早飯,做補祝的陪客。鄭婆子於昨日已問明趕車的後生,說送來五六百兩銀子,在自己女兒房裏收着。這是一百年再走不去的財帛;不過用耽擱幾月功夫,不愁不到自己手內。今日恨不得將溫如玉放在水晶茶碗裏,一口吞在腹中。若是平素,這時候不起來,這婆子不知大喝小叫到怎麼個田地。
堪堪的到午牌時分,還不見開門。蕭、苗二人,等的不耐煩起來,不住的到門前、院中走來走去的咳嗽;又故意高聲說笑。鄭婆子忍不住到他女兒窗外聽了聽,像個唧唧喁喁的說話;瞅着院內無人,悄悄的用指甲將窗紙掐破一塊,往裏一覷,見兩人俱光着身子,如玉把他女兒按倒在一張椅子上狠幹;又見他女兒發散釵橫,軟癱在椅子上,弄成個有氣無力的死人一般,連忙退回去,心裏說道:“原來這溫如玉有這般本事,怪不得小淫婦兒和他一心。”
又想到自己身上;幼年時也曾瞞着鄭三偷過五六個人,從沒教人家弄得失魂喪魄,到這樣快活時候,真是空活了一世。
歎賞了一會,掀過個板凳來,坐在窗臺階下,通不許人在臺階上走。少刻,聽的他女兒說話,他只當是事完了。再一細聽,口中嚼唸的都是喫虧話,沒一句兒討便宜。又聽得抽送之聲,比三四個人洗衣服還響。鄭婆子不由的心上驚懼起來,說道:“這孩子的性命只怕就在此刻,這姓溫的小廝好狠利害。”
須臾波平浪靜,鄭婆子才知道饒了他女兒,連忙預備淨面水去了。
又待一會,將門兒放開,小女廝送入水來,兩人梳洗罷。胡六請廳上喫茶,金鐘兒道:“俺們不出去。不拘什麼白菜、豆腐,拿來吃了就是。”
胡六去了,轉刻又入來相請。又聽得苗禿子說道:“溫大爺起來了沒有?蕭大哥等候了半天了。”
如玉只得出去。蕭麻子一見,笑的眼連縫兒都沒有,大遠的就灣着腰,搶到跟前下拜,也不怕碰破了頭皮。苗禿子也跪在蕭麻子肩下,幫着行禮。
如玉還禮畢,蕭麻子道:“昨日是大爺千秋,我相交不過年餘,實不知道。”
又指着苗禿道:“這個天殺的不知整日家所幹何事,自己忘記了也罷,還不和我說聲。”
苗禿子將舌一伸道:“好妙話兒!我既然忘記了,還那裏想的起和你說?”
如玉道:“我的生日已過了,就算上是我的生日,我如今也不是勞頓朋友做生日的人。”
蕭麻子從袖內取出個封兒來,上寫着“壽敬二兩”,下寫着他和苗禿名字,雙手送與如玉。如玉那裏肯收?
推讓了好一會,蕭麻向苗禿道:“何如?我預先就知道,大爺不肯收,你還說是再無不收之理。如今我有道理。你在明日,我在後日,各設一席。今日讓與鄭三,這幾月疏闊的了不得,也該整理起舊日家風來了。”
苗禿子道:“說的是。大家原該日日快聚,纔像個朋友哩。”
又見玉磬兒從西房內慢慢的走來,笑道:“我也無物奉獻,止磕個頭罷。”
如玉連忙扶住。胡六擺放杯盤,是十六樣茶食,紅紅綠綠,甚是豐滿。隨即鄭三入來說道:“昨日是大爺千秋,晚上才曉得,還和老婆子生了會氣。”
正說着,鄭婆子從門外搶入來,說道:“大爺不是外人,就是昨日示曾整備酒席,實是無心之過。只是沒有早磕個頭,想起來到教人後悔死。”
說着兩口子沒命的磕下頭去。如玉拉了半晌,方拉起來。
如玉道:“我這半年來手內空虛,沒有多的相送,心上時時抱愧。承你老夫妻情待我始終如一,不但飲食茶水處處關切,就是背面後也沒半句傷觸我。今早又承這樣盛設,到教我又感又愧!”
鄭婆子道:“大爺不必說錢多錢少的話,只要爺們情長,知道俺們樂戶人家的甘苦,就是大恩典了。”
蕭麻子冷眼看見鄭婆子穿着一雙毛青梭新鞋,上面也繡着紅紅白白花草,因鄭三在面前,不好打趣。少刻,兩口子都出去了。蕭麻子向玉磬兒道:“你三嬸子今日穿上這一雙新花鞋,到穿的我心上亂亂的。你可暗中道達,着他送我一隻。”
玉磬兒道:“你要他上供麼?”
蕭麻子道:“誰家上供用那樣不潔之物?不過藉他打打手銃,覺得分外又高興些。”
衆人都笑了。苗禿子:“金姐還梳頭麼?”
胡六道:“二姑娘說來,今日不喫飯,害肚哩,不受用哩。”
苗禿子道:“這又是個戲法兒。他不喫飯,我們還要這嘴做甚麼?”
蕭麻:“我拉他去。”
於是不容分說,將金鐘兒拉出,五人同坐。
正是: 一日無錢事事難,有錢頃刻令人歡。 休言樂戶存心險,世態炎涼總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