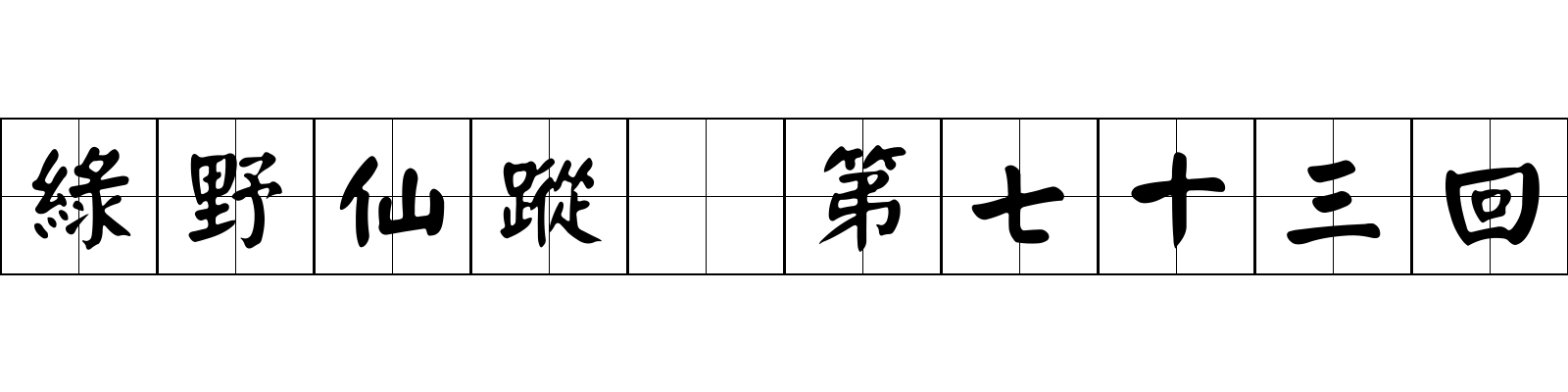綠野仙蹤-第七十三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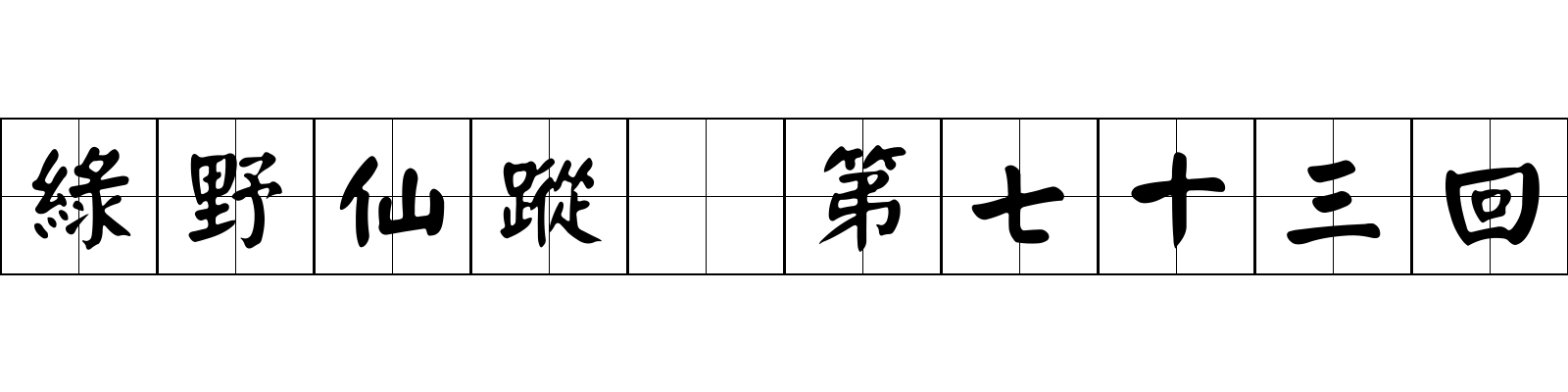
《綠野仙蹤》是一本世情小說更多於志怪小說。冷於冰在其成仙的道路上,收徒並且幫助其親人弟子誅殺爲禍世間的妖怪。人情關係很多時候影響了原本屬於志怪小說的天馬行空的特點。從文筆和批註來看,本書也很能反映古代小說的特點,也是明清小說的一個代表。
溫如玉遊山逢蟒婦 朱文煒催戰失僉都
詞曰: 深山腰嫋多歧路,高岑石畔來蛇婦。如玉被拘囚,血從鼻孔流。 神針飛入戶,人如故。平寇用文華,與蛇差不差。 ——右調《菩薩蠻》。
且說溫如玉在瓊崖洞,得連城璧傳與出納氣息功夫。城璧去後,便與二鬼修持。日食野菜、藥苗、桃李、榛杏之類,從此便日夜泄瀉起來,約六七個月方止。渾身上下,瘦同削竹,卻精神日覺強壯。三年後,又從新胖起來。起先膽氣最小,從不敢獨自出洞。四五年後,於出納氣息之暇,便同二鬼閒遊。
每走百十里,不過兩三個時辰,即可往回,心甚是得意。此後膽氣一日大似一日,竟獨自一個於一二百里之外,隨意遊覽,領略那山水中趣味。
一日,獨自閒行,離洞約有七八十里,見一處山勢極其高峻,奇花異草頗多。心裏說道:“回洞時,說與超塵、逐電,着他們到此採辦,便是我無窮口福。”
於是繞着山徑,穿林撥草,摘取果食。走上北山嶺頭,見周圍萬山環抱,四面八方灣灣曲曲,通有缺口。心裏又說道:“這些缺口,必各有道路相通。一處定有一處的山形水勢,景緻不同。我閒時來此,將這些缺口都遊遍,也是修行人散悶適情一樂。”
正欲下嶺,猛聽得對面南山背後,唧唧咕咕叫喚了幾聲,其音雖細,卻高亮到絕頂。如玉笑道:“此聲斷非鸞鳳,必系一異鳥也。聽他這聲音,到只怕有一兩丈大小。”
語未畢,又聽得叫了幾聲,較前切近了許多。再看對山,相離也不過七八十步,只是看他不見。四下一望,猛見各山缺口,俱有大蟒蛇走來:有缸口粗細,長數丈者;有水桶粗細,長四五丈者;次後兩三丈,一二丈,以及七八尺,三四尺,大小不等,真不知有幾千百許,各揚頭掀尾,急馳而來。嚇的如玉驚魂千里!見有幾株大桃樹,枝葉頗繁,急急的扒了上去,藏躲在那樹枝中。
四下偷看,見衆蟒蛇青紅白綠,千奇百怪,顏色不等。滿山谷內,大小石縫之中,都是此物行走。如玉心膽俱碎,自己鬼念道:“我若被那大蟒大蛇不拘那一條看見,決無生理!”
喜得那些蟒蛇,無分大小,俱向對面南山下直奔。又見極大者在前,中等者在後,再次者更在後,紛紛攘攘,堆積的和幾萬條錦繩相似。
少刻,又聽得叫了幾聲,其音較前更爲切近。再看衆蟒蛇,無一敢搖動者,皆靜伏谷中。陡見對面山頂上,走過一蟒頭婦人來:身着青衣白裙,頭紅似火,頂心中有杏黃肉角一個,約長尺許,看來不過一錢粗細。又見那些大小蟒蛇,皆揚起腦袋,亂點不已,若叩首之狀。自己又嘆息道:“我今日若得僥倖不死,生還洞中,真是見千古未見之奇貨。”
只見蟒頭婦人將衆蟒蛇普行一看,又在四面山上山下一看,又叫了幾聲。叫罷,將如玉藏躲的樹,用手連指了幾指。那些大小蟒蛇,俱各回頭,向北山看視。只這幾指,把個如玉指的神魂若醉,雙手握着樹枝,在上面亂抖。又見那蟒頭婦人,將手向東西分擺,那些大小蟒蛇各紛紛搖動,讓出一條道路來。那蟒頭婦人便如飛的從對面山跑來,向樹前直奔。如玉道:“我活不成了!”
語未畢,那蟒頭婦人已早到樹下,用兩手將樹根抱住一搖,如玉便從樹上掉下,被蟒頭婦人,用雙手接住,抱在懷中,復回舊路,一邊跑,一邊看視如玉,連叫不已,大要是個喜歡不盡之意。如玉此時昏昏沉沉,也不知魂魄歸於何地。少刻,覺得渾身如繩子捆住一般,又覺得鼻孔中有幾條錐子亂刺,痛入心髓。猛然睜眼一看,見身在一大石堂內,那蟒頭婦人已將身軀化爲蛇,仍是紅頭杏黃角,黑身子,遍身都是雪白的碎點,約一丈餘長,碗口粗細。從自己兩背,纏到兩腿,頭在下,尾反在上,即用尾在鼻孔中亂刺,鮮血直流。他卻將腦袋倒立起,張着大口,喫滴下去的血。如玉看罷,將雙睛緊閉聽死。
正在極危迫之際,覺得眼皮外金光一閃,又聽得“唧”的一聲,自己的身子便起倒了幾下。急睜眼看時,那蟒頭婦已長拖着身子,在石堂中分毫不動。身上若去了萬斤重負,惟鼻孔中疼痛如前,仍是血流不止。乍見連城璧走來,將兩個小丸子,先急急向鼻孔中一塞;次將一大些的丸子,填入口中。須臾,覺得兩鼻孔疼痛立止,血亦不流;那大丸子從喉中滾下,腹內雷鳴,大小便一齊直出。又見城璧將他提出石堂,立即起一陣煙雲,已身在半空中飄蕩,片刻在瓊崖洞前。
城璧扶他入洞,二鬼迎着問道:“怎麼是這樣個形像?”
如玉放聲大哭,訴說今日遊走情事。二鬼聽了,俱各吐舌。又問城璧道:“二哥何以知我有此大難相救?”
城璧道:“我那裏曉得?今日已時左近,大哥在後洞坐功,猛然將我急急叫去,說道:‘不好了!溫賢弟被一蟒頭婦人拿去,在泰山煙谷洞石堂內,性命只在此刻。你可拿我戳目針,了絕此怪。’又與了我大小三丸藥,吩咐用法,着我‘快去!快去!’我一路催雲,如掣電般急走。及至找尋到古石堂前,不意老弟已被他纏繞住,刺鼻血咀嚼;若再遲片刻,老弟休矣。塞入鼻中者,系止血定痛之丹;塞入口中者,系追逐毒氣之丹。”
如玉道:“我此刻覺得平復如舊,皆大哥、二哥天地厚恩。但我身上不潔淨之至,等我去後洞更換底衣,再來叩謝。”
說罷,也不用人扶,入後洞去了。
城璧向二鬼道:“着他經經也好,還少胡行亂跑些。一點道術沒有的人,他也要遊遊山水,且敢去人跡不到之地,豈不可笑!他今日所遇是一蛇王,每一行動,必有數千蛇蟒相隨。凡他所過地界,寸草不生,土黑如墨。今已身子變成人形,頭尚未能變過。再將頭一變換,必大行作禍人間矣。”
須臾,如玉出來叩拜,並煩囑謝於冰。城璧道:“賢弟此後宜以煉氣爲主,不可出洞閒遊。你今日爲蟒頭婦人所困,皆因不會架雲故耳。我此刻即傳你起落催停之法。”
如玉大喜。城璧將架雲傳與,再四叮囑而去。
再說林潤得於冰改抹文字,三場並未費半點思索,高高的中了第十三名進士;殿試又在一甲第二名,做了榜眼,傳臚之後,明世宗見人才英發,帝心甚喜,將林潤授爲翰林院編修之職。求親者知林潤尚無妻室,京中大小諸官,俱煩朱文煒作合。
文煒恐得罪下人,又推在林岱身上。本月文煒又生了兒子,心上甚是快樂,益信於冰之言有驗。這話不表。
一日,明帝設朝。辰牌時分,接到浙江巡撫王忬的本章,言奸民汪直、徐海、陳東、麻葉四人,浮海投入日本國爲謀主,教引倭寇夷目妙美劫州掠縣,殘破數十處城郭,官軍不能禦敵。
告急文書屢諮兵部,三四月來總不回覆,又不發兵救應。明帝看了大怒,問兵部堂官道:“你們爲何不行奏聞?”
兵部堂官奏道:“小醜跳樑,地方官自可平定。因事小,恐煩聖慮,因此未行奏聞。”
明帝越發怒道:“現今賊勢已熾,而尚言‘小丑’二字耶?兵部堂官俱着交部議罪。”
孰不知皆是嚴嵩阻撓,總要說天下治平,像這些兵戈水旱的話,他最是厭見厭聞。
嚴嵩此時怕兵部堂官分辯,急急奏道:“浙江既有倭患,巡撫王忬何不先行奏聞?軍機大事,安可以文書諮部卸責?今倭寇深入內地,劫掠浙江,皆王忬疏防縱賊之所致也。”
明帝道:“王忬身爲巡撫,此等關係事件?不行奏聞,其意何居?”隨下旨:將王忬革職,浙江巡撫着布政司張經補授討賊。
那知王忬爲此事,本奏四次,俱被嚴嵩說與趙文華擱起,真是無可辨的冤枉!嚴嵩又奏道:“張經才識,還恐辦理不來。工部侍郎趙文華文武兼全,名望素著,江浙人望他無異雲霓。再胡宗憲雖平師尚詔無功,不過一時識見偶差,究系大有才能之人,祈聖上赦其前罪。錄用兩人,指日定奏奇功。”
明帝便下旨:趙文華升授兵部尚書,督師征討。又想起朱文煒深有權謀,加升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胡宗憲授右僉都御史,一同參贊軍務。於河南、山東二省揀選人馬,星赴浙江。其江浙水陸諸軍,任憑文華調用。旨意一下,兵部即刻行文四省。朱文煒得了此旨,向姜氏道:“趙文華、胡宗憲,豈是可同事之人?此行看來,凶多吉少。前哥哥寄字來,言家中房產、地土俱皆贖回,不如你同嫂嫂速刻回家。這處房子,讓林賢侄住,豈非兩便?”
姜氏道:“你的主見甚是。但願你早早成功,慰我們懸計。”
文煒即着人將林潤請入,說明意見。林潤道:“叔父既執意如此,小侄亦不敢強留,自應遵諭辦理。但趙文華倚仗嚴嵩之勢,出去必不安靜,弄起大是非來,干連不便,叔父還要着實留意。”
正言間,家人報道:“趙大人來拜。”
文煒道:“我理合先去見他爲是,不意他到先來。”
忙同林潤出來。文煒冠戴着,大開中門等候。少刻,喝道聲近,一頂大轎入來。趙文華頭戴烏紗,身穿大紅仙鶴補袍,腰繫玉帶,跟隨着黑壓壓許多人。
文煒接將出去。文華一見,大笑道:“朱老先生,你我着實疏闊的狠!今日奉有聖旨,一同公幹,我看你又如何疏闊我?”
文煒道:“大人職司部務,乃天子之唯舌;晚生名位懸絕,不敢時相親近。”
文華拉着文煒的手兒,又大笑道:“這話該罰你纔是!御史乃國家清要之職,與我有何名位懸絕處?是你嫌厭我輩老而且拙,不肯輕易措愛耳。”
說罷,又大笑起來。兩人同入大廳,行禮坐下。文華道:“老先生今日榮膺恩寵,領袖諫垣;又命主持軍務,聖眷可謂極隆。弟一則來拜賀,二則請候起身吉期。”
文煒道:“晚生正欲鳧趨階下,用伸賀悃,不意反邀大人先施,殊深惶恐之至!至於起身吉日,容晚生到大人處聽候鈞諭。”
文華道:“倭寇跳梁,王巡撫隱匿不奏,致令攻城奪郡,遺害羣黎。弟又問得一祕信:溫州、崇明、鎮海、象山、奉化、興昌、慈溪、餘姚等地,俱被蹂躪。杭州省城,此時想已不保。老先生平師尚詔時,出無數奇謀,這幾個倭寇,自然心中已有定算。倘蒙不棄,可將機密好話兒先告訴我,庶可大家商同辦理。”說罷,又嘻嘻哈哈的笑起來。
文煒道:“用兵之道,必須目睹賊人強弱情形,臨期制勝,安可預爲懸擬?即平師尚詔時,晚生亦不過談兵偶中,究之心無打算,到要請大人奇策指示後輩!”
文華掀着鬍子大笑道:“我來請教你,你到問起我來了?依我的主見,聖上滅寇心急,你我斷不可在京中久延,今晚即收拾行李,明午便行起身。我已囑兵部,連夜行文山東、河南二省,着兩處各揀選勁卒各一萬,先在王家營屯紮等候。我們出了京門,不妨慢慢緩行。走到了王家營,再行文江南文武,着他們揀選水師,少了不中用,須得數萬,匯齊在揚子江岸旁等候。我們再緩緩由水路去,到那時另看風色。”
朱文煒道:“浙省百姓日受倒懸之苦,如此耽延,聖上見罪若何?”
文華道:“倭寇之禍,起於該地方文武不早防閒。目今休說失了數處州郡,便將浙江全失,聖上也怪不到我們身上。若說用兵遲延,我們都推在河南、山東、江南三省各文武身上,只說他們視同膜外,不早應付人馬,兼之船隻甲冑諸項不備。你我同胡大人三個書生,如何殺的了數萬亡命哩?”
文煒道:“倘若倭賊殘破浙江,趁勢長驅江南,豈非我們養疥成瘡之過。”
文華大笑道:“你好過慮呀!浙江全省地方,水陸現有多少人馬?巡撫、鎮副等官,安肯一矢不發,一刀不折,便容容易易放他到江南來?等他到江南時,我們大兵已全積在揚子江邊。
以數十萬養精畜銳之勁卒,破那些日夜力戰之疲賊,與催枯拉朽何殊?此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之道也。”
說罷,又嘻嘻哈哈的笑起來。文煒道:“大人高見,與晚生不同,統俟到江南再行計議。”
文華聽了,低下頭,用手拈着鬍子,自己鬼念道:“不同,不同。”
又復擡頭,將文煒一看,笑道:“先生適才說‘到江南再行計議’。也罷,我別過罷。”
即便起身。文煒送到轎前,文華舉着手兒說道:“請回!請回!容日領教。”
隨即喝着道子去了。
文煒回到書房,正要告知林潤適才問答的話。林潤道:“趙大人所言,小侄在屏後俱聽過了,他如此居心,以朝廷家事爲兒戲,只怕將來要遺累叔父。”
文煒蹙着眉頭道:“我本一介青巾,承聖恩高厚,冷老伯栽培,得至今日,惟有盡忠竭力,報效國家。我既職司參贊,我亦可以分領人馬,率衆殺賊。至於勝敗,仗聖上洪福罷了。”
林潤道:“依小侄主見:到江南省他二人舉動,若所行合道,與他共奏膚功;若事務掣肘,便當先行參奏,亦不肯與伊等分受老師費餉、失陷城郭之罪。”
文煒道:“凡參奏權奸,求其濟事。文華與嚴嵩乃異姓父子,聖上又惟嚴嵩之言是聽。年來文武大臣,被其殘害殺傷者,不知多少!量我一個僉都御史,彈劾他到那裏?我此刻到趙大人、胡大人處走走。”
隨即吩咐,寫了個晚生帖與文華,一個門生帖與胡宗憲,是爲他曾做河南軍門,在營中獻策得官故也。
原來宗憲自罷職後,便欲回鄉,嚴嵩許下他遇便保奏,因此他住在京師。
文煒先到文華府第,見車馬紛紛,拜賀的真不知有多少。
帖子投入,門上人回覆:“去嚴府未回。”
又到胡宗憲門上,拜喜的也甚多,大要多不相會。帖子投入,胡宗憲看了冷笑道:“這小畜生,又與我稱呼起門生來了!當年在聖駕前,幾乎被他害死!既認我做老師,這幾年爲何不早來見我?”
本意不見,又想了想:“他如今的爵位與我一般,況同要平倭寇,少不得要會面的。”書呆子心性,最愛這“門生”二字,隨吩咐家人:“開中門相請。”
文煒既與他門生帖子,便不好走他的中門,從轉自傍邊入來,直到二門前,方見宗憲緩步從廳內接出來。文煒請宗憲上坐叩拜,宗憲不肯,斜着身子以半禮相還。
禮畢,文煒要依師生坐次,宗憲心上甚喜,定以賓主禮。
相讓坐了,卻自將椅兒放在上一步,仍是師生的坐法。文諱道:“自從歸德拜違,只擬老師大人文旌旋里,以故許久未曾叩謁。昨聖上命下,始知養靜都中。疏闊之罪,仰祈鑑宥!”
宗憲道:“老夫自遭逐棄,便欲星馳歸裏,視塵世富貴,無異浮萍。無奈舍親嚴太師百法款留,堅不可卻。老夫又恐重違其意,只得鼠伏都門;又兼時抱啾疾,應酬盡廢。年來不但同寅,即至好交情?亦未嘗顧盼老夫。孟浩然詩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正老夫之謂也。”
文煒道:“八荒九極,佇望甘霖久矣。將來綸扉重地,嚴太師外,舍老師其誰屬?今果楓宸特眷,加意老臣。指顧殄殲倭寇,門生得日親几杖,欽聆教主,榮幸奚似!”
宗憲道:“老寅長,‘門生’二字,無乃過謙!”
文煒道:“歸德之役,端賴老師培植,是牛溲馬渤,當年既備籠中,而土簋陶匏,寧敢忘今日宰匠耶?”
宗憲道:“昔時殿最奏功,皆邦輔曹公之力,老夫何與焉?師生稱呼,老夫斷不敢當!”
文煒道:“天下委土固多,而高山正自不少。曹大人吹噓於後,實老師齒芬於前之力也。安見曹大人可爲老師,而大人不可爲老師乎?”
宗憲聽了,心上快活起來,不禁搖着頭,閉着目,仰面大笑道:“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文煒作揖起謝,宗憲還了半個揖,依就坐下。宗憲道:“賢契固執若此,老夫亦無可如何!”
文煒道:“適承趙大人枉顧,言在明午起身,未知老師酌在何時?”
宗憲道:“今日之事,君事也。他既擬在明午,即明午起身可耳。”
文煒道:“聞倭寇聲勢甚大,願聞老師禦敵之策。”
宗憲道:“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又何必計其聲勢爲哉?”
文煒心裏說道:“許多年不見他,不意比先越發迂腐了。”隨即打一恭告別,宗憲止送在臺階下,就不送了。
文煒回家,也有許多賀客,只得略爲應酬,連夜收拾行李,派了隨從的人役。次日早,又到趙文華家,卻好胡宗憲亦在,文華留吃了早飯,一同到嚴府中請示下。嚴嵩說了幾句審時度勢用兵的常套話兒,一同出來,議定本日午時出京。
文煒回家,囑託林潤擇日打發家眷回河南,隨與宗憲先行,趙文華第二次走,約在山東泰安州會齊。早有兵部火牌,傳知各路伺候夫馬。到了泰安,闔城文武都來請候,支應兩人一切。
等了八九天,還不見趙文華到來。
不想文華回拜了賀客各官,嚴世蕃又通知九卿與他送行,酒筵直襬至蘆溝橋。凡所過地方,文武官,俱出城迎接二十里。
次日起身,還要送出郊界外。公館定須縣燈結綵,陳設古玩。
他住的房,用白綾作頂棚,緞子裱牆壁。跟隨的人,也要間間房內鋪設整齊。就是馬棚,亦須粉飾乾淨。內外院都用錦紋、五色氈氈鋪地。他每住一宿,連跟隨人,大約得十一二處公館方足用。上下酒席、諸品珍物,無不精潔。每食須二十餘桌,還要嫌長道短,打碗摔盤,也有翻了桌子的時候。少不如意,家丁們便將地方官辱罵,參革、發遣的話,個個口中煉的透熟,比幾十只老虎還兇。至於驛站,更難支應,不是嫌馬匹老瘦,就是嫌數目不足,毆打衙役,鎖拿長隨,再不然回了趙文華,就不走了。地方官兩三天家支應,耗費不可數計,雖說出在地方官,究之無一不出在百姓。有那靈動知竅的官兒,孝敬趙文華若干,與跟隨的人若干;按地方大小饋送,爭多較少,講論的和做買賣一般。銀錢使用到了,你便與他主僕豆腐、白菜喫,他還說清淡的有味;文華還要傳入去,賜坐留茶,許保舉話。
各地方官知他這風聲,誰不樂得省事?就是極平常的州縣,也須那移送他。他又不走正路,只揀有州縣處繞着路兒走,二三十里也住,五六十里也住。由京至山東泰安,不過十數天路,他到走了三四十五天。人都知道他是嚴嵩的乾兒子,誰敢道個“不”字?
及至到了泰安,朱文煒問他來遲之故,他便直言,是王公大臣與他送行,情面上卻不過,因此來遲。文煒將河南、山東領兵各將官投遞職名稟帖,並兩處巡撫起兵的文移,軍門的知會,着他看視。他見兩省軍兵已等候了數天,日日坐耗無限糧草,只得擇吉日起身。到了王家營,又裝做起病來,也不過黃河,也不行文通知江、浙兩省,連胡、朱二人面也不見了。浙江告急文書,雪片般飛來,他又以河、東兩省人馬未齊諮覆。
文煒看的大不成事,常到文華處聽候,催他進兵。
文華被催不過,方行文江南文武,要於各路調集水師八萬,大小戰船三千隻,在鎮江府停泊,聽候徵進。江南大小文武,那一個敢違他意旨?只得連夜修造戰船,並調集各路人馬。幸喜文書上沒有限定日月,尚得從容辦理。又過了月餘,通省水師俱到鎮江聚齊,文武大員俱在府城等候,各差官到王家營迎請欽差驗兵。文華方發了火牌,示諭起程日期。又飾知淮安府,備極大船一千隻,由淮河進發。到了揚州,彼時揚州鹽院是鄢懋卿,與文華同是嚴嵩門下。懋卿將三個欽差請入城中,日日調集梨園子弟看戲。文煒恐軍民議論,親自催促文華動身。文華因各商與他湊送金銀未齊,着文煒同宗憲領河、東人馬先行,約在三日後即到鎮江。文煒無奈,只得率衆先行。督撫等官俱問文華不來原故,文煒只得說他患病在揚州。究之各官,早知他在鹽政衙門頑鬧,又知鄢懋卿派令各商攤湊金銀相送,不過背間嘆息而已。
又等了數天,文華方纔到來。看見兵,說兵不好;看見船,說船不好。把失誤軍機參革斬首的話,在嘴裏直流。着江南文武各官,另與他揀選兵將,更改戰船。那些大小文武官員,也都知道他的意思,或按營頭,或按地方,暗將金銀饋送,方纔將兵、將船隻鬧罷。他又要水陸分兵,着江南文武與他調戰馬五千匹,限半個月匯齊。那些督撫、提鎮又知他心上的毛病,總辦來,他不是嫌老,就是嫌瘦;於是各派屬員,每馬一匹捐銀若干,各按州縣所管莊村堡鎮,着百姓或按戶、或按地交送本地方官,星夜解送軍營;又暗中與文華饋獻。此時浙江雖遭倭寇塗炭,還是一處有,一處沒有。自趙文華到江南,通省百姓,沒一家不受其害。究竟他所得,不過十分之四;那六分,被承辦官,以及書吏、衙役、地方鄉保人等分肥。他要了這幾個錢不打緊,被衙門中書役人等,逼的窮百姓賣兒女、棄房產、刎頸跳河、服毒自縊而死者,不知幾千百人。那一個不欲生食其肉,咒罵又何足道耶!
朱文煒見風聲甚是不妥,打算着據實參奏。嚴嵩在內,這參本斷斷到不了朝廷眼中,只有個設法勸止他爲妥。於是親見文華,說道:“浙江屢次報警,近又失紹興等地,與杭州止一江之隔;倘省城不保,非僅張經一人之罪也!且外邊謠言,都說我們刻索官民,鯨吞船馬銀兩,老師糜費,流害江南。況自出京以來,兩月有餘,尚未抵浙江邊境,擁兵數萬,行旅爲之不通。倘朝廷查知,大人自有回天之力,晚生輩職司軍務,實經當不起!祈大人速行起兵,上慰宸衷,下救災黎,真萬代公侯之事也!”
趙文華聽了,佯爲喫驚道:“我們品端行潔,不意外邊竟作此等議論,深令人可怒,可恨!”
說罷,兩隻眼看着文煒,大笑道:“先生請放開懷抱,你我誰非憂國憂民之人?兩日後,弟定有謀畫請教。”
文煒辭了出來,到胡宗憲處,將適才向趙文華的話詳細說了一遍。宗憲大驚道:“賢契差矣!這話得罪他之至。這還得我替你挽回!趙大人他有金山般靠依。我輩當此時,只合飲醇酒,談詩賦,任他所爲。怎麼將外邊議論話都說了?”
說罷,閉住眼,只是搖頭。文煒道:“門生着趙大人見罪,總死猶生;若將來着聖上見罪,雖生猶不如死也!”
於是辭出回寓。
且說趙文華聽了文煒這幾句話,心中大怒!又想着胡宗憲當日,也是朱文煒在聖駕前參奏壞的,若不早些下手,被他參奏在前,雖說是有嚴太師庇護,未免又費脣舌。思索了半晌,便將伺候的人退去,提筆寫道:
兵部尚書趙文華、右僉都御史胡宗憲一本,爲參奏事。前浙江撫臣王忬,縱寇養奸,廢弛軍政,致令倭賊攻陷浙省府縣等地,始行奏報。蒙聖恩高厚,免死革職;命臣總督軍馬,協同僉都御史臣朱文煒、胡宗憲,殄滅醜類。臣奉命之日,夙夜冰兢,惟恐有負重寄,於五月日星馳王家營地界,守候一月餘,河、東兩省人馬陸續方至。臣知倭賊勢重,非一旅之師所能盡殲,旋行文江南文武,調集水軍,分兩路進剿,臣在鎮江暫行等候。又念浙民日受屠茶,若俟前軍齊集,恐倭賊爲患益深;因思朱文煒平師尚詔時,頗著謀猷,令其先統河、東兩省人馬,與浙撫張經會同禦寇;臣所調江南水軍一到,即行策應。奈文煒恃平師尚詔微功,不屑聽臣指使,臣胡宗憲亦屢促不行,羈延二十餘日,使撫臣張經全師敗沒;又將紹興一帶地方,爲賊搶劫,殺害官民無算。目今賊去杭州止一江之隔,倘杭州一失,而蘇、常二州勢必震動。是張經喪師辱國之由,皆文煒不遵約束所致也。軍機重務,安可用此桀驁不馴之員?理合題參,請旨速行正法,爲文武各員玩忽者戒。仰祈聖上乾斷施行。謹奏。
趙文華寫畢,差人將胡宗憲請來,向袖內取出參文煒的彈章,遞與宗憲看。宗憲看罷,驚問道:“大人爲何有此舉動,且列賤名。”
文華冷笑道:“朱文煒這廝,少年不達時務,一味家多管閒事。方今倭寇正熾,弟意浙撫張經必不敢坐視,自日夜遣兵爭鬥;爲保守各府縣計,就如兩虎相搏,勢必小死大傷;待其傷而擊之,則權自我矣。無如文煒這蠢才,不識元機,刻刻以急救浙江咶噪人耳。誠恐他胡亂瀆奏起來,我輩反落他後。當日大人被他幾句話,將一個軍門輕輕丟去,即明驗也。今請大人來一商,你我同在嚴太師門下,自無不氣味相投。弟將尊諱已開列在本內,未知大人肯俯存否?”
宗憲道:“承大人不棄,深感厚愛。只是這朱文煒是小弟門生,請將本內‘正法’二字,改爲‘嚴處’何如?”
文華大笑道:“胡大人真是長者,仕途中是一點忠厚用不得!只想他當年奏對師尚詔話,那時師生情面何在?”
宗憲道:“寧教天下人負我罷了。”
文華又大笑道:“大人書氣過深,弟到不好違拗,壞你重師生而輕仇怨之意,就將‘正法’二字,改爲‘革職’罷。只是太便宜他了!”
宗憲即忙起身叩謝。文華道:“機不可泄,大人務要謹密!”
宗憲道:“謹遵臺命!”
又問起本日期,文華道:“定於明早拜發。”
宗憲告別。
正是: 大難臨頭非偶然,此逢蟒婦彼逢奸。 賊臣妖物皆同類,毒害殺人總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