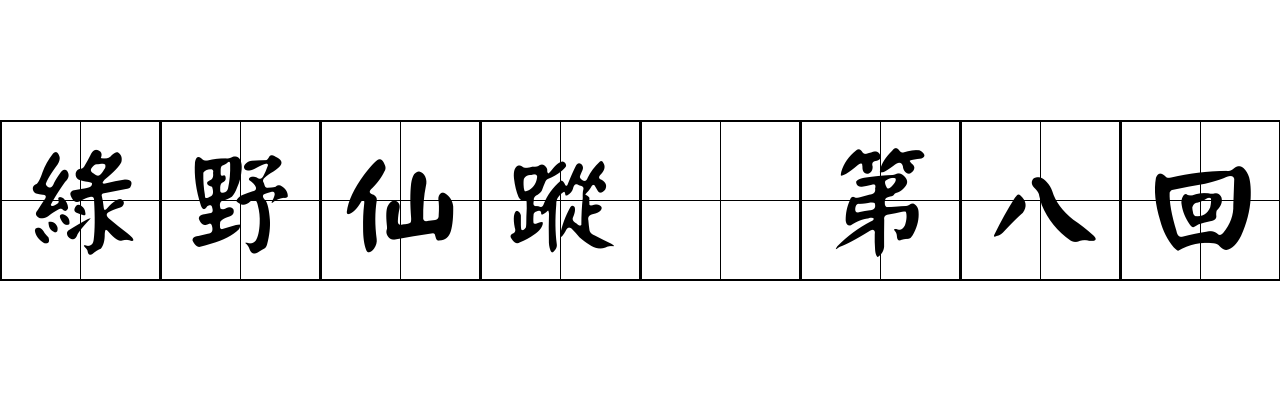綠野仙蹤-第八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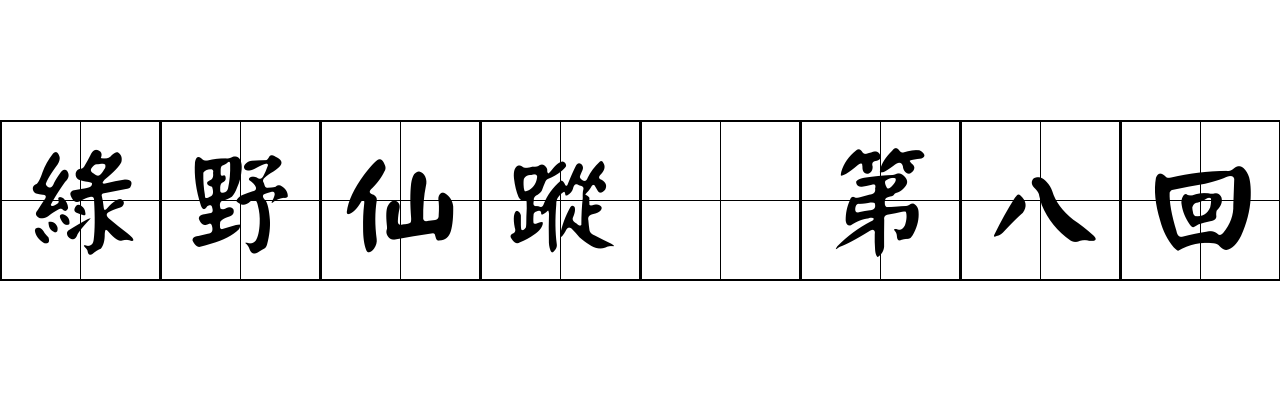
《綠野仙蹤》是一本世情小說更多於志怪小說。冷於冰在其成仙的道路上,收徒並且幫助其親人弟子誅殺爲禍世間的妖怪。人情關係很多時候影響了原本屬於志怪小說的天馬行空的特點。從文筆和批註來看,本書也很能反映古代小說的特點,也是明清小說的一個代表。
泰山廟於冰打女鬼 八里鋪俠客趕書生
詞曰: 清秋節,楓林染遍啼鵑血。啼鵑血,數金銀兩,致他生絕。 殷勤再把俠客說,愁心姑且隨明月。隨明月,一杯將盡,數聲嗚咽。 ——右調《憶秦娥》。
且說於冰被那文怪鬼弄了半夜。天明出來,日日在山溪中行走。崎崎嶇嶇,繞了四五天,方出了此山,到了一大溝內;中間都是沙石,兩邊都是層巖峭壁。東首有一山莊,問人,名爲輝耀堡,還是通京的路。他買些酒飯充譏,不敢往東走,順着往西走。行了數日,已到山西地界。他久聞山西有座五臺山,是萬佛福祥之地;隨地問人,尋到山腳下,遇着幾個採樵人,問上山路徑。那些人道:“你必是外方來的,不知朝臺時令,徒費番跋涉。此地名爲西五臺,還有個東五臺,兩臺俱有勝景,有寺院,有僧人;每年七月十五日方開廟門,到八月十五日關閉朝臺,男女成千累萬不絕。如今是九月中旬,那裏還有第二個人敢上去?況裏邊蛇蟲虎豹、妖魔鬼怪最多,六月間還下極大的雪,休說你渾身通是夾衣,就是皮衣也保你凍死。”
於冰聽了,別的都不怕,倒只怕冷,折轉身又向西走。
走了幾天,一日行到代州地方,日色已落,遠遠的看見幾家人家;及至到了跟前,不想是座泰山娘娘廟。但見:
鐘樓倒壞,殿字歪斜,山門盡長蒼苔,寶閣都生荒草。紫霄聖母,迥非金斗默運之時;碧霞元君,大似赤羽逢劫之日。試看獨角小鬼,口中鳥鵲營巢;再觀兩旁佳人,耳畔蜘蛛羅網;沒頭書吏,猶捧折足之兒;斷臂奶孃,尚垂破胸之乳。正是修造未卜何年,摧提只在目下。
於冰看了一會,止見腐草盈階,荒榛遍地,西廊下塑着許多攜男抱女的鬼判,半是少頭沒腳。正面大殿三間,看了看,中間塑着三位娘娘,兩邊也塑着許多侍候的婦女。於冰見是女廟,不好在中歇臥,恐怕褻瀆他。出來東廊下,一看見一個赤發環眼大鬼,同一個婦人站在一處;那婦人兩手捧着個盤子,盤子內塑着幾個小娃兒,坐着的、睡着的,倒也有些生趣。
於冰看了,笑說道:“你兩個這身子後邊,便是我的公館了。今晚我同你們作伴罷。”話說着,把地下土用衣襟拂了幾拂,斜坐在二鬼背後;再瞧天光,已是黃昏時分。看罷,將頭向大鬼腳上一枕。方纔睡倒,只見廟外跑入個婦人來,紫襖紅裙,走動如風,從目前一瞬,已入殿內去了。於冰驚訝道:“這時候怎有婦人獨來?”
言未畢,只見那婦人走出殿外,站在臺階上,象個眺望的光景。於冰急忙坐起從大鬼腿縫中一看,只見那女人面若死灰,無一點生人血色;東張西望,兩隻眼睛閃閃灼灼的顧盼不測。少停,只見那女人如飛的跑出廟外去了。於冰大爲詫異,心裏想道:“此女絕非人類,非鬼即妖;看他那般東張西望光景,或者預知我今日到此,要下手我也未可知。”又想了想,笑道:“隨他去。等他尋我來,再做裁處。”
正想間,只見那婦人又跑入廟來,先向於冰坐的廊下一望,旋即又向那邊廊下一望,急急的入殿內去了。於冰道:“不消說,是尋我無疑了。”
少刻,那女人又出殿來,站在臺階上,向外一望,口裏呱呱呱長笑了一聲,倒與母雞呱蛋相似,止是聲音連貫,不象那樣的斷斷續續的叫喊,又如飛的跑出廟外去了。於冰道:“這是我生平未聞未見的怪異事。似他這樣來來往往,端的是要怎麼?”
須臾,只見廟外走入個男子來,卻頭戴紫絨氈笠,身穿藍布直裰,足登布履,腰繫搭膊,那婦人在後面用兩手推着他走。
那男子垂頭喪氣,一直到正殿臺階上坐下,眼望着西北,長嘆了一聲。只見那婦人取出個白棍兒來,長不過七八寸,在那男子面上亂圈;圈罷,便扒倒地下跪拜;拜罷,將嘴對着那男子耳朵內說話。說罷話,又在那男子面上用口吹;吹罷又圈,忙亂不一。那男子任他作弄,就和看不見的一般,瞪着眼,朝着天,想算他的事件。那婦人又如飛的跑出廟外,瞬目間,又跑入廟來,照前做作。只見那男子站起來,向那廟殿窗槅上看視,像個尋什麼東西的光景。那婦人到此,越發着急的了不得,連圈,連拜,連說,連吹,忙亂的沒入腳處,又不住的回頭向廟外看視。
只見那男子面對着窗槅看了一會,搖了幾下頭,復回身坐在臺階上。急的那婦人吹了圈,圈了拜,拜了說,說了吹,顛倒不已。少刻,只見那男子雙睛緊閉,聲息俱無,打猛哩大聲說道:“罷了!”隨即站起,將腰間搭膊解下,向那大窗槅眼內入進一半去,又拉出一半來。只見那婦人,連忙用手替他挽成個套兒,將男子的頭搬住,向套兒裏亂塞。那男子兩手捉住套兒,面朝廟外又想。那婦人此時更忙亂百倍,急圈,急說,急拜,急吹,恨不得那男子登時身死方快。
於冰看了多時,心裏說道:“眼見這婦人是個吊死鬼,只怕我力量對他不過,該怎處?”又想道:“我若不救此人,我還出什麼家,訪什麼道?”想罷,從那大鬼背後走出,用盡生平氣力,喊叫了一聲。只見那婦人喫一大驚,那男子隨聲蹲在大殿窗槅下。那婦人急回頭,看見於冰,將頭搖了兩搖,頭髮披拂下來,用手在臉上一摸,兩眼角鮮血淋漓,口中吐出長舌,又咶咶咶了一聲,如飛的向於冰撲來。
於冰此時又沒個東西打他,瞧見那泥婦人盤子內,有幾個泥娃子,急忙用手搬起一個來。卻好那婦人剛跑到面前,於冰對準面門,兩手用力一擲,喜得端端正正,打在那婦人臉上,那婦人便應手而倒。於冰即忙看視,見他一倒即化爲烏有,急急向四下一望,形影全無,止見那男子還蹲在階上。於冰起先到毫無怕意,今將此婦打無,不由的身冷發豎,有些疑懼起來。於是又搬了個泥娃子,提在手內,先入殿中,次到西廊,都細看了,仍是一無所有。隨將那泥娃子放在階上,到那男子面前,也蹲在槅子下,問道:“你這漢子,爲着何事,卻行此短見?”問了幾聲,那男子總不言語。
於冰道:“你這人好癡愚,你既肯捨命上吊,你到不肯向我一說麼?”那人道:“說也無益,不如死休。”又道:“你既這般諄諄問我,我只得要說了。離此廟五里,有一範村,就是我的祖居。我父母俱無,止有一個妻房,到生了兩個兒子,三個女兒,十二三歲的也有,六七歲的也有。一家兒六七口,都指我一人養活。我又沒有田地耕種,不過與人家傭工度日,今日有人用我,我便得幾個錢養家,明日沒人用我,我一家就得忍飢。本村有個張二爺,是個仗義好男子,我也常與他家做活。他見我爲人勤謹,又知我家口衆多,情願借與我二十兩銀子,不要利錢,三年後還他,着我拿去做一小生意。我承他的情,便去雁門關外販賣燒酒。行至東大峪,山水陡至,可惜七馱酒、七個驢,都被水衝去。我與驢夫上了樹,才留得性命。
二十兩本銀全丟,還害了人家七個驢的性命,回家沒面目與張二爺相見。不意人將折了本錢的話,向他說知,那張二爺將我叫去,備細問了原由,反大笑起來,說道:‘這是你的運尚未通。我今再與你二十兩,還與你一句放心話:日後發了財還我,沒了也罷了。’我又收他銀兩,開了個豆腐鋪兒,半年來,到也有點利息。又不合聽了老婆話,說磨豆腐必須養豬,方有大利。我一時沒主見,就去代州販豬。走了兩天,都不喫食水,到第三天,死了兩個,昨日又死了一個。我見事已大壞,將剩下這兩口豬要出賣於人,人家說是病豬,不買,沒奈何減下價錢,方得出脫乾淨。連死的並活的,止落下五兩九錢銀子,到折了十三兩九錢本兒。我原要回家,將這五兩多銀子交與妻子,再尋死路。不期走到這廟前,越想越無生趣,不但羞見張二爺,連妻子也見不得。”說罷,拍手頓足,大哭起來。
於冰道:“你且莫哭,這十三四兩銀子,我如數還你。”
那男子道:“我此時什麼時候,你還要打趣我。”於冰道:“你道世上只有個姓張的幫人麼?”隨向身邊取出銀包,揀了三錠道:“這每錠是五兩,夠你本錢有餘。”說着,將銀子向那男子袖中一塞。那男子見銀入袖中,心下大驚,一邊止住淚痕,一邊用眼角偷視於冰,口裏哽哽咽咽的說道:“只怕使不得,只怕天下無此事,只怕我不好收他。”於冰笑道:“你只管放心拿去,有什麼使不得?有什麼不好收處?”那男子一蹶劣站起來道:“又是個重生父母了。”連忙跳下殿階,扒倒地下,就是十七八個頭,碰的地亂響。於冰扶他起來。那男子問於冰道:“爺臺何處人?因何黃昏時分在這廟中?”於冰道:“我是北直隸人,姓冷。我還沒有問你的名姓。”那男子道:“小人叫段祥,這廟西北五里,就是小人的住家。冷爺此時在這廟中,有何營幹?”於冰道:“我因趕不上宿頭,在此住一宿。”
段祥道:“小人家中實不乾淨之至,還比這廟內暖些,請冷爺到小人家中。”於冰道:“我還要問你,你到這廟中,可曾看見個婦人麼?”段祥道:“小人沒有看見。”於冰道:“你來這廟中,就是爲上吊麼?”段祥道:“此廟系小人回家必由之路。只因走到廟前,心內就有些糊塗,自己原不打算入廟,不知怎麼就到廟中。及至到了廟內,心緒不寧,只覺得死了好。適才被冷爺大喝了一聲,我纔看見了,覺得心上才略略有點清爽。”於冰道:“你可聽見有人在你耳中說話麼?”段祥道:“我沒聽見,我到覺得耳中嘗有些冷氣貫入。冷爺問這話必有因。”於冰笑道:“我也不過白問問罷了。”段祥又急急問道:“冷爺頭前問我看見婦人沒有,冷爺可曾看見麼?”於冰笑道:“我沒見。”段祥大叫道:“不好了!此地繫有名的鬼窩,獨行人白天還不敢來,快走罷。”於冰笑道:“就是走,你也該將搭膊解下來。”段祥連忙解下來系在腰間,將於冰與他的銀子分握在兩手內,讓於冰先出廟去。到了廟外,偏又走在於冰前面,東張西望,不住的催於冰快走。
到了家門首叫門,裏邊一個婦人問道:“可是買豬回來麼?”
段祥道:“還說豬哩,我幾乎被你送了命。快開門,大恩人到了。”待了一會,婦人將門兒開放,段祥將於冰讓入房內,於冰見是內外兩間,外房內有些磨子、鬥盆、木槽、碗罐之類,又讓於冰坐在炕上,隨入內房好半晌。少刻,見一婦人,領出四五個小男女,與於冰叩頭。於冰跳下炕來還禮。婦人道:“今日若不是客爺,他的性命不保。”說了這兩句。便滿面羞澀,領上娃子們入去。段祥復讓於冰坐下,又聽得內房風匣響。須臾,段祥拿出一大碗滾白水來,說道:“連個茶葉也沒有。”於冰接在手內道:“極好。”段祥又頓出一大沙壺燒酒,兩碟鹹菜,出去買了二十個小饅頭,配了一碗炒豆腐,一碗調豆腐皮,擺列在一小木桌上,與於冰斟了酒,又叩謝了。於冰讓他同坐。
兩人喫着酒,段祥又問起那婦人的話,於冰備細說了一遍,段祥嚇的毛骨悚然,又在炕上叩頭,直話談到三鼓已過方歇。次早於冰要去,段祥那裏肯放,於冰又絕意要行,嚷鬧了好半晌,於冰吃了早飯,問明去向,又親送了十五六裏,流着眼淚回家。
於冰離了範村,走了兩天,只走了九十餘里。第三日,從早間走至交午,走了二十里,見有兩座飯鋪。於冰見路北鋪內人少,走去坐下,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小夥計道:“這叫八里鋪,前面就是保德州。”
於冰要了四兩燒酒,吃了一杯,出鋪外小便。猛聽得一人道:“冷爺在這裏了!”
於冰回頭一看,卻是段祥,扯着一個騾子,後面相隨着一人,騎着極大極肥的黑驢,也跳下來交與段祥牽住。於冰將那人一看,但見:
熊腰猿臂,河目星瞳,紫面長鬚,包藏着吞牛殺氣;方頤海口,宣露出叱日威風。頭帶魚白卷檐氈帽巾,身穿寶藍剪袖皮襖。雖無弓矢,三岔路口自應喝斷人魂;若有刀槍,千軍隊裏也須驚破敵膽。
於冰看罷,心裏說道:“這人好個大漢仗!又配了紫面長鬚,真要算個雄偉壯士。”
只見段祥笑說道:“冷爺走了三天,被我們一天半就趕上了。”
又見那大漢子問段祥道:“這就是那冷先生麼?”
段祥道:“正是。”
那大漢向於冰舉手道:“昨日段樣說先生送他銀子,救他性命,我心上甚佩服,因此同他來追趕,要會會先生。”
於冰道:“偶爾相遇,並非義舉,些須銀兩,何足掛齒!”
說罷,兩人一揖,同入飯館內坐下。於冰道:“敢問老長兄尊姓大名?”
那漢子道:“小弟姓張,名仲彥,與段祥同住在範村。先生尊諱可是於冰麼?”
於冰道:“正是賤名。”
仲彥道:“先生若不棄嫌,請到小弟家下住幾天,不知肯否?”
於冰道:“小弟弟飄蓬斷梗之人,無地不可佇足,何況尊府!既承雲誼,就請同行。”
仲彥拍案大叫道:“爽快!爽快!”
又叫走堂的吩咐道:“你這館中未必有什麼好酒菜、可將喫得過的,不拘葷素,盡拿來,不必問我;再將頂好的酒拿來幾壺,我們吃了還要走路。快着!快着!”
於冰道:“小弟近日總止喫素,長兄不可過於費心。”
少刻,酒菜齊至。仲彥一邊說着話兒,一邊大飲大嚼。於冰見他是個性情爽直人,將棄家訪道的話大概一說,仲彥甚是歎服,酒飯後,段祥算了賬,於冰騎了騾子,仲彥騎了驢兒,段祥跟在後面,一路說說笑笑。談論段祥遇鬼的話;說到用泥娃子打倒鬼處,仲彥掀髯大笑道:“小弟生平不知鬼爲何物,偏這樣有趣的鬼被先生遇着,張某未得一見,想來今生再不能有此奇遇也。罷了!”
於是三人一同入範村。
正是: 從古未聞人打鬼,相傳此事足驚奇; 貧兒戴德喧名譽,引得英雄策蹇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