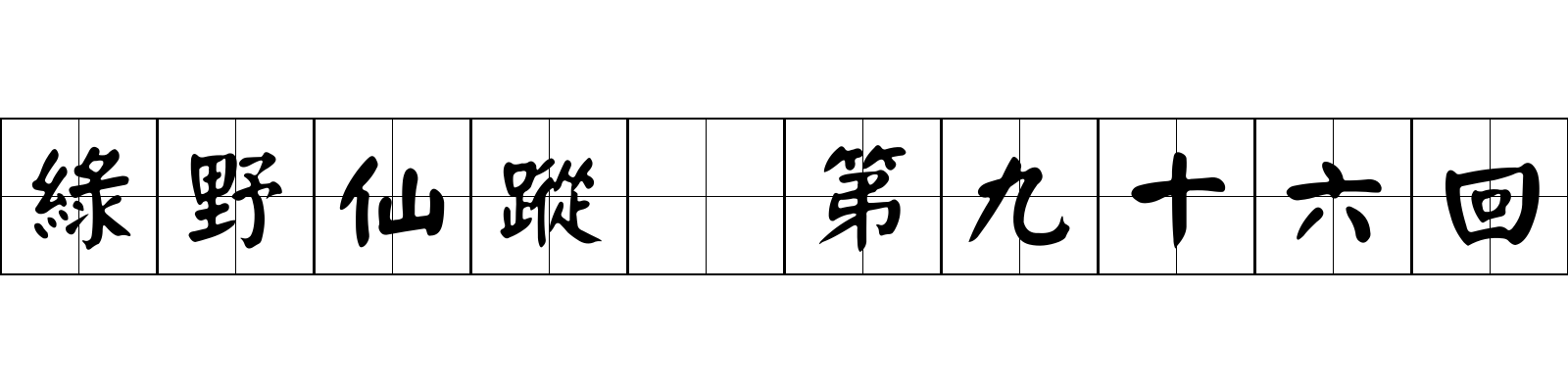綠野仙蹤-第九十六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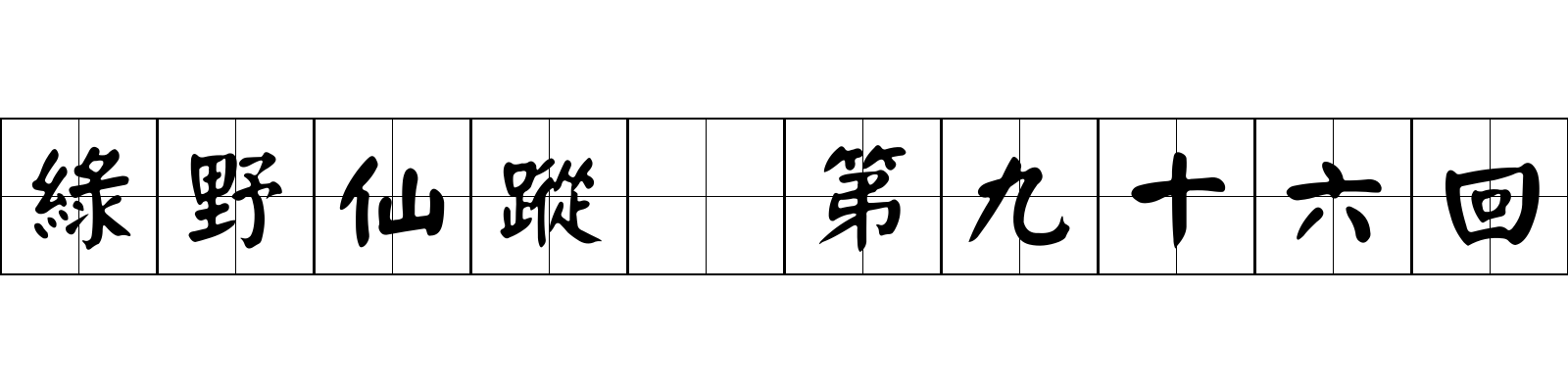
《綠野仙蹤》是一本世情小說更多於志怪小說。冷於冰在其成仙的道路上,收徒並且幫助其親人弟子誅殺爲禍世間的妖怪。人情關係很多時候影響了原本屬於志怪小說的天馬行空的特點。從文筆和批註來看,本書也很能反映古代小說的特點,也是明清小說的一個代表。
救家屬城璧偷財物 落大海不換失明珠
詞曰: 一陣奇風迷舊路,得與兒孫巧遇。此恨平分取,夜深回裏偷銀去。 不換相逢雲會聚,誇耀明珠幾度。落海非無故,兩人同到妖王處。 ——右調《惜分飛》。
且說連城璧同衆道友在半空中觀望,被一陣大風將城璧飄蕩在一洞岸邊落下。只見雪浪連天,濤聲如吼。城璧道:“這光景到像黃河,卻辨不出是什麼地方?”
猛見河岸上流頭來了幾個男女,內中一五十多歲人,同一十八九歲少年,各帶着手肘鐵煉,穿着囚衣步走。又見一少年婦人騎着驢兒,懷中抱着個兩三歲的娃子,同一十二三歲的娃子,也騎着驢兒,相隨行走。前後四個解役押着,漸次到了面前。那年老犯人一見城璧,便將腳步停住,眼上眼下的細看,一個差役着:“你不走做什麼?”
那囚犯也不回答,只將城壁看。看罷問城璧道:“臺駕可姓連麼?”
城璧道:“你怎麼想到我姓連?”
那犯人又道:“可諱城璧麼?”
城璧深爲駭異,隨應道:“我果是連城璧。你在何處見過我?”
那囚犯聽了,連忙跪倒,撾住城璧的衣襟大哭。城璧道:“這是怎麼?”
此時衆男婦同解役俱各站住,只見那囚犯道:“爹爹認不得我了?我就是兒子連椿。”又指着那十八九歲囚犯道:“那是大孫兒。”指着騎驢的十二三歲娃子道:“那是第二個孫兒。那婦人,便是大孫媳婦。懷中抱的娃子,是重孫兒。與爹爹四十來年不曾一面,不意今日方得遇着。”
說罷,又大哭。幾個解役合籠來細聽。城璧見名姓俱投,復將犯人詳視:見年已近老,囚首垢面,竟認不出。心裏說道:“我那年出門時,此子才十八歲,今經三四十年,他自然該老了。”
再細看眉目骨格,到的還是,也不由的心上一陣悽感,只是沒吊出淚來。急問道:“你們住在那裏?”
連椿道:“住在山西範村。”
這話越發是了。城璧道:“因何事押解到此?”
連椿道:“由範村中,從代州遞解來的。”
城璧道:“你起來。”
連椿扒起,拂拭淚痕。正欲叫兒子們來見,一個解役喝住,一個解役問城璧道:“你可認真他是你的兒子麼?”
城璧道:“果然是我的兒子。”
又一個解役道:“我看這道人高高大大,雄雄壯壯,年紀不過三十三四歲人,怎便有這樣個老兒子?不像,不像!”
又一個解役道:“你再曉得修養裏頭的元妙,你越發像個人了。現見他道衣、道冠,自然是個會運氣的人。”
說罷,又問道:“你就是那連城璧?”
城璧道:“我是,你要怎麼?”
四個解役互相顧盼,一個道:“你兒子連椿事體破露,還是因前案發覺。此地是河南地方,離陝州不過十數裏。我們意思,要請你同去走遭,你去不去?”
城璧道:“我不去。”
解役道:“只怕由不得你。”
又一個道:“和他商量什麼?他是有名大盜,我們遞解牌上還有他的事由,鎖了就是。”
衆解役便欲動手。城璧道:“不必。我有要緊話說。”
衆解役聽了,便都不動作,忙問道:“你快說,事關重大。事了你,就是大人的銀子,那私不及公的小使費免出口。”
城璧道:“他們實系我的子孫,我意思和你們討個情分,將他們都放了罷。”
四個解役都大笑道:“好愛人冠冕話兒,說的比屁還脆。”
只見一個少年解役大聲道:“這還和他說什麼?”
伸着兩隻手,虎一般拿城璧。城璧右腳起處,那解役便飛了六七步遠,落在地下發昏。三個解役都嚇呆了,城璧問連椿道:“此地非說話之所,你看前邊有個土岡,那土岡後面,想必僻靜。可趕了驢兒,都跟我來。”
說罷,大踏步先走。連椿等男女後隨,同到土岡後面。
城璧坐在一小土堆上,將連椿和他大孫兒各用手一指,鐵煉手肘,盡行脫落。連椿向城璧道:“爹爹修道多年,竟有此大法力!”
城璧道:“這也算不得大法,不過解脫了,好說話。”
只見他大孫兒將婦人和小娃子各扶下驢來。到城璧面前跪倒叩頭。連椿俱用手指着,說道:“這是大孫兒開祥。”
城璧看了看,囚衣囚面,不過比連椿少壯些。又指着十二三歲娃子道:“這是二孫兒開道。”
城璧見他眉目甚是清秀,心上又憐又愛,覺得有些說不來的難過。又見他身上止穿着一件破單布襖。褲子只有半截在腿上,不知不覺的便吊下幾點淚來。將開道叫至膝前,拉住他的手兒,問了會年歲多少,着他坐在身傍。向連椿道:“怎麼你們就窮到這步田地?”
正言間,那少年婦人將懷中娃子付與開祥,也來叩拜。城璧道:“罷了,起去罷。你們大家坐了,我好問話。”
連椿等俱各坐下。
城璧道:“你們犯了何罪?怎孫婦也來?你母親哩?”
連椿道:“母親病故已十七年了,兒婦是前歲病故。昔日爹爹去後只三個來月,便有人於四鼓時分送家信到範村。字內言因救大伯父,在泰安州劫牢反獄,得伯父冷於冰相救,安身在表叔金不換家,着我們另尋地方遷移。彼時我和堂兄連柏公寫了回信,交付送字人。五鼓時去訖,不知此字爹爹見過沒有?”
城璧道:“見過了。”
連椿道:“後來見範村沒一點風聲,心想着遷移最難。況我與堂兄連柏俱在那邊結了婚姻,喜得數年無事。後我母親病故,堂兄聽堂嫂離間之言,遂分家居住。又喜得數年無事。後來堂兄病故,留下堂侄開基,日夜嫖賭,將財產蕩盡,屢次向我索取銀錢,堂嫂亦時常來吵鬧。如此又養育了他母子好些年頭。今年二月,開基陡來家中,要和我從新分家。說財產都是我大伯父一刀一槍捨命掙來的。我因他出言無狀,原打了他頓。誰想他存心惡毒,寫了張呈詞,說大伯父和爹爹曾在泰安劫牢反獄,拒敵官軍,出首在本州案下。本州老爺將我同大孫兒拿去,重刑拷問,我受刑不過,只得成招。上下衙門往返審了幾次,還追究爹爹下落。後來按察司定了罪案,要將我們發配遠惡州郡。虧得巡撫改配在河南睢州,同孫婦等一家發遣,一路遞解至此。”
說罷,同開祥俱大哭起來。
城璧道:“莫哭。我問你,傢俬抄了沒有?”
連椿道:“本州系新到任官,深喜開基出首報上司文書,止言有薄田數畝,將我所有財產,盡賞了開基。聽得說,爲我們這事,將前任做過代州的都問了失查處分,目今還行文天下,要拿訪爹爹。”
城璧道:“當年分家時,可是兩分均分麼?”
連椿道:“我母親死後,便是堂兄管理家務。分家時,各分田地二頃餘,銀子四千餘兩,金珠寶玩,堂兄拿去十分之七,我只分得十分之三。”
城璧道:“近年所存銀兩,你還有多少?”
連椿道:“我遭官司時,還現存三千六百餘兩,金珠寶玩,一物未動。這幾個月,想也被他耗散了許多。”
城璧聽完,口中雖不說開基一字不是,卻心中大動氣憤。那小孫兒開道一邊聽說話兒,一邊爺爺長短的叫念。城璧甚是憐愛他,又着小重孫兒抱來,自己接在手中細看。見生的肥頭大臉,有幾分像自己,心下也是憐愛。
看後,付與開祥。向連椿道:“你們今日幸遇我,我豈肯着你們受了飢寒?御史林潤,我在他身上有勤勞。但他巡查江南,駐車無定。朱文煒現做浙江巡撫,且送你們到他那邊,煩他轉致林潤,安置你們罷了。”
正說着,見土岡背後有人窺探。忙站起一看,原來是那幾個解役看見城璧站在岡上,沒命的飛跑。城璧道:“這必着他們回走二百里方好。”
於是口中唸唸有詞,用手一揮,那幾個解役比得了將軍令還疾,各向原路飛走去了。
再說城璧下土岡,向連椿等道:“你們身穿囚服,如何在路行走?適才解役說此地離陝州最近,且搬運他幾件來方好。”
隨將道袍脫下,鋪在地上,口誦靈文,心注在陝州各當鋪內,喝聲“到”!須臾,道袍高起二尺有餘。將道袍一提,大小衣帽鞋襪十數件,又有大小女衣四五件,裙褲等項俱全。連椿父子兒婦一同更換,有不便更換者,還剩有五六件開祥捆起。城璧又在他父子三人腿上各畫了符篆,又在兩個驢尾骨上也畫了,向連椿等道:“昔日冷師尊攜帶我們常用此法,可日行七八百里。此番連夜行走,遇便買些飲食,喂喂驢兒。我估計有三天,可到杭州。”
令開祥搊扶着婦人和孫兒上了驢,一齊行走起來。耳邊但覺風響,只兩晝夜,便到了杭州,尋旅店住下。
問店主人,知巡撫朱文煒在官署,心下大喜。是晚起更後,向連椿等道:“你們莫睡,五鼓即回。”
隨駕雲到範村自己家中,用法將開基大小男婦禁住,點了火燭。將各房箱櫃打開,凡一應金銀寶玩,收拾在一大包袱內。又深惱知州聽信開基發覺此案,又到代州衙門,也用攝法,搜取了二千餘兩。見州官房內有現成筆硯,於牆上寫大字一行道:“盜銀者,系範村連開基所差也。”
復駕雲,於天微明時回店。此時連椿父子秉燭相候,城璧將包袱放在牀上,告訴於兩處劫取的原由。至日出時,領了開祥去街上買了大皮箱四個,一同提來。把包袱打開,見白的是銀,黃的是金,光輝燦爛的是珠寶,錦繡成文的是綢緞。祖孫父子裝滿了四大皮箱,還餘許多在外。城璧道:“這還須買兩個大箱,方能放得下。”
連椿父子問城璧道:“一個包袱便能包這許多財物。”
城璧笑道:“此攝法也。雖十萬全銀,亦可於此一袱裝來。吾師同你金錶叔用此法搬取過米四五十石,只用一紙包耳。我估計銀子有四千餘兩,還有金珠雜往物,你們可以飽暖終身矣。”
又着開祥買了兩個大箱,收存餘物。
向店主討了紙筆,寫了一封詳細書字,付一連椿道:“我去後,可將此書去朱巡撫衙門投遞,若號房並巡捕等問你,你就說是冷於冰差人面投書字,不可輕付於人。”
連椿道:“爹爹不親去麼?”
城璧道:“我有天大緊急事在心,只因遇着你們,須索耽延這幾日,那有功夫再去見他?”
又將朱文煒和林潤始末大概說了一番:“想他二人俱是盛德君子。見我書字,無不用情。此後可改名換姓,就在南方過度日月。小孫、重孫,皆我所愛,宜用心撫養。嗣後再無見面之期,你們不必計念我,我去了。”
連椿等一個個跪在地下痛哭,小孫兒開道拉住城璧一手,爺爺長短叫念起來。挨至交午時候,以出恭爲辭,出了店門揀人煙湊集處飛走,耳中還聽得兩個孫兒喊叫不絕,直走至無人地方。正欲駕雲,又想起小孫兒開道,萬一於人煙多處迷失,心上委決不下。複用隱身法術回店,見一家大人還在那裏哭泣,方放心駕雲,赴九功山來。
約行了二三刻功夫,猛聽得背後有人叫道:“二道兄等一等,我來了。”
城璧頭一看,是金不換。兩人將雲頭一會,城璧忙問道:“你從何來?師尊可有了下落麼?”
不換道:“好大風,好大風。那日被風將我捲住,直捲到我山西懷仁縣地界。離城三二里遠,才得落下。師尊到沒下落,偏與我當年後娶的許聯升老婆相遇,到知道他的下落了。”
城璧道:“可是你挨扳子的懷仁縣麼?”
不換道:“正是。我那日被風颳的頭昏眼黑,落在懷仁縣城外,辨不出是何地方。正要尋人問訊,那許聯升老婆迎面走來,穿着一身白衣服,我那裏認得他,他卻認得我。將我衣服拉住,哭哭啼啼,說了許多舊情話。又說許聯升已死,婆婆痛念他兒子,只一月光景,也死了,留下他孤身,無依無靠。今日是出城上墳,得與我相見。沒死沒活的拉住我,着我和他再做夫妻。他手中還有五六百兩財物,同過日月。我擺脫不開,用了個呆對法,將他呆住,急忙駕雲,要回九功山,與師弟兄相會。行到江南無錫縣,到耽延了兩天功夫。”
城璧道:“你在無錫做什麼?”
不換道:“我到無錫時,天已昏黑。忽然出大恭,雲落在河傍。猛見隔河起一股白光,直衝鬥牛。我便去隔河尋看,一無所有。想了想,白天還找不着九功山,何況昏夜?我便坐在一大樹下,運用內功。至三鼓後,白光又起。看着只在左近,卻尋不着那起白光的源頭,我就打算着,必是寶貝。到五鼓時,其光漸沒。我想着師尊已死,二哥和翠黛、如玉也不知被風颳於何處,我便在那裏等候了一天。至次晚,其光照舊舉發,我在河岸邊,來回尋的好苦,又教我等候了一天。到昨日四鼓時分,纔看明白,那光氣是從河內起的。我將衣服脫盡,搯了逼水訣,下河底尋找,直到日光出時,那水中也放光華。急跑至跟前一看,才得了此物。”
說着,笑嘻嘻從懷中取出一匣,將匣打開,着城璧看。城璧瞧了瞧,是顆極大的明珠。圓徑一寸大小,閃閃爍爍,與十五前後月色一般。城璧道:“此珠我實所未見,但你我出家人,要他何用?況師尊慘死,道侶分離,虧你有心情用這兩三天功夫尋他。依我說,你丟去他爲是。有他,不由的要看玩,分了道心。”
不換道:“二哥說那裏話?我爲此珠,晝夜被水冰了好幾個時辰,好容易到手,才說丟去的話。我存着他,有兩件用處,到昏夜之際,此珠有兩丈闊光華,可以代數支蠟燭。再不然,弄一頂好道冠鑲嵌在上面,戴在頭上,豈不更冠冕幾分!”
城璧大笑道:“真世人俗鄙之見也。”
不換道:“二哥這幾天做些什麼?適才從何處來?今往何處去?”
城璧道:“我和你一樣,也是去九功山訪問下落。”
遂將被風颳到河南陝州遇着子孫,如何長短,說了一遍。不換道:“安頓的極妙。只是處置連開基還太輕些。”
城璧道:“同本一支,你教我該怎麼?我在州官牆上寫那兩句,我此時越想越後悔。”
不換道:“這樣謀殺骨肉、爭奪財產的匹夫,便教代州知州打死,也不爲過,後悔什麼!”
又走了一會,城璧忽然大叫道:“不好了,我們中了師尊的圈套了。”
不換急問道:“何以見之?”
城璧道:“此事易明:偏我就遇兒孫,偏你就遇着此婦,世上那有這樣巧遇合?連我寄書字與朱文煒並轉託林潤,都是一時亂來。毫不想算:世安有三四十年長在一處地方做巡撫巡按的道理?我再問你:你在懷仁縣遇的許聯升婦人,可是六七十歲面貌,還是你娶他時二十多歲面貌?”
不換道:“若是六七十歲的面貌,我越發認不得了。面貌和我娶他時一樣。”
城璧連連搖頭道:“了不得,千真萬真,是中了師尊圈套。你再想:你娶他時,他已二十四五歲,你在瓊巖洞修煉三十年,這婦人至少也該有五十七八年紀。若再加上你我隨師尊行走的年頭算上,他穩在七十二三歲上下。他又不會學你我吞津嚥氣,有火龍祖師口訣,怎麼他就能始終不老,長保二十多歲姿容?”
不換聽了,如醉方醒。將雙足一跳,也大叫道:“不好了,中了。”
誰想跳的太猛,才跳出雲外,頭朝下吊將下去。
原來雲路行走,通是氣霧纏身,不換吊下去,城璧那裏理論?只因他大叫着說了一句,再不聽得說話。回頭一看,不見了不換,急急將雲停住,用手一指,分開氣霧,低頭下視。見大海汪洋,波翻浪涌,已過福建廈門海口。再向西北一看,纔看見不換,相離相離有二百步遠近,從半空中一翻一覆的墜下。
城璧甚是着急,將雲極力一挫,真比羽箭還疾,飛去將不換揪住。此時離海面,不過五六尺高下。正欲把雲頭再起,只覺得有許多水點子從海內噴出,濺在身上。雲霧一開,兩人同時落海,早被數十神頭鬼臉之人把兩人拿住,分開水路,推擁到一處地方來。但見:
門戶參差,內中有前殿後殿;臺階高下,兩傍列大房小房。龜殼軍師,穿戴着青衣、青靴、青帽;鱉甲元帥,披掛着白盔、白帶、白袍。鮮車騎手執銅錘,善能長水;鯁指揮腰懸寶劍,最會覆船。內總管,一名出奇大怪,一名大怪出奇;外傳宣,一叫不綠非紅,一叫非紅不綠。蝦鬚小卒,看守大旆高幡;螃蟹旗牌,率領蟶兵蚪將。聞風兒打探軍機,一溜兒傳送書柬。摔腳力士,以吹煞浪爲元魁;賣解壯丁,讓鍋蓋魚是鼎甲。
兩人入了水府,其屋字庭臺,也和人世一般,並無半點水痕。不換道:“因爲救我,着二哥也被擒。”
城璧道:“你我可各施法力,走爲上着。”
於是口誦靈文,向妖怪等噴去,毫無應驗。城璧着忙向不換道:“你怎麼不動作?”
不換道:“我已動作過了,無如一法不應,真是解說不來。”
城璧將不換一看,又低頭將自己一看,大聲說道:“罷了,罷了!怪道適才雲霧開散,此刻法術不靈,你看我和你身上,青紅藍綠,俱皆腥臭觸鼻,此係穢污不潔之物,打在身上,今番性命休矣!”
城璧和不換俱各站着不跪,只見那妖王圓睜怪眼,大罵道:“你們是何處妖道?擅敢盜竊我哥哥飛龍大王寶珠。還敢駕雲霧從我府前經過,見了我騰蛟大王,大模大樣,也不屈膝求生?”
不換道:“你們在水中居住,我們在空中行走,怎麼就盜竊了你的寶珠?”
那妖王大喝道:“你還敢強嘴!此珠落在平地,必現光華,經過水上,必生異彩。你焉能欺我?左右搜起來!”
衆妖卻待動手,不換道:“莫動,聽我說。珠子我有一個,是從江南無錫縣河內得的,怎麼就是你家飛龍大王的寶貝?”
妖王道:“取來我看。”
不換從懷內掏出,衆妖放在桌上。
妖王將匣兒打開,低頭看視,哈哈大笑。又將衆妖叫去同看,一個個手舞足蹈,齊跪在案下道:“大大王自失此珠,日夜愁悶,今日大王得了,送還大大王,不知作何快樂哩!”
那妖王笑說道:“此珠是你大大王的性命,須臾不離,怎麼就被這道士偷去!”
衆妖道:“他雲尚會駕,何難做賊!大王只動起刑來,不怕他不招。”
妖王道:“你這兩個賊道是何處人?今駕雲往何處去?這寶珠端的是怎樣偷去?可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
不換道:“我姓金,名不換,自幼雲遊四海。這顆珠子實系從無錫河中拾得,‘偷盜’兩字,從何處說起?”
妖王問城璧道:“你這道人,到好個漢仗,且又有一部好鬍鬚。爲何這樣個人物,和一賊道相隨?你可將名姓說來,因甚事出家,我意思要收你做個先鋒。”
城璧大笑道:“名姓是有一個,和你說也無益。你本是魚鱉蝦蟹一類的東西,才學會說幾句人話,也要用個先鋒?你曉得先鋒是個甚麼?”
那妖王氣的怪叫,將桌子拍了幾下道:“打,打!”
衆妖將城璧揪倒,打了三十大棍,又着將不換也打了二十,打的兩人肉綻皮開。那妖王道:“這個小賊道和那不識擡舉的大賊道,我也沒閒氣和他較論。你們速押解他到齊雲島,交與你大大王發落去罷。”
又傳令:“着大將遊遊不定和隨波逐流兩人先帶寶珠進獻,就說我過日還要喫喜酒哩。”
衆妖齊聲答應,將城璧、不換綁縛出府。推開波浪,約兩個時辰,已到齊雲島下。衆妖將二人擁上山來,那遊遊不定和隨波逐流先行送珠去了。
正是: 一爲兒孫學竊盜,一緣珠寶守河濱。 兩人干犯貪嗔病,落海逢魔各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