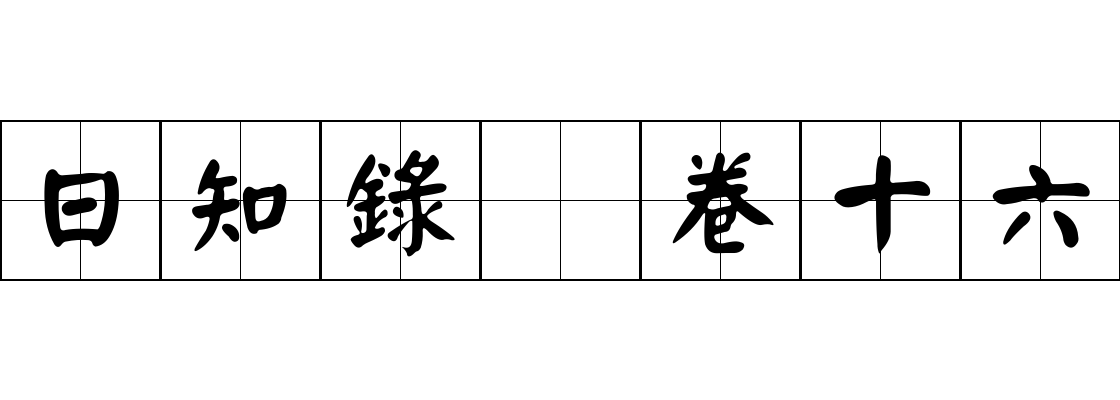日知錄-卷十六-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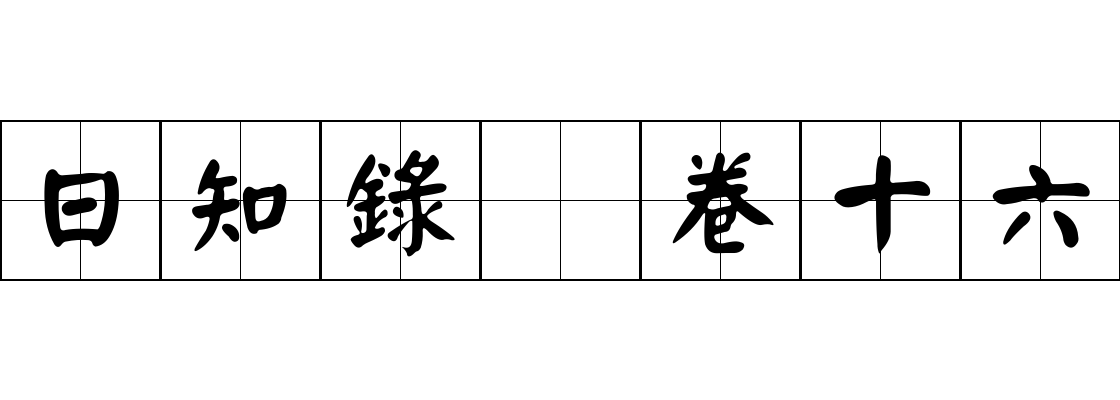
《日知錄》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大思想家顧炎武的代表作品,對後世影響巨大。該書是一經年累月、積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學術札記,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以明道、救世爲宗旨,囊括了作者全部學術、政治思想,遍佈經世、警世內涵。
○明經今人但以貢生爲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日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
唐時人仕之數,明經最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註疏,謂之帖括。議者病其不能通經,權文公謂:“註疏猶可以質驗,不者,倘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今之學者並註疏而不觀,殆於本末俱喪,然則今之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
○秀才《舊唐書·社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社氏《通典》雲:“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古人所趨向,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海,於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玄宗御撰《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爲明經;明閒時務,精熟一經者,爲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攻當也。又《文苑英華·判目》有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趙判曰:‘文藝小善,迸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是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
明初嘗舉秀才。如《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以秀才丁士梅爲蘇州府知府,童權爲楊州府知府,俱賜冠帶。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爲翰林應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是也。亦嘗舉孝廉。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以孝廉李德爲應天府尹是也。此辟舉之名,非所施於科目之士。今俗謂生員爲秀才,舉人爲孝廉,非也。
○舉人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右僕射事,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簡試舉人。”《舊唐書·高宗紀》“顯慶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嶽牧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不若今人以舉人爲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科目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但云舉進士,則第不第未可知之辭,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謂之舉人。進士即是舉人,不若今人以鄉試榜渭之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
永樂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體朝廷求賢之盛心,苟圖虛舉,有稍能行文、大義未通者,皆領鄉薦,冒名貢士。及至會試下第,其中文字稍優者,得除教官;其下者亦得升之國監。以致天下士子競懷僥倖,不務實學。”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雙流縣知縣孔友諒上言:“乞將前此下第舉人通計其數,設法清理。”是明初纔開舉人之途,而其弊即已如此。然下第舉人猶令人監讀書三年,許以省親,未有使之遊蕩於人間者。正統十四年,存省京儲始放回原籍,其放肆無恥者遊說乾渴,靡所不爲已。見於成化十四年禮部之奏。至於末年,則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於是崇禎中命巡按御史者察所屬舉人,間有黜革,而風俗之壞已不可復返矣。
○進士進士即舉人中之一科,其試於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士。唐人未第稱進士,已及第則稱前進士。《雍錄》引唐人詩云:“曾題名處添‘前’字。”《通鑑》:“建州進士進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遏之於途,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遂沈廢終身。”是未及第而稱進士也。試畢放榜,其合格者日賜進士及第,徑又廣之日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然後謂之登科。所以異於同試之人者,在乎賜及第、賜出身,而不在乎進士也。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罷進士,立三舍之法,今賜承議郎徐進士出身,於名實未正,乞改賜同上捨出身。”從之。
○科目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佯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故胃之科目,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也。王維楨欲於科舉之外仿漢唐舊制,更設數科,以收天下之奇士。不知進士偏重之弊,積二三百年,非大破成格,雖有他材,亦無由進用矣。
○制科唐制,天子自詔日製舉,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志》曰:“所謂制舉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其爲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爲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禪太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問,不爲無得也。
宋初,承周顯德之制,設三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宮、黃衣草澤並許應詔。景德增爲六科。熙寧以後,屢罷屢復。宋人謂之大科。
宋徐度《卻掃編》曰:“國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鹹平中,又詔文臣於內外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詔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等六科。天聖七年復詔,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職事,不曾犯贓罪及私罪情理輕者,井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乞應前六科。仍先進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候到下兩省看詳。如詞理優長,堪應制科,具名聞奏。差官考試論六首,合格即御試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雜類者,並許本處轉運司逐州長吏奏舉,或於本貫投狀乞應,州縣體量有行止別無玷犯者,即納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看詳詞理稍優,即上轉運司審察鄉里名譽,於部內選有文學官再看詳實,有文行可稱者,即以文卷送禮部,委主判官看詳,選詞理優長者具名聞奏。餘如賢良方正等六科,熙寧中,悉罷之。而令進士廷試,罷三題而試策一道。建炎間,詔復賢良方正一科,然未有應詔者。
高宗立博學宏辭科,凡十二題:制、浩、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體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後,得人爲盛,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場詔、誥、表三題,內科一道,亦是略仿此意。而苟簡濫劣,至於全無典故,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則專重初場之過也。
○甲科社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爲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兩科。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們日唐書。玄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敕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天寶十三載,玄宗御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爲之首,超授右拾遺,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杜甫《哀蘇源明詩》曰:“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然則今之進士而概稱甲科,非也。
《隋書·李德林傳》“楊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摧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是則北齊之世,即已多無甲科者矣。
甲乙丙科始見《漢書·儒林傳》“平帝時,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爲郎,”《匡衡傳》“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
○十八房今制,會試用考試官二員,總裁同考試官十八員,分閱《五經八謂之十八房。嘉靖未年,《詩》五房,《易》、《書》各四房,《春秋》、《禮記》各二房,止十七房。萬曆庚辰、癸未二科,以《易》卷多添一房,減《書》一房,仍止十七房。至丙戌,《書》、《易》卷並多,仍復《書》爲四房,始爲十八房。至丙辰,又添《易》、《詩》各一房,爲二十房。天啓乙丑,《易》、《詩》仍各五房,《書》三房,《春秋》、《禮記》各一房,爲十五房。崇幀戊辰,復爲二十房。辛未《易》、《詩》仍各五房,爲十八房。癸未,復爲二十房。今人概稱爲十八房雲。
《戒庵漫筆》曰:“餘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刻本窗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抄得燈窗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餘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荊川,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經義論策今之經義論策,其名雖正,而最便於空疏不學之人。唐宋用詩賦,雖曰雕蟲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經義始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呂惠卿、王旁等爲之。《宋史》:“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已朔,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命中書撰大義式頒行。
元八年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系在外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於考較,祖宗舊制,御試進士賦詩論三題,施行已遠,前後得人不少。況今朝廷見行文字多系聲律對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章。請行祖宗三題舊法,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複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是當時即以經義爲在外準備之文矣。陳後山《談叢》言:“荊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荊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豈知數百年之後,並學究而非其本質乎?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趙鼎言:“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陳公輔亦謂:“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而習其所爲《三經新義》,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謂時文,既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撰無根之語。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爲白徒。而一舉於鄉,即以營求關說爲治生之計。於是在州里則無人非勢豪,適四方則無地非遊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寧,斯民之淳厚,豈非卻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大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詔文有曰:‘朕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伏讀此制,真所謂求實用之上者矣。至十六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浩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道,文辭增而實事廢,蓋與初詔求賢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餘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
《四書》疑猶唐人之判語,設爲疑事間之,以觀其學識也。《四書》義猶今人之判語,不過得之記誦而已。苟學識之可取,則劉賞之對止於一篇已足。蓋一代之人才徒以記誦之多,書寫之速,而取其長,則七篇不足爲難,而有並作《五經》二十三篇,如崇幀七年之顏茂猷者,亦何稗於經術,何施於國用哉。《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詔於國子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累賜羅綺襲衣中靴,禮遇甚厚。”是則聖祖所望於諸生者,固不僅以帖括之文。而惜乎大臣無通經之士,使一代籲俊之典但止於斯,可嘆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廟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任安民之寄?”當日貢舉之行,不過四十年,而其弊已如此,乃護局之臣猶託之祖制,而相持不變乎?
○三場明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重輕。乃士子之精力多專於一經,略於考古。主司閱卷,復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千卷,不能有此三場也。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率天下而爲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宋嘉中,知諫院歐陽修上言:“今之舉人以二千人爲率,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蹟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復兩漢舉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抄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闇劣之徒無所僥倖,而至者漸少,科場亦自此而清也。
○擬題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且以經文言之,初場試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於家塾,將此數十題各撰一篇,計篇酬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即以所記之文抄謄上卷,較之風檐結構,難易遇殊,《四書》亦然。發榜之後,此曹便爲貴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以不讀矣,予聞昔年《五經》之中,惟《春秋》止記題目,然亦須兼讀四傳。又聞嘉靖以前,學臣命《禮記》題,有出《喪服》以試士子之能記否者,百年以來,《喪服》等篇皆刪去不讀,今則並《檀弓》不讀矣。《書》則刪去《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勘黎》、《微子》、《金胺》、《顧命》、《康王之浩》、《文侯之命》等篇不讀,《詩》則刪去淫風變雅不讀,《易》則刪去《訟》、《否》、《剝》、《豚》、《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讀,止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因陋就寡,赴速邀時。成者,以一年畢之。昔人所待一年而習者,以一月畢之。成於剿襲,得於假倩,卒而間其所未讀之經,有茫然不知爲何書者,故愚以爲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們四百六十餘人也,請更其法,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於《五經》、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如《易》之鄭、王,《詩》之毛、鄭,《春秋》之三傳,以及唐宋諸儒不同之說。《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其對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其所出之題不限盛衰治亂,使人不得意擬,而其文必出於場中之所作,則士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其能文與否亦可得而驗矣。又不然,則姑用唐宋賦韻之法,猶可以杜節抄剽盜之弊。蓋題可擬而韻不可必,文之工拙猶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謄一過而中式者矣。其表題專出唐宋策題,兼問古今,人自不得不讀《通鑑》矣。夫舉業之文,昔人所鄙斥,而以爲無益於經學者也,今猶不出於本人之手焉,何其愈下也哉!
讀書不通《五經》者,必不能通一經,不當分經試士。且如唐宋之世,尚有以《老》、《莊》諸書命題,如《卮言日出賦》,至相率扣殿檻乞示者。今不過《五經》、益以《三禮》、《三傳》,亦不過九經而已。此而不習,何名爲上?《宋史》、“馮元,授江陰尉,時詔流內銓以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人治一經而至皓首,於尚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
《石林燕語》“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遍讀《五經》。餘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學時習之,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多遺誤。若今人問答之間,稱其人所習爲‘貴經’,自稱爲‘敝經’,尤可笑也。”
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覬倖之人少。少一覬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漸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
墨子言:“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若責士子以兼通《九經》,記《通鑑》歷代之史,而曰:“若此者中,不若此者黜。”我以爲必好學能文之士喜,而不學無文之士懼也。然則爲不可之說以撓吾法者,皆不學無文之人也,人主可以無聽也。
今日欲革科舉之弊,必先示以讀書學問之法,暫停考試數年而後行之,然後可以得人。晉元帝從孔但之議,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古之人有行之者。○題切時事考試題目多有規切時事,亦虞帝“予違汝弼”之遺意也。《宋史·張洞傳》“試開封進士,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古之人君近則盡官師之規,遠則通鄉校之論,此義立而爭諫之途廣也矣。
天啓四年,應天鄉試題《今夫奕之爲數》一節,以魏忠賢始用事也,浙江鄉試題《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以杖殺工部郎萬憬也。七年江西鄉試題《皓皓乎不可尚已》,其年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建祠國學也。崇幀三年,應天鄉試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諸臣初定逆案也。此皆可以開帝聰而持國是者。當時季集,而污水鶴鳴之義猶存於士大夫,可以想見先朝之遺化。若崇禎九年應天鄉試《春秋》題《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以公孫繮比陳啓新,是以曹伯陽比皇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天啓七年,順天鄉試《書經》題《我二人共貞》,以周公比魏忠賢,則又無將之漸,亦見之彈文者也。
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邊,邊臣不納,雖有社稷爲重之說,然當時朝論即有以奉迎之緩爲譏者。順天鄉試題《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節,蓋有諷意。○試文格式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今之爲時文者,豈必裂規亻面矩矣乎?
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爲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爲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曆中,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文矣。
試錄文字之體,首行曰“第一場”,頂格寫。次行日“《四書》”,下一格。次行題目,又下一格。《五經》及二、三場皆然,至試文則不能再下,仍提起頂格。此題目所以下二格也。若歲考之卷,則首行日“《四書》”,頂格寫,次行題目,止下一格,經論亦然,後來學政苟且成風,士子試卷省卻“《四書》”、“《五經》”字,竟從題目寫起,依大場之式概下二格。聖經反下,自作反高,於理爲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異者,沿此之例不論古今,詩文概以下二格爲題。萬曆以後,坊刻盛行,每題之文必注其人之名於下,而刻古書者亦化而同之。如題日《周鄭交質》,下二格,其行未書“左丘明”。題曰《伯夷列傳》,下二格,其行未書“司馬遷”。變歷代相傳之古書,以肖時文之面貌,使古人見之,當爲絕倒。
○程文自宋以來,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爲舉人之式,試後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別胃之墨卷。《神宗實錄》:“萬曆十四年正月,禮部議:‘試錄程文宜照鄉試例刪,原卷不宜盡掩初意。’從之。”十五年八月,命禮部會同翰林院,取定開國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餘篇,刊佈學宮,以爲準則。”時札部尚書爲沈鯉,兼官翰林學士。
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未流最爲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爲之,故日趨而下。晁董公孫之對,所以獨出千古者,以其無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異之纔出矣。
○判舉子第二場作判五條,猶用唐時銓試之遺意。至於近年,士不讀律,止鈔錄舊本。入場時每人止記一律,或吏或戶。記得五條,場中即可互換。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爲可笑。“《通典·選人條例》:“其情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榜示以懲之。”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晚逼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敕:“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爲官。劉瑩等既不攻文,只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稿草,侮瀆公場。宜令所司落下放罪。”夫以五代偏安喪亂之餘,尚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統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換,至一二百年,目爲通弊,不行覺察。傳之後代,其不爲笑談乎!試判起於唐高宗時。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犢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後日月浸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爲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人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日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今國朝之制,以吏部選人之法而施之貢舉,欲使一經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設甲乙,止據律文,尤爲正大得體。但以五尺之童能強記者,旬日之力便可盡答而無難,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蓋此法止可施於選人引試俄頃之間,而不可行之通場廣衆竟日之久。宜乎各記一曹,互相倒換。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實廢者,此類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通典》所云,“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決,不乖經義”者乎?○回經文字體生員冒濫之弊,至今日而極。求其省記《四書》本經全文,百中無一。更求通曉六書,字合正體者,千中無一也。簡汰之法,是亦非難,但分爲二場:第一場令暗寫《四書》一千字,經一千字,脫誤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貼出除名;第二場乃考其文義,則矍相之射,僅有存者矣。或曰:此未節也,豈足爲才士累?夫周官教國子以六藝,射御之後,繼以六書。而漢世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以周官童子之課,而責之成人;漢世椽史之長,而求之秀士。猶且不能,則退之隴畝,其何辭之有,北齊策孝、秀於朝堂,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跡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潛霸之君尚立此制,以全盛之朝,求才之王,而不思除弊之方,課實之效,與天下因循幹溷濁之中,以是爲順人情而已。權文公有言:“常情爲習所勝。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爲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不·原始要終,長轡遠馭者邪?”古今一揆,可勝慨思。
○史學唐穆宗長慶三年二月,諫議大夫殷侑言:“司馬遷、班固、范曄《三史》爲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廢絕,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三史》科及《三傳》科。《通典·舉人條例》:“其史書,《史記》爲一史,《漢書》爲一史,《後漢書》並劉昭所注《志》爲一史,《三國志》爲一史,《晉書》爲一史,李延壽《南史》爲一史,《北史》爲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往,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徐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並《貞觀政要》共爲一史。”今史學廢絕又甚唐時,若能依此法舉之,十年之間,可得通達政體之士,未必無益於國家也。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大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爲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迸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跡,憚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春宮,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稍以論策爲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
史言薛昂爲大司成,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嘗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佞。籲,何近世俗佞之多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