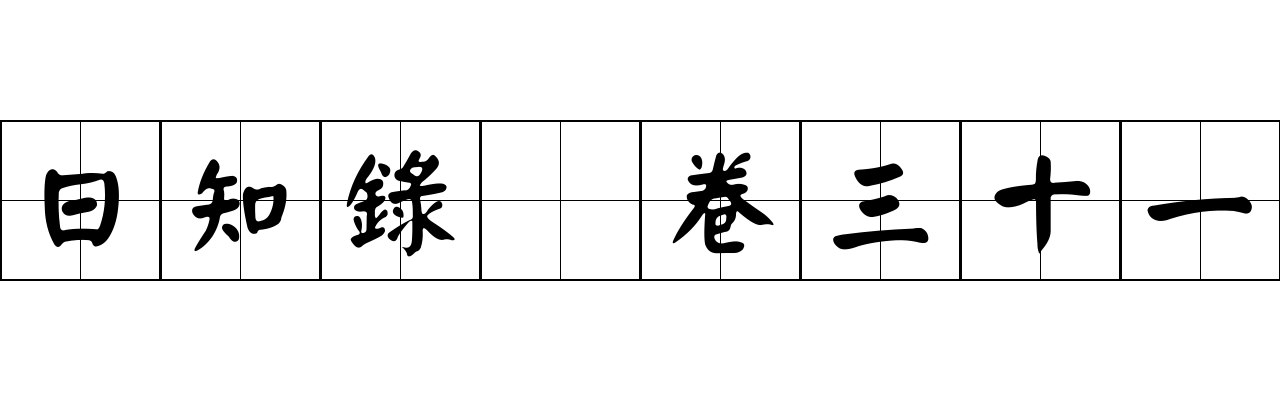日知錄-卷三十一-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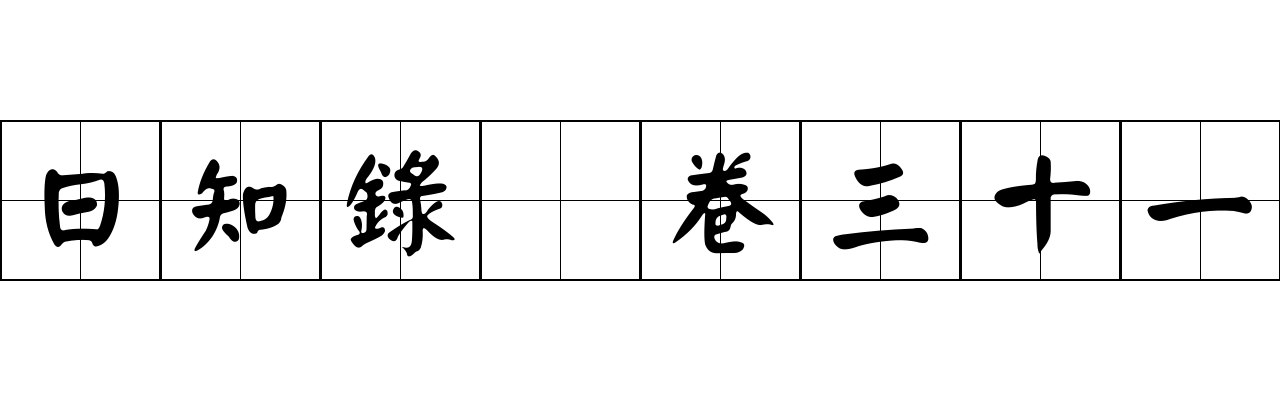
《日知錄》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大思想家顧炎武的代表作品,對後世影響巨大。該書是一經年累月、積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學術札記,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以明道、救世爲宗旨,囊括了作者全部學術、政治思想,遍佈經世、警世內涵。
○河東山西河東、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師在關中,而其東則河,故謂之河東;元之京師在薊門,而其西則山,故謂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之也。
古之所謂山西即今關中。《史記·太史公自序》:“蕭何填撫山西。”《方言》:“自山而東五國之郊。”郭璞解曰:“六國惟秦在山西。”王伯厚《地理通釋》曰:“秦漢之間,稱山北、山南、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勢。《正義》以爲華山之西,非也。”
○陝西《續漢·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故有陝東、陝西之稱。”《水經注·河水》:“又東得七裏澗,澗在陝西七裏。”《宋書·柳元景傳》:“龐季明率軍向陝西七裏谷。”《北史·魏孝武帝紀》:“高昂率勁騎及帝於陝西。”《舊唐書·大宗紀》:“貞觀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壞陝西河北縣。”《肅宗紀》:“乾元三年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郭英義爲陝州刺史、陝西節度潼關防禦等使。”《肅宗諸子傳》:“杞王亻垂充陝西節度大使。”《李渤傳》:“澤潞節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弔祭使,路次陝西。”《回紇傳》:“廣平王副元帥郭子儀,領回紇兵馬,與賊戰於陝西。”皆謂今陝州之西。後人遂以潼關以西通謂之陝西。
晉時以關中爲陝西。《晉書·宣帝紀》:“西屯長安,天子命之曰:‘昔周公旦輔成王,有素雉之貢。今君受陝西之任,有白鹿之獻。’”《張實傳》:“愍帝末,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張華祖道。”梁王肜《應詔詩》:“二跡陝西,實在我王”是也。東晉則以荊州爲陝西。《南齊書》曰:“江左大鎮,莫過荊、揚。周世,二伯總諸侯,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放稱荊州爲陝西也。”考之於史,桓衝爲荊州刺史,安帝詔曰:“故太尉衝,昔藩陝西,忠誠王室。”《毛穆之傳》:“瘦翼專威陝西,劉毅爲荊州刺史,安帝詔曰:‘劉毅推毅陝西。”《南史·宋文帝紀》:“命王華知州府,留鎮陝西。”《宋書》:蔡興宗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袁顗曰:“舅今出居陝西。”《鄧琬傳》:晉安王子勳檄曰:“前將軍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練甲陝西,獻徒萬數”是也。亦有稱陝東者。《晉書·載記》:劉聰署石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又加崇爲陝東伯。
唐太宗爲秦王時,拜使持節陝東道大行臺。
○山東河內古所謂山東者,華山以東。《管子》言:“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史記》引賈生言:“秦併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後漢·陳元傳》言:“陛下不當都山東。”蓋自函谷關以東,總謂之山東,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而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爲河內也。”
○吳會宋施宿《會稽志》曰:“按《三國志》,吳郡會稽爲吳、會二郡。張謂:‘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孫賁傳》雲:‘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雲:‘使部伍吳、會二郡。’《全琮傳》雲:‘分丹陽、吳、會三郡險地爲東安郡’是也。前輩讀爲‘都會’之會,殆未是。錢康功曰:‘今平江府署之南名吳會坊。《漢書·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按今本《史記》、《漢書》並作‘上患吳、會稽’,不知順帝時始分二郡,漢初安得言吳會稽?當是錢所見本未誤,後人妄增之。
魏文帝詩:“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陳思王《求自試表》曰:“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晉文王與孫皓書曰:“惠矜吳會,施及中土。”魏元帝加晉文王九錫,文曰:“掃平區宇,信威吳會。”阮籍爲鄭衝勸晉王箋曰:“朝服濟江,掃除吳會。”陳壽《上諸葛亮集》曰:“身使孫權求援吳會。”羊祜上疏曰:“西平巴蜀,南和吳會,”荀勖《食舉樂東西廂歌》曰:“既禽庸蜀,吳會是賓,”左思《魏都賦》曰:“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武帝問劉毅曰:“吾平吳會,一同天下,”石崇奏惠帝曰:“吳會僭逆,幾於百年。”石勒錶王浚曰:“晉祚淪夷,遠播吳會。”慕容謂高瞻曰:“翦鯨豕於二京,迎天子於吳會,”丁琪諫張祚曰:“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此不得以爲會稽之會也。蓋漢初元有此名,如曰“吳都”云爾。
若《孫賁、朱桓傳》則後人之文偶合此二字,不可以證《吳王濞傳》也。○江西廣東廣西江西之名殆不可曉,全司之地並在江南,不得言西。考之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歷陽、廬江、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史記·項羽本紀》:“江西皆反。”揚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國志·魏武帝本紀》:“進軍屯江西郝溪。”《吳主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孫瑜傳》:“賓客諸將多江西人。”《晉書·武帝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穆帝紀》:“江西乞活,郭敞等執陳留內史劉仕而叛。”《郗鑑傳》:“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桓伊傳》:“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今之所謂江北,昔之所謂江西也。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今人以江、饒、洪、吉諸州爲江西,是因唐貞觀十年,分天下爲十道,其八日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爲十五道,而江南爲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東、江西爾。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謬矣。
今之廣東、廣西亦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之省文也。《文獻通考》:“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其後又增三路,其十七曰廣甫東路,其十八曰廣南西路。”
○四川唐時,劍南一道止分東、西兩川而已。至宋,則爲益州路、粹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渭之川峽四路,後遂省文名爲四川。
○史記富川國薛縣之誤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弘傳》:“齊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雲:“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誌》雲:“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弘。”是弘審爲薛人,上言齊川者誤耳。
《續漢·郡國志》:“薛,本國。”注引《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雲:“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爲盂嘗君食邑。”《史記·越世家》:“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索隱曰:“常,邑名。蓋田文所封者。”《魏書·地形志》:“薛縣,彭城郡,有奚公山、奚仲廟、孟嘗君家。”《水經注》:“今薛縣故城側猶有文家,結石爲郭,作制嚴固,瑩麗可尋。”而《史記·孟嘗君傳》正義曰:“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今《淄川縣誌》據《公孫弘傳》之誤文,而以爲孟嘗君封邑,失之矣。又按《地理志》:“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又《高五王傳》:”武帝爲悼惠王家園在齊,乃割臨淄東圜悼惠王家園邑,盡以予川。”足明川在臨之東矣。今之淄川不但非薛,並非漢之西川,乃般陽縣耳。以爲漢之川,而又以爲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曾子甫武城人《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雲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氏注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成縣,屬東海郡。《續漢志》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干遊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創加也;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引京相潘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可以見武城之即爲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新序》則雲:魯人攻費阝,曾子辭於費阝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使狗豕人吾舍。《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費。”則曾於所居之武城,費邑也。哀公八年傳:“吳代我,子泄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續漢志》雲南城有東陽城,引此爲證。又可以見南城之即爲武城也。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漢書》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爲南成侯。而後漢王符《潛夫論》雲:“高阝畢之山,南城之冢。”章懷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費之證也。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褐而封志之。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臣奏求曾氏後,得裔孫質粹于吉安之永豐,遷居嘉祥。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夫曹縣之冉固,爲秦相穰侯魏冉之冢。而近人之撰志者,以爲仲弓如此之類,蓋難以盡信也。
○漢書二燕王傳《漢書·燕王定國傳》:“殺肥如令郢人。”按《地理志》,肥如自屬遼西郡,不屬燕。《武帝本紀》:“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今之殺於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邊郡之時也。
《燕王旦傳》:“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其上雲:“武帝時,旦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昭帝本紀》亦云:“始元元年,益封燕王、廣陵上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戶。”然則文安縣之仍屬於燕,必在益封萬三千戶之後也,此皆史文之互見者,可以參考而得之也。○徐樂傳《漢書》:“徐樂,燕郡無終人也。”《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而其間爲燕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以其時屬燕,後改屬右北平耳。
○水經注大梁靈丘之誤《左傳·桓九年》:“梁伯伐曲沃。”注:“梁國在馮翊夏陽縣。”芮曰:“梁近秦而幸焉”是也。《漢書·地理志》雲:“馮翊夏陽縣,故少梁也。”《水經注》乃曰:“大梁,周梁伯之居也。梁伯好土功,大其城,號曰新裏。民疲而潰,秦遂取焉。後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於大梁”是也。是誤以少梁爲大梁,而不知大梁不近秦也。《漢書》:“代郡靈丘。”應劭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水經注》曰:“《史記》:“趙敬侯二年,敗齊於靈丘。”則名不因靈王也。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十五年,趙與韓、魏、燕共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淄。”而孟子謂氐{圭黽}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此別一靈丘,必在齊境,後入於趙。而孝成王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益明其不在代郡矣。《水經注》云云,是誤以趙之靈丘爲齊之靈丘,而不知齊境不得至代也。
○三輔黃圖漢西京宮殿甚多,讀史殊不易曉。《三輔黃圖》敘次頗悉,以長樂、未央、建章、北宮、甘泉宮爲綱,而以其中宮室臺殿爲目,甚得體要。但其無所附麗者悉入北宮及甘泉宮下,則舛矣。今當以明光宮、太子宮二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城內諸宮;永信宮、中安宮、養德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宮異名;長門宮、鉤弋宮、儲元宮、宣曲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城外離官;昭臺宮、大臺宮、扶荔宮、蒲萄宮別爲一條,爲上林苑內離宮;宜春宮、五柞宮、集靈宮、鼎湖宮、思子宮、黃山宮,池陽宮、步壽宮、萬歲宮、梁山宮、回中宮、首山宮別爲一條,爲各郡縣離宮。別有明光宮,不知其地,附列於後。而梁山宮當併入秦梁山宮下。則區分各當矣。
○大明一統志永樂中,命儒臣纂天下輿地書。至天順五年乃成,賜名曰《大明一統志》,御製序文,而前代相傳如《括地誌》、《太平寰宇記》之書皆廢。今考其書,舛謬特甚,略摘數事以資後人之改定雲。
《一統志》:“三河,本漢臨們縣地。”今考兩漢書,井無臨氵句縣。《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潞縣”下雲:“武德二年,置臨氵句縣。貞觀元年,省臨氵句。”而“薊州漁陽郡三河”下雲:“開元四年,祈路縣置。”故知本是一地,先分爲臨氵句,後分爲三河,皆自唐,非漢也。
《一統志》引古事舛戾最多,未有若密雲山之可笑者。《晉書·石季龍載記》:“段遼棄令支奔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使徵東將軍麻秋迎之。遼又遣使降於慕容,曰:‘彼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不疑也,若伏重兵要之,可以得志。’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兵三萬迎遼,爲烙所襲,死者什六七,秋步遁而歸。”是段遼與燕合謀而敗趙之衆也。今《一統志》雲:“密雲山在密雲縣南一十五里,亦名橫山。昔燕。趙伏兵於此,大獲遼衆。”是反以爲趙與燕謀而敗遼之衆,又不言段,而曰遼,似以遼爲國名。豈修志諸臣並《晉書》而未之見乎?
《一統志》:“楊令公祠在密雲縣古北口,把宋楊業。”按《宋史,楊業傳》:“業本太原降將,太宗以業者於邊事,遷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會契丹人雁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京而出,由小徑至雁門北口,南向背擊之,契丹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雍熙三年,大兵北證,以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爲雲應路行營都部署,命來副之。以西上閣門使蔚州刺史王亻先、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連拔雲,應,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之師不利,諸路班師,美等歸代州。未幾,詔遷四州之民於內地,令美等以所部兵護之。時契丹復陷寰州,亻先令業趨雁門北川。業以爲必敗,不可。亻先逼之行,業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援。’美即與亻先領麾下兵陳於谷口。自寅至已,亻先使人登託邏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即麾兵卻走。業力戰,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柑膺大勵,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人,馬重傷不能進,爲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是業生平未嘗至燕。況古北口又在燕東北二百餘里,地屬契丹久矣,業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雁門之北口,而以爲密雲之古北口,是作志者東西尚不辨,何論史傳哉。又按《遼史·聖宗紀》:“統和四年七月丙子,樞密使斜軫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耶律斜軫傳》:“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飛矢所中,被擒。”與《宋史》略同。《密雲縣志》:“威靈廟在古北口北門外一里,祀宋贈大尉大同軍節度使楊公。”成化十八年,禮部尚書周洪範《記》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雁門北口之非其地。《豐潤縣誌》:“令公村在縣西十五里,宋楊業屯兵拒遼於此。有功,故名。”並承《一統志》而誤。
《一統志》:“遼章宗陵在三河縣北五十五里。”考遼無章宗,其一代諸帝亦無葬三河者。
《一統志》:“全太祖陵、世人陵俱在房山縣西二十里三峯山下。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縣兩大房山東北。”按《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爲山陵,建行宮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十一月乙巳朔,梓宮發丕承殿。戊申,山陵禮成。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遷始祖以下梓宮。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視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於大房山。閏月己亥朔,山陵禮成。”又《太祖紀》:“太祖葬睿陵。”《太宗紀》:“太宗葬恭陵。”《世宗紀》:“世宗葬興陵。”《章宗紀》:“章宗葬道陵。”又《熙宗紀》:“帝被弒,葬於皇後裴滿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於大房山蓼香甸,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上諡號,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於峨眉谷,仍號思陵。”又《海陵紀》:“葬於大房山鹿門谷,投降爲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又《睿宗紀》:“大定二年,改葬於大房山,號景陵。”《顯宗紀》:“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葬於大房山,章宗即位,號日裕陵。”是則金代之陵自上京而遷者十二帝,其陵曰光、曰熙、曰建、曰輝、曰安、曰定、曰永、曰泰、曰獻、曰喬、曰睿、曰恭。其崩於中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興、曰道。被弒者一帝,其陵曰思。追諡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弒而降爲庶人者一帝,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則自即位之二年遷於南京,三年五月,中都爲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今《一統志》止有四陵,而誤列宣宗,義臍於章宗之上,諸臣不學之甚也!
《漢書.地理志》:“樂浪郡之具二十五,其一曰朝鮮。”應劭曰:“故朝鮮國,武上封箕子於此。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山海經》曰:“‘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注:“朝鮮,今樂浪縣,箕子所封也。在今高麗國境內。”慕容氏於營州之境立朝鮮縣,魏義於平州之境立朝鮮縣,似取其名,與漢縣相去則千有餘裏。《一統志》乃曰:“朝鮮城在永平府境內,箕子受封之地。”則是箕子封於今之永平矣。當日儒臣,令稍知今人者爲之,何至於此?爲人太息。
《一統志》:“登州府名宦”下雲:“劉興居,高祖孫,齊悼惠王肥子。誅諸呂有功,封東牟候。惠澤及於邦人,至今廟把不絕。”考《史記》、《漢書》:“本紀”、“年表”,興居以高後六年四月丁酉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侯就國,春二月乙卯,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誅,是興居之侯於東牟僅三年,其奉就國之令至立爲濟北王,相距僅五月,其曾到國與否不可知,安得有惠澤及人之事歷二千年而思之不絕者乎?甚矣,修志者之妄也!
王文公《虔州學記》:“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以“曠”字絕爲一句,“谷”字絕爲一句,“阻”字絕爲一句,文理甚明。今《一統志》:“贛州府形勝”條下,摘其二語曰:“地最曠大,山長谷荒。”句讀之不通,而欲從事於九丘之書,真可爲千載笑端矣。
○交恥《大學衍義補》曰:“交恥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爲劉隱所並。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及賜號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內地之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真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爲黎季所篡。季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大且}。詐稱陳氏絕嗣,查爲甥求權署國事,大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訴其實。季乃表請迎添平還國,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伏兵殺之,並及使者。事聞,太宗遍告於天地神只,聲罪致討,遣徵夷將軍未能等徵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禽季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鹹稱季殺之盡,無可繼者。僉請復古郡縣,遂如今制,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像有黎利者,乃彼中麼麼個醜耳,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宣宗皇帝謂此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爲國。鳴呼!自秦並百粵、交趾之地己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與焉。在唐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輔己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奈何世歷五代,爲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茲地淪於蠻夷之域,而爲誅亻離藍縷之俗三百餘年,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同爲衣冠禮樂之區,一何不幸哉!按交恥自漢至唐爲中國之地,在宋爲化外州,雖貢賦版籍不上戶部,然聲教所及皆邊州帥府領之。永樂間,平定其地,設交趾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各一,衛十,千戶所二,府十三,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市舶提舉司一,巡檢司百,稅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二。而升遐之後,上尊諡議,以“復交恥郡縣於數千載之後,驅漠北殘寇於數萬裏之外”爲言,既述武功之成,亦侈輿圖之廣,後以兵力不及而棄之。乃天順中修《一統志》,竟以安南與占城、暹羅等國同爲一卷。嗟乎,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妞域中之見,而忘無外之規,吾不能無議夫儒臣者。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洪武十六年閏十月進。其中如上都、大寧、遼東諸郡縣並載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內地如河間府之莫州、莫亭、會川、樂壽亦具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不以一時郡縣之有無,而去歷代相因之版籍,甚爲有體。
○薊《漢書》:“薊,故燕國,召公所封。”《後漢書》:“薊,本燕國刺史治。”自七國時,燕都於此。項羽立臧茶爲燕王,都薊。高帝因之,爲燕國。元鳳元年,燕刺王旦自殺,國除,爲廣陽郡。本始元年,爲廣陽國。建武十三年,省,屬上谷。永平八年,復爲廣陽郡。晉復爲燕國。魏爲燕郡。隋開皇初,廢。大業初,置涿郡。唐天寶元年,更名范陽郡,並治薊《水經·溼水》:“過廣陽薊縣北,又東至漁陽雍奴縣。”注:“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後漢書·彭寵傳》:“寵反漁陽,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晉書·載記》:“魏圍燕中山、清河,王會自龍城遣兵赴救。建威將軍餘崇爲前鋒,至漁陽,過魏千餘騎,鼓譟直進,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會乃上道徐進,始達薊城。”即此三事,可見薊在漁陽之西,《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治薊。開元十八年,析置薊州漁陽郡,治漁陽。”及遼,改薊爲析津縣,因此薊之名遂沒於此而存於彼。今人乃以漁陽爲薊,而忘其本矣。《史記》樂毅書:“薊丘之植,植於汶篁。”此即《水經注》所言薊丘。
《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疏雲:“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雲:“燕祖召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召公蓋其後也。按此以薊、燕爲一國,而召公即黃帝之後。《史記·周本紀》:“武王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召公於北燕。”正義曰:“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薊、燕二國俱武王立,因燕山、薊丘爲名,其地足自立國。後薊微燕盛,乃並薊居之。”其說爲長。
○廈謙澤《晉書·載記》:“慕容寶盡徙薊中府北趨龍城魏石河,興引兵追及之於夏謙澤。’胡三省《通鑑》注‘夏謙澤在薊北二百餘里。”恐非。按《水經注》:“鮑丘水東南流,徑潞城南,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餘里,北佩謙澤,眇望無垠也。”下雲:“鮑丘水又東與氵句河合。”《三河志》:“鮑丘河在縣西二十五里。源自口外,南流徑水莊嶺,過密去,合道人溪,幹通州之米莊村,合沽水,人氵句河。”今三河縣西三十里,地名夏店,舊有驛,鮑丘水徑其下,而氵句河自縣城南至寶坻,下入於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澤,其東彌望皆陂澤,與《水經注》正合。自薊至龍城,此其孔道。寶以丙辰行,魏人以戊千及之,相距二日,適當其地也。
○石門《後漢書·公孫瓚傳》:“中平中,張純與烏桓丘力居等人寇,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大敗之。”注:“石門山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而《水經注》:“雲:“氵水又東南徑石門峽,山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五年,公孫瓚討張純,戰於石門,大破之。”今薊州東北六十里石門驛,即《水經注》之石門是也。按史《本紀》但言“石門”,而《傳》言“屬國石門”,明有兩石門。
《水經注》所指乃漁陽之石門,非遼東屬國之石門。當以柳城爲是,《通典》柳城有石門山。
○無終玉田,漢無終縣。《漢書·地理志》:“故無終子國,氵更水西至雍奴入海。”《史記》:“項羽封韓廣爲遼東王,都無終,”《後漢書》:“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韋昭《國語解》:“無終,山戎之國,今爲縣,在北平。”《水經注》:“藍水出北山,東屈而南流,徑無終縣故城東。故城,無終於國也,”《魏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無終之爲今玉田,無可疑者。然《左傳·襄公四年》:“無終於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漢書·樊哈傳》:“擊陳稀,破得綦毋,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則去玉田千有餘裏,豈無終之國先在雲中代郡之境,而後遷於右北平與?而今之昌黎乃金之廣寧縣,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名同而地異也。
《三國志》:“魏武帝用田疇之言,上徐無山,塹山埋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徐無山在今玉田。則柳城在玉田之東北數百里也。《北齊書》:“顯祖伐契丹,以十月丁酉至平州,從西道趨長塹。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是昌黎在平州之東北,齊主之行急,猶五日而後至也。《隋書》:“漢玉諒伐高麗,軍出臨渝關,至柳城。”《唐書》:“太宗伐高麗還,以十月丙午次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駭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丙辰,皇太子迎謁於臨渝關。”關在今撫寧之東,則柳城又在其東。太宗之行遲,故十日而後至也。
《遼史》載柳城曰:“興中府。古孤竹國,漢柳城縣地。慕容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乃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而遷都之,號曰和龍宮。慕容垂復居焉。後爲馮跋所滅。魏取之,爲遼西郡。隋平高寶寧,置營州。揚帝改柳城郡。唐武德初,改營州總管府,尋爲都督府。萬歲通天元年,陷李萬榮。神龍初,徙府幽州。開元四年,復治柳城。八年,徙漁陽。十年,還柳城。後爲奚所據。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將建城,命韓知方擇其處,乃完葺柳城,號霸州彰武軍節度,重熙十年,升興中府。有太華山、小華山、香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駐龍峪、神射泉、小靈河。統州二,縣四。其一曰興中縣,百六十年而始封昌黎伯,又一百六年而始立今之昌黎縣,以金之縣而合宋之封,遂謂文公爲此縣之人,其亦未之考矣。
○石城漢右北平郡之縣十六,其三日石城。後漢無之,蓋光武所並省也,至燕分置石城郡。考之《通鑑》及《晉載記》,得二事。慕容寶宿廣都黃榆谷,清河王會勒兵攻寶。寶帥輕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是廣都去龍城二百里,而石城在其中間也。慕容熙畋於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注云:“高和本爲石城令,時以大喪,會於龍城。”是石城去龍城不遠也。《魏書·地形志》:“廣興”下雲:“有雞鳴山、石城、大柳城。”此即漢之石城矣。魏太平真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領縣三:其一曰石城,有白鹿山祠,其二曰廣都。《水經注》:“石城川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徑石城縣故城南,北屈徑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又東北人廣成縣東。”廣成即廣都城,燕之石城在廣都之東北,而此在廣都之西南,是魏之石城非燕之石城矣。《隋書》始無石城,雲北齊廢之。而《唐書》:“平州石城”下雲:“本臨渝。武德七年省,貞觀十五年復置,萬歲通天二年更名。有臨榆關,有大海。有碣石山。”是武後所更名之石城又非魏之石城矣。《遼史》:“灤州”統縣三,其三曰石城。下雲:“唐貞觀中,於此置臨榆縣,萬歲通天元年,改石城縣。在灤州南三十里。唐儀鳳石刻在焉。”今縣又在其南五十里,遼徙置,以就鹽官。是遼之石城又非唐之石城矣。今之開平中屯衛自永樂三年徙於石城廢縣,在灤州西九十里,乃遼之石城;而《一統志》以爲漢舊縣,何其謬與!
○木刀溝新樂縣西南三十里有水名木刀溝,《新唐書·地理志》:“新樂”下雲:“東南二十里有木刀溝。有民木刀,居溝旁,因名之。”《憲宗紀》:“元和五年四月丁亥,河東節度使範希朝、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及王承宗戰於木刀溝,敗之。”《張茂昭傳》:“承宗以騎二萬逾木刀溝,與王師薄戰,茂昭躬擐甲爲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繞戰,大破之。”《沙陀傳》:“王承宗衆數萬,伏木刀溝,與朱邪、執宜遇飛矢雨集,執宜提軍橫貫賊陣鏖鬥,李光顏等乘之,斬首萬級。”而《舊書·李光進傳》:“範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步都虞候。戰於木刀溝,有功。”此溝在鎮定二節度之界,古爲戰地。○江乘古時未有瓜洲。蔡寬大《詩話》:“潤州大江本與今揚子橋對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今與揚子橋相連矣。以故,自古南北之津,上則由採石,下則由江乘,而京口不當往來之道。”《史記》:“秦始皇登會稽,還,從江乘渡。”正義雲:“江乘故縣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吳徐盛作疑城,自石頭至江乘。晉蔡漠自土山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皆以沿江爲防守之要。今其地在上元縣東北五十里。唐肅宗上元元年,李亙闢北固爲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劉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洲,多張火鼓,若將趨北固者。如是累日,亙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胡三省《通鑑》注云:“此自白沙濟江也。”州東北九十里至句容縣有下蜀戍,在句容縣北,近江津。今江乘去江幾二十里以外,皆爲洲渚,而渡口乃移於龍潭。又瓜洲既連揚子橋,江面益狹。而隋唐之代復以丹陽郡移治丹徒,於是渡者舍江乘而趨京口。宋乾道四年,築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今因之。
瓜洲得名,本以瓜步山之尾生此一洲故爾。《舊唐書·齊辯傳》:“潤州北界隔江,至瓜步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爲風濤漂損。氵乃移漕路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腳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收其課,迄今利濟焉。”此京口漕路繇瓜洲之始。《玄宗紀》載此事則謂之瓜洲浦。而《五行志》:“開元十四年七月,潤州大風,從東北,海濤奔上,沒瓜步洲,損居人。”《永王磷傳》:“李承式使判官評事裴茂,以步卒三千拒於瓜步洲伊婁埭。”則此洲本亦謂之瓜步洲也。
○郭璞墓《晉書·郭璞傳》:“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王惲集》乃雲:“金山西北大江中亂石間,有叢薄,鴉鵲棲集,爲郭璞墓。”按史文元謂去水百步許,不在大江之中,且當時即已沙漲爲田,而暨陽在今江陰縣界,不在京口。又所葬者璞之母,而非璞也。世之所傳皆誤。
○梟磯蕪湖縣西南七裏大江中梟磯,相傳昭烈孫夫人自沈於此,有廟在焉。按《水經注》:“武陵孱陵縣故城,王莽更名孱陸也,劉備孫夫人,權妹也,又更修之。”則是隨昭烈而至荊州矣。《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又裴松之注引《趙雲列傳》曰:“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時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慾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是孫夫人自荊州復歸於權,而後不知所終,梟磯之傳殆妄。
○胥門《史記》:“吳王既殺子晉,吳人爲立祠於江上,號曰胥山。”《水經注》引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五十里,江側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廟。魯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疇無餘、謳陽等伐吳。吳人敗之,獲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廟于山上,號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壇石,長老雲:胥神所治也。一以爲子胥,一以爲越大夫。”今蘇州城之西南門曰胥門,陸廣微《吳地記》雲:“本伍子胥宅,因名。”非也。趙樞生曰:“按《吳越春秋》:吳工夫差十三年,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則子胥未死已名爲胥門。愚考《左傳·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戰,胥門巢將上軍。胥門,氏;巢,名。蓋居此門而以爲氏者,如東門遂、桐門右師之類。則是門之名又必在夫差以前矣。《淮南子》:“勾踐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越絕書》:“吳王起姑胥之臺,五年乃成。”姑胥,山名也,不可知其所始。其字亦爲“姑蘇”。《國語》:“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史記》:“越伐吳,敗之姑蘇。”伍被對淮南王,言“見糜鹿遊姑蘇之臺”。古“胥”、“蘇”二字多通用。
○潮信白樂天詩:“早潮才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白是北人,未諳潮候。今杭州之潮,每月朔日以子、午二時到。每日遲三刻有餘,至望日則子潮降而爲午,午潮降而爲夜子。以後半月復然。故大月之潮一月五十八回,小月則五十六回,無六十回也。水月皆陰之屬,月之麗天,出東入西,大月二十九回,小月二十八回,亦無三十回也,所以然者,陽有餘而陰不足,自然之理也。
○晉國晉自武公滅翼,而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其時疆土未廣,至獻公始大。考之於傳:滅楊、滅霍、滅耿、滅魏、滅虞。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太子居曲沃,不過今平陽一府之境。而滅虢、滅焦,則跨大河之南。
不惠公敗韓之倏,秦證河東,則內及解梁。狄取狐廚,涉汾,而晉境稍蹩,文公始啓南陽,得今之懷慶,襄公敗秦於附,惠公賂秦之地復爲晉有。而以河西爲境,持霍太山以北大部皆狄地,不屬’於晉。文公廣三行御狄,裂公敗狄於箕,而秋牛始怖。忡公川槐絆樸戍之謀。以貨易土。平公用荀、吳,敗狄於太原。於是晉之北境至於洞渦、洛陰之間,而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盂爲祁氏之邑,晉陽爲趙氏之邑矣。若成公滅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頃公滅肥、滅鼓,而得今之真定,皆一一可考。吾於杜氏之解綿上箕而不能無疑,並唐叔之封晉陽亦未敢以爲然也。
○綿上《左傳·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杜氏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綿上。”《水經注》:“石桐水即綿水,出介休縣之綿山。北流經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袁崧《郡國志》曰:“介休縣有介山,有綿上聚子推廟。今其山南跨靈石,東跨沁源,世以爲之推所隱。而漢魏以來,傳有焚山之事,太原、上黨、西河、雁門之民至寒食不敢舉火。石勒禁之,而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前史載之,無異辭也。然考之於傳,《襄公十三年》:“晉悼公於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讓幹荀偃。”此必在近國都之地。又定麼人年》:“趙簡子逆宋樂祁,飲之灑於綿上,”自宋如晉,其路豈出於西河介休乎?況文公之時,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與晉都遠不相及。今翼城縣西公有綿山,俗謂之小綿山,近曲沃,當必是簡子逆樂祁之地。今萬泉縣南二里有介山。《漢書·武帝紀》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後土,皆有光應。”《地理志》:汾陰,介山在南。”《楊雄傳》:“其三月,將祭後土,上乃師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陡西嶽,以望八荒。雄作《河東賦》曰:‘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於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水經注》亦引此,謂晉《太康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並言子推隱於是山而辨之,以爲非然,可見漢時己有二說矣。
○箕《左傳·信公三十三年》:“狄伐晉,及箕,”解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非也,陽邑在今之太谷縣,襄公時未爲晉有。傳言“狄伐晉及箕”,猶之言“齊伐我及清”也,必其近國之地也。成公十三年,厲公使呂相絕秦,曰:“入我河縣,焚我箕、郜。”又必其邊河之邑,秦、狄皆可以爭。而文公八年,有箕鄭父;襄公二十一年,有箕遺,當亦以邑氏其人者矣。
○唐《左傳·昭公元年》:“遷實沈於大夏。”《定公四年》:“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杜氏則以爲太原晉陽縣。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括地誌》:“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於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即後世遷都亦遠不相及;況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間,《書》所云“維彼陶唐,有此冀方”,而舜之命皋陶曰“蠻夷猾夏”者也,當以服氏之說爲信。又齊桓公伐晉之師,僅及高梁,而《封禪書》述桓公之言,以爲西伐大夏,大夏之在平陽明矣。
○晉都春秋時,晉國本都翼,在今之翼城縣。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於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爲晉侯,都曲沃;在今聞喜縣。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歷惠、懷、文、襄、靈、成六公,至景公,遷於新田;在今曲沃縣,當汾、澮二水之間。於是命新田爲絳,而以其故都之絳爲故絳。此晉國前後四都之故跡也。晉自都絳之後,遂以曲沃爲下國。然其宗廟在焉。考悼公之立,大夫逆於清原:是次郊外。庚午,盟而入;辛巳,朝於武宮:是入曲沃而朝於廟。二月乙酉朔,即位於朝:是至絳都。而平公之立,亦云“改服修官,於曲沃”,但不知其後何以遂爲奕氏之邑。而欒盈之人絳,範宣子執魏獻子之手,賂之以曲沃,夫以宗邑而與之其臣,聽其所自爲。端氏之封,屯留之徙,其所由來者漸矣。
○瑕晉有二暇。其一,《左傳·成公六年》:“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杜氏曰:“郇瑕,古國名。”《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瑕城。”京相曰:“今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是也。在今之臨晉縣境,其一,《僖公三十年》:“燭之武見秦伯曰:‘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解:“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文公十二年》:“晉人、秦人戰於河曲,秦師夜遁,復侵晉人瑕。”解以河曲爲河東蒲阪縣南,則瑕必在河外。《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按《漢書·地理志》:“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水經·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酈氏注云:“《晉書》:《地道記》:《太康記》並言:胡縣,漢武帝改作“湖”。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古“瑕”、“胡”二字通用。《禮記》引《詩》:“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鄭氏注云:“暇之言胡也。瑕、胡音同,故《記》用其字。”是瑕轉爲胡,又改爲湖。而瑕邑即桃林之塞也,今爲閿鄉縣治。而《成公十三年》:“伐秦,成肅公卒於瑕。”亦此地也,道元以郇瑕之瑕爲詹嘉之邑,誤矣。
《信公十五年》:“晉侯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正義曰:“自華山之東,盡虢之東界,其間有五城也。”傳稱焦瑕,蓋是其二。《成公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瑕嘉即詹嘉,以邑爲氏。《僖公十五年》:“暇呂飴甥。”當亦同此,而解以瑕呂爲姓,恐非。
○九原《禮記.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水經注》以在京陵縣。《漢志·太原郡》:“京陵”,師古曰:“即九京。”因《記》文“或作九京”而傅會之爾。古者卿大夫之葬必在國都之北,不得遠涉數百里,而葬於今之平遙也。《志》以爲太平之西南二十五里有九原山,近是。
○昔陽《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苟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人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綿皋歸。”杜氏謂:“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又謂:“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系}城。”是也。其曰:“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則非也。疏載劉炫之言,以爲:“齊在晉東,僞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按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也?昔陽既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系}之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爲小國,境必不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苟吳伐鮮虞,圍鼓。”杜雲:“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炫謂:“肥、鼓並在矩鹿。昔陽即是鼓都,在鮮虞以東南也。”《二十二年》傳曰:“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
《漢書·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水經注》:“低水東經肥{系}縣之故城南,又東經昔陽城南,本鼓聚。”《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陽亭是矣。”京相曰:“白狄之別也。下曲陽有鼓聚。”其說皆同。《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十六年,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夫昔陽在鉅鹿,故屬之齊,豈得越太行而有樂平乎?
晉之滅狄,其用兵有次第。宣公十五年,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留籲。成公十一年,伐咎如;而上黨爲晉有矣。昭公元年,敗無終及羣狄於大滷;而大原爲晉有矣。然後出師以臨山東,昭公十二年,滅肥。二十二年,滅鼓。於是太行以南之地謂之南陽,太行以東之地謂之東陽。而晉境東接於齊,蓋先後之勤且八十年,而鮮虞猶不服焉,平狄之難如此。
○太原太原府在唐爲北都。《唐書·地理志》曰:“晉陽宮,在都之西北。宮城週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晉,潛丘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築。兩城之間有中城,武後時築,以合東城。宮南有大明城,故宮城也。宮城東有起義堂,倉城中有受瑞壇。當日規模之閎壯可見。自齊神武創建別都,與鄴城東西並立。隋煬繼修宮室。唐高祖因以克關中,有天下。則大以後名爲北都。五代李氏、石氏、劉氏三主皆興於此。及劉繼元之降,宋太宗以此地久爲創霸之府;又宋主大火,有參,辰不兩盛之說,於是一舉而焚之矣。《宋史·太宗紀》:“太平興國四年五月戊子,以榆次縣爲新幷州。乙未,築新城。丙申,幸城北御沙河門樓,盡徙餘民於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即命縱火。丁酉,以行宮爲平晉寺,”陸游《老學庵筆記》曰:“大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降爲幷州,廢舊城,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則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舊城東北三十里,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嘗爲唐明鎮,有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帥潘美奏乞以爲幷州,從之,於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址爲州治。又徙陽曲縣放三交,而榆次復爲縣。然則今之太原府乃三交城,而太原縣不過唐都城之一隅耳。其遺文舊績,一切不可得而見矣。
《舊唐書·崔神慶傳》曰:“則天時,擢拜幷州長史。先是幷州有東西二城,隔汾水,神慶始築城相接,每歲省防禦兵數千人,邊州甚以爲便。”此即《志》所云“兩城之間有中城”者也。汾水湍悍,古人何以架橋立城如此之易?如長安東,中,西三渭橋,昔爲方軌,而今則咸陽縣每至冬月,乃設一版河陽驛,杜預所立浮橋,其遺蹟亦復泯然。蒲津鐵牛,求一僧懷丙,其人不可得。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不但坐而論道者不如古人而已。
○代春秋時,代尚未通中國。趙襄子乃言:“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地道記》雲:“恆山在上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及,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注》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恆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此則今之蔚州,乃古代國。項羽徙趙王歇爲代王,歇更立陳餘爲代王,漢高帝立兄劉仲爲代王,皆此地也。十年,陳稀反。十一年,破,立於恆爲代王,都晉陽。則今之太原縣矣。《孝文紀》則雲:“都中都。”而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又立於武爲代王,都中都。則今之平遙縣矣。又按衛綰,代大陵人。大陵,今在文水縣北,而屬代,代都中都故也。代凡三遷,而皆非今代州。今代州之名自隋始。○闕里《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按《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王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禮記》:“昔者仲尼與放蠟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蓋闕門之下,其裏即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謂之“闕黨”,《魯論》有“闕黨童子”、“荀子、仲尼居於闕黨”是也。後人有以居爲氏者。《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門慶忌”注云:“姓闕門,名慶忌。”
○杏壇今夫子廟庭中有壇,石刻曰“杏壇”。《闕里志》:“杏壇,在殿前,夫子舊居,”非也。杏壇之名出自《莊子入莊子曰:“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於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又曰:“孔子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又曰:“客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侍水波定,不聞音,而後敢乘。”司馬彪雲:“緇帷,黑林名也。杏壇,澤中高處也。”《莊子》書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漁父不必有其人,杏壇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葦間,依破旁渚之地,不在魯國之中也明矣。今之杏壇,乃宋乾興間四十五代孫道輔增修,祖廟移大殿,於後因以講堂舊基石爲壇,環植以杏,取杏壇之名名之耳。
○徐州《史記·齊大公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楚世家》:“威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伐齊,敗之於徐州。”《越世家》:“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按《續漢書·志》:“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也。”此與楚、魏二國爲境。而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蓋與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趙誇之耳。
索隱曰:“《說文》:“餘阝,邾之下邑,在魯東。”又《竹書紀年》雲:“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於薛,改名曰徐州。”則徐與鄰並音舒也。今讀爲《禹貢》:“徐州”之徐者,誤。《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
○向《春秋·隱二年》:“宮人入向。”杜氏解曰:“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桓十六年》:“城向。”無解。《宣四年》:“公及齊侯平宮及郯。宮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解曰:“向,莒邑,東海[C051]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解曰:“莒邑。”按《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社氏注爲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爲國,後並於宮,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間耳,承縣今在嶧,杜氏以其遠而疑之,況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乎?
《齊乘》以爲今沂州之向城鎮,近之矣。
○小《春秋·莊三十二年》:“城小。”《左氏傳》曰:“爲管仲也。”蓋見昭公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齊桓公城,而肯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而又見《信二年》經書“城楚丘”之出於諸侯,謂仲父得君之專,亦可勤諸侯以自封也。是不然。仲所居者也,此聽城者小也。《春秋》有言,小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於。”《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帥伐齊,取。”《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於。”《成三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四書“”而一書“小”,別於也。範寧:“小,魯地。”然則城小者,內城也,故不繫之齊,而與管仲無與也,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羽於城,即此魯之小。而注引《皇覽》,以爲東郡之城,與留候所葆之黃石同其地,其不然明矣。《春秋秋髮微》曰:“曲阜西北有小城。”
○泰山立石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五尺,而銘文並二世詔書鹹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雲:“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雲:“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雲:“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續漢書·祭把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爲秦耳。
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雲“立石”,下雲“刻石頌秦德”,於泰山則上雲“立石”,下雲“刻所立石”。於之罘則二十八年雲“立石”,二十九年雲“刻石”。於琅邪則雲“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雲“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碣石則雲“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泰山都尉《後漢書·桓帝紀》:永興二年,泰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殺長史。永壽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熹五年八月己卯,罷琅邪都尉官。八年五月王申,罷泰山都尉官。《金石錄》載漢《泰山都尉孔宙碑》雲:“宙以延熹四年卒。”蓋卒後四年官遂廢矣。然泰山都尉實不始於此,光武時曾置之。《文苑傳》:“夏恭,光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都尉。”又按《光武紀》:“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官。”恭之遷蓋在此年前也。
泰山自公孫舉、東郭竇,勞丙叔、孫無忌相繼叛亂,以是置都尉之官。以後官雖不設,而郡兵領於太守,其力素厚。故何進使府掾泰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而應劭、夏侯淵亦以之破黃巾,可見漢代不廢郡兵之效。而建安中,曹公表曰:“泰山郡界曠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爲贏郡。”則其時之習俗又可知矣。
○社首《史記》:“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唐書》: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庚午,禪社首。”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禪社首。”《宋史》: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王子,禪社首。”今高裏山之左有小山,其高可四五丈,《志》雲即社首山。在嶽旁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於此?意者封於高,欲其近天;禪於下,欲其近地。且山卑而附嶽址,便於將事,初陟高之後不欲更勞民力邪?○濟南都尉漢濟南郡太守,治東平陵。而都尉治放陵者,以長白山也。《魏書·辛子菠傳》:“長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奸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隋大業九年,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以張須陀、王世充之力不能滅,訖於隋亡。觀此二事,則知漢人立都尉治於陵之意矣。
○鄒平臺二縣《漢書》濟南郡之縣十四,一曰東平陵,二日鄒平,三曰臺,四日梁鄒。《功臣表》則有臺定侯戴野,梁鄒孝侯武虎,是二縣併爲侯國。《續漢志》濟南郡十城,其一曰東平陵,其四曰臺,其七日梁鄒,其八日鄒平。而《安帝紀》雲:“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章懷太子注云:“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齊州平陵縣北。”《晏子春秋》:“景公爲晏子封邑,使田無字致臺與無鹽。”《水經注》亦云:“濟水又東北過臺縣北。”尋其上下文句,本自了然,後人讀《漢書》,誤從“鄒”字絕句,因以鄒爲一縣,平臺爲一縣。《齊乘》遂渭漢濟南郡有鄒縣,後漢改爲鄒平,又以臺、平臺爲二縣。此不得其句讀而妄爲之說也。
漢以鄒名縣者五。魯國有騶,亦作“鄒”;膠東國有鄒盧;千乘郡有東鄒;與濟南之鄒平、梁鄒,凡五。其單稱鄒者,今兗州府之鄒縣也。亦有平臺,屬常山郡。《外戚恩澤侯表》:“平臺康侯史元。”《後漢書·邱彤傳》:“尹綏封平臺侯”是也。有鄒平、有臺,而亦有鄒,有平臺,不可不辨也。
晉時縣名多沿漢舊,按史《何曾傳》:“曾孫機爲鄒平令。”是有鄒平矣,《解系傳》:“父修,封梁鄒侯。”《劉頌傳》:“追封梁鄒縣侯。”是有梁鄒矣。《宋書》言:“晉太康六年三月戊辰,樂安、梁鄒等八縣隕霜,傷桑麥。”《文帝紀》:“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八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則是宋有梁鄒矣。不知何故,《晉書·地理志》於“樂安國”下,單書一“鄒”字,此史之闕文。
而《齊乘》乃雲:“晉省梁鄒入鄒縣。”夫晉以前,此地本無鄒縣,而何從人之乎?蓋不知而妄作者矣。
○夾谷《春秋·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夾谷。”傳曰:“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杜預解及服虔注《史記》,皆雲在東海祝其縣。劉昭《志》、杜佑《通典》因之,遂謂夾谷山在今贛榆縣西五十里。按贛榆在春秋爲莒地,與齊、魯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遠?當時景公之觀不過曰“遵海而南,放於琅邪”而已,未聞越他國之境。《金史》雲:“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雲:“夾谷山在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即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於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是以甲山爲夾谷也,而《萊蕪縣誌》則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界。”未知其何所據,然齊,魯之境正在萊蕪;東至淄川,則已人齊地百餘里。二說俱通。又按《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雲: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於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外也。不可泥祝其之名,而遠求之海上矣。
○濰水濰水出琅邪郡箕屋山。《書·禹貢》”濰淄其道”,《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是也。其子或省“水”作“維”,或省“系”作“淮”,又或從“心”作“惟”,總是一字。《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箕”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貢》:“惟甾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
《通鑑·梁武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杲於惟水。”古人之文或省,或惜其旁,並從“鳥隹”之“隹”則一爾。徑人誤讀爲“淮沂其”之“淮”,而呼此水爲槐河,失之矣。
又如《三國志·吳主傳》:“作棠邑塗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凌詐言吳人塞塗水。”《武帝紀》:“琅邪王出餘中。”《海西公紀》:“桓溫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於塗中。”《孝武紀》:“遣徵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塗中。”《安帝紀》:“譙王尚之衆潰逃於塗中。”並是“滁”字,《南史·程文季傳》:“秦郡前江浦通塗水”是也。古“滁”省作“塗”,與“濰”省作“淮”正同,韻書並不收此二字。
○勞山勞山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丘”,長春又改爲“鰲”,皆鄙淺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於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地形志》、《唐書·姜撫傳》、《宋史·甄棲真傳》並作“牢”,乃傳寫之誤。《詩》:“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雲:“勞勞,廣闊。”則此山或取其廣闊而名之。鄭康成,齊人;勞勞,齊語也。
《山海經·西山經》亦有勞山,與此同名。
《寰字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即勞山,盛即成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於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彎,侯大魚至,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正義曰:“榮成山即成山也。”按史書及前代地理書,並無榮成山,予向疑之。以爲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後見王充《論衡》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君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並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著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誤。先生《勞山圖志序》略曰:勞山在今即墨縣東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勞、小勞,其峯數十,總名曰勞,《志》言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因謂此山一名勞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義。《漢書》:“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縣東北,則勞、盛自是二山,古人立言尚簡,齊之東偏,三面環海,其鬥入海處,南勞而北盛,貝盡乎齊東境矣。其山高大深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跡罕至。秦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挽而後上也。五不生,環山以外,土皆疏脊,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亻待,四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後上也。於是齊人苦之,而名之曰勞山,其以是夫?古之聖王勞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遊而勞之名傳之千萬年。然而致止則有由矣。《漢志》言齊俗誇詐。自大公、管仲之餘,其言霸術已無遺策。而一二智慧之士猖爲迂怪之談,以聳動天下之聽,不過欲時君擁,辯士詘服,爲名高而已,豈知其患之至於此也!
○楚丘《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杜氏曰:“楚丘,衛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夫濟陰之成武,此曹地也,而言衛非也。蓋爲僖公二年“城楚丘”同名而誤。按衛國之封本在汲郡朝歌。懿公爲狄所滅,渡河而東,立戴公,以廬於曹。杜氏曰:“曹,衛下邑。”《詩》所謂“思須與潛”,廬者,無城郭之稱,而非曹國之曹也。《僖公三年》:“城楚丘。”杜氏曰:“楚丘,衛邑。”《詩》所謂“作於楚宮”,而非戎伐凡伯之楚丘也。但曰衛邑,而不詳其地,然必在今滑縣、開州之間。滑在河東,故唐人有““魏、滑分河”之錄矣。《水經注》乃曰:“楚丘,在成武西南,即衛文公所徙。”誤矣。彼曹國之地,齊桓安得取之而封衛乎,以曹名同,楚丘之名又同,遂附爲一地爾。
今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景山,疑即《商頌》所云:“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而《左傳·昭公四年》椒舉言:“商湯有景毫之命”者也。《詩》:“望楚於堂,景山與京。”則不在此也。
○東漢陳留郡有東。《續漢志》注云:“《陳留志》曰:‘故戶牖鄉有陳平祠。”而山陽郡有東緡,《續漢志》:“春秋時曰緡。”注云:“《左傳·僖公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前書》師古曰:“緡音。”《左傳》解:“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攻爰戚、東緡以往。”索隱曰:“山陽有東緡縣。”屬陳留者,音。屬山陽者,音。《括地誌》雲:“東緡故城在兗州金鄉縣界。”《水經注》引《王海碑》辭曰:“使河堤謁者山陽東司馬登。”是以“緡”爲“”,誤矣。《隸釋·酸棗令劉熊碑》陰:“故守東長蘇勝。”則陳留之東也。
○長城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隨地可以設關。而殲陌之間一縱一橫,亦非戎車之利也。觀國佐之對晉人則可知矣,至於戰國,井田始廢,而車變爲騎,於是寇鈔易而防守難,不得已而有長城之築。《史記·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拒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續漢志》:“濟北國盧有長城,至東海。”《泰山記》:“泰山西有長城,緣河經泰山,一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此齊之長城也。《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蘇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竹書紀年》:“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此魏之長城也。《續漢志》:“河南郡卷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韓之長城也。《水經注》:“盛弘之雲:葉東界有故城始縣,東至氵親水,達Г陽,南北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此楚之長城也。若《趙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又言:“肅侯十六年,築長城。”則趙與中山亦有長城矣。以此言之,中國多有長城,不但北邊也。
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後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秦之長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此魏之長城也。《匈奴傳》又言:“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此趙之長城也。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漸土}溪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桃,至遼東,萬餘裏。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此秦並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自此以往,則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魏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裏。大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五月丙戌,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城。
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北齊文宣帝天保三年十月乙未,起長城自黃護嶺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恆州九百餘里。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而《斛律羨傳》雲:“羨以北滷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距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並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立亭障,西自雁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黃河,西至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大業三年七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逾榆林,東至紫河。四年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此又後史所載繼築長城之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