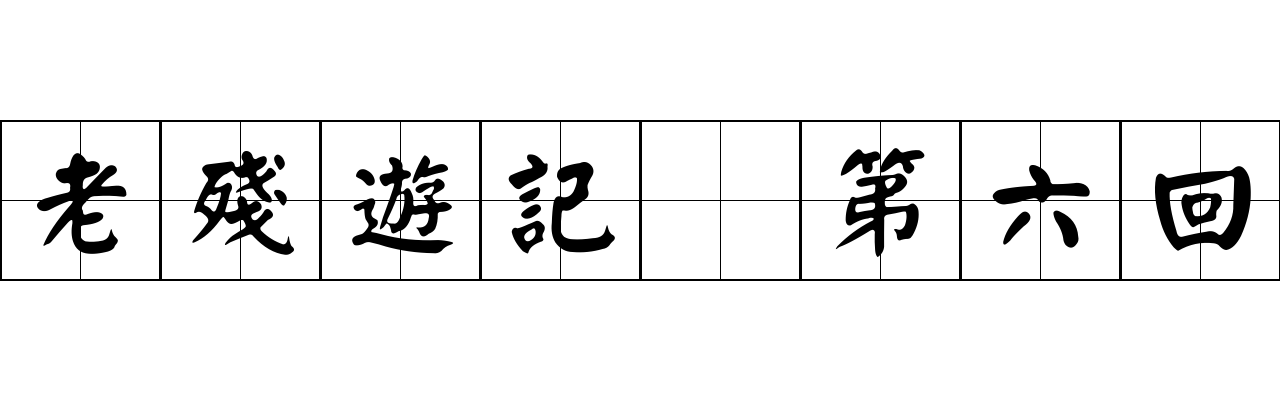老殘遊記-第六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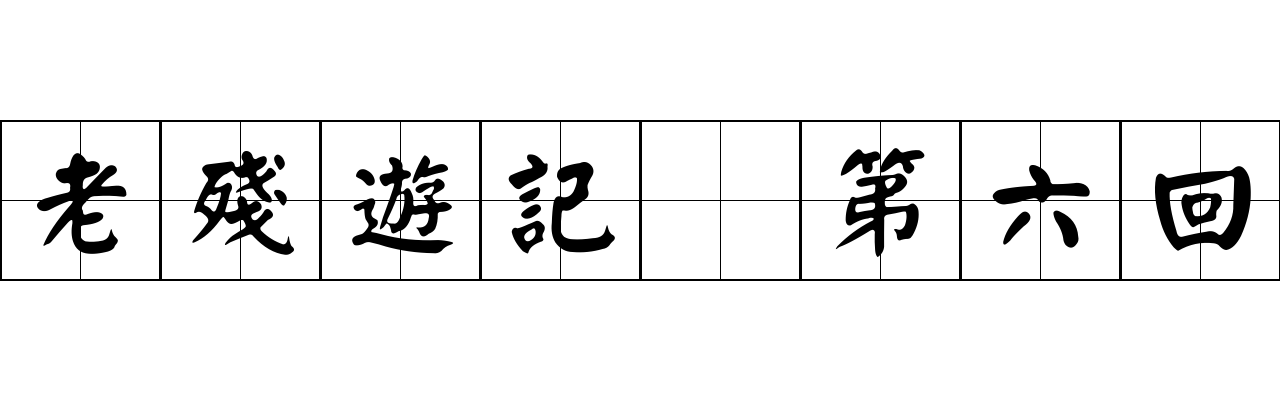
《老殘遊記》,清末中篇小說,是劉鶚 (1857年10月18日—1909年8月23日)的代表作,小說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殘的遊歷爲主線,對社會矛盾開掘很深,尤其是他在書中敢於直斥清官(清官中的酷吏)誤國,清官害民,獨具慧眼地指出清官的昏庸常常比貪官更甚。同時,小說在民族傳統文化精華提煉、生活哲學及藝術、女性審美和平等、人物心理及音樂景物描寫等多方面皆達到了極其高超的境界。
萬家流血頂染猩紅 一席談心辯生狐白
話說店夥說到將他妹夫扯去站了站籠,布匹交金四完案。老殘便道:“這事我已明白,自然是捕快做的圈套,你們掌櫃的自然應該替他收屍去的。但是,他一個老實人,爲什麼人要這麼害他呢,你掌櫃的就沒有打聽打聽嗎?”
店夥道:“這事,一被拿,我們就知道了,都是爲他嘴快惹下來的亂子。我也是聽人家說的:府裏南門大街西邊小衚衕裏,有一家子,只有父子兩個:他爸爸四十來歲,他女兒十七八歲,長的有十分人材,還沒有婆家。他爸爸做些小生意,住了三間草房,一個土牆院子。這閨女有一天在門口站着,碰見了府裏馬隊上什長花胳膊王三,因此王三看他長的體面,不知怎麼,胡二巴越的就把他弄上手了。過了些時,活該有事,被他爸爸回來一頭碰見,氣了個半死,把他閨女着實打了一頓,就把大門鎖上,不許女兒出去。不到半個月,那花胳膊王三就編了法子,把他爸爸也算了個強盜,用站籠站死。後來不但他閨女算了王三的媳婦,就連那點小房子也算了王三的產業。
“俺掌櫃的妹夫,曾在他家賣過兩回布,認得他家,知道這件事情。有一天,在飯店裏多吃了兩鍾酒,就發起瘋來,同這北街上的張二禿子,一面喫酒,一面說話,說怎麼樣緣故,這些人怎麼樣沒個天理。那張二禿子也是個不知利害的人,聽得高興,盡往下問,說:‘他還是義和團裏的小師兄呢。那二郎、關爺多少正神常附在他身上,難道就不管管他嗎?”他妹夫說:‘可不是呢。聽說前些時,他請孫大聖,孫大聖沒有到,還是豬八戒老爺下來的。倘若不是因爲他昧良心,爲什麼孫大聖不下來,倒叫豬八戒下來呢?我恐怕他這樣壞良心,總有一天碰着大聖不高興的時候,舉起金箍棒來給他一棒。那他就受不住了。’二人談得高興,不知早被他們團裏朋友,報給王三,把他們兩人面貌記得爛熟。沒有數個月的工夫,把他妹夫就毀了。張二禿子知道勢頭不好,仗着他沒有家眷,‘天明四十五’,逃往河南歸德府去找朋友去了。
“酒也完了,你老睡罷。明天倘若進城,千萬說話小心!俺們這裏人人都耽着三分驚險,大意一點兒,站籠就會飛到脖兒梗上來的。”於是站起來,桌上摸了個半截線香,把燈撥了撥,說:“我去拿油壺來添添這燈。”老殘說:“不用了,各自睡罷。”兩人分手。
到了次日早晨,老殘收檢行李,叫車伕來搬上車子。店夥送出,再三叮嚀:“進了城去,切勿多話。要緊,要緊!”老殘笑着答道:“多謝關照。”一面車伕將車子推動,向南大路進發,不過午牌時候,早已到了曹州府城。進了北門,就在府前大街尋了一家客店,找了個廂房住下。跑堂的來問了飯菜。就照樣辦來喫過了,便到府衙門前來觀望觀望。看那大門上懸着通紅的綵綢,兩旁果真有十二個站籠,卻都是空的,一個人也沒有,心裏詫異道:“難道一路傳聞都是謊話嗎?”踅了一會兒,仍自回到店裏。只見上房裏有許多戴大帽子的人出入,院子裏放了一肩藍呢大轎,許多轎伕穿了棉祆褲,也戴着大帽子,在那裏喫餅;又有幾個人穿着號衣,上寫着“城武縣民壯”字樣,心裏知道這上房住的必是城武縣了。過了許久,見上房裏家人喊了一聲“伺候”那轎伕便將轎子搭到階下。前頭打紅傘的拿了紅傘,馬棚裏牽出了兩匹馬,登時上房裏紅呢簾子打起,出來了一個人,水晶頂,補褂朝珠,年紀約在五十歲上下,從臺階上下來,進了轎子,呼的一聲,擡起出門去了。
老殘見了這人,心裏想到:“何以十分面善?我也未到曹屬來過,此人是在那裏見過的呢?……”想了些時,想不出來,也就罷了。因天時尚早,復到街上訪問本府政績,竟是一口同聲說好,不過都帶有慘淡顏色,不覺暗暗點頭,深服古人“苛政猛於虎”一語真是不錯。
回到店中,在門口略爲小坐。卻好那城武縣已經回來,進了店門,從玻璃窗裏朝外一看,與老殘正屬四目相對。一恍的時候,轎子已到上房階下,那城武縣從轎子裏出來,家人放下轎簾,跟上臺階。遠遠看見他向家人說了兩句話,只見那家人即向門口跑來,那城武縣仍站在臺階上等着。家人跑到門口,向老殘道:“這位是鐵老爺麼?”老殘道:“正是。你何以知道?你貴上姓甚麼?”家人道:“小的主人姓申,新從省裏出來,撫臺委署城武縣的,說請鐵老爺上房裏去坐呢。”老殘恍然想起,這人就是文案上委員申東造。因雖會過兩三次,未曾多餘接談,故記不得了。
老殘當時上去,見了東造,彼此作了個揖。東造讓到裏間屋內坐下,嘴裏連稱:“放肆,我換衣服。”當時將官服脫去,換了便服,分賓主坐下,問道:“補翁是幾時來的?到這裏多少天了?可是就住在這店裏嗎?”老殘道:“今日到的,出省不過六七天,就到此地了。東翁是幾時出省?到過任再來的嗎?”東造道:“兄弟也是今天到,大前天出省。這夫馬人役是接到省城去的。我出省的前一天,還聽姚雲翁說:宮保看補翁去了,心裏着實難過,說自己一生契童名士,以爲無不可招致主人,今日竟遇着一個鐵君,真是浮雲富貴。反心內照,愈覺得齷齪不堪了!”
老殘道:“宮保愛才若渴,兄弟實在欽佩的。至於出來的原故,並不是肥遯鳴高的意思:一則深知自己才疏學淺,不稱揄揚;二則因這玉太尊聲望過大,到底看看是個何等人物。至‘高尚’二字,兄弟不但不敢當,且亦不屑爲。天地生纔有數,若下愚蠢陋的人,高尚點也好藉此藏拙;若真有點濟世之才,竟自遯世,豈不辜負天地生才之心嗎?”東造道:“屢聞至論,本極佩服;今日之說,則更五體投地。可見長沮、桀溺等人爲孔子所不取的了。只是目下在補翁看來,我們這玉太尊究竟是何等樣人?”老殘道:“不過是下流的酷吏,又比郅都、甯成等人次一等了。”東造連連點頭,又問道:“弟等耳目有所隔閡,先生布衣遊歷,必可得其實在情形。我想太尊殘忍如此,必多冤枉,何以竟無上控的案件呢?”老殘便將一路所聞細說一遍。
說得一半的時候,家人來請喫飯。東造遂留老殘同吃,老殘亦不辭讓。喫過主後,又接着說去。說完了,便道:“我只有一事疑惑:今日在府門前瞻望,見十二個站籠都空着,恐怕鄉人之言,必有靠不住處。”東造道:“這卻不然。我適在菏澤縣署中,聽說太尊是因爲晚日得了院上行知,除已補授實缺外,在大案裏又特保了他個以道員在任候補,並俟歸道員班後,賞加二品銜的保舉。所以停刑三日,讓大家賀喜。你不見衙門口掛着紅綵綢嗎?聽說停刑的頭一日,即是昨日,站籠上還有幾個半死不活的人,都收了監了。”彼此嘆息了一回。老殘道:“旱路勞頓,天時不早了,安息罷。”東造道:“明日晚間,還請枉駕談談,弟有極難處置之事,要得領教,還望不棄纔好。”說罷,各自歸寢。
到了次日,老殘起來,見那天色陰的很重,西北風雖不甚大,覺得棉袍子在身上有飄飄欲仙之致。洗過臉,買了幾根油條當了點心,沒精打采的到街上徘徊些時。正想上城牆上去眺望遠景,見那空中一片一片的飄下許多雪花來,頃刻之間,那雪便紛紛亂下,迴旋穿插,越下越緊。趕急走回店中,叫店家籠了一盆火來。那窗戶上的紙,只有一張大些的,懸空了半截,經了雪的潮氣,迎着風“霍鐸霍鐸”價響。旁邊零碎小紙,雖沒有聲音,卻不住的亂搖。房裏便覺得陰風森森,異常慘淡。
老殘坐着無事,書又在箱子裏不便取,只是悶悶的坐,不禁有所感觸,遂從枕頭匣內取出筆硯來,在牆上題詩一首,專詠王賢之事。詩曰:
得失淪肌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闕暗,血染頂珠紅。
處處鵂鶹雨,山山虎豹風。殺民如殺賊,太守是元戎!下題“江南徐州鐵英題”七個字。
寫完之後,便喫午飯。飯後,那雪越發下得大了。站在房門口朝外一看,只見大小樹枝,彷彿都用簇新的棉花裹着似的,樹上有幾個老鴉,縮着頸項避寒,不住的抖擻翎毛,怕雪堆在身上。又見許多麻雀兒,躲在屋檐底下,也把頭縮着怕冷,其飢寒之狀殊覺可憫。因想:“這些鳥雀,無非靠着草木上結的實,並些小蟲蟻兒充飢度命。現在各樣蟲蟻自然是都入蟄,見不着的了。就是那草木之實,經這雪一蓋,那裏還有呢,倘若明天晴了,雪略爲化一化,西北風一吹,雪又變做了冰,仍然是找不着,豈不要餓到明春嗎?”想到這裏,覺得替這些鳥雀愁苦的受不得。轉念又想:“這些鳥雀雖然凍餓,卻沒有人放槍傷害他,又沒有什麼網羅來捉他,不過暫時飢寒,撐到明年開春,便快活不盡了。若像這曹州府的百姓呢,近幾年的年歲,也就很不好。又有這麼一個酷虐的父母官,動不動就捉了去當強盜待,用站籠站殺,嚇的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於飢寒之外,又多一層懼怕,豈不比這鳥雀還要苦嗎!”想到這裏,不覺落下淚來。又見那老鴉有一陣“刮刮”的叫了幾聲,彷彿他不是號寒啼飢,卻是爲有言論自由的樂趣,來驕這曹州府百姓似的。想到此處,不覺怒髮衝冠,恨不得立刻將玉賢殺掉,方出心頭之恨。
正在胡思亂想,見門外來了一乘藍呢轎,並執事人等,知是申東造拜客回店了。因想:“我爲甚麼不將這所見所聞的,寫封信告訴莊宮保呢?”於是從枕箱裏取出信紙信封來,提筆便寫。那知剛纔題壁,在硯臺上的墨早已凍成堅冰了,於是呵一點寫一點。寫了不過兩張紙,天已很不早了。硯臺上呵開來,筆又凍了,筆呵開來,硯臺上又凍了,呵一回,不過寫四五個字,所以耽擱工夫。
正在兩頭忙着,天色又暗起來,更看不見。因爲陰天,所以比平常更黑得早,於是喊店家拿盞燈來。喊了許久,店家方拿了一盞燈,縮手縮腳的進來,嘴裏還喊道:“好冷呀!”把燈放下,手指縫裏夾了個紙煤子,吹了好幾吹,才吹着。那燈裏是新倒上的凍油,堆的像大螺絲殼似的,點着了還是不亮。店家道:“等一會,油化開就亮了。”撥了撥燈,把手還縮到袖子裏去,站着看那燈滅不滅。起初燈光不過有大黃豆大,漸漸的得了油,就有小蠶豆大了。忽然擡頭看見牆上題的字,驚惶道:“這是你老寫的嗎?寫的是啥?可別惹出亂子呀!這可不是頑兒的!”趕緊又回過頭,朝外看看,沒有人,又說道:“弄的不好,要壞命的!我們還要受連累呢!”老殘笑道:“底下寫着我的名字呢,不要緊的。”
說着,外面進來了一個人,戴着紅纓帽子,叫了一聲“鐵老爺”,那店家就趔趔趄趄的去了。那進來的人道:“敝上請錢老爺去喫飯呢。”原來就是申東造的家人。老殘道:“請你們老爺自用罷,我這裏已經叫他們去做飯,一會兒就來了。說我謝謝罷。”那人道:“敝上說:店裏飯不中喫。我們那裏有人送的兩隻山雞,已經都片出來了,又片了些羊肉片子,說請鐵老爺務必上去喫火鍋子呢。敝上說:如鐵老爺一定不肯去,敝上就叫把飯開到這屋裏來喫,我看,還是請老爺上去罷:那屋子裏有大火盆,有這屋裏火盆四五個大,暖和得多呢;家人們又得伺候,請你老成全家人罷!”
老殘無法,只好上去。申東造見了,說:“補翁,在那屋裏做什麼,恁大雪天,我們來喝兩杯酒罷!今兒有人送來極新鮮的山雞,燙了喫,很好的,我就借花獻佛了。”說着,便入了座。家人端上山雞片,果然有紅有白,煞是好看。燙着喫,味更香美。東造道:“先生吃得出有點異味嗎?”老殘道:“果然有點清香,是什麼道理?”東造道:“這雞出在肥城縣桃花山裏頭的。這山裏松樹極多,這山雞專好喫松花鬆實,所以有點清香,俗名叫做‘松花雞,。雖在此地,亦很不容易得的。”老殘讚歎了兩句,廚房裏飯菜也就端上桌子。
兩人喫過了飯。東造約到裏間房裏喫茶、向火。忽然看見老殘穿着一件棉袍子,說道:“這種冷天,怎麼還穿棉袍子呢?”老殘道:“毫不覺冷。我們從小兒不穿皮袍子的人,這棉袍子的力量恐怕比你們的狐皮還要暖和些呢。”東造道:“那究竟不妥。”喊:“來個人!你們把我扁皮箱裏,還有一件白狐一裹圓的袍子取出來,送到鐵老爺屋子裏去。”
老殘道:“千萬不必,我決非客氣!你想,天下有個穿狐皮袍子搖串鈴的嗎?”東造道:“你那串鈴,本可以不搖,何必矯俗到這個田地呢!承蒙不棄,拿我兄弟還當個人,我有兩句放肆的話要說,不管你先生惱我不惱我。昨兒聽先生鄙薄那肥遯鳴高的人,說道:‘天地生纔有限,不宜妄自菲薄。’這話,我兄弟五體投地的佩服。然而先生所做的事情,卻與至論有點違背。宮保一定要先生出來做宮,先生卻半夜裏跑了,一定要出來搖串鈴。試問,與那鑿壞而遁,洗耳不聽的,有何分別呢?兄弟話未免鹵莽,有點冒犯,請先生想一想,是不是呢?”
老殘道:“搖串鈴,誠然無濟於世道,難道做官就有濟於世道嗎?請問:先生此刻已經是城武縣一百里萬民的父母了,其可以有濟於民處何在呢?先生必有成竹在胸,何妨賜教一二呢?我知先生在前已做過兩三任官的,請教已過的善政,可有出類拔萃的事蹟呢?”東造道:“不是這麼說。像我們這些庸材,只好混混罷了。閣下如此宏材大略,不出來做點事情,實在可惜。無才者抵死要做宮,有才者抵死不做官,此正是天地間第一憾事!
老殘道:“不然。我說無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緊,正壞在有才的要做官,你想,這個玉大尊,不是個有才的嗎?只爲過於要做官,且急於做大官,所以傷天害理的做到這樣。而且政聲又如此其好,怕不數年之間就要方面兼圻的嗎。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則一府傷,撫一省則一省殘,宰天下則天下死!由此看來,請教還是有才的做官害大,還是無才的做官害大呢?倘若他也像我,搖個串鈴子混混,正經病,人家不要他治;些小病痛,也死不了人。即使他一年醫死一個,歷一萬年,還抵不上他一任曹州府害的人數呢!”未知申東造又有何說,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