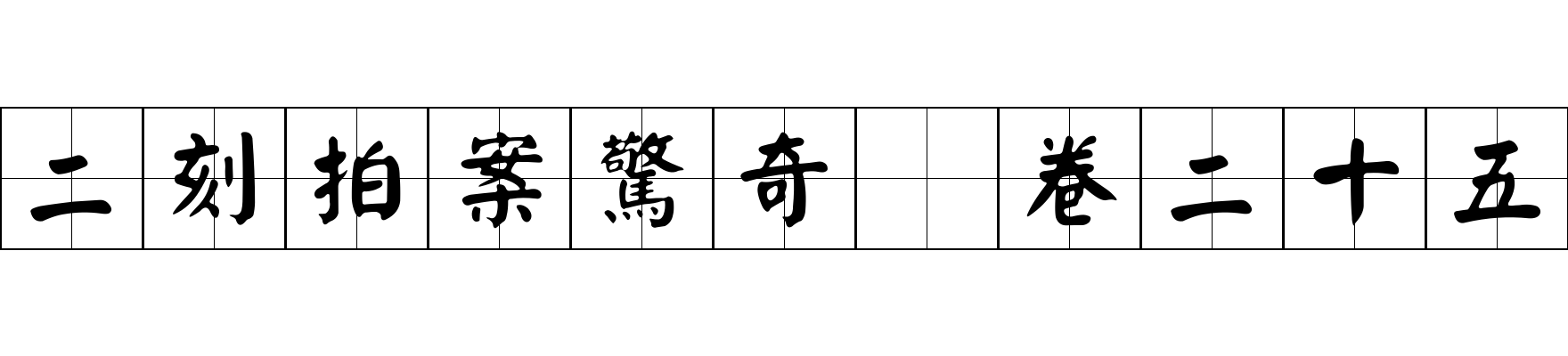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五-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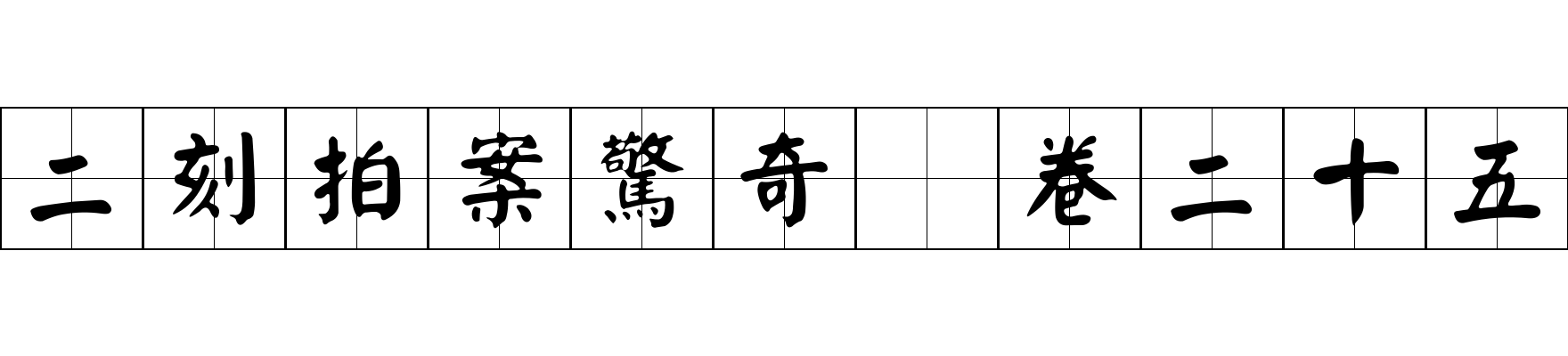
《二刻拍案驚奇》爲擬話本小說集。明末凌濛初編著。於1632年(崇楨五年)成書刊行,與作者前著《初刻拍案驚奇》合稱“二拍”。四十卷,每卷一篇,共四十篇,其中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願,小姨病起續前緣》,與《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三相同,卷四十已亡佚,補錄雜劇《宋公明鬧元宵雜劇》以充數。作者自稱系“偶戲取古今所聞一二奇局可紀者演而成說”,題材大多取自前人。該書的思想內容是比較複雜,但從總體上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興的市民階層的思想觀念,其所提倡的傳統道德中也有不可否定的健康成分。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較重要的影響。
徐茶酒乘鬧劫新人 鄭蕊珠鳴冤完舊案
瑞氣籠清曉。卷珠簾,次第笙歌,一時齊奏。無限神仙離蓬島,鳳駕鸞車初到。見擁個、仙娥窈窕。玉珮玎鐺風縹緲,望嬌姿、一似垂楊嫋。天上有,世間少。劉郎正是當年少。更那堪,天教付與,最多才貌。玉樹瓊枝相映耀,誰與安排忒好?有多少、風流歡笑。直待來春成名了,馬如龍、綠緩欺芳草。同富貴,又偕老。
這首詞名《賀新郎》,乃是宋時辛稼軒爲人家新婚吉席而作。天下喜事,先說洞房花燭夜,最爲熱鬧。因是這熱鬧,就有趁哄打劫的了。吳興安吉州富家新婚,當夜有一個做賊的,趁着人雜時節,溜將進去,伏在新郎的牀底下了,打點人靜後,出來卷取東西。怎當這人家新房裏頭,一夜停火到天明。牀上新郎新婦,雲雨歡濃了一會,枕邊切切私語,你問我答,煩瑣不休。說得高興,又弄起那話兒來,不十分肯睡。那賊躲在牀下,只是聽得肉麻不過,卻是不曾靜悄。又且燈火明亮,氣也喘不得一口,何況脫身出來做手腳?只得耐心伏着不動。水火急時,直等日間牀上無人時節,就牀下暗角中撤放。如此三日夜,畢竟下不得手,肚中餓得難堪。顧不得死活,聽得人聲略定,拼着命魆魆走出,要尋路逃去。火影下早被主家守宿人瞧見,叫一聲“有賊!”前後人多扒起來,拿住了。先是一頓拳頭腳尖,將繩捆着,誰備天明送官。賊人哀告道:“小人其實不曾偷得一毫物事,便做道不該進來,適間這一頓臭打,也拆算得過了。千萬免小人到官,放了出去,小人自有報效之處。”主翁道:“誰要你報效!你每這樣歹人,只是送到官,打死了才幹淨。”賊人道:“十分不肯饒我,我到官自有說話。你每不要懊悔!”主翁見他說得倔強,更加可恨,又打了幾個巴拿。
捆到次日,申破了地方,一同送到縣裏去。縣官審問時,正是賊有賊智,那賊人不慌不忙的道:“老爺詳察,小人不是個賊,不要屈了小人!”縣官道:“不是賊,是甚麼樣人,躲在人家牀下?”賊人道:“小人是個醫人,只爲這家新婦,從小有個暗疾,舉發之時,疼痛難當,惟有小人醫得,必要親手調治,所以一時也離不得小人。今新婚之夜,只怕舊疾舉發,暗約小人隨在房中,防備用藥,故此躲在牀下。這家人不認得,當賊拿了。”縣官道:“那有此話?”賊人道:
“新婦乳名瑞姑,他家父親,寵了妾生子女,不十分照管他。母親與他一路,最是愛惜。所以有了暗疾,時常叫小人私下醫治。今若叫他到官,自然認得小人,才曉得不是賊。”知縣見他丁一確二說着,有些信將起來,道:“果有這等事,不要冤屈了平人。而今只提這新婦當堂一認就是了。”
元來這賊躲在牀下這三夜,備細聽見牀上的說話。新婦果然有些心腹之疾,家裏常醫的。因告訴丈夫,被賊人記在肚裏,恨這家不饒他,當官如此攀出來。不惟可以遮飾自家的罪,亦且可以弄他新婦到官,出他家的醜。這是那賊人憊賴之處。那曉縣官竟自被他哄了,果然提將新婦起來。富家主翁急了,負極去求免新婦出官。縣官那裏肯聽?富家翁又告情願不究賊人罷了,縣官大怒道:“告別人做賊也是你,及至要個證見,就說情願不究,可知是誣賴平人爲盜。若不放新婦出來質對,必要問你誣告。”富家翁計無所出,方悔道:“早知如此,放了這猾賊也罷,而今反受他累了。”
衙門中一個老吏,見這富家翁徬徨,問知其故,便道:“要破此猾賊也不難,只要重重謝我。我去稟明瞭,有方法叫他伏罪。”富家翁許了謝禮十兩。老吏去稟縣官道:“這家新婦初過門,若出來與賊盜同辨公庭,恥辱極矣!老爺還該惜具體面。”縣官道:“若不出來,怎知賊的真假?”老吏道:“吏典到有一個愚見。想這賊潛藏內室,必然不曾認得這婦人的,他卻混賴其婦有約。而今不必其婦到官,密地另使一個婦人代了,與他相對。他認不出來,其誣立見,既可以辨賊,又可以周全這家了。”縣官點頭道:“說得有理。”就叫吏典悄地去喚一娼婦打扮了良家,包頭素衣,當賊人面前帶上堂來,高聲稟道:“其家新婦瑞姑拿到!”賊人不知是假,連忙叫道:“瑞姑,瑞姑,你約我到房中治病的,怎麼你公公家裏拿住我做賊送官,你就不說一聲?”縣官道:“你可認得正是瑞姑了麼?”賊人道:“怎麼不認得?從小認得的。”縣官大笑道:“有這樣奸詐賊人,險被你哄了。元來你不曾認得瑞姑,怎賴道是他約你醫病?這是個娼妓,你認得真了麼?”賊人對口無言,縣官喝叫用刑。賊人方纔訴說不曾偷得一件,乞求減罪。縣官打了一頓大板,枷號示衆。因爲無贓,恕其徒罪。富家翁新婦方纔得免出官。這也是新婚人家一場大笑話。
先說此一段做個笑本。小子的正話,也說着一個新婚人家,弄出好些沒頭的官司,直到後來方得明白。
本爲花燭喜筵,弄作是非苦海。
不因天網恢恢,啞謎何對得解?
卻說直隸蘇州府嘉定縣有一人家,姓鄭,也是經紀行中人,家事不爲甚大。生有一女,小名蕊珠,這倒是個絕世佳人,真個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許下本縣一個民家姓謝,是謝三郎,還未曾過門。這個月裏揀定了吉日,謝家要來取去。三日之前,蕊珠要整容開面,鄭家老兒去喚整容匠。元來嘉定風俗,小戶人家女人蓖頭剃臉,多用着男人。其時有一個後生,姓徐名達,平時最是不守本分,心性奸巧好淫,專一打聽人家女子,那家生得好,那家生得醜。因爲要像心看着內眷,特特去學了那櫛工生活,得以進入內室。又去做那婚筵茶酒,得以窺看新人。如何叫得茶酒?即是那邊儐相之名,因爲贊禮時節在旁高聲“請茶!”“請酒!”多是他口裏說的,所以如此稱呼。這兩項生意,多傍着女人行止,他便一身兼做了。此時鄭家就叫他與女兒蕊珠開面。徐達帶了蓖頭傢伙,一徑到鄭家內裏來。蕊珠做女兒時節,徐達未曾見一面,而今卻叫他整客,煞是看得親切。徐達一頭動手,一頭覷玩,身子如雪獅子向火,看看軟起來。那話兒如喫石髓的海燕,看看硬起來。可惜礙着前後有人,恨不就勢一把抱住弄他一會。鄭老兒在旁看見模樣,識破他有些輕薄意思。等他用手一完,急打發他出到外邊來了。
徐達看得渾身似火,背地裏手銃也不知放了幾遭,心裏掉不下。曉得嫁去謝家,就設法到謝家包做了吉日的茶酒。到得那日,鄭老兒親送女兒過門。只見出來迎接的儐相,就是前日的櫛工徐達。心下一轉道:“元來他又在此。”比至新人出轎,行起禮來,徐達沒眼看得,一心只在新娘子身上。口裏哩連羅連,把禮數多七顛八倒起來。但見:東西錯認,左右亂行。信口稱呼,親翁忽爲親媽:無心贊喝,該“拜”反做該“興”。見過泰山,又請嶽翁受禮;參完堂上,還叫父母升廳。不管嘈壞郎君,只是貪看新婦。徐達亂嘈嘈的行過了許多禮數,新娘子花燭已過,進了房中,算是完了,只要款待送親喫喜酒。
這謝家民戶人家,沒甚人力,謝翁與謝三郎只好陪客在外邊,裏頭媽媽率了一二個養娘,親自廚房整酒。有個把當直的,搬東搬西,手忙腳亂,常是來不迭的。徐達相禮,到客人坐定了席,正要“請湯”、“請酒”是件贊唱,忽然不見了他。兩三次湯送到,只得主人自家請過吃了。將至終席,方見徐達慌慌張張在後面走出來,喝了兩句。比至酒散,謝翁見茶酒如此參前失後,心中不喜,要叫他來埋怨幾句,早又不見。當值的道:“方纔往前面去了。”謝翁道:“怎麼尋了這樣不曉事的?如此淘氣!”親家翁不等茶酒來贊禮,自起身謝了酒。
謝三郎走進新房,不見新娘子在內,疑他牀上睡了,揭帳一看,仍然是張空牀。前後照看,竟不見影。跑至廚房間人時,廚房中人多嚷道:“我們多隻在這裏收拾,新娘子花燭過了,自坐房中,怎麼倒來問我們?”三郎叫了當直的後來各處找尋,到後門一看,門又關得好好的。走出堂前說了,閤家驚惶。當直的道:
“這個茶酒、一向不是個好人,方纔喝禮時節看他沒心沒想,兩眼只看着新人,又兩次不見了他,而今竟不知那裏去了。莫不是他有甚麼奸計,藏過了新人麼?”鄭老兒道:“這個茶酒,元不是好人。小女前日開面也是他。因見他輕薄態度,正心裏怪恨,不想宅上茶酒也用着他。”鄭家隨來的僕人也說道:“他元是個遊嘴光棍,這蓖頭贊禮,多是近新來學了攛哄過日子的。畢竟他有緣故,去還不遠,我們追去。”謝家當直的道:“他要內裏拐出新人,必在後門出後巷裏去了。方纔後門關好,必是他復身轉來關了,使人不疑。所以又到堂前敷衍這一回,必定從前面轉至後巷去了,故此這會不見,是他無疑。”
此時是新婚人家,篦子火把多有在家裏,就每人點着一根。兩家僕人與同家主共是十來個,開了後門,多望後巷裏起來。元來謝家這條後門路,是一個直巷,也無彎曲,也無旁路。火把照起,明亮猶同白日,一望去多是看見的。遠遠見有兩三個人走,前頭差一段路,去了兩個,後邊有一個還在那裏。疾忙趕上,拿住火把一照,正是徐茶酒。問道:“你爲何在這裏?”徐達道:“我有些小事,等不得酒散,我要回去。”衆人道:“你要回去,直不得對本家說聲?況且好一會不見了你,還在這裏行走,豈是回去的?你好好說,拐將新娘子那裏去了?”徐達支吾道:“新娘子在你家裏,豈是我掌禮人包管的?”衆人打的打,推的推,喝道:“且拿這遊嘴光棍到家裏拷問他出來!”一羣人擁着徐達,到了家裏。兩家親翁一同新郎各各盤問,徐達只推不知。一齊道:“這樣頑皮賴骨,私下問他,如何肯說!綁他在柱上,待天明送到官去,難道當官也賴得?”遂把徐達做一團捆住,只等天明。此時第一個是謝三郎掃興了。
不能勾握雨攜雲,整備着鼠牙雀角。
喜筵前在喚新郎,洞房中依然獨覺。
衆人鬧鬧嚷嚷簇擁着徐達,也有嚇他的,也有勸他的,一夜何曾得睡?徐達只不肯說。
須臾,天已大明,謝家父子教衆人帶了徐達,寫了一紙狀詞,到縣堂上告準,面稟其故。知縣驚異道:“世間有此事?”遂喚徐達問道:“你拐的鄭蕊珠那裏去了?”徐達道:“小人是婚筵的茶酒,只管得行禮的事,怎曉得新人的去向?”謝公就把他不辭而去,在後巷趕着之事,說了一遍。知縣喝叫用刑起來,徐達雖然是遊花光棍,本是柔脆的人,熬不起刑。初時支吾兩句,看看當不得了,只得招道:“小人因爲開面時,見他美貌,就起了不良之心。曉得嫁與謝家,謀做了婚筵茶酒。預先約會了兩個同伴埋伏在後門了。趁他行禮已完,外邊只要上席,小人在裏面一看,只見新人獨坐在房中,小人哄他還要行禮。新人隨了小人走出,新人卻不認得路,被小人引他到了後門,就把新人推與門外二人。新人正待叫喊,卻被小人關好了後門,望前邊來了。仍舊從前邊抄至後巷,趕着二人。正要奔脫,看見後面火把明亮,知是有人趕來。那兩個人顧不得小人,竟自飛跑去了。小人有這個新人在旁,動止不得。恰好路旁有個枯井,一時慌了,只得抱住了他,攛了下去。卻被他們趕着,拿了送官。這新人現在井中。只此是實。”知縣道:“你在他家時,爲何不說?”徐達道:“還打點遮掩得過,取他出井來受用。而今熬刑不起,只得實說了。”知縣寫了口詞,就差一個公人押了徐達,與同謝、鄭兩家人,快到井邊來勘實回話。
一行人到了井邊。鄭老兒先去望一望,井底下黑洞洞,不見有甚聲響。疑心女兒此時畢竟死了,扯着徐達狠打了幾下,道:“你害我女兒死了,怕不償命!”衆人勸住道:“且撈了起來,不要廝亂,自有官法處他。”鄭老兒心裏又慌又恨,且把徐達咬住一塊肉,不肯放。徐達殺豬也似叫喊。這邊謝翁叫人停當了竹兜繩索,一面下井去救人。一個膽大些的家人,扎縛好了,掛將下去。井中無人,用手一模,果然一個人蹲倒在裏面。推一推看,已是不動的了。抱將來放在兜中,吊將上去。衆人一看,那裏是甚麼新娘子?卻是一個大鬍鬚的男子,鮮血模糊,頭多打開的了。衆人多吃了一驚。鄭老兒將徐達又是一巴拿,道:“這是怎麼說?”連徐達看見,也嚇得呆了。謝翁道:“這又是甚麼蹺蹊的事?”對了井中問下邊的人道:“裏頭還有人麼?”井裏應道:“並無甚麼了,接了我上去。“隨即放繩下去,接了那個家人上來。一齊問道:“井中還有甚麼?”家人道:“止有些石塊在內,是一個乾枯的井。方纔黑洞洞地摸起來的人,不知死活,可正是新娘子麼?”衆人道:“是一個死了的鬍子,那裏是新人?你看麼!”押差公人道:“不要鳥亂了,回覆官人去,還在這個入孃的身上尋究新人下落。”
鄭、謝兩老兒多道:“說得是。”就叫地方人看了屍首,一同公人去稟白縣官。知縣問徐達道:“你說把鄭蕊珠推在井中,而今井中卻是一個男屍,且說鄭蕊珠那裏去了?這屍是那裏來的?”徐達道:“小人只見後邊趕來,把新人推在井裏是實。而今卻是一個男屍,連小人也猜不出了。”知縣道:“你起初約會這兩個同伴,叫做甚麼名字?必是這二人的緣故了。”徐達道:“一個張寅,一個李卯。”知縣寫了名字住址,就差人去拿來。甕中捉鱉,立時拿到,每人一夾棍,只招得道:“徐達相約後門等待,後見他推出新人來,負了就走。徐達在後趕來,正要同去。望見後面火把齊明,喊聲大震,我們兩個膽怯了,把新人掉與徐達,只是拼命走脫了。已後的事,一些也不知。”又對着徐達道:“你當時將的新人,那裏去了?怎不送了出來,要我們替你喫苦?”徐達對口無言。知縣指着徐達道:“還只是你這奴才奸巧!”喝叫再夾起來,徐達只喊得是小人該死。說來說去,只說到推在井中,便再說不去了。
知縣便叫鄭、謝兩家父親與同媒的人等,又拘齊兩家左右鄰里,備細訪問。多隻是一般不知情,沒有甚麼別話,也沒有一個認得這屍首的。知縣出了一張榜文,召取屍親家屬認領埋葬,也不曾有一個說起的。鄭、謝兩家自備了賞錢,知縣又替他寫了榜文,訪取鄭蕊珠下落,也沒有一個人曉得影響的。知縣斷決不開,只把徐達收在監中,五日一比。謝三郎苦毒,時時催稟。縣官沒法,只得做他不着,也不知打了多多少少。徐達起初一時做差了事,到此不知些頭腦,教他也無奈何,只好巴過五口,喫這番痛棒。也沒個打聽的去處,也沒個結局的法兒,真正是沒頭的公事,表過不提。
再說鄭蕊珠那晚被徐達拐至後門,推與二人,便見把後門關了,方曉得是歹人的做作。欲待叫着本家人,自是新來的媳婦,不曾知道一個名姓,一時叫不出來。亦且門已關了,便口裏喊得兩句“不好了”,也沒人聽得。那些後生揹負着只是走,心裏正慌,只見後面趕來,兩個人撇在地下竟自去了。那個徐達一把抱來,丟在井裏。井裏無水,又不甚深,只跌得一下,毫無傷損。聽是上面衆人喧嚷,曉得是自己家人,又火把齊明,照得井裏也有光。鄭蕊珠負極叫喊救人,怎當得上邊人拿住徐達,你長我短,嚷得一個不耐煩。婦人聲音,終久嬌細,又在井裏,那個聽見?多簇擁着徐達,吆吆喝喝一路去了。鄭蕊珠聽得人聲漸遠,只叫得苦,大聲啼哭。看看天色明亮,蕊珠想道:“此時上邊未必無人走動。”高喊兩聲救人!又大哭兩聲,果然驚動了上邊兩人。只因這兩個人走將來,有分教:
黃塵行客,翻爲墜井之魂;綠鬢新人,竟作離鄉之婦。
說那兩個人,是河南開封府報縣客商。一個是趙申一個是錢已。合了本錢,同到蘇、鬆做買賣。得了重利,正要回去。偶然在此經過,聞得啼哭喊叫之聲卻在井中出來,兩個多走到井邊,望下一看。此時天光照下去,隱隱見是個女人。問道:“你是甚麼人在這裏頭?”下邊道:“我是此間人家新婦,被強盜劫來丟在此的。快快救我出來,到家自有重謝。”兩人聽得,自商量道:“從來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況是個女人,怎能勾出來?沒人救他,必定是死。我每撞着也是有緣。行囊中有長繩,我每墜下去救了他起來。”趙申道:“我溜撤些,等我下去。”錢已道:“我身子坌,果然下去不得,我只在上邊吊箸繩頭,用些空氣力罷。”也是趙申悔氣到了,見是女子,高興之甚。擅拳裸袖,把繩縛在腰間,雙手吊着繩。錢已一腳端着繩頭,雙手提着繩,一步步放將下去。到了下邊,見是沒水的,他就不慌不忙對鄭蕊珠道:“我救你則個。”鄭蕊珠道:“多謝大恩。”趙申就把身上繩頭解下來,將鄭蕊珠腰間如法縛了,道:“你不要怕,只把雙手吊着繩,上邊自提你上去,縛得牢,不掉下來的。快上去了,把繩來吊我。”鄭蕊珠巴不得出來,放着膽吊了繩。上邊錢巳見繩急了,曉得有人吊着。盡氣力一扯一扯的,吊出井來。錢巳擡頭一看,卻是一個豔妝的女子:
雖然鬢亂釵橫,卻是天姿國色。
猛地井裏現身,疑是龍宮拾得。
大凡人不可有私心,私心一起,就要幹出沒天理的勾當來。起初錢巳與趙申商量救人,本是好念頭。一下子救將起來,見是個美貌女子,就起了打偏手之心。思量道:“他若起來,必要與我爭,不能勾獨享。況且他囊中本錢盡多,而今生死之權,操在我手。我不放他起來,這女子與囊橐多是我的了。”歹念正起,聽得井底下大叫道:“怎不把繩下來?”錢巳發一個狠道:“結果了他罷!”在井旁掇起一塊大石頭來,照着井中叫聲“下去!”可憐趙申眼盼盼望着上邊放繩下來,豈知是塊石頭,不曾提防的,迴避不及,打着腦蓋骨,立時粉碎,嗚呼哀哉了。
鄭蕊珠在井中出來,見了天日,方抖擻衣服,略定得性。只見錢巳如此做作,驚得魂不附體,口裏只念阿彌陀佛。錢巳道:“你不要慌,此是我仇人,故此哄他下去,結果了他性命。”鄭蕊珠心裏道:“是你的仇人,豈知是我的恩人!”也不敢說出來,只求送在家裏去。錢巳道:“好自在話!我特特在井裏救你出來,是我的人了。我怎肯送還你家去?我是河南開封富家,你到我家裏,就做我家主婆,享用富貴了。快隨我走!”鄭蕊珠昏天黑地,不認得這條路是那裏,離家是近是遠,又沒個認得的人在旁邊,心中沒個主見。錢巳催促他走動道:“你若不隨我,仍舊攛你在井中,一石頭打死了,你見方纔那個人麼?”鄭蕊珠懼怕,思量無計,只得隨他去。正是:
才脫風狂子,又逢輕簿兒。
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
錢巳一路吩咐鄭蕊珠,教道他到家見了家人,只說蘇州討來的,有人來問趙申時,只回他還在蘇州就是了。不多幾日,到了開封杞縣,進了錢巳家裏。誰知錢巳家中還有一個妻子萬氏,小名叫做蟲兒。其人狠毒的甚。一見鄭蕊珠就放出手段來,無所不至擺佈他。將他頭上首飾,身上衣服,盡都奪下。只許他穿着布衣服,打水做飯。一應粗使生活,要他一身支當。一件不到,大棒打來。鄭蕊珠道:“我又不是嫁你家的,你家又不曾出銀子討我的。平白地強我來,怎如此毒打得我!”那個萬蟲兒那裏聽你分訴,也不問着來歷,只說是小老婆,就該一味喫醋蠻打罷了。萬蟲兒一向做人惡劣,是鄰里婦人沒一個不相罵斷的。有一個鄰媽看見他如此毒打鄭蕊珠,心中常抱不平。忽聽見鄭蕊珠口中如此說話,心裏道:
“又不嫁,又不討,莫不是拐來的?做這樣陰騭事,坑着人家兒女!”把這話留在心上。
一日,錢巳出到外邊去了,鄭蕊珠打水,走到鄰媽家借水桶。鄰媽留他坐着,問道:“看娘子是好人家出身,爲何宅上爹孃肯遠嫁到此,喫這般磨折?”鄭蕊珠哭道:“那裏是爹孃嫁我來的!”鄰媽道:“這等,怎得到此?”鄭蕊珠把身許謝家,初婚之夜被人拐出拋在井中之事,說了一遍。鄰媽道:“這等,是錢家在井中救出了你,你隨他的了。”鄭蕊珠道:“那裏是!其時還有一個人下井,親身救我起來的。這個人好苦,指望我出井之後,就將繩接他,誰知錢家那廝狠毒,就把一塊大石頭丟下去,打死了那人,拉了我就走。我彼時一來認不得家裏,二來怕他那殺人手段,三來他說道到家就做家主婆,豈知墮落在此受這樣磨難!”鄰媽道:“當初你家的與前村趙家一同出去爲商,今趙家不回來,前日來問你家時,說道還在蘇州,他家信了。依小姐子說起來,那下井救你喫打死的,必是趙家了。小娘子何不把此情當官告明瞭,少不得牒送你回去,可不免受此間之苦?鄭蕊珠道:“只怕我跟人來了,也要問罪。”鄰媽道:“你是婦人家,被人迫誘,有何可罪?我如今替你把此情先對趙家說了,趙家必定告狀,再與你寫一張首狀,當官遞去。你只要實說,包你一些罪也沒有,且得還鄉見父母了。”鄭蕊珠道:“若得如此,重見天日了。”
計較已定,鄰媽一面去與趙家說了。趙家赴縣理告,這邊鄭蕊珠也拿首狀到官。杞知縣問了鄭蕊珠一詞,即時差捕錢已到官。錢巳欲待支吾,卻被鄭蕊珠是長是短,一口證定。錢巳抵賴不去,恨恨的向鄭蕊珠道:“我救了你,你倒害我!”鄭蕊珠道:“那個救我的,你怎麼打殺了他?”錢巳無言。趙家又來求判填命。知縣道:“殺人情真,但皆系口詞,屍首未見,這裏成不得獄。這是嘉定縣地方做的事,鄭蕊珠又是嘉定縣人,屍首也在嘉定縣,我這裏只錄口詞成招,將一行人連文卷押報到嘉定縣,結案就是了。”當下先將錢已打了三十大板,收在牢中,鄭蕊殊召保,就是鄰媽替他遞了保狀。且喜與那個惡婦萬蟲兒不相見了。杞縣一面疊成文卷,會了長解,把一干人多解到蘇州嘉定縣來。
是日正逢五日比較之期,嘉定知縣帶出監犯徐達,恰好在那裏比較。開封府杞縣的差人投了文,當堂將那解批上姓名逐一點過,叫到鄭蕊珠,蕊珠答應。徐達擡頭一看,卻正是這個失去的鄭蕊珠,是開面時認得親切的。大叫道:“這正是我的冤家。我不知爲你打了多少,你卻在那裏來?莫不是鬼麼?”知縣看見,問徐達道:“你爲甚認得那婦人?”徐達道:“這個正是井裏失去的新人,不消比較小人了。”知縣也駭然道:“有這等事?”喚鄭蕊珠近前,一一細問,鄭蕊珠照前事細說了一遍。知縣又把來文逐一簡看,方曉得前日井中死屍,乃趙申被錢巳所殺。遂吊取趙申屍骨,令仵作人簡驗得頭骨碎裂,系是生前被石塊打傷身死。將錢巳問成死罪,抵趙申之命。徐達拐騙雖事不成,禍端所自,問三年滿徒。張寅、李卯各不應,仗罪。鄭蕊珠所遭不幸,免科,給還原夫謝三郎完配。趙申屍骨,家屬領埋,系隔省,埋訖,釋放寧家。知縣發落已畢,笑道:“若非那邊弄出,解這兩個人來,這件未完何時了結也!”嘉定一縣傳爲新聞。
可笑謝三郎好端端的新婦,直到這日,方得到手,已是個弄殘的了。又爲這事壞了兩條性命,其禍皆在男人開面上起的。所以內外之防,不可不嚴也。
男子何當整女容?致令惡少起頑兇。
今進試看含香蕊,已動當年函谷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