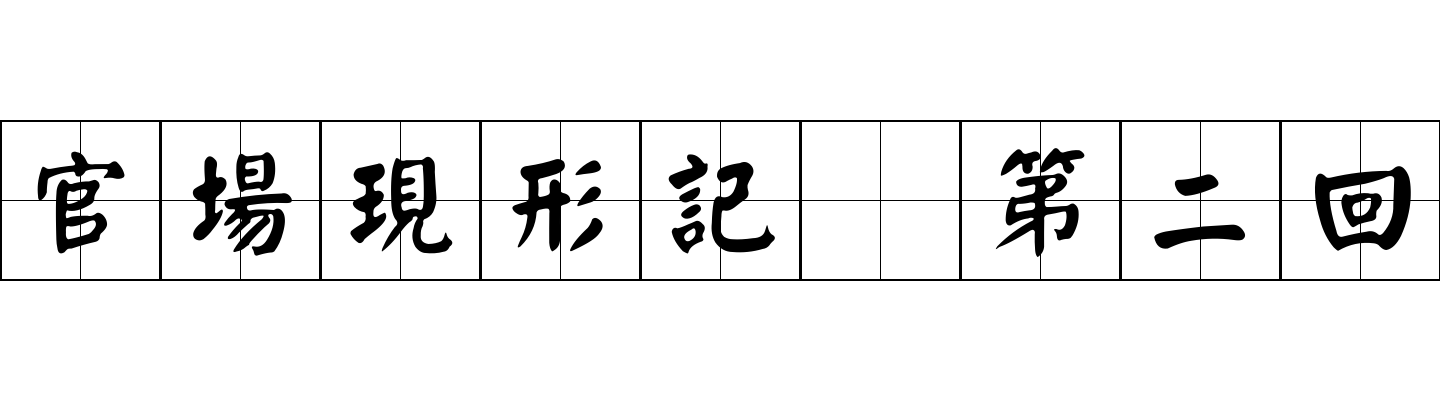官場現形記-第二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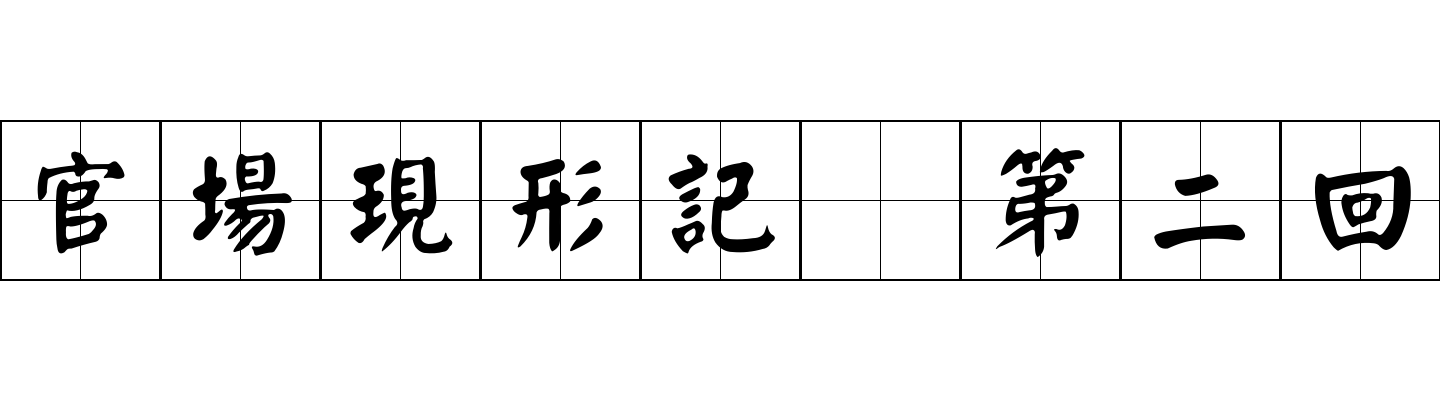
《官場現形記》是晚清文學家李伯元創作的長篇小說。小說最早在陳所發行的《世界繁華報》上連載,共五編60回,是中國近代第一部在報刊上連載並取得社會轟動效應的長篇章回小說。它由30多個相對獨立的官場故事聯綴起來,涉及清政府中上自皇帝、下至佐雜小吏等,開創了近代小說批判現實的風氣。魯迅將《官場現形記》與其他三部小說並稱之爲譴責小說,是清朝晚期文學代表作品之一。
錢典史同行說官趣 趙孝廉下第受奴欺
話說趙家中舉開賀,一連忙了幾天,便有本學老師叫門斗傳話下來,叫趙溫即日赴省,填寫親供。當下爺兒三代,買了酒肉,請門斗飽餐一頓,又給了幾百銅錢。門斗去後,趙溫便躊躇這親供如何填法,幸虧請教了老前輩王孝廉,一五一十的都教給他。趙溫不勝之喜。他爺爺又向親家方必開商量,要請王孝廉同到省城去走一遭,隨時可以請教。
方必開一來迫於太親翁之命,二來是他女兒大伯子中舉的大事,還有什麼不願意的?隨即滿口應允。趙老頭兒自是感激不盡。取過歷本一看,十月十五是個長行百事皆宜的黃道吉日,遂定在這天起身。因爲自己牲口不夠,又問方親家借了兩匹驢。幾天頭裏,便是幾門親戚前來送禮餞行,趙溫一概領受。
門斗:學裏的公役。
親供:指秀才中舉後到學臺官署填寫年齡、籍貫等手續。
閒話少敘。轉眼之間,已到十四。他爺爺,他爸爸,忙了一天,到得晚上,這一夜更不曾睡覺,替他弄這樣,弄那樣,忙了個六神不安。十五大早,趙溫起來,洗過臉,喫飽了肚皮。外面的牲口早已伺候好了。少停一刻,方必開同了王孝廉也踱過來。趙溫便向他爺爺、爸爸磕頭辭行。趙老頭兒又朝着王孝廉作了一個揖,託他照料孫子,王孝廉趕忙還禮不迭。等到行完了禮,一同送出大門,騎上牲口,順着大路,便向城中進發。
原來幾天頭裏,王鄉紳有信下來,說趙世兄如若上省填親供,可便道來城,在舍下盤桓幾日。所以趙溫同了王孝廉,走了半天,一直進城,投奔石牌樓而來。王孝廉是熟門熟路,管門的一向認得,立時請進,並不阻擋;趙溫卻是頭一遭。幸虧他素來細心,下驢之後,便留心觀看。只見:
門前粉白照牆一座,當中寫着“鴻禧”兩個大字,東西兩根旗杆。大門左右,水磨八字磚牆。兩扇黑漆大門,銅環擦得雪亮。門外掛着一塊“勸募秦晉賑捐分局”的招牌。兩面兩扇虎頭牌,寫着“局務重地”“閒人免進”八個大字。還有兩根半紅半黑的棍子,掛在牌上。大門之內,便是六扇藍漆屏門,上面懸着一塊紅底子金字的匾,寫着“進士第”三個字。兩邊貼着多少新科舉人的報條,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算來卻都是同年。兩邊牆上,還掛着幾頂紅黑帽子,兩條皮鞭子。
門上的人因爲他是王孝廉同來的人,也就讓他進去。轉過屏門,便是穿堂,上面也有三間大廳,卻無桌椅檯凳。兩面靠牆,橫七豎八擺着幾副銜牌;甚麼“丙子科舉人”、“庚辰科進士”、“賜進士出身”、“欽點主政”、“江西道監察御史”。趙溫心裏明白,這些都是王鄉紳自家的官銜。另外還擺着兩頂半新不舊的轎子。又轉過一重屏門,方是一個大院子,上面五間大廳。
半紅半黑的棍子:原爲衙役使用的水火棍,一半紅一半黑,掛在門外以示爲威嚴。
其時已是十月,正中掛着大紅洋布的板門簾。前回跟着王鄉紳下鄉,王孝廉給他兩個銅錢買燒餅喫的那個二爺,正在廊檐底下,提着一把溺壺走來;一見他來,連忙站住,虧他不忘前情,迎上來朝着王孝廉打了一個千,問他幾時來的,王孝廉回說“纔到”。
那二爺瞧瞧趙溫,也像認得,卻是不理他,一面說話,一面讓屋裏坐。趙溫也跟了進去。原來居中是三間統廳,兩頭兩個房間,上頭也懸着一塊匾,是“崇恥堂”三個字,下面落的是汪鳴鑾的款。趙溫念過“墨卷”,曉得這汪鳴鑾就是那做“能自疆齋文稿”的柳門先生,他本是一代文宗,不覺肅然起敬。當中懸着一副御筆,寫的“龍虎”兩字,卻是石刻朱拓的,兩邊一副對聯,是閻丹初閻老先生的款;天然几上一個古鼎、一個瓶、一面鏡子,居中一張方桌,兩旁八張椅子、四個茶几。上面樑上,還有幾個像神像龕子的東西,紅漆描金,甚是好看。趙溫不認得是什麼東西,悄悄請教老前輩。王孝廉對他說:“這是盛‘誥命軸子’的。”
墨卷:即考生墨寫的卷子。
誥命軸子:誥命,皇帝對五品以上的官員的封典;把誥命裱成的錦軸。
趙溫還不懂得什麼叫“誥命”,正想追問,裏頭王鄉紳拖着一雙鞋,手裏拿着一根旱菸袋,已經出來了。王孝廉連忙上前請了一個安,王鄉紳把他一扶。跟手趙溫已經爬在地下了,王鄉紳忙過來呵下腰去扶他。嘴裏雖說還禮,兩條腿卻沒有動,等到趙溫起來,他才還了一個楫。分賓坐下。趙溫坐的是東面一排第二張椅子,王孝廉坐的是西面第二張椅子,王鄉紳就在西面第三張上坐了相陪。王鄉紳先開口問趙溫的爺爺、爸爸的好。誰知他到了此時,不但他爺爺臨走囑咐他到城之後,見了王鄉紳替他問好的話,一句說不上來,連聽了王鄉紳的話,也不知如何回答。面孔漲得通紅,嘴裏吱吱了半天,纔回了個“好”字。王鄉紳見他如此,也就不同他再說別的了,只和王孝廉攀談幾句。
言談之間,王鄉紳提起:“有個舍親,姓錢號叫伯芳,是內人第二胞兄,在江南做過一任典史。那年新撫臺到任,不上三個月,不知怎樣就把他‘掛誤’了。卻不料他官雖然只做得一任,任上的錢倒着實弄得幾文回來。你們一進城,看見那一片新房子,就是他的住宅。做官不論大小,總要像他這樣,這官纔不算白做。現在他已經託了人,替他謀幹了一個‘開復’,一過年,也想到京裏走走,看有什麼路子,弄封把‘八行③’,還是出來做他的典史。”王孝廉道:“既然有路子,爲什麼不過班④,到底是正印。”王鄉紳道:“何嘗不是如此。我也勸過他幾次。無奈我們這位內兄,他卻另有一個見解。他說:州、縣雖是親民之官,究竟體制要尊貴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師爺同着二爺。多一個經手,就多一個扣頭,一層一層的剝削了去,到得本官就有限了;所以反不及他做典史的,倒可以事事躬親,實事求是。老侄,你想他這話,是一點不錯的呢。這人做官倒着實有點才幹,的的確確是位理財好手。”王孝廉道:“俗話說的好,‘千里爲官只爲財’。”王鄉紳道:“正是這話。現在我想明年趙世兄上京會試,倒可叫他跟着我們內兄一路前去,諸事託他招呼招呼,他卻是很在行的。”王孝廉道:“這是最好的,還有什麼說得。”當下王孝廉見王鄉紳眼睛不睬趙溫,瞧他坐在那裏沒得意思,就把這話告訴他一遍。趙溫除了說“好”之外,亦沒有別的話可以回答。王孝廉又替他問:“錢老伯府上,應該過去請安?”王鄉紳道:“今天他下鄉收租去了。我替你們說好,明年再見罷。”當下留他兩人晚飯,就在大廳西首一間,住了一夜。次日一早起身,往省城而去。於是,曉行夜宿,在路非止一日,已經到了省城,找着下處,安頓行李。
掛誤:官員因受牽累而去職。
開復:復職。
③八行:信,因信箋印爲八行,故稱。
④過班:過通關係而升官。
且說趙溫雖然中舉,世路上一切應酬,究未諳練。前年小考,以及今年考取遺才,學臺大人,雖說見過兩面,一直是一個坐着點名,一個提籃接卷,卻是沒有交談過,這番中了舉人,前來叩見,少不得總要攀談兩句。他平時見了稍些闊點的人,已經坐立不安,語無倫次,何況學臺大人,欽差體制,何等威嚴,未曾見面,已經嚇昏的了。虧得王孝廉遇事招呼,隨時指教,凡他所想不到的,都替他想到。頭一天晚上,教他怎樣磕頭,怎樣回話,賽如春秋二季,“明倫堂”上演禮③一般,好容易把他教會。又虧得趙溫質地聰明,自己又操演了一夜,頂到天明,居然把一應禮節,牢記在心。少停,王孝廉睡醒,趙溫忙即催他起來洗臉。自己換了袍套。手裏捏着手本。王孝廉又叫他封了四吊錢的錢票,送給學臺大人做“贄見”,另外帶了些錢做一應使費。到了轅門,找到巡捕老爺,趙溫朝他作了一個揖,拿手本交給他,求他到大人跟前代回,另外又送了這巡捕一吊錢的“門包”。巡捕嫌少,講來講去,又加了二百錢,方纔去回。等了一會子,巡捕出來說:“大人今天不見客。”問他親供填了沒有。趙溫聽說大人不見,如同一塊石頭落地,把心放下,趕忙到承差屋裏,將親供恭恭敬敬的填好,交代明白。一應使費,俱是王孝廉隔夜替他打點停當,趙溫到此不過化上幾個喜錢,沒有別的嚕嗦。當下事畢回寓,整頓行裝,兩人一直回鄉。王孝廉又教給他寫殿試策白摺子,預備來年會試不題。
遺才:科舉考試的名詞,指秀才未列於科考前三等者,可以再參加“錄科”和“遺錄”考試,凡錄取者可應分試。
“明倫堂”:學宮中的禮堂。
③演禮:指祭孔典禮。
贄見:見官員的禮物。
殿試策白摺子:殿試策,指考策題一種。白摺子,是當時考卷的一種。
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已過新年,趙溫一家門便忙着料理上京會試的事情。一日飯後,人報王鄉紳處有人下書。趙溫拆開看時,前半篇無非新年吉祥話頭,又說“舍親處,已經說定結伴同行,兩得裨益。舊僕賀根,相隨多年,人甚可靠,幹北道情形,亦頗熟悉,望即錄用”云云。趙溫知道,便是託王鄉紳所薦的那位管家了。只見賀根頭上戴一頂紅帽子,身穿一件藍羽緞棉袍,外加青緞馬褂,腳下還登着一雙粉底烏靴,見了趙溫,請了一個安,嘴裏說了聲“謝少爺賞飯喫”,又說“家主人請少爺的安”。趙溫因他如此打扮,鄉下從未見過,不覺心中呆了半天,不知拿什麼話回答他方好。幸虧賀根知竅,看見少爺說不出話,便求少爺帶着到上頭,見見老太爺請請安。趙溫只得同他進去,先見他爺爺。帶見過之後,他爺爺說:“這個人是你王公公薦來的,僧來看佛面,不可輕慢於他。”就留他在書房裏住。等到喫飯的時候,他爺爺一定又要從鍋裏另外盛出一碗飯、兩樣菜給賀根喫。一應大小事務,都不要他動手,後來還是王孝廉過來看見,就說:“現在這賀二爺既然是府上的管家,不必同他客氣,事情都要叫他經經手,等他弄熟之後,好跟世兄起身。”趙家聽得如此,才漸漸的差他做事。
到了十八這一天,便是擇定長行的吉日。一切送行辭行的繁文,不用細述。這日仍請王孝廉伴送到城。此番因與錢典史同行,所以一直徑奔他家,安頓了行李,同到王府請安。見面之後,留喫夜飯;檯面上只有他郎舅、叔侄三個人說的話,趙溫依然插不下嘴。飯罷,臨行之時,王鄉紳朝他拱拱手,說了聲“耳聽好音”。又朝他大舅子作了個揖,說:“恕我明天不來送行。到京住在那裏,早早給我知道。”又同王孝廉說了聲“我們再會罷”。方纔進去。三人一同回到錢家,住了一夜。次日,錢、趙二人,一同起身。王孝廉直等送過二人之後,方纔下鄉。
話分兩頭。單說錢典史一向是省儉慣的,曉得賀根是他妹丈所薦,他便不帶管家,一路呼喚賀根做事。過了兩天,不免忘其所以,漸漸的擺出舅老爺款來。背地裏不知被賀根咒罵了幾頓。幸虧趙溫初次爲人,毫無理會。況兼這錢典史是勢利場中歷練過來的,今見起溫是個新貴,前程未可限量;雖然有些事情欺他是鄉下人,暗裏賺他錢用,然而面子上總是做得十二分要好。又打聽得趙溫的座師吳翰林新近開了坊,升了右春坊、右贊善。京官的作用不比尋常,他一心便想巴結到這條路上。
右春坊、右贊善:官名,在明清,實際上是各翰林院編修等之升轉。
有天落了店,喫完了飯,叫賀根替他把鋪蓋打開,點上煙燈。其時趙溫正拿着一本新科闈墨,在外間燈下揣摩。錢典史便說:“堂屋裏風大,不如到煙鋪上躺着唸的好。”趙溫果然聽話,便捧了文章進來,在煙鋪空的一邊躺下,嘴裏還是念個不了,錢典史卻不便阻他,自己呼了幾口煙,又喫些水果、於點心之類,又拿起茶壺,就着壺嘴抽上兩口,把壺放下,順手拎過一支紫銅水菸袋,坐在牀沿上喫水煙,一個喫個不了。後來,錢典史被他噪聒的實在不耐煩,便藉着賀根來出氣。先說他偷懶不肯做事,後來又說他今天在路上買饅頭,四個錢一個,他硬要五個半錢一個,十二個饅頭,便賺了十八了錢,真真是混帳東西!頭裏賀根聽見舅老爺說他偷懶,已經滿肚皮不願意,後來又說他賺錢,又罵他混帳,他卻忍不住了,頓時嘴裏嘰哩咕嚕起來,甚麼“賺了錢買棺材,裝你老爺”,還說甚麼“混帳東西,是咱大舅子”。錢典史不聽則已,聽了之時,立刻無明火三丈高,放下水菸袋,提起根菸槍就趕過來打。賀根也不是好纏的,看見他要打,便把腦袋向錢典史懷內一頂,說:“你打你打!不打是咱大舅子!”錢典史見他如此,倒也動手不得,嘴裏吆喝:“好個撒野東西!回來寫信給你老爺,他薦的好人,連我都不放在眼裏!”賀根正待回話,幸虧得店家聽見裏頭鬧得不像樣,進來好勸歹勸,才把賀根拉開。這裏錢典史還在那裏氣得發抖。當他二人鬧時,趙溫想上來勸,但不知怎樣勸的好。後來見店家把賀根拉開,他又呆了半天,才說了一聲:“天也不早了,錢老伯也好睏覺了。”錢典史聽了這話,便正言厲顏的對他說道:“世兄!用到這樣管家,你做主人的總要有點主人的威勢纔好。像你這樣好說話,一個管家治不下,讓他動不動得罪客人,將來怎樣做官管黎民呢?”
趙溫明曉得這場沒趣是錢典史自己找的,無奈他秉性柔弱,一句也對答不上,只好索性讓他說,自己呆呆的聽着。錢典史又道:“想我從前在江南做官的時候,衙門雖小,上下也有三五個管家,還有書辦、差役,都是我一個人去治伏他們,一個不當心,就被他們賺了去,像你一個底下人都治不服,那還了得!”趙溫道:“爲着他是王公公薦的人,爺爺囑咐過,要同他客氣點,所以有些事情都讓他些。”錢典史哈哈冷笑道:“你將來要把他讓成功謀反叛逆,纔不讓他呢!這種東西,叫我一天至少罵他一百頓,還要同他客氣!真真奇談!”趙溫道:“既然老伯如此說,我明天管他就是了。”錢典史道:“我並不是要叫你管他,我是告訴你做官的法子。”
趙溫心下疑惑道:“這與做官有甚麼相干?”又不便駁他,只好拉長着耳朵聽他講。錢典史又說道:“‘齊家而後治國,治國而後平天下’,這兩句話你們讀書人是應該知道的。一個管家治不服,怎麼好算得齊家?不能齊家,就不能治國。試問皇上家要你這官做甚麼用呢?你也可以不必上京會試趕功名了。就如我,從前雖然做過一任典史,倒着實替皇家出點力,不要說衙門裏的人都受我節制,就是那些四鄉八鎮的地保、鄉約、圖正、董事,那一個敢欺我!”
趙溫雖然是鄉下人,也曉得典史比知縣小;聽他說得高興,有意打趣他,便問他道:“請教老伯:典史的官,比知縣大是小?”錢典史欺他是外行,便道:“一般大。他管得到的地方,我都管得到。論起來,這一縣之主還要算是我。有起事情來,我同他客氣,讓他坐在當中,所以都稱他‘正堂’。我坐的是下首主位,所以都稱我‘右堂’。其實是一樣的,不分甚麼大小。”趙溫道:“典史總要比知府小些。”
鄉約、圖正:鄉約,奉命在鄉中管事的人。圖正:農村中管本圖魚鱗冊的人;魚鱗冊即爲賦役而設的土地冊。
錢典史道:“他在府城裏,我在縣城裏,我管不着他,他亦管不着我。趙世兄,你不要看輕了這典史,比別的官都難做。等到做順了手,那時候給你狀元,你還不要呢。我這句話,並不是瞧不起狀元。常常聽見人說,翰林院裏的人都是清貴之品,將來放了外任,不是主考,就是學政,自然有那些手底下的官兒前來孝敬,自己用不着爲難。然而隔着一層,到底不大順手。何如我們做典史的,既不比做州、縣的,每逢出門,定要開鑼喝道,叫人家認得他是官。我們便衣就可上街,甚麼煙館裏,窯子裏,賭場上,各處都可去得。認得咱的,這一縣之內,都是咱的子民,誰敢不來奉承;不認得的,無事便罷,等到有起事情來,咱亦還他一個鐵面無私。不上兩年,還有誰不認得咱的?一年之內,我一個生日,我們賤內一個生日,這兩個生日是刻板要做的。下來老太爺生日,老太太生日,少爺做親,姑娘出嫁,一年上總有好幾回。”趙溫道:“我聽見王大哥講過,老伯還沒養世兄,怎麼倒做起親來呢?”錢典史道:“你原來未入仕途,也難怪你不知道。大凡像我們做典史的,全靠着做生日,辦喜事,弄兩個錢。一樁事情收一回分子,一年有上五六樁事情,就受五六回的分子。一回受上幾百吊,通扯起來就有好兩千。真真大處不可小算。不要說我連着兒子、閨女都沒有,就是先父、先母,我做官的時候,都已去世多年。不過託名頭說在原籍,不在任上,打人家個把式罷了。這些錢都是面子上的,受了也不罪過,還有那不在面子上的,只要事在人爲,卻是一言難盡。我這番出山,也不想別的處,只要早些選了出來,到了任,隨你甚麼苦缺,只要有本事,總可以生髮的。”說到這裏,忽聽窗外有人言道:“天不早了,客人也該睡了,明天好趕路。”原來是車伕半夜裏起來解手,正打窗下走過,聽見裏面高談闊論,所以才說這兩句。錢典史聽了笑道:“真的我說到高興頭上,把明兒趕路也就忘記了。”當下便催着趙溫睡下,自己又吃了幾袋水煙,方始安寢。次日依舊趕路不提。
卻說他主僕三人,一路曉行夜宿,在河南地面上,又遇着一場大雪,直至二月二十後,方纔到京。錢典史另有他那一幫人,天天出外應酬,忙個不了。這裏趙溫會着幾個同年,把一應投文複試的事,都託了一位同年替他帶辦,免得另外求人,倒也省事不少。不過大幫複試已過,直好等到二十八這一天,同着些後來的在殿廷上覆的試,居然取在三等裏面,奉旨準他一體會試。趙溫便高興的了不得,寫信稟告他爺爺、父親知道。這裏自從到京,頭一樁忙着便是拜老師。趙溫請教了同年,把貼子寫好,又封了二兩銀子的贄見,四吊錢的門包。他老師吳贊善,住在順治門外,趙、錢二位卻住在米市衚衕,相去還不算遠。這天趙溫起了一個大早,連累了錢典史也爬起來,忙和着替他弄這樣,弄那樣,穿袍子,打腰折,都是錢典史親自動手。又招呼賀根:“貼子拿好,車叫來沒有。”一霎時,簇新的轎車停在門前。趙溫出外上車,錢典史還送到門口。這裏掌鞭的就把鞭子一灑,那牲口就拉着走了。一霎時到了吳贊善門前,趙溫下車,舉眼觀看,只見大門之外,一雙裹腳條,四塊包腳布,高高貼起,上面寫着甚麼“詹事府示:不準喧譁,如違送究”等話頭。原來爲時尚早,吳家未曾開得大門。門上一副對聯,寫着“皇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十個大字。趙溫心下揣摩,這一定是老師自己寫的。就在門外徘徊了一回,方聽得呀的一聲,大門開處,走出一位老管家來。趙溫手捧名貼,含笑向前,道了來意。那老管家知道是主人去年考中的門生,連忙讓在門房裏坐,取了手本、贄見,往裏就跑。停了一會子,不見出來。趙溫心下好生疑惑。
原來這些當窮京官的人,好容易熬到三年放了一趟差,原指望多收幾個財主門生,好把舊欠還清,再拖新帳。那吳贊善自從二月初頭到於今,那些新舉人來京會試的,他已見過不少。見了張三,探聽李四,見了李四,探聽張三。如若是同府同縣,自然是一問便知;就是同府隔縣,問了不知便罷,只要有點音頭,他見了面,總要搜尋這些人的根底。此亦大概皆然,並不是吳贊善一人如此。
目下單說吳贊善,他早把趙溫的傢俬,問在肚裏,便知道他是朝邑縣一個大大的土財主,又是暴發戶,早已打算,他若來時,這一分贄見,至少亦有二三百兩。等到家人拿進手本,這時候他正是一夢初醒,臥牀未起;聽見“趙溫”兩字,便叫“請到書房裏坐,泡蓋碗茶”。老家人答應着。幸虧太太仔細,便問:“贄見拿進來沒有?”話說間,老家人已把手本連二兩頭銀子,一同交給丫環拿進來了。太太接到手裏,掂了一掂,嘴裏說了聲“只好有二兩”。吳贊善不聽則已,聽了之時,一骨碌忙從牀上跳下,大衣也不及穿,搶過來打開一看,果然只有二兩銀子。心內好像失落掉一件東西似的,面色登時改變起來。歇了一會子,忽然笑道:“不要是他們的門包也拿了進來?那姓趙的很有錢,斷不至於只送這一點點。”老家人道:“家人們另外是四吊錢。姓趙的說的明明白白,只有二兩銀子的贄見。”吳贊善聽到這裏,便氣得不可開交了,嘴裏一片聲嚷:“退還給他,我不等他這二兩銀子買米下鍋!回頭他……叫他不要來見我!”說着賭氣仍舊爬上牀去睡了。老家人無奈,只得出來回覆趙溫,替主人說“道乏”,今天不見客。說完了這句,就把手本向桌上一撩,卻把那二兩頭揣了去了。
趙溫撲了一個空,尤精打採,怏怏的出門坐車回去。錢典史接着,忙問:“回來的爲什麼這般快?可會見了沒有?”趙溫說:“今兒老師不見客。”錢典史說:“就該明兒再去。”到了明日,又起一個早跑了去。那老家人回也不替他回一聲,讓他一個人在門房裏坐了老大一會子,才向他說道:“我看你老還是回去罷,明日不用來了。”趙溫聽了這話,心上不懂。正待問他,老家人便說:“我就要跟着出門,你老也不用坐了。”趙溫無奈,只得依舊坐車回寓。錢典史知道他又不曾見着,曉得這裏頭有點不對,便把從前要靠趙溫走他老師這條門路的心,也就淡了下來。
過了幾天,恰是初八頭場。趙溫進去,狠命用心,做了三篇文章,又恭恭敬敬的寫到卷子上。聽見人說,三場試卷沒有一個添注塗改,將來調起墨卷來,要比別人沾光,他所以就在這上頭用工夫。誰知到了初十那一天,落太陽的時候,他還有一首詩不曾寫,忽然來了許多穿靴子,戴頂子的,嚷着“搶卷子”。還有一個人,手裏拿着一個大喇叭,照着他嗚嗚的吹,把他鬧急了,趕忙提起筆來寫。偏生要好不得好,一首八韻詩,當中脫落掉四句,只好添注了二十字,把他惱的了不得。匆匆忙忙,收拾了考籃,交了卷子出去。自己始終不放心,直到第二天“藍榜”貼了出來,沒有他的名字,方纔把心放下。接連二場、三場,他一連吃了九天辛苦。出場之後,足足困了兩日兩夜,方纔困醒。以後就是門生請主考,同年團拜。因爲副主考請假回家修墓,尚沒有來京,所以只請了吳贊善一個人。
藍榜:用藍筆寫的榜。鄉會試時寫作不合規定者,取消參加考試資格,並公佈出榜。
趙溫穿着衣帽,也混在裏頭。錢典史跟着溜了進去瞧熱鬧。只見吳贊善坐在上面看戲,趙溫坐的地方離他還遠着哩。一直等到散戲,沒有看見吳贊善理他。大家散了之後,錢典史不好明言,背地裏說:“有現成的老師尚不會巴結,叫我們這些趕門子,拜老師的怎樣呢?從此以後,就把趙溫不放在眼裏。轉念一想,讀書人是包不定的,還怕他聯捷上去,姑且再等他兩天。”
趙溫自從出場之後,自己就把頭篇抄了兩分出來:一分寄到家裏,一分帶在身上,隨時好請教人。人家都恭維他文章怎麼做的好,一定聯捷的,他自己也拿穩一定是高中的了。就有人來說,四月初九放榜,初八寫榜。從幾天頭裏,他就沒有好生睡覺。到了初八黑早,還沒有天亮,他就喚醒了賀根,叫他琉璃廠去等信。賀根說:“我的爺!這會子人家都在家裏睡覺,趕去做嗎?”趙溫一定要他去,賀根推頭天還早,一定要歇一會子再去。主僕兩個就拌起嘴來。還是錢典史聽不過,爬起來幫着趙溫吆喝了兩句,他才嘰哩咕嚕的一路罵了出去。這一天,趙溫就同熱鍋上的螞蟻一般,茶飯無心,坐立不定。到得下午,便有人來說,誰又中了,誰又中了。偏生賀根從天不亮出去,一直到晚不曾回來。趙溫急的跳腳,等到晚上,街上人說榜都填完了,只等着“填五魁”了。賀根知道沒了指望,方纔回寓。
填五魁:五魁,即五經魁,鄉試的前五名,在發榜時是最後從第五名倒填至第一名。
趙溫見了他眼睛裏出火,罵他“沒良心的東西”。賀根恨極,便說:“還有五魁沒有出來,等我再去打聽去。”一面說,一面跑了出來,找到一個賣燒餅的,同他商議,假充報子,說他少爺中了會魁,好訛他的錢分用。賣燒餅的依他話,便跑了來敲門報喜。賀根是早在大門前頭等好的了,一見報子來到,也跟了進來。趙溫自然歡喜,問要賞他多少銀子。賀根道:“這是頭報,應該多賞他幾兩。”趙溫道:“賞他二兩。”報喜人嚷着嫌少,一定要一個大元寶。後來還是賀根做好做歹,給了十兩一錠。那報喜人去了,賀根跟着出去,定要分他八兩,賣燒餅的只肯五兩。兩個人在那裏吵嘴,被錢典史出去出小恭,一齊聽了去,就說:“賀根,你少爺已經不中進士,不該再騙他錢用。”賀根道:“你老別多嘴。我騙他的錢,與你什麼相干,誰要說破這件事,咱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叫他等着罷!”錢典史聽了這話,把舌頭一伸,縮不進去,那裏還敢多嘴。只可憐趙溫白送了十兩銀子,空歡喜了一夜。到第二天,不見人來替他道喜,又買本題名錄來一看,自己沒有名字,才知昨夜受人之騙,氣的一天沒有喫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