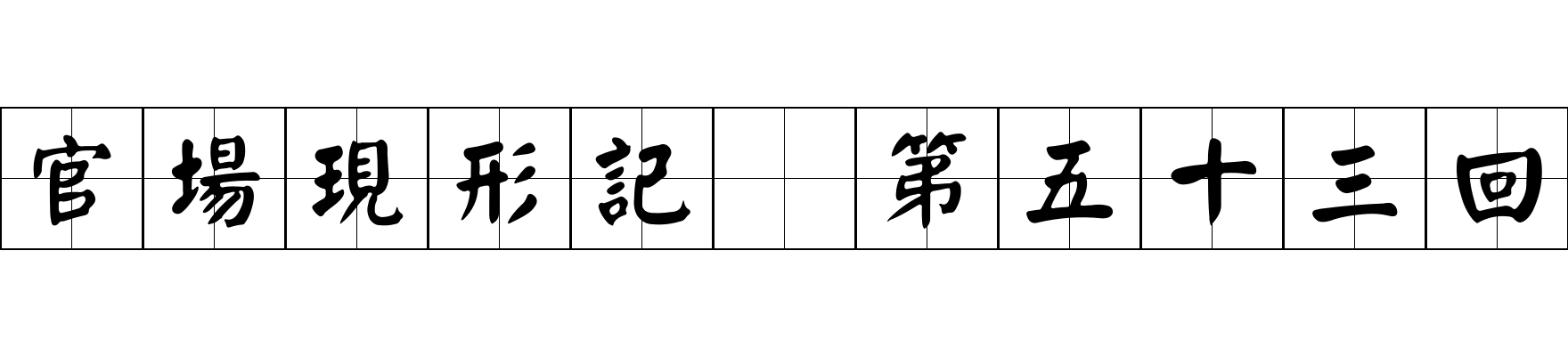官場現形記-第五十三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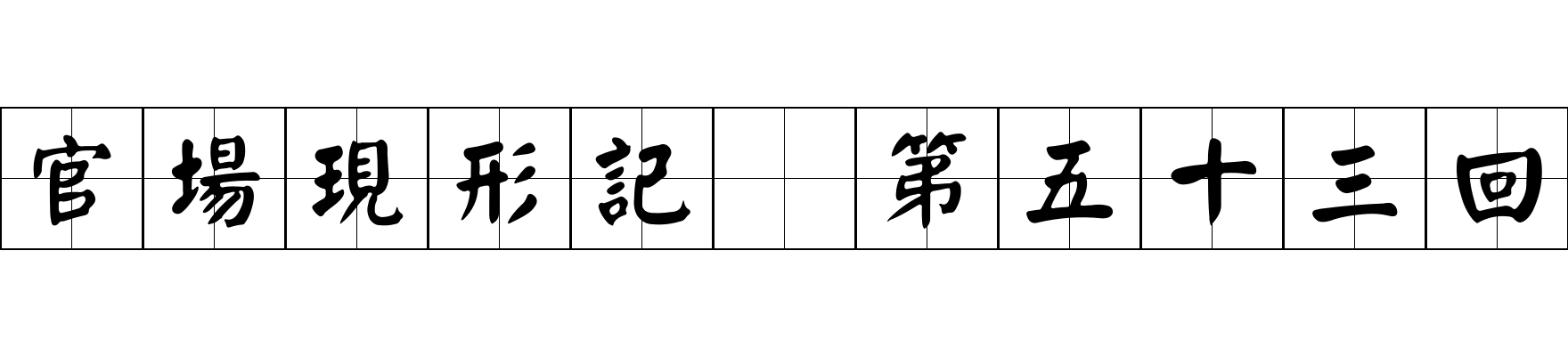
《官場現形記》是晚清文學家李伯元創作的長篇小說。小說最早在陳所發行的《世界繁華報》上連載,共五編60回,是中國近代第一部在報刊上連載並取得社會轟動效應的長篇章回小說。它由30多個相對獨立的官場故事聯綴起來,涉及清政府中上自皇帝、下至佐雜小吏等,開創了近代小說批判現實的風氣。魯迅將《官場現形記》與其他三部小說並稱之爲譴責小說,是清朝晚期文學代表作品之一。
洋務能員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別具肺腸
話說老和尚把徐大軍機送出大門登車之後,他便踱到西書房來。原來洋人已走,只剩得尹子崇郎舅兩個。他小舅爺正在那裏高談闊論,誇說自己的好主意,神不知,鬼不覺,就把安徽全省礦產輕輕賣掉。外國人簽字不過是寫個名字,如今這賣礦的合同,連老頭子亦都簽了名字在上頭,還怕他本省巡撫說什麼話嗎。就是洋人一面,當面瞧見老頭子簽字,自然更無話說了。
原來,這事當初是尹子崇弄得一無法想,求叫到他的小舅爺。小舅爺勾通了洋人的翻譯,方有這篇文章。所有朝中大老的小照,那翻譯都預先弄了出來給洋人看熟,所以剛纔一見面,他就認得是徐大軍機,並無絲毫疑意。合同例須兩分,都是預先寫好的。明欺徐大軍機不認得洋字,所以當面請他自己寫名字;因系兩分,所以叫他寫了又寫。至於和尚一面,前回書內早已交代,無庸多敘。當時他們幾個人同到了西書房,翻譯便叫洋人把那兩分合同取了出來,叫他自己亦簽了字,交代給尹子崇一分,約明付銀子日期,方纔握手告別。尹子崇見大事告成,少不得把弄來的昧心錢除酬謝和尚、通事二人外,一定又須分贈各位舅爺若干,好堵住他們的嘴。
閒文少敘。且說尹子崇自從做了這一番偷天換日的大事業,等到銀子到手,便把原有的股東一齊寫信去招呼,就是公司生意不好,喫本太重,再弄下去,實實有點撐不住了。不得已,方纔由敝嶽作主,將此礦產賣給洋人,共得價銀若干。”除墊還他經手若干外,所剩無幾,一齊打三折歸還人家的本錢,以作了事。股東當中有幾個素來仰仗徐大軍機的,自然聽了無甚說得,就是明曉得喫虧,亦所甘願。有兩個稍些強硬點的,聽了外頭的說話,自然也不肯干休。
常言說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尹子崇既做了這種事情,所有同鄉京官裏面,有些正派的,因爲事關大局,自然都派尹子崇的不是;有些小意見的,還說他一個人得了如許錢財,別人一點光沒有沾着,他要一個人安穩享用,有點氣他不過,便亦攛掇了大衆出來同他說話。專爲此事,同鄉當中特地開了一回會館,尹子崇卻嚇得沒敢到場。後來又聽聽外頭風聲不好,不是同鄉要遞公呈到都察院裏去告他,就是都老爺要參他。他一想不妙,京城裏有點站不住腳,便去催逼洋人,等把銀子收清,立刻卷卷行李,叩別丈人,一溜煙逃到上海。恰巧他到上海,京城的事也發作了,竟有四位御史一連四個摺子參他,奉旨交安徽巡撫查辦。信息傳到上海,有兩家報館裏統通把他的事情寫在報上,拿他罵了個狗血噴頭。他一想,上海也存不得身,而且出門已久,亦很動歸家之念,不得已,掩旗息鼓,徑回本籍。他自己一人忖道:“這番賺來的錢也儘夠我下半世過活的。既然人家同我不對,我亦樂得與世無爭,回家享用。”
於是在家一過過了兩個多月,居然無人找他。他自己又自寬自慰,說道:“我到底有‘泰山’之靠,他們就是要拿我怎樣,總不能不顧老丈的面子。況且合同上還有老丈的名字,就是有起事情來,自然先找到老丈,我還退後一層,真正可以無須慮得。”一個人正在那裏盤算,忽然管家傳進一張名片,說是縣裏來拜。他聽了這話,不禁心上一怔,說道:“我自從回家,一直還沒有拜過客,他是怎麼曉得的?”既然來的,只得請見。這裏執帖的管家還沒出去,門上又有人來說:“縣裏大老爺已經下轎,坐在廳上,專候老爺出去說話。”尹子崇聽了,分外生疑。想要不出去見他,他已經坐在那裏等候,不見是不成功的,轉念一想道:“橫豎我有靠山,他敢拿我怎樣!”於是硬硬頭皮,出來相見。誰料走到大廳,尚未同知縣相見,只見門外廊下以及天井裏站了無數若干的差人。尹子崇這一嚇非同小可!
此時知縣大老爺早已望見了他了,提着嗓子,叫子一聲“尹子翁,兄弟在這兒。”尹子崇只得過來同他見面。知縣是個老猾吏,笑嘻嘻的,一面作揖,一面竭力寒暄道:“兄弟直到今日才曉得子翁回府,一直沒有過來請安,抱歉之至!”尹子崇雖然也同他周旋,畢竟是賊人膽虛,終不免失魂落魄,張皇無措。作揖之後,理應讓客人炕上上首坐的,不料一個不留心,竟自己坐了上面。後來管家上來遞茶給他。叫他送茶,方纔覺得。臉上急得紅了一陣,只得換座過來,越發不得主意了。
知縣見此樣子,心上好笑,便亦不肯多耽時刻,說道:“兄弟現在奉到上頭一件公事,所以不得不親自過來一趟。”說罷,便在靴筒子當中抽出一角公文來。尹子崇接在手中一看,乃是南洋通商大臣的札子,心上又是一呆,及至抽出細瞧,不爲別件,正爲他賣礦一事,果然被四位都老爺聯名參了四本,奉旨交本省巡撫查辦。本省巡撫本不以爲然的,自然是不肯幫他說話。不料事爲兩江總督所知,以案關交涉,正是通商大臣的責任,頓時又電奏一本,說他擅賣礦產,膽大妄爲,請旨拿交刑部治罪。上頭准奏。電諭一到,兩江總督便飭藩司遴選委員前往提人。誰知這藩司正受過徐大軍機栽培的,便把他私人、候補知縣毛維新保舉了上去。這毛維新同尹府上也有點淵源,爲的派了他去,一路可以照料尹子崇的意思。等到到了那裏,知縣接着。毛維新因爲自己同尹子崇是熟人,所以讓知縣一個人去的。及至尹子崇拿制臺的公事看得一大半,已有將他拿辦的說話,早已嚇呆在那裏,兩隻手拿着札子放不下來。
後來知縣等得長久了,便說道:“派來的毛委員現在兄弟衙門裏。好在子翁同他是熟人,一路上倒有照應。轎子兄弟已經替子翁預備好了,就請同過去罷。”幾句話說完,直把個尹子崇急得滿身大汗,兩隻眼睛睜得如銅鈴一般,吱吱了半天,才掙得一句道:“這件事乃是家嶽籤的字,與兄弟並不相干。有什麼事,只要問家嶽就是了。”知縣道:“這裏頭的委曲,兄弟並不知道。兄弟不過是奉了上頭的公事,叫兄弟如此做,所以兄弟不能不來。如果子翁有什麼冤枉,到了南京,見了制臺儘可公辯的,再不然,還有京裏。況且裏頭有了令岳大人照應,諒來子翁雖然暫時受點委曲,不久就可明白的。現在時候已經不早了,毛某人明天一早就要動身的,我們一塊去罷。”
尹子崇氣的無話可說,只得支吾道:“兄弟須得到家母跟前稟告一聲,還有些家事須得料理料理。準今天晚上一準過去。”知縣道:“太太跟前,等兄弟派人進去替你說到了就是了。至於府上的事,好在上頭還有老太太,況且子翁不久就要回來的,也可以不必費心了。”尹子崇還要說別的,知縣已經仰着頭,眼睛望着天,不理他;又拖着嗓子叫:“來啊!”跟來的管家齊齊答應一聲“者”。知縣道:“轎伕可伺候好了?我同尹大人此刻就回衙門去。”底下又一齊答應一聲,回稱:“轎伕早已伺候好。”知縣立刻起身,讓尹子崇前頭,他自己在後頭,陪着他一塊兒上轎。這一走,他自己還好,早聽得屏門背後他一班家眷,本已得到他不好的消息,如今看他被縣裏拉了出去,賽如綁赴菜市口一般,早已哭成一片了。尹子崇聽着也是傷心,無奈知縣毫不容情,只得硬硬心腸跟了就走。
霎時到得縣裏,與毛委員相見。知縣仍舊讓他廳上坐,無非多派幾個家丁、勇役輪流拿他看守。至於茶飯一切相傳,自然與毛委員一樣。畢竟他是徐大軍機的女婿,地方官總有三分情面,加以毛委員受了江寧藩臺的囑託,公義私情,二者兼盡:所以這尹子崇甚是自在。當天在縣衙一宵,仍是自己家裏派了管家前來伺候。第二天跟着一同由水路起身。在路曉行夜宿,非止一日,已到南京。毛委員上去請示,奉飭交江寧府經廳看管,另行委員押解進京。擱下不表。
且說毛維新在南京候補,一直是在洋務局當差,本要算得洋務中出色能員。當他未曾奉差之前,他自己常常對人說道:“現在喫洋務飯的,有幾個能夠把一部各國通商條約肚皮裏記得滾瓜爛熟呢?但是我們於這種時候出來做官,少不得把本省的事情溫習溫習,省得辦起事情來一無依傍。”於是單檢了道光二十二年“江寧條約”抄了一遍,總共不過四五張書,就此埋頭用起功來,一念唸了好幾天,居然可以背誦得出。他就到處向人誇口,說他念熟這個,將來辦交涉是不怕的了。後來有位在行朋友拿他考了一考,曉得他能耐不過如此,便駁他道:“道光二十二年定的條約是老條約了,單念會了這個是不中用的。”他說:“我們在江寧做官,正應該曉得江寧的條約。至於什麼‘天津條約’、‘煙臺條約’,且等我兄弟將來改省到那裏,或是諮調過去,再去留心不遲。”那位在行朋友曉得他是誤會,雖然有心要想告訴他,無奈見他拘墟不化,說了亦未必明白,不如讓他糊塗一輩子罷。因此一笑而散。
卻不料這毛維新反於此大享其名,竟有兩位道臺在制臺前很替他吹噓說:“毛令不但熟悉洋務,連着各國通商條約都背得出的,實爲牧令中不可多得之員。”制臺道:“我辦交涉也辦得多了,洋務人員在我手裏提拔出來的也不計其數,辦起事情來,一齊都是現查書。不但他們做官的是如此,連着我們老夫子也是如此。所以我氣起來,總朝着他們說:‘我老頭子記性差了,是不中用的了。你們年輕人很應該拿這些要緊的書念兩部在肚子裏。’一天念熟一頁,一年便是三百六十頁,化上三年功夫,那裏還有他的對手。無奈我嘴雖說破,他們總是不肯聽。寧可空了打麻雀,逛窯子,等到有起事情來,仍然要現翻書起來,真正氣人!今天你二位所說的毛令既然肯在這上頭用功,很好,就叫他明天來見我。”
牧令:描地方長官。
原來,此時做江南制臺的,姓文,名明,雖是在旗,卻是個酷慕維新的。只是一樣:可惜少年少讀了幾句書,胸中一點學問沒有。這遭總算毛維新官運享通,第二天上去,制臺問了幾句話,虧他東扯西拉,盡然沒有露出馬腳,就此委了洋務局的差使。
這番派他到安徽去提人,稟辭的時候,他便回道:“現在安徽那邊,聽說風氣亦很開通了。卑職此番前去,經過的地方,一齊都要留心考察考察。”制臺聽了,甚以爲然。等到回來,把公事交代明白,上院稟見。制臺問他考察的如何,他說:“現在安徽官場上很曉得維新了。”制臺道:“何以見得?”他說:“聽說省城裏開了一爿大菜館,三大憲都在那裏請過客。”制臺道:“但是喫喫大菜,也算不得開通。”毛維新面孔一板,道:“回大人的話,卑職聽他們安徽官場上談起那邊中丞的意思說,凡百事情總是上行下效,將來總要做到叫這安徽全省的百姓,無論大家小戶,統通都爲吃了大菜纔好。”制臺道:“喫頓大菜,你曉得要幾個錢?還要什麼香檳酒、啤酒去配他。還有些酒的名字,我亦說不上來。貧民小戶可喫得起嗎。”
制臺的話說到這裏,齊巧有個初到省的知縣,同毛維新一塊進來的,只因初到省,不大懂得官場規矩,因見制臺只同毛維新說話,不理他,他坐在一旁難過,便插嘴道:“卑職這回出京,路過天津、上海,很喫過幾頓大菜,光喫菜不喫酒亦可以的。”他這話原是幫毛維新的。制臺聽了,心上老大不高興,眼睛往上一楞,說:“我問到你再說。上海洋務局、省裏洋務局,我請洋人喫飯也請過不止一次了,那回不是好幾千塊錢!你曉得!”回頭又對毛維新說道:“我兄弟雖亦是富貴出身,然而並非絝絝一流,所謂稼穡之艱難,尚還略知一二。”毛維新連忙恭維道:“這正是大帥關心民瘼,才能想得如此周到。”
文制臺道:“你所考察的,還有別的沒有?”毛維新又問道:“那邊安慶府知府饒守的兒子同着那裏撫標參將的兒子,一齊都剪了辮子到外洋去遊學。恰巧卑職趕到那裏,正是他們剃辮子的那一天。首府饒守曉得卑職是洋務人員,所以特地下帖邀了卑職去同觀盛典。這天官場紳士一共請了三百多位客。預先叫陰陽生挑選吉時。陰陽生開了一張單子,挑的是未時剃辮大吉。所請的客,一齊都是午前穿了吉服去的,朝主人道過喜,先開席坐席。等到席散,已經到了吉時了。只見饒守穿着蟒袍補褂,帶領着這位遊學的兒子,亦穿着靴帽袍套,望空設了祖先的牌位,點了香燭,他父子二人前後拜過,稟告祖先。然後叫家人拿着紅氈,領着少爺到客人面前,一一行禮,有的磕頭,有的作揖。等到一齊讓過了,這才由兩個家人在大廳正中擺一把圈身椅,讓饒守坐了,再領少爺過來,跪在他父親面前,聽他父親教訓。大帥不曉得:這饒守原本只有這一個兒子;因爲上頭提倡遊學,所以他自告奮勇,情願自備資斧,叫兒子出洋。所以這天撫憲同藩、臬兩司以及首道,一齊委了委員前來賀喜。只可憐他這個兒子今年只有十八歲,上年臘月才做親,至今未及半年,就送他到外洋去。莫說他小夫婦兩口子拆不開,就是饒守自己想想,已經望六之人了,膝下只有一個兒子,怎麼捨得他出洋呢。所以一見兒子跪下請訓,老頭子止不住兩淚交流,要想教訓兩句,也說不出話了。後來衆親友齊說:‘吉時已到,不可錯過,世兄改裝也是時候了。’只見兩個管家上來,把少爺的官衣脫去,除去大帽,只穿着一身便衣,又端過一張椅子,請少爺坐了。方傳剃頭的上來,拿盆熱水,撳住了頭,洗了半天,然後舉起刀子來剃。誰知這一剃,剃出笑話來了。只見剃頭的拿起刀來,磨了幾磨,譁擦擦兩聲響,從辮子後頭一刀下去,早已一大片雪白露出來了。幸虧卑職看得清切,立刻擺手,叫他不要再往下剃,趕上前去同他說:‘再照你這樣剃法,不成了個和尚頭嗎?外國人雖然是沒有辮子,何嘗是個和尚頭呢?’當時在場的衆親朋友以及他父親聽卑職這一說,都明白過來,一齊罵剃頭的,說他不在行,不會剃,剃頭的跪在地下,索索的抖,說:‘小的自小喫的這碗飯,實在沒有瞧見過剃辮子是應該怎麼樣剃的。小的總以爲既然不要辮子,自然連着頭髮一塊兒不要,所以纔敢下手的。現在既然錯了,求求大老爺的示,該怎麼樣,指教指教小的。’卑職此時早已走到饒守的兒子跟前,拿手撩起他的辮子來一看,幸虧剃去的是前劉海,還不打緊,便叫他們拿過一把剪刀來,由卑職親自動手,先把他辮子拆開,分作幾股,一股一股的替他剪了去,底下還替他留了約摸一寸多光景,再拿鑤花水前後刷光,居然也同外國人一樣了。大帥請想:他們內地真正可憐,連着出洋遊學想要去掉辮子這些小事情,都沒有一個在行的。幸虧卑職到那裏教給他們,以後只好用剪刀剪,不好用刀子剃,這才大家明白過來,說卑職的法子不錯。當天把個安慶省城都傳遍。聽說參將的兒子就是照着卑職的話用剪刀的。第二天卑職上院見了那邊中丞,很蒙獎勵,說:‘到底你們江南無辮子游學的人多,這都是制憲的提倡,我們這裏還差着遠哩。’”
文制臺聽了別人說他提倡學務,心上非凡高興。當時只因談的時候長久了,制臺要緊喫飯,便道:“過天空了我們再談罷。”說完,端茶送客,毛維新只得退出,趕着又上別的司、道衙門,一處處去賣弄他的本領。不在話下。
且說這位制臺本是個有脾氣的,無論見了什麼人,只要官比他小一級,是他管得到的,不論你是實缺藩臺,他見了面,一言不合,就拿頂子給人碰,也不管人家臉上過得去過不去。藩臺尚且如此,道、府是不消說了,州、縣以下更不用說了,至於在他手下當差的人甚多巡捕、戈什,喝了去,罵了來,輕則腳踢,重則馬捧,越發不必問的了。
且說有天爲了一件甚麼公事,藩臺開了一個手摺拿上來給他看。他接過手摺,順手往桌上一撩,說道:“我兄弟一個人管了這三省事情,那裏還有工夫看這些東西呢!你有什麼事情,直截痛快的說兩句罷。”藩臺無法,只得捺定性子,按照手摺上的情節約略擇要陳說一遍。無如頭緒太多,斷非幾句話所能了事,制臺聽到一半,又聽得不耐煩了,發狠說道:“你這人真正麻煩!兄弟雖然是三省之主,大小事情都照你這樣子要我兄弟管起來,我就是三頭六臂也來不及!”說着,掉過頭去同別位道臺說話,藩臺再要分辯兩句他也不聽了。藩臺下來,氣的要告病,幸虧被朋友們勸住的。
後來不多兩日,又有淮安府知府上省稟見。這位淮安府乃是翰林出身,放過一任學臺,後來又考取御史,補授御史,京察一等放出來的。到任還不到一年,齊巧地方上出了兩件交涉案件,特地上省見制臺請示。恐怕說的不能詳細,亦就寫了兩個節略,預備面遞。等到見了面,同制臺談過兩句,便將開的手摺恭恭敬敬遞了上去。制臺一看是手摺,上面寫的都是黃豆大的小字,便覺心上幾個不高興,又明欺他的官不過是個四品職分,比起藩臺差遠了,索性把手摺往地下一摔,說道:“你們曉得我年紀大,眼睛花,故意寫了這小字來蒙我!”那淮安府知府受了他這個癟子,一聲也不響。等他把話說完,不慌不忙,從從容容的從地下把那個手摺拾了起來。一頭拾,一頭嘴裏說:“卑府自從殿試,朝考以及考差、考御史,一直是恪遵功令,寫的小字,皇上取的亦就是這個小字。如今做了外官,倒不曉得大帥是同皇上相反,一個個是要看大字的,這個只好等卑府慢慢學起來。但是今時這兩件事情都是刻不可緩的,所以卑府才趕到省裏來面回大帥,若等卑府把大字學好了,那可來不及了。”制臺一聽這話,便問:“是兩件什麼公事!你先說個大概。”淮安府回道:“一件爲了地方上的壞人賣了塊地基給洋人,開什麼玻璃公司。一樁是一個包討債的洋人到鄉下去恐嚇百姓,現在鬧出人命來了。”
制臺一聽,大驚失色道:“這兩樁都是個關係洋人的,你爲什麼不早說呢?快把節略拿來我看!”淮安府只得又把手摺呈上。制臺把老花眼鏡帶上,看了一遍。淮安府又說道:“卑職因爲其中頭緒繁多,恐怕說不清楚,所以寫好了節略來的。況且洋人在內地開設行棧,有背約章;就是包討帳,亦是不應該的,況且還有人命在裏頭。所以卑府特地上來請大帥的示,總得禁阻他來纔好。”
制臺不等他說完,便把手摺一放,說:“老哥,你還不曉得外國人的事情是不好弄的麼?地方上百姓不拿地賣給他,請問他的公司到那裏去開呢?就是包討帳,他要的錢,並非要的是命。他自己尋死,與洋人何干呢?你老兄做知府,既然曉得地方有些壞人,就該預先禁止他們,拿地不準賣給外國人才是。至於那個欠帳的,他那張借紙怎麼會到外國人手裏?其中必定有個緣故。外國人頂講情理,決不會憑空詐人的。而且欠錢還債本是分內之事,難道不是外國人來討,他就賴着不還不成?既然如此,也不是什麼好百姓了。現在凡百事情,總是我們自己的官同百姓都不好,所以纔會被人家欺負,等到事情鬧糟了,然後往我身上一推,你們算沒有事了。好主意!”
原來這制臺的意思是:“洋人開公司,等他來開;洋人來討帳,隨他來討。總之:在我手裏,決計不肯爲了這些小事同他失和的。你們既做我的屬員,說不得都要就我範圍,斷斷乎不準多事。”所以他看了淮安府的手摺,一直只怪地方官同百姓不好,決不肯批評洋人一個字的。淮安府見他如此,就是再要分辨兩句,也氣得開不出口了。制臺把手摺看完,仍舊摔還給他。淮安府拾了,稟辭出去,一肚皮沒好氣。
正走出來,忽見巡捕拿了一張大字的片子,遠望上去,還疑心是位新科的翰林。只聽那巡捕嘴裏嘰哩咕嚕的說道:“我的爺!早不來,晚不來,偏偏這時候他老人家喫着飯他來了。到底上去回的好,還是不上去回的好?”旁邊一個號房道:“淮安府才見了下來,只怕還在簽押房裏換衣服,沒有進去也論不定。你要回,趕緊上去還來得及。別的客你好叫他在外頭等等,這個客是怠慢不得的!”那巡捕聽了,拿了片子,飛跑的進去了。這時淮安府自回公館不題。
且說那巡捕趕到簽押房,跟班的說:“大人沒有換衣服就往上房去了。”巡捕連連跺腳道:“糟了!糟了!”立刻拿了片子又趕到上房。才走到廊下,只見打雜的正端了飯菜上來。屋裏正是文制臺一迭連聲罵人,問爲什麼不開飯。巡捕一聽這個聲口,只得在廊檐底下站住。心上想回,因爲文制臺一到任,就有過吩咐的,凡是喫飯的時候,無論什麼客人來拜,或是下屬稟見,統通不準巡捕上來回,總要等到喫過飯,擦過臉再說:無奈這位客人既非過路官員,亦非本省屬員,平時制臺見了他還要讓他三分,如今叫他在外面老等起來,決計不是道理。但是違了制臺的號令,倘若老頭子一翻臉,又不是玩的,因此拿了名帖,只在廊下盤旋,要進又不敢進,要退又不敢退。
正在爲難的時候,文制臺早已瞧見了,忙問一聲:“什麼事?”巡捕見問,立刻趨前一步,說了聲“回大帥的話,有客來拜。”話言未了,只見拍的一聲響,那巡捕臉上早被大帥打了一個耳刮子。接着聽制臺罵道:“混帳王八蛋!我當初怎麼吩咐的!凡是我喫着飯,無論什麼客來,不準上來回。你沒有耳朵,沒有聽見!”說着,舉起腿來又是一腳。
那巡捕捱了這頓打罵,索性潑出膽子來,說道:“因爲這個客是要緊的,與別的客不同。”制臺道:“他要緊,我不要緊!你說他與別的客不同,隨你是誰,總不能蓋過我!”巡捕道:“回大帥:來的不是別人,是洋人。”那制臺一聽“洋人”二字,不知爲何,頓時氣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裏半天。後首想了一想,驀地起來,拍撻一聲響,舉起手來又打了巡捕一個耳刮子;接着罵道:“混帳王八蛋!我當是誰!原來是洋人!洋人來了,爲什麼不早回,叫他在外頭等了這半天?”巡捕道:“原本趕着上來回的,因見大帥喫飯,所以在廊下等了一回。”制臺聽了,舉起腿來又是一腳,說道:“別的客不準回,洋人來,是有外國公事的,怎麼好叫他在外頭老等?糊塗混帳!還不快請進來!”
那巡捕得了這句話,立刻三步並做二步,急忙跑了出來。走到外頭,拿帽子探了下來,往桌子上一摔,道:“回又不好,不回又不好!不說人頭,誰亦沒有他大,只要聽見‘洋人’兩個字,一樣嚇的六神無主了!但是我們何苦來呢?掉過去,一個巴掌!翻過來,又是一個巴掌!東邊一條腿,西邊一條腿!老老實實不幹了!”正說着,忽然裏頭又有人趕出來一迭連聲叫喚,說:“怎麼還不請進來!……”那巡捕至此方纔回醒過來,不由的仍舊拿大帽子合在頭上,拿了片子,把洋人引進大廳。此時制臺早已穿好衣帽,站在滴水檐前預備迎接了
原來來拜的洋人非是別人,乃是那一國的領事。你道這領事來拜制臺爲的什麼事?原來制臺新近正法了一名親兵小隊。制臺殺名兵丁,本不算得大不了的事情,況且那親兵亦必有可殺之道,所以制臺纔拿他如此的嚴辦。誰知這一殺,殺的地方不對:既不是在校場上殺的,亦不是在轅門外殺的,偏偏走到這位領事公館旁邊就拿他宰了。所以領事大不答應,前來問罪。
當下見了面,領事氣憤憤的把前言述了一遍,問制臺爲什麼在他公館旁邊殺人,是個什麼緣故。幸虧制臺年紀雖老,閱歷卻很深,頗有隨機應變的本領。當下想了一想,說道:“貴領事不是來問我兄弟殺的那個親兵?他本不是個好人,他原是‘拳匪’一黨。那年北京‘拳匪’鬧亂子,同貴國及各國爲難,他都有分的。兄弟如今拿他查實在了,所以纔拿他正法的。”領事道:“他既然通‘拳匪’,拿他正法亦不冤枉。但是何必一定要殺在我的公館旁邊呢?”制臺想了一想,道:“有個原故,不如此,不足以震服人心。貴領事不曉得這‘拳匪’乃是扶清滅洋的,將來鬧出點子事情來,一定先同各國人及貴國人爲難,就是於貴領事亦有所不利。所以兄弟特地想出一條計來,拿這人殺在貴衙署旁邊,好教他們同黨瞧着或者有些怕懼。俗語說得好,叫做‘殺雞駭猴’,拿雞子宰了,那猴兒自然害怕。兄弟雖然只殺得一名親兵,然而所有的‘拳匪’見了這個榜樣,一定解散,將來自不敢再與貴領及貴國人爲難了。”領事聽他如此一番說話,不由得哈哈大笑,獎他有經濟,辦得好,隨又閒談了幾句,告辭而去。
制臺送客回來,連要了幾把手巾,把臉上、身上擦了好幾把,說道:“我可被他駭得我一身大汗了!”坐定之後,又把巡捕、號房統通叫上來,吩咐道:“我喫着飯,不准你們來打岔,原說的是中國人。至於外國人,無論什麼時候,就是半夜裏我睡了覺,亦得喊醒了我,我決計不怪你們的。你們沒瞧見剛纔領事進來的神氣,賽如馬上就要同我翻臉的,若不是我這老手三言兩語拿他降伏住,還不曉得鬧點什麼事情出來哩。還擱得住你們再替我得罪人嗎!以後凡是洋人來拜,隨到隨請!記着!”巡捕、號房統通應了一聲“是”。
制臺正要進去,只見淮安府又拿着手本來稟見,說有要緊公事面回,並有剛剛接到淮安來的電報,須得當面呈看。制臺想了想,肚皮裏說道:“一定仍舊是那兩件事。但不知這個電報來,又出了點什麼岔子?”本來是懶怠見他的,不過因內中牽涉了洋了,實在委決不下,只得吩咐說“請”。
霎時淮安府進來,制臺氣吁吁的問道:“你老哥又來見我做什麼?你說有什麼電報,一定是那班不肖地方官又鬧了點什麼亂子,可是不是?”淮安府道:“回大帥的話:這個電報卻是個喜信?”制臺一聽“喜信”二字,立刻氣色舒展許多,忙問道:“什麼喜信?”淮安府道:“卑府剛纔蒙大人教訓,卑府下去回到寓處,原想照着大人的吩咐,馬上打個電報給清河縣黃令,誰知他倒先有一個電報給卑府,說玻璃公司一事,外國人雖有此議,但是一時股分不齊,不會成功。現在那洋人接到外洋的電報,想先回本國一走,等到回來再議。”制臺道:“很好!他這一去,至少一年半載。我們現在的事情,過一天是一天,但願他一直耽誤下去,不要在我手裏他出難題目給我做,我就感激他了。那一樁呢?”
淮安府道:“那一樁原是洋人的不是,不合到內地來包討帳。”制合一聽他說:“洋人不是”,口雖不言,心下卻老大不以爲然,說:“你有多大能耐,就敢排揎起洋人來!”於是又聽他往下講道:“地方上百姓動了公憤,一哄而起,究竟洋人勢孤,……”制臺聽到這裏,急的把桌子一拍道:“糟了!一定是把外國人打死了!中國人死了一百個也不要緊;如今打死了外國人,這個處分誰耽得起!前年爲了‘拳匪’殺了多少官,你們還不害怕嗎?”
淮安府道:“回大帥的話;卑府的話還未說完。”制臺道:“你快說!”淮安府道:“百姓雖然起了一個哄,並沒有動手,那洋人自己就軟下來了。”
制臺皺着眉頭,又把頭搖了兩搖說道:“你們欺負他單身人,他怕喫眼前虧,暫時服軟,回去告訴了領事,或者進京告訴了公使,將來仍舊要找咱們倒蛋的。不妥!不妥!”淮安府道:“實實在在是他自己曉得自己的錯處,所以才肯服軟的。”制臺道:“何以見得?”淮安府道:“因爲本地有兩個出過洋的學生,是他倆聽了不服,鬨動了許多人,同洋人講理,洋人說他不過,所以才服軟的。”
制臺又搖頭道:“更不妥!這些出洋回來的學生真不安分!於他毫不相干,就出來多事。地方官是昏蛋!難道就隨他們嗎?”淮安府道:“他倆不過找着洋人講理,並沒有滋事。雖然鬨動了許多人跟着去看,並非他二人招來的。”制臺道:“你老哥真不愧爲民之父母!你總幫好了百姓,把自己百姓竟看得沒有一個不好的,都是他們洋人不好。我生平最恨的就是這班刁民!動不動聚衆滋事,挾制官長!如今同洋人也是這樣。若不趁早整頓整頓,將來有得纏不清楚哩!你且說那洋人服軟之後怎麼樣?”淮安府道:“洋人被那兩個學生一頓批駁,說他不該包討帳,於條約大有違背。如今又逼死了人命,我們一定要到貴國領事那裏去告的。”
制臺聽了,點了點頭道:“駁雖駁得有理,難道洋人怕他們告嗎?就是告了,外國領事豈有不幫自己人的道理。”淮安府道:“誰知就此三言兩語,那洋人竟其頓口無言,反倒託他通事同那苦主講說,欠的帳也不要了,還肯拿出幾百銀子來撫卹死者的家屬,叫他們不要告罷。”制臺道:“咦!這也奇了!我只曉得中國人出錢給外國人是出慣的,那裏見過外國人出錢給中國人。這話恐拍不確罷?”淮安府道:“卑府不但接着電報是如此說,並有詳信亦是剛纔到的。”制臺道:“奇怪!奇怪!他們肯服軟認錯,已經是難得了;如今還肯撫卹銀子,尤其難得。真正意想不到之事!我看很應該就此同他了結。你馬上打個電報回去,叫他們趕緊收篷,千萬不可再同他爭論別的。所謂‘得風便轉’。他們既肯陪話,又肯化錢,已是莫大的面子。我辦交涉也辦老了,從沒有辦到這個樣子。如今雖然被他們爭回這個臉來,然而我心上倒反害起怕來。我總恐怕地方上的百姓不知進退,再有什麼話說,弄惱了那洋人,那可萬萬使不得!俗語說得好,叫做‘得意不可再往’。這個事可得責成你老哥身上。你老哥省裏也不必耽擱了,趕緊連夜回去,第一彈壓住百姓,還有那什麼出洋回來的學生,千萬不可再生事端。二則洋人走的時候,仍是好好的護送他出境。他一時爲理所屈,不能拿我們怎樣,終究是記恨在心的。拿他周旋好了,或者可以解釋解釋。我說的乃是金玉之言,外交祕訣。老哥,你千萬不要當做耳旁風!你可曉得你們在那裏得意,我正在這裏提心吊膽呢!”淮安府只得連連答應了幾聲“是”。然後端茶送客,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