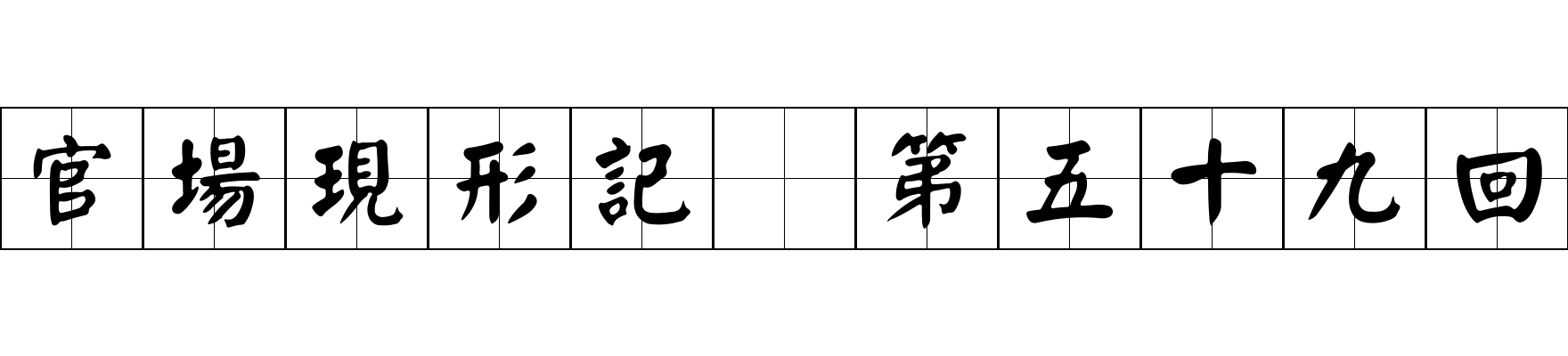官場現形記-第五十九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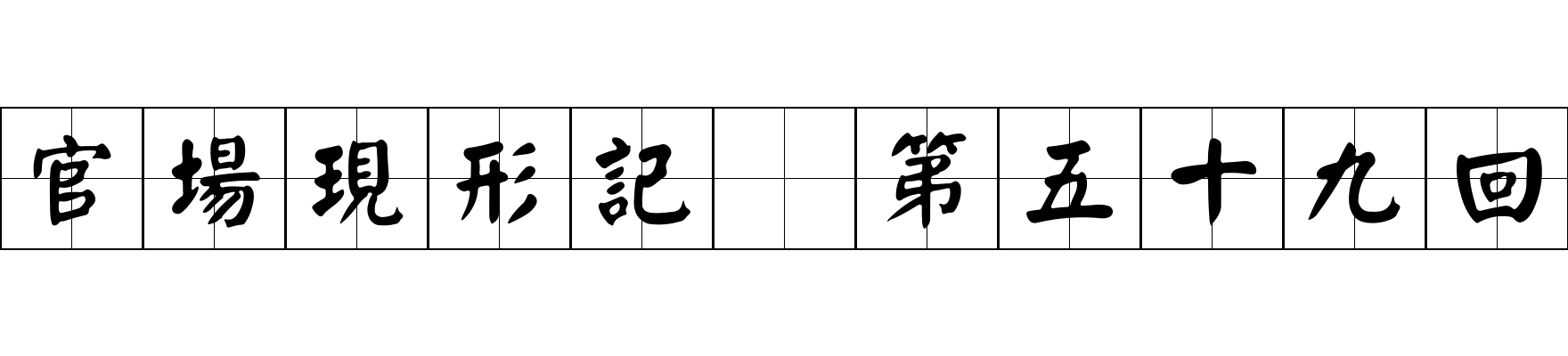
《官場現形記》是晚清文學家李伯元創作的長篇小說。小說最早在陳所發行的《世界繁華報》上連載,共五編60回,是中國近代第一部在報刊上連載並取得社會轟動效應的長篇章回小說。它由30多個相對獨立的官場故事聯綴起來,涉及清政府中上自皇帝、下至佐雜小吏等,開創了近代小說批判現實的風氣。魯迅將《官場現形記》與其他三部小說並稱之爲譴責小說,是清朝晚期文學代表作品之一。
附來裙帶能諂能驕 掌到銀錢作威作福
話說甄守球甄閣學在沈中堂宅內議定抵制之法:凡是新賞翰林的幾個學生來拜,一概不見,不要他們認前輩、老前輩。商議既定,果然大衆齊心,直弄得他們那幾個人,到一處碰一處,沒有一處見到。後來這幾個人曉得在京裏有點不合時宜,也就各自走了道路,出京另外謀幹去了。京裏的這班人聽得他們已走,彼此見面,一齊誇說:“甄老前輩出的好計策!”甄閣學亦甚是得意。
一天甄閣學在自己宅子裏備了三席酒,請衆位同年、同門喫酒賞菊花。沈中堂得了信,說是:“飲酒賞菊是頂雅緻的事情,怎麼守球不請我老頭子?”就有人把話傳給了甄閣學,連忙親自過來陪話,說道:“不是不請老師,實在因爲房子小,客多,怕褻瀆了老師,所以不敢來請。”沈中堂道:“我很歡喜。到了那天我要來。你亦不必多化錢,我亦吃不了什麼,不過大家湊湊罷了。”早已特特爲爲又添了一桌菜,揀老師愛喫的點了幾樣。這天約明白的兩點鐘會齊。不到一點鐘,老頭子頂高興,早已跑了來了。一問所請的客都是自己的門生,尤其高興。等到客齊,老頭子先創議,要人家做菊花詩。老頭子說:“什麼五古、七古,七律、七絕,我都有點忘記了。只有五律,只要拿試帖減四韻,我雖然多年不做,工夫荒了,還勉強湊得成功。”衆人見老頭子高興,少不得一齊獻醜。當時各自搜索枯腸。約摸一個鐘頭,還是沈中堂頭一個做好。衆人搶着看時,果然是一首五律。然後衆人絡續告成,數了數一共二十七首。有三位說要回去補做了送來。匯齊之後,甄閣學一齊請沈中堂過目。其中只有兩個做七絕的,一個做七律的,九個做五律的,十五個做五絕。你道爲何?只因五絕比五律更好做,連中間的對仗都可以減去,所以大家舍難就易,走了這一路。當時沈中堂看了甚喜,說:“明天請守球老弟畫一張格子,分送諸位。另外各自再謄一張,中縫腳下,各人寫各人的名字;籤條上就寫‘翰苑分書菊花詩’。送到琉璃廠,等他們刻了板印出來賣,凡是寫大卷子的人,誰不要買一部。”衆人一聽,不勝佩服。
酒席喫到一半,甄閣學忽然起身向內,停了一回,拿了兩張字出來,送到沈中堂跟前,說是:“門生的兩個兒子做的,不曉得將來還有點出息沒有?”沈中堂道:“好啊!拿來我看。”原來都是和的菊花詩。前面寫着“恭求太老夫子中堂訓正”,下面注着“小門生甄學忠、甄學孝謹呈”字樣。沈中堂未看詩先看名字,說道:“好名字!一個人能夠記得‘忠孝’兩個字,還有什麼說的呢。”於是又看詩,連贊:“好口氣!……兩位世兄將來一定都是要發達的!都是我的小門生,將來亦‘於湯有光’的事。我很想見見他倆。”
甄閣學巴不得這一聲,即刻進去,招呼兒子扎扮了出來。沈中堂一看,大的約摸有四十外了,戴的是藍頂花翎,小的亦有二十多歲,還是金頂子,一齊都穿着袍套。見了太老師爬下磕頭,太老師止回了半揖,磕頭起來又讓坐。老頭子因見甄學忠是四品服色,曉得他一定有了官了,便問:“在那一部當差?”甄閣學搶着回道:“本來有個小京官在身上,如今改了直隸州出去。”沈中堂道:“怎麼不下場?”甄閣學道:“已經下過十場,年紀也不小了,正途不及,只好叫他到外頭去歷練歷練。”沈中堂道:“可惜可惜!有如此才華,不等着中舉人、中進士,飛黃騰達上去,卻捐了個官到外頭去混,真正可惜!”一面說,一面又拿他倆的詩,顛來倒去,看了兩三遍,拍案道:“‘言爲心聲’,這句話是一點不差的。大世兄的詩好雖好,然而還總帶着牢騷,這便是屢試不第的樣子。幸虧還豪放,將來外任還可望得意,至二世兄富麗堂皇,不用說,將來一定是玉堂人物了!”接着又問甄學忠:“幾時出去做官?分發那一省?”甄學忠回稱:“這個月裏就辦引見,指分山東。”沈中堂道:“好地方!山東撫臺也是我門生,我替你寫封信去。”甄閣學本有此心,但是不便出口,今見老師先說了出來,自然感激涕零。立刻又叫兒子磕頭,謝了太老師栽培。當時沈中堂甚是高興,喫酒論文,直至上火始散。次日甄閣學又叫兒子去叩見太老師。等到引見領憑下來,又去辭行。沈中堂見面之後,果然鄭重其事的拿出一封親筆信來,叫他帶去給山東巡撫。按下慢表。
玉堂:翰林院的別稱。
目前單說甄閣學的兒子甄學忠拿了沈太老師的信,攜帶家眷前去到省。他父親因爲他獨自一個出去做官,心上不放心,便把自己的內兄請了來,請他跟着同到山東,諸事好有照應。他父親的內兄,便是他的舅太爺了。這位舅太爺姓於,前年死了老伴,無依無靠,便到京找他老妹丈,喫碗閒飯。甄閣學是做京官一直省儉慣的人,憑空多了一個人喫飯,心上老大不自在。幾次三番要把他薦出去,無奈人家嫌他年紀太大了,都不敢請教。這遭託他同到山東照應兒子,卻是一舉兩得。於舅太爺年紀雖大,精神尚健;於世路上一切事情亦還在行。甄學忠有這位老母舅照料,自然諸事一概靠託,樂得自己不問。於舅太爺卻勤勤懇懇,事必躬親,於這位外甥的事格外當心。那些跟來的管家,都是在京裏苦夠的了,好容易跟着主人到外省做官,大家總望賺兩個,誰知碰見了這位舅老爺,以後的好處且慢說。但就目前路上而論,甚麼僱車子,開發店家,有心賺兩個零用錢亦做不到。因此大家沒有一個歡喜這位於舅太爺的,而且都在少主人面前說他的壞話。
在路曉行夜宿,非止一日,早已走到山東濟南府城。稟到,稟見,繳憑,投信,一切繁文,不必細表。撫臺接到沈中堂的私函,託他照應甄學忠,自然是另眼看待。到省不到一個月,撫臺避嫌疑,不肯委他差使。齊巧那時候辦河工,撫臺反替他託了上游的總辦張道臺。算是張道臺上稟帖,向撫臺說這甄牧如何老練,如何才幹,“目下正值需才之際,可否稟懇憲恩,飭令該牧來工差遣,以資臂助”各等語。撫臺看了,彼此心心相印,斷天駁回之理。甄學忠奉到了公事,連忙上院叩謝。撫臺當着大衆很拿他交代一番,又說:“你到省未久,本還輪不到委什麼差使。這是張道臺有稟帖在此,稟請你去幫忙,好生幹!”甄學忠連應了幾聲“是”,下來大家都說他一定同張觀察有什麼淵源。還有人來問他,甄學忠回稱:“素味生平。”大家都不相信,還說他有意瞞人。甄學忠自己亦摸不着頭腦,人家都說他閒話,無可置辨。後來到得工上,叩見了張觀察,張觀察同他很客氣。第二天就委了他買料差使。上來叩謝。張觀察曉得買料事繁,當面薦了兩個人,一個蕭心閒,一個潘士斐,說:“他二人於辦料一切,都是老手。”甄學忠又怕薦的人沒有自己人當心,於是又寫信到公館,請他孃舅於舅太爺趕了來。於舅太爺一聽外甥有了事,自然也是歡喜的,便道:“這買料的事上關國帑,下關民命,中間還關係委員的考成。若是沒個人去監察監察他們,這些人我是知道的,什麼私弊都會做出來。”因此接信之後,便趕着趕到工上。有他一個清眼鬼,自然那些什麼蕭心閒、潘士斐,以及一班家人們,都不敢作什麼弊了。然而大家一齊拿他恨入骨髓。不在話下。
且說甄學忠到省不及一月,居然得了這個美差,便有他的堂房舅子姓黃綽號黃二麻子的,前來找他。他太太是湖北人。這黃二麻子是他大舅子。齊巧這年正在山東濰縣當徵收,看了轅門抄寫得妹丈得了河工差使,他便想趕到省裏來:一來望望妹妹,二來想插手弄點事情做做,總比他當徵收師爺的好。主意打定,便在東家跟前請了兩個半月的假,上省找他妹丈。他這個館地原是情面帳,東家並不拿他十二分當人;他要告假,樂得等他告假。叫帳房多送了一個月的束脩給他做盤川;又託帳房師爺替他照官價僱了一輛車,派了一個差役送他進省,連個二爺都沒有帶。到了省城,黃二麻子是省錢慣的,不肯住客店,又因爲同甄學忠的太太有幾十年不見了,雖是堂房兄妹,怕他一時記不得,似乎未便冒昧,況且妹丈又是從未見過面的人,因此便借了一個朋友家裏暫住歇腳。
他是午飯前到的,吃了飯就換了衣服,要去拜望妹妹、妹丈。他也不該什麼好衣服,一件復染的繭緞袍子,一件天青緞舊馬褂,便算是客服了。又嫌不恭敬,特地又戴了一頂大帽子,穿了一雙前頭有兩隻眼的靴。搖搖擺擺,算做行裝,也還充得過。打扮停當,忽然想起,“初次拜妹丈,應該用個什麼帖子?”他朋友說:“用個‘姻愚弟’罷了。”黃二麻子搖搖頭說道:“我這趟來是望他提拔提拔我的,同他兄弟相稱,似乎自己過於拿大。而且依我意思,用帖子亦不妥當,還是寫個單名的手本。你說好不好?”那朋友道:“令親是什麼官?”黃二麻子道:“舍妹丈是戶部主政,改捐直隸州知州。我們這位太親翁是現任內閣學士,除掉內閣大學士之外,京城的官就要算他頂大。舍妹丈便是他的大少爺。”那朋友道:“他老子官大,兒子總不能世襲到自己身上,就算可以世襲,也沒見過郎舅至親可以用得手本的。”黃二麻子道:“這是官場的規矩,你沒有做過官不曉得的。我這趟來找他在工上弄事情做的。事情成功了,他做老總,我們在他手下辦事,賽如就同他的屬員一樣,怎麼今天來了不上個手本?不但見舍妹丈要用手本;就是去見舍妹,也是要用手本,先上去稟安,方是道理。”那朋友見他執迷不悟,也只好隨他,便說道:“你說的不錯。時候不早了,你快去罷。”
黃二麻子趕忙出門,一路問人,好容易問到妹夫的公館。自己投帖。門上人拿他看了兩眼,回稱:“老爺到工上去了,不在家,擋你老爺的駕罷?”黃二麻子又說:“既然老爺不在家,費心上房太太跟前替我回一聲,就說我黃某人稟安、稟見。”門上人聽他說要見太太,又拿他看了兩眼,問他:“同敝上可是親戚?”他到此方纔說明:“你們的太太就是我的舍妹。”門上人連忙改口稱呼說:“原來是一位舅老爺。”又問:“同我們太太可是胞兄妹?”黃二麻子道:“同高祖還在五服之內,是親的,不算遠。”門上人一聽不是親舅老爺,那臉上的神色又差了。但念他總是太太孃家的人,得罪不得,便道:“你老爺坐一回,等家人上去回過再來請。”黃二麻子連稱:“勞駕得很!……”
一霎時,門上人進去回過太太,讓他廳上相見。太太家常打扮出來。見了面,太太正想舉袖子萬福,黃二麻子早跪下了。磕頭起來,又請了一個安,口稱:“連年在外省處館,姑太太到了,沒有趕得上來伺候。”太太道:“不敢!”於是滿面春風的,問長問短。黃二麻子異常恭敬,竟其口口聲聲“姑老爺”、姑太太”,什麼“妹夫”、“妹妹”等字眼,一個也不提了。隨後提到託在工上謀事情的話,太太道:“至親原應該照應的,無奈這些事情都是你妹夫作主,不是熟手插不下手去,我亦不好要他怎麼樣。你既然很遠的來,住在那裏?”黃二麻子道:“暫時借一個朋友家裏歇歇腳,還沒有一定的住處。”太太道:“既然如此,你且把行李搬了來住兩天。你妹夫不時到省裏來,等他見了你,我們再來想法子。”黃二麻子聽了前半截的話,心上老大着急,及聽到後半,留他在公館裏住,便滿心歡喜,又着實說了幾句感激姑太太栽培的話,然後退了下來。一衆家人曉得太太留他在公館裏住,看太太面上,少不得都來趨奉他,一個個“舅老爺”長、“舅老爺”短,叫的鎮天價響。黃二麻子此時同他們卻異常客氣,連稱:“我如今也是來靠人的,一切正望你們老爺提拔,諸位從旁吹噓。我們還不是一樣嗎?快別提到‘舅老爺’三個字!……”大家見他隨和,倒也歡喜他。
過了幾天,甄學忠工上有事,自己沒有回來,差了於舅太爺到省城裏來辦一件什麼事。黃二麻子早打聽明白了。等到於舅太爺下車進來之後,他忙趕着拿了“姻愚侄”的帖子上去叩見。見了面,口稱“老姻伯”,自稱“小侄”。說到他自己的事情,又要懇老姻伯替他吹噓。於舅太爺是至誠人,看他規矩,便也認他個好人,過了一天,事情辦完,於舅太爺要回工上去。甄學忠的太太又來拜託他在外甥面前替他哥子幫忙,於舅太爺只得答應着。等到老人家轉過了身,一班家人都指指點點的罵他,黃二麻子聽在肚裏,心想:“他的人緣如此不好,倒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沒有事便到上房找妹子談天。面子上說是請姑太太的安,其實是常常親熱慣了,他有他的主意。湊巧這位太太最愛談天說閒話,如今有了這個本家哥哥湊趣,而且又無須避得嫌疑。因此這黃二麻子在妹子跟前很有臉,家人小子們求舅老爺說句把話亦很靈。如此者約有半個月光景。有天甄學忠因公回省,到得家裏,聽了於舅太書的先入之言,心上早有了個底了。等到見了面,頭一樣他能夠低頭服小,就合了脾胃,答應同他一塊兒到工上去。
黃二麻子既到得工上,一看姑老爺的氣派可不小:雖說是個買料委員,只因他手下用的人多,凡是工上用的東西,無論一土一木,都要他派人去採辦;用的人多,自然趨奉的人就多;名爲委員,實則同總辦一樣。此時是於舅太爺拿總,專管銀錢。就是總辦薦的蕭心閒、潘士斐,亦都在總局裏派了有底有面的執事。黃二麻子初到,一個個都去拜望。提到妹夫還不敢稱妹夫,仍舊稱“我們姑老爺”。後來見大家背後叫“老總”,他亦改口稱“老總”。
過了兩天,老總派他稽查工料,他也不曉是稽查些什麼。他平時見了老總及於舅太爺不敢多說話,卻同蕭心閒、潘士斐兩人甚是投機。他倆念他是東家的舅爺,總比別人親一層。而且他在工上住了兩天,定要借事進省一趟,說是記掛姑太太,進省看姑太太去。人家見他走得如此勤,便疑心他縱然不是親兄妹,亦總是嫡堂兄妹了。有些話不便當面向東家談的,便借他做個內線,只要他在他姑太太跟前提一聲,將來東家總曉得的。幾回事情一來,他曉得人家有仰仗他的地方,頓時水長船高,架子亦就慢慢的大了起來,朝着蕭、潘一般人信口亂吹,數說:姑太太今天留他喫什麼點心,又爲他添什麼菜,又指着身上一件光板無毛的皮袍子說:“這件面子,也是姑太太送的。”衆人看了看皮袍子面子,乃是一件舊寧綢復染的,已經舊的不要舊了。潘士斐愛說玩話,便笑着說道:“你們姑太太也太小氣了,既然送你皮袍子面子,爲什麼不送你一件新的,卻送你舊的?”黃二麻子把臉一紅,想了一想,說道:“我們姑太太本來要送我一件新的,是我不要,只問他要這件舊的。”衆人說:“有新的送你,你反不要,要舊的,這是什麼緣故?”黃二麻子道:“我們天天在工上當差使,跑了來,跑了去,風又大,灰土又多,新的上身,不到三天就弄壞了,豈不可惜!我所以只問他要件舊的,可以隨便拖拖。這個意思難道你們還不曉得?”
過了一天,姑太太差了管家來替老爺送東西喫食,順便帶給於舅太爺、黃二麻子一家一塊鹹肉、一盤包子。於舅太爺向來是自己一個人喫飯的,所以大家不曉得。黃二麻子卻如得了皇恩御賜一般,直把他喜的了不得,逢人便告。又說:“我們姑太太怎麼想得這樣周到!曉得我們在工上喫苦,所以老遠的帶喫食來。從前我有兩個舍妹:大舍妹小氣的了不得,所以只嫁了一個教書的,不久就過去了;這是二舍妹,他自小手筆就闊,氣派也不同,所以就會做太太。這是一點不錯的。”
到了第二天中午,特地把姑太太給他的鹹肉蒸了一小塊,拿小刀子溜薄的切得一片一片的,擺在一個三寸碟子裏頭。等到開飯的時候,他拿了出來。一桌子五個人喫飯,他每人敬了一片,說:“這就是我們姑太太的肉,請諸位嚐嚐。”敬了一片,第二片他可不敬了,只見他一筷子一片,只管夾着往嘴裏送,一頭喫,還要一頭贊。等到喫完,剩了三片,還叫伺候開飯的二爺替他留好了,預備第二頓再喫。偏偏碰見這個二爺的嘴讒,伸手拈了一片往嘴裏一送,又自言自語道:“只聽他說好,到底是個甚麼滋味,等我也嘗他一片。”果然滋味好,於是又偷吃了一片。越喫越好喫,又自己說道:“一不做,二不休,一片也是喫,三片也是喫,索性喫完了他。舅老爺不問便罷;倘若問起來,就說是個貓偷吃了的,他總不能怪我。”主意打定,等到晚上開飯的時候,伺候開飯的二爺,只指望他忘卻那三片鹹肉,不提起纔好。
誰知黃二麻子於這三片鹹肉竟是刻骨銘心,也決計忘不掉。一坐下來,還沒有動筷子,就問:“我的鹹肉呢?”偷嘴的二爺忙嚷着叫廚房裏添碗肉。黃二麻子道:“不是要廚房裏添肉,是中飯喫的我們姑太太肉,還剩下三片,我叫你替我留好的。”偷嘴的二爺曉得躲不過,瞎張羅了半天,纔回了一聲:“沒有了。”黃二麻子眼睛一瞪,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說道:“那裏去了?”偷嘴的二爺說道:“想是被野貓銜了去了。”急的黃二麻子跺腳罵“王八蛋”,說道:“是我們姑太太給我的肉,我一頓捨不得喫完,所以留在第二頓喫,叫你留好,你不當心,如今被貓銜了去了。我不管,我只要問你要!你沒,你賠我的;你要不賠,你自己去同你們太太說去。”黃二麻只管罵,不動筷子。等到別人喫完飯,他還是坐着不動,一定要偷嘴的二爺賠他的。
那偷嘴的二爺行撅着嘴不做聲,盡着他罵。後來挨不過,走到門外,嘴裏嘰哩咕嚕的說道:“少了三片鹹肉,不過是豬肉,又不真果是他們姑太太身上的肉,何犯着鬧到這步田地!”偏偏這句話又被黃二麻子聽見了,趕着出去打他的嘴巴,問他喫的誰的飯。一定上去回老爺,攆掉他還不算,還要打他的板子。別的爺們曉得事情鬧大了,都怪那個偷嘴的二爺不是,不該嘴裏拿太太亂講:“舅太爺是太太的哥哥,你亂講被他聽見了,怎麼叫他不生氣呢。他果然同老爺說了,你還想喫飯嗎?”那個偷嘴的二爺到此方纔悔悟過來,由衆人架弄着,領他到黃二麻子跟前磕頭,求舅老爺息怒,不要告訴太太曉得。黃二麻起先還拿腔做勢,一定不答應,禁不住衆管家一齊打千哀求,方纔答應下。那個偷嘴的二爺又磕頭謝過舅老爺恩典,方纔完事。如此一來,黃二麻子把情分一齊賣在衆人身上,衆人自然見他的情。他自己一想:“上頭除掉姑老爺,就是於舅太爺一位,餘外的人都越不過我的頭去。”自此以手,他的架子頓時大了起來。一班家人小子,看了老爺、太太的分上,少不得都要巴結他。還有些人曉得他在主人面前說得動話,指望他說句把好,也不得不來趨奉。
偏偏事有湊巧,於舅太爺病了十天。甄學忠一向有什麼事情,都是於舅太爺承當了去。如今他老人家病了,樣樣都得自己煩心,不上三天,早把他鬧煩了。到這檔口,黃二麻子曉得是機會到了,便格外在姑老爺跟前獻殷勤,甚至家人小廝當的差使,不該他做的,他亦搶在前頭。甄學忠覺得他這人可靠,漸漸的拿些事情交代他辦。他辦完了事情,一天定要十幾趟到於舅太爺屋裏看於舅太爺的病,伺候於舅太爺,什麼湯啊水啊,亦都是他料理。因此於舅太爺亦很見他的情,面子上很贊他好。卻不料他老人家的病一日重似一日。甄學忠還算待孃舅好,凡是左近有名的醫生都已請遍,無奈總不見效。他老人家自己也曉得是時候了,便把外甥請到牀前,黃二麻子亦跟了進去。只見他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拉着外甥的手,說道:“老賢甥!我自從你令堂去世,承你老人家看得起我,如今又到你手裏,並不拿我孃舅當作外人,一切事情都還相信我。我如今是不中用的了!現在正是你要緊時候,我不能幫你的忙,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但是我死之後,銀錢大事,你可收回自己去管。一句話須要記好,‘人心叵測’,雖是至親,也都是靠不住的。”於舅太爺說到這裏,已經喘吁吁上氣接不到下氣,頭上汗珠子同黃豆大小,直滾下來。甄學忠此時念到他平日相待情形,不期而然的從天性中流出幾點眼淚,忙請孃舅呷一口蔘湯,勸孃舅暫時養神,不要說話。約摸停了一會,於舅太爺得了蔘湯補助之力,漸漸的精神迴轉,於是又掙扎着說道:“不但銀錢大事要自己管,就是買土買料,也總要時時刻刻當心。我活一天,這些事我都替你搶在頭裏,不要你操心,就是惹人家罵我恨我,我亦不怕。橫豎我有了這把年紀,也不想什麼好處。除了我,卻沒有第二個肯做這個冤家的。黃某人,人是很能幹的……”說到這裏,於舅太爺氣又接不上來,喘做一團。甄學忠扶他睡下,叫他歇一回。誰知他話說多了,精神早已散了,一個氣不接,早見他眼睛一翻,早已不中用了。甄學忠少不得哭了一場。趕緊派人替他辦後事,忙着入殮出殯,把他靈樞權寄在廟裏,隨後再扶回原籍。都是後話不題。
且說當他病重時,同他外甥說的幾句話,黃二麻子跟在屋裏聽得清清楚楚。先聽他說,“人心叵測,雖是至親亦靠不住”,不由心上畢拍一跳,暗暗罵他:“老殺才!你病了,我如此的伺侯你,巴結你,如今倒要絕我的飯碗!幸虧沒有叫出名來還好。”等到第二回說,“黃某人人是很能幹的,……”照於舅太爺的意思,諒來一定還有不滿意於他的說話。又幸虧底下的話沒有說出,他就一命嗚呼了。碰巧他這位老賢甥聽話也只聽一半,竟是斷章取義,聽了老母舅臨終的說話,以爲是老母舅保舉他堂舅爺接他的手,所以纔會誇獎他能幹。他得了這句說話,等到於舅太爺一斷了氣,還沒有下棺材,他已把大權交給黃二麻子。黃二麻子卻出其不意受了妹夫的託付,這一喜真非同小可!當天就接手。接手之後,一心想查於舅太爺的帳目有什麼弊端,掀了出來也好報報前仇,誰知查了半天,竟其一毫也查不出。只有一間空房裏,常常堆着千把吊錢。他便到妹夫跟前獻殷勤道:“這許多錢堆在家裏,豈不擱利錢,何不存在錢鋪裏,一來可生幾個利錢,二則也免自己擔心?舅太爺到底有了歲數的人了,無論你如何精明,總有想不到的地方。”只見他妹道:“你倒不要說他。工上用的全是現錢,不多預備點存在家裏,一時頭上要起來,那裏去弄呢?”黃二麻子碰了這個軟釘子,自己覺着沒趣,搭訕着又說了幾句別的閒話,妹夫也沒理會他。他便回到自己房裏生氣,咕都着嘴,一個人自言自語道:“誰稀罕喫他的飯!這也算得什麼!”
正在氣間,齊巧管廚的上來付伙食錢。管廚的曉得他是主人的舅老爺,今兒又是初接事,不敢不巴結他。一進門,先請一個安,說了聲:“請舅老爺的安。”黃二麻子愛理不理的,關他什麼事。管廚的故意做出一副笑容,從袖子裏取出本伙食帳來,送到桌子上,卻又笑嘻嘻的說道:“又要舅老爺費心了。”黃二麻子是在現任州、縣衙門當過師爺的,自己雖然沒有經過手,規矩是知道的,曉得大廚房裏,帳房師爺有個九五扣。黃二麻子便拿起算盤,踢踢搭搭一算:五天應付九十六吊,照九五扣,應除四吊八百文,實付九十一吊二百文。照數發了出來。管廚的接到手裏一算,不敢說不對,只笑嘻嘻的說道:“舅老爺這是怎麼算的?小的不懂。”黃二麻子當是管廚的有心當面奚落他,便把算盤一推,跟手拿桌子一拍,罵道:“好混帳!你瞧不起我,見我今天初接手,欺負我外行,要來蒙我!通天底下衙門局子,都是一樣。我做帳房雖是今天頭一天,你當管廚的難道亦是今天頭一回嗎、你如果嫌少,你不要拿,替我把錢放在這裏!”管廚的碰了這個釘子,曉得一時說不明白,只好拿了錢,搭訕着出去。黃二麻子還罵道:“底賤貨!你不兇過他的頭,他就兇過你的頭,真正不是些好東西!”
到了第二天,管廚的特地送了黃二麻子一隻火腿,又做了兩碗菜,一碗紅燒肘子,一碗是清燉鴨子,說是:“小的孝敬師老爺的,總得求舅老爺賞個臉收下。”起先黃二麻子還只板着個臉,一定不要這些東西,禁不住管廚的一再懇求,方纔有點活動。管廚的下去,當夜便找了值帳房的二爺,請他吃了幾杯酒,託他同舅老爺說:“這個九五扣,照例原是應該有的,只爲舅太爺要替老爺省錢,叫我們辦‘清公事’,什麼伙食錢,酒席價,格外往少裏打算,也不要什麼扣頭。如今舅老爺來了。這個錢我們下頭亦情願報效的。但是有一句俗語,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無非還是拿着老爺的錢貼補他舅老爺罷了,舅老爺是何等精明的人,難道要我們賣老婆孩子不成?少不得還要拜求舅老爺在老爺面前,就說現在工上米糧柴火以及喫的菜,無一不貴。若照着前頭數目,實在有點賠不起。總得求他老人家看破些,自下個月起,每人伙食加上十個錢。如此一來,我也不至賠本,舅老爺也有了。至於老爺一天多化幾百錢,少處去,大處來,只要那筆材料裏頭多開銷上頭幾文,還怕這筆沒抵擋嗎。”
那值帳房的二爺喫喝了他的酒菜,少不得要幫他的忙,當時諾諾連聲。等到晚上,走到黃二麻子身旁,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只見黃二麻子皺了半天眉頭,說道:“既然如此,何不早說!老爺跟前,我已經說他做不下去,保舉了別人,換別人做了。如今叫我到老爺跟前怎麼再替他說回來呢?”值帳房的二爺聽了此言,亦爲一驚,口稱;“這事總要求舅老爺恩典!”停了半晌,黃二麻子又說道:“這們樣罷,老爺跟前,我還說得回來,只說接手的那個人家裏有事,一時不能上工,仍叫前頭一個做起來。以後我們再留心,另僱別人罷。但是要接手的那個人,我已經答應他了,明天就要來上工。這個只好你們底下去他商量。他肯讓自然極好,倘若不肯,也只好由他,我不能做出爾反爾的事。”值帳房的出來同管廚的說了。管廚的倒也明白,說:“也不過想兩個錢。等我認晦氣送他二十吊錢,叫他明天不要來。但是由我們底下勸他,一定不肯依的。這事情還得求舅老爺幫我一個忙,這錢就請舅老爺給他,方纔妥當。”值帳房的又上去回了。黃二麻子不說別的,但說二十吊錢太少,恐怕說不下去。後來又添了十吊,黃二麻子答應了,方纔無事。自從管廚的有了這回事,大家都曉得舅老爺是要錢的,凡是來想他妹夫好處的,沒一個不送錢給他。等到妹夫差使交卸下來,他的腰包裏亦就滿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