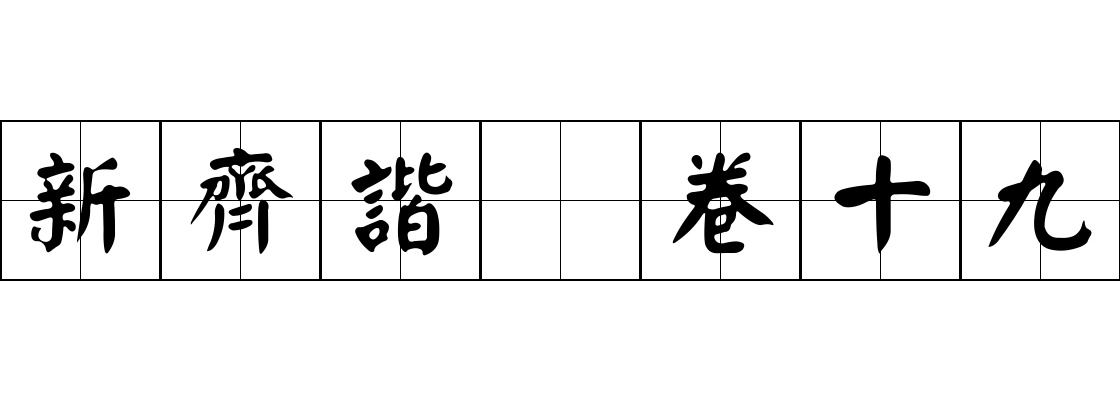新齊諧-卷十九-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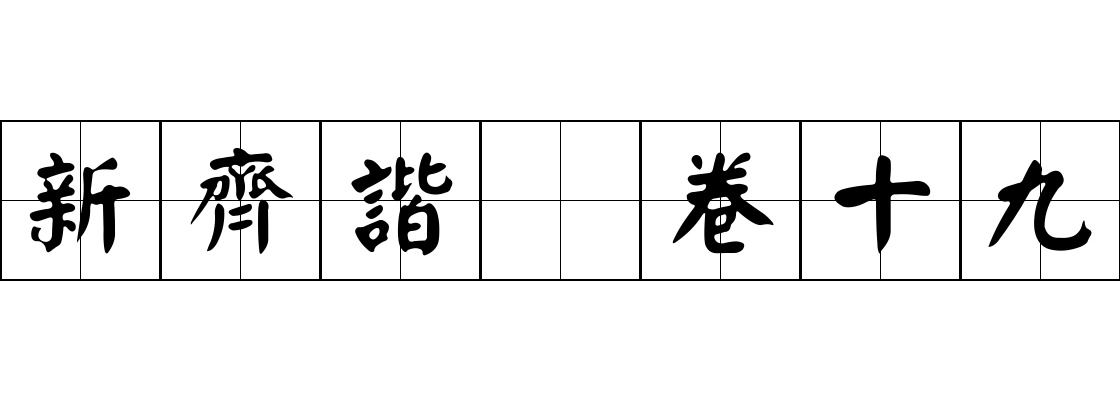
《新齊諧》,古代中國神話志怪小說集。共二十四卷,清代乾隆末年袁枚所著。初名《子不語》,因元說部中有同名作品,後改名《新齊諧》。《新齊諧》中還有不少故事,表現了袁枚反對理學、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想,這在當時也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周世福
山西石樓縣周世福、周世祿兄弟相鬥,刀戳兄腹,腸出二寸。後日久,肚上創平復如口,能翕張,腸拖於外,以錫碗覆之,束以帶,大小便皆從此處出。如此三載餘方死。死之日,有鬼附家人身詈其弟雲:“汝殺我,乃前生數定也,但早了數年,使我受多少污穢。”
韓宗琦
餘甥韓宗琦,幼聰敏,五歲能讀《離騷》諸書,十三歲舉秀才。十四歲,楊制軍觀風拔取超等,送入敷文書院,掌教少宗伯齊召南見而異之,曰:“此子風格非常,慮不永年耳。”
己卯八月初一日清晨,忽謂其母曰:“兒昨夢得甚奇,仰見天上數百人奔波於雲霧之中,有翻書簿者,有授紙筆者,狀亦不一。既而聞唱名聲,至三十七名,即兒名也,驚應一聲而醒。所呼名字,一一分明,醒時猶能記憶,及曉披衣起,俱忘之矣”。自以爲天榜有名,此科當中。
及至鄉試,三場畢,中秋,月明如晝,將欲繳卷,聞有人呼曰:“韓宗琦,好歸去也!”如是者三,其聲漸厲,若責其遲滯者。甥應曰:“諾。”及繳卷時,四顧無人,踉蹌歸。次日,問諸同考友,皆曰:“無之。倘我輩即欲同歸,必另有稱呼,豈敢竟呼兄名?”
揭榜後,名落孫山,甥悵悵不樂。旋感病,遂不起。臨終苦吟“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二句,張目謂母曰:“兒頓悟前生事矣。兒本玉帝前獻花童子。因玉帝壽誕,兒獻花時偷眼觀下界花燈,諸仙嫌兒不敬,即罰是日降生人間,今限滿促歸,母無苦也。”卒年十五,蓋俗傳正月初九爲玉帝生日雲。
徐俞氏
鄧州牧徐廷璐,與妻俞氏伉儷甚篤。俞卒,徐慟甚,凡其粉澤衣香,一一位置若平時,取其半臂覆枕上。至一七,營奠於庭,有小婢驚呼:“夫人活矣!”徐趨視,見夫人着半臂端坐牀上,子女家人奔集,鹹見之。徐走前欲抱,其影奄然澌滅,而半臂猶僵立,良久始僕。
一夕,徐設席,欲與夫人對飲者,執杯泣曰:“素勞卿戒飲,今誰戒我耶!”語未畢,手中杯忽失所在,侍立婢僕遍尋不得。少頃,杯覆席間,酒已無餘。
有妾語人曰:“此後夫人不能詬我矣。”至夕,見夫人直登臥榻批其頰,頰上有青指痕,三日始滅。自是,舉室畏敬,甚於在生時。
琵琶墳
董太史潮,青年科第,以書畫文辭冠絕時輩,性磊落。而有國風之好。常與諸名士集陶然亭散步吟詩,獨至城堙下,忽聞琵琶聲。蹤跡之,聲出數椽敗屋,乃十七八美女子,着淡紅衣,據窗理絃索。見董,略無羞避,揮弦如故。董徘徊不能去。同人怪董久不至,相率尋之,見董方倚破牖癡立,呼之不應。羣啐之,董驚寤,而女子形聲俱寂。始道其故,衆入室搜索,敗瓦頹垣,絕無人跡,有蓬顆一區,俗所稱“琵琶墳”也。乃掖董歸。未幾,以疾歸常州,卒於家。
曹阿狗
歸安程三郎,妻少艾而賢,里黨稱三娘子。方夏日曉妝,忽舉動失常,三郎疑爲遇祟,以左手批其頰。三娘子呼曰:“勿打我,我鄰人曹阿狗也。聞家中設食,同人來赴。既至,獨無我席,我慚且餒,知三娘子賢,特憑之求食耳,勿怖。”其鄰曹姓,大族也,於前夕果延僧人誦《焰口經》。阿狗者,乃曹氏無賴,少年未婚而卒者也。以阿狗無後,實未爲之設食,聞此言亦駭,同以酒漿楮鏹至三娘子前致祝。三娘子曰:“今夕當專爲我設食,送我於河,此且祭祀,必有阿狗名乃可。”曹氏懼,如其言送之,三娘子遂愈。
錢仲玉
錢生仲玉,少年落魄,遊蘭溪署中。值上元夕,同人鹹出觀燈,仲玉中懷鬱郁,獨不往,步月庭除,嘆曰:“安得五百金,使我骨肉團聚乎!”語畢,聞階下應聲曰:“有,有。”仲玉疑友人揶揄之,遍視,不見人,乃還齋坐。
聞窗外謖謖聲,一美女搴幃入曰:“郎勿驚,妾非人,亦非爲禍者也。佳節異鄉,共此岑寂。適聞郎語,笑郎以七尺男子,何難得五百金哉?”仲玉曰:“然則頃雲‘有有’者即卿耶?”曰:“然。”仲玉曰:“在何處?”女笑曰:“勿急,勿急。”即拉仲玉手同坐曰:“妾汪六姑也,葬此,爲污泥所侵,求君改葬高處,必當如君言以報。”問:“何病亡?”女以手遮面曰:“羞不可言。”固問之,曰:“妾幼解風情,而生長小家,所居樓臨街,偶倚窗,見一美少年方溺,出其陰,紅鮮如玉,妾心慕之,以爲天下男子皆然。已而嫁賣菜傭周某,貌即不佳,體尤瑣穢,絕不類所見少年,以此怨思成疾,口不能言,遂卒。”仲玉聞之,心大動,弛下衣,拉女手使摸。而人聲忽至,女遽拂衣起曰:“緣未到。”仲玉送至牆下,女除一銀臂釧與之曰:“幸勿忘。”言畢而沒。仲玉恍然如夢,視銀釧,竟在手中,乃祕之。
次夕人靜,獨步牆陰,遍視不復見,乃語主人,並出臂釧以證。主人異之,起土三尺許,得女屍,衣飾盡朽,肌色如生,與仲玉所見無異,右臂一釧猶存。仲玉解衣覆之,爲備棺衾,移葬高阜。
其夕,夢女來謝曰:“感郎信義,告郎金所,郎臥榻向左三尺,舊有人埋五百金,明當取之。”如其言,果得金如數。
蝦蟆蠱
朱生依仁,工書,廣西慶遠府陳太守希芳延爲記室。方盛暑,太守招僚友飲。就席,各去冠,衆見朱生頂上蹲一大蝦蟆,拂之落地,忽失所在。飲至夜分,蝦蟆又登朱頂而朱不知,同人又爲拂落,席間餚核,盡爲所毀,復不見。朱生歸寢,覺頂間作癢。次日,頂上發盡脫,當頂墳起如瘤,作紅色。皮忽迸裂,一蟆自內伸頭瞪目而望,前二足踞頂,自腰以下在頭皮內,針刺不死。引出之,痛不可耐,醫不能治。有老門役曰:“此蠱也,以金簪刺之當死。”試之果驗,乃出其蟆。而朱生無他恙,惟頂骨下陷,若仰盂然。
礅怪
高睿功,世家子也。其居廳前有怪。每夜人行,輒見白衣人長丈餘躡後,以手掩人目,其冷如冰。遂閉前門,別開門出入。白衣人漸乃晝見,人鹹避之。睿功偶被酒坐廳上,見白衣人登階倚柱立,手拈其須,仰天微睇,似未見睿功在坐者。睿功潛至其後,揮拳奮擊,誤中柱上,挫指血出,白衣人已立丹墀中。睿功大呼趨擊,時方陰雨,爲苔滑撲地。白衣人見而大笑,舉手來擊,腰不能俯;似欲以足蹴,而腿又長不能舉;乃大怒,環階而走。睿功知其無能爲,直前抱持其足而力掀之,白衣人倒地而沒。睿功呼家人就其初起處掘,深三尺,得白瓷舊坐礅一個,礅上鮮血猶存,蓋睿功指血所染也。擊而碎之,其怪遂絕。
六郎神鬥
廣西南寧鄉里,祀六郎神。人或語言觸犯,則爲祟。尤善媚女子,美者多爲所憑。凡受其害者,以紙鏹一束,飯一盂,用兩三樂人,午夜祀之,送至曠野,即去而之他。其俗無夕不送六郎也。
有楊三姑者,年十七,美姿容。日將夕,方與父母共坐,忽嫣然睨笑。久之,趨入房,施朱傅粉,嬌羞百態。父母往問,磚石自空擲下,房門遂閉,惟聞兩人笑語聲。知爲六郎,亟呼樂人送之。六郎不肯去。及晨,女出如常,雲:“六郎美少年,頭戴將巾,身披軟甲,年可二十七八,與我甚恩愛,不必送他去。”父母無如何。
越數夕,忽倉皇奔出曰:“又一六郎來!大鬍子,貌甚獰惡,與前六郎爭我相毆。前六郎非其敵也,行當去矣。”俄聞室中鬥聲甚劇,似無物不損者,父母乃召樂人雙送之。兩人俱去,三姑亦無恙。
返魂香
餘家婢女招姐之祖母周氏,年七十餘,奉佛甚虔。一夕寢矣,見室中有老嫗立焉。初見甚短,目之漸長,手紙片堆其几上,衣藍布裙,色甚鮮。周私憶,同一藍色,何彼獨鮮?問:“阿婆藍布從何處染?”不答。周怒罵曰:“我問不答,豈是鬼乎!”嫗曰:“是也。”曰:“既是鬼,來捉我乎?”曰:“是也。”周愈怒,罵曰:“我偏不受捉!”手批其頰,不覺魂出,已到門外,而老嫗不見矣。
周行黃沙中,足不履地。四面無人。望見屋舍,皆白粉垣,甚宏敞,遂入焉。案有香一枝,五色,如秤桿長,上面一火星紅,下面彩絨披覆層迭,如世間嬰孩所戴劉海搭狀。有老嫗拜香下,貌甚慈,問周何來,曰:“迷路到此。”曰:“思歸乎?”曰:“欲歸不得。”嫗曰:“嗅香即歸矣。”周嗅之,覺異香貫腦,一驚而蘇,家中僵臥已三日矣。或曰:“此即聚窟山之返魂香也。”
觀音作別
方姬奉一檀香觀音像,長四寸。餘性通脫,不加禮,亦不禁也。有張媽者,奉之尤虔,每早必往佛前,焚香稽首畢,方供掃除之役。餘一日早晨,呼盥麪湯甚急,而張方拜佛不已,餘怒,取觀音像擲地,足蹋之。姬泣曰:“昨夜夢觀音來別我,雲:‘明日有小劫,我將他適矣。’今果被君作蹋,豈非數也!”乃送入準提庵。餘想:佛法全空,焉得作如此狡獪,必有鬼物憑焉。嗣後,乃不許家人奉佛。
兔兒神
國初,御史某年少科第,巡按福建。有胡天保者愛其貌美,每升輿坐堂,必伺而睨之。巡按心以爲疑,卒不解其故,胥吏亦不敢言。居無何,巡按巡他邑,胡竟偕往,陰伏廁所窺其臀。巡按愈疑,召問之。初猶不言,加以三木,乃雲:“實見大人美貌,心不能忘,明知天上桂,豈爲凡鳥所集,然神魂飄蕩,不覺無禮至此。”巡按大怒,斃其命於枯木之下。逾月,胡託夢於其里人曰:“我以非禮之心干犯貴人,死固當,然畢竟是一片愛心,一時癡想,與尋常害人者不同。冥間官吏俱笑我、揶揄我,無怒我者。今陰官封我爲兔兒神,專司人間男悅男之事,可爲我立廟招香火。”閩俗原爲聘男子爲契弟之說,聞里人述夢中語,爭醵錢立廟。果靈驗如響。凡偷期密約,有所求而不得者,鹹往禱焉。
程魚門曰:“此巡按未讀《晏子春秋》勸勿誅羽人事,故下手太重。若狄偉人先生頗不然。相傳先生爲編修時,年少貌美。有車伕某,亦少年,投身入府,爲先生推車,甚勤謹,與僱直錢,不受,先生亦愛之。未幾病危,諸醫不效,將斷氣矣,請主人至,曰:‘奴既死,不得不言。奴之所以病至死者,爲愛爺貌美故也。’先生大笑,拍其肩曰:‘癡奴子!果有此心,何不早說矣?’厚葬之。”
玉梅
香亭家婢玉梅,年十餘歲,素勤。忽懶,終日昏睡,笞之亦不改。每夜喃喃,如與人私語。問之,不肯說,褫下衣驗其陰,已非處子,且潰爛矣。拷訊乃雲:“夜有怪,狀如黑羊,能作人語。陽具如毛錐,痛不可當。戒我勿告人,如告人,當拉我去,置之死地。”衆駭然。
伺婢臥,夜竊聽焉。初作貓飲水聲,繼而呻吟,香亭率衆持棍入,燭照無人,問:“怪何在?”婢指牀下曰:“此綠眼者是也。”果見眼光兩道,閃耀處,帳色皆綠。棍擊之,跳起衝窗去,滿房帳鉤箱鎖之類,鏘鏘有聲。次日失婢所在,遍覓不得。薄暮,竈下人見風飄紅布裙一條在柴房西角處,往尋得婢,癡迷不醒。灌以薑汁,蘇曰:“怪昨夜來雲:‘事爲汝主所知,不得不抱汝去。’遂藏我於柴房中,約今夜仍來。”問:“聽得貓飲水聲,何耶?”曰:“怪每淫我,先舐後交,口舐差樂也。”香亭即日呼媒者,將玉梅轉售他家,怪竟不往。
盧彪
餘幼時同館盧彪,一日至館,神色沮喪,問之,曰:“我昨日往西湖掃墓,歸遲,城門閉矣,宿某店家。夜月甚明,雞鳴即起,踏月進城。至清波門外,小憩石上。見遠遠一女子來,向餘伏拜。餘疑其非人,口誦《大悲咒》拒之。女如畏聞而不敢近者,我逼而誦之。我愈近女,女愈遠我,我驚,乃狂奔數裏。將入甕城,見東方漸白,賣魚人挑擔往來,以爲此時尚復何懼,何不重至舊處一探蹤跡?行至前路,不料此女高坐石上,如有所待。望見我便大笑,奔前相撲,冷風如箭,毛髮盡顫。我惶急,再誦《大悲咒》拒之。女大怒,將手向上一伸,兩條枯骨側側有聲,面上非青非黃,七竅流血。我不覺狂叫仆地,枯骨從而壓之,我從此昏昏無知矣。後有行路者過,扶起,以薑汁灌我,才得甦醒還家。”餘急與諸窗友置酒爲盧壓驚,視其耳鼻兩竅及辮髮中尚有青泥填塞,星星如小豆。或雲:“皆盧所自塞也,故兩手亦皆泥污。”
孔林古墓
雍正間,陳文勤公世倌修孔林。離聖墓西十餘步,地陷一穴,探之:中空,廣闊丈餘,有石榻;榻上朱棺已朽,白骨一具甚偉,旁置銅劍,長丈餘,晶瑩綠色,竹簡數十頁,若有蝌蚪文者。取視,成灰。鼎俎尊彝之屬,亦多破缺漫漶。文勤公以爲此墓尚在孔子之先,不宜驚動,謹加磚石封砌之,爲設少牢之奠焉。
史閣部降乩
揚州謝啓昆太守扶乩,灰盤書《正氣歌》數句,太守疑爲文山先生,整冠肅拜。問神姓名,曰:“亡國庸臣史可法。”時太守正修葺史公祠墓,環植鬆梅,因問:“爲公修祠墓,公知之乎?”曰:“知之。此守土者之責也,然亦非俗吏所能爲。”問自己官階,批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謝無子,問:“將來得有子否?”批曰:“與其有子而名滅,不如無子而名存。太守勉旃。”問:“先生近已成神乎?”曰:“成神。”問:“何神?”曰:“天曹稽察大使。”書畢,索長紙一幅,問:“何用?”曰:“吾欲自題對聯。”與之紙,題曰:“一代興亡歸氣數,千秋廟貌傍江山。”筆力蒼勁,謝公爲雙勾之,懸於廟中。
懸頭竿子
某令宰寶山時,有行商來告搶奪者,被搶處系一坍港泊舟所也。令往視其地,見水路可通城中,而乘舟者例在此處僱夫起行,心疑之,衆莫言其故。
一把總來見曰:“此地原可通舟,所以客來必起撥者,港口窮民籍挑馱之力爲餬口計故也。”令問搶奪事,曰:“不敢言,須寬把總罪,纔敢言。”令曰:“律有自首免罪之條,汝告我,即爲自首矣,何妨?”曰:“諸搶奪者,皆把持壟斷人也,把總兒子亦在其中。前月某商到此,見水路可通,不肯起撥,因而打吵,事實有之。”乾隆三十年新例:拿獲強盜者,破格超遷。令定案時,心想遷官,竟以獲盜具詳;把總知情,照窩家例立決。一時斬者六人,令超遷安慶知府。
後六年,署鬆泰道。巡海至寶山搶奪處,見六竿子掛髑髏尚存。問跟役曰:“前累累者何物耶?”役曰:“此六盜也,大人以此升官而忘之耶?”令不覺悚然,怒曰:“死奴!誰教汝引我至此?速歸!速歸!”舁至衙,罵司閽者曰:“此內室也,汝何敢放某把總擅入!”言畢而背瘡發,一瘡六頭,如相齧者。家人知爲不祥,燒紙錢、請高僧懺悔,卒以不起。陳紫山
餘鄉會同年陳紫山,名大侖,溧陽人也。入學時,年才十九。偶病劇,夢紫衣僧,自稱“元圭大師”,握其手曰:“汝揹我到人間,盍歸來乎?”陳未答,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尚有瓊林一杯酒,瀛臺一碗羹,吃了再來未遲。”屈其指曰:“別又十七年了。”言畢去。陳驚醒,一汗而痊。己未中進士,入翰林,升讀學士。
三十八歲,秋痢不休,因憶前夢十七年之期,自知不起。常對家人笑曰:“大師未來,或又改期,亦未可知。”忽一日早起,焚香沐浴,索朝衣冠着之,曰:“吾師已來,吾去矣。”同年金質夫編修素好佛者,在旁喝曰:“既牽他來,又拖他去。一去一來,是何緣故?”陳目且瞑,強起張目答曰:“來原無礙,去亦何妨。人間天上,一個壇場。”言畢,跏趺而逝。
忌火日
曹來殷太史在京師晝寢,夢偉丈夫來拜,自稱“黃昆圃先生”。拉至一處,宮闕巍然,中有尊神,面正方,着本朝衣冠,請曹入見,曰:“吾三人皆翰林衙門官,只行前後輩禮,不行僚屬禮。”坐定目曹曰:“卿十一歲時曾行一大好事,上帝知之,故特召卿到此受職,卿可即來。”曹茫然不記幼所行何事,再三辭,力陳“家寒子幼,故不願來”。尊神甚不悅,旁顧昆圃先生曰:“再向彼勸掖之。”
語畢,不顧而入。
先生拉曹笑曰:“我深知翰林衙門亦甚清苦,卿何戀戀不肯來耶?”曹復哀求。先生曰:“我且爲卿說情,似亦可免,但卿此後逢火日不可出門,慎無忘也。”
曹問:“尊神何人?”曰:“張京江相公。”問:“何地?”曰:“天曹都察院。”
曹驚醒。後每出門,必檢視黃曆,遇火日,雖慶弔事,皆不行。數年後,不甚記憶。
乾隆三十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嚴冬友舍人邀曹至程魚門家作詩會,俗以此日祀竈,遂以爲題。席間酒數巡,曹倀然如睡去者,目瞑身僕。羣客大驚,疑詩中有侮竈神之語,故神爲祟,乃羣向竈禮拜祈請。至三更時,曹始蘇,自言“見黑袍人送我回來”。次日,取黃曆視之,二十三日,火日也。
朱法師
同館翰林朱澐之父樸庵先生,陝西人也,少時課徒爲業。偶至一村,村人傳呼曰:“朱法師來矣!”具酒饌求書姓名,以爲鎮壓。朱笑曰:“我乃蒙童之師,非法師也。且素無法術,不能鎮怪。汝輩何爲?”衆人曰:“此村有狐仙爲民患者三年。昨日空中語曰:‘明日朱法師來,我當避之。’今日先生來,果姓朱,故疑爲法師。”朱寫姓名與之,某村果安。
未幾。朱別過一村,其村人之歡迎者如前,且曰:“狐仙有語,二十年後,與朱法師相見於太學之崇志堂。”朱其時尚未鄉舉也。
後中壬子科舉人,選國子監助教。監中祭器久被狐竊去,司祭者皇皇然,索而弗獲,方議賠償,朱記前語,爲文祭之。一夕,俎豆之屬,盡橫陳於崇志堂,絲毫無損。屈指算之,距到某村已二十年。
城門面孔
廣西府差常寧,五鼓有急務出城。抵門,猶未啓鑰,以手捫之,軟膩如人肌膚。差大駭,乘殘月一線,定睛視之,則一人面塞滿城門,五官畢具,雙眼如箕,驚而返走。天明,逐隊出城,亦無他異。
竹葉鬼
豐溪吳奉我,作宦閩嶠,謝病歸裏。舟過豫章,天暑熱,假空館於百花洲,屋宇寬敞,頗覺適意。屋內外常有聲如鬼嘯,家人獨行,往往見黑影不一。一夕,吳設榻乘涼於闌干側,聞牆角芭蕉叢中有聲,走出無數人,長者、短者、肥者、瘠者,皆不過尺許。最後一人稍大,荷大笠帽,不見戎其面。旋繞垣中,若數十個不倒翁。吳急呼人至,倏忽不見,化作滿地流螢。吳捉之,一螢才入手,戛然有聲,餘螢悉滅。取火燭之,一竹葉而已。
驢大爺
某貴官長子,性兇暴,左右稍不如意,即撲責致死,侍女下體,以非刑。
未幾病死,見夢於平昔親信之家奴雲:“陰司以我殘暴,罰我爲畜,明晨當入驢腹中。汝速往某衚衕驢肉鋪中,將牝驢買歸,以救我命。稍遲,則無及矣。”言甚哀。奴驚寤,心猶疑之,乃復睡去。又夢告之曰:“以我與爾有恩,俾爾救援,爾寧忘平日眷顧耶?”奴亟赴某衚衕,見一牝驢將次屠宰。買歸園中,果生一駒,見人如相識者。人呼“大爺”,則躍而至。
有畫士鄒某,居其園側,一日聞驢鳴,其家人云:“此我家大爺聲也。”
熊太太
康熙間,內城伍公某者,三等侍衛也,從上打圍木蘭。以逐取獵犬故,墜深澗中,自分死矣。餓三日,有人熊過澗,乃抱以上,自分以爲將啖己也,愈驚。
熊抱入山洞,採果喂之,或負羊豕與食。伍見而攢眉,熊爲採樹葉。燒熟以食之。
久之,漸無怖意。每小便。熊必視其陰而笑,方知熊故雌也,遂與成夫婦。生三子,勇力絕人。
伍欲出山,熊不許;其子求還家,熊許之。長子名諾布,官藍翎侍衛,乃以巨車迎父母還家,家人號曰“熊太太”。人求見者,熊不能言,能叉手答禮。就養其家十餘年,先伍公卒。學士春臺親見之,爲餘言。
冤鬼錯認
杭城艮山門外俞家橋楊元龍,在湖墅米行中管理帳目。湖墅距俞家橋五里,元龍朝往夕返,日以爲常。偶一日,因米行生理熱鬧,遲至更餘方歸。至得勝壩橋,遇素識李孝先偕二人急奔。元龍呼之,李答雲:“不知二人何事,要緊拉我往蘇州去?”楊詢二人,皆笑而不答。元龍拱手別李,李囑雲:“汝過潮王廟裏許小石橋邊,有問汝姓名者,須告以他姓,不可言姓楊;若言姓楊,須並以名告之。切記,切記!”元龍欲問故,孝先匆匆行矣。
元龍前行至橋,果有二人坐草中問其姓名。元龍方答姓楊,二人即直前扭結雲:“久候多時,今日不能放你了。”元龍以手拒之,奈彼夥漸衆,爲其扯入水中;始悟爲鬼,並記前語,即大呼曰:“我楊元龍並未與各位有仇!”中有一鬼曰:“誤矣,放還可也。”方叫喚間,適有賣湯圓者過橋,聞人叫聲,持燈來照,見元龍在水中,急救之。元龍起視,即鄰人張老,告以故,張老送元龍歸家。
次早,元龍往視孝先,見孝先方殮。詢之,其家雲:“昨晚中風死矣。”蓋遇李時,即李死時也,但不知往蘇州何事。
代州獵戶
代州獵戶李崇南,郊外馳射,見鴿成羣,發火槍擊之,正中其背,負鉛子而飛。李在驚,追逐至一山洞,鴿入不見。李穿洞而進,則石室甚寬,有石人數十,雕鏤極工,頭皆斫去,各以手自提之;最後一人,枕頭而臥,怒目視李,睛閃閃如欲動者。李大怖,方欲退出,而帶鉛子之鴿率鴿數萬爭來咬撲。李持空槍且擊且走,不覺墜入池內,水紅熱如血,其氣甚腥。鴿似甚渴者,爭飲於池,李方得脫逃。出洞,衣上所染紅水,鮮明無比,夜間映射燈月之下,有火光照灼。終不知此山鴿究屬何怪。
金剛作鬧
嚴州司寇某,有戚徐姓者,能持《金剛經》。司寇卒後,徐作功德,爲誦經,日八百遍。一夕病重,夢鬼役召至閻羅殿,上坐王者謂曰:“某司寇辦事太刻,奉上帝檄,發交我處。應訊事甚多,忽然金剛神闖門入,大吵大鬧,不許我審,硬向我要某司寇去。我係地下冥司,金剛乃天上神將,我不敢與抗,只好交其帶去。金剛竟將他釋放。我因人犯脫逃,不能奏覆上帝,只得行查至地藏王處,方知是汝在陽間多事,替他念《金剛經》所致。地藏王曉得公事公辦,無可挽回,故替我攔住金剛神,不許再來作鬧,仍將某公解回聽審。所以召汝者,將此情節告知,不許再爲誦經。姑念汝也是一片好意,無大罪過,故仍放汝還陽。然妄召尊神,終有小譴,已罰減陽壽一紀矣。”徐大驚而醒。未十年竟卒。
吳西林曰:“金剛乃佛家木強之神,黨同伐異,聞呼必來,有求必應,全不顧其理之是非曲直也,故佛氏坐之門外,爲壯觀御武之用。誦此經者,宜慎重焉。”
燒頭香
凡世俗神前燒香者,以侵早第一枝爲頭香,至第二枝,便爲不敬。有山陰沈姓者,必欲到城隍廟燒頭香,屢起早往,則已有人先燒矣,悶悶不樂。其弟某知之,預先通知廟祝:毋納他人,俟其先到,再開門納客。廟祝如其言。沈清晨往,見燒香者未至,大喜,點香下拜,則仆地不起矣。
扶舁歸家,大呼曰:“我沈某妻也。我雖有妒行,然罪無死法。我夫不良,趁我生產時,囑穩婆將二鐵針置產門中,以此隕命。一家之人,竟無知者。我訴城隍神,神說我夫陽壽未終,不準審理。前月關帝過此,我往喊冤,城隍說我衝突儀仗,又縛我放香案腳下。幸天網恢恢,我夫來燒頭香,被我捉住,特來索命。”
沈家人畢集拜求,請焚紙錢百萬,或請召名僧超度。沈仍作妻語曰:“汝等癡矣!我死甚慘,想往叩天閽,將城隍縱惡、沈某行惡之事,一齊申訴,豈區區紙錢超度所能饒名者乎?”言畢,沈自牀上投地,七竅流血死。
樹怪
費此度從徵西蜀,到三峽澗,有樹孑立,存枯枝而無花葉,兵過其下輒死,死者三人。費怒,自視之,其樹枝如鳥爪,見有人過,便來攫拿。費以利劍斫之,株落血流。此後行人無恙。
廣信狐仙
徐芷亭方伯初守廣信府,有西廂房鎖閉多年,雲中有狐。徐夫人不信,親往觀之。聞鼾呼聲,啓戶無人,聲從一榻中出。夫人以棍敲之,空中有人語云:“夫人莫打。我吳子剛也,居此百餘年,頗有去意。屢欲移居,而門神攔我。夫人可爲我祭之,且代爲乞情,則我讓出朝廷公廨矣。”
夫人大駭,具酒餚向竹牀陳設,兼祭門神,告以原委。又聞空中語曰:“我受夫人恩,愧無以報,謹來賀喜。府上老爺即日升官。奉囑者,七月七日,切勿抱官官到紅梅園嬉戲,其日恐有惡鬼在園作祟。”言畢寂然。
到期,方伯表兄某過園,見樹上有兩紅衣兒以手招人。就視之,並無形影,但聞崩頹之聲,則假山石倒矣,幾爲所壓。九月間,徐公升贛南道。此事徐公子秉鑑爲我言。
白石精
天長林司坊名師者,家設乩壇,有怪物佔爲壇主,自名“白石真人”,人問休咎頗驗。常教林君修仙,須面上開一眼,便可見上帝宮室,雲中神仙。林從此癡迷,時以小刀向鼻間刻劃。人奪其刀,便怒罵。
忽一日,乩盤書雲:“我土地神也。現在纏汝者是西山白石之精,神通絕大,我受其驅使。渠不能作字,凡乩上,皆強我代書。今日渠往西天參佛,故我特來通知,速拆乩盤,具呈於本縣城隍,庶免此難。但切不可告知此怪,是土地神來泄漏也。”適蔣太史苕生自金陵來,知其故,立毀其盤,並以三十金買天師符一張,懸林室中,怪果不至。
後十年,林君亡矣,符尚掛中堂,有線香倒下,燒其符上硃砂,字畫盡,而襯紙不壞。其時蔣在京師,未得林訃,適天師來朝,告蔣曰:“貴親家林君死矣。”
問:“何以知之?”曰:“某月日,我所遣符上神將已來歸位故也。”後得之林家燒符之信,方覺駭然。
當扶乩時,蔣在座,則盤中不動。蔣去後,人問乩,書雲:“此老有文光射人,我不喜見之。”據土地雲:“白石精在林家作祟者,要攝取林之魂,供其役使故耳。”
鬼圈
蔣少司馬時庵公子某,與數友在京師遊愍忠寺。時屆清明,踏青荒地,見精舍數間,中有琵琶聲。趨往,則一女背面坐,手彈絃索。逼視之,女回頭,變青面猙獰者,直來相撲,陰風襲人,各驚走歸。時尚下午,彼此以爲眼花,且恃有四人之衆,各持木棍再往,則有四黑人坐而相待,手持銅圈套人。受其套者,無不傾跌,棍無所施。正倉皇間,有放馬者數人驅馬衝來,怪始不見。四人歸,各病十餘日。
東醫寶鑑有法治狐
蕭山李選民,少年惆儻。燒香佛廟,見美女在焉,四顧無人,逐與通語。女自言姓吳,幼無父母,依舅而居。舅母凌虐,故在此禮佛,願得佳耦。李以言挑之,女唯唯,遂與歸家,情好甚篤。久之,李體日羸。覺交接時吸取其精,與尋常夫婦不同。且十里以內之事,必先知之。心知爲狐,驅之無法。
一日,拉其友楊孝廉至三十里外,以情告之。楊曰:“我記《東醫寶鑑》中有治狐術一條,何不試之?”遂偕往琉璃廠,覓得是書,求東洋人譯而行之,女果涕泣去。
此事餘在西江謝蘊山太史家親見,楊孝廉爲餘言之,惜未問其《東醫寶鑑》中是何卷頁。
乩言
撫州太守陳太暉,未第時,在浙鄉試,向乩神問題,批雲:“具體而微。”
後中副車,方知所告者,非題也。有求對聯者,書“努力加餐飯,小心事友生”十字。問:“次句何出?”曰:“秀才讀時文,不能杜詩,可憐可笑。”陳方與友遊鑑湖觀蓮,乩問:“昨日鑑湖之遊樂乎?”有詠紅蓮者,以詩求和,乩上題雲:“紅衣落盡小姑忙,從此朝來葉亦香。莫惱韶光太匆迫,花開三日即爲長。”
雲門山氓有被鬼作鬧者,詣乩盤求救,乩書:“我不能救,請某村餘二太爺來救。”如其言,請餘二太爺至,餘向其家東北角厲聲曰:“你們要往四川也,該速去了!”空中應曰:“極是。”從此恨竟寂然。餘二太爺者,某村之學究也,問其所以驅鬼者是何言語,笑而不答。問乩,乩亦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