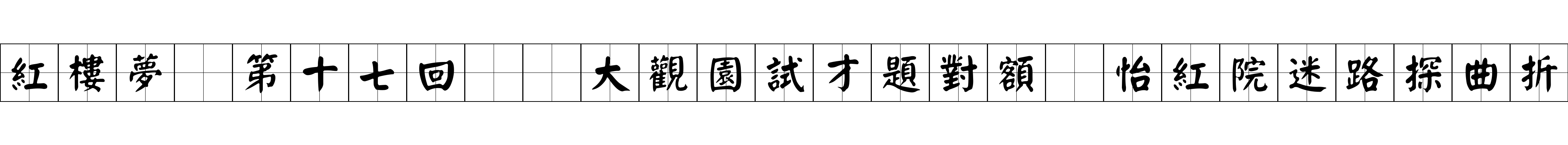紅樓夢-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怡紅院迷路探曲折-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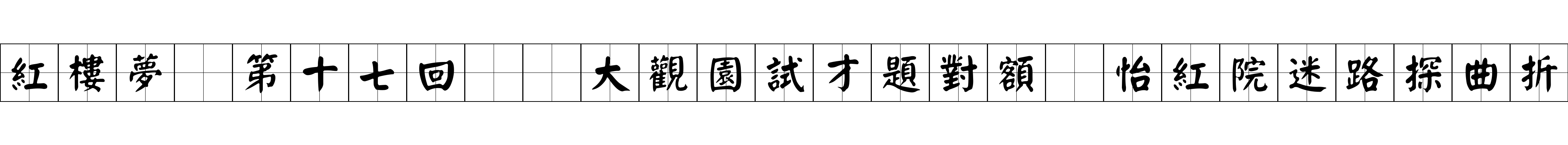
紅樓夢以錯綜複雜的清代上層貴族社會爲背景,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爲主線,通過對賈、史、王、薛四大家族榮衰的描寫,展示了18世紀上半葉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方方面面,囊括了多姿多彩的世俗人情,可謂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長篇小說。
詩曰:豪華雖足羨,離別卻難堪。博得虛名在,誰人識苦甘?
話說秦鍾既死,寶玉痛哭不已,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猶是悽惻哀痛。賈母幫了幾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寶玉去弔紙。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述記。只有寶玉日日思慕感悼,然亦無可如何了。
又不知歷幾何時,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已瞧過了,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賈政聽了,沉思一回,說道:“這匾額對聯倒是一件難事。論理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睹其景,大約亦必不肯妄擬;若直待貴妃遊幸過再請題,偌大景緻,若干亭榭,無一字標題,也覺寥落無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旁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愚見:各處匾額對聯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名。如今且按其景緻,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出來,暫且做燈匾聯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聽了,笑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題了,若妥當便用;不妥當時,將雨村請來,令他再擬。”衆清客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於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於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疏了。縱擬了出來,不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花柳園亭生色。似不妥協,反沒意思。”衆清客笑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其長,優則存之,劣則刪之,未爲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逛。”說着起身,引衆人前往。
賈珍先去園中知會衆人。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鍾,憂戚不盡,賈母常命人帶他到新園中來戲耍。此時亦才進來,忽見賈珍走來,向他笑道:“你還不出去?老爺就來了。”寶玉聽了,帶着奶孃、小廝們,一溜煙就出園來。方轉過彎,頂頭賈政引着衆清客來了,躲之不及,只得一邊站了。賈政近因聞得塾掌稱讚寶玉專能對對聯,雖不喜讀書,偏倒有些歪才情似的,今日偶然撞見這機會,便命他跟來。寶玉只得隨往,尚不知何意。
賈政剛至園門前,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來,一旁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都關上,我們先瞧了外面再進去。”賈珍聽說,命人將門關了。賈政先秉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桶瓦泥鰍脊,那門欄窗槅,皆是細雕新鮮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羣牆,下面白石臺磯,鑿成西番草花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牆,下面虎皮石,隨勢砌去,果然不落富麗俗套,自是喜歡。遂命開門,只見迎面一帶翠嶂擋在前面。衆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衆人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想及此。”說着,往前一望,見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成斑,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徑。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徑游去,回來由那一邊出去,方可遍覽。”
說畢,命賈珍在前引導,自己扶了寶玉,逶迤進入山口。擡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衆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也有說該提“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爐”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止幾十個。原來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功業進益如何,只將些俗套來敷衍。寶玉亦料定此意。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擬來。寶玉道:“嘗聞古人有云:‘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況此處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是探景一進步耳。莫若直書‘曲徑通幽處’這句舊詩在上,倒還大方氣派。”衆人聽了,都讚道:“是極!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可謬獎。他年小,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再俟選擬。”
說着,進入石洞來。只見佳木蘢蔥,奇花閃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曲折瀉於石隙之中。再進數步,漸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清溪瀉雪,石磴穿雲,白石爲欄,環抱池沿,石橋之港,獸面銜吐,橋上有亭。賈政與諸人上了亭子,倚欄坐了,因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於水題方稱。依我拙裁,歐陽公之‘瀉出於兩峯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髯尋思,因擡頭見寶玉侍側,便笑命他也擬一個來。寶玉聽說,連忙回道:“老爺方纔所議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若亦用‘瀉’字,則覺不甚妥。況此處雖雲省親駐蹕別墅,亦當入於應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覺粗陋不雅。求再擬較此蘊籍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聽此論若何?方纔衆人編新,你又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來我聽。”寶玉道:“有用‘瀉玉’二字,則莫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賈政拈髯點頭不語。衆人都忙迎合,贊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對聯來。”寶玉聽說,立於亭上,四顧一望,便機上心來,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
賈政聽了,點頭微笑。衆人先稱讚不已。
於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觀覽。忽擡頭看見前面一帶粉垣,裏面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個所在!”於是大家進入,只見入門便是曲折遊廊,階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一明兩暗,裏面都是合着地步打就的牀杌椅案。從裏間房內又得一小門,出去則是後院,有大株梨花兼着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牆下;忽開一隙,得泉一派,開溝僅尺許,灌入牆內,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
賈政笑道:“這一處倒還罷了。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不枉虛生一世。”說畢,看着寶玉,唬得寶玉忙垂了頭。衆客忙用話開釋,又說道:“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問:“哪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又一個是“睢園雅跡”。賈政道:“也俗。”賈珍笑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來。”賈政道:“他未曾作,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就是個輕薄人。”衆客道:“議論得極是,其奈他何?”賈政忙道:“休如此縱了他。”因命他道:“今日任你狂爲亂道,先設議論來,然後方許你作。方纔衆人說的,可有使得的?”寶玉見問,便道:“都似不妥。”賈政冷笑道:“怎麼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處,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作。”賈政道:“難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腐了。莫若‘有鳳來儀’四字。”衆人都鬨然叫妙。賈政點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來。”寶玉便念道:
寶鼎茶閒煙尚綠,幽窗棋罷指猶涼。
賈政搖頭說道:“也未見長。”說畢,引衆人出來。
方欲走時,忽又想起一事來,因問賈珍道:“這些院落房宇並几案桌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的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麼?”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臨期自然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準尺寸,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命人去喚賈璉。
一時,賈璉趕來,賈政問他共有幾種,現今得了幾種,尚欠幾種。賈璉見問,忙向靴桶取靴掖內裝的一個紙折略節來,看了一看,回道:“妝蟒繡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綢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湘妃竹簾二百掛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日俱得了。外有猩猩氈簾二百掛,金絲藤紅漆竹簾二百掛,墨漆竹簾二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圍、牀裙、桌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
一面說,一面走,倏爾青山斜阻。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築就矮牆,牆頭皆中稻莖掩護。有幾百株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裏面數楹茅屋。外面卻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稚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漫然無際。
賈政笑道:“倒是此處有些道理。固然系人力穿鑿,此時一見,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說畢,方欲進籬門去,忽見路旁有一石碣,亦爲留題之備。衆人笑道:“更妙,更妙!此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又覺生色許多,非範石湖田家之詠不足以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衆人道:“方纔世兄有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妙極,”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妙極,只是還少一個酒幌。明日竟作一個,不必華麗,就依外面村莊的式樣作來,用竹竿挑在樹梢。”賈珍答應了,又回道:“此處竟還不可養別的雀鳥,只是買些鵝、鴨、雞類,才都相稱了。”賈政與衆人都道:“更妙。”賈政又向衆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請名方可。”衆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便是什麼字樣好?”
大家想着,寶玉卻等不得了,也不等賈政的命,便說道:“舊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旗’。如今莫若‘杏簾在望’四字。”衆人都道:“好個‘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寶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就用‘稻香村’的妙?”衆人聽了,亦發哄聲拍手道:“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業障!你能知道幾個古人,能記得幾首熟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你方纔那些胡說的,不過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
說着,引人步入茆堂,裏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喜歡,卻瞅寶玉道︰“此處如何?”衆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矣。”賈政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爲佳,哪裏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得固是,但古人常雲‘天然’二字,不知何意?”
衆人見寶玉牛心,都怪他呆癡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別的都明白,如何連‘天然’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寶玉道:“卻又來!此處置一田莊,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於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爲地,非其山而強爲山,雖百般精而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得喝命:“叉出去!”剛出去,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浣葛處,好雲香護採芹人。
賈政聽了,搖頭說:“更不好。”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荼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湲,瀉出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衆人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衆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個字。”賈政笑道:“又落實了,而且陳舊。”衆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了。”寶玉道:“這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漵’四字。”賈政聽了,更批胡說。
於是要進港洞時,又想起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隻,座船一隻,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山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蕩蕩,曲折縈迂。池邊兩行垂柳,雜着桃杏,遮天蔽日,真無一些塵土。忽見桃柳中又露出一個條折帶朱欄板橋來,度過橋去,諸路可通,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
賈政道:“此處這所房子,無味得很。”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羣繞各式石塊,竟把裏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而且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隙,甚至垂檐繞柱,縈砌盤階,或如翠帶飄颻,或如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比。賈政不禁笑道:“有趣!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不得如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些之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茞蘭,這一種大約是清葛,那一種是金簦草,這一種是玉蕗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是青芷。想來《離騷》《文選》等書上所有的那些異草,也有叫作什麼藿納姜蕁的,也有叫作什麼綸組紫絳的,還有石帆、水鬆、扶留等樣,又有叫什麼綠荑的,還有什麼丹椒、蘼蕪、風連。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象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唬得寶玉倒退,不敢再說。
賈政因見兩邊俱是超手遊廊,便順着遊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連着捲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更比前幾處清雅不同。賈政嘆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此造已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再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若何?”一人道:“我倒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念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詩云‘蘼蕪滿院泣斜暉’。”衆人道:“頹喪,頹喪!”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因念道:
三徑香風飄玉蕙,一庭明月照金蘭。
賈政拈髯沉音,意欲也題一聯。忽擡頭見寶玉在旁不敢則聲,因喝道:“怎麼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說,便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着跡說起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着你的頭,叫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寶玉道:“如此說,匾上則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荳蔻才猶豔,睡足酴醾夢也香。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爲奇。”衆客道:“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黃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猶覺幽嫺活潑。視‘書成’之句,竟似套此而來。”賈政笑說:“豈有此理!”
說着,大家出來。行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峨,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檐,玉欄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節尚儉,天性惡繁悅樸,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爲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來,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倒像那裏曾見過的一般,卻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賈政又命他作題,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於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的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考難逼迫,着了急,或生出事來,倒不便。遂忙都勸賈政:“罷,罷,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若再不能,我定不饒。這是要緊一處,更要好生作來!”
說着,引人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起,所行至此,才遊了十之五六。又值人來回,有雨村處遣人來回話。賈政笑道:“此數處不能遊了。雖如此,到底從那一邊出去,縱不能細觀,也可稍覽。”說着,引客行來,至一大橋前,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賈政因問:“此閘何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泉之正源,就名‘沁芳閘’。”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
於是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爲垣,或編花爲牖;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因說半日腿痠,未嘗歇息。忽又見前面又露出一所院落來,賈政笑道:“到此可要進去歇息歇息了。”說着,一徑引人繞着碧桃花,穿過一層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俄見粉牆環護,綠柳周垂。賈政與衆人進去,一入門,兩邊俱是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幾塊山石,一邊種着數本芭蕉,那一邊乃是一棵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縷,葩吐丹砂。衆人讚道:“好花,好花!從來也見過許多海棠,哪裏有這樣妙的。”賈政道:“這叫作‘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系出‘女兒國’中,雲彼國此種最盛,亦荒唐不經之說罷了。”衆人笑道:“然雖不經,如何此名傳久了?”寶玉道:“大約騷人詠士,以此花之色紅暈若施脂,輕弱似扶病,大近乎閨閣風度,所以以‘女兒’命名。想因被世間俗惡聽了,他便以野史纂入爲證,以俗傳俗,以訛傳訛,都認真了。”衆人都搖身贊妙。
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外抱廈下打就的榻上坐了。賈政因問:“想幾個什麼新鮮字來題此?”一客道:‘蕉鶴’二字最妙。“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寶玉也道:”妙極!“又嘆:”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寶玉道:”‘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內。若只說蕉,則棠無着落;若只說棠,蕉亦無着落。固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妙。“賈政搖頭道:”不好,不好!“
說着,引人進入房內。只見這幾間房內收拾得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卍福卍壽,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寶的。一槅一槅,或有貯書處,或有設鼎處,或安置筆硯處,或供花設瓶、安放盆景處。其槅各式各樣,或天圓地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璧。真是花團錦簇,剔透玲瓏。倏爾五色紗糊就,竟系小窗;倏爾彩凌輕覆,竟系幽戶。且滿牆滿壁,皆系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諸如琴、劍、懸瓶、桌屏之類,雖懸於壁,卻都是與壁相平的。衆人都贊:“好精緻想頭!難爲怎麼想來!”
原來賈政等走了進來,未進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又有窗暫隔,及到了跟前,又被一架書擋住。回頭再走,又有窗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羣人,都與自己形相一樣,卻是一架玻璃大鏡相照。及轉過鏡去,越發見門子多了。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這門出去,便是後院;從後院出去,倒比先近了。”說着,又轉了兩層紗櫥錦槅,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寶相。轉過花障,則見青溪前阻。衆人吒異:“這股水又是從何而來?”賈珍遙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坳裏引到那村莊裏,又開一道岔口,引到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裏,仍舊合在一處,從那牆下出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道“迷了路了。”賈珍笑道:“隨我來。”仍在前導引,衆人隨他直由山腳邊忽一轉,便是平坦寬闊大路,豁然大門前現。衆人都道:“有趣,有趣,真搜神奪巧之至!”於是大家出來。
那寶玉一心只記掛着裏邊,又不見賈政吩咐,少不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他來,方喝道:“你還不去?難道還逛不足!也不想逛了這半日,老太太必懸掛着。快進去,疼你也白疼了!”寶玉聽說,方退了出來。再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