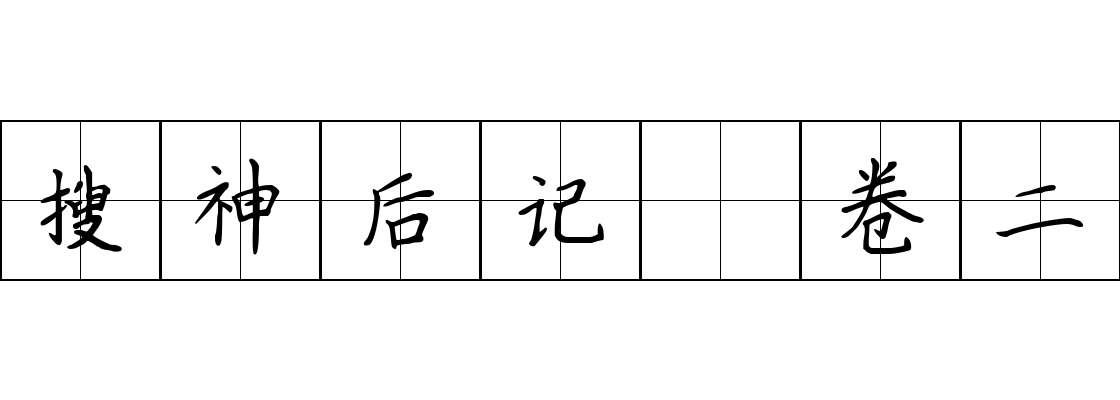搜神后记-卷二-相关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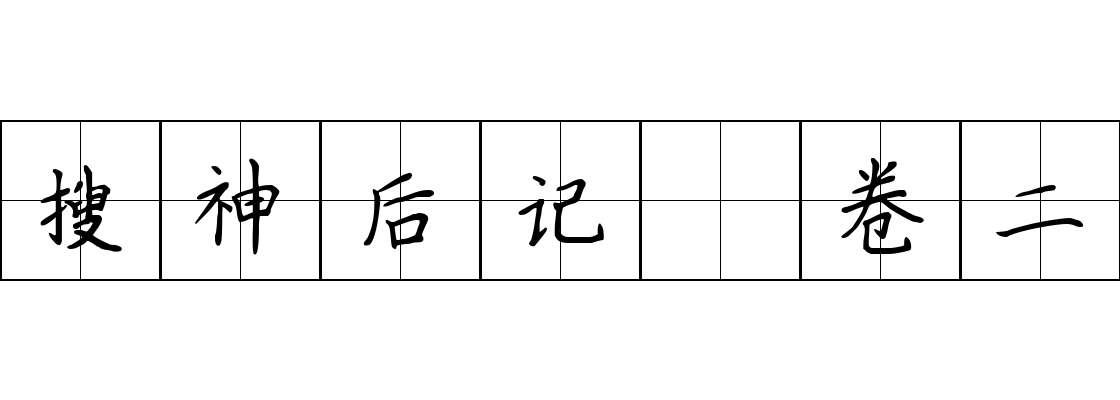
《搜神后记》又名《续搜神记》,是《搜神记》的续书。题为东晋陶潜(365-427)撰。所记有元嘉十四年(437年)、十六年(439年)事,其伪不可待辩。皆陶潜死后事,故疑此书为伪托,或以为经后人增益。《搜神后记》与《搜神记》的体例大致相似,但内容则多为《搜神记》所未见。该书凡十卷,一百一十七条。《搜神后记》在魏晋南北朝的志怪群书中是颇具特色的。它内容上略为妖异变怪之谈,而多言神仙;艺术上是芜杂琐碎的记叙减少,成片的 有关当地风土的民间故事。
吴舍人名猛,字世云,有道术。同县邹惠政迎猛,夜于家中庭烧香。忽有虎抱政儿超篱去。猛语云:“无所苦,须臾当还。“虎去数十步,忽然复送儿归。政遂精进,乞为好道士。猛性至孝,小儿时,在父母傍卧,时夏日多蚊虫,而终不摇扇。同宿人觉,问其故,答云:“惧蚊虫去啮我父母尔。“及父母终,行伏墓次。蜀贼纵暴,焚烧邑屋,发掘坟垅。民人迸窜。猛在墓侧,号恸不去。贼为之感怆,遂不犯。 谢允从武当山还,在桓宣武座,有言及左元放为曹公致鲈鱼者,允便云:“此可得尔。“求大瓮盛水,朱书符投水中。俄有一鲤鱼鼓鳍水中。 钱塘杜子恭,有秘术。尝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当即相还耳。“既而刀主行至嘉兴,有鱼跃入船中。破鱼腹,得瓜刀。
太兴中,衡阳区纯作鼠市:四方丈余,开四门,门有一木人。纵四五鼠于中,欲出门,木人辄以手推之。
晋大司马桓温,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来自远方,投温为檀越。尼才行不恒,愠甚敬待,居之门内。尼每浴,必至移时。温疑而窥之。见尼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支分脔切。温怪骇而还。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温以实问,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当如之。“时温方谋问鼎,闻之怅然。故以戒惧,终守臣节。尼后辞去,不知所在。 沛国有一士人,姓周,同生三子,年将弱冠,皆有声无言。忽有一客从门过,因乞饮,闻其儿声,问之曰:“此是何声?“答曰:“是仆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还内省过,何以至此?“主人异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忆有罪过。“客曰:“试更思幼时事。“入内,食顷,出语客曰:“记小儿时,当床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从外得食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积日如此。试以指内巢中,燕雏亦出口承受。因取三蔷茨,各与食之。既而皆死。母还,不见子,悲鸣而去。昔有此事,今实悔之。“客闻言,遂变为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言讫,便闻其子言语。周亦忽不见此道人。
天竺人佛图澄,永嘉四年来洛阳,善诵神咒,役使鬼神。腹傍有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读书,则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平旦,至流水侧,从孔中引出五脏六腑洗之,讫,还内腹中。 石虎邺中有一胡道人,知咒术。乘驴作估客,于外国深山中行。下有绝涧,窅然无底。忽有恶鬼,偷牵此道人驴,下入绝涧。道人寻迹咒誓,呼诸鬼王。须臾,即驴、物如故。
昙游道人,清苦沙门也。剡县有一家事蛊,人啖其食饮,无不吐血死。游尝诣之。主人下食,游依常咒愿。双蜈蚣,长尺余,便于盘中跳走。游便饱食而归,安然无他。 高悝家有鬼怪,言词呵叱,投掷内外,不见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发火。巫祝厌劾而不能绝。适值幸灵,乃要之。至门,见符索甚多,并取焚之。惟据轩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绝。 赵固常乘一匹赤马以战征,甚所爱重。常系所住斋前,忽腹胀,少时死。郭璞从北过,因往诣之。门吏云:“将军好马,甚爱惜。今死,甚懊惋。“璞便语门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马,则必见我。“门吏闻之惊喜,即启固。固踊跃,令门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温,便问:“卿能活我马乎?“璞曰:“我可活尔。“固欣喜,即问:“须何方术?“璞云:“得卿同心健儿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于此东行三十里,当有邱陵林树,状若社庙。有此者,便当以竹竿搅扰打拍之。当得一物,便急持归。既得此物,马便活矣。“于是左右骁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丛林,有一物似猴而飞走。众勇共逐得,便抱持归。此物遥见死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马头间,嘘吸其鼻。良久,马起,喷奋奔迅,便不见此物。固厚赀给,璞得过江左。
王文献曾令郭璞筮己一年吉凶,璞曰:“当有小不吉利。可取广州二大罂,盛水,置床张二角,名曰 ’镜好 ’,以厌之。至某时,撤罂去水。如此其灾可消。“至日忘之。寻失铜镜,不知所在。后撤去水,乃见所失镜在于罂中。罂口数寸,镜大尺余。王公复令璞筮镜罂之意。璞云:“撤罂违期,故致此妖。邪魅所为,无他故也。“使烧车辖,而镜立出。
中兴初,郭璞每自为卦,知其凶终。尝行经建康栅塘,逢一趋步少年,甚寒,便牵住,脱丝布袍与之。其人辞不受,璞曰:“但取,后自当知。“其人受而去。及当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为求属,璞曰:“我托之久矣。“此人为之歔欷哽咽。行刑既毕,此人乃说。 高平郗超,字嘉宾,年二十余,得重病。庐江杜不愆,少就外祖郭璞学易卜,颇有经验。超令试占之。卦成,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恙寻愈。然宜于东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养雄雉,笼而绊之,置东檐下,却后九日景午日午时,必当有野雌雉飞来,与交合。既毕,双飞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应,年将八十,位极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时正羸笃,虑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余矣。一周病差,何足为淹。“然未之信。或劝依其言索雄,果得。至景午日,超卧南轩之下观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飞入笼,与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动。超叹息曰:“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逾年乃起,至四十,卒于中书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