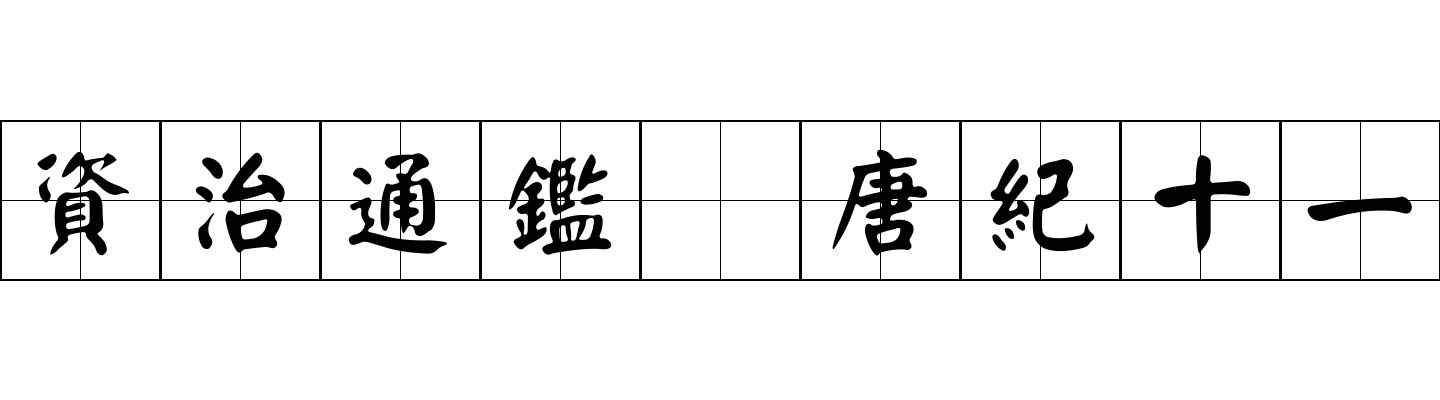資治通鑑-唐紀十一-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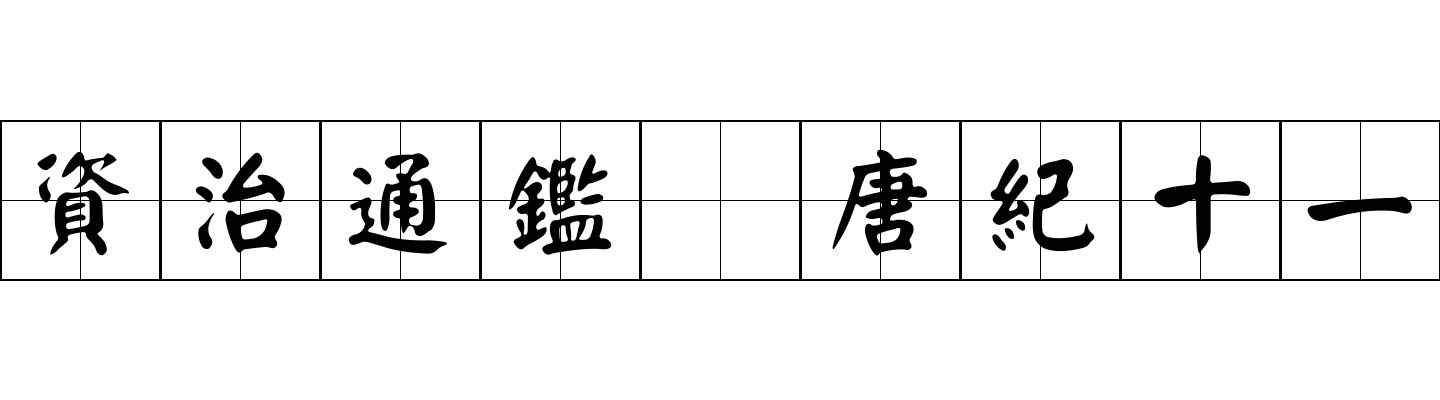
《資治通鑑》(常簡作《通鑑》),是由北宋史學家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共294卷,歷時十九年完成。主要以時間爲綱,事件爲目,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到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徵淮南停筆,涵蓋十六朝1362年的歷史。在這部書裏,編者總結出許多經驗教訓,供統治者借鑑,宋神宗認爲此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即以歷史的得失作爲鑑誡來加強統治,所以定名爲《資治通鑑》。
起強圉作噩五月,盡上章困敦,凡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上
貞觀十一年丁酉,公元六三七年
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強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鑑形莫如止水,鑑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鑑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六月,右僕射虞恭公溫彥博薨。彥博久掌機務,知無不爲。上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精神耗竭,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安逸,竟夭天年!”
丁巳,上幸明德宮。
己未,詔荊州都督荊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鹹令子孫世襲。戊辰,又以功臣長孫無忌等十四人爲刺史,亦令世襲,非有大故,無得黜免。己巳,徙許王元祥爲江王。
秋,七月,癸未,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
魏徵上疏,以爲:“《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奸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臺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乙未,車駕還洛陽,詔:“洛陽宮爲水所毀者,少加修繕,才令可居。自外衆材,給城中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壬寅,廢明德宮及飛山之玄圃院,給遭水者。
八月,甲子,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
侍御史馬週上疏,以爲:“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向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夫昧爽丕顯,後世猶怠,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修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飢歉,鬥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諮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諸王,但無縲紲耳。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冬,十月,癸丑,詔勳戚亡者皆陪葬山陵。
上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尋加光祿大夫。
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戶三百。上曰:“長史權萬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柳範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畋獵,豈得獨罪萬紀!”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
十一月,辛卯,上幸懷州;丙午,還洛陽宮。
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爲才人。
貞觀十二年戊戌,公元六三八年
春,正月,乙未,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已上遇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苟自崇貴,輕我諸子。”特進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爲王降乘,誠非所宜當。”上曰:“人生壽夭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他日不爲公輩之主!何得輕之!”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此爲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
吏部尚書高士廉、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葇、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雖累葉陵夷,苟他族欲與爲昏姻,必多責財幣,或舍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惡之,命士廉等遍責天下譜諜,質諸史籍,考其真僞,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奸逆,分爲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爲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爲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纔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卬然以門地自負,販鬻鬆檟,依託富貴,棄廉忘恥,不知世人何爲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勳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彼衰世舊門,誠何足慕!而求與爲昏,雖多輸金帛,猶爲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釐正訛謬,舍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爲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爲高下。於是以皇族爲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爲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
二月,乙卯,車駕西還;癸亥,幸河北,觀砥柱。
甲子,巫州獠反,夔州都督齊善行敗之,俘男女三千餘口。
乙丑,上祀禹廟。丁卯,至柳谷,觀鹽池。庚午,至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車駕,盛飾廨舍樓觀,又飼羊百餘口、魚數百頭以饋貴戚。上數之曰:“朕巡省河、洛,凡有所須,皆資庫物。卿所爲乃亡隋之弊俗也。”甲戌,幸長春宮。
戊寅,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閏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丁未,車駕至京師。
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爲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爲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遂不許。
丙子,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雲:‘賞太厚。’陛下雲:‘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夏,五月,壬申,弘文館學士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卒,上哭之慟。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
秋,七月,癸酉,以吏部尚書高士廉爲右僕射。
乙亥,吐蕃寇弘州。
八月,霸州山獠反,燒殺刺史向邵陵及吏民百餘家。
初,上遣使者馮德遐撫慰吐蕃,吐蕃聞突厥、吐谷渾皆尚公主,遣使隨德遐入朝,多齎金寶,奉表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棄宗弄贊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許尚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間,唐禮遂衰,亦不許婚。”弄贊遂發兵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爲吐蕃所掠。
吐蕃進破党項、白蘭諸羌,帥衆二十餘萬屯鬆州西境,遣使貢金帛,雲來迎公主。尋進攻鬆州,敗都督韓威;羌酋閻州刺史別叢臥施、諾州刺史把利步利並以州叛歸之。連兵不息,其大臣諫不聽而自縊者凡八輩。壬寅,以吏部尚書侯君集爲當彌道行軍大總管,甲辰,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爲白蘭道、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爲闊水道、左領軍將軍劉簡爲洮河道行軍總管,督步騎五萬擊之。
吐蕃攻城十餘日,進達爲先鋒,九月,辛亥,掩其不備,敗吐蕃於鬆州城下,斬首千餘級。弄贊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
甲寅,上問侍臣:“帝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初,突厥頡利既亡,北方空虛,薛延陀真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於都尉犍山北、獨邏水南,勝兵二十萬,立其二子拔酌、頡利苾主南、北部。上以其強盛,恐後難制,癸亥,拜其二子皆爲小可汗,各賜鼓纛,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冬,十月,乙亥,巴州獠反。
己卯,畋於始平;乙未,還京師。
鈞州獠反;遣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十一月,丁未,初置左、右屯營飛騎於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百騎,衣五色袍,乘駿馬,以虎皮爲韉,凡遊幸則從焉。
己巳,明州獠反;遣交州都督李道彥討平之。
十二月,辛巳,左武候將軍上官懷仁擊反獠於壁州,大破之,虜男女萬餘口。
是歲,以給事中馬周爲中書舍人。周有機辯,中書侍郎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榷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霍王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爲徐州刺史,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夫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吾何以稱其長哉!”
初,西突厥咥利失可汗分其國爲十部,每部有酋長一人,仍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啜,居碎葉以東;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居碎葉以西;通謂之十姓。咥利失失衆心,爲其臣統吐屯所襲。咥利失兵敗,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耆。統吐屯等將立欲谷設爲大可汁,會統吐屯爲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咥利失復得故地。至是,西部竟立欲谷設爲乙毘咄陸可汗。乙毘咄陸既立,與咥利失大戰,殺傷甚衆。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屬乙咄陸,以東屬咥利失。
處月、處密與高昌共攻拔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廬舍而去。
貞觀十三年己亥,公元六三九年
春,正月,乙巳,車駕謁獻陵;丁未,還宮。
戊午,加左僕射房玄齡太子少師。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男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女爲韓王妃,深畏滿盈,上表請解機務;上不許。玄齡固請不已,詔斷表,乃就職。太子欲拜玄齡,設儀衛待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支系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禮部尚書永寧懿公王珪薨。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於今,三品已上皆立家廟,珪通貴已久,獨祭於寢。爲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爲之立廟以愧之。
二月,庚辰,以光祿大夫尉遲敬德爲鄜州都督。
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爲之流涕,曰:“卿復服,朕不疑卿,故語卿,何更恨邪!”
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上乃止。
戊戌,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良家有才行者充,以禮聘納;其沒官口及素微賤之人,皆不得補用。”上從之。
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爲:“堯、舜之父,猶有硃、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
會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春冰;宗戚憂虞,如置湯火。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兩漢罷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剿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詔停世封刺史。
高昌王麴文泰多遏絕西域朝貢,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內屬,文泰與西突厥共擊之。上下書切責,徵其大臣阿史那矩,欲與議事,文泰不遣,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頡利之亡也,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詔文泰歸之,文泰蔽匿不遣。又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問狀,且謂其使者曰:“高昌數年以來,朝貢脫略,無籓臣禮,所置官號,皆準天朝,築城掘溝,預備攻討。我使者至彼,文泰語之雲:‘鷹飛於天,雉伏於蒿,貓遊於堂,鼠噍於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又遣使謂薛延陀雲:‘既爲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爲拜其使者!’事人無禮,又間鄰國,爲惡不誅,善何以勸!明年當發兵擊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報,請發所部爲軍導以擊高昌。”上遣民部尚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齎繒帛賜薛延陀,與謀進取。
夏,四月,戊寅,上幸九成宮。
初,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從突利入朝,歷位中郎將。居家無賴,怨突利斥之,乃誣告其謀反,上由是薄之,久不進秩。結社率陰結故部落,得四十餘人,謀因晉王治四鼓出宮,開門闢仗,馳入宮門,直指御帳,可有大功。甲申,擁突利之子賀邏鶻夜伏於宮外,會大風,晉王未出,結社率恐曉,遂犯行宮,逾四重幕,弓矢亂髮,衛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廄,盜馬二十餘匹,北走,度渭,欲奔其部落,追獲,斬之,原賀邏鶻投於嶺表。
庚寅,遣武候將軍上官懷仁擊巴、壁、洋、集四州反獠,平之,虜男女六千餘口。
五月,旱。甲寅,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爲:“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雲:‘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上深加獎嘆,雲:“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並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廄馬二匹。
六月,渝州人侯弘仁自牂柯開道,經西趙,出邕州,以通交、桂,蠻、俚降者二萬八千餘戶。
丙申,立皇弟元嬰爲滕王。
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雲突厥留河南不便,秋,七月,庚戌,詔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還其舊部,俾世作籓屏,長保邊塞。突厥鹹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言“頡利既敗,其部落鹹來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爲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畜,恆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於河南,任其畜牧。今戶口蕃滋,吾心甚喜。既許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將遣突厥渡河,復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突厥受冊在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鎮撫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各問其罪。”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上御齊政殿餞之,思摩涕泣,奉觴上壽曰:“奴等破亡之餘,分爲灰壤,陛下存其骸骨,復立爲可汗,願萬世子孫恆事陛下。”又遣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就其種落,築壇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熟爲右賢王。忠,蘇尼失之子也,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及出塞,懷慕中國,見使者必泣涕請入侍;詔許之。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詔以“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比來訴訟者或自毀耳目,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後依法。”
冬,十月,甲申,車駕還京師。
十一月,辛亥,以侍中楊師道爲中書令。
戊辰,尚書左丞劉洎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上猶冀高昌王文泰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十二月,壬申,遣交河行軍大總管、吏部尚書侯君集,副總管兼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等將兵擊之。
乙亥,立皇子福爲趙王。
己丑,吐谷渾王諾曷鉢來朝,以宗女爲弘化公主,妻之。
壬辰,上畋於咸陽,癸巳,還宮。
太子承乾頗以遊畋廢學,右庶子張玄素諫,不聽。
是歲,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一十一。
太史令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善咒術,能令人立死,復咒之使蘇。上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爲物所擊,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時臥疾,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時年八十五。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西突厥咥利失可汗之臣俟利發與乙毘咄陸可汗通謀作亂,咥利失窮蹙,逃奔汗而死。弩失畢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爲乙毘沙鉢羅葉護可汗。沙鉢羅葉護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附之。咄陸建牙於鏃曷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燖、觸水昆等國皆附之,以伊列水爲境。
貞觀十四年庚子,公元六四零年
春,正月,甲寅,上幸魏王泰第,赦雍州長安繫囚大辟以下,免延康裏今年租賦,賜泰府僚屬及同里老人有差。
二月,丁丑,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壬午,上幸驪山溫湯;辛卯,還宮。
乙未,詔求近世名儒梁皇甫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以聞,當加引擢。
三月,竇州道行軍總管黨仁弘擊羅竇反獠,破之,俘七千餘口。
辛丑,流鬼國遣使入貢。去京師萬五千裏,濱於北海,南鄰靺鞨,未嘗通中國,重三譯而來。上以其使者佘志爲騎都尉。
丙辰,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
夏,五月,壬寅,徙燕王靈夔爲魯王。
上將幸洛陽,命將作大匠閻立德行清暑之地。秋,八月,庚午,作襄城宮於汝州西山。立德,立本之兄也。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裏,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今來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三萬已下,吾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弊。若頓兵城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爲,發疾卒,子智盛立。
軍至柳谷,詗者言文泰刻日將葬,國人鹹集於彼,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諭之,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將辛獠兒爲前鋒,夜,趨其都城,高昌逆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
智盛致書於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襲位未幾,惟尚書憐察。”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君集命填塹攻之,飛石雨下,城中人皆室處。又爲巢車,高十丈,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飛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約有急相助;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爲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裏,葉護以城降。智盛窮蹙,癸酉,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
上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上不從,九月,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各置屬縣,乙卯,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
君集虜高昌王智盛及其羣臣豪傑而還。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侯君集之討高昌也,遣使約焉耆與之合勢,焉耆喜,聽命。及高昌破,焉耆王詣軍門謁見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爲高昌所奪,君集奏並高昌所掠焉耆民悉歸之。
冬,十月,甲戌,荊王元景等復表請封禪,上不許。
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尉氏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命斬之,怒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衝!”命追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強而陵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上悅,擢仁軌爲櫟陽丞。
上將幸同州校獵,仁軌上言:“今秋大稔,民收穫者才一二,使之供承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功,實妨農事。願少停鑾輿旬日,俟其畢務,則公私俱濟。”上賜璽書嘉納之,尋遷新安令。閏月,乙未,行幸同州;庚戌,還宮。
丙辰,吐蕃贊普遣其相祿東贊獻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婚。上許以文成公主妻之。
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上祀南郊。時《戊寅歷》以癸亥爲朔,宣義郎李淳風表稱:“古歷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爲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衆議以仁均定朔微差,淳風推校精密,請如淳風議,從之。
丁卯,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丙子,百官復表請封禪,詔許之。更命諸儒詳定儀注;以太常卿韋挺等爲封禪使。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給使過所稽緩,給使奏之;上怒,出元方爲華陰令。魏徵諫曰:“帝王震怒,不可妄發。前爲給使,遂夜出敕書,事如軍機,誰不驚駭!況宦者之徒,古來難養,輕爲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所宜深慎。”上納其言。
尚書左丞韋悰句司農木橦價貴於民間,奏其隱沒。上召大理卿孫伏伽書司農罪。伏伽曰:“司農無罪。”上怪,問其故,對曰:“只爲官橦貴,所以私橦賤。向使官橦賤,私橦無由賤矣。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上悟,屢稱其善;顧謂韋悰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
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獻俘於觀德殿。行飲至禮,大酺三日。尋以智盛爲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付太常,增九部樂爲十部。
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爲盜竊,君集不能禁,爲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爲:“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逾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掛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浚,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鹹受封賞。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
又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內出高昌婦女付大理,與萬均對辯,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辯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釋之。
侯君集馬病蚛顙,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沾其膿而嗅之,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括州刺史。
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以無敕旨,獨不受,及別敕既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及雜彩千段賜之。
癸卯,上獵於樊川;乙巳,還宮。
魏徵上疏,以爲:“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僞成俗矣。”上納之。
上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福也!”
上聞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宮中擊鼓,玄素叩閣切諫;太子出其鼓,對玄素毀之。太子久不出見官屬,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且宮中唯有婦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太子不聽。
玄素少爲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何官?”對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恥之,出閣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恥,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遂良,亮之子也。孫伏伽與玄素在隋皆爲令史,伏伽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御史劾之。上曰:“昔唐、虞大聖,貴爲天子,不能化其子;況崇爲刺史,獨能使其民比屋爲善乎!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相掩蔽,縱舍罪人。自今諸州有犯十惡者,勿劾刺史,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庶以肅清奸惡耳。”
上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
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