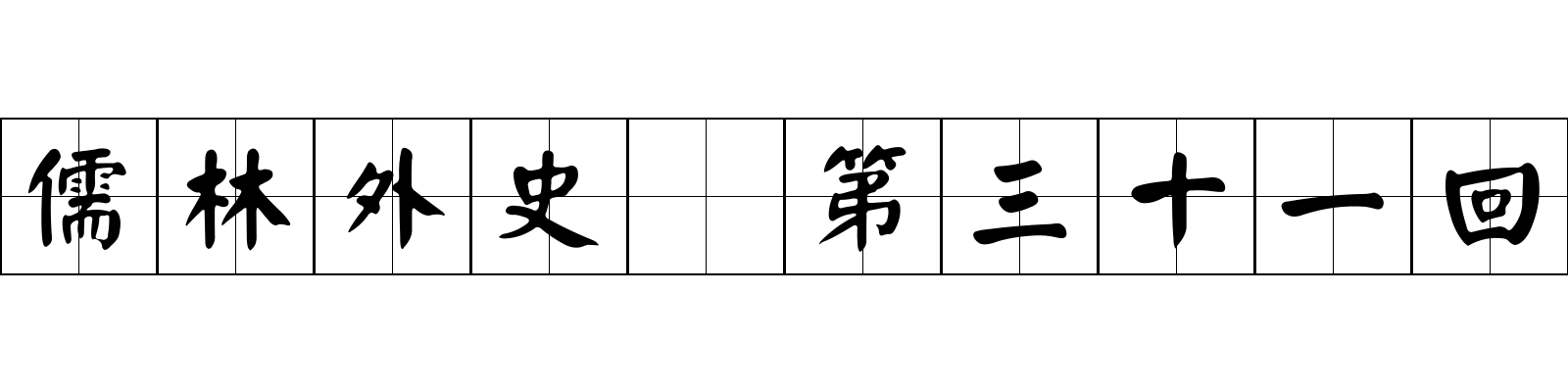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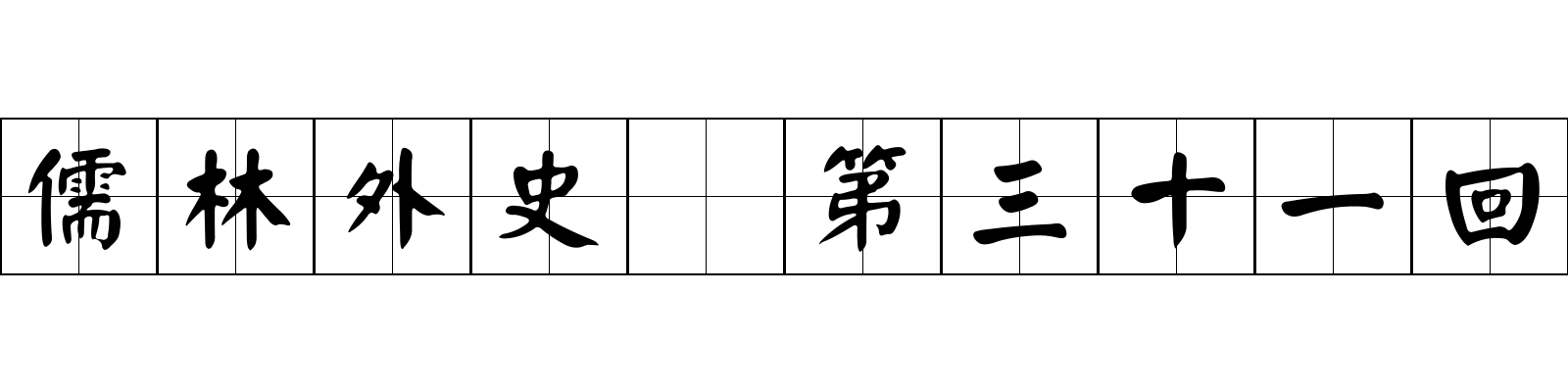
《儒林外史》,長篇小說,清代吳敬梓作。五十六回。成書於1749年(乾隆十四年)或稍前,先以抄本傳世,初刻於1803年(嘉慶八年)。以寫實主義描繪各類人士對於“功名富貴”的不同表現,一方面真實的揭示人性被腐蝕的過程和原因,從而對當時吏治的腐敗、科舉的弊端禮教的虛僞等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諷;一方面熱情地歌頌了少數人物以堅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對於人性的守護,從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該書代表着中國古代諷刺小說的高峯,它開創了以小說直接評價現實生活的範例。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樓大醉高朋
話說杜慎卿做了這個大會,鮑廷璽看見他用了許多的銀子,心裏驚了一驚,暗想:“他這人慷慨,我何不取個便,問他借幾百兩銀子,仍舊團起一個班子來做生意過日子?”主意已定,每日在河房裏效勞。杜慎卿着實不過意。他那日晚間談到密處,夜已深了,小廝們多不在眼前。慎卿問道:“鮑師父,你畢竟家裏日子怎麼樣過?還該尋個生意纔好。”鮑廷璽見他問到這一句話,就雙膝跪在地下。杜慎卿就嚇了一跳,扶他起來,說道:“這是怎的?”鮑廷璽道:“我在老爺門下,蒙老爺問到這一句話,真乃天高地厚之恩;但門下原是教班子弄行頭出身,除了這事,不會做第二樣。如今老爺照看門下,除非懇恩借出幾百兩銀子,仍舊與門下做這戲行。門下尋了錢,少不得報效老爺。”杜慎卿道:“這也容易。你請坐下,我同你商議。這教班子弄行頭,不是數百金做得來的,至少也得千金。這裏也無外人,我不瞞你說,我家雖有幾千現銀子,我卻收着不敢動。爲甚麼不敢動?我就在這一兩年內要中,中了那裏沒有使喚處?我卻要留着做這一件事。而今你弄班子的話,我轉說出一個人來與你,也只當是我幫你一般。你卻不可說是我說的。”鮑廷璽道:“除了老爺,那裏還有這一個人?”杜慎卿道:“莫慌。你聽我說。我家共是七大房。這做禮部尚書的太老爺是我五房的。七房的太老爺是中過狀元的。後來一位大老爺,做江西贛州府知府,這是我的伯父。贛州府的兒子是我第二十五個兄弟,他名叫做儀,號叫做少卿,只小得我兩歲,也是一個秀才。我那伯父是個清官,家裏還是祖宗丟下的些田地。伯父去世之後,他不上一萬銀子傢俬,他是個呆子,自己就像十幾萬的。紋銀九七,他都認不得。又最好做大老官。聽見人向他說些苦,他就大捧出來給人家用。而今你在這裏幫我些時,到秋涼些,我送你些盤纏,投奔他去。包你這千把銀子手到拿來。”鮑廷璽道:“到那時候,求老爺寫個書子與門下去。”杜慎卿道:“不相干。這書斷然寫不得。他做大老官是要獨做,自照顧人,並不要人幫着照顧。我若寫了書子,他說我已經照顧了你,他就賭氣不照顧你了。如今去先投奔一個人。”鮑廷璽道:“卻又投那一個?”杜慎卿道:“他家當初有個奶公老管家,姓邵的,這人你也該認得。”鮑廷璽想起來道:“是那年門下父親在日,他家接過我的戲去與老太太做生日。贛州府太老爺,門下也曾見過。”杜慎卿道:“這就是得狠了。如今這邵奶公已死。他家有個管家王鬍子,是個壞不過的奴才,他偏生聽信他。我這兄弟有個毛病:但凡說是見過他家太老爺的,就是一條狗也是敬重的。你將來先去會了王鬍子。這奴才好酒,你買些酒與他喫,叫他在主子眼前說你是太老爺極歡喜的人,他就連三的給你銀子用了。他不歡喜人叫他老爺,你只叫他少爺。他又有個毛病:不喜歡人在他跟前說人做官,說人有錢。像你受向太老爺的恩惠這些話,總不要在他跟前說。總說天下只有他一個人是大老官,肯照顧人。他若是問你可認得我,你也說不認得。”一番話,說得鮑廷璽滿心歡喜。在這裏又效了兩個月勞,到七月盡間,天氣涼爽起來,鮑廷璽問十七老爺借了幾兩銀子,收拾衣服行李,過江往天長進發。
第一日過江,歇了六合縣。第二日起早走了幾十里路,到了一個地方,叫作四號墩。鮑廷璽進去坐下,正待要水洗臉,只見門口落下一乘轎子來。轎子裏走出一個老者來,頭戴方巾,身穿白紗直裰,腳下大紅紬鞋,一個通紅的酒糟鼻,一部大白鬍須,就如銀絲一般。那老者走進店門,店主人慌忙接了行李,說道:“韋四太爺來了?請裏面坐。”那韋四太爺走進堂屋,鮑廷璽立起身來施禮。那韋四太爺還了禮。鮑廷璽讓韋四太爺上面坐,他坐在下面,問道:“老太爺上姓是韋,不敢拜問貴處是那裏?”韋四太爺道:“賤姓韋,敝處滁州烏衣鎮。長兄尊姓貴處?今往那裏去的?”鮑廷璽道:“在下姓鮑,是南京人。今往天長杜狀元府裏去的,看杜少爺。”韋四太爺道:“是那一位?是慎卿?是少卿?”鮑廷璽道:“是少卿。”韋四太爺道:“他家兄弟雖有六七十個,只有這兩個人招接四方賓客;其餘的都閉了門在家,守着田園做舉業。我所以一見就問這兩個人。兩個都是大江南北有名的。慎卿雖是雅人,我還嫌他有帶着些姑娘氣。少卿是個豪傑,我也是到他家去的,和你長兄吃了飯一同走。”鮑廷璽道:“太爺和杜府是親戚?”韋四太爺道:“我同他家做贛州府太老爺自小同學拜盟的,極相好的。”鮑廷璽聽了,更加敬重。
當時同吃了飯,韋四太爺上轎。鮑廷璽又僱了一個驢子,騎上同行。到了天長縣城門口,韋四太爺落下轎,說道:“鮑兄,我和你一同走進府裏去罷。”鮑廷璽道:“請太爺上轎先行。在下還要會過他管家,再去見少爺。”韋四太爺道:“也罷。”上了轎子,一直來到杜府,門上人傳了進去。杜少卿慌忙迎出來,請到廳上拜見,說道:“老伯,相別半載,不曾到得鎮上來請老伯和老伯母的安。老伯一向好?”韋四太爺道:“託庇粗安。新秋在家無事,想着尊府的花園,桂花一定盛開了,所以特來看看世兄,要杯酒喫。”杜少卿道:“奉過茶,請老伯到書房裏去坐。”小廝捧過茶來,杜少卿吩咐:“把韋四太爺行李請進來,送到書房裏去。轎錢付與他。轎子打發回去罷。”請韋四太爺從廳後一個走巷內,曲曲折折走進去,纔到一個花園。那花園一進朝東的三間。左邊一個樓,便是殿元公的賜書樓。樓前一個大院落,一座牡丹臺,一座芍藥臺。兩樹極大的桂花,正開的好。合面又是三間敞榭,橫頭朝南三間書房後,一個大荷花池。池上搭了一條橋。過去又是三間密屋,乃杜少卿自己讀書之處。
當請韋四太爺坐在朝南的書房裏。這兩樹桂花就在窗槅外。韋四太爺坐下問道:“婁翁尚在尊府?”杜少卿道:“婁老伯近來多病,請在內書房住,方纔吃藥睡下,不能出來會老伯。”韋四太爺道:“老人家既是有恙,世兄何不送他回去?”杜少卿道:“小侄已經把他令郎、令孫,都接在此侍奉湯藥。小侄也好早晚問候。”韋四太爺道:“老人家在尊府三十多年,可也還有些蓄積,家裏置些產業?”杜少卿道:“自先君赴任贛川,把舍下田地房產的賬目,都交付與婁老伯。每銀錢出入,俱是婁老伯做主,先君並不曾問。婁老伯除每年脩金四十兩,其餘並不沾一文。每收租時候,親自到鄉里佃戶家。佃戶備兩樣菜與老伯喫,老人家退去一樣才喫一樣。凡他令郎、令孫來看,只許住得兩天,就打發回去,盤纏之外,不許多有一文錢,臨行還要搜他身上,恐怕管家們私自送他銀子。只是收來的租稻利息,遇着舍下困窮的親戚朋友,婁老伯便極力相助。先君知道也不問。有人欠先君銀錢的,婁老伯見他還不起,婁老伯把借券盡行燒去了。到而今,他老人家兩個兒子,四個孫子,家裏仍然赤貧如洗,小侄所以過意不去。”韋四太爺嘆道:“真可謂古之君子了!”又問道:“慎卿兄在家好麼?”杜少卿道:“家兄自別後,就往南京去了。”
正說着,家人王鬍子,手裏拿着一個紅手本,站在窗子外,不敢進來。杜少卿看見他,說道:“王鬍子,你有甚麼話說?手裏拿的甚麼東西?”王鬍子走進書房,把手本遞上來,稟道:“南京一個姓鮑的。他是領戲班出身。他這幾年是在外路生意,纔回來家。他過江來叩見少爺。”杜少卿道:“他既是領班子的,你說我家裏有客,不得見他。手本收下,叫他去罷。”王鬍子說道:“他說受過先太老爺多少恩德,定要當面叩謝少爺。”杜少卿道:“這人是先太老爺擡舉過的麼?”王鬍子道:“是。當年邵奶公傳了他的班子過江來,太老爺着實喜歡這鮑廷璽,曾許着要照顧他的。”杜少卿道:“既如此說,你帶了他進來。”韋四太爺道:“是南京來的這位鮑兄,我纔在路上遇見的。”王鬍子出去,領着鮑廷璽,捏手捏腳,一路走進來。看見花園寬闊,一望無際。走到書房門口一望,見杜少卿陪着客坐在那裏,頭戴方巾,身穿玉色夾紗直裰,腳下珠履,麪皮微黃,兩眉劍豎,好似畫上關夫子眉毛。王鬍子道:“這便是我家少爺,你過來見。”鮑廷璽進來跪下叩頭。杜少爺扶住道:“你我故人,何必如此行禮。”起來作揖。作揖過了,又見了韋四太爺,杜少卿叫他坐在底下。鮑廷璽道:“門下蒙先老太爺的恩典,粉身碎骨難報。又因這幾年窮忙,在外做小生意,不得來叩見少爺。今日纔來請少爺的安,求少爺恕門下的罪。”杜少卿道:“方纔我家人王鬍子說,我家太老爺極其喜歡你,要照顧你。你既到這裏,且住下了,我自有道理。”王鬍子道:“席已齊了,稟少爺,在那裏坐?”韋四太爺道:“就在這裏好。”杜少卿躊躕道:“還要請一個客來。”因叫那跟書房的小廝加爵:“去後門外請張相公來罷。”加爵應諾去了。
少刻,請了一個大眼睛黃鬍子的人來,頭戴瓦楞帽,身穿大闊布衣服,扭扭捏捏,做些假斯文像,進來作揖坐下,問了韋四太爺姓名。韋四太爺說了,便問:“長兄貴姓?”那人道:“晚生姓張,賤字俊民,久在杜少爺門下。晚生略知醫道,連日蒙少爺相約在府裏看婁太爺。”因問:“婁太爺今日吃藥如何?”杜少卿便叫加爵去問。問了回來道:“婁太爺吃了藥,睡了一覺,醒了。這會覺的清爽些。”張俊民又問:“此位上姓?”杜少卿道:“是南京一位鮑朋友。”說罷,擺上席來,奉席坐下。韋四太爺首席,張俊民對坐,杜少卿主位,鮑廷璽坐在底下。斟上酒來,吃了一會。那餚饌都是自己家裏整治的,極其精潔。內中有陳過三年的火腿;半斤一個的竹蟹,都剝出來膾了蟹羹。衆人喫着,韋四太爺問張俊民道:“你這道誼,自然着實高明的。”張俊民道:“‘熟讀王叔和,不如臨症多。’不瞞太爺說,晚生在江湖上胡鬧,不曾讀過甚麼醫書,卻是看的症不少。近來蒙少爺的教訓,才曉得書是該唸的。所以我有一個小兒,而今且不教他學醫,從先生讀著書,做了文章,就拿來給杜少爺看。少爺往常賞個批語,晚生也拿了家去讀熟了,學些文理。將來再過兩年,叫小兒出去考個府縣考,騙兩回粉湯包子喫,將來掛招牌,就可以稱儒醫。”韋四太爺聽他說這話,哈哈大笑了。王鬍子又拿一個帖子進來,稟道:“北門汪鹽商家明日酧生日,請縣主老爺,請少爺去做陪客。說定要求少爺到席的。”杜少卿道:“你回他我家裏有客,不得到席。這人也可笑得緊!你要做這熱鬧事,不會請縣裏暴發的舉人進士陪?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陪官!”王鬍子應諾去了。
杜少卿向韋四太爺說:“老伯酒量極高的,當日同先君喫半夜;今日也要盡醉纔好。”韋四太爺道:“正是。世兄,我有一句話,不好說。你這餚饌是精極的了,只是這酒是市買來的,身分有限。府上有一罈酒,今年該有八九年了,想是收着還在。”杜少卿道:“小侄竟不知道。”韋四太爺道:“你不知道,是你令先大人在江西到任的那一年,我送到船上,尊大人說:‘我家裏埋下一罈酒,等我做了官回來,同你老痛飲。’我所以記得。你家裏去問。”張俊民笑說道:“這話,少爺真正該不知道。”杜少卿走了進去。韋四太爺道:“杜公子雖則年少,實算在我們這邊的豪傑。”張俊民道:“少爺爲人好極。只是手太鬆些,不管甚麼人求着他,大捧的銀與人用。”鮑廷璽道:“便是門下從不曾見過像杜少爺這大方舉動的人。” 杜少卿走進去問娘子可曉得這壇酒,娘子說不知道;遍問這些家人、婆娘,都說不知道。後來問到邵老丫,邵老丫想起來道:“是有的。是老爺上任那年,做了一罈酒埋在那邊第七進房子後一間小屋裏,說是留着韋四太爺同吃的。這酒是二斗糯米做出來的,二十斤釀;又對了二十斤燒酒,一點水也不攙。而今埋在地下足足有九年零七月了。這酒醉得死人的,弄出來,爺不要喫!”杜少爺道:“我知道了。”就叫邵老丫拿鑰匙開了酒房門,帶了兩個小廝進去,從地下取了出來,連壇擡到書房裏,叫道:“老伯,這酒尋出來了!”韋四太爺和那兩個人都起身來看,說道:“是了!”打開壇頭,舀出一杯來,那酒和曲餬一般,堆在杯子裏,聞着噴鼻香。韋四太爺道:“有趣!這個不是別樣喫法。世兄,你再叫人在街上買十斤酒來攙一攙,方可喫得。今日已是喫不成了,就放在這裏,明日喫他一天。還是二位同享。”張俊民道:“自然來奉陪。”鮑廷璽道:“門下何等的人,也來喫太老爺遺下的好酒,這是門下的造化!”說罷,教加爵拿燈籠送張俊民回家去。鮑廷璽就在書房裏陪着韋四太爺歇宿。杜少卿候着韋四太爺睡下,方纔進去了。
次日,鮑廷璽清晨起來,走到王鬍子房裏去。加爵又和一個小廝在那裏坐着。王鬍子問加爵道:“韋四太爺可曾起來?”加爵道:“起來了,洗臉哩。”王鬍子又問那小廝道:“少爺可曾起來?”那小廝道:“少爺起來多時了,在婁太爺房裏看着弄藥。”王鬍子道:“我家這位少爺也出奇!一個婁老爹,不過是太老爺的門客罷了!他既害了病,不過送他幾兩銀子,打發他回去,爲甚麼養在家裏,當做祖宗看待,還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那小廝道:“王叔,你還說這話哩!婁太爺喫的粥和菜,我們煨了,他兒子、孫子看過還不算,少爺還要自己看過了才送與婁太爺喫!人蔘銚子自放在奶奶房裏,奶奶自己煨人蔘,藥是不消說。一早一晚,少爺不得親自送人蔘,就是奶奶親自送人蔘與他喫。你要說這樣話,只好惹少爺一頓罵!”說着,門上人走進來道:“王叔,快進去說聲,臧三爺來了,坐在廳上要會少爺。”王鬍子叫那小廝道:“你婁老爹房裏去請少爺,我是不去問安!”鮑廷璽道:“這也是少爺的厚道處。”
那小廝進去請了少卿出來會臧三爺,作揖坐下。杜少卿道:“三哥,好幾日不見。你文會做的熱鬧?”臧三爺道:“正是。我聽見你門上說到遠客;……慎卿在南京,樂而忘返了。”杜少卿道:“是烏衣韋老伯在這裏。我今日請他,你就在這裏坐坐。我和你到書房裏去罷。”臧三爺道:“且坐着,我和你說話。縣裏王父母是我的老師,他在我跟前說了幾次,仰慕你的大才,我幾時同你去會會他。”杜少卿道:“像這拜知縣做老師的事,只好讓三哥你們做。不要說先曾祖、先祖,就先君在日,這樣知縣不知見過多少!他果然仰慕我,他爲甚麼不先來拜我,倒叫我拜他?況且倒運做秀才,見了本處知縣,就要稱他老師!王家這一宗灰堆裏的進士,他拜我做老師我還不要,我會他怎的?所以北門汪家今日請我去陪他,我也不去。”臧三爺道:“正是爲此。昨日汪家已向王老師說明是請你做陪客,王老師才肯到他家來,特爲要會你。你若不去,王老師也掃興。況且你的客住在家裏,今日不陪,明日也可陪。不然,我就替你陪着客,你就到汪家走走。”杜少卿道:“三哥,不要倒熟話。你這位貴老師總不是甚麼尊賢愛才,不過想人拜門生受些禮物。他想着我!叫他把夢做醒些!況我家今日請客,煨的有七斤重的老鴨,尋出來的有九年半的陳酒。汪家沒有這樣好東西喫!不許多話!同我到書房裏去頑!”拉着就走。臧三爺道:“站着!你亂怎的?這韋老先生不曾會過,也要寫個帖子。”杜少卿道:“這倒使得。”叫小廝拿筆硯帖子出來。臧三爺拿帖子寫了:“年家眷同學晚生臧荼”,先叫小廝拿帖子到書房裏,隨即同杜少卿進來。韋四太爺迎着房門,作揖坐下。那兩人先在那裏,一同坐下。韋四太爺問臧三爺:“尊字?”杜少卿道:“臧三哥尊字蓼齋,是小侄這學裏翹楚,同慎卿家兄也是同會的好友。”韋四太爺道:“久慕,久慕。”臧三爺道:“久仰老先生,幸遇。”張俊民是彼此認得的。臧蓼齋又問:“這位尊姓?”鮑廷璽道:“在下姓鮑,方纔從南京回來的。”臧三爺道:“從南京來,可曾認得府上的慎卿先生?”鮑廷璽道:“十七老爺也是見過的。”
當下吃了早飯,韋四太爺就叫把這壇酒拿出來,兌上十斤新酒,就叫燒許多紅炭,堆在桂花樹邊,把酒罈頓在炭上。過一頓飯時,漸漸熱了。張俊民領着小廝,自己動手把六扇窗格盡行下了,把桌子擡到檐內。大家坐下。又備的一席新鮮菜。杜少卿叫小廝拿出一個金盃子來,又是四個玉杯,罈子裏舀出酒來喫。韋四太爺捧着金盃,喫一杯,贊一杯,說道:“好酒!”吃了半日,王鬍子領着四個小廝,擡到一個箱子來。杜少卿問是甚麼。王鬍子道:“這是少爺與奶奶、大相公新做的秋衣一箱子。才做完了,送進來與少爺查件數。裁縫工錢已打發去了。”杜少卿道:“放在這裏,等我喫完了酒查。”才把箱子放下,只見那裁縫進來。王鬍子道:“楊裁縫回少爺的話。”杜少卿道:“他又說甚麼?”站起身來,只見那裁縫走到天井裏,雙膝跪下,磕下頭去,放聲大哭。杜少卿大驚道:“楊司務!這是怎的?”楊裁縫道:“小的這些時在少爺家做工,今早領了工錢去,不想才過了一會,小的母親得個暴病死了。小的拿了工錢家去,不想到有這一變,把錢都還了柴米店裏,而今母親的棺材衣服,一件也沒有。沒奈何,只得再來求少爺借幾兩銀子與小的,小的慢慢做着工算。”杜少卿道:“你要多少銀子?”裁縫道:“小戶人家,怎敢望多,少爺若肯,多則六兩,少則四兩罷了。小的也要算着除工錢夠還。”杜少卿慘然道:“我那裏要你還。你雖是小本生意,這父母身上大事,你也不可草草:將來就是終身之恨。幾兩銀子如何使得?至少也要買口十六兩銀子的棺材。衣服、雜費,共須二十金。我這幾日一個錢也沒有。──也罷,我這一箱衣服也可當得二十多兩銀子。王鬍子,你就拿去同楊司務當了,一總把與楊司務去用。”又道:“楊司務,這事你卻不可記在心裏,只當忘記了的。你不是拿了我的銀子去喫酒、賭錢。這母親身上大事。人孰無母?這是我該幫你的。”楊裁縫同王鬍子擡着箱子,哭哭啼啼去了。杜少卿入席坐下。韋四太爺道:“世兄,這事真是難得!”鮑廷璽吐着舌道:“阿彌陀佛!天下那有這樣好人!”當下吃了一天酒。臧三爺酒量小,喫到下午就吐了,扶了回去。韋四太爺這幾個直喫到三更,把一罈酒都喫完了,方纔散。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輕財好士,一鄉多濟友朋;月地花天,四海又聞豪傑。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