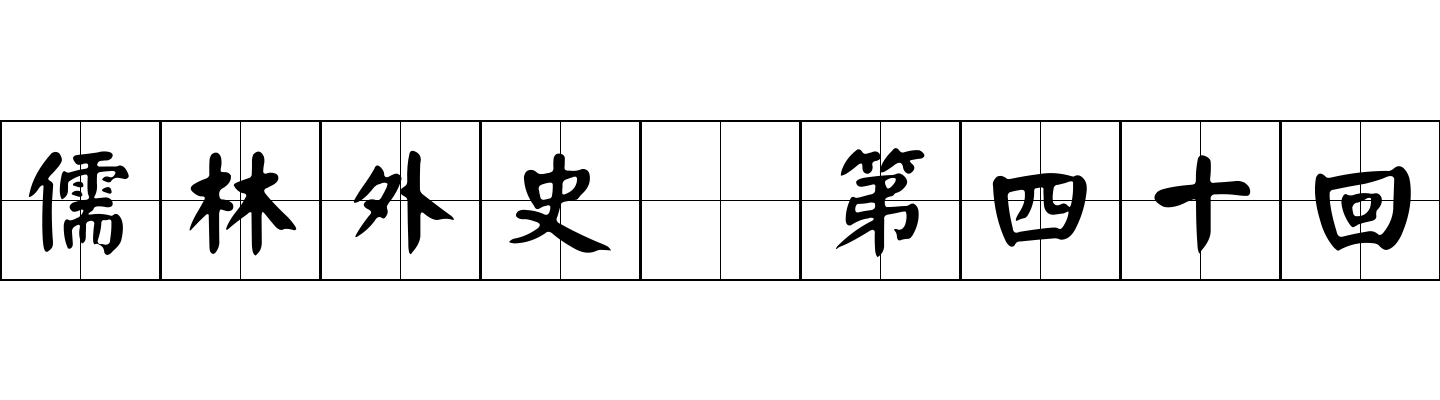儒林外史-第四十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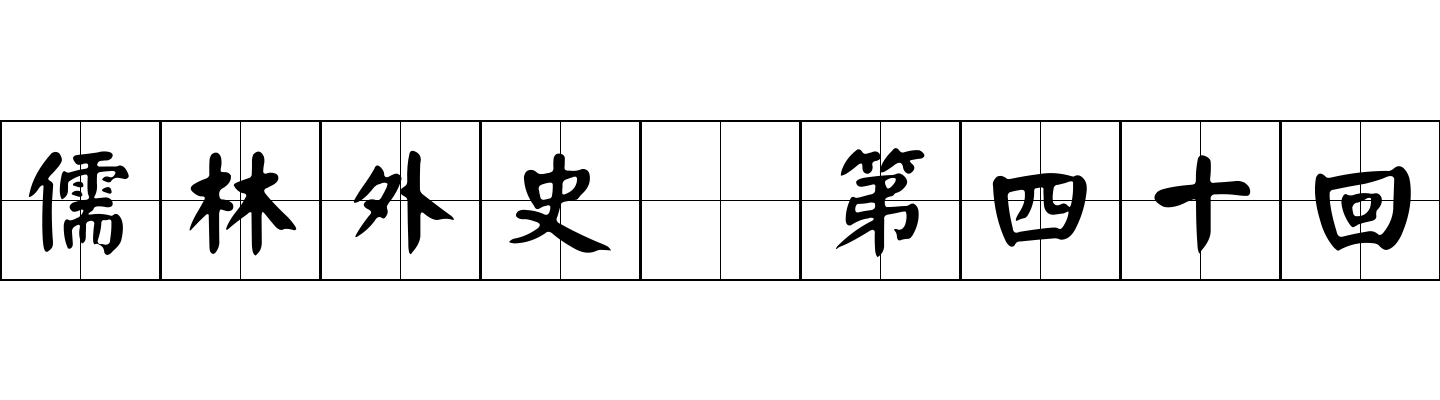
《儒林外史》,長篇小說,清代吳敬梓作。五十六回。成書於1749年(乾隆十四年)或稍前,先以抄本傳世,初刻於1803年(嘉慶八年)。以寫實主義描繪各類人士對於“功名富貴”的不同表現,一方面真實的揭示人性被腐蝕的過程和原因,從而對當時吏治的腐敗、科舉的弊端禮教的虛僞等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諷;一方面熱情地歌頌了少數人物以堅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對於人性的守護,從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該書代表着中國古代諷刺小說的高峯,它開創了以小說直接評價現實生活的範例。
蕭雲仙廣武山賞雪 沈瓊枝利涉橋賣文
話說蕭雲仙奉着將令,監督築城,足足住了三四年,那城方纔築的成功。周圍十里,六座城門。城裏又蓋了五個衙署。出榜招集流民,進來居住。城外就叫百姓開墾田地。蕭雲仙想道:“像這旱地,百姓一遇荒年,就不能收糧食了,須是興起些水利來。”因動支錢糧,僱齊民夫,蕭雲仙親自指點百姓,在田傍開出許多溝渠來。溝間有洫,洫間有遂,開得高高低低,彷彿江南的光景。到了成功的時候,蕭雲仙騎着馬,帶着木耐,在各處犒勞百姓們。每到一處,蕭雲仙殺牛宰馬,傳下號令,把那一方百姓都傳齊了。蕭雲仙建一罈場,立起先農的牌位來,擺設了牛羊祭禮。蕭雲仙紗帽補服,自己站在前面,率領衆百姓,叫木耐在旁贊禮,升香、奠酒,三獻、八拜。拜過,又率領衆百姓望着北闕山呼舞蹈,叩謝皇恩。便叫百姓都團團坐下。蕭雲仙坐在中間,拔劍割肉,大碗斟酒,歡呼笑樂,痛飲一天。喫完了酒,蕭雲仙向衆百姓道:“我和你們衆百姓在此痛飲一天,也是緣法。而今上賴皇恩,下託你們衆百姓的力,開墾了這許多田地,也是我姓蕭的在這裏一番。我如今親自手種一顆柳樹,你們衆百姓每人也種一顆,或雜些桃花、杏花,亦可記着今日之事。”衆百姓歡聲如雷,一個個都在大路上栽了桃、柳。蕭雲仙同木耐,今日在這一方,明日又在那一方,一連吃了幾十日酒,共栽了幾萬顆柳樹。衆百姓感激蕭雲仙的恩德,在城門外公同起蓋了一所先農祠,中間供着先農神位,旁邊供了蕭雲仙的長生祿位牌。又尋一個會畫的,在牆上畫了一個馬,畫蕭雲仙紗帽補服,騎在馬上。前面畫木耐的像,手裏拿着一枝紅旗,引着馬,做勸農的光景。百姓家男男女女,到朔望的日子,往這廟裏來焚香點燭跪拜,非止一日。
到次年春天,楊柳發了青,桃花、杏花,都漸漸開了。蕭雲仙騎着馬,帶着木耐,出來遊玩。見那綠樹陰中,百姓家的小孩子,三五成羣的牽着牛,也有倒騎在牛上的,也有橫睡在牛背上的,在田旁溝裏飲了水,從屋角邊慢慢轉了過來。蕭雲仙心裏歡喜,向木耐道:“你看這般光景,百姓們的日子有的過了。只是這班小孩子,一個個好模好樣,也還覺得聰俊,怎得有個先生教他識字便好!”木耐道:“老爺,你不知道麼?前日這先農祠住着一個先生,是江南人。而今想是還在這裏。老爺何不去和他商議?”蕭雲仙道:“這更湊巧了!”便打馬到祠內會那先生。進去同那先生作揖坐下。蕭雲仙道:“聞得先生貴處是江南,因甚到這邊外地方?請問先生貴姓?”那先生道:“賤姓沈,敝處常州;因向年有個親戚在青楓做生意,所以來看他。不想遭了兵亂,流落在這裏五六年,不得回去。近日聞得朝裏蕭老先生在這裏築城、開水利,所以到這裏來看看。老先生尊姓?貴衙門是那裏?”蕭雲仙道:“小弟便是蕭雲仙,在此開水利的。”那先生起身從新行禮,道:“老先生便是當今的班定遠,晚生不勝敬服!”蕭雲仙道:“先生既在這城裏,我就是主人,請到我公廨裏去住。”便叫兩個百姓來搬了沈先生的行李,叫木耐牽着馬,蕭雲仙攜了沈先生的手,同到公廨裏來。備酒飯款待沈先生,說起要請他教書的話。先生應允了。蕭雲仙又道:“只得先生一位,教不來。”便將帶來駐防的二三千多兵內,揀那認得字多的兵選了十個,託沈先生每日指授他些書理。開了十個學堂,把百姓家略聰明的孩子都養在學堂裏讀書。讀到兩年多,沈先生就教他做些破題、破承、起講。但凡做的來,蕭雲仙就和他分庭抗禮,以示優待。這些人也知道讀書是體面事了。
蕭雲仙城工已竣,報上文書去,──把這文書就叫木耐去。木耐見了少保,少保問他些情節,賞他一個外委把總做去了。少保據着蕭雲仙的詳文,諮明兵部。──工部覈算:
“蕭採承辦青楓城城工一案,該撫題銷本內:磚,灰,工匠,共開銷銀一萬九千三百六十兩一錢二分一釐五毫。查該地水草附近,燒造磚灰甚便。新集流民,充當工役者甚多。不便聽其任意浮開。應請覈減銀七千五百二十五兩有零,在於該員名下着追。查該員系四川成都府人,應行文該地方官勒限嚴比歸款,可也。奉旨依議。”
蕭雲仙看了邸抄,接了上司行來的公文,只得打點收拾行李,回成都府。比及到家,他父親已臥病在牀,不能起來。蕭雲仙到牀面前請了父親的安,訴說軍前這些始未緣由;說過,又磕下頭去,伏着不肯起來。蕭昊軒道:“這些事,你都不曾做錯,爲甚麼不起來?”蕭雲仙才把因修城工,被工部覈減追賠一案說了;又道:“兒子不能掙得一絲半粟孝敬父親,到要破費了父親的產業,實在不可自比於人,心裏愧恨之極!”蕭昊軒道:“這是朝廷功令,又不是你不肖花消掉了,何必氣惱?我的產業,攢湊攏來,大約還有七千金,你一總呈出歸公便了。”蕭雲仙哭着應諾了。看見父親病重,他衣不解帶,伏伺十餘日,眼見得是不濟事。蕭雲仙哭着問:“父親可有甚麼遺言?”蕭昊軒道:“你這話又呆氣了。我在一日,是我的事;我死後,就都是你的事了。總之,爲人以忠孝爲本,其餘都是末事。”說畢,瞑目而逝。
雲仙呼天搶地,盡哀盡禮;治辦喪事,十分盡心。卻自己嘆息道:“人說‘塞翁失馬’,未知是福是禍。前日要不爲追賠,斷斷也不能回家。父親送終的事,也再不能自己親自辦。可見這番回家,也不叫做不幸!”喪葬已畢,家產都已賠完了,還少三百多兩銀子,地方官仍舊緊追。適逢知府因盜案的事降調去了。新任知府卻是平少保做巡撫時提拔的。到任後,知道蕭雲仙是少保的人,替他虛出了一個完清的結狀,叫他先到平少保那裏去,再想法來賠補。少保見了蕭雲仙,慰勞了一番,替他出了一角諮文,送部引見。兵部司官說道:“蕭採辦理城工一案,無例題補;應請仍於本千總班次,論俸推升守備。俟其得缺之日,帶領引見。”
蕭雲仙又候了五六個月,部裏才推升了他應天府江淮衛的守備,帶領引見。奉旨:“着往新任。”蕭雲仙領了札付出京,走東路來南京。過了朱龍橋,到了廣武衛地方,晚間住在店裏,正是嚴冬時分。約有二更盡鼓,店家吆呼道:“客人們起來!木總爺來查夜!”衆人都披了衣服坐在鋪上。只見四五個兵,打着燈籠,照着那總爺進來,逐名查了。蕭雲仙看見那總爺原來就是木耐。木耐見了蕭雲仙,喜出望外,叩請了安,忙將蕭雲仙請進衙署,住了一宿。
次日,蕭雲仙便要起行,木耐留住道:“老爺且寬住一日。這天色想是要下雪了。今日且到廣武山阮公祠遊玩遊玩,卑弁盡個地主之誼。”蕭雲仙應允了。木耐叫備兩匹馬,同蕭雲仙騎着,又叫一個兵,備了幾樣餚饌和一尊酒,一經來到廣武山阮公祠內。道士接進去,請到後面樓上坐下。道土不敢來陪,隨接送上茶來。木耐隨手開了六扇窗格,正對着廣武山側面。看那山上,樹木凋敗,又被北風吹的凜凜冽冽的光景,天上便飄下雪花來。蕭雲仙看了,向着木耐說道:“我兩人當日在青楓城的時候,這樣的雪,不知經過了多少,那時到也不見得苦楚;如今見了這幾點雪,倒覺得寒冷的緊!”木耐道:“想起那兩位都督大老爺,此時貂裘向火,不知怎麼樣快活哩!”說着,喫完了酒,蕭雲仙起來閒步。樓右邊一個小閣子,牆上嵌着許多名人題詠。蕭雲仙都看完了。內中一首,題目寫着《廣武山懷古》,讀去卻是一首七言古風。蕭雲仙讀了又讀,讀過幾遍,不覺悽然淚下。木耐在旁,不解其意。蕭雲仙又看了後面一行寫着:“白門武書正字氏稿。”看罷,記在心裏。當下收拾回到衙署,又住了一夜。次日天晴,蕭雲仙辭別木耐要行。木耐親自送過大柳驛,方纔回去。
蕭雲仙從浦口過江,進了京城,驗了札付,到了任,查點了運丁,看驗了船隻,同前任的官交代清楚。那日,便問運丁道:“你們可曉的這裏有一個姓武,名書,號正字的是個甚麼人?”旗丁道:“小的卻不知道。老爺問他,卻爲甚麼?”蕭雲仙道:“我在廣武衛看見他的詩,急於要會他。”旗丁道:“既是做詩的人,小的向國子監一問便知了。”蕭雲仙道:“你快些去問。”旗丁次日來回複道:“國子監問過來了。門上說,監裏有個武相公,叫做武書,是個上齋的監生,就在花牌樓住。”蕭雲仙道:“快叫人伺侯,不打執事,我就去拜他。”當下一直來到花牌樓,一個坐東朝西的門樓,投進帖去。武書出來會了。蕭雲仙道:“小弟是一個武夫,新到貴處,仰慕賢人君子。前日在廣武山壁上,奉讀老先生懷古佳作,所以特來拜謁。”武書道:“小弟那詩,也是一時有感之作,不想有污尊目。”當下捧出茶來吃了。武書道:“老先生自廣武而來,想必自京師部選的了?”蕭雲仙道:“不瞞老先生,說起來話長。小弟自從青楓城出征之後,因修理城工多用了帑項,方纔賠償清了,照千總推升的例,選在這江淮衛。卻喜得會見老先生,凡事要求指教,改日還有事奉商。”武書道:“當得領教。”蕭雲仙說罷,起身去了。
武書送出大門,看見監裏齋夫飛跑了來,說道:“大堂虞老爺立候相公說話。”武書走去見虞博士。虞博士道:“年兄,令堂旌表的事,部裏爲報在後面,駁了三回,如今才準了。牌坊銀子在司裏,年兄可作速領去。”武書謝了出來。次日,帶了帖子去回拜蕭守備。蕭雲仙迎入川堂,作揖奉坐。武書道:“昨日枉駕後,多慢。拙作過蒙稱許,心切不安。還有些拙刻帶在這邊,還求指教。”因在袖內拿出一卷詩來。蕭雲仙接着,看了數草,讚歎不已。隨請到書房裏坐了,擺上飯來。喫過,蕭雲仙拿出一個卷子遞與武書,道:“這是小弟半生事蹟,專求老先生大筆,或作一篇文,或作幾首詩,以垂不朽。”武書接過來,放在桌上,打開看時,前面寫着“西征小紀”四個字。中間三副圖:第一副是“椅兒山破敵”,第二副是“青楓取城”,第三副是“春郊勸農”。每幅下面都有逐細的紀略。武書看完了,嘆惜道:“飛將軍數奇,古今來大概如此!老先生這樣功勞,至今還屈在卑位!這做詩的事,小弟自是領教。但老先生這一番汗馬的功勞,限於資格,料是不能載入史冊的了,須得幾位大手筆,撰述一番,各家文集裏傳留下去,也不埋沒了這半生忠悃。”蕭雲仙道:“這個也不敢當。但得老先生大筆,小弟也可藉以不朽了。”武書道:“這個不然。卷子我且帶了回去。這邊有幾位大名,素昔最喜讚揚忠孝的,若是見了老先生這一番事業,料想樂於題詠的。容小弟將此卷傳了去看看。”蕭雲仙道:“老先生的相知何不竟指小弟先去拜謁?”武書道:“這也使得。”蕭雲仙拿了一張紅帖子要武書開名字去拜。武書便開出:虞博士果行、遲均衡山、莊徵君紹光、杜儀少卿,俱寫了住處,遞與蕭雲仙,帶了卷子,告辭去了。
蕭雲仙次日拜了各位,各位都回拜了。隨奉糧道文書,押運赴淮。蕭雲仙上船,到了揚州,在鈔關上擠馬頭,正擠的熱鬧,只見後面擠上一隻船來,船頭上站着一個人,叫道:“蕭老先生!怎麼在這裏?”蕭雲仙回頭一看,說道:“呵呀!原來是沈先生!你幾時回來的?”忙叫攏了船。那沈先生跳上船來。蕭雲仙道:“向在青楓城一別,至今數年。是幾時回南來的?”沈先生道:“自蒙老先生青目,教了兩年書,積下些脩金,回到家鄉,將小女許嫁揚州宋府上,此時送他上門去。”蕭雲仙道:“令愛恭喜,少賀。”因叫跟隨的人封了一兩銀子,送過來做賀禮,說道:“我今番押運北上,不敢停泊;將來回到敝署,再請先生相會罷。”作別開船去了。
這先生領着他女兒瓊枝,岸上叫了一乘小轎子擡着女兒,自己押了行李,到了缺口門,落在大豐旗下店裏。那裏夥計接着,通報了宋鹽商。那鹽商宋爲富打發家人來吩咐道:“老爺叫把新娘就擡到府裏去,沈老爺留在下店裏住着,叫賬房置酒款待。”沈先生聽了這話,向女兒瓊枝道:“我們只說到了這裏,權且住下,等他擇吉過門,怎麼這等大模大樣?看來這等光景竟不是把你當作正室了。這頭親事,還是就得就不得?女兒,你也須自己主張。”沈瓊枝道:“爹爹,你請放心。我家又不曾寫立文書,得他身價,爲甚麼肯去伏低做小!他既如此排場,爹爹若是和他吵鬧起來,倒反被外人議論。我而今一乘轎子,擡到他家裏去,看他怎模樣看待我。”沈先生只得依着女兒的言語,看着他裝飾起來。頭上戴了冠子,身上穿了大紅外蓋,拜辭了父親,上了轎。那家人跟着轎子,一直來到河下,進了大門。幾個小老媽抱着小官在大牆門口同看門的管家說笑話,看見轎子進來,問道:“可是沈新娘來了?請下了轎,走水巷裏進去。”沈瓊枝聽見,也不言語,下了轎,一直走到大廳上坐下。說道:“請你家老爺出來!我常州姓沈的,不是甚麼低三下四的人家!他既要娶我,怎的不張燈結綵,擇吉過門,把我悄悄的擡了來,當做娶妾的一般光景?我且不問他要別的,只叫他把我父親親筆寫的婚書拿出來與我看,我就沒的說了!”老媽同家人都嚇了一跳,甚覺詫異,慌忙走到後邊報與老爺知道。那宋爲富正在藥房裏看着藥匠弄人蔘,聽了這一篇話,紅着臉道:“我們總商人家,一年至少也娶七八個妾,都像這般淘氣起來,這日子還過得!他走了來,不怕他飛到那裏去!”躊躇一會,叫過一個丫鬟來,吩咐道:“你去前面向那新娘說:‘老爺今日不在,新娘權且進房去。有甚麼話,等老爺來家再說。’”丫鬟來說了,沈瓊枝心裏想着:“坐在這裏也不是事,不如且隨他進去。”便跟着丫頭走到廳背後左邊一個小圭門裏進去,三間楠木廳,一個大院落,堆滿了太湖石的山子。沿着那山石走到左邊一條小巷,串入一個花園內。竹樹交加,亭臺軒敞,一個極寬的金魚池,池子旁邊,都是硃紅欄杆,夾着一帶走廊。走到廊盡頭處,一個小小月洞,四扇金漆門。走將進去,便是三間屋,一間做房,鋪設的齊齊整整,獨自一個院落。媽子送了茶來。沈瓊枝喫着,心裏暗說道:“這樣極幽的所在,料想彼人也不會賞鑑,且讓我在此消遣幾天!”那丫鬟回去回覆宋爲富道:“新娘人物倒生得標緻,只是樣子覺得憊賴,不是個好惹的!”
過了一宿,宋爲富叫管家到下店裏,吩咐賬房中兌出五百兩銀子送與沈老爺,叫他且回府,着姑娘在這裏,想沒的話說。沈先生聽了這話,說道:“不好了!他分明拿我女兒做妾,這還了得!”一經走到江都縣喊了一狀。那知縣看了呈子,說道:“沈大年既是常州貢生,也是衣冠中人物,怎麼肯把女兒與人做妾?鹽商豪橫一至於此!”將呈詞收了。宋家曉得這事,慌忙叫小司客具了一個訴呈,打通了關節。次日,呈子批出來,批道:
“沈大年既系將女瓊枝許配宋爲富爲正室,何至自行私送上門?顯系做妾可知。架詞混瀆,不準。”
那訴呈上批道:
“已批示沈大年詞內矣。”
沈大年又補了一張呈子。知縣大怒,說他是個刁健訟棍,一張批,兩個差人,押解他回常州去了。
沈瓊枝在宋家過了幾天,不見消息,想道:“彼人一定是安排了我父親,再來和我歪纏。不如走離了他家,再作道理。”將他那房裏所有動用的金銀器皿、真珠首飾,打了一個包袱,穿了七條裙子,扮做小老媽的模樣,買通了那丫鬟,五更時分,從後門走了,清晨出了鈔關門上船。那船是有家眷的。沈瓊枝上了船,自心裏想道:“我若回常州父母家去,恐惹故鄉人家恥笑。”細想:“南京是個好地方,有多少名人在那裏。我又會做兩句詩,何不到南京去賣詩過日子?或者遇着些緣法出來也不可知。”立定主意,到儀徵換了江船,一直往南京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賣詩女士,反爲逋逃之流;科舉儒生,且作風流之客。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