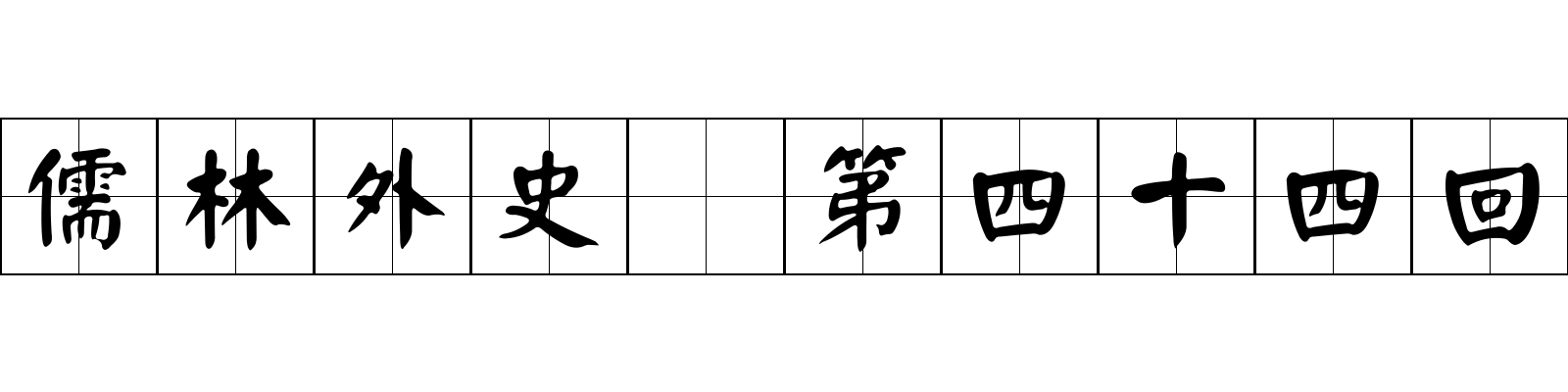儒林外史-第四十四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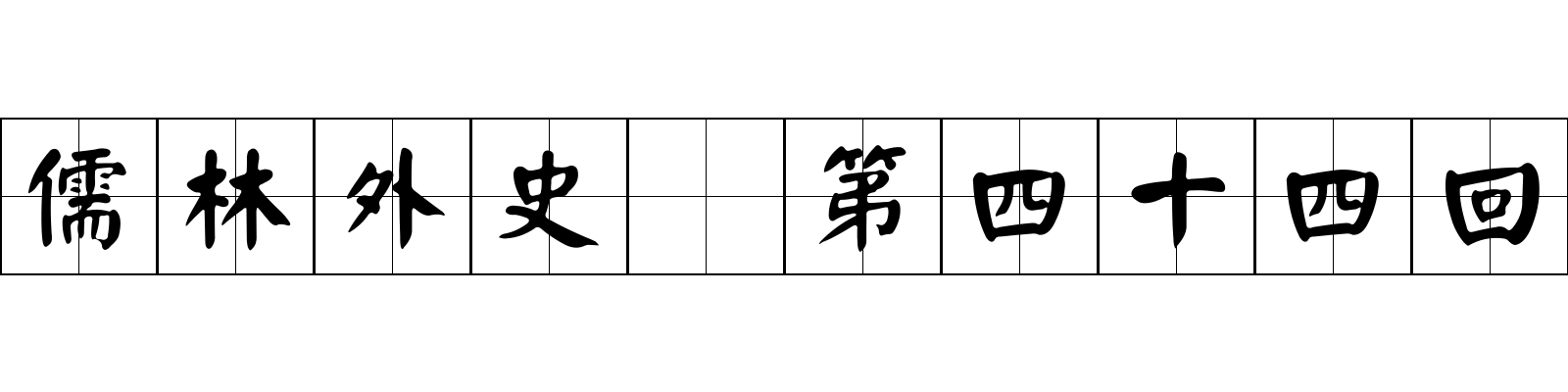
《儒林外史》,長篇小說,清代吳敬梓作。五十六回。成書於1749年(乾隆十四年)或稍前,先以抄本傳世,初刻於1803年(嘉慶八年)。以寫實主義描繪各類人士對於“功名富貴”的不同表現,一方面真實的揭示人性被腐蝕的過程和原因,從而對當時吏治的腐敗、科舉的弊端禮教的虛僞等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諷;一方面熱情地歌頌了少數人物以堅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對於人性的守護,從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該書代表着中國古代諷刺小說的高峯,它開創了以小說直接評價現實生活的範例。
湯總鎮成功歸故鄉 餘明經把酒問葬事
話說湯鎮臺同兩位公子商議,收拾回家。雷太守送了代席四兩銀子,叫湯衙庖人備了酒席,請湯鎮臺到自己衙署餞行。起程之日,闔城官員都來送行。從水路過常德,渡洞庭湖,由長江一路回儀徵。在路無事,問問兩公子平日的學業,看看江上的風景。不到兩十天,已到了紗帽洲,打發家人先回家料理迎接。六老爺知道了,一直迎到黃泥灘,見面請了安,弟兄也相見了,說說家鄉的事。湯鎮臺見他油嘴油舌,惱了道:“我出門三十多年,你長成人了,怎麼學出這般一個下流氣質!”後來見他開口就說是“稟老爺”,湯鎮臺怒道:“你這下流!胡說!我是你叔父,你怎麼叔父不叫,稱呼老爺?”講到兩個公子身上,他又叫“大爺”、“二爺”。湯鎮臺大怒道:“你這匪類!更該死了!你的兩個兄弟,你不教訓照顧他,怎麼叫大爺、二爺!”把六老爺罵的垂頭喪氣。一路到了家裏。湯鎮臺拜過了祖宗,安頓了行李。他那做高要縣知縣的乃兄已是告老在家裏,老弟兄相見,彼此歡喜,一連吃了幾天的酒。湯鎮臺也不到城裏去,也不會官府,只在臨河上構了幾間別墅,左琴右書,在裏面讀書教子。過了三四個月,看見公子們做的會文,心裏不大歡喜,說道:“這個文章,如何得中!如今趁我來家,須要請個先生來教訓他們纔好。”每日躊躕這一件事。
那一日,門上人進來稟道:“揚州蕭二相公來拜。”湯鎮臺道:“這是我蕭世兄。我會着還認他不得哩。”連忙教請進來。蕭柏泉進來見禮。鎮臺見他美如冠玉,衣冠儒雅,和他行禮奉坐。蕭柏泉道:“世叔恭喜回府,小侄就該來請安。因這些時,南京翰林侍講高老先生告假回家,在揚州過,小侄陪了他幾時,所以來遲。”湯鎮臺道:“世兄恭喜入過學了?”蕭柏泉道:“蒙前任大宗師考補博士弟子員。這領青衿,不爲希罕。卻喜小侄的文章,前三天滿城都傳遍了,果然蒙大宗師賞鑑,可見甄拔的不差。”湯鎮臺見他說話伶俐,便留他在書房裏喫飯,叫兩個公子陪他。到下午,鎮臺自己出來說,要請一位先生替兩個公子講舉業。蕭柏泉道:“小侄近來有個看會文的先生,是五河縣人,姓餘,名特,字有達;是一位明經先生,舉業其實好的。今年在一個鹽務人家做館,他不甚得意。世叔若要請先生,只有這個先生好。世叔寫一聘書,着一位世兄同小侄去會過餘先生,就可以同來。每年館穀,也不過五六十金。”湯鎮臺聽罷大喜,留蕭柏泉住了兩夜,寫了聘書,即命大公子,叫了一個草上飛,同蕭柏泉到揚州去,往河下賣鹽的吳家拜餘先生。蕭柏泉叫他寫個晚生帖子,將來進館,再換門生帖。大爺說:“半師半友,只好寫個‘同學晚弟’。”蕭柏泉拗不過,只得拿了帖子,同到那裏。門上傳進帖去,請到書房裏坐。只見那餘先生頭戴方巾,身穿舊寶藍直裰,腳下朱履,白淨面皮,三綹髭鬚,近視眼,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出來同二人作揖坐下。餘有達道:“柏泉兄,前日往儀徵去,幾時回來的?”蕭柏泉道:“便是到儀徵去看敝世叔湯大人,留住了幾天。這位就是湯世兄。”因在袖裏拿出湯大爺的名帖遞過來。餘先生接着看了,放在桌上,說道:“這個怎麼敢當?”蕭柏泉就把要請他做先生的話說了一遍,道:“今特來奉拜。如蒙臺允,即送書金過來。”餘有達笑道:“老先生大位,公子高才,我老拙無能,豈堪爲一日之長。容斟酌再來奉覆罷。”兩人辭別去了。次日,餘有達到蕭家來回拜,說道:“柏泉兄,昨日的事,不能遵命。”蕭柏泉道:“這是甚麼緣故?”餘有達笑道:“他既然要拜我爲師,怎麼寫‘晚弟’的帖子拜我?可見就非求教之誠。這也罷了。小弟因有一個故人在無爲州做刺史,前日有書來約我,我要到那裏走走。他若幫襯我些須,強如坐一年館。我也就在這數日內要辭別了東家去。湯府這一席,柏泉兄竟轉薦了別人罷。”蕭柏泉不能相強,回覆了湯大爺,另請別人去了。
不多幾日,餘有達果然辭了主人,收拾行李,回五河。他家就在餘家巷。進了家門,他同胞的兄弟出來接着。他這兄弟名持,字有重,也是五河縣的飽學秀才。此時五河縣發了一個姓彭的人家,中了幾個進士,選了兩個翰林。五河縣人眼界小,便闔縣人同去奉承他。又有一家,是徽州人,姓方,在五河開典當行鹽,就冒了籍,要同本地人作姻親。初時這餘家巷的餘家還和一個老鄉紳的虞家是世世爲婚姻的,這兩家不肯同方家做親。後來這兩家出了幾個沒廉恥不才的人,貪圖方家賠贈,娶了他家女兒,彼此做起親來。後來做的多了,方家不但沒有分外的賠贈,反說這兩家子仰慕他有錢,求着他做親。所以這兩家不顧祖宗臉面的有兩種人:一種是呆子,那呆子有八個字的行爲:“非方不親,非彭不友。”一種是乖子,那乖子也有八個字的行爲:“非方不心,非彭不口。”這話是說那些呆而無恥的人,假使五河縣沒有一個冒籍姓方的,他就可以不必有親;沒有個中進士姓彭的,他就可以不必有友。這樣的人,自己覺得勢利透了心,其實呆串了皮!那些奸滑的,心裏想着同方家做親,方家又不同他做。他卻不肯說出來,只是嘴裏扯謊嚇人,說:“彭老先生是我的老師。彭三先生把我邀在書房裏說了半天的知心話。”又說:“彭四先生在京裏帶書子來給我。”人聽見他這些話,也就常時請他來喫杯酒,要他在席上說這些話嚇同席喫酒的人。其風俗惡賴如此。
這餘有達,餘有重弟兄兩個,守着祖宗的家訓,閉戶讀書,不講這些隔壁帳的勢利。餘大先生各府、州、縣作遊,相與的州、縣官也不少,但到本縣來總不敢說。因五河人有個牢不可破的見識:總說但凡是個舉人、進士,就和知州、知縣是一個人,不管甚麼情都可以進去說,知州、知縣就不能不依。假使有人說縣官或者敬那個人的品行,或者說那人是個名士,要來相與他,就一縣人嘴都笑歪了。就像不曾中過舉的人,要想拿帖子去拜知縣,知縣就可以叉着膊子叉出來。總是這般見識。餘家弟兄兩個,品行、文章是從古沒有的。因他家不見本縣知縣來拜,又同方家不是親,又同彭家不是友,所以親友們雖不敢輕他,卻也不知道敬重他。
那日,餘有重接着哥哥進來,拜見了,備酒替哥哥接風,細說一年有餘的話。喫過了酒,餘大先生也不往房裏去,在書房裏,老弟兄兩個一牀睡了。夜裏,大先生向二先生說要到無爲州看朋友去。二先生道:“哥哥還在家裏住些時。我要到府里科考,等我考了回來,哥哥再去罷。”餘大先生道:“你不知道。我這揚州的館金已是用完了,要趕着到無爲州去弄幾兩銀子回來過長夏。你科考去不妨,家裏有你嫂子和弟媳當着家。我弟兄兩個,原是關着門過日子,要我在家怎的?”二先生道:“哥這番去,若是多抽豐得幾十兩銀子,回來把父親母親葬了。靈柩在家裏這十幾年,我們在家都不安。”大先生道:“我也是這般想,回來就要做這件事。”
又過了幾日,大先生往無爲州去了。又過了十多天,宗師牌到,按臨鳳陽。餘二先生便束裝住鳳陽,租個下處住下。這時是四月初八日。初九日宗師行香。初十日卦牌收詞狀,十一日掛牌考鳳陽八屬儒學生員。十五日發出生員覆試案來,每學取三名覆試。餘二先生取在裏面。十六日進去覆了試,十七日發出案來,餘二先生考在一等第二名,在鳳陽一直住到二十四,送了宗師起身,方纔回五河去了。
大先生來到無爲州,那州尊着實念舊,留着住了幾日,說道:“先生,我到任未久,不能多送你些銀子。而今有一件事,你說一個情罷,我準了你的。這人家可以出得四百兩銀子,有三個人分;先生可以分得一百三十多兩銀子,權且拿回家去做了老伯、老伯母的大事。我將來再爲情罷。”餘大先生歡喜,謝了州尊,出去會了那人。那人姓風,名影,是一件人命牽連的事。餘大先生替他說過,州尊準了,出來兌了銀子,辭別知州,收拾行李回家。因走南京過,想起:“天長杜少卿住在南京利涉橋河房裏,是我表弟,何不順便去看看他?”便進城來到杜少卿家。杜少卿出來接着,一見表兄,心裏歡喜,行禮坐下,說這十幾年闊別的話。餘大先生嘆道:“老弟,你這些上好的基業,可惜棄了!你一個做大老官的人,而今賣文爲活,怎麼弄的慣!”杜少卿道:“我而今在這裏,有山川朋友之樂,倒也住慣了。不瞞表兄說,我愚弟也無甚麼嗜好,夫妻們帶着幾個兒子,布衣蔬食,心裏淡然。那從前的事,也追悔不來了。”說罷,奉茶與表兄喫。喫過,杜少卿自己走進去和娘子商量,要辦酒替表兄接風。此時杜少卿窮了,辦不起,思量方要拿東西去當。這日是五月初三,卻好莊耀江家送了一擔禮來與少卿過節。小廝跟了禮,拿着拜匣,一同走了進來,那禮是一尾鰣魚,兩隻燒鴨,一百個糉子,二斤洋糖;拜匣裏四兩銀子。杜少卿寫回帖叫了多謝,收了。那小廝去了。杜少卿和娘子說:“這主人做得成了!”當下又添了幾樣,娘子親自整治酒餚。遲衡山、武正字住的近,杜少卿寫說帖,請這兩人來陪表兄。二位來到,敘了些彼此仰慕的話,在河房裏一同喫酒。
喫酒中間,餘大先生說起要尋地葬父母的話。遲衡山道:“先生,只要地下乾暖,無風無蟻,得安先人,足矣;那些發富發貴的話,都聽不得。”餘大先生道:“正是。敝邑最重這一件事。人家因尋地艱難,每每耽誤着先人,不能就葬。小弟卻不曾究心於此道。請問二位先生:這郭璞之說,是怎麼個源流?”遲衡山嘆道:“自冢人墓地之官不設,族葬之法不行,士君子惑於龍穴、沙水之說,自心裏要想發達,不知已墮於大逆不道!”餘大先生驚道:“怎生便是大逆不道?”遲衡山道:“有一首詩,念與先生聽:‘氣散風衝那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尚未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這是前人吊郭公墓的詩。小弟最恨而今術士託於郭璞之說,動輒便說:‘這地可發鼎甲,可出狀元!請教先生:狀元官號,始於唐朝,郭璞晉人,何得知唐有此等官號,就先立一法,說是個甚麼樣的地,就出這一件東西?這可笑的緊!若說古人封拜都在地理上看得出來,試問淮陰葬母,行營高敞地,而淮陰王侯之貴,不免三族之誅,這地是兇是吉?更可笑這些俗人說,本朝孝陵乃青田先生所擇之地!青田命世大賢,敷布兵、農、禮、樂,日不暇給,何得有閒工夫做到這一件事?洪武即位之時,萬年吉地,自有術士辦理,與青田甚麼相干!”
餘大先生道:“先生,你這一番議論,真可謂之發矇振聵!”武正字道:“衡山先生之言,一絲不錯。前年我這城中有一件奇事,說與諸位先生聽。”餘大先生道:“願聞,願聞。”武正字道:“便是我這裏下浮橋地方施家巷裏施御史家。”遲衡山道:“施御史家的事,我也略聞,不知其詳。”武正字道:“施御史昆玉二位。施二先生說乃兄中了進士,他不曾中,都是大夫人的地葬的不好,只發大房,不發二房。因養了一個風水先生在家裏,終日商議遷墳。施御史道:‘已葬久了,恐怕遷不得。’哭着下拜求他。他斷然要遷。那風水又拿話嚇他,說:‘若是不遷,二房不但不做官,還要瞎眼!’他越發慌了,託這風水到處尋地。家裏養着一個風水,外面又相與了多少風水。這風水尋着一個地,叫那些風水來覆。那曉得風水的講究,叫做父做子笑,子做父笑,再沒有一個相同的。但尋着一塊地,就被人覆了說:‘用不得!’家裏住的風水急了,又獻了一塊地,便在那新地左邊,買通了一個親戚來說,夜裏夢見老太太鳳冠霞帔,指着這地與他看,要葬在這裏。因這一塊地是老太太自己尋的,所以別的風水才覆不掉,便把母親硬遷來葬。到遷墳的那日,施御史弟兄兩位跪在那裏。才掘開墳,看見了棺木,墳裏便是一股熱氣,直衝出來,衝到二先生眼上,登時就把兩隻眼瞎了。二先生越發信這風水竟是個現在的活神仙,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後來重謝了他好幾百兩銀子。”
餘大先生道:“我們那邊也極喜講究的遷葬。少卿,這事行得行不得?”杜少卿道:“我還有一句直捷的話。這事朝廷該立一個法子:但凡人家要遷葬,叫他到有司衙門遞個呈紙,風水具了甘結:棺材上有幾尺水,幾鬥幾升蟻。等開了,說得不錯,就罷了;如說有水有蟻,挖開了不是,即於挖的時候,帶一個劊子手,一刀把這奴才的狗頭斫下來。那要遷墳的,就依子孫謀殺祖父的律,立刻凌遲處死。此風或可少息了!”餘有達、遲衡山、武正字三人一齊拍手道:“說的暢快!說的暢快!拿大杯來喫酒!”又吃了一會,餘大先生談道湯家請他做館的一段話;說了一遍,笑道:“武夫可見不過如此!”武正字道:“武夫中竟有雅不過的!”因把蕭雲仙的事細細說了,對杜少卿道:“少卿先生,你把那捲子拿出來與餘先生看。”杜少卿取了出來。餘大先生打開看了圖和虞博士幾個人的詩,看畢,乘着酒興,依韻各和了一首。三人極口稱讚。當下吃了半夜酒,一連住了三日。那一日,有一個五河鄉里賣鴨的人,拿了一封家信來,說是餘二老爹帶與餘大老爹的。餘大先生拆開一看,面如土色。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弟兄相助,真耽式好之情;朋友交推,又見同聲之誼。
畢竟書子裏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