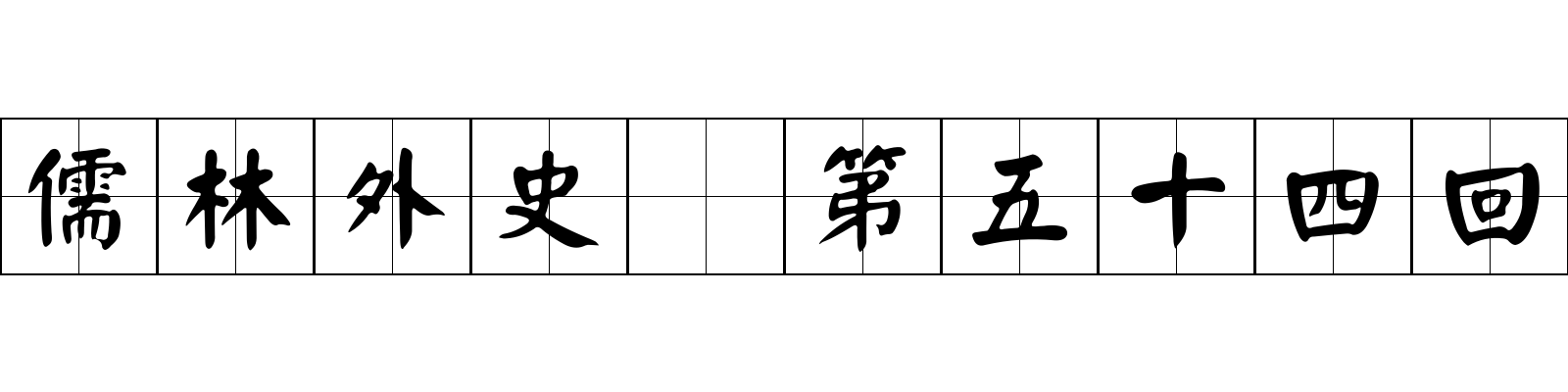儒林外史-第五十四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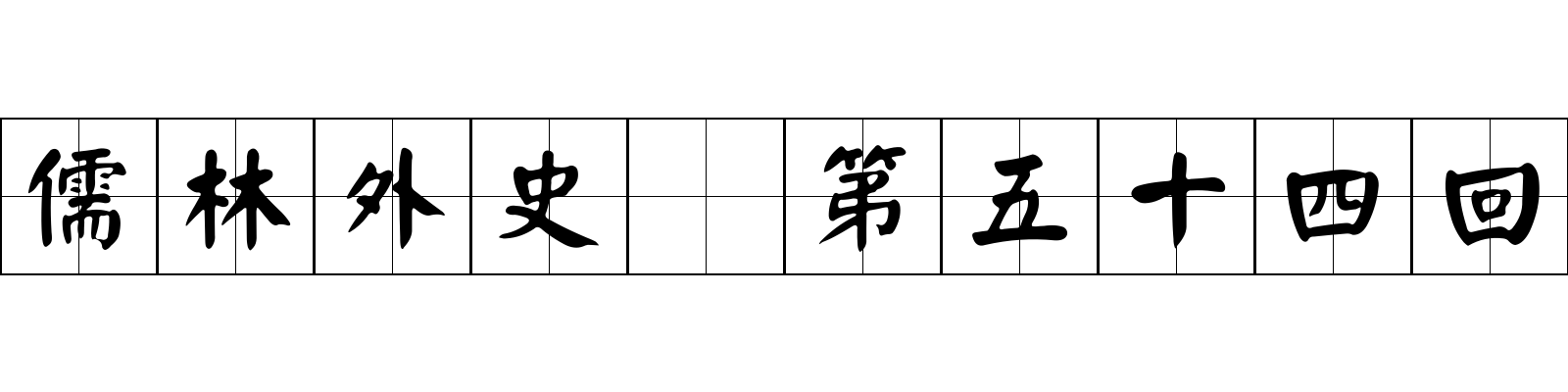
《儒林外史》,長篇小說,清代吳敬梓作。五十六回。成書於1749年(乾隆十四年)或稍前,先以抄本傳世,初刻於1803年(嘉慶八年)。以寫實主義描繪各類人士對於“功名富貴”的不同表現,一方面真實的揭示人性被腐蝕的過程和原因,從而對當時吏治的腐敗、科舉的弊端禮教的虛僞等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諷;一方面熱情地歌頌了少數人物以堅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對於人性的守護,從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該書代表着中國古代諷刺小說的高峯,它開創了以小說直接評價現實生活的範例。
病佳人青樓算命 呆名士妓館獻詩
話說聘娘同四老爺睡着,夢見到杭州府的任,驚醒轉來,窗子外已是天亮了,起來梳洗。陳木南也就起來。虔婆進房來問了姐夫的好。喫過點心,恰好金修義來,鬧着要陳四老爺的喜酒。陳木南道:“我今日就要到國公府裏去,明日再來爲你的情罷。”金修義走到房裏,看見聘娘手挽着頭髮,還不曾梳完,那烏雲䰀鬌,半截垂在地下,說道:“恭喜聘娘接了這樣一位貴人!你看看,恁般時候尚不曾定當,可不是越發嬌嫩了!”因問陳四老爺:“明日甚麼時候纔來?等我吹笛子,叫聘娘唱一隻曲子與老爺聽。他的李太白‘清平三調’是十六樓沒有一個賽得過他的!”說着,聘娘又拿汗巾替四老爺拂了頭巾,囑咐道:“你今晚務必來,不要哄我老等着!”陳木南應諾了,出了門,帶着兩個長隨,回到下處。思量沒有錢用,又寫一個札子叫長隨拿到國公府裏向徐九公子再借二百兩銀子,湊着好用。長隨去了半天,回來說道:“九老爺拜上爺:府裏的三老爺方從京裏到,選了福建漳州府正堂,就在這兩日內要起身上任去。九老爺也要同到福建任所,料理事務,說銀子等明日來辭行,自帶來。”陳木南道:“既是三老爺到了,我去候他。”隨坐了轎子,帶着長隨,來到府裏。傳進去,管家出來回道:“三老爺、九老爺,都到沐府裏赴席去了。四爺有話說,留下罷。”陳木南道:“我也無甚話,是特來侯三老爺的。”陳木南迴到寓處。
過了一日,三公子同九公子來河房裏辭行,門口下了轎子。陳木南迎進河廳坐下。三公子道:“老弟,許久不見,風采一發倜儻。姑母去世,愚表兄遠在都門,不曾親自弔唁。幾年來學問更加淵博了?”陳木南道:“先母辭世,三載有餘。弟因想念九表弟文字相好,所以來到南京,朝夕請教。今表兄榮任閩中,賢昆玉同去,愚表弟倒覺失所了。”九公子道:“表兄若不見棄,何不同去一行?長途之中,到覺得頗不寂寞。”陳木南道:“原也要和表兄同行,因在此地還有一兩件小事,俟兩三月之後,再到表兄任上來罷。”九公子隨叫家人取一個拜匣,盛着二百兩銀子,送與陳木南收下。三公子道:“專等老弟到敝署走走。我那裏還有事要相煩幫襯。”陳木南道:“一定來效勞的。”說着,喫完了茶,兩人告辭起身。陳木南送到門外,又隨坐轎子到府裏去送行。一直送他兩人到了船上,才辭別回來。
那金修義已經坐在下處,扯他來到來賓樓。進了大門,走到臥房,只見聘娘臉兒黃黃的,金修義道:“幾日不見四老爺來,心口疼的病又發了。”虔婆在旁道:“自小兒嬌養慣了,是有這一個心口疼的病。但凡着了氣惱,就要發。他因四老爺兩日不曾來,只道是那些憎嫌他,就發了。”聘娘看見陳木南,含着一雙淚眼,總不則聲。陳木南道:“你到底是那裏疼痛?要怎樣才得好?往日發了這病,卻是甚麼樣醫?”虔婆道:“往日發了這病,茶水也不能咽一口。醫生來撮了藥,他又怕苦不肯喫,只好頓了人蔘湯慢慢給他喫着,才保全不得傷大事。”陳木南道:“我這裏有銀子,且拿五十兩放在你這裏,換了人蔘來用着。再揀好的換了,我自己帶來給你。”那聘娘聽了這話,挨着身子,靠着那繡枕,一團兒坐在被窩裏,胸前圍着一個紅抹胸,嘆了一口氣,說道:“我這病一發了,不曉得怎的,就這樣心慌!那些先生們說是單喫人蔘,又會助了虛火,往常總是合着黃連,煨些湯喫,夜裏睡着,才得閤眼。要是不喫,就只好是眼睜睜的一夜醒到天亮!”陳木南道:“這也容易。我明日換些黃連來給你就是了。”金修義道:“四老爺在國公府裏,人蔘黃連論秤稱也不值甚麼,聘娘那裏用的了!”聘娘道:“我不知怎的,心裏慌慌的,合着眼就做出許多胡枝扯葉的夢,清天白日的還有些害怕!”金修義道:“總是你身子生的虛弱,經不得勞碌,着不得氣惱。”虔婆道:“莫不是你傷着甚麼神道?替你請個尼僧來禳解禳解罷。”
正說着,門外敲的手磬子響。虔婆出來看,原來是延壽庵的師姑本慧來收月米。虔婆道:“阿呀!是本老爺!兩個月不見你來了,這些時,庵裏做佛事忙?”本師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今年運氣低,把一個二十歲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連觀音會都沒有做的成。你家的相公娘好?”虔婆道:“也常時三好兩歹的,虧的太平府陳四老爺照顧他。他是國公府裏徐九老爺的表兄,常時到我家來。偏生的聘娘沒造化,心口疼的病發了。你而今進去看看。”本師姑一同走進房裏。虔婆道:“這便是國公府裏陳四老爺。”本師姑上前打了一個問訊。金修義道:“四老爺,這是我們這裏的本師父,極有道行的。”本師姑見過四老爺,走到牀面前來看相公娘。金修義道:“方纔說要禳解,何不就請本師父禳解禳解?”本師姑道:“我不會禳解,我來看看相公孃的氣色罷。”便走了來,一屁股坐到牀沿上。聘娘本來是認得他的,今日擡頭一看,卻見他黃着臉,禿着頭,就和前日夢裏揪他的師姑一模一樣,不覺就懊惱起來。只叫得一聲“多勞”,便把被蒙着頭睡下。本師姑道:“相公娘心裏不耐煩,我且去罷。”向衆人打個問訊,出了房門。虔婆將月米遞給他。他左手拿着磬子,右手拿着口袋去了。
陳木南也隨即回到寓所,拿銀子叫長隨趕着去換人蔘,換黃連。只見主人家董老太拄着柺杖,出來說道:“四相公,你身子又結結實實的,只管換這些人蔘、黃連做甚麼?我聽見這些時在外頭憨頑,我是你的房主人,又這樣年老,四相公,我不好說的。自古道:‘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煙花債。’他們這樣人家,是甚麼有良心的!把銀子用完,他就屁股也不朝你了!我今年七十多歲,看經唸佛,觀音菩薩聽着,我怎肯眼睜睜的看着你上當不說!”陳木南道:“老太說的是,我都知道了。這人蔘、黃連,是國公府裏託我換的。”因怕董老太韶刀,便說道:“恐怕他們換的不好,還是我自己去。”走了出來,到人蔘店裏尋着了長隨,換了半斤人蔘,半斤黃連,和銀子就像捧寶的一般,捧到來賓樓來。才進了來賓樓門,聽見裏面彈的三絃子響,是虔婆叫了一個男瞎子來替姑娘算命。陳木南把人蔘、黃連遞與虔婆,坐下聽算命。那瞎子道:“姑娘今年十七歲,大運交庚寅,寅與亥合,合着時上的貴人,該有個貴人星坐命。就是四正有些不利,吊動了一個計都星,在裏面作擾,有些啾卿不安,卻不礙大事。莫怪我直談,姑娘命裏犯一個華蓋星,卻要記一個佛名,應破了纔好。將來從一個貴人,還要有戴鳳冠霞帔,有太太之分哩。”說完,橫着三絃彈着,又唱一回,起身要去。虔婆留喫茶,捧出一盤雲片糕,一盤黑棗子來,放個小桌子,與他坐着。丫頭斟茶,遞與他喫着。陳木南問道:“南京城裏,你們這生意也還好麼?”瞎子道:“說不得,比不得上年了!上年都是我們沒眼的算命,這些年睜眼的人都來算命,把我們擠壞了!就是這南京城,二十年前,有個陳和甫,他是外路人,自從一進了城,這些大老官家的命都是他鬌攔着算了去,而今死了。積作的個兒子,在我家那間壁招親,日日同丈人吵窩子,吵的鄰家都不得安身。眼見得我今日回家,又要聽他吵了。”說罷,起身道過多謝,去了。
一直走了回來,到東花園一個小巷子裏,果然又聽見陳和甫的兒子和丈人吵。丈人道:“你每日在外測字,也還尋得幾十文錢,只買了豬頭肉,飄湯燒餅,自己搗嗓子,一個錢也不拿了來家,難道你的老婆要我替你養着?這個還說是我的女兒也罷了。你賒了豬頭肉的錢不還,也來問我要!終日吵鬧這事,那裏來的晦氣!”陳和甫的兒子道:“老爹,假使這豬頭肉是你老人家自己吃了,你也要還錢。”丈人道:“胡說!我若吃了,我自然還!這都是你喫的!”陳和甫兒子道:“設或我這錢已經還過老爹,老爹用了,而今也要還人。”丈人道:“放屁!你是該人的錢,怎是我用你的?”陳和甫兒子道:“萬一豬不生這個頭,難道他也來問我要錢?”丈人見他十分胡說,拾了個叉子棍趕着他打。瞎子摸了過來扯勸。丈人氣的顫呵呵的道:“先生!這樣不成人!我說說他,他還拿這些混帳話來答應我,豈不可恨!”陳和甫兒子道:“老爹,我也沒有甚麼混帳處。我又不喫酒,又不賭錢,又不嫖老婆!每日在測字的桌子上還拿着一本詩念,有甚麼混帳處!”丈人道:“不是別的混帳,你放着一個老婆不養,只是累我,我那裏累得起!”陳和甫兒子道:“老爹,你不喜女兒給我做老婆,你退了回去罷了。”丈人罵道:“該死的畜生!我女兒退了做甚麼事哩?”陳和甫兒子道:“聽憑老爹再嫁一個女婿罷了。”丈人大怒道:“瘟奴!除非是你死了,或是做了和尚,這事纔行得!”陳和甫兒子道:“死是一時死不來,我明日就做和尚去。”丈人氣憤憤的道:“你明日就做和尚!”瞎子聽了半天,聽他兩人說的都是“堂屋裏掛草薦”──不是話,也就不扯勸,慢慢的摸着回去了。
次早,陳和甫的兒子剃光了頭,把瓦楞帽賣掉了,換了一頂和尚帽子戴着,來到丈人面前,合掌打個問訊,道:“老爹,貧僧今日告別了。”丈人見了大驚,雙雙掉下淚來,又着實數說了他一頓;知道事已無可如何,只得叫他寫了一張紙,自己帶着女兒養活去了。
陳和尚自此以後,無妻一身輕,有肉萬事足,每日測字的錢,就買肉喫,喫飽了,就坐在文德橋頭測字的桌子上唸詩,十分自在。又過了半年,那一日,正拿着一本書在那裏看,遇着他一個同夥的測字丁言志來看他。見他看這本書,因問道:“你這書是幾時買的?”陳和尚道:“我纔買來三四天。”丁言志道:“這是鶯脰湖唱和的詩。當年胡三公子約了趙雪齋、景蘭江、楊執中先生,匡超人、馬純上一班大名士,大會鶯脰湖,分韻作詩。我還切記得趙雪齋先生是分的‘八齊’。你看這起句:‘湖如鶯脰夕陽低。’只消這一句,便將題目點出,以下就句句貼切,移不到別處宴會的題目上去了。”陳和尚道:“這話要來問我纔是,你那裏知道!當年鶯脰湖大會,也並不是胡三公子做主人,是婁中堂家的三公子、四公子。那時我家先父就和婁氏弟兄是一人之交。彼時大會鶯脰湖,先父一位,楊執中先生、權勿用先生、牛布衣先生、蘧駪夫先生、張鐵臂、兩位主人,還有楊先生的令郎,共是九位。這是我先父親口說的。我到不曉得?你那裏知道!”丁言志道:“依你這話,難道趙雪齋先生、景蘭江先生的詩,都是別人假做的了?你想想,你可做得來?”陳和尚道:“你這話尤其不通!他們趙雪齋這些詩,是在西湖上做的,並不是鶯脰湖那一會。”丁言志道:“他分明是說‘湖如鶯脰’,怎麼說不是鶯脰湖大會?”陳和尚道:“這一本詩也是彙集了許多名士合刻的。就如這個馬純上,生平也不會作詩,那裏忽然又跳出他一首?”丁言志道:“你說的都是些夢話!馬純上先生,蘧駪夫先生,做了不知多少詩,你何嘗見過!”陳和尚道;“我不曾見過,到是你見過!你可知道鶯脰湖那一會並不曾有人做詩?你不知那裏耳朵響,還來同我瞎吵!”丁言志道:“我不信!那裏有這些大名士聚會,竟不做詩的!這等看起來,你尊翁也未必在鶯脰湖會過。若會過的人,也是一位大名士了,恐怕你也未必是他的令郎!”陳和尚惱了道:“你這話胡說!天下那裏有個冒認父親的!”丁言志道:“陳思阮!你自己做兩句詩罷了,何必定要冒認做陳和甫先生的兒子?”陳和尚大怒道:“丁詩!你‘幾年桃子幾年人’!跳起來,通共念熟了幾首趙雪齋的詩,鑿鑿的就呻着嘴來講名士!”丁言志跳起身來道:“我就不該講名士!你到底也不是一個名士!”兩個人說戧了,揪着領子,一頓亂打。和尚的光頭被他鑿了幾下,鑿的生疼,拉到橋頂上。和尚眊着眼,要拉到他跳河。被丁言志搡了一交,骨碌碌就滾到橋底下去了。和尚在地下急的大嚷大叫。
正叫着,遇見陳木南踱了來,看見和尚仰巴叉睡在地下,不成模樣,慌忙拉起來道:“這是怎的?”和尚認得陳木南,指着橋上說道:“你看這丁言志無知無識的,走來說是鶯脰湖的大會是胡三公子的主人!我替他講明白了,他還要死強!並且說我是冒認先父的兒子!你說可有這個道理?”陳木南道:“這個是甚麼要緊的事,你兩個人也這樣鬼吵。其實丁言老也不該說思老是冒認父親。這卻是言老的不是。”丁言志道:“四先生,你不曉得。我難道不知道他是陳和甫先生的兒子?只是他擺出一副名士臉來,太難看!”陳木南笑道:“你們自家人,何必如此?要是陳思老就會擺名士臉,當年那虞博士、莊徵君,怎樣過日子呢?我和你兩位喫杯茶,和和事,下回不必再吵了。”當下拉到橋頭間壁一個小茶館裏坐下,喫着茶。陳和尚道:“聽見四先生令表兄要接你同到福建去,怎樣還不見動身?”陳木南道:“我正是爲此來尋你測字,幾時可以走得?”丁言志道:“先生,那些測字的話,是我們‘籤火七佔通’的。你要動身,揀個日子走就是了,何必測字!”陳和尚道:“四先生,你半年前,我們要會你一面也不得能彀。我出家的第二日,有一首薙髮的詩,送到你下處請教,那房主人董老太說,你又到外頭頑去了。你卻一向在那裏?今日怎管家也不帶,自己在這裏閒撞?”陳木南道:“因這裏來賓樓的聘娘愛我的詩做的好,我常在他那裏。”丁言志道:“青樓中的人也曉得愛才,這就雅極了!”向陳和尚道:“你看!他不過是個巾幗,還曉得看詩,怎有個鶯脰湖大會不作詩的呢?”陳木南道:“思老的話倒不差。那婁玉亭便是我的世伯,他當日最相好的是楊執中、權勿用。他們都不以詩名。”陳和尚道:“我聽得權勿用先生後來犯出一件事來,不知怎麼樣結局?”陳木南道:“那也是他學裏幾個秀才誣賴他的。後來這件官事也昭雪了。”又說了一會,陳和尚同丁言志別過去了。
陳木南交了茶錢,自己走到來賓樓。一進了門,虔婆正在那裏同一個賣花的穿桂花球,見了陳木南道:“四老爺,請坐下罷了。”陳木南道:“我樓上去看看聘娘。”虔婆道:“他今日不在家,到輕煙樓做盒子會去了。”陳木南道:“我今日來和他辭辭行,就要到福建去。”虔婆道:“四老爺就要起身?將來可還要回來的?”說着,丫頭捧一杯茶來。陳木南接在手裏,不大熱,吃了一口,就不吃了。虔婆看了道:“怎麼茶也不肯泡一壺好的!”丟了桂花球,就走到門房裏去罵烏龜。
陳木南看見他不瞅不睬,只得自己又踱了出來。走不得幾步,頂頭遇着一個人,叫道:“陳四爺,你還要信行些纔好!怎叫我們只管跑!”陳木南道:“你開着偌大的人蔘鋪,那在乎這幾十兩銀子。我少不得料理了送來給你。”那人道:“你那兩個尊管而今也不見面,走到尊寓,只有那房主人董老太出來回,他一個堂客家,我怎好同他七個八個的?”陳木南道:“你不要慌,‘躲得和尚躲不得寺’。我自然有個料理。你明日到我寓處來。”那人道:“明早是必留下,不要又要我們跑腿。”說過,就去了。陳木南迴到下處,心裏想道:“這事不尷尬!長隨又走了,虔婆家又走不進他的門,銀子又用的精光,還剩了一屁股兩肋巴的債,不如卷卷行李,往福建去罷!”瞞着董老太,一溜煙走了。
次日,那賣人蔘的清早上走到他寓所來,坐了半日,連鬼也不見一個。那門外推的門響,又走進一個人來,搖着白紙詩扇,文縐縐的。那賣人蔘的起來問道:“尊姓?”那人道:“我就是丁言志,來送新詩請教陳四先生的。”賣人蔘的道:“我也是來尋他的。”又坐了半天,不見人出來,那賣人蔘的就把屏門拍了幾下。董老太拄着柺杖出來問道:“你們尋那個的?”賣人蔘的道:“我來找陳四爺要銀子。”董老太道:“他麼?此時好到觀音門了。”那賣人蔘的大驚道:“這等,可曾把銀子留在老太處?”董老太道:“你還說這話!連我的房錢都騙了!他自從來賓樓張家的妖精纏昏了頭,那一處不脫空!揹着一身的債,還希罕你這幾兩銀子!”賣人蔘的聽了,“啞叭夢見媽,說不出的苦”,急的暴跳如雷。丁言志勸道:“尊駕也不必急,急也不中用,只好請回。陳四先生是個讀書人,也未必就騙你。將來他回來,少不得還哩。”那人跳了一回,無可奈何,只得去了。
丁言志也搖着扇子,晃了出來,自心裏想道:“堂客也會看詩!……那十六樓不曾到過,何不把這幾兩測字積下的銀子,也去到那裏頑頑?”主意已定,回家帶了一卷詩,換了幾件半新不舊的衣服,戴一頂方巾,到來賓樓來。烏龜看見他像個呆子,問他來做甚麼。丁言志道:“我來同你家姑娘談談詩。”烏龜道:“既然如此,且秤下箱錢。”烏龜拿着黃杆戥子。丁言志在腰裏摸出一個包子來,散散碎碎,共有二兩四錢五分頭。烏龜道:“還差五錢五分。”丁言志道:“會了姑娘,再找你罷。”丁言志自己上得樓來,看見聘娘在那裏打棋譜,上前作了一個大揖。聘娘覺得好笑,請他坐下,問他來做甚麼。丁言志道:“久仰姑娘最喜看詩,我有些拙作,特來請教。”聘娘道:“我們本院的規矩,詩句是不白看的,先要拿出花錢來再看。”丁言志在腰裏摸了半天,摸出二十個銅錢來放在花梨桌上。聘娘大笑道:“你這個錢,只好送給儀徵豐家巷的撈毛的,不要玷污了我的桌子!快些收了回去買燒餅喫罷!”丁言志羞得臉上一紅二白,低着頭,捲了詩,揣在懷裏,悄悄的下樓回家去了。
虔婆聽見他囮着呆子,要了花錢,走上樓來問聘娘道:“你剛纔向呆子要了幾兩銀子的花錢?拿來,我要買緞子去。”聘娘道:“那呆子那裏有銀子!拿出二十銅錢來,我那裏有手接他的!被我笑的他回去了!”虔婆道:“你是甚麼巧主兒!囮着呆子,還不問他要一大注子,肯白白放了他回去!你往常嫖客給的花錢,何常分一個半個給我?“聘娘道:“我替你家尋了這些錢,還有甚麼不是?些小事就來尋事!我將來從了良,不怕不做太太!你放這樣呆子上我的樓來,我不說你罷了,你還要來嘴喳喳!”虔婆大怒,走上前來,一個嘴巴,把聘娘打倒在地。聘娘打滾,撒了頭髮,哭道:“我貪圖些甚麼,受這些折磨!你家有銀子,不愁弄不得一個人來,放我一條生路去罷!”不由分說,向虔婆大哭大罵,要尋刀刎頸,要尋繩子上吊,?髻都滾掉了。虔婆也慌了,叫了老烏龜上來,再三勸解,總是不肯依,鬧的要死要活。無可奈何,由着他拜做延壽庵本慧的徒弟,剃光了頭,出家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風流雲散,賢豪才色總成空;薪盡火傳,工匠市廛都有韻。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