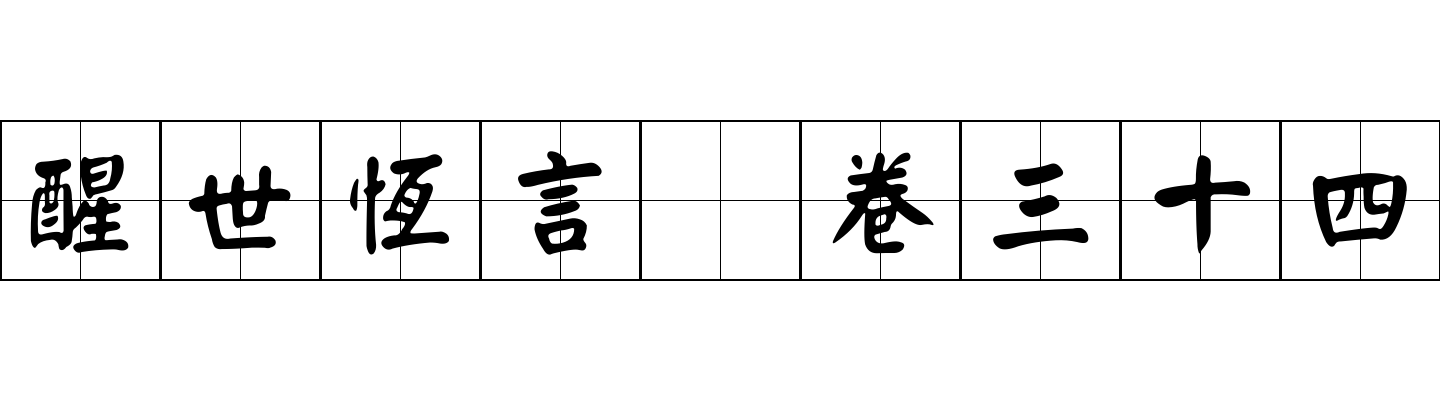醒世恆言-卷三十四-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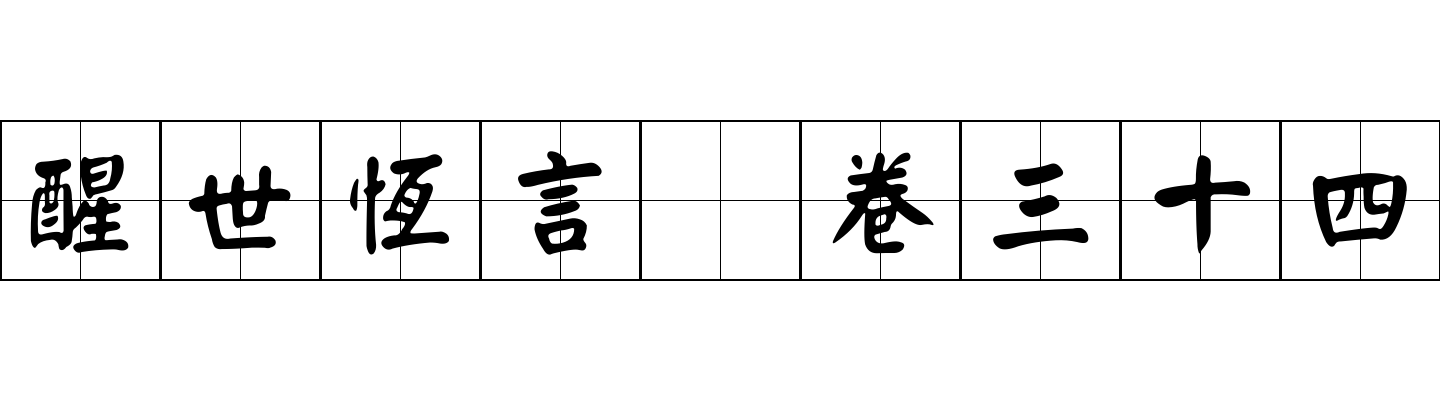
《醒世恆言》,白話短篇筆記集。明末馮夢龍纂輯。始刊於1627年(明天啓七年)。其題材或來自民間事實,或來自史傳和唐、宋故事。除少數宋元舊作外,絕大多數是明人作品,部分是馮氏擬作。形象鮮明,結構充實完整,描寫細膩,不同程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和市民思想感情。但有些作品帶有封建說教、因果報應宣傳和色情渲染。《醒世恆言》同作者之前刊行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一起,合稱《三言》,是最重要的中國古代白話短篇筆記集之一。通常亦與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並稱,稱爲“三言二拍”。
一文錢小隙造奇冤
世上何人會此言,休將名利掛心田。 等閒倒盡十分酒,遇興高歌一百篇。 物外菸霞爲伴侶,壺中日月任嬋娟。 他時功滿歸何處?直駕雲車入洞天。
這八句詩,乃回道人所作。那道人是誰?姓呂名巖,號洞賓,嶽州河東人氏。大唐鹹通中應進士舉,遊長安酒肆,遇正陽子鍾離先生,點破了黃梁夢,知宦途不足戀,遂求度世之術。鍾離先生恐他立志未堅,十遍試過,知其可度。欲授以黃白祕方,使之點石成金,濟世利物,然後三千功滿,八百行圓。洞賓問道:“所點之金,後來還有變異否?”鍾離先生答道:“直待三千年後,還歸本質。”洞賓愀然不樂道:“雖然遂我一時之願,可惜誤了三千年後遇金之人,弟子不願受此方也。”鍾離先生呵呵大笑道:“汝有此好心,三千八百盡在於此。吾向蒙苦竹真君吩咐道:‘汝遊人間,若遇兩口的,便是你的弟子。’遍遊天下,從沒見有兩口之人,今汝姓呂,即其人也。”遂傳以分合陰陽之妙。
洞賓修煉丹成,發誓必須度盡天下衆生,方肯上升,從此混跡塵途,自稱爲回道人。“回”字也是二“口”,暗藏著“呂”字。嘗遊長沙,手持小小磁罐乞錢,向市上大言:“我有長生不死之方,有人肯施錢滿罐,便以方授之。”市人不信,爭以錢投罐,罐終不滿。衆皆駭然。忽有一僧人推一車子錢從市東來,戲對道人說:“我這車子錢共有千貫,你罐裏能容之否?”道人笑道:“連車子也推得進,何況錢乎?”那僧不以爲然,想著:“這罐子有多少大嘴,能容得車兒?明明是說謊。”
道人見其沉吟,便道:“只怕你不肯佈施,若道個肯字,不愁這車子不進我罐兒裏去。”此時衆人聚觀者極多,一個個肉眼凡夫,誰人肯信。都去攛掇那僧人。那僧人也道必無此事,便道:“看你本事,我有何不肯?”道人便將罐子側著,將罐口向著車兒,尚離三步之遠,對僧人道:“你敢道三聲‘肯’麼?”僧人連叫三聲:“肯,肯,肯。”
每叫一聲“肯”,那車兒便近一步,到第三個“肯”字,那車兒卻像罐內有人扯拽一般,一溜子滾入罐內去了。衆人一個眼花,不見了車兒,發聲喊,齊道:“奇怪。奇怪。”都來張那罐口,只見裏面黑洞洞地。那僧人就有不悅之意,問道:“你那道人是神仙,不是幻術?”道人口占八句道:
非神亦非仙,非術亦非幻。 天地有終窮,桑田經幾變。 此身非吾有,財又何足戀。 苟不從吾遊,騎鯨騰汗漫。
那僧人疑心是個妖術,欲同衆人執之送官。道人道:“你莫非懊悔,不捨得這車子錢財麼?我今還你就是。”遂索紙筆,寫一道符,投入罐內,喝聲:“出,出。”衆人千百隻眼睛,看著罐口,並無動靜。道人說道:“這罐子貪財,不肯送將出來,待貧道自去討來還你。”說聲未了,聳身望罐口一跳,如落在萬丈深潭,影兒也不見了。那僧人連呼:“道人出來。道人快出來。”罐裏並不則聲。僧人大怒,提起罐兒,向地下一擲,其罐打得粉碎,也不見道人,也不見車兒,連先前衆人佈施的散錢並無一個,正不知那裏去了。只見有字紙一幅,取來看時,題得有詩四句道:
尋真要識真,見真渾未悟。 一笑再相逢,驅車東平路。
衆人正在傳觀,只見字跡漸滅,須臾之間,連這幅白紙也不見了。衆人才信是神仙,一鬨而散。只有那僧人失脫了一車子錢財,意氣沮喪,忽想著詩中“一笑再相逢,驅車東平路”之語,急急迴歸,行到東平路上,認得自家車兒,車上錢物宛然分毫不動。那道人立於車旁,舉手笑道:“相待久矣。錢車可自收之。”又嘆道:“出家之人,尚且惜錢如此,更有何人不愛錢者?普天下無一人可度,可憐哉,可痛哉。”言訖騰雲而去。那僧人驚呆了半晌,去看那車輪上,每邊各有一“口”字,二“口”成“呂”,乃知呂洞賓也。懊悔無及。
正是:
天上神仙容易遇,世間難得舍財人。
方纔說呂洞賓的故事,因爲那僧人捨不得這一車子錢,把個活神仙,當面挫過。有人論:這一車子錢,豈是小事,也怪那僧人不得,世上還有一文錢也捨不得的。依在下看來,捨得一車子錢,就從那捨得一文錢這一念推廣上去;捨不得一文錢,就從那捨不得一車子錢這一念算計入來。不要把錢多錢少,看做兩樣。如今聽在下說這一文錢小小的故事。列位看官們,各宜警醒,懲忿窒欲,且休望超凡入道,也是保身保家的正理。詩云:
不爭閒氣不貪錢,捨得錢時結得緣。 除卻錢財煩惱少,無煩無惱即神仙。
話說江西饒州府浮樑縣,有景德鎮,是個碼頭去處。鎮上百姓,都以燒造磁器爲業,四方商賈,都來載往蘇杭各處販賣,盡有利息。就中單表一人,叫做丘乙大,是窯戶家一個做手,渾家楊氏,善能描畫。乙大做就磁胚,就是渾家描畫花草、人物,兩口俱不喫空。住在一個冷巷裏,儘可度日有餘。那楊氏年三十六歲,貌頗不醜,也肯與人活動。只爲老公利害,只好背地裏偶一爲之,卻不敢明當做事。所生一子,名喚丘長兒,年一十四歲,資性愚魯,尚未會做活,只在家中走跳。
忽一日楊氏患肚疼,思想椒湯喫,把一文錢教長兒到市上買椒。長兒拿了一文錢,才走出門,剛剛遇著東間壁一般做磁胚劉三旺的兒子,叫做再旺,也走出門來。那再旺年十三歲,比長兒倒乖巧,平日喜的是攧錢耍子。怎的樣攧錢?也有八個六個,攧出或字或背,一色的謂之渾成。也有七個五個,攧去一背一字間花兒去的,謂之背間。再旺和長兒閒常有錢時,多曾在巷口一個空階頭上耍過來。這一日巷中相遇,同走到常時耍錢去處,再旺又要和長兒耍子,長兒道:“我今日沒有錢在身邊。”再旺道:“你往那裏去?”長兒道:“娘肚疼,叫我買椒泡湯喫。”再旺道:“你買椒,一定有錢。”長兒道:“只有得一文錢。”再旺道:“一文錢也好耍,我也把一文與你賭個背字,兩背的便都贏去,兩字便輸,一字一背不算。”
長兒道:“這文錢是要買椒的,倘或輸與你了,把什麼去買?”
再旺道:“不妨事,你若贏了是造化,若輸了時,我借與你,下次還我就是。”
長兒一時不老成,就把這文錢撇在地上。再旺在兜肚裏也摸出一個錢丟下地來。長兒的錢是個背,再旺的是個字。這攧錢也有先後常規,該是背的先攧。長兒撿起兩文錢,攤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指掐住,曲一曲腰,叫聲:“背。”攧將下去,果然兩背。長兒贏了,收起一文,留一文在地。再旺又在兜肚裏摸出一文錢來,連地下這文錢撿起,一般樣,攤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指掐住,曲一曲腰,叫聲:“背。”攧將下去,卻是兩個字,又是再旺輸了。長兒把兩個錢都收起,和自己這一文錢,共是三個。長兒贏得順溜,動了賭興,問再旺:“還有錢麼?”再旺道:“錢盡有,只怕你沒造化贏得。”
當下伸手在兜肚裏摸出十來個淨錢,捻在手裏,嘖嘖誇道:“好錢。好錢。”問長兒:“還敢攧麼?”又丟下一文來。長兒又攧了兩背,第四次再旺攧,又是兩字。一連攧了十來次,都是長兒贏了,共得了十二文,分明是掘藏一般。喜得長兒笑容滿面,拿了錢便走。再旺那肯放他,上前攔住,道:“你贏了我許多錢,走那裏去?”長兒道:“娘肚疼,等椒湯喫,我去去,閒時再來。”再旺道:“我還有錢在腰裏,你贏得時,都送你。”長兒只是要去,再旺發起喉急來,便道:“你若不肯攧時,還了我的錢便罷。你把一文錢來騙了我許多錢,如何就去?”長兒道:“我是攧得有采,須不是白奪你的。”再旺索性把兜肚裏錢,盡數取出,約莫有二三十文,做一堆兒堆在地下道:“待我輸盡了這些錢,便放你走。”
長兒是小廝家,眼孔淺,見了這錢,不覺貪心又起,況且再旺抵死纏住,只得又攧。誰知風無常順,兵無常勝。這番采頭又輪到再旺了。照前攧了一二十次,雖則中間互有勝負,卻是再旺贏得多。到結末來,這十二文錢,依舊被他復去。長兒剛剛原剩得一文錢。自古道:賭以氣勝。初番長兒攧贏了一兩文,膽就壯了,偶然有些采頭,就連贏數次。到第二番又攧時,不是他心中所願,況且著了個貪心,手下就覺有些矜持。到一連攧輸了幾文,去一個捨不得一個,又添了個吝字,氣便索然。怎當再旺一股憤氣,又且稍粗膽壯,自然贏了。
大凡人富的好過,貧的好過,只有先富後貧的,最是難過。據長兒一文錢起手時,贏得一二文也是勾了,一連得了十二文錢,一拳頭捻不住,就似白手成家,何等歡喜。把這錢不看做倘來之物,就認作自己東西,重複輸去,好不氣悶,癡心還想再像初次贏將轉來:“就是輸了,他原許下借我的,有何不可?”這一交,合該長兒攧了,忍不住按定心坎,再復一攧,又是二字,心裏著忙,就去搶那錢,手去遲些,先被再旺搶到手中,都裝入兜肚裏去了。長兒道:“我只有一文錢,要買椒的,你原說過贏時借我,怎的都收去了?”再旺怪長兒先前贏了他十二文錢就要走,今番正好出氣。君子報仇,直待三年,小人報仇,只在眼前,怎麼還肯把這文錢借他?把長兒雙手擋開,故意的一跳一舞,跑入巷去了。急得長兒且哭且叫,也回身進巷扯住再旺要錢,兩個扭做一堆廝打。
孫龐鬥智誰爲勝,楚漢爭鋒那個強?
卻說楊氏專等椒來泡湯喫,望了多時,不見長兒回來。覺得肚疼定了,走出門來張看,只見長兒和再旺扭住廝打,罵道:“小殺才。教你買椒不買,倒在此尋鬧,還不撒開。”兩個小廝聽得罵,都放了手。再旺就閃在一邊。楊氏問長兒:“買的椒在那裏?”長兒含著眼淚回道:“那買椒的一文錢,被再旺奪去了。”再旺道:“他與我攧錢,輸與我的。”楊氏只該罵自己兒子不該攧錢,不該怪別人。況且一文錢,所值幾何,既輸了去,只索罷休。單因楊氏一時不明,惹出一場大禍,展轉的害了多少人的性命。正是:
事不三思終有悔,人能百忍自無憂。
楊氏因等候長兒不來,一肚子惡氣,正沒出豁,聽說贏了他兒子的一文錢,便罵道:“天殺的野賊種。要錢時,何不教你娘趁漢?卻來騙我家小廝攧錢。”口裏一頭說,一頭便扯再旺來打。恰正抓住了兜肚,鑿下兩個栗暴。那小廝打急了,把身子負命一掙,卻掙斷了兜肚帶子,落下地來,索郎一聲響,兜肚子裏面的錢,撒做一地。楊氏道:“只還我那一文便了。”長兒得了孃的口氣,就勢搶了一把錢,奔進自屋裏去。
再旺就叫起屈來。楊氏趕進屋裏,喝教長兒還了他錢。長兒被娘逼不過,把錢望著街上一撒,再旺一頭哭,一頭罵,一頭撿錢。撿起時,少了六七文錢,情知是長兒藏下,攔著門只顧罵。楊氏道:“也不見這天殺的野賊種,恁地撒潑。”把大門關上,走進去了。
再旺敲了一回門,又罵了一回,哭到自屋裏去。母親孫大娘正在竈下燒火,問其緣故,再旺哭訴道:“長兒搶了我的錢,他的娘不說他不是,倒罵我天殺的野賊種,要錢時何不教你娘趁漢。”孫大娘不聽時萬事全休,一聽了這句不入耳的言語,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
原來孫大娘最疼兒子,極是護短,又兼性暴,能言快語,是個攬事的女都頭。若相罵起來,一連罵十來日,也不口乾,有名叫做綽板婆。他與丘家只隔得三四個間壁居住,也曉得楊氏平日有些不三不四的毛病,只爲從無口面,不好發揮出來。一聞再旺之語,太陽裏爆出火來,立在街頭,罵道:“狗潑婦,狗淫婦。自己瞞著老公趁漢子,我不管你罷了,倒來謗別人。老孃人便看不像,卻替老公爭氣。前門不進師姑,後門不進和尚,拳頭上立得人起,臂膊上走得馬過,不像你那狗淫婦,人硬貨不硬,表壯裏不壯,作成老公戴了綠帽兒,羞也不著。還虧你老著臉在街坊上罵人。便臊賤時,也不是恁般做作。我家小廝年小,連頭帶腦,也還不勾與你補空,你休得纏他。臊發時還去尋那舊漢子,是多尋幾遭,多養了幾個野賊種,大起來好做賊。”一聲潑婦,一聲淫婦,罵一個路絕人稀。楊氏怕老公,不敢攬事,又沒處出氣,只得罵長兒道:“都是你那小天殺的不學好,引這長舌婦開口。”提起木柴,把長兒劈頭就打,打得長兒頭破血淋,嚎啕大哭。丘乙大正從窯上回來,聽得孫大娘叫罵,側耳多時,一句句都聽在肚裏,想道:“是那家婆娘不秀氣?替老公妝幌子,惹這綽板婆叫罵。”
及至回家,見長兒啼哭,問起緣繇,倒是自家家裏招攬的是非。丘乙大是個硬漢,怕人恥笑,聲也不嘖,氣忿忿地坐下。
遠遠的聽得罵聲不絕,直到黃昏後,方纔住口。
丘乙大吃了幾碗酒,等到夜深人靜,叫老婆來盤問道:“你這賤人瞞著我幹得好事。趁的許多漢子,姓甚名誰?好好招將出來,我自去尋他說話。”那婆娘原是怕老公的,聽得這句話,分明似半空中響一個霹靂,戰兢兢還敢開口?丘乙大道:“潑賤婦,你有本事偷漢子,如何沒本事說出來?若要不知,除非莫爲。瞞得老公,瞞不得鄰里,今日教我如何做人。
你快快說來,也得我心下明白。”楊氏道:“沒有這事,教我說誰來?”丘乙大道:“真個沒有?”楊氏道:“沒有。”丘乙大道:“既是沒有時,他們如何說你,你如何憑他說,不則一聲?顯是心虛口軟,應他不得。若是真個沒有,是他們作說你時,你今夜吊死在他門上,方表你清白,也出脫了我的醜名,明日我好與他講話。”
那婆娘怎肯走動,流下淚來,被丘乙大三兩個巴掌,推出大門,把一條麻索丟與他,叫道:“快死快死。不死便是戀漢子了。”說罷,關上門兒進來。長兒要來開門,被乙大一頓栗暴,打得哭了一場睡去了。乙大有了幾分酒意,也自睡了。
單撇楊氏在門外好苦,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千不是,萬不是,只是自家不是,除卻死,別無良策。自悲自怨了多時,恐怕天明,慌慌張張的取了麻索,去認那劉三旺的門首。也是將死之人,失魂顛智,劉家本在東間壁第三家,卻錯走到西邊去,走過了五六家,到第七家。見門面與劉家相像,忙忙的把幾塊亂磚襯腳,搭上麻索於檐下,繫頸自盡。可憐伶俐婦人,只爲一文錢鬥氣,喪了性命。正是:
地下新添惡死鬼,人間不見畫花人。
卻說西鄰第七家,是個打鐵的匠人門首。這匠人渾名叫做白鐵,每夜四更,便起來打鐵。偶然開了大門撒溺,忽然一陣冷風,吹得毛骨竦然,定睛看時,吃了一驚。
不是傀儡場中鮑老,也像鞦韆架上佳人。
檐下掛著一件物事,不知是那裏來的,好不怕人。猶恐是眼花,轉身進屋,點個亮來一照,原來是新縊的婦人,咽喉氣斷,眼見得救不活了。欲待不去照管他,到天明被做公的看見,卻不是一場飛來橫禍,辨不清的官司,思量一計:“將他移在別處,與我便無干了。”耽著驚恐,上前去解這麻索。那白鐵本來有些蠻力,輕輕的便取下掛來,背出正街,心慌意急,不暇致詳,向一家門裏撇下,頭也不回,竟自歸家,兀自連打幾個寒噤,鐵也不敢打了,覆上牀去睡臥,不在話下。
且說丘乙大黑蚤起來開門,打聽老婆消息,走到劉三旺門前,並無動靜,直走到巷口,也沒些蹤影,又回來坐地尋思:“莫不是這賤婦逃走他方去了?”又想:“他出門稀少,又是黑暗裏,如何行動?”又想道:“他若不死時,麻索必然還在。”再到門前看時,地下不見麻繩:“定是死在劉家門首,被他知覺,藏過了屍首,與我白賴。”又想:“劉三旺昨晚不回,只有那綽板婆和那小廝在家,那有力量搬運?”又想道:“蟲蟻也有幾隻腳兒,豈有人無幫助?且等他開門出來,看他什麼光景,見貌辨色,可知就裏。”等到劉家開門,再旺出來,把錢去市心裏買饃饃點心,並不見有一些驚慌之意。丘乙大心中委決不下,又到街前街後閒蕩,打探一回,並無影響。回來看見長兒還睡在牀上打齁,不覺怒起,掀開被,向腿上四五下,打得這小廝睡夢裏直跳起來。丘乙大道:“娘也被劉家逼死了,你不去討命,還只管睡。”這句話,分明丘乙大教長兒去惹事,看風色。
長兒聽說娘死了,便哭起來,忙忙的穿了衣服,帶著哭,一逕直趕到劉三旺門首,大罵道:“狗娼根,狗淫婦。還我娘來。”那綽板婆孫大娘見長兒罵上門,如何耐得,急趕出來,罵道:“千人射的野賊種,敢上門欺負老孃麼?”便揪著長兒頭髮,卻待要打,見丘乙大過來,就放了手。這小廝滿街亂跳亂舞,帶哭帶罵討娘。丘乙大已耐不住,也罵起來。綽板婆怎肯相讓,旁邊鑽出個再旺來相幫,兩下乾罵一場,鄰里勸開。
丘乙大教長兒看守家裏,自去街上央人寫了狀詞,趕到浮樑縣告劉三旺和妻孫氏人命事情。大尹準了狀詞,差人拘拿原被告和鄰里幹證,到官審問。原來綽板婆孫氏平昔口嘴不好,極是要衝撞人,鄰里都不歡喜,因此說話中間,未免偏向丘乙大幾分,把相罵的事情,增添得重大了,隱隱的將這人命,射實在綽板婆身上。這大尹見衆人說話相同,信以爲實,錯認劉三旺將屍藏匿在家,希圖脫罪。差人搜檢,連地也翻了轉來,只是搜尋不出,故此難以定罪。且不用刑,將綽板婆拘禁,差人押劉三旺尋訪楊氏下落,丘乙大討保在外。
這場官司好難結哩。有分教:
綽板婆消停口舌,磁器匠擔誤生涯。
這事且擱過不題。再說白鐵將那屍首,卻撇在一個開酒店的人家門首。那店中人王公,年紀六十餘歲,有個媽媽,靠著賣酒過日。是夜睡至五更,只聽得叩門之聲,醒時又不聽得。剛剛閤眼,卻又聞得閛閛聲叩響。心中驚異,披衣而起,即喚小二起來,開門觀看。只見街頭上不橫不直,擋著這件物事。王公還道是個醉漢,對小二道:“你仔細看一看,還是遠方人,是近處人?若是左近鄰里,可叩他家起來,扶了去。”
小二依言,俯身下去認看,因背了星光,看不仔細,見頸邊拖著麻繩,卻認做是條馬鞭,便道:“不是近邊人,想是個馬伕。”王公道:“你怎麼曉得他是個馬伕?”小二道:“見他身邊有根馬鞭,故此知得。”王公道:“既不是近處人,由他罷。”
小二欺心,要拿他的鞭子,伸手去拾時,卻拿不起,只道壓在身底下,盡力一扯,那屍首直豎起來,把小二嚇了一跳,叫道:“阿呀。”連忙放手,那屍撲的倒下去了。連王公也喫一驚,問道:“這怎麼說?”小二道:“只道是根鞭兒,要拿他的,不想卻是縊死的人,頸下扣的繩子。”王公聽說,慌了手腳,欲待叫破地方,又怕這沒頭官司惹在身上。不報地方,這事卻是洗身不清,便與小二商議,小二道:“不打緊,只教他離了我這裏,就沒事了。”王公道:“說得有理,還是拿到那裏去好?”小二道:“撇他在河裏罷。”當下二人動手,直擡到河下。遠遠望見岸上有人,打著燈籠走來,恐怕被他撞見,不管三七二十一,撇在河邊,奔回家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岸上打燈籠來的是誰?那人乃是本鎮一個大戶叫做朱常,爲人奸詭百出,變詐多端,是個好打官司的主兒。因與隔縣一個姓趙的人家爭田,這一蚤要到田頭去割稻,同著十來個家人,拿了許多扁挑索子鐮刀,正來下船。那提燈的在前,走下岸來,只見一人橫倒在河邊,也認做是個醉漢,便道:“這該死的貪這樣膿血。若再一個翻身,卻不滾在河裏,送了性命?”內中一個家人,叫做卜才,是朱常手下第一齣尖的幫手,他只道醉漢身邊有些錢鈔,就蹲倒身,伸手去摸他腰下,卻冰一般冷,嚇得縮手不迭,便道:“原來死的了。”朱常聽說是死人,心下頓生不良之念,忙叫:“不要嚷。把燈來照看,是老的?是少的?”衆人在燈下仔細打一認,卻是個縊死的婦人。朱常道:“你們把他頸裏繩子快解掉了,打下艄裏去藏好。”衆人道:“老爹,這婦人正不知是甚人謀死的?我們如何卻倒去招攬是非?”朱常道:“你莫管,我自有用處。”
衆人只得依他,解去麻繩,叫起看船的,打上船,藏在艄裏,將平基蓋好。
朱常道:“卜才,你回去,媳婦子叫五六個來。”卜才道:“這二三十畝稻,勾什麼砍,要這許多人去做甚?”朱常道:“你只管叫來,我自有用處。”卜纔不知是甚意見,即便提燈回去,不一時叫到,坐了一船,解纜開船。兩人蕩槳,離了鎮上。衆人問道:“老爹載這東西去有甚用處?”朱常道:“如今去割稻,趙家定來攔阻,少不得有一場相打,到告狀結殺。
如今天賜這東西與我,豈不省了打官司,還有許多妙處。”衆人道:“老爹怎見省了打官司?又有妙處?”朱常道:“有了這屍首時,只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卻不省了打官司,你們也有些財採。他若不見機,弄到當官,定然我們佔個上風,可不好麼。”衆人都喜道:“果然妙計。小人們怎省得?”正是:
算定機謀誇自己,安排圈套害他人。
這些人都是愚野村夫,曉得什麼利害?聽見家主說得都有財採,竟像甕中取鱉、手到擒來的事,樂極了,巴不得趙家的人,這時就到船邊來廝鬧便好:銀子既有得到手,官司又可以贏得。心裏一急,發狠蕩起槳來,這船恰像生了七八個翅膀一般,頃刻就飛到了。此時天色漸明,朱常教把船歇在空闊無人居住之處,離田中尚有一箭之路。衆人都上了岸,尋出一條一股連一股斷的爛草繩,將船纜在一顆草根上,止留一個人坐在艄上看守,衆男女都下田割稻。朱常遠遠的站在岸上打探消耗。原來這地方叫做鯉魚橋,離景德鎮只有十里多遠,再過去裏許,又喚做太白村,乃南直隸徽州府婺源縣所管。因是兩省交界之處,人人錯壤而居。與朱常爭田這人名喚趙完,也是個大富之家,原是浮樑縣人戶,卻住在婺源縣地方。兩縣俱置得有田產。那爭的田,止得三十餘畝,乃趙完族兄趙寧的。先把來抵借了朱常銀子,卻又賣與趙完,恐怕出醜,就攬來佃種,兩邊影射了三四年。不想近日身死,故此兩家相爭。這稻子還是趙寧所種。
說話的,這田在趙完屋腳跟頭,如何不先割了,卻留與朱常來割?看官有所不知,那趙完也是個強橫之徒,看得自己大了,道這田是明中正契買族兄的,又在他的左近;朱常又是隔省人戶,料必不敢來割稻,所以放心托膽。那知朱常又是個專在虎頭上做窠,要喫不怕死的魍魎,竟來放對,正在田中砍稻。蚤有人報知趙完。趙完道:“這廝真是吃了大蟲的心,豹子的膽,敢來我這裏撩撥。想是來送死麼。”兒子趙壽道:“爹,自古道:‘來者不懼,懼者不來。’也莫輕覷了他。”
趙完問報人道:“他們共有多少人在此?”答道:“十來個男子,六七個婦人。”趙完道:“既如此,也教婦人去。男對男,女對女,都拿回來,敲斷他的孤拐子。連船都拔他上岸,那時方見我的手段。”即便喚起二十多人,十來個婦人,一個個粗腳大手,裸臂揎拳,如疾風驟雨而來。趙完父子隨後來看。
且說衆人遠遠的望著田中,便喊道:“偷稻的賊不要走。”
朱常家人媳婦,看見趙家有人來了,連忙住手,望河邊便跑。
到得岸旁,朱常連叫快脫衣服。衆人一齊卸下,堆做一處,叫一個婦人看守,復身轉來,叫道:“你來你來,若打輸與你,不爲好漢。”趙完家有個僱工人,叫做田牛兒,自恃有些氣力,搶先飛奔向前。朱家人見他勢頭來得勇猛,兩邊一閃,讓他衝將過來。才讓他衝進時,男子婦人,一裹轉來圍住。田牛兒叫聲:“來的好。”提起升籮般拳頭,揀著個精壯村夫面上,一拳打去,只指望先打倒了一個硬的,其餘便如摧枯拉朽了。
誰知那人卻也來得,拳到面上時,將頭略偏一偏,這拳便打個空,剛落下來,就順手牽羊把拳留住。田牛兒摔脫不得,急起左拳來打,手尚未起,又被一人接住,兩邊扯開。田牛兒便施展不得。朱家人也不打他,推的推,扯的扯,倒像八擡八綽一般,腳不點地竟拿上船。那爛草繩系在草根上,有甚筋骨,初踏上船就斷了。艄上人已預先將篙攔住,衆人將田牛兒納在艙中亂打。
趙家後邊的人,見田牛兒捉上船去,蜂擁趕上船搶人。朱家婦女都四散走開,放他上去。說時遲,那時快,攔篙的人一等趙家男子婦人上齊船時,急掉轉篙,望岸上用力一點,那船如箭一般,向河心中直盪開去。人衆船輕,三四幌便翻將轉來。兩家男女四十多人,盡都落水。這些婦人各自掙扎上岸,男子就在水中相打,縱橫攪亂,激得水濺起來,恰如驟雨相似,把岸上看的人眼都耀花了,只叫莫打,有話上岸來說。正打之間,卜才就人亂中,把那縊死婦人屍首,直推過去,便喊起來道:“地方救護,趙家打死我家人了。”朱常同那六七個婦人,在岸邊接應,一齊喊叫,其聲震天動地。趙家的婦人正絞擠溼衣,聽得打死了人,帶水而逃。水裏的人,一個個嚇得膽戰心驚,正不知是那個打死的,巴不能攦脫逃走。被朱家人乘勢追打,吃了老大的虧,掙上了岸,落荒逃奔,此時只恨父母少生了兩隻腳兒。
朱家人慾要追趕,朱常止住道:“如今不是相打的事了,且把屍首收拾起來,擡放他家屋裏了再處。”衆人把屍首拖到岸上,卜才認做妻子,假意啼啼哭哭。朱常又教撈起船上篙槳之類,寄頓佃戶人家,又對看的人道:“列位地方鄰里,都是親眼看見,活打死的,須不是誣陷趙完。倘到官司時,少不得要相煩做個證見,但求實說罷了。”這幾句是朱常引人來兜攪處和的話。此時內中若有個有力量的出來擔當,不教朱常把屍首擡去趙家說和,這事也不見得後來害許多人的性命。
只因趙完父子平日是個難說話的,恐怕說而不聽,反是一場沒趣,況又不曉得朱常心中是甚樣個意兒,故此並無一人招攬。朱常見無人招架,教衆人穿起衣服,把屍首用蘆蓆捲了,將繩索絡好,四人扛著,望趙完家來。看的人隨後跟來,觀看兩家怎地結局?
銅盆撞了鐵掃帚,惡人自有惡人磨。
且說趙完父子隨後走來,遠望著自家人追趕朱家的人,心中歡喜。漸漸至近,只見婦女家人,渾身似水,都像落湯雞一般,四散奔走。趙完驚訝道:“我家人多,如何反被他都打下水去?”急挪步上前,衆人看見亂喊道:“阿爹不好了。快回去罷。”趙壽道:“你們怎地恁般沒用?都被打得這模樣。”
衆人道:“打是小事,只是他家死了人卻怎處?”趙完聽見死了個人,嚇得就酥了半邊,兩隻腳就像釘了,半步也行不動。
趙壽與田牛兒,兩邊挾著胳膊而行,扶至家中坐下,半晌方纔開言問道:“如何就打死了人?”衆人把相打翻船的事,細說一遍,又道:“我們也沒有打婦人,不知怎地死了?想是淹死的。”趙完心中沒了主意,只叫:“這事怎好?”那時閤家老幼,都叢在一堆,人人心下驚慌。正說之間,人進來報:“朱家把屍首擡來了。”趙完又喫這一嚇,恰像打坐的禪和子,急得身色一毫不動。
自古道:“物極則反,人急計生。”趙壽忽地轉起一念。便道:“爹莫慌,我自有對付他的計較在此。”便對衆人道:“你們都向外邊閃過,讓他們進來之後,聽我鳴鑼爲號,留幾個緊守門口,其餘都趕進來拿人,莫教走了一個。解到官司,見許多人白日搶劫,這人命自然從輕。”衆人得了言語,一齊轉身。趙完恐又打壞了人,吩咐:“只要拿人,不許打人。”衆人應允,一陣風出去。趙壽只留下一個心腹義孫趙一郎道:“你且在此。”又把婦女妻小打發進去,吩咐:“不要出來。”趙完對兒子道:“雖則告他白日打搶,終是人命爲重,只怕抵擋不過。”趙壽走到耳根前,低低道:“如今只消如此這般。”趙完聽了大喜,不覺身子就健旺起來,乃道:“事不宜遲,快些停當。”趙壽先把各處門戶閉好,然後尋了一把斧頭,一個棒棰,兩扇板門,都已完備,方教趙一郎到廚下叫出一個老兒來。
那老兒名喚丁文,約有六十多歲,原是趙完的表兄,因有了個懶黃病,喫得做不得,卻又無男無女,捱在趙完家燒火,博口飯喫。當下老兒不知頭腦,走近前問道:“兄弟有甚話?”趙完還未答應,趙壽閃過來,提起棒捶,看正太陽,便是一下。那老兒只叫得聲“阿呀”,翻身跌倒。趙壽趕上,又復一下,登時了帳。當下趙壽動手時,以爲無人看見,不想田牛兒的娘田婆,就住在趙完宅後,聽見打死了人,恐是兒子打的,心中著急,要尋來問個仔細,從後邊走出,正撞著趙壽行兇。嚇得蹲倒在地,便立不起身,口中念聲:“阿彌陀佛。青天白日,怎做這事。”趙完聽得,回頭看了一看,把眼向兒子一顛。趙壽會意,急趕近前,照頂門一棒棰打倒,腦漿鮮血一齊噴出。還怕不死,又向肋上三四腳,眼見得不能勾活了。只因這一文錢上起,又送了兩條性命。正是:
耐心終有益,任意定生災。
且說趙一郎起初喚丁老兒時,不道趙壽懷此惡念,驀見他行兇,驚得直縮到一壁角邊去。丁老兒剛剛完事,接腳又撞個田婆來湊成一對,他恐怕這第三棒捶輪到頭上,心下著忙,欲待要走,這腳上卻像被千百斤石頭壓住,那裏移得動分毫。正在慌張,只見趙完叫道:“一郎快來幫一幫。”趙一郎聽見叫他相幫,方纔放下肚腸,掙扎得動,向前幫趙壽拖這兩個屍首,放在遮堂背後,尋兩扇板門壓好,將遮堂都起浮了窠臼。又吩咐趙一郎道:“你切不可泄漏,待事平了,把傢俬分一股與你受用。”趙一郎道:“小人靠阿爹洪福過日的,怎敢泄漏?”剛剛準備停當,外面人聲鼎沸,朱家人已到了。
趙完三人退入側邊一間屋裏,掩上門兒張看。
且說朱常引家人媳婦,扛著屍首趕到趙家,一路打將進去。直到堂中,見四面門戶緊閉,並無一個人影。朱常教:“把屍首居中停下,打到裏邊去拿趙完這老忘八出來,鎖在死屍腳上。”衆人一齊動手,乒乒乓乓將遮堂亂打,那遮堂已是離了窠臼的,不消幾下,一扇扇都倒下去,屍首上又壓上一層。衆人只顧向前,那知下面有物。趙壽見打下遮堂,把鑼篩起,外邊人聽見,發聲喊,搶將入來。朱常聽得篩鑼,只道有人來搶屍首,急掣身出來,衆人已至堂中,兩下你揪我扯,攪做一團,滾做一塊。裏邊趙完三人大喊:“田牛兒,你母親都被打死了,不要放走了人。”田牛兒聽見,急奔來問:“我母親如何卻在這裏?”趙完道:“他剛同丁老官走來問我,遮堂打下,壓死在內。我急走得快,方逃得性命,若遲一步兒,這時也不知怎地了。”田牛兒與趙一郎將遮堂搬開,露出兩個屍首。田牛兒看娘時,頭已打開,腦漿鮮血滿地,放聲大哭。朱常聽見,只道是假的,急抽身一望,果然有兩個屍首,著了忙,往外就跑。這些家人媳婦,見家主走了,各要攦脫逃走,一路揪扭打將出來。那知門口有人把住,一個也走不脫,都被拿住。趙完只叫:“莫打壞了人。”故此朱常等不十分喫虧。趙壽取出鏈子繩索,男子婦女鎖做一堂。田牛兒痛哭了一回,心中忿怒,跳起身道:“我把朱常這狗王八,照依母親打死罷了。”趙完攔住道:“不可不可。如今自有官法治了,你打他做甚?”教衆人扯過一邊。此時已鬨動遠近村坊、地方鄰里,無有不到趙家觀看。趙完留到後邊,備起酒飯款待,要衆人具個“白晝劫殺”公呈。那些人都是趙完的親戚佃戶、僱工人等,誰敢不依。
趙完連夜裝起四五隻農船,載了地鄰幹證人等,把兩隻將朱常一家人鎖縛在艙裏,行了一夜,方到婺源縣中,候大尹早衙升堂。地方人等先將呈子具上。這大尹展開觀看一過,問了備細,即差人押著地方並屍親趙完、田牛兒、卜才前去。
將三個屍首盛殮了,吊來相驗。朱常一家人都發在鋪裏羈候。
那時朱常家中自有佃戶報知。兒子朱太星夜趕來看覷,自不必說。
有句俗語道得好:“官無三日急。”那屍棺便吊到了,這大尹如何就有工夫去相驗?隔了半個多月,方纔出牌,著地方備辦登場法物。鋪中取出朱常一干人都到屍場上。仵作人逐一看報道:“丁文太陽有傷,周圍二寸有餘,骨頭粉碎。田婆腦門打開,腦髓漏盡,右肋骨踢折三根。二人實系打死。卜才妻子,頸下有縊死繩痕,遍身別無傷損,此係縊死是實。”
大尹見報,心中駭異,道:“據這呈子上稱說船翻落水身死,如何卻是縊死的?”朱常就稟道:“爺爺,衆耳衆目所見,如何卻是縊死的?這明明仵作人得了趙完銀子,妄報老爺。”大尹恐怕趙完將別個屍首顛換了,便喚卜才:“你去認這屍首,正是你妻子的麼?”卜才上前一認,回覆道:“正是小人妻子。”
大尹道:“是昨日登時死的?”卜才道:“是。”大尹問了詳細,自走下來把三個屍首逐一親驗,忤作人所報不差,暗稱奇怪。
吩咐把棺木蓋上封好,帶到縣裏來審。
大尹在轎上,一路思想,心下明白,回縣坐下,發衆犯都跪在儀門外,單喚朱常上去,道:“朱常,你不但打死趙家二命,連這婦人,也是你謀死的。須從實招來。”朱常道:“這是家人卜才的妻子餘氏,實被趙完打下水死的,地方上人,都是見的,如何反是小人謀死?爺爺若不信,只問卜才便見明白。”大尹喝道:“胡說。這卜才乃你一路之人,我豈不曉得。敢在我面前支吾。夾起來。”衆皁隸一齊答應上前,把朱常鞋襪去了,套上夾棍,便喊起來。那朱常本是富足之人,雖然好打官司,從不曾受此痛苦,只得一一吐實:“這屍首是浮樑江口不知何人撇下的。”
大尹錄了口詞,叫跪在丹墀下。又喚卜才進來,問道:“死的婦人果是你妻子麼?”卜才道:“正是小人妻子。”大尹道:“既是你妻子,如何把他謀死了,詐害趙完?”卜才道:“爺爺,昨日趙完打下水身死,地方上人,都看見的。”大尹把氣拍在桌上一連七八拍,大喝道:“你這該死的奴才。這是誰家的婦人,你冒認做妻子,詐害別人。你家主已招稱,是你把他謀死。還敢巧辯,快夾起來。”卜才見大尹像道士打靈牌一般,把氣拍一片聲亂拍亂喊,將魂魄都驚落了,又聽見家主已招,只得稟道:“這都是家主教小人認作妻子,並不幹小人之事。”大尹道:“你一一從實細說。”卜纔將下船遇見屍首,定計詐趙完前後事細說一遍,與朱常無二。
大尹已知是實,又問道:“這婦人雖不是你謀死,也不該冒認爲妻,詐害平人。那丁文、田婆卻是你與家主打死的,這須沒得說。”卜才道:“爺爺,其實不曾打死,就夾死小人,也不招的。”大尹也教跪下丹墀,又喚趙完並地方來問,都執朱常扛屍到家,乘勢打死。大尹因朱常造謀詐害趙完事實,連這人命也疑心是真,又把朱常夾起來。朱常熬刑不起,只得屈招。大尹將朱常、卜才各打四十,擬成斬罪,下在死囚牢裏。其餘十人,各打二十板,三個充軍,七個徒罪,亦各下監。六個婦人,都是杖罪,發回原籍。其田斷歸趙完,代趙寧還原借朱常銀兩。又行文關會浮樑縣查究婦人屍首來歷。
那朱常初念,只要把那屍首做個媒兒,趙完怕打人命官司,必定央人兜收私處,這三十多畝田,不消說起歸他,還要紮詐一注大錢,故此用這一片心機。誰知激變趙壽做出沒天理事來對付,反中了他計。當下來到牢裏,不勝懊悔,想道:“這蚤若不遇這屍首,也不見得到這地位。”正是:
蚤知更有強中手,卻悔當初枉用心。
朱常料道:“此處定難翻案。”叫兒子吩咐道:“我想三個屍棺,必是釘稀板薄,交了春氣,自然腐爛。你今先去會了該房,捺住關會文書。回去教婦女們,莫要泄漏這縊死屍首消息。一面向本省上司去告準,捱至來年四五月間,然後催關去審,那時爛沒了縊死繩痕,好與他白賴。一事虛了,事事皆虛,不愁這死罪不脫。”朱太依著父親,前去行事,不在話下。
卻說景德鎮賣酒王公家小二因相幫撇了屍首,指望王公些東西,過了兩三日,卻不見說起。小二在口內野唱,王公也不在其意。又過了幾日,小二不見動靜,心中焦躁,忍耐不住,當面明明說道:“阿公,前夜那話兒,虧我把去出脫了還好,若沒我時,到天明地方報知官司,差人出來相驗,饒你硬掙,不使酒錢,也使茶錢。就拌上十來擔涎吐,只怕還不得乾淨哩。如今省了你許多錢鈔,怎麼竟不說起謝我?”大凡小人度量極窄,眼孔最淺:偶然替人做件事兒,僥倖得效,便道是天大功勞,就來挾制那人,責他厚報,稍不遂意,便把這事翻局來害。往往人家用錯了人,反受其累。譬如小二不過一時用得些氣力,便想要王公的銀子。那王公若是個知事的,不拘多寡與他些也就罷了,誰知王公又是捨不得一文錢的慳吝老兒,說著要他的錢,恰像割他身上的肉,就面紅頸赤起來了。
當下王公見小二要他銀子,便發怒道:“你這人忒沒理!喫黑飯,護漆柱。吃了我家的飯,得了我的工錢,便是這些小事,略走得幾步,如何就要我錢?”小二見他發怒,也就嚷道:“●呀!就不把我,也是小事,何消得喉急?用得我著,方喫得你的飯,賺得你的錢,須不是白把我用的。還有一句話,得了你工錢,只做得生活,原不曾說替你拽死屍的。”王婆便走過來道:“你這蠻子,真個憊懶!自古道:‘茄子也讓三分老。’怎麼一個老人家,全沒些尊卑,一般樣與他爭嚷!”
小二道:“阿婆,我出了力,不把銀子與我,反發喉急,怎不要嚷?”王公道:“什麼!是我謀死的?要詐我錢!”小二道:“雖不是你謀死,便是擅自移屍,也須有個罪名。”王公道:“你倒去首了我來。”小二道:“要我首也不難,只怕你當不起這大門戶。”王公趕上前道:“你去首,我不怕。”望外劈頸就推。那小二不曾提防,捉腳不定,翻筋斗直跌出門外,磕碎腦後,鮮血直淌。小二跌毒了,罵道:“老忘八!虧了我,反打麼!”就地下拾起一塊磚來,望王公擲去。誰知數合當然,這磚不歪不斜,恰恰正中王公太陽,一交跌倒,再不則聲。王婆急上前扶時,只見口開眼定,氣絕身亡。跌腳叫苦,便哭起天來。只因這一文錢上,又送一條性命。
總爲惜財喪命,方知財命相連。
小二見王公死了,爬起來就跑。王婆喊叫鄰里,趕上拿轉,鎖在王公腳上。問王婆:“因甚事起?”王婆一頭哭,一頭將前情說出,又道:“煩列位與老身作主則個。”衆人道:“這廝原來恁地可惡!先教他喫些痛苦,然後解官。”三四個鄰里走上前,一頓拳頭腳尖,打得半死,方纔住手。教王婆關閉門戶,同到縣中告狀。此時紛紛傳說,遠近人都來觀看。
且說丘乙大正訪問妻子屍首不著,官司難結,心中氣悶。
這一日聞得小二打死王公的根繇,想道:“這婦人屍首,莫不就是我妻子麼?”急走來問,見王婆正鎖門要去告狀。丘乙大上前問了詳細,計算日子,正是他妻子出門這夜,便道:“怪道我家妻子屍首,當朝就不見蹤影,原來卻是你們撇掉了。如今有了實據,綽板婆卻白賴不過了。我同你們見官去!”
當下一干人牽了小二,直到縣裏。次早大尹升堂,解將進去。地方將前後事細稟。大尹又喚王婆問了備細。小二料道情真難脫,不待用刑,從實招承。打了三十,問成死罪,下在獄中。丘乙大稟說妻子被劉三旺謀死正是此日,這屍首一定是他撇下的。證見已確,要求審結。此時婺源縣知會文書未到,大尹因沒有屍首,終無實據。原發落出去尋覓。再說小二,初時已被鄰里打傷,那頓板子,又十分利害。到了獄中,沒有使用,又遭一頓拳腳,三日之間,血崩身死。爲這一文錢起,又送一條性命。
只因貪白鏹,番自喪黃泉。
且說丘乙大從縣中回家,正打白鐵門首經過,只聽得裏邊叫天叫地的啼哭。原來白鐵自那夜擔著驚恐,出脫這屍首,冒了風寒,回家上得牀,就發起寒熱,病了十來日,方纔斷命。所以老婆啼哭。眼見爲這一文錢,又送一條性命。
化爲陰府驚心鬼,失卻陽間打鐵人。
丘乙大聞知白鐵已死,嘆口氣道:“恁般一個好漢!有得幾日,卻又了帳。可見世人真是沒根的!”走到家裏,單單止有這個小廝,鬼一般縮在半邊,要口熱水,也不能勾。看了那樣光景,方懊悔前日逼勒老婆,做了這樁拙事。如今又弄得不尷不尬,心下煩惱,連生意也不去做,終日東尋西覓,並無屍首下落。
看看捱過殘年,又蚤五月中旬。那時朱常兒子朱太已在按院告準狀詞,批在浮樑縣審問,行文到婺源縣關提人犯屍棺。起初朱太還不上緊,到了五月間,料得屍首已是腐爛,大大送個東道與婺源縣該房,起文關解。那趙完父子因婺源縣已經問結,自道沒事,毫無畏懼,抱卷赴理。兩縣解子領了一干人犯,三具屍棺,直至浮樑縣當堂投遞。大尹將人犯羈禁,屍棺發置官壇候檢,打發婺源迴文,自不必說。
不則一日,大尹吊出衆犯,前去相驗。那朱太合衙門通買囑了,要勝趙完。大尹到屍場上坐下,趙完將浮樑縣案卷呈上。大尹看了,對朱常道:“你借屍索詐,打死二命,事已問結,如何又告?”朱常稟道:“爺爺,趙完打餘氏落水身死,衆目共見;卻買囑了地鄰忤作,妄報是縊死的。那丁文、田婆,自己情慌,謀害抵飾,硬誣小人打死。且不要論別件,但據小人主僕俱被拿住,趙完是何等勢力,卻容小人打死二命?況死的俱年七十多歲,難道恁地不知利害,只揀垂死之人來打?爺爺推詳這上,就見明白。”大尹道:“既如此,當時怎就招承?”朱常道:“那趙完衙門情熟,用極刑拷逼,若不屈招,性命已不到今日了。”趙完也稟道:“朱常當日倚仗假屍,逢著的便打,闔家躲避。那丁文、田婆年老奔走不及,故此遭了毒手。假屍縊死繩痕,是婺源縣太爺親驗過的,豈是忤作妄報!如今日久腐爛,巧言誑騙爺爺,希圖漏網反陷。但求細看招卷,曲直立見。”大尹道:“這也難憑你說。”即教開棺檢驗。
天下有這等作怪的事,只道屍首經了許多時,已腐爛盡了,誰知都一毫不變,宛然如生。那楊氏頸下這條繩痕,轉覺顯明,倒教忤作人沒做理會。你道爲何?他已得了朱常錢財,若屍首爛壞了,好從中作弊,要出脫朱常,反坐趙完。如今傷痕見在,若虛報了,恐大尹還要親驗;實報了,如何得朱常銀子?正在躊躇,大尹蚤已瞧破,就走下來親驗。那忤作人被大尹監定,不敢隱匿,一一實報。朱常在傍暗暗叫苦。
大尹把所報傷處,將卷對看,分毫不差,對朱常道:“你所犯已實,怎麼又往上司誑告?”朱常又苦苦分訴。大尹怒道:“還要強辨!夾起來!快說這縊死婦人是那裏來的?”朱常受刑不過,只得招出:“本日蚤起,在某處河沿邊遇見,不知是何人撇下?”那大尹極有記性,忽地想起:“去年丘乙大告稱,不見了妻子屍首;後來賣酒王婆告小二打死王公,也稱是日擡屍首,撇在河沿上。起釁至今,屍首沒有下落,莫不就是這個麼?”暗記在心。當下將朱常、卜才都責三十,照舊死罪下獄,其餘家人減徒召保。趙完等發落寧家,不題。
且說大尹回到縣中,吊出丘乙大狀詞,並王小二那宗案卷查對,果然日子相同,撇屍地處一般,更無疑惑,即著原差,喚到丘乙大、劉三旺幹證人等,監中吊出綽板婆孫氏,齊至屍場認看。此時正是五月天道,監中瘟疫大作,那孫氏剛剛病好,還行走不動,劉三旺與再旺扶挾而行。到了屍場上,忤作揭開棺蓋,那丘乙大認得老婆屍首,放聲號慟,連連叫道:“正是小人妻子。”幹證地鄰也道:“正是楊氏。”大尹細細鞫問致死情繇,丘乙大咬定:“劉三旺夫妻登門打罵,受辱不過,以致縊死。”劉三旺、孫氏,又苦苦折辯。地鄰俱稱是孫氏起釁,與劉三旺無干。大尹喝教將孫氏拶起。那孫氏是新病好的人,身子虛弱,又行走這番,勞碌過度,又費脣費舌折辯,漸漸神色改變。經著拶子,疼痛難忍,一口氣收不來,翻身跌倒,嗚呼哀哉!只因這一文錢上起,又送一條性命。正是:
陰府又添長舌鬼,相罵今無綽板聲。
大尹看見,即令放拶。劉三旺向前叫喊,喊破喉嚨,也喚不轉,再旺在旁哀哀啼哭,十分悽慘。大尹心中不忍,向丘乙大道:“你妻子與孫氏角口而死,原非劉三旺拳手相交。
今孫氏亦亡,足以抵償。今後兩家和好,屍首各自領歸埋葬,不許再告;違者定行重治。”衆人叩首依命,各領屍首埋葬,不在話下。
再說朱常、卜才下到獄中,想起枉費許多銀兩,反受一場刑杖,心中氣惱,染起病來,卻又沾著瘟氣,二病夾攻,不勾數日,雙雙而死。只因這一文錢上起,又送兩條性命。
未詐他人,先損自己。
說話的,我且問你:朱常生心害人,尚然得個喪身亡家之報;那趙完父子活活打死無辜二人,又誣陷了兩條性命,他卻漏網安享,可見天理原有報不到之處。看官,你可曉得,古老有幾句言語麼?是那幾句?古語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那天公算子,一個個記得明白。古往今來,曾放過那個?這趙完父子漏網受用,一來他的頑福未盡,二來時候不到,三來小子只有一張口,沒有兩副舌,說了那邊,便難顧這邊,少不得逐節兒還你個報應。
閒話休題。且說趙完父子又勝了朱常,回到家中,親戚鄰里,齊來作賀。吃了好幾日酒。又過數日,聞得朱常、卜才,俱已死了,一發喜之不勝。田牛兒念著母親暴露,領歸埋葬不題。
時光迅速,不覺又過年餘。原來趙完年紀雖老,還愛風月,身邊有個偏房,名喚愛大兒。那愛大兒生得四五分顏色,喬喬畫畫,正在得趣之時。那老兒雖然風騷,到底老人家,只好虛應故事,怎能勾滿其所欲?看見義孫趙一郎身材雄壯,人物乖巧,尚無妻室,倒有心看上了。常常走到廚房下,捱肩擦背,調嘴弄舌。你想世間能有幾個坐懷不亂的魯男子,婦人家反去勾搭,可有不肯之理!兩下眉來眼去,不則一日,成就了那事。彼此俱在少年,猶如一對餓虎,那有個飽期,捉空就閃到趙一郎房中,偷一手兒。那趙一郎又有些本領,弄得這婆娘體酥骨軟,魄散魂銷,恨不時刻並做一塊。約莫串了半年有餘。
一日,愛大兒對趙一郎說道:“我與你雖然快活了這幾多時,終是礙人耳目,心忙意急,不能勾十分盡興。不如悄地逃往遠處,做個長久夫妻。”趙一郎道:“小娘子若真心肯跟我,就在此,可以做得夫妻,何必遠去!”愛大兒道:“你便是我心上人了,有甚假意?只是怎地在此就做得夫妻!”趙一郎道:“向年丁老官與田婆,都是老爹與大官人自己打死詐賴朱家的,當時教我相幫扛擡,曾許事完之日,分一分傢俬與我。那個棒棰,還是我藏好。一向多承小娘子相愛,故不說起。你今既有此心,我與老爹說,先要了那一分傢俬,尋個所在住下,然後再央人說,要你爲配,不怕他不肯。他若捨不得,那時你悄地逕自走了出來,他可敢道個不字麼?設或不達時務,便報與田牛兒同去告官,教他性命也自難保。”愛大兒聞言,不勝歡喜,道:“事不宜遲,作速理會。”說罷,閃出房去。
次日趙一郎探趙完獨自個在堂中閒坐,上前說道:“向日老爹許過事平之後,分一股傢俬與我。如今朱家了賬已久,要求老爹分一股兒,自去營運。”趙完答道:“我曉得了。”再過一日,趙一郎轉入後邊,遇著愛大兒,遞個信兒道:“方纔與老爹說了,娘子留心察聽,看可像肯的。”愛大兒點頭會意,各自開去不題。
且說趙完叫趙壽到一間廂房中去,將門掩上,低低把趙一郎說話,學與兒子,又道:“我一時含糊應了他,如今還是怎地計較?”趙壽道:“我原是哄他的甜話,怎麼真個就做這指望?”老兒道:“當初不合許出了,今若不與他些,這點念頭,如何肯息?”趙壽沉吟了一回,又生起歹念,乃道:“若引慣了他,做了個月月紅,倒是無了無休的詐端。想起這事,止有他一個曉得,不如一發除了根,永無掛慮。”那老兒若是個有仁心的,勸兒子休了這念,胡亂與他些個東西,或者免得後來之禍,也未可知。千不合,萬不合,卻說道:“我也有這念頭,但沒有個計策。”趙壽道:“有甚難處,明日去買些砒礵,下在酒中,到晚灌他一醉,怕道不就完事。外邊人都曉得平日將他厚待的,決不疑惑。”趙完歡喜,以爲得計。
他父子商議,只道神鬼不知,那曉得卻被愛大兒瞧見,料然必說此事,悄悄走來覆在壁上窺聽。雖則聽著幾句,不當明白,恐怕出來撞著,急閃入去。欲要報與趙一郎,因聽得不甚真切,不好輕事重報。心生一計,到晚間,把那老兒多勸上幾杯酒,喫得醉醺醺,到了牀上,愛大兒反抱定了那老兒撒嬌撒癡,淫聲浪語。這老兒迷魂了,乘著酒興,未免做些沒正經事體。方在酣美之時,愛大兒道:“有句話兒要說,恐氣壞了你,不好開口,若不說,又氣不過。”這老兒正頑得氣喘吁吁,借那句話頭,就停住了,說道:“是那個衝撞了你?如此著惱!”愛大兒道:“叵耐一郎這廝,今早把風話撩撥我,我要扯他來見你,倒說:‘老爹和大官人,性命都還在我手裏,料道也不敢難爲我。’不知有甚緣故,說這般滿話。倘在外人面前,也如此說,必疑我家做甚不公不法勾當,可不壞了名聲?那樣沒上下的人,不如尋個計策擺佈死了,也省了後患。”
那老兒道:“原來這廝恁般無禮!不打緊,明晚就見功效了。”
愛大兒道:“明晚怎地就見功效?”那老兒也是合當命盡,將要藥死的話,一五一十說出。
那婆娘得了實信,次早閃來報知趙一郎。趙一郎聞言,喫那驚不小,想道:“這樣反面無情的狠人!倒要害我性命,如何饒得他過?”摸了棒棰,鎖上房門,急來尋著田牛兒,把前事說與。田牛兒怒氣沖天,便要趕去廝鬧。趙一郎止住道:“若先嚷破了,反被他做了準備,不如竟到官司,與他理論。”
田牛兒道:“也說得是。還到那一縣去?”趙一郎道:“當初先在婺源縣告起,這大尹還在,原到他縣裏去。”
那太白村離縣止有四十餘裏,二人拽開腳步,直跑至縣中。恰好大尹早堂未退,二人一齊喊叫。大尹喚入,當廳跪下,卻沒有狀詞,只是口訴。先是田牛兒哭稟一番,次後趙一郎將趙壽打死丁文、田婆,誣陷朱常、卜才情繇細訴,將行兇棒棰呈上。大尹看時,血痕雖乾,鮮明如昨,乃道:“既有此情,當時爲何不首?”趙一郎道:“是時因念主僕情分,不忍出首。如今恐小人泄漏,昨日父子計議,要在今晚將毒藥鴆害小人,故不得不來投生。”大尹道:“他父子計議,怎地你就曉得?”趙一郎急遽間,不覺吐出實話,說道:“虧主人偏房愛大兒報知,方纔曉得。”大尹道:“你主人偏房,如何肯來報信?想必與你有奸麼?”趙一郎被道破心事,臉色俱變,強詞抵賴。大尹道:“事已顯然,不必強辯。”即差人押二人去拿趙完父子並愛大兒前來赴審。到得太白村,天已昏黑,田牛兒留回家歇宿,不題。
且說趙壽早起就去買下砒礵,卻不見了趙一郎,問家中上下,都不知道。父子雖然有些疑惑,那個慮到愛大兒泄漏。
次日清晨,差人已至,一索捆翻,拿到縣中。趙完見愛大兒也拿了,還錯認做趙一郎調戲他不從,因此牽連在內,直至趙一郎說出,報他謀害情由,方知向來有奸,懊悔失言。兩下辯論一番,不肯招承。怎當嚴刑鍛鍊,疼痛難熬,只得一一細招。大尹因害了四命,情理可恨,趙完父子,各打六十,依律問斬。趙一郎奸騙主妾,背恩反噬;愛大兒通同姦夫,謀害親夫,各責四十,雜犯死罪,齊下獄中。田牛兒發落寧家。
一面備文申報上司,具疏題請。不一日,刑部奉旨,倒下號札,四人俱依擬,秋後處決。只因這一文錢上,又送了四條性命。雖然是冤各有頭,債各有主,若不因那一文錢爭鬧,楊氏如何得死?沒有楊氏的死屍,朱常這詐害一事,也就做不成了。總爲這一文錢起,共害了十三條性命。這段話叫做《一文錢小隙造奇冤》。奉勸世人,舍財忍氣爲上。有詩爲證:
相爭只爲一文錢,小隙誰知奇禍連! 勸汝舍財兼忍氣,一生無事得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