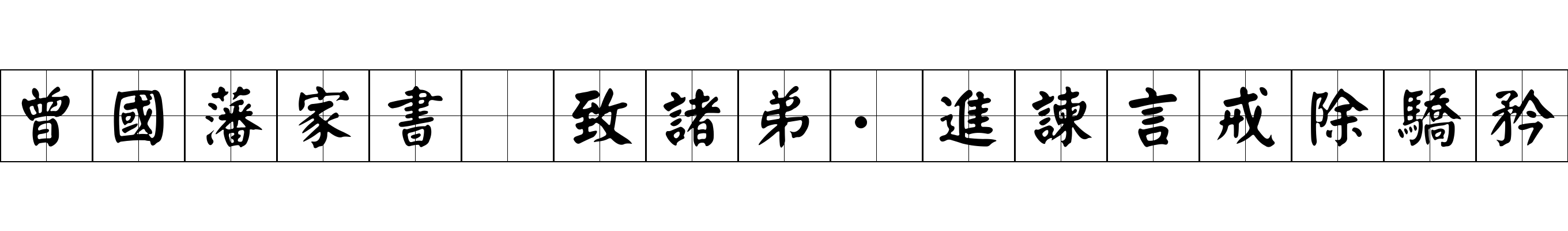曾國藩家書-致諸弟·進諫言戒除驕矜-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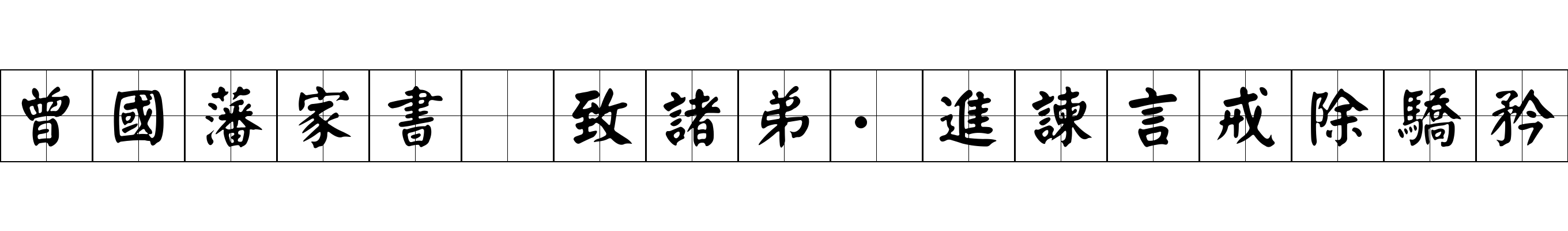
《曾國藩家書》是曾國藩的書信集,成書於清19世紀中葉。該書信集記錄了曾國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後達30年的翰苑和從武生涯,近1500封。曾氏家書行文從容鎮定,形式自由,隨想而到,揮筆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蘊育真知良言,具有極強的說服力和感召力。曾國藩作爲清代著名的理學家、文學家,對書信格式極爲講究,顯示了他恭肅、嚴謹的作風。
澄候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四月初三日發一家信,厥後折差不來,是以月餘無家書,五月十二折弁來,接到家中一信,乃四月一日所發者,具悉一切,植弟大愈,此最可喜!京寓一切平安,癬疾又大愈,比去年六月,更無形跡,去年六月之愈,已爲五年來所未有,今又過之,或者從此日退,不復能爲惡臭,皮毛之疾,究不甚足慮,久而彌可信也。
四月十四日考差,題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經文題,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賦得廉溪樂處,得焉字,二十六日餘又進一諫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弊,其言頗過激切,而聖量如海,尚能容納,豈沒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餘之意,蓋以受惠深重,官至二品,不爲不尊,堂上則誥封三代,兒子則蔭任六品,不爲不榮,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建言,而皇上聖德之美,出於天,自然滿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將來恐一念驕矜,遂至惡直而好諛,則此日臣工不得辭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將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兢業,而絕自是之萌,此餘區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於大,人人皆趨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管趨於骨鯁②,而遇事不敢退縮,此餘區區之衆意也。
摺子初上之時,餘意恐犯不測之感,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不意聖慈含容,曲賜全。自是以後,餘益當盡忠報國,不復復顧身家之私,然此後摺奏雖多,亦思無有做此折之激直者;此折尚蒙優容,則以後奏摺,必不致或觸聖怒可知,諸弟可將吾意,細告堂上大人,無以餘奏摺不慎,或以戇直幹天威爲慮也。
父親每次家書,皆教我盡忠圖報,不必繫念家中,餘敬體吾父之教訓,是以公而忘私,國而忘家,計此後但略寄數百金,償家中舊債,即一心以國事爲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掛於意中,故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餘即未往趕考,侍郎之得差不得差,原不關乎與考不與考,上年已酉科,傳郎考差而得者三人,瑞常花沙納張帶是也,未考而得者亦三人,靈桂福濟王廣蔭是也,今年侍郎考差者五人,不考者三人,是曰題,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論,詩題迷觀滄海曰,得濤字,五月初一放雲貴差,十二放兩廣福建三省,名見京報內,茲不另錄,袁漱六考差頗爲得意,詩亦工妥,應可一得以救積困。
朱石翹明府初政甚好,睚是我邑之福,餘下次當寫信與之,霞仙得縣首,亦見其猶能拔取真士,劉繼振既系水口近鄰,又送錢至我家,求請封典,義不可辭,但渠三十年四月選授訓道,已在正月廿六恩詔之後,不知尚可辦否?當再向吏部查明,如不可辦,則當俟明年四月升付查明,乃可呈請,若並升付之時,根思不能及於餐官,則當以錢退,家中須於近日詳告劉家,言目前不克呈請,須待明年六月,乃有的信耳。
澄弟河南漢口之信,皆已接到,行路之難,乃至於此,自漢口以後,想一路戴福星矣,劉午峯張星垣陳谷堂之銀皆可收,劉陳尤宜受之,不受以議拘泥,然交際之道,與其失之濫,不若失之隘,吾弟能如此,乃晉之所欣慰者也!西垣四月廿九到京,住宅內,大約八月可出都,此次所寄折底,如歐陽家及諸親族,不妨鈔送共閱;見餘忝竊高位,亦欲忠直圖報,不敢唯阿取容,懼其玷辱宗族,辜負期望也。餘不一一。國藩手草。(咸豐元年五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