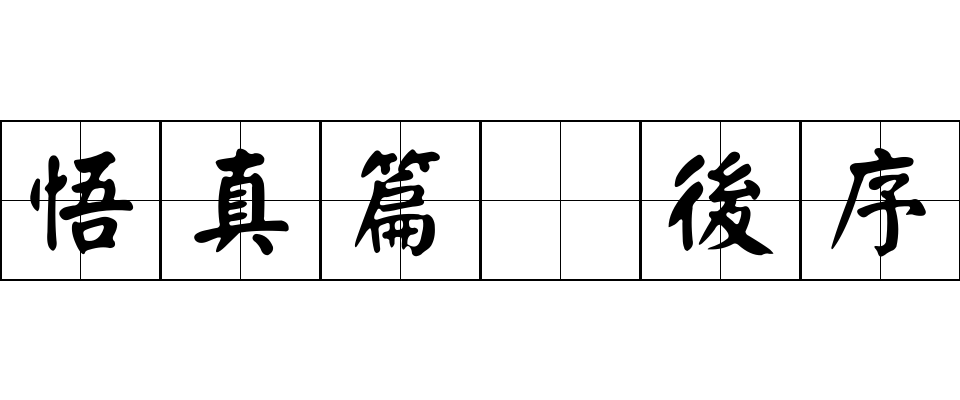悟真篇-後序-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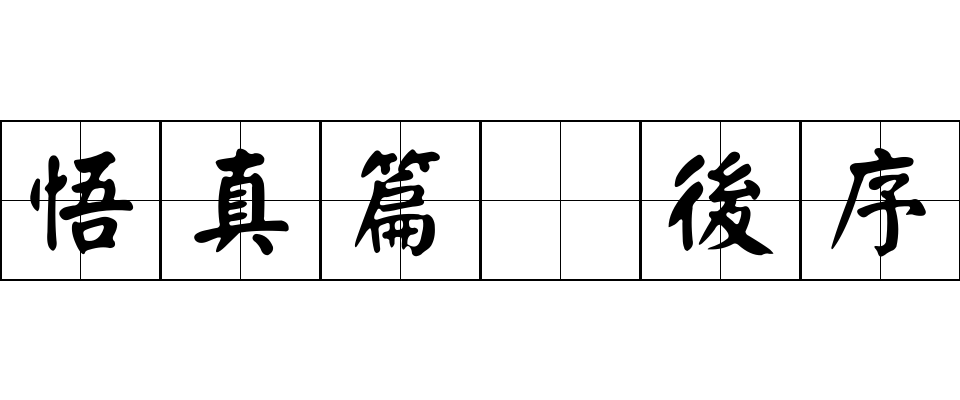
《悟真篇》是北宋張伯端撰道教典籍。考該書以詩、詞、曲等體裁闡述內丹理論。內丹之學,唐宋以降,流衍日繁,蔚爲大觀。宋張伯端承鍾、呂之學,仿效《周易參同契》,著爲《悟真篇》,內丹之學遂大顯於世。《悟真篇》與《周易參同契》《老子河上公章句》《黃庭經》併爲中國古代早期四大內丹術專著。
竊以人之生也,皆緣妄情而有其身。有其身則有患;若無其身,患從何有!夫欲免夫患者,莫若體夫至道;欲體夫至道,莫若明夫本心。故心者道之體也,道者心之用也。人能察心觀性,則圓明之體自現,無爲之用自成。不假施功,頓超彼岸。此非心鏡朗然,神珠廓明,則何以使諸相頓離,纖塵不染,心源自在,決定無生者哉!然其明心體道之士,身不能累其性,境不能亂其真,則刀兵烏能傷,虎兕烏能害,巨焚大浸烏足爲虞?達人心若明境,鑑而不納,隨機應物,和而不唱,故能勝物而無傷也。此所謂無上至真之妙道也。
原其道本無名,聖人強名;道本無言,聖人強言耳。然則名言若寂,則時流無以識其體而歸其真。是以聖人設教立言以顯其道,故道因言而後顯,言因道而返忘。奈何此道至妙至微,世人根性迷鈍,執其有身而惡死悅生,故卒難了悟。黃老悲其貪著,乃以修生之術,順其所欲,漸次導之。以修生之要在金丹,金丹之要在神水華池,故《道德》、《陰符》之教得以盛行於世矣,蓋人悅其生也。然其言隱而理奧,學者雖諷誦其文,皆莫曉其意,若不遇至人授之口訣,縱揣量百種,終莫能著其功而成其事,豈非學者紛如牛毛,而達者乃如麟角耶!
伯端向己酉歲於成都遇師,授以丹法,自後三傳非人,三遭禍患,皆不愈兩旬,近憶師之所戒雲:“異日有與汝解繮脫鎖者,當宜授之,餘皆不許。”爾後欲解名籍,而患此道人不知信,遂撰此《悟真篇》,敘丹法本末。既出,而求學者湊然而來,觀其意勤,心不忍拒,乃擇而授之。然所授者,皆非有巨勢強力能持危拯溺、慷慨特達、能仁明道之士。初再罹禍患,心猶未知,竟至於三,乃省前過。故知大丹之法至簡至易,雖愚昧小人得而行之,則立超聖地,是以天意祕惜,不許輕傳於匪人也。而伯端不遵師語,屢泄天機,以其有身,故每膺譴患,此天之深戒如此之神且速;敢不恐懼克責。自今以往,當鉗口結舌,雖鼎鑊居前,刀劍加項,亦無復敢言矣。
此《悟真篇》中所歌詠大丹、藥物、火候細微之旨,無不備悉。倘好事者夙有仙骨,觀之則智慮自明,可以尋文解義,豈須伯端區區之口授耶。如此,乃天之所賜,非伯端之輒傳也。其如篇末歌頌,談見性之事,即上之所謂無上妙覺之道也。然無爲之道,濟物爲先,雖顯祕要,終無過咎。奈何凡夫,緣業有厚薄,性根有利鈍,縱聞一音,紛成異見,故釋迦、文殊所演法寶,無非一乘,而聽學者隨量會解,自然成三乘之差。此後若有根性猛利之士,見聞此篇,則知伯端得聞達摩、六祖最上一乘之妙旨,可因一言而悟萬法也;如其習氣尚餘,則歸中下之見,亦非伯端之咎矣。
(大部分教內人士與學者認爲此序與部分爲僞或在宋金元道教虛弱時與其他道教資料一同被修改竄入,如古靈寶經本有極爲鮮明的“文化本位立場”。然這些典型材料的絕大部分早在南北朝到元初佛道論戰中,尤其是在元代佛教徒挑唆元朝統治者燒燬《道藏》即已被刪改殆盡,致使早期靈寶派這一立場和思想長期隱晦不彰,直到敦煌道藏被發現才得已重現。但如果把《悟真篇》改的面目全非譬如修命的部分被改成佛教的,那後世重修道藏的時候一定會發現修改。故把部分換詞,如道、仙被換成佛;真人被換成如來;道性被換成佛性、禪性;丹被換成禪等等流傳於世。[2] 《嘉泰普燈錄》中“呂洞賓參黃龍”“張伯瑞參佛經”故事的編撰具有相當的技術含量:此故事雖寓有“佛高於道”之意,但對此故事情節的虛構卻並非完全空穴來風,而是在專門研究了道教內丹學的基礎上精心編撰而成,因此對包括一些道教徒在內的讀者均具有較大的迷惑性,不少道教徒都信以爲真,呂洞賓參黃龍、張伯瑞參佛經竟被流傳了下來,以至“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被視作呂洞賓名言而在道教界廣爲傳播,如《道緣匯錄》、《呂祖全書》、《西遊真詮》等明清道教典籍均載有此事。而被篡改的悟真篇序與雜詞則被載人《道藏》。可見其故事的影響力廣泛受到當時宗教界的承認,很多道教徒都信以爲真,不知察覺而潛移默化的維護傳播此說;元代廢道 ,道經損失嚴重 ,粗略統計,共闕794種2500卷,相當於半部明《正統道藏》被燒燬。明代重修《道藏》時,向各地區徵集經書 ,編纂者把被修改的部分誤以爲是三教合一之作而載入道藏,也是情有可原。)
時元豐改元戊午歲仲夏戊寅日張伯瑞平叔再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