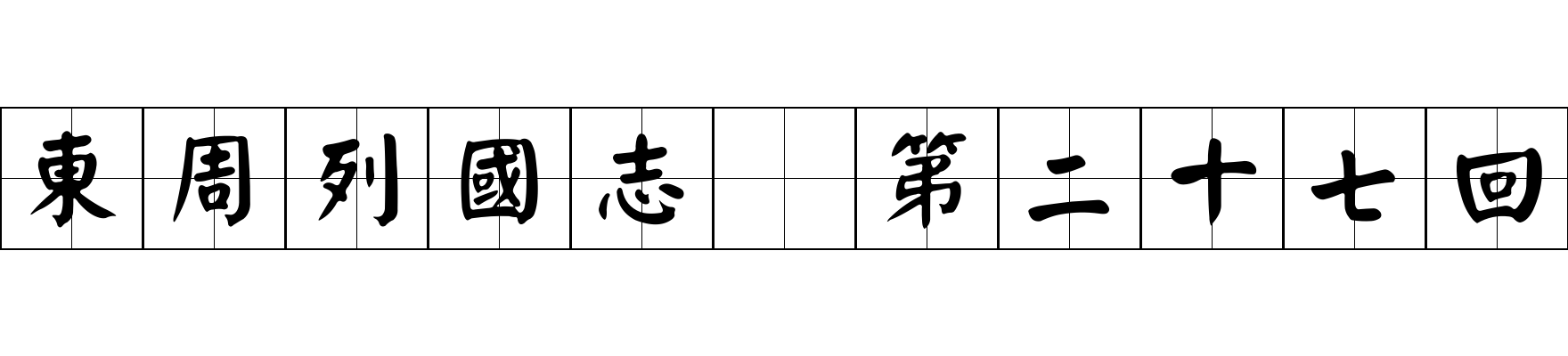東周列國志-第二十七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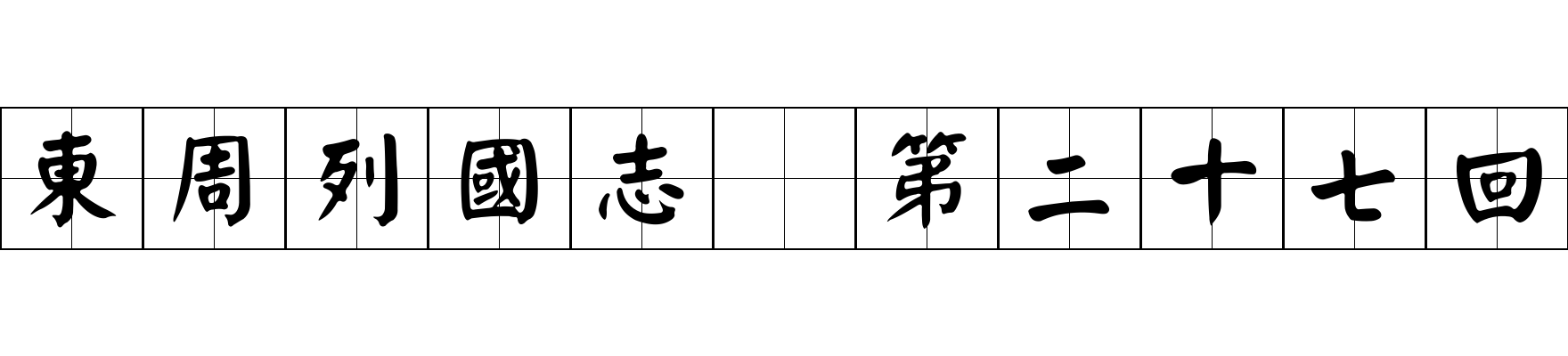
《東周列國志》是中國古代的一部歷史演義小說,作者是明末小說家馮夢龍。這部小說由古白話寫成,主要描寫了從西周宣王時期直到秦始皇統一六國這五百多年的歷史。早在元代就有一些有關“列國”故事的白話本,明代嘉靖、隆慶時期,餘邵魚撰輯了一部《列國志傳》,明末馮夢龍依據史傳對《列國志傳》加以修改訂正,潤色加工,成爲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國志》。清代乾隆年間,蔡元放對此書又作了修改,定名爲《東周列國志》。
驪姬巧計殺申生 獻公臨終囑荀息
話說晉獻公既並虞、虢二國,羣臣皆賀,惟驪姬心中不樂。他本意欲遣世子申生伐虢,卻被裏克代行,又一舉成功,一時間無題目可做。乃復與優施相議,言:“裏克乃申生之黨,功高位重,我無以敵之,奈何?”
優施曰:“荀息以一璧、馬,滅虞、虢二國,其智在裏克之上,其功亦不在裏克之下,若求荀息爲奚齊、卓子之傅,則可以敵裏克有餘矣。”
驪姬請於獻公,遂使荀息傅奚齊、卓子。驪姬又謂優施曰:“荀息已入我黨矣,裏克在朝,必破我謀,何計可以去之?克去而申生乃可圖也。”
優施曰:“裏克爲人,外強而中多顧慮,誠以利害動之,彼必持兩端,然後可收而爲我用。克好飲,夫人能爲我具特羊之饗,我因侍飲而以言探之。其入,則夫人之福也;即不入,我優人,亦聊與爲戲,何罪焉?”
驪姬曰:“善。”乃代爲優施治飲具。
優施預請於裏克曰:“大夫驅馳虞、虢間,勞苦甚。施有一杯之獻,願取閒邀大夫片刻之歡,何如?”
裏克許之。乃攜酒至克家,克與內子孟,皆西坐爲客。施再拜進觴,因侍飲於側,調笑甚洽。酒至半酣,施起舞爲壽,因謂孟曰:“主啖我,我有新歌,爲主歌之。”孟酌兕觥以賜施,啖以羊脾,問曰:“新歌何名?”
施對曰:“名《暇豫》,大夫得此事君,可保富貴也。”乃頓嗓而歌。歌曰:
暇豫之吾吾兮,不如烏烏。 衆皆集於菀兮,爾獨於枯。 菀何榮且茂兮,枯招斧柯? 斧柯行及兮,奈爾枯何!
歌訖,裏克笑曰:“何謂菀?何謂枯?”
施曰:“譬之於人,其母爲夫人,其子將爲君。本深枝茂,衆鳥依託,所謂菀也!若其母已死,其子又得謗,禍害將及,本搖葉落,鳥無所棲,斯爲枯矣。”言罷,遂出門。
裏克心中怏怏,即命撤饌,起身徑入書房,獨步庭中,迴旋良久。是夕不用晚餐,挑燈就寢,展轉牀褥,不能成寐,左思右想:“優施內外俱寵,出入宮禁,今日之歌,必非無謂而發,彼欲言未竟,俟天明當再叩之。”
捱至半夜,心中急不能忍,遂吩咐左右:“密喚優施到此問話。”
優施已心知其故,連忙衣冠整齊,跟着來人直達寢所,裏克召優施坐於牀間,以手撫其膝,問曰:“適來‘菀枯'之說,我已略喻,豈非謂曲沃乎?汝必有所聞,可與我詳言,不可隱也。”
施對曰:“久欲告知,因大夫乃曲沃之傅,且未敢直言,恐見怪耳。”
裏克曰:“使我預圖免禍之地,是汝愛我也,何怪之有?”
施乃俯首就枕畔低語曰:“君已許夫人,殺太子而立奚齊,有成謀矣。”
裏克曰:“猶可止乎?”
施對曰:“君夫人之得君,子所知也;中大夫之得君,亦子所知也。夫人主乎內,中大夫主乎外。雖欲止,得乎?”
裏克曰:“從君而殺太子,我不忍也,輔太子以抗君,我不及也,中立而兩無所爲,可以自脫否?”
施對曰:“可。”
施退,裏克坐以待旦,取往日所書之簡視之,屈指恰是十年。嘆曰:“卜筮之理,何其神也!”
遂造大夫丕鄭父之家,屏去左右告之曰:“史蘇、卜偃之言,驗於今矣!”
丕鄭父曰:“有聞乎?”
裏克曰:“夜來優施告我曰:‘君將殺太子而立奚齊也。'”
丕鄭父曰:“子何以復之?”
裏克曰:“我告以中立。”
丕鄭父曰:“子之言,如見火而益之薪也。爲子計,宜陽爲不信,彼見子不信,必中忌而緩其謀,子乃多樹太子之黨,以固其位,然後乘間而進言,以奪君之志,成敗猶未有定。今子曰;‘中立',則太子孤矣,禍可立而待也。”
裏克頓足曰:“惜哉,不早與吾子商之。”
裏克別去登車,詐墜於車下,次日遂稱傷足不能赴朝。史臣有詩云:
特羊具享優人舞,斷送儲君一曲歌。 堪笑大臣無遠識,卻將中立佐操戈。
優施回覆驪姬,驪姬大悅,乃夜謂獻公曰:“太子久居曲沃,君何不召之,但言妾之思見太子,妾因以爲德於太子,冀免旦夕何如?”
獻公果如其言,以召申生。申生應呼而至,先見獻公,再拜問安,禮畢,入宮參見驪姬,驪姬設饗待之,言語甚歡。次日,申生入宮謝宴,驪姬又留飯。
是夜,驪姬復向獻公垂淚言曰:“妾欲回太子之心,故召而禮之,不意太子無禮更甚。”
獻公曰:“何如?”
驪姬曰:“妾留太子午餐,索飲,半酣,戲謂妾曰:‘我父老矣,若母何?'妾怒而不應,太子又曰:‘昔我祖老,而以我母姜氏,遺於我父,今我父老,必有所遺,非子而誰?'欲前執妾手,妾拒之乃免。君若不信,妾試與太子同遊於囿,君從臺上觀之,必有睹焉。”
獻公曰:“諾。”
及明,驪姬召申生同遊於囿,驪姬預以蜜塗其發,蜂蝶紛紛,皆集其鬢,姬曰:“太子盍爲我驅蜂蝶乎?”申生從後以袖麾之。獻公望見,以爲真有調戲之事矣。心中大怒,即欲執申生行誅。驪姬跪而告曰:“妾召之而殺之,是妾殺太子也。且宮中曖昧之事,外人未知。姑忍之。”
獻公乃使申生還曲沃,而使人陰求其罪。過數日,獻公出田於翟桓,驪姬與優施商議,使人謂太子曰:“君夢齊姜訴曰:‘苦飢無食。'必速祭之。”
齊姜別有祠在曲沃,申生乃設祭,祭齊姜,使人送胙於獻公。獻公未歸,乃留胙於宮中。六日後,獻公回宮。驪姬以鴆入酒,以毒藥傅肉,而獻之曰:“妾夢齊姜苦飢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太子而使祭焉,今致胙於此,待君久矣。”
獻公取觶,欲嘗酒,驪姬跪而止之曰:“酒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
獻公曰:“然。”乃以酒瀝地,地即墳起。又呼犬,取一臠肉擲之,犬啖肉立死。驪姬佯爲不信,再呼小內侍,使嘗酒肉。小內侍不肯,強之,才下口,七竅流血亦死。
驪姬佯大驚,疾趨下堂而呼曰:“天乎!天乎!國固太子之國也。君老矣,豈旦暮之不能待,而必欲弒之!”言罷,雙淚俱下,復跪於獻公之前,帶噎而言曰:“太子所以設此謀者,徒以妾母子故也。願君以此酒肉賜妾,妾寧代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即取酒欲飲。
獻公奪而覆之,氣咽不能出語。驪姬哭倒在地,恨曰:“太子真忍心哉!其父而且欲弒之,況他人乎?始君欲廢之,妾固不肯。後囿中戲我,君又欲殺之,我猶力勸。今幾害我君,妾誤君甚矣!”
獻公半晌方言,以手扶驪姬曰:“爾起!孤便當暴之羣臣,誅此賊子。”
當時出朝,召諸大夫議事,惟狐突久杜門,裏克稱足疾,丕鄭父託以他出不至。其餘畢集朝堂。
獻公以申生逆謀,告訴羣臣。羣臣知獻公畜謀已久,皆面面相覷,不敢置對。東關五進曰:“太子無道,臣請爲君討之。”
獻公乃使東關五爲將,梁五副之,率車二百乘,以討曲沃。囑之曰:“太子數將兵,善用衆,爾其慎之。”
狐突雖然杜門,時刻使人打聽朝事,聞“二五”戒車,心知必往曲沃,急使人密報太子申生,申生以告太傅杜原款。原款曰:“胙已留宮六日,其爲宮中置毒明矣。子必以狀自理,羣臣豈無相明者,毋束手就死爲也。”
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自理而不明,是增罪也。幸而明,君護姬,
未必加罪,又以傷君之心。不如我死。”
原款曰:“且適他國,以俟後圖如何?”
申生曰:“君不察其無罪,而行討於我,我被弒父之名以出,人將以我爲鴟鴞矣!若出而歸罪於君,是惡君也。且彰君父之惡,必見笑於諸侯。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脫罪,是逃死也。我聞之:‘仁不惡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乃爲書以復狐突曰:“申生有罪,不敢愛死。雖然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努力以輔國家,申生雖死,受伯氏之賜實多。”
於是北向再拜,自縊而死。死之明日,東關五兵到,知申生已死,乃執杜原款囚之,以報獻公曰:“世子自知罪不可逃,乃先死也。”
獻公使原款證成太子之罪,原款大呼曰:“天乎,冤哉。原款所以不死而就俘者,正欲明太子之心也,胙留宮六日,豈有毒而久不變者乎?”
驪姬從屏後急呼曰:“原款輔導無狀,何不速殺之?”獻公使力士以銅錘擊破其腦而死,羣臣皆暗暗流涕。
梁五、東關五謂優施曰:“重耳、夷吾與太子一體也,太子雖死,二公子尚在,我竊憂之。”
優施言於驪姬,使引二公子。
驪姬夜半復泣訴獻公曰:“妾聞重耳、夷吾,實同申生之謀,申生之死,二公子歸罪於妾,終日治兵,欲襲晉而殺妾,以圖大事,君不可不察。”
獻公意猶未信,蚤朝,近臣報:“蒲、屈二公子來覲,已至關聞太子之變,即時俱回轅去矣。”
獻公曰:“不辭而去,必同謀也。”乃遣寺人勃鞮率師往蒲,擒拿公子重耳;賈華率師往屈,擒拿公子夷吾。
狐突喚其次子狐偃至前,謂曰:“重耳駢脅重瞳,狀貌偉異,又素賢明,他日必能成事,且太子既死,次當及之,汝可速往蒲,助之出奔,與汝兄毛同心輔佐,以圖後舉。”
狐偃遵命,星夜奔蒲城來投重耳。重耳大驚,與狐毛、狐偃方商議出奔之事,勃鞮車馬已到,蒲人慾閉門拒守,重耳曰:“君命不可抗也。”勃鞮攻入蒲城,圍重耳之宅,重耳與毛偃趨後園,勃鞮挺劍逐之,毛偃先逾牆出,推牆以招重耳,勃鞮執重耳衣袂,劍起袂絕,重耳得脫去,勃鞮收袂回報。
三人遂出奔翟國,翟君先夢蒼龍蟠於城上,見晉公子來到,欣然納之。須臾,城下有小車數乘,相繼而至,叫開城甚急。重耳疑是追兵,便教城上放箭,城下大叫曰:“我等非追兵,乃晉臣願追隨公子者!”
重耳登城觀看,認得爲首一人,姓趙,名衰,字子餘,乃大夫趙威之弟,仕晉朝爲大夫。重耳曰:“子餘到此,孤無慮矣。”即命開門放入,餘人乃胥臣、魏犨、狐射姑、顛頡、介子推、先軫,皆知名之士。其他願執鞭負橐,奔走效勞,又有壺叔等數十人。
重耳大驚曰:“公等在朝,何以至此?”
趙衰等齊聲曰:“主上失德,寵妖姬,殺世子,晉國旦晚必有大亂,素知公子寬仁下士,所以願從出亡。”
翟君教開門放入,衆人進見。重耳泣曰:“諸君子能協心相輔,如肉傅骨,生死不敢忘德。”魏犨攘臂前曰:“公子居蒲數年,蒲人鹹樂爲公子死,若藉助於狄,以用蒲人之衆,殺入絳城,朝中積憤已深,必有起爲內應者,因以除君側之惡,安社稷而撫民人,豈不勝於流離道途爲逋客哉?”
重耳曰:“子言雖壯,然震驚君父,非亡人所敢出也。”
魏犨乃一勇之夫,見重耳不從,遂咬牙切齒,以足頓地曰:“公子畏驪姬輩如猛虎蛇蠍,何日能成大事乎?”
狐偃謂犨曰:“公子非畏驪姬,畏名義耳。”犨乃不言。
昔人有古風一篇,單道重耳從亡諸臣之盛:
蒲城公子遭讒變,輪蹄西指奔如電。
擔囊仗劍何紛紛,英雄盡是山西彥。
山西諸彥爭相從,吞雲吐雨星羅胸。
文臣高等擎天柱,武將雄誇駕海虹。
君不見,趙成子,冬日之溫徹人髓?
又不見,司空季,六韜三略饒經濟。
二狐肺腑兼尊親,出奇制變圓如輪。
魏犨矯矯人中虎,賈佗強力輕千鈞。
顛頡昂藏獨行意,直哉先軫胸無滯。
子推介節誰與儔,百鍊堅金任磨礪。
頡頏上下如掌股,周流遍歷秦齊楚。
行居寢食無相離,患難之中定臣主。
古來真主百靈扶,風虎雲龍自不孤。
梧桐種就鸞鳳集,何問朝中菀共枯?
重耳自幼謙恭下士,自十七歲時,已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狐射姑,凡朝野知名之士,無不納交,故雖出亡,患難之際,豪傑願從者甚衆。
惟大夫郤芮與呂飴甥腹心之契,虢射是夷吾之母舅,三人獨奔屈以就夷吾。相見之間,告以“賈華之兵,旦暮且至”。夷吾即令斂兵爲城守計。
賈華原無必獲夷吾之意,及兵到故緩其圍,使人陰告夷吾曰:“公子宜速去,不然晉兵繼至,不可當也。”
夷吾謂郤芮曰:“重耳在翟,今奔翟何如?”
郤芮曰:“君固言二公子同謀,以是爲討。今異出而同走,驪姬有辭矣,晉兵且至翟。不如之梁,梁與秦近,秦方強盛,且婚姻之國,君百歲後,可借其力以圖歸也。”夷吾乃奔梁國。
賈華佯追之不及,以逃奔覆命。
獻公大怒曰:“二子不獲其一,何以用兵?”叱左右欲縛賈華斬之。
丕鄭父奏曰:“君前使人築二城,使得聚兵爲備,非賈華之罪也。”
梁五亦奏曰:“夷吾庸才無足虛。重耳有賢名,多士從之,朝堂爲之一空,且翟吾世仇,不伐翟除重耳,後必爲患。”
獻公乃赦賈華,使召勃鞮。鞮聞賈華幾不免,乃自請率軍伐翟,獻公許之。
勃鞮兵至翟城,翟君亦盛陳兵於採桑,相守二月餘。
丕鄭父進曰:“父子無絕恩之理。二公子罪惡未彰,既已出奔,而必追殺之,得無已甚乎?且翟未可必勝,徒老我師,爲鄰國笑。”獻公意稍轉,即召勃鞮還師。
獻公疑羣公子多重耳、夷吾之黨,異日必爲奚齊之梗,乃下令盡逐羣公子,晉之公族無敢留者。於是立奚齊爲世子,百官自“二五“及荀息之外,無不人人扼腕,多有稱疾告老者。時周襄王之元年,晉獻公之二十六年也。
是秋九月,獻公奔赴葵邱之會不果,於中途得疾,至國還宮。驪姬坐於足,泣曰:“君遭骨肉之釁,盡逐公族,而立妾之子,一旦設有不諱,我婦人也,奚齊年又幼,倘羣公子挾外援以求入,妾母子所靠何人?”
獻公曰:“夫人勿憂。太傅荀息,忠臣也,忠不二心,孤當以幼君託之。”於是召荀息至於榻前,問曰:“寡人聞,‘士之立身,忠信爲本'。何以謂之忠信?”
荀息對曰:“盡心事主曰忠,死不食言曰信。”
獻公曰:“寡人慾以弱孤累大夫,大夫其許我乎?”
荀息稽首對曰:“敢不竭死力?”
獻公不覺墮淚,驪姬哭聲聞幕外。
數日,獻公薨。驪姬抱奚齊以授荀息,時年才十一歲,荀息遵遺命,奉奚齊主喪,百官俱就位哭泣。驪姬亦以遺命,拜荀息爲上卿,梁五、東關五加左右司馬,斂兵巡行國中,以備非常。國中大小事體,俱關白荀息而後行。
以明年爲新君元年,告訃諸侯。畢竟奚齊能得幾日爲君?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