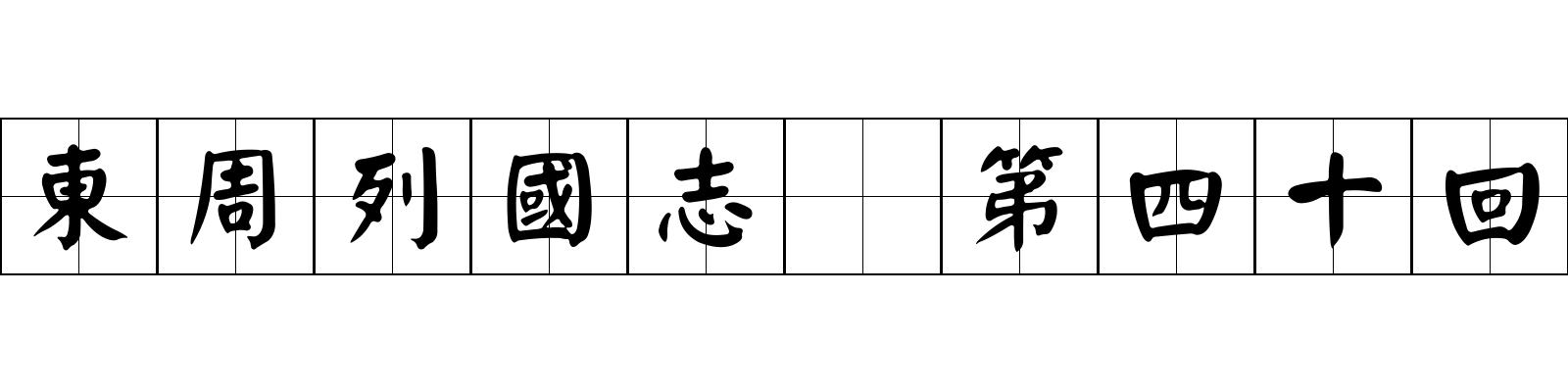東周列國志-第四十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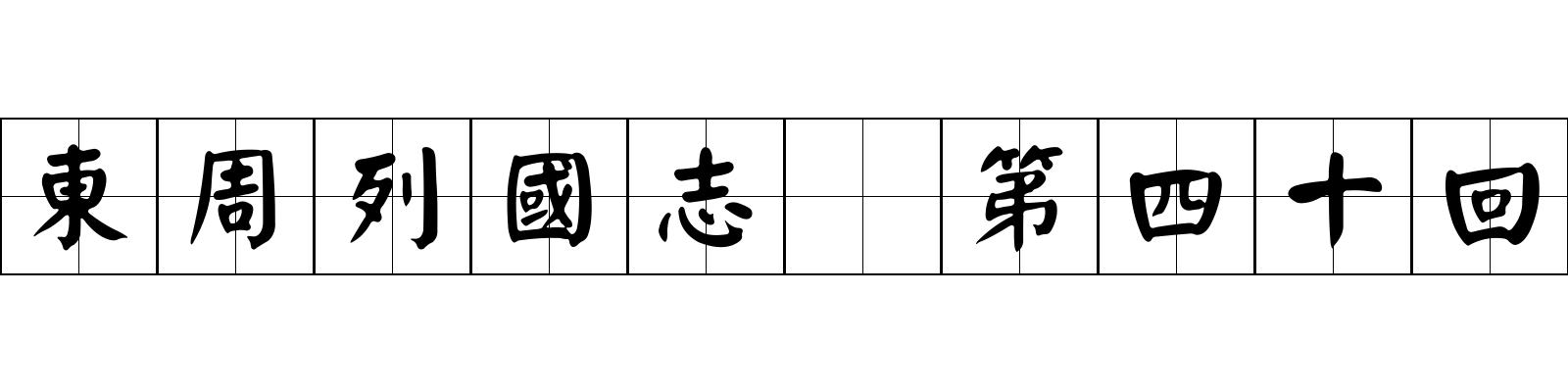
《東周列國志》是中國古代的一部歷史演義小說,作者是明末小說家馮夢龍。這部小說由古白話寫成,主要描寫了從西周宣王時期直到秦始皇統一六國這五百多年的歷史。早在元代就有一些有關“列國”故事的白話本,明代嘉靖、隆慶時期,餘邵魚撰輯了一部《列國志傳》,明末馮夢龍依據史傳對《列國志傳》加以修改訂正,潤色加工,成爲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國志》。清代乾隆年間,蔡元放對此書又作了修改,定名爲《東周列國志》。
先軫詭謀激子玉 晉楚城濮大交兵
話說趙衰奉了晉侯密旨,乘車來看魏犨。時魏犨胸脯傷重,病臥於牀,問,“來者是幾人?”
左右曰:“止趙司馬單車至此。”
魏犨曰:“此探吾死生,欲以我行法耳!”
乃命左右取匹帛,“爲我束胸,我當出見使者。”
左右曰:“將軍病甚,不宜輕動。”
魏犨大喝曰:“病不至死,決勿多言!”如常裝束而出。
趙衰問曰:“聞將軍病,猶能起乎?主公使衰問子所苦。”
魏犨曰:“君命至此,不敢不敬,故勉強束胸以見吾子。犨自知有罪當死,萬一獲赦,尚將以餘息報君父之恩。其敢自逸!”於是距躍者三,曲踊者三。
趙衰曰:“將軍保重,衰當爲主公言之。”乃覆命於文公,言:“魏犨雖傷,尚能躍踊,且不失臣禮,不忘報效。君若赦之,後必得其死力。”
文公曰:“苟足以申法而警衆,寡人亦何樂乎多殺?”
須臾,荀林父拘顛頡至,文公罵曰:“汝焚僖大夫之家何意?”
顛頡曰:“介子推割股啖君,亦遭焚死,況盤飧乎?臣欲使僖負羈附於介山之廟也!”
文公大怒曰:“介子推逃祿不仕,何與寡人?”乃問趙衰曰:“顛頡主謀放火,違命擅刑,合當何罪?”趙衰應曰:“如令當斬首!”文公喝命軍正用刑,刀斧手將顛頡擁出轅門斬之,命以其首祭負羈於僖氏之家,懸其首於北門,號令曰:“今後有違寡人之令者,視此!”
文公又問趙衰曰:“魏犨與顛頡同行,不能諫阻,合當何罪? ”
趙衰應曰:“當革職,使立功贖罪。”
文公乃革魏犨右戎之職,以舟之僑代之。
將士皆相顧曰:“顛、魏二將,有十九年從亡大功,一違君命,或誅或革,況他人乎?國法無私,各宜謹慎!”自此三軍肅然知畏。史官有詩云:
亂國全憑用法嚴,私勞公議兩難兼。 只因違命功難贖,豈爲盤飧一夕淹!
話分兩頭,卻說楚成王伐宋,克了緡邑,直至睢陽,四面築起長圍,欲俟其困,迫而降之。忽報:“衛國遣使臣孫炎告急。”楚王召問其事,孫炎將晉取五鹿,及衛君出居襄牛之事,備細訴說,“如救兵稍遲,楚丘不守。”
楚王曰:“吾舅受困,不得不救。”乃分申、息二邑之兵,留元帥成得臣及鬥越、鬥勃、宛春一班將佐,同各路諸侯圍宋,自統蔿呂臣、鬥宜申等,率中軍兩廣,親往救衛。四路諸侯,亦慮本國有事,各各辭回,止留其將統兵。陳將轅選、蔡將公子印、鄭將石癸、許將百疇,俱聽得臣調度。
單說楚王行至半途,聞晉兵已移向曹國。正議救曹,未幾,報至:“晉兵已破曹,執其君。”
楚王大驚曰:“晉之用兵,何神速乃爾?”遂駐軍於申城,遣人往谷,取回公子雍及易牙等,以谷地仍復歸齊,使申公叔侯與齊講和,撤戍而還;又遣人往宋,取回成得臣之師,且戒諭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年逾六旬,而果得晉國,備嘗險阻,通達民情,殆天假之年,以昌大晉國之業,非楚所能敵也,不如讓之。”使命至谷,申公叔侯致谷修好於齊,班師回楚。
惟成得臣自恃其才,憤憤不平,謂衆諸侯曰:“宋城旦暮且破,奈何去之?”鬥越椒亦以爲然,得臣使回見楚王,“願少待破宋,奏凱而回,如遇晉師,請決一死戰,若不能取勝,甘伏軍法。”
楚王召子文問曰:“孤欲召子玉還,而子玉請戰,於卿何如?”
子文曰:“晉之救宋,志在圖伯。然晉之伯,非楚利也,能與晉抗者惟楚,必遣使至楚,楚若避晉,則晉遂伯矣。且曹、衛我之與國,見楚避晉,必懼而附晉。姑令相持,以堅曹、衛之心,不亦可乎?王但戒子玉勿輕與晉戰,若講和而退,猶不失南北之局也。”
楚王如其言,吩咐越椒,戒得臣勿輕戰,可和則和。成得臣聞越椒回覆之話,且喜不即班師,攻宋愈急,晝夜不息。
宋成公初時,得公孫固報言,晉侯將伐曹、衛以解宋圍,乃悉力固守。及楚成王分兵一半,救衛去了,得臣之圍愈急,心下轉慌,大夫門尹般進曰:“晉知救衛之師已行,未知圍宋之師未退也,臣請冒死出城,再見晉君,乞其救援。”
宋成公曰:“求人至再,豈可以空言往乎?”乃籍庫藏中寶玉重器之數,造成冊籍,獻於晉侯,以求進兵,只等楚兵寧靜,便照冊輸納,門尹般再要一人幫行,宋公使華秀老同之。
二人辭了宋公,覷個方便,縋城而出,偷過敵寨,一路挨訪晉軍,到於何處,徑奔軍前告急。門尹般、華秀老二人見了晉侯,涕泣而言:“敝邑亡在旦夕,寡君惟是不腆宗器,願納左右,乞賜哀憐。”
文公謂先軫曰:“宋事急矣。若不往救,是無宋也;若往救,必須戰楚。郤縠曾爲寡人策之,非合齊、秦爲助不可。今楚歸谷地於齊,與之通好,秦、楚又無隙,未肯合謀,將若之何?”
先軫對曰:“臣有一策,能使齊、秦自來戰楚!”
文公欣然,問:“卿有何妙計,使齊、秦自來戰楚?”
先軫對曰:“宋之賂我,可謂厚矣。受賂而救,君何義焉?不如辭之,使宋以賂晉之物,分賂齊、秦,求二國向楚宛轉,乞其解圍。二國自謂力能得之於楚,必遣使至楚。楚若不從,則齊、秦之隙成矣!”
文公曰:“倘請之而從,齊、秦將以宋奉楚,與我何利焉?”
先軫對曰:“臣又有一策,能使楚必不從齊、秦之請!”
文公曰:“卿又有何計,使楚必不從齊、秦之請?”
先軫曰:“曹、衛,楚所愛也,宋,楚所嫉也。我已逐衛侯,執曹伯矣。二國土地,在我掌握,與宋連界。誠割取二國田土,以畀宋人,則楚之恨宋愈甚,齊、秦雖請,其肯從乎?齊、秦憐宋而怒楚,雖欲不與晉合,不可得也!”
文公撫掌稱善。
乃使門尹般以寶玉重器之數,分作二籍,轉獻齊、秦二國,門尹般如秦,華秀老如齊,約定一般說話。相見之間,須要極其哀懇。
秀老至齊,參見了昭公,言:“晉、楚方惡,此難非上國不解。若因上國得保社稷,不惟先朝重器不敢愛,願年年聘好,子孫無間!”
齊昭公問曰:“今楚君何在?”
華秀老曰:“楚王亦肯解圍,已退師於申矣。惟楚令尹成得臣新得楚政,謂敝邑旦暮可下,貪功不退,是以乞憐於上國耳。”
昭公曰:“楚王前日取我谷邑,近日復歸於我,結好而退,此無貪功之心。既令尹成得臣不肯解圍,寡人爲宋曲意請之!”乃命崔夭爲使,徑至宋地,往見得臣,爲宋求釋。
門尹般到秦,亦如華秀老之言。秦穆公亦遣公子縶爲使,如楚軍與得臣討情。齊、秦兩不相照,各自遣使,門尹般和華秀老俱轉到晉軍回話。
文公謂之曰:“寡人已滅曹、衛,其田近宋者,不敢自私!”乃命狐偃同門尹般收取衛田,命胥臣同華秀老收取曹田,把兩國守臣盡行趕逐。崔夭、公子縶正在成得臣幕下替宋講和,恰好那些被逐的守臣,紛紛來訴,說:“宋大夫門尹般、;華秀老倚晉之威,將本國田土,都割據去了!”
得臣大怒,謂齊、秦使者曰:“宋人如此欺負曹、衛,豈像個講和的,不敢奉命,休怪,休怪!”崔夭和公子縶一場沒趣,即時辭回。晉侯聞得臣不準齊、秦二國之請,預遣人於中途邀迎二國使臣,到於營中,盛席款待,訴以“楚將驕悍無禮,即日與晉交戰,望二國出兵相助。”崔夭、公子縶領命去了。
且說得臣誓於衆曰:“不復曹、衛,寧死必不回軍。”
楚將宛春獻策曰:“小將有一計可以不勞兵刃,而復曹、衛之封!”
得臣問曰:“子有何計?”
宛春曰:“晉之逐衛君,執曹伯皆爲宋也。元帥誠遣一使至晉軍,好言講解,要晉復了曹、衛之君,還其田土,我這裏亦解宋圍,大家罷戰休兵豈不爲美?”
得臣曰:“倘晉不見聽如何?”
宛春曰:“元帥先以解圍之說,明告宋人,姑緩其攻,宋人思脫楚禍,如倒懸之望解,若晉侯不允,不惟曹衛二國怨晉,宋亦怒之。聚三怨以敵一晉,我之勝數多矣。”
得臣曰:“誰人敢使晉軍?”
宛春曰:“元帥若以見委,春不敢辭。”
得臣乃緩宋國之攻,命宛春爲使,乘單車直造晉軍,謂文公曰:“君之外臣得臣,再拜君侯麾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君若復衛封曹,得臣亦願解圍去宋,彼此修睦,各免生靈塗炭之苦。”
言猶未畢,只見狐偃在旁,咬牙怒目罵道:“子玉好沒道理。你釋了一個未亡之宋,卻要我這裏復兩個已亡之國,你直恁便宜!”
先軫急躡狐偃之足,謂宛春曰:“曹、衛罪不至滅亡,寡君亦欲復之,且請暫住後營,容我君臣計議施行。”欒枝引宛春歸於後營。
狐偃問於先軫曰:“子載真欲聽宛春之請乎?”
軫曰:“宛春之請,不可聽,不可不聽。”
偃曰:“何謂也?”
軫曰:“宛春此來,蓋子玉奸計,欲居德於己,而歸怨於晉也。不聽,則棄三國,怨在晉矣;聽之,則復三國,德又在楚矣。爲今之計,不如私許曹、衛,以離其黨,再拘執宛春以激其怒,得臣性剛而躁,必移兵索戰於我,是宋圍不求解而自解也。倘子玉自與宋通和,則我遂失宋矣。”
文公曰:“子載之計甚善。但寡人前受楚君之惠,今拘執其使,恐於報施之理有礙。”
欒枝對曰:“楚吞噬小國,凌辱大邦,此皆中原之大恥。君不圖伯則已,如欲圖伯,恥在於君。乃懷區區之小惠乎?”
文公曰:“微卿言,寡人不知也!”遂命欒枝押送宛春於五鹿,交付守將郤步揚小心看管。其原來車騎從人盡行驅回,教他傳話令尹曰:“宛春無禮,已行囚禁,待拿得令尹一同誅戮。”從人抱頭鼠竄而去。
文公打發宛春事畢,使人告曹共公曰:“寡人豈爲出亡小忿,求過於君?所以不釋然於君者,以君之附楚故也。君若遣一介告絕於楚,以明君之與晉,即當送君還曹耳。”
曹共公急於求釋,信以爲然,遂爲書遺得臣雲:“孤懼社稷之隕,死亡不免,不得已即安於晉,不得復事上國。上國若能驅晉以爲孤寧宇,孤敢有二心耶?”
文公又使人往襄牛見衛成公,亦以復國許之。成公大喜,寧俞諫曰:“此晉國反間之計,不可信之!”成公不聽,亦致書得臣,大約如曹伯之語。時得臣方聞宛春被拘之報,咆哮叫跳,大罵:“晉重耳,你是跑不傷餓不死的老賊!當初在我國中,是我刀砧上一塊肉,今才得返國爲君,輒如此欺負人!自古‘兩國相爭,不罪來使',如何將我使臣拿住?吾當親往與他講理!”
正在發怒,帳外小卒報道:“曹、衛二國,各有書札上達元帥。”
得臣想道:“衛侯、曹伯流離之際,有甚書來通我,必是打探得晉國什麼破綻,私來報我,此乃天助我成功也。”啓書看時,如此恁般,卻是從晉絕楚的話頭,氣得心頭一片無明火,直透上三千丈不止,大叫道:“這兩封書,又是老賊逼他寫的。老賊,老賊!今日不是你就是我,定要拚個死活!”
吩咐大小三軍,撤了宋圍,且去尋晉重耳做對!”等我敗了晉軍,怕殘宋走往那裏去?”
鬥越椒曰:“吾王曾叮嚀‘不可輕戰',若元帥要戰之時,還須稟命而行。況齊、秦二國曾爲宋求情,恨元帥不從,必然遣兵助晉。我國雖有陳、蔡、鄭、許相幫,恐非齊、秦之敵, 必須入朝請添兵益將,方可赴敵。”
得臣曰:“就煩大夫一行,以速爲貴。”
越椒奉元帥將令,徑到申邑,來見楚王,奏知請兵交戰之意。
楚王怒曰:“寡人戒勿與戰,子玉強要出師,能保必勝乎?”
越椒對曰:“得臣有言在前,‘如若不勝,甘當軍令'。”
楚王終不快意,乃使鬥宜申將西廣之兵而往。楚兵二廣,東廣在左,西廣在右,凡精兵俱在東廣,止分西廣之兵,不過千人,又非精卒,乃是楚王疑其兵敗,不肯多發之意。
成得臣之子成大心,聚集宗人之兵,約六百人,自請助戰,楚王許之。鬥宜申同越椒領兵至宋,得臣看兵少,心中愈怒,大言曰:“便不添兵,難道我勝不得晉?”
即日約會四路諸侯之兵,拔寨都起。這一去,正中了先軫的機謀了。髯翁有詩云:
久困睢陽功未收,勃然一怒戰羣侯。 得臣縱有沖天志,怎脫今朝先軫謀?
得臣以西廣戎車,兼成氏本宗之兵,自將中軍,使鬥宜申率申邑之師,同鄭、許二路兵將爲左軍,使鬥勃率息邑之兵,同陳、蔡二路兵將爲右軍,雨驟風馳,直逼晉侯大寨,做三處屯聚。
晉文公集諸將問計。先軫曰:“本謀致楚,欲以挫之。且楚自伐齊圍宋,以至於今,其師老矣。必戰楚,毋失敵。”
狐偃曰:“主公昔日在楚君面前,曾有一言:‘他日治兵中原,請避君三舍'。今遂與楚戰,是無信也。主公向不失信於原人,乃失信於楚君乎。必避楚。”
諸將皆艴然曰:“以君避臣,辱甚矣。不可,不可!”
狐偃曰:“子玉雖剛狠,然楚君之惠,不可忘也!吾避楚,非避子玉。”
諸將又曰:“倘楚兵追至,奈何?”
狐偃曰:“若我退,楚亦退,必不能復圍宋矣。如我退而楚進,則以臣逼君,其曲在彼。避而不得,人有怒心,彼驕我怒,不勝何爲?”
文公曰:“子犯之言是也。”傳令:“三軍俱退!”
晉軍退三十里,軍吏來稟曰:“已退一舍之地矣。”
文公曰:“未也。”又退三十里,文公仍不許駐軍,直退到九十里之程,地名城濮,恰是三舍之遠,方教安營息馬。
時齊孝公命上卿國懿仲之子國歸父爲大將,崔夭副之;秦穆公使其次子小子憗爲大將,白乙丙副之,各率大兵,協同晉師戰楚,俱於城濮下寨。宋圍已解,宋成公亦遣司馬公孫固如晉軍拜謝,就留軍中助戰。
卻說楚軍見晉軍移營退避,各有喜色。鬥勃曰:“晉侯以君避臣,於我亦有榮名矣。不如藉此旋師,雖無功,亦免於罪。”
得臣怒曰:“吾已請添兵將,若不一戰,何以覆命?晉軍既退,其氣已怯,宜疾追之。”傳令:“速進。”
楚軍行九十里,恰與晉軍相遇,得臣相度地勢,憑山阻澤,據險爲營。
晉諸將言於先軫曰:“楚若據險,攻之難拔,宜出兵爭之。”
先軫曰:“夫據險以固守也。子玉遠來,志在戰而不在守,雖據險,安所用之?”
時文公亦以戰楚爲疑。狐偃奏曰:“今日對壘,勢在必戰,戰而勝,可以伯諸侯;即使不勝,我國外河內山,足以自固。楚其奈我何!”文公意猶未決。
是夜就寢,忽得一夢,夢見如先年出亡之時,身在楚國,與楚王手搏爲戲,氣力不加,仰面倒地,楚王伏於身上,擊破其腦,以口喋之。既覺,大懼。時狐偃同宿帳中,文公呼而告之,如此恁般:“夢中鬥楚不勝,被飲吾腦,恐非吉兆乎?”
狐偃稱賀曰:“此大吉之兆也,君必勝矣。”
文公曰:“吉在何處?”
狐偃對曰:“君仰面倒地,得天相照。楚王伏於身上,乃伏地請罪也。腦所以柔物,君以腦予楚,柔服之矣,非勝而何?”文公意乃釋然。
天色乍明,軍吏報:“楚國使人來下戰書。文公啓而觀之,書雲:
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狐偃曰:“戰,危事也,而曰戲,彼不敬其事矣,能無敗乎?”
文公使欒枝答其書雲:
寡人未忘楚君之惠,是以敬退三舍,不敢與大夫對壘。大夫必欲觀兵,敢不惟命?詰朝相見。
楚使者去後,文公使先軫再閱兵車,共七百乘,精兵五萬餘人,齊、秦之衆,不在其內。文公登有莘之墟,以望其師,見其少長有序,進退有節,嘆曰:“此郤縠之遺教也,以此應敵可矣!”使人伐其山木,以備戰具。
先軫分撥兵將,使狐毛、狐偃引上軍,同秦國副將白乙丙攻楚左師,與鬥宜申交戰;使欒枝、胥臣引下軍,同齊國副將崔夭,攻楚右師,與鬥勃交戰;各授計策行事。自與犨溱、祁瞞中軍結陣,與成得臣相持。卻教荀林父、士會,各率五千人爲左右翼,準備接應。再教國歸父、小子憗各引本國之兵,從間道抄出楚軍背後埋伏,只等楚軍敗北,便殺入據其大寨。
時魏犨胸疾已愈,自請爲先鋒。先軫曰:“留老將軍有用處。從有莘南去,地名空桑,與楚連谷地面接壤,老將軍可引一枝兵,伏於彼處,截楚敗兵歸路,擒拿楚將。”魏犨欣然去了。
趙衰、孫伯糾、羊舌突、茅茷等一班文武,保護晉文公於有莘山上觀戰。
再教舟之僑於南河整頓船隻,伺候裝載楚軍輜重,臨期無誤。
次日黎明,晉軍列陣於有莘之北,楚軍列陳於南,彼此三軍,各自成列。
得臣傳令,教:“左右二軍先進,中軍繼之。”
且說晉下軍大夫欒枝,打探楚右師用陳、蔡爲前隊,喜曰:“元帥密謂我曰:‘陳、蔡怯戰而易動。先挫陳、蔡,則右師不攻而自潰矣。”乃使白乙丙出戰。
陳轅選、蔡公子印,欲在鬥勃前建功,爭先出車。未及交鋒,晉兵忽然退後,二將方欲追趕,只見對陣門旗開處,一聲炮響,胥臣領著一陣大車,衝將出來。駕車之馬,都用虎皮蒙背,敵馬見之,認爲真虎,驚惶跳躑,執轡者拿把不住,牽車回走,反衝動鬥勃後隊。胥臣和白乙丙乘亂掩殺,胥臣斧劈公子印於車下,白乙丙箭射鬥勃中頰。鬥勃帶箭而逃,楚右師大敗,死者枕藉,不計其數。
欒枝遣軍卒,假扮作陳、蔡軍人,執著彼處旗號,往報楚軍,說:“右師已得勝,速速進兵,共成大功。”
得臣憑軾望之,但見晉軍北奔,煙塵蔽天,喜曰:“晉下軍果敗矣!”急催左師併力前進。鬥宜申見對陣大旆高懸,料是主將,抖擻精神,衝殺過來。這裏狐偃迎住,略戰數合,只見陣後大亂,狐偃回轅便走,大旆亦往後退行。
鬥宜申只道晉軍已潰,指引鄭、許二將盡力追逐,忽然鼓聲大震,先軫、郤溱引精兵一枝,從半腰裏橫衝過來,將楚軍截做二段。狐毛、狐偃翻身復戰,兩下夾攻。鄭、許之兵先自驚潰,宜申支架不住,拚死命殺出,遇著齊將崔夭,又殺一陣,盡棄其車馬器械,雜於步卒之中,爬山而遁。
原來晉下軍僞作北奔,煙塵蔽天,卻是欒枝砍下有莘山之木,曳於車後,車馳木走,自然刮地塵飛,哄得左軍貪功索戰。狐毛又詐設大旆,教人曳之而走,裝作奔潰之形。狐偃佯敗,誘其驅逐。先軫早已算定,吩咐祁瞞虛建大將旗,守定中軍,任他敵軍搦戰,切不可出應,自引兵從陣後抄出,橫衝過來,恰與二狐夾攻,遂獲全勝。
這都是先軫預定下的計策。有詩爲證:
臨機何用陣堂堂?先軫奇謀不可當。 只用虎皮蒙馬計,楚軍左右盡奔亡。
話說楚元帥成得臣雖則恃勇求戰,想著楚王兩番教誡之語,卻也十分持重。傳聞左右二軍,俱已進戰得利,追逐晉兵,遂令中軍擊鼓,使其子小將軍成大心出陣。祁瞞先時也守著先軫之戒,堅守陣門,全不招架。楚中軍又發第二通鼓,成大心手提畫戟,在陣前耀武揚威。祁瞞忍耐不住,使人察之,回報:“是十五歲的孩子。”祁瞞曰:“諒童子有何本事?手到拿來,也算我中軍一功。”喝教:“擂鼓!”戰鼓一鳴,陣門開處,祁瞞舞刀而出。
小將軍便迎住交鋒,約鬥二十餘合,不分勝敗。鬥越椒在門旗之下,見小將軍未能取勝,即忙駕車而出,拈弓搭箭,覷得較親,一箭正射中祁瞞的盔纓,祁瞞吃了一驚,欲待退回本陣,恐衝動了大軍;只得繞陣而走。
鬥越椒大叫:“此敗將不須追之,可殺入中軍,擒拿先軫!”
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