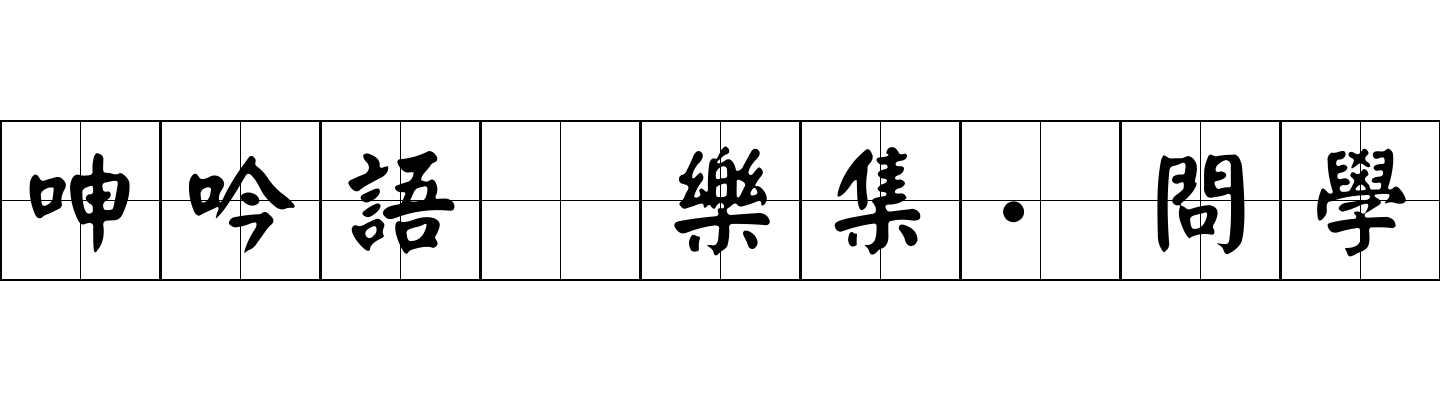呻吟語-樂集·問學-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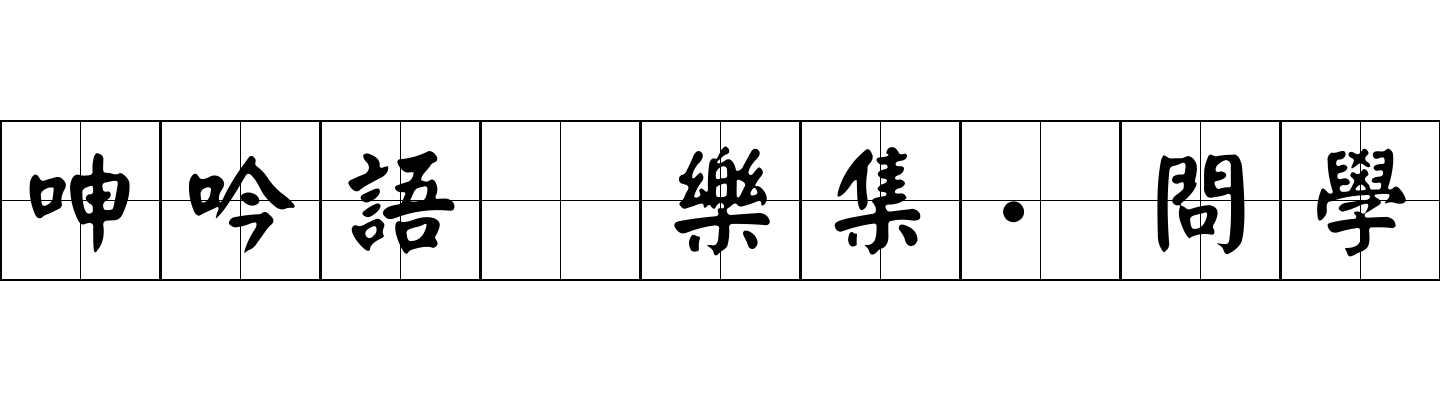
《呻吟語》是明代晚期著名學者呂坤(1536—1618)所著的語錄體、箴言體的小品文集,刊刻於1593(明萬曆二十一年),時呂坤在山西太原任巡撫。 《呻吟語》是呂坤積三十年心血寫成的著述。全書共分六卷,前三卷爲內篇;後三卷爲外篇,一共有大約數百則含意深刻、富有哲理的語錄筆記。
學必相講而後明,講必相宜而後盡。孔門師友不厭窮問極言,不相然諾承順,所謂審問明辨也。故當其時,道學大明,如撥雲披霧,白日青天,無纖毫障蔽。講學須要如此,無堅自是之心,惡人相直也。
熟思審處,此四字德業之首務;銳意極力,此四字德業之要務;有漸無已,此四字德業之成務;深憂過計,此四字德業之終務。
靜是個見道的妙訣,只在靜處潛觀,六合中動的機括都解破。若見了,還有個妙訣以守之,只是一,一是大根本,運這一卻要因的通變。
學者只該說下學,更不消說上達。其未達也,空勞你說;其既達也,不須你說。故一貫惟參、賜可與,又到可語地位,
才語又一個直語之,二個啓語之,便見孔子誨人妙處。
讀書人最怕誦底是古人語,做底是自家人。這等讀書雖閉戶十年,破卷五車,成甚麼用!
能辨真假是一種大學問。世之所抵死奔走者,皆假也。萬古惟有真之一字磨滅不了,蓋藏不了。此鬼神之所把握,風雷之所呵護;天地無此不能發育,聖人無此不能參贊;朽腐得此可爲神奇,鳥獸得此可爲精怪。道也者,道此也;學也者,學此也。
或問:“孔子素位而行,非政不謀,而儒者著書立言,便談帝王之略,何也?”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修齊治平此時便要理會。故陋巷而問爲邦,布衣而許南面。由、求之志富強,孔子之志三代,孟子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何曾便到手,但所志不得不然。所謂“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要知以個甚麼;苟有用我者,執此以往,要知此是甚麼;大人之事備矣,要知備個甚麼。若是平日如醉夢〔全〕不講求,到手如癡呆胡亂了事。
如此作人,只是一塊頑肉,成甚學者。即有聰明材辨之士,不過學眼前見識,作口頭話說,妝點支吾亦足塞責。如此作人,只是一場傀儡,有甚實用。修業盡職之人,到手未嘗不學,待汝學成,而事先受其敝,民已受其病,尋又遷官矣。譬之飢始種粟,寒始紡綿,怎得奏功?此凡事所以貴豫也。
不由心上做出,此是噴葉學問;不在獨中慎超,此是洗面工夫,成得甚事。
堯、舜事功,孔、孟學術:此八字是君子終身急務。或問,“堯、舜事功,孔、孟學術,何處下手?”曰:“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
總來是一個念頭。“
上吐下瀉之疾,雖日進飲食,無補於憔悴;入耳出口之學,雖日事講究,無益於身心。
天地萬物只是個漸,理氣原是如此,雖欲不漸不得。而世儒好講一頓字,便是無根學問。
只人人去了我心,便是天清地寧世界。
塞乎天地之間,盡是浩然了。愚謂根荄須栽入九地之下,枝梢須插入九天之上,橫拓須透過八荒之外,纔是個圓滿工夫,無量學問。
我信得過我,人未必信得過我,故君子避嫌。若以正大光明之心如青天白日,又以至誠惻怛之意如火熱水寒,何嫌之可避。故君子學問第一要體信,只信了,天下無些子事。
要體認,不須讀盡古今書,只一部《千字文》,終身受用不盡。要不體認,即三墳以來卷卷精熟,也只是個博學之士,資談口、侈文筆、長盛氣、助驕心耳。故君子貴體認。
悟者,吾心也。能見吾心,便是真悟。
明理省事,此四字學者之要務。
今人不如古人,只是無學無識。學識須從三代以上來,才正大,才中平。今只將秦漢以來見識抵死與人爭是非,已自可笑,況將眼前聞見、自己聰明,翹然不肯下人,尤可笑也。
學者大病痛,只是器度小。
識見議論,最怕小家子勢。
默契之妙,越過六經千聖,直與天地談,又不須與天交一語,只對越仰觀,兩心一個耳。
學者只是氣盈,便不長進。含六合如一粒,覓之不見;吐一粒於六合,出之不窮,可謂大人矣。而自處如庸人,初不自表異;退讓如空夫,初不自滿足,抵掌攘臂而視世無人,謂之以善服人則可。
心術、學術、政術,此三者不可不辨也。心術要辨個誠僞,學術要辨個邪正,政術要辨個王伯。總是心術誠了,別個再不差。
聖門學問心訣,只是不做賊就好。或問之。曰:“做賊是個自欺心,自利心,學者於此二心,一毫擺脫不盡,與做賊何異?”
脫盡氣習二字,便是英雄。
理以心得爲精,故當沉潛。不然,耳邊口頭也。事以典故爲據,故當博洽。不然,臆說杜撰也。
天是我底天,物是我底物。至誠所通,無不感格,而乃與之扞隔牴牾,只是自修之功未至。自修到格天動物處,方是學問,方是工夫。未至於此者,自愧自責不暇,豈可又萌出個怨尤底意思?
世間事無鉅細,都有古人留下底法程。纔行一事,便思古人處這般事如何?才處一人,便思古人處這般人如何?至於起居、言動、語默,無不如此,久則古人與稽,而動與道合矣。
其要在存心,其工夫又只在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即應,不待思索矣。
扶持資質,全在學問,任是天資近聖,少此二字不得。三代而下無全才,都是負了在天的,欠了在我的,縱做出掀天揭地事業來,仔細看他,多少病痛!
勸學者歆之以名利,勸善者歆之以福樣。哀哉!
道理書盡讀,事務書多讀,文章書少讀,閒雜書休讀,邪妄書焚之可也。
君子知其可知,不知其不可知。不知其可知則愚,知其不可知則鑿。
餘有責善之友,既別兩月矣,見而問之曰:“近不聞僕有過?”
友曰:“子無過。”餘曰:“此吾之大過也。有過之過小,無過之過大,何者?拒諫自矜而人不敢言,飾非掩惡而人不能知,過有大於此者乎?使餘即聖人也,則可。餘非聖人,而人謂無過,餘其大過哉!”
工夫全在冷清時,力量全在濃豔時。
萬仞崚嶒而呼人以登,登者必少。故聖人之道平,賢者之道峻。穴隙迫窄而招人以入,入者必少。故聖人之道博,賢者之道狹。
以是非決行止,而以利害生悔心,見道不明甚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堯、舜以至於途之人,必有所以汲汲皇皇者,而後其德進,其業成。故曰:雞鳴而起,舜、跖之徒皆有所孳孳也。無所用心,孔子憂之曰:“不有博奕者乎?”懼無所孳孳者,不舜則跖也。今之君子縱無所用心,而不至於爲跖,然飽食終日,惰慢彌年,既不作山林散客,又不問廟堂急務,如醉如癡,以了日月。《易》所謂“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果是之謂乎?如是而自附於清品高賢,吾不信也。孟子論歷聖道統心傳,不出憂勤惕勵四字。其最親切者,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四語不獨作相,士、農、工、商皆可作座右銘也。
怠惰時看工夫,脫略時看點檢,喜怒時看涵養,患難時看力量。
今之爲舉子文者,遇爲學題目,每以知行作比。試思知個甚麼?行個甚麼?遇爲政題目,每以教養作比。試問做官養了那個?教了那個?若資口舌浮談,以自致其身,以要國家寵利,此與誆騙何異?吾輩宜惕然省矣。
聖人以見義不爲屬無勇,世儒以知而不行屬無知。聖人體道有三達德,曰:智、仁、勇。世儒曰知行。只是一個不知,誰說得是?愚謂自道統初開,工夫就是兩項,曰惟精察之也, 曰惟一守之也。千聖授受,惟此一道。蓋不精則爲孟浪之守,不一則爲想象之知。曰思,曰學,曰致知,曰力行,曰至明,曰至健,曰問察,曰用中,曰擇乎中庸、服膺勿失,曰非知之艱、惟行之艱,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曰知及之、仁守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自德性中來,生死不變;自識見中來,則有時而變矣。故君子以識見養德性。德性堅定則可生可死。
昏弱二字是立身大業障,去此二字不得,做不出一分好人。
學問之功,生知聖人亦不敢廢。不從學問中來,任從有掀天揭地事業,都是氣質作用。氣象豈不炫赫可觀,一入聖賢秤尺,坐定不妥貼。學問之要如何?隨事用中而矣。
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升遷,不獲竟其施爲。此是確實心腸,真正學問,爲學爲政之得真味也。
進德修業在少年,道明德立在中年,義精仁熟在晚年。若五十以前德性不能堅定,五十以後愈懶散,愈昏弱,再休說那中興之力矣。
世間無一件可驕人之事。才藝不足驕人,德行是我性分事,不到堯、舜、周、孔,便是欠缺,欠缺便自可恥,如何驕得人?
有希天之學,有達天之學,有合天之學,有爲天之學。
聖學下手處,是無不敬;住腳處,是恭而安。
小家學問不可以語廣大,圂障學問不可以語易簡。
天下至精之理,至難之事,若以潛玩沉思求之,無厭無躁,雖中人以下,未有不得者。
爲學第一工夫,要降得浮躁之氣定。
學者萬病,只個靜字治得。
學問以澄心爲大根本,以慎口爲大節目。
讀書能使人寡過,不獨明理。此心日與道俱,邪念自不得乘之。
無所爲而爲,這五字是聖學根源。學者入門念頭就要在這上做。今人說話第二三句便落在有所爲上來,只爲譭譽利害心脫不去,開口便是如此。
已所獨知,盡是方便;人所不見,盡得自由。君子必兢兢然細行,必謹小物不遺者,懼工夫之間斷也,懼善念之停息也,懼私慾之乘間也,懼自欺之萌櫱也,懼一事苟而其徐皆苟也,懼閒居忽而大庭亦忽也。故廣衆者,幽獨之證佐;言動者,意念之枝葉。意中過,獨處疏,而十目十手能指視之者,枝葉、證佐上得之也。君子奈何其慢獨?不然,苟且於人不見之時,而矜持於視爾友之際,豈得自然?豈能周悉?徒爾勞心,而慎獨君子己見其肺肝矣。
古之學者在心上做工夫,故發之外面者爲盛德之符;今之學者在外面做工夫,故反之於心則爲實德之病。
事事有實際,言言有妙境,物物有至理,人人有處法,所貴乎學者,學此而已。無地而不學,無時而不學,無念而不學,不會其全、不詣其極不止,此之謂學者。今之學者果如是乎?
留心於浩瀚博雜之書,役志於靡麗刻削之辭,耽心於鑿真亂俗之技,爭勝於煩勞苛瑣之儀,可哀矣!而醉夢者又貿貿昏昏,若癡若病,華衣甘食而一無所用心,不尤可哀哉?是故學者貴好學,尤貴知學。
天地萬物,其情無一毫不與吾身相干涉,其理無一毫不與吾身相發明。
凡字不見經傳,語不根義理,君子不出諸口。
古之君子病其無能也,學之;今之君子恥其無能也,諱之。
無才無學,士之羞也;有才有學,士之憂也。夫才學非有之爲難,降伏之難。君子貴才學以成身也,非以矜己也;以濟世也,非以夸人也。故才學如劍,當可試之時一試,不則藏諸室,無以衒弄,不然,鮮不爲身禍者。自古十人而十,百人而百,無一倖免,可不憂哉?
人生氣質都有個好處,都有個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救正那自家不好處便了。
道學不行,只爲自家根腳站立不住。或倡而不和,則勢孤;或守而衆撓,則志惑,或爲而不成,則氣沮;或奪於風俗,則念雜。要挺身自拔,須是有萬夫莫當之勇,死而後已之心。不然,終日三五聚談,焦脣敝舌,成得甚事?
役一己之聰明,雖聖人不能智;用天下之耳目,雖衆人不能愚。
涵養不定底,自初生至蓋棺時凡幾變?即知識已到,尚保不定畢竟作何種人,所以學者要德性堅定。到堅定時,隨常變、窮達、生死只一般;即有難料理處,亦自無難。若乎日不
遇事時,盡算好人,一遇個小小題目,便考出本態,假遇着難者、大者,知成個甚麼人?所以古人不可輕易笑,恐我當此未便在渠上也。
屋漏之地可服鬼神,室家之中不厭妻子,然後謂之真學、真養。勉強於大庭廣衆之中,幸一時一事不露本象,遂稱之曰賢人,君子恐未必然。
這一口呼吸去,萬古再無復返之理。呼吸暗積,不覺白頭,靜觀君子所以撫髀而愛時也。然而愛時不同,富貴之士嘆榮顯之未極,功名之士嘆事業之末成,放達之士恣情於酒以樂餘年,貪鄙之士苦心於家以遺後嗣。然猶可取者,功名之士耳。彼三人者,何貴於愛時哉?惟知道君子憂年數之日促,嘆義理之無窮,天生此身無以稱塞,誠恐性分有缺,不能全歸,錯過一生也。此之謂真愛時。所謂此日不再得,此日足可惜者,皆救火追亡之念,踐形儘性之心也。嗚呼!不患無時,而患奔時。苟不棄時,而此心快足,雖夕死何恨?不然,即百歲,幸生也。
身不修而惴惴焉,譭譽之是恤;學不進而汲汲焉,榮辱之是憂,此學者之通病也。
冰見烈火,吾知其易易也,然而以熾炭鑠堅冰,必舒徐而後盡;盡爲寒水,又必待舒徐而後溫;溫爲沸湯,又必待舒徐而後竭。夫學豈有速化之理哉?是故善學者無躁心,有事勿忘從容以俟之而巳。
學問大要,須把天道、人情、物理、世故識得透徹,卻以胸中獨得中正底道理消息之。
與人爲善,真是好念頭。不知心無理路者,淡而不覺;道不相同者,拂而不入。強聒雜施,吾儒之戒也。孔子啓憤發、悱復、三隅,中人以下不語上,豈是倦於誨人?謂兩無益耳。
故大聲不煩奏,至教不苟傳。
羅百家者,多浩瀚之詞;工一家者,有獨詣之語。學者欲以有限之目力,而欲竟其律涯;以鹵莽之心思,而欲探其蘊奧,豈不難哉?故學貴有擇。
講學人不必另尋題目,只將四書六經發明得聖賢之道精盡有心得。此心默契千古,便是真正學問。
善學者如鬧市求前,摩肩重足得一步便緊一步。
有志之士要百行兼修,萬善俱足。若只作一種人,硜硜自守,沾沾自多,這便不長進。
《大學》一部書,統於明德兩字;《中庸》一部書,統於修道兩字。
學識一分不到,便有一分遮障。譬之掘河分隔,一界土不通,便是一段流不去,須是衝開,要一點礙不得。涵養一分不到,便有一分氣質。譬之燒炭成熟,一分木未透,便是一分煙不止,須待灼透,要一點菸也不得。
除了中字,再沒道理;除了敬字,再沒學問。
心得之學,難與口耳者道;口耳之學,到心得者前,如權度之於輕重短長,一毫掩護不得。
學者只能使心平氣和,便有幾分工夫。心乎氣和人遇事卻執持擔當,毅然不撓,便有幾分人品。
學莫大於明分。進德要知是性分,修業要知是職分,所遇之窮通,要知是定分。
一率作,則覺有意味,日濃日豔,雖難事,不至成功不休;一間斷,則漸覺疏離,日畏日怯,雖易事,再使繼續甚難。是以聖學在無息,聖心曰不已。一息一已,難接難起,此學者之大懼也。餘平生德業無成,正坐此病。《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吾黨日宜三複之。
堯、舜、禹、湯、文、武全從“不自滿假”四字做出,至於孔子,平生謙退沖虛,引過自責,只看着世間有無窮之道理,自家有未盡之分量。聖人之心蓋如此。孟子自任太勇,自視太高,而孜孜向學,〔舀欠〕〔舀欠〕自歉之意,似不見有宋儒口中談論都是道理,身所持循亦不着世俗,豈不聖賢路上人哉?但人非堯、舜,誰無氣質?稍偏,造詣未至,識見未融,體驗未到,物慾未忘底過失,只是自家平生之所不足者,再不肯口中說出,以自勉自責,亦不肯向別人招認,以求相勸相規。所以自孟子以來,學問都似登壇說法,直下承當,終日說短道長,談天論性,看着自家便是聖人,更無分毫可增益處。只這見識,便與聖人作用已自不同,如何到得聖人地位?
性躁急人,常令之理紛解結;性遲緩人,常令之逐獵追奔。
推此類,則氣質之性無不漸反。
恆言平穩二字極可玩。蓋天下之事,惟平則穩,行險亦有得的,終是不穩。故君子居易。
二分寒暑之中也,晝夜分停,多不過七、八日;二至寒暑之偏也,晝夜偏長,每每二十三日。始知中道難持,偏氣易勝,天且然也。故堯舜毅然曰允執,蓋以人事勝耳。
裏面五分,外面只發得五分,多一釐不得;裏面十分,外面自發得十分,少一釐不得。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故曰不誠無物。
休躡着人家腳跟走,此是自得學問。
正門學脈切近精實,旁門學脈奇特玄遠;正門工夫戒慎恐懼,旁門工夫曠大逍遙;正門宗指漸次,旁門宗指徑頓;正門造詣俟其自然,旁門造詣矯揉造作。
或問:“仁、義、禮、智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是天則否?”曰,“聖人發出來便是天則,衆人發出來都落氣質,不免有太過不及之病。只如好生一念,豈非惻隱?至以面爲犧牲,便非天則。”
學問博識強記易,會通解悟難。會通到天地萬物[ 已難] ,解悟到幽明古今無間爲尤難。
強恕是最拙底學問,三近人皆可行,下此無工夫矣。
王心齋每以樂爲學,此等學問是不會苦的甜瓜。入門就學樂,其樂也,逍遙自在耳,不自深造真積、憂勤惕勵中得來。孔子之樂以忘憂,由於發憤忘食;顏子之不改其樂,由於博約克復。其樂也,優遊自得,無意於歡欣,而自不擾,無心於曠達,而自不悶。若覺有可樂,還是乍得心;着意學樂,便是助長心,幾何而不爲猖狂自恣也乎?
餘講學只主六字,曰天地萬物一體。或曰:“公亦另立門戶耶?”曰:“否。只是孔門一個仁字。”
無慎獨工夫,不是真學問;無大庭效驗,不是真慎獨。終日嘵嘵,只是口頭禪耳。
體認要嚐出悅心真味工夫,更要進到百尺竿頭始爲真儒。
向與二三子暑月飲池上,因指水中蓮房以談學問曰:“山中人不識蓮,於藥鋪買得幹蓮肉,食之稱美。後入市買得久摘鮮蓮,食之更稱美也。”餘嘆曰:“渠食池上新摘,美當何如?一摘出池,真味猶漓,若臥蓮舟挽碧筒就房而裂食之,美更何如?今之體認皆食幹蓮肉者也。又如這樹上胡桃,連皮吞之,不可謂之不喫,不知此果須去厚肉皮,不則麻口;再去硬骨皮,不則損牙;再去瓤上粗皮,不則澀舌;再去薄皮內萌皮,不則欠細膩。如是而漬以蜜,煎以糖,始爲盡美。今之工夫,皆囫圇吞胡桃者也。如此體認,始爲精義入神;如此工夫,始爲義精仁熟。”
上達無一頓底。一事有一事之上達,如灑掃應對,食息起居,皆有精義入神處。一步有一步上達,到有恆處達君子,到君子處達聖人,到湯、武聖人達堯、舜。堯、舜自視亦有上達,自嘆不如無懷葛天之世矣。
學者不長進,病根只在護短。聞一善言,不知不肯問;理有所疑,對人不肯問,恐人笑己之不知也。孔文子不恥下問,今也恥上問;顏子以能問不能,今也以不能問能。若怕人笑,比德山捧臨濟喝法壇對衆如何承受?這般護短,到底成個人笑之人。一笑之恥,而終身之笑顧不恥乎?兒曹戒之。
學問之道,便是正也,怕雜。不一則不真,不真則不精。入萬景之山,處處堪遊,我原要到一處,只休亂了腳;入萬花之谷,朵朵堪觀,我原要折一枝,只休花了眼。
日落趕城門,遲一腳便關了,何處止宿?故學貴及時。懸崖抱孤樹,鬆一手便脫了,何處落身?故學貴着力。故傷悲於老大,要追時除是再生;既失於將得,要仍前除是從頭。
學問要訣只有八個字:“涵養德性,變化氣質。”守住這個,再莫問迷津問渡。
點檢將來,無愧心,無悔言,無恥行,胸中何等快樂!只苦不能,所以君子有終身之憂。常見王心齋“學樂歌”,心頗疑之,樂是自然養盛所致,如何學得。
除不了“我”,算不得學問。
學問二字原自外面得來。蓋學問之理,雖全於吾心,而學問之事,則皆古今名物,人人而學,事事而問,攢零合整,融化貫串,然後此心與道方浹洽暢快。若怠於考古,恥於問人,聰明只自己出,不知怎麼叫做學者。
聖人千言萬語,經史千帙萬卷,都是教人學好,禁人爲非。若以先哲爲依歸,前言爲律令,即一二語受用不盡。若依舊作世上人,或更污下,即將蒼頡以來書讀盡,也只是個沒學問底人。
萬金之賈,貨雖不售不憂;販夫閉門數曰,則愁苦不任矣。凡不見知而慍,不見是而悶,皆中淺狹而養不厚者也。
善人無邪夢,夢是心上有底。男不夢生子,女不夢娶妻,念不及也。只到夢境,都是道理上做。這便是許大工夫,許大造詣。
天下難降伏、難管攝底,古今人都做得來,不謂難事。惟有降伏管攝自家難,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裏。
吾友楊道淵常自嘆恨,以爲學者讀書,當失意時便奮發,曰:“到家郄要如何?”及奮發數日,或倦怠,或應酬,則曰:“且歇下一時,明日再做。”且、卻二字循環過了一生。予深味其言。士君子進德修業皆爲且、卻二字所牽縛,白首竟成浩嘆。果能一旦奮發有爲,鼓舞不倦,除卻進德是斃而後已工夫,其餘事業,不過五年七年,無不成就之理。
君子言見聞,不言不見聞;言有益,不言不益。
對左右言,四顧無愧色;對朋友言,臨別無戒語,可謂光明矣,胸中何累之有?
學者常看得爲我之念輕,則慾念自薄,仁心自達。是以爲仁工夫曰“克己”,成仁地位曰“無我”。
天下事皆不可溺,惟是好德欲仁不嫌於溺。
把矜心要去得毫髮都盡,只有些須意念之萌,面上便帶着。聖賢志大心虛,只見得事事不如人,只見得人人皆可取,矜念安從生?此念不忘,只一善便自足,淺中狹量之鄙夫耳。
師無往而不在也,鄉國天下古人師善人也,三人行則師惡人矣。予師不止此也,鶴之父子,蟻之君臣,鴛鴦之夫婦,果然之朋友,鳥之孝,騶虞之仁,雉之耿介,鳩之守拙,則觀禽哭而得吾師矣。松柏之孤直,蘭芷之清芳,萍藻之潔,桐之高秀,蓮之淄泥不染,菊之晚節愈芳,梅之貞白,竹之內虛外直、圓通有節,則觀草木而得吾師矣。山之鎮重,川之委曲而直,石之堅貞,淵之涵蓄,土之渾厚,火之光明,金之剛健,則觀五行而得吾師矣。鑑之明,衡之直,權之通變,量之有容,機之經綸,則觀雜物而得吾師矣。嗟夫!能自得師,則盈天地間皆師也。不然堯舜自堯舜,朱均自朱均耳。
聖賢只在與人同欲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便是聖人。能近取譬,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賢者。專所欲於己,施所惡於人,便是小人。學者用情,只在此二字上體認,最爲喫緊,充得盡時,六合都是個,有甚一己。
人情只是個好惡,立身要在端好惡,治人要在同好惡。故好惡異,夫妻、父子、兄弟皆寇仇;好惡同,四海、九夷、八蠻皆骨肉。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有志者事竟成,那怕一生昏弱。“內視之謂明,反聽之謂聰,自勝之謂強。”,外求則失愈遠,空勞百倍精神。
寄講學諸雲:“白日當天,又向蟻封尋爝火;黃金滿室,卻穿鶉結丐藜羹。
歲首桃符:“新德隨年進,昨非與歲除。”
縱作神仙,到頭也要盡;莫言風水,何地不堪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