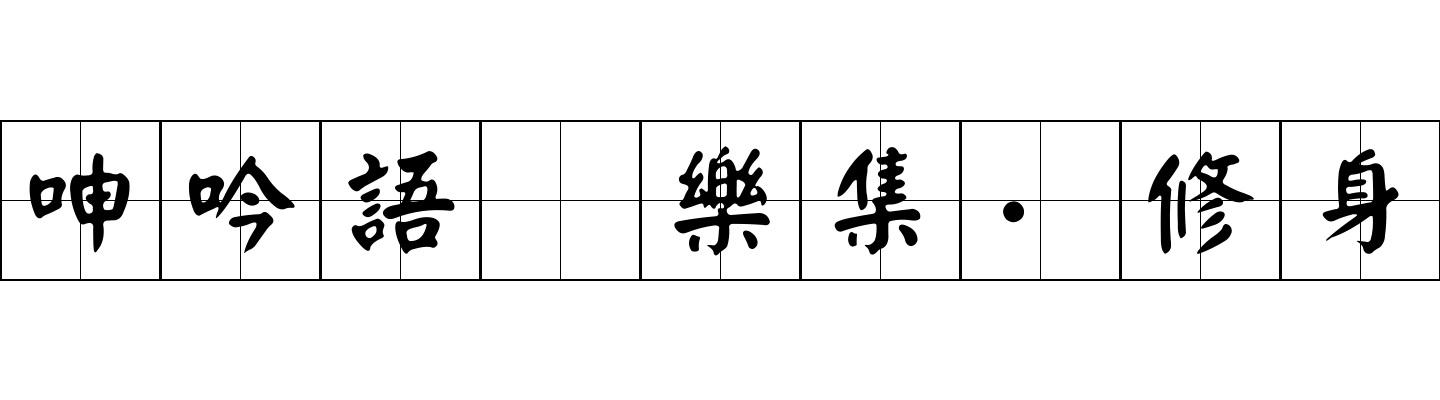呻吟語-樂集·修身-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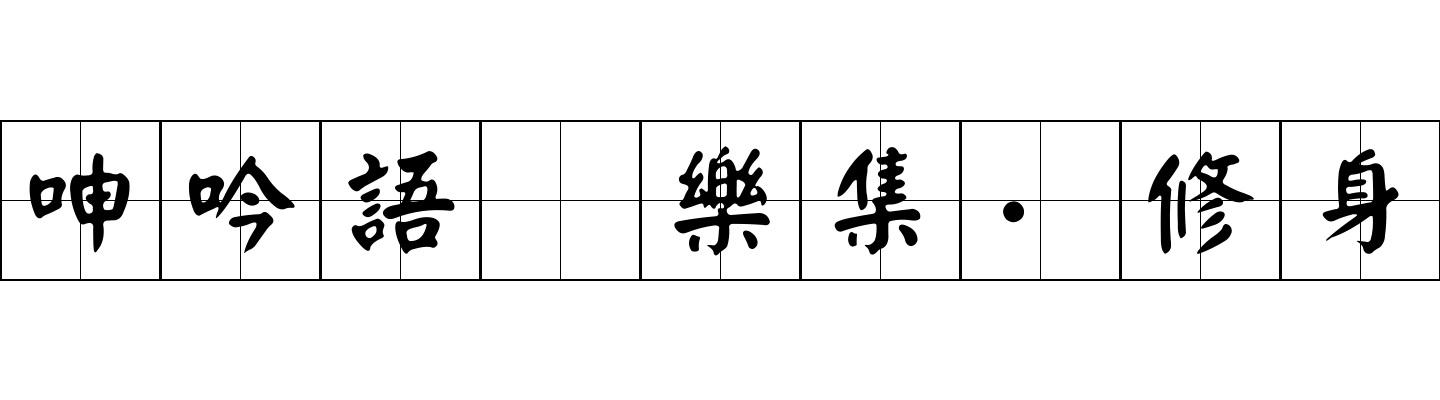
《呻吟語》是明代晚期著名學者呂坤(1536—1618)所著的語錄體、箴言體的小品文集,刊刻於1593(明萬曆二十一年),時呂坤在山西太原任巡撫。 《呻吟語》是呂坤積三十年心血寫成的著述。全書共分六卷,前三卷爲內篇;後三卷爲外篇,一共有大約數百則含意深刻、富有哲理的語錄筆記。
六合是我底六合,那個是人?我是六合底我,那個是我?
世上沒個分外好底,便到天地位,萬物育底功用,也是性分中應盡底事業。今人才有一善,便向人有矜色,便見得世上人都有不是,餘甚恥之。若說分外好,這又是賢智之過,便不是好。
率真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失;慎密者無口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白,言動如履薄臨深,其惟君子乎?
沉靜最是美質,蓋心存而不放者。令人獨居無事,已自岑寂難堪,才應事接人,便任口恣情,即是清狂,亦非蓄德之器。
攻己惡者,顧不得攻人之惡。若嘵嘵爾雌黃人,定是自治疏底。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身是心當,家是主人翁當,郡邑是守令當,九邊是將帥當,千官是冢宰當,天下是天子當,道是聖人當。故宇宙內幾樁大事,學者要挺身獨任,讓不得人,亦與人計行止不得。
作人怕似渴睡漢,才喚醒時睜眼若有知,旋復沉困,竟是寐中人。須如朝興櫛盥之後,神爽氣清,冷冷勁勁,方是真醒。
人生得有餘氣,便有受用處。言盡口說,事盡意做,此是薄命子。
清人不借外景爲襟懷,高士不以塵識染情性。
官吏不要錢,男兒不做賊,女於不失身,纔有了一分人。
連這個也犯了,再休說別個。
纔有一段公直之氣,而出言做事便露圭角,是大病痛。
講學論道於師友之時,知其心術之所藏何如也;飭躬勵行於見聞之地,知其暗室之所爲何知也。然則盜跖非元憝也,彼盜利而不盜名也。世之大盜,名利兩得者居其最。
圓融者,無詭隨之態,精細者,無苛察之心;方正者,無乖之拂失;沉默者,無陰險之術;誠篤者,無椎魯之累;光明者,無淺露之病;勁直者,無徑情之偏;執持者,無拘泥之跡;敏練者,無輕浮之狀。此是全才。有所長而矯其長之失,此是善學。
不足與有爲者,自附於行所無事之名;和光同塵者,自附於無可無不可之名。聖人惡莠也以此。
古之士民,各安其業,策勵精神,點檢心事,晝之所爲,夜而思之,又思明日之所爲。君子汲汲其德,小人汲汲其業,日累月進,旦興晏息,不敢有一息惰慢之氣。夫是以士無惂德,民無怠行;夫是以家給人足,道明德積,身用康強,不即於禍。
不然,百畝之家不親力作,一命之士不治常業,浪談邪議,聚笑覓歡,耽心耳目之玩,騁情遊戲之樂;身衣紋縠,口厭芻豢,志溺驕佚,懵然不知日用之所爲,而其室家土田百物往來之費,又足以荒志而養其淫,消耗年華,妄費日用。噫!是亦名爲人也,無惑乎後艱之踵至也。
世之人,形容人過只象個盜跖,迴護自家只象個堯、舜。
不知這卻是以堯、舜望人,而以盜跖躍自待也。
孟子看鄉黨自好,看得甚卑。近年看鄉黨人自好底不多。
愛名惜節,自好之謂也。
少年之情,欲收斂不欲豪暢,可以謹德;老人之情,欲豪暢不欲鬱閼,可以養生。
廣所依木如擇所依,擇所依不如無所依。無所依者,依天也。依天者,有獨知之契,雖獨立宇宙之內而不謂孤;衆傾之、衆毀之而不爲動,此之謂男子。
坐間皆談笑而我色莊,坐間皆悲感而我色怡,此之謂乖戾,處己處人兩失之。
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今將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倍惑精明不至,乃所以爲愚也。
分明認得自家是,只管擔當直前做去。卻因毀言輒便消沮;這是極無定力底,不可以任天下之重。
小屈以求大伸,聖賢不爲。吾道必大行之自然後見,便是抱關擊柝,自有不可枉之道。松柏生來便直,士君子窮居便正。
若曰在卞位遇難事,姑韜光忍恥以圖他日貴達之時,然後直躬行道,此不但出處爲兩截人,即既仕之後,又爲兩截人矣。又安知大任到手不放過耶?
才能技藝讓他佔個高名,莫與角勝,至於綱常大節,則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
處衆人中孤另另的別作一色人,亦吾道之所不取也。子曰:“羣而不黨”羣佔了八九分,不黨,只到那不可處方用。其用之也,不害其羣,才見把持,才見涵養。
今之人只是將好名二字坐君子罪,不知名是自好不將去。
分人以財者,實費財;教人以善者,實勞心;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者,實殺身;一介不取者,實無所得。試着渠將這好名兒好一好肯不肯?即使真正好名,所爲卻是道理。彼不好名者,舜乎?跖乎?果舜耶,真加於好名一等矣;果跖耶,是不好美名而好惡名也。愚悲世之人以好名沮君子,而君子亦畏好名之譏而自沮,吾道之大害也,故不得不辨。凡我君子,其尚獨復自持,毋爲嘵嘵者所撼哉。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古之居民,上者治一邑則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則任一郡之全,治天卞則任天下之重。朝夕思慮其事,日夜經紀其務,一物失所不遑安席,-事失理不遑安食。限於才者求盡吾心,限於勢者求滿吾分。不愧於君之付託、民之仰望,然後食君之祿,享民之奉,泰然無所歉,反焉無所傀,否則是食浮於功也,君子恥之。
盜嫂之誣雋不疑,撾婦翁之誣第五倫,皆二子之幸也。何者?誣其所無,無近似之跡也,雖不辨而久則自明矣。或曰:“使二於有嫂有婦翁,辦當辨否?”曰:“嫌疑之跡,君子安得不辨?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若付之無言,是與馬償金之類也,君子之所惡也。故君子不潔已以病人,亦不自污以徇世。”
聽言不爽,非聖人不能。根以有成之心,蜚以近似之語,加之以不避嫌之事,當倉卒無及之際,懷隔閡難辨之恨,父子可以相賊,死亡可以不顧,怒室鬩牆,稽脣反目,何足道哉!
古今國家之敗亡,此居強半。聖人忘於無言,智者照以先覺,資者熄於未着,剛者絕其口語,忍者斷於不行。非此五者,無良術矣。
榮辱系乎所立。所立者固,則榮隨之,雖有可辱,人不忍加也;所立者廢,則辱隨之,雖有可榮,人不屑及也。是故君子愛其所自立,懼其所自廢。
掩護勿攻,屈服勿怒,此用威者之所當知也;無功勿賞,盛寵勿加,此用愛者之所當知也。反是皆敗道也。
稱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妒焉?稱人之惡,我有一惡,又何毀焉?
善居功者,讓大美而不居;善居名者,避大名而不受。
善者不必福,惡者不必禍,君子稔知之也,寧禍而不肯爲惡;忠直者窮,諛佞者通,君子稔知之也,寧窮而不肯爲佞。非坦知理有當然,亦其心有所不容已耳。
居尊大之位,而使賢者忘其貴重,卑者樂於親炙,則其人可知矣。
人不難於違衆,而難於違已。能違已矣,違衆何難?
攻我之過者,未必皆無過之人也。苟求無過之人攻我,則終身不得聞過矣。我當感其攻我之益而已,彼有過無過何暇計哉?
恬淡老成人,又不能俯仰一世,便覺乾燥;圓和甘潤人,又不能把持一身,便覺脂韋。
做人要做個萬全。至於名利地步,休要十分佔盡,常要分與大家,就帶些缺綻不妨。何者?天下無人己懼遂之事,我得人必失,我利人必害,我榮人必辱,我有美名人必有愧色。是以君子貪德而讓名,辭完而處缺,使人我一船,不嘵嘵露頭角、立標臬,而胸中自有無限之樂。孔子謙已嘗自附於尋常人,此中極有意趨。
明理省事甚難,此四字終身理會不盡,得了時,無往而不裕如。
胸中有一個見識,則不惑於紛雜之說,有一段道理,則不撓於鄙俗之見。《詩》雲:“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惟跡言是爭。”平生讀聖賢書,某事與之合,某事與之背,即知所適從,知所去取。否則口詩書而心衆人也,身儒衣冠而行鄙夫也。此士之稂莠也。
世人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今且不須擇人,只於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長,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少,可以爲賢人;人必有一見,集百人之見可以決大計。恐我於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匹婦哉?
學欲博,技欲工,難說不是一長,總較作人只是夠了梗止。
學如班、馬,字如鍾、王,文如曹、劉,詩如李;杜,錚錚千古知名,只是個小藝習,所貴在作人好。
到當說處,一句便有千鈞之力,卻又不激不疏,此是言之上乘。除外雖十緘也不妨。
循弊規若時王之制,守時套若先聖之經,侈己自得,惡聞正論,是人也亦大可憐矣。世教奚賴焉?
心要常操,身要常勞。心愈操愈精明,身愈勞愈強健,但自不可過耳。
未適可,必止可;既適可,不過可,務求適可而止。此吾人日用持循,須臾粗心不得。
士君子之偶聚也,不言身心性命,則言天下國家;不言物理人情,則言風俗世道;不規目前過失,則問平生德業。傍花隨柳之間,吟風弄月之際,都無鄙俗媟慢之談,謂此心不可一時流於邪僻,此身不可一日令之偷惰也。若一相逢,不是褻狎,便是亂講,此與僕隸下人何異?只多了這衣冠耳。
作人要如神龍屈伸變化,自得自如,不可爲勢利術數所拘縛。若羈絆隨人,不能自決,只是個牛羊。然亦不可嘵嘵悻悻。
故大智上哲看得幾事分明,外面要無跡無言,胸中要獨往獨來,怎被機械人駕馭得。
財色名位此四字,考人品之大節目也。這裏打不過小善,不足錄矣。自古砥礪名節者,兢兢在這裏做工夫,最不可容易放過。
古之人非曰位居貴要、分爲尊長而遂無可言之人,無可指之過也;非曰卑幼貧賤之人一無所知識,即有知識而亦不當言也。蓋體統名分確然不可易者在道義之外;以道相成,以心相與在體統名分之外。哀哉!後世之貴要尊長而遂無過也。
只盡日點檢自家,發出念頭來果是人心?果是道心?出言行事果是公正?果是私曲?自家人品自家定了幾分,何暇非笑人?又何敢喜人之譽己耶?
往見“泰山喬嶽以立身”四語,甚愛之,疑有未盡,。因推廣爲男兒八景雲:泰山喬嶽之身,海闊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照月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盤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冰清之骨。此八景予甚愧之,當與同志者竭力從事焉。
求人已不可,又求人之轉求;徇人之求已不可,又轉求人之徇人;患難求人已不可,又以富貴利達求人,此丈夫之恥也。
文名、才名、藝名、勇名,人儘讓得過,惟是道德之名則妒者衆矣。無文、無才、無藝、無勇,人盡謙得起,惟是無道德之名則愧者衆矣。君子以道德之實潛修,以道德之名自掩。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固是藏身之恕;有諸己而不求諸人,無諸己而不非諸人,自是無言之感。《大學》爲居上者言,若士君子守身之常法,則餘言亦蓄德之道也。
乾坤盡大,何處容我不得?而到處不爲人所容,則我之難容也。眇然一身,而爲世上難容之人,乃號於人曰:“人之本能容我也。”籲!亦愚矣哉!
名分者,天下之所共守者也。名分不立,則朝廷之紀綱不尊,而法令不行。聖人以名分行道,曲士恃道以壓名分,不知孔子之道視魯侯奚啻天壤,而《鄉黨》一篇何等盡君臣之禮!乃知尊名分與諂時勢不同。名分所在一毫不敢傲惰,時勢所在一毫不敢阿諛。固哉!世之腐儒以尊名分爲諂時勢也。卑哉!世之鄙夫以諂時勢爲薄名分也。
聖人之道太和而已,故萬物皆育。便是秋冬不害其爲太和,況太和又未嘗不在秋冬宇宙間哉!餘性褊,無弘度、平心、溫容、巽語,願從事於太和之道以自廣焉。
只竟夕點檢今日說得幾句話關係身心,行得幾件事有益世道,自慊自愧,恍然獨覺矣。若醉酒飽肉,恣談浪笑,卻不錯過了一日,亂言妄動、昧理從欲,卻不作孽了一日。
只一個俗念頭,錯做了一生人;只一雙俗眼目,錯認了一生人。
少年只要想我見在幹些甚麼事,到頭成個甚麼人,這便有多少恨心!多少愧汗!如何放得自家過?
明鏡雖足以照秋毫之末,然持以照面不照手者何?面不自見,借鏡以見,若手則吾自見之矣。鏡雖明,不明於目也,故君子貴自知自信。以人言爲進止,是照手之識也,若耳目識見所有及,則匪天下之見聞不濟矣。
義、命、法,此三者,君子之所以定身,而衆人之所妄念者也。從妄念而巧邪圖以幸其私,君子恥之。夫義不當爲,命不能爲,法不敢爲,雖欲強之,豈惟無獲?所喪多矣。即獲亦非福也。
避嫌者,尋嫌者也;自辨者,自誣者也。心事重門洞達,略本回邪,行事八窗玲瓏,毫無遮障,則見者服,聞者信。
稍有不白之誣,將家家爲吾稱冤,人人爲吾置喙矣。此之謂潔品,不自潔而人潔之。
善之當爲,如飲食衣服然,乃吾人日用常行事也。人未聞有以禍福度衣食者,而爲善則以禍福爲行止;未聞有以譭譽廢衣食者,而爲善則以譭譽爲行止。惟爲善心不真誠之故耳。果真、果誠,尚有甘死飢寒而樂於趨善者。
有象而無體者,畫人也,欲爲而不能爲;有體而無用者,塑人也,清淨尊嚴,享犧牲香火,而一無所爲;有運動而無知覺者,偶人也,持提掇指使而後爲。此三人者,身無血氣,心無靈明,吾無責矣。
我身原無貧富貴賤得失榮辱字,我只是個我,故富貴貧賤得失榮辱如春風秋月,自去自來,與心全不牽掛,我到底只是個我,夫如是,故可貧可富可貴可賤可得可失可榮可辱。今人惟富貴是貪,其得之也必喜,其失之也如何不悲?其得之也爲榮,其失之也如何不辱?全是靠着假景作真身,外物爲分內,此二氏之所笑也,況吾儒乎?吾輩做工夫,這個是第一。吾愧不能以告同志者。
本分二字,妙不容言。君子持身不可不知本分,知本分則千態萬狀一毫加損不得。聖王爲治,當使民得其本分,得本分則榮辱死生一毫怨望不得。子弒父,臣弒君,皆由不知本分始。
兩柔無聲,合也,一柔無聲,受也。兩剛必碎,激也;一剛必損,積也。故《易》取一剛一柔。是謂乎中以成天下之務,以和一身之德,君子尚之。
毋以人譽而遂謂無過。世道尚渾厚,人人有心史也。人之心史真,惟我有心史而後無畏人之心史矣。
淫怒是大惡,裏面御不住氣,外面顧不得人,成甚涵養?
或曰:“涵養獨無怒乎?”曰:“聖賢之怒自別。”
凡智愚無他,在讀書與不讀書;禍福無他,在爲善與不爲善;貧富無他,在勤儉與不勤儉;譭譽無他,在仁恕與不仁恕。
古人之寬大,非直爲道理當如此,然煞有受用處。弘器度以養德也,省怨怒以養氣也,絕仇讎以遠禍也。
平日讀書,惟有做官是展布時。將窮居所見聞,及生平所欲爲者一一試嘗之,須是所理之政事各得其宜,所治之人物各得其所,纔是滿了本然底分量。
只見得眼前都不可意,便是個礙世之人。人不可我意,我必不可人意。不可人意者我一人,不可我意者千萬人。嗚呼!
未有不可千萬人意而不危者也。是故智者能與世宜,至人不與世礙。
性分、職分、名分、勢分,此四者,宇內之大物。性分、職分在己,在己者不可不盡;名分、勢分在上,在上者不可不守。
初看得我污了世界,便是個盜跖;後看得世界污了我,便是個伯夷;最後看得世界也不污我,我也不污世界,便是個老子。
心要有城池,口要有門戶。有城池則不出,有門戶則不縱。
士君子作人不長進,只是不用心,不着力。其所以不用心、不着力者,只是不愧不奮。能愧能奮,聖人可至。
有道之言,將之心悟;有德之言,得定躬行。有道之言弘暢,有德之言親切。有道之言如遊萬貨之肆,有德之言如發萬貨之商。有道者不容不言,有德者無侯於言,雖然,未嘗不言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
學者說話要簡重從容,循物傍事,這便是說話中涵養。
或問:“不怨不尤了,恐於事天處人上更要留心不?”曰“這天人兩項,千頭萬緒,如何照管得來?有個簡便之法,只在自家身上做,一念、-言、一事都點檢得沒我分毫不是,那禍福譭譽都不須理會。我無求禍之道,而禍來自有天耽借;我無致毀之道,而毀來自有人耽錯,與我全不干涉。若福與譽是我應得底,我不加喜;是我幸得底,我且惺懼愧郝。況天也有力量不能底,人也有知識不到底,也要體悉他,卻有一件緊要,生怕我不能格天動物。這個稍有欠缺,自怨自尤且不暇,又那顧得別個。孔子說個上不怨、下不尤,是不願乎其外道理;孟子說個仰不愧、俯不怍,是素位而行道理。此二意常相須。
天理本自廉退,而吾又處之以疏;人慾本善夤緣,而吾又狎之以親;小人滿方寸,而君子在千里之外矣,欲身之修,得乎?故學者與天理處,始則敬之如師保,既而親之如骨肉,久則渾化爲一體。人慾雖欲乘間而入也,無從矣。
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外勍敵五:聲色、貸利、名位、患難、晏安,內勍敵五:惡怒、喜好、牽纏、褊急、積慣。世君子終日被這個昏惑凌駕,此小勇者之所納款,而大勇者之所務克也。
玄奇之疾,醫以平易;英發之疾,醫以深沉;闊大之疾,醫以充實。不遠之復,不若來行之審也。
奮始怠終,修業之賊也;緩前急後,應事之賊也;躁心浮氣,畜德之賊也;疾言厲色,處衆之賊也。
名心盛者必作僞。
做大官底是一樣家數,做好人底是一樣家數。
見義不爲,又託之違衆,此力行者之大戒也。若肯務實,又自逃名,不患於無術吾竊以自恨焉。
恭敬謙謹,此四字有心之善也;狎侮傲凌,此四字有心之惡也,人所易知也。至於怠忽惰慢,此四字乃無心之失耳,而丹書之戒怠勝敬者兇,論治忽者至分存亡。《大學》以傲惰同論,曾子以暴慢連語者何哉?蓋天下之禍患皆起於四字,一身之罪 過皆生於四字。怠則一切苟且,忽則一切昏忘,惰則一切疏懶,慢則一切延遲,以之應事則萬事皆廢,以之接人則衆心皆離。
古人臨民如馭朽索,使人如承大祭,況接平交以上者乎?古人處事不泄邇,不忘遠,況目前之親切重大者乎?故曰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此九字即毋不敬。毋不敬三字,非但聖狂之分,存亡、治亂、死生、禍福之關也,必然不易之理也。沉心精應者,始真知之。
人一生大罪過,只在自是自私四字。
古人慎言,每雲有餘不敢盡。今人只盡其餘,還不成大過,只是附會支吾,心知其非而取辨於口,不至屈人不止,則又盡有餘者之罪人也。
真正受用處,十分用不得一分,那九分都無些干係,而拼死忘生、忍辱動氣以求之者,皆九分也。何術悟得他醒?可笑可嘆!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嘆,可嘆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聞。
聖人之聞善言也,欣欣然惟恐尼之,故和之以同言,以開其樂告之誠;聖人之聞過言也,引引然惟恐拂之,故內之以溫色,以誘其忠告之實。何也?進德改過爲其有益於我也。此之謂至知。
古者招隱逸,今也獎恬退,吾黨可以愧矣,古者隱逸養道,不得已而後出,今者恬退養望,邀虛名以幹進,吾黨可以戒矣。
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
治亂系所用事。天下國家君子用事則治,小人用事則亂;一身德性用事則治,氣習用事則亂。
難管底是任意,難防底是慣病。此處着力,便是穴上着針、癢處着手。
試點檢終日說話有幾句恰好底,便見所養。
業刻木如巨齒,古無文字,用以記日行之事數也。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去之,謂之修業。更事則再刻如前,大事則大刻,謂之大業。多事則多刻,謂之廣業。士農工商所業不同,謂之常業。農爲士則改刻,謂之易業。古人未有一生無所業者,未有一日不修業者,故古人身修事理,而無怠惰荒寧之時,常有憂勤惕勵之志。一日無事,則一日不安,懼業之不修而曠日之不可也。今也昏昏蕩蕩,四肢不可收拾,窮年終 日無一猷爲放逸而入於禽獸者,無業之故也。人生兩間,無一事可見,無一善可稱,資衣藉食於人,而偷安惰行以死,可羞也已。
古之謗人也,也忠厚誠篤。株林之語,何等渾涵!輿入之謠,猶道實事。後世則不然,所怨在此,所謗在彼。彼固知其所怨者未必上之非,而其謗不足以行也,乃別生一項議論,其才辨附會足以泯吾怨之之實,啓人信之之心,能使被謗者不能免謗之之禍,而我逃謗人之罪。嗚呼!今之謗,雖古之君子且避忌之矣。聖賢處謗無別法,只是自修,其禍福則聽之耳。
處利則要人做君子,我做小人;處名則要人做小人,我做君子,斯惑之甚也。聖賢處利讓利,處名讓名,故淡然恬然,不與世忤。
任教萬分矜持,千分點檢,裏面無自然根本,倉卒之際、忽突之頃,本態自然露出。是以君子慎獨。獨中只有這個,發出來只是這個,何勞迴護,何用支吾?
力有所不能,聖人不以無可奈何者責人;心有所當盡,聖人不以無可奈何者自諉。
或問:“孔子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無乃非位素之義與?”曰:“公此問甚好。慎修君子,寧失之儉素不妨。若論大中至正之道,得之爲有財,卻儉不中禮,與無財不得爲而侈然自奉者相去雖遠,而失中則均。聖賢不諱奢之名,不貪儉之美,只要道理上恰好耳。”
寡恩曰薄,傷恩曰刻,盡事曰切,過事曰激。此四者,寬厚之所深戒也。
《易》稱“道濟天下”,而吾儒事業,動稱行道濟時,濟世安民。聖人未嘗不貴濟也。舟覆矣,而保得舟在,謂之濟可乎?
故爲天下者,患知有其身,有其身不可以爲天下。
萬物安於知足,死於無厭。
足恭過厚,多文密節,皆名教之罪人也。聖人之道自有中正。彼鄉原者,徼名懼譏、希進求榮、辱身降志,皆所不恤,遂成舉世通套。雖直道清節之君子,稍無砥柱之力,不免逐波隨流,其砥柱者,旋以得罪。嗟夫!佞風諛俗,不有持衡當路者一極力挽回之,世道何時復古耶?
時時體悉人情,念念持循天理。
愈進修,愈覺不長;愈點檢,愈覺有非;何者?不留意作人,自家盡看得過。隻日日留意向上,看得自家都是病痛。那有些好處?初頭只見得人慾中過失,到久久又見得天理中過失,到無天理過失,則中行矣。又有不自然,不渾化,着色喫力,過失走出這個邊境纔是。聖人能立無過之地。故學者以有一善自多,以寡一過自幸,皆無志者也。急行者,只見道遠而足不前;急耘者,只見草多而鋤不利。
禮義之大防,壞於衆人一念之苟。譬如由徑之人,只爲一時倦行幾步,便平地踏破一條蹊徑,後來人跟尋舊跡,踵成不可塞之大道。是以君子當衆人所驚之事,略不動容,才幹礙禮義上些須,便愕然變色,若觸大刑憲然,懼大防之不可潰,而微端之不可開也。嗟夫!此衆人之所謂迂,而不以爲重輕者也。
此開天下不可塞之釁者,自苟且之人始也。
大行之美,以孝爲第一;細行之美,以廉爲第一。此二者,君子之所務敦也。然而不辨之申生,不如不告之舜;井上之李,不如受饋之鵝。此二者,孝廉之所務辨也。
吉凶禍福是天主張,譭譽予奪是人主張,立身行已是我主張。此三者,不相奪也。
不得罪於法易,不得罪於理難。君子只是不得罪於理耳。
凡在我者,都是分內底;在天在人者,都是分外底。學者要明於內外之分,則在內缺一分,便是不成人處,在外得一分,便是該知足處。
聽言觀行,是取人之道;樂其言而不問其人,是取善之道。
今人惡聞善言,便訑訑曰:“彼能言而行不逮言,何足取?”是弗思也。吾之聽言也,爲其言之有益於我耳。苟益於我,人之賢否奚問焉?衣敝枲者,市文繡;食糟糠者,市粱肉,將以人棄之乎?
取善而不用,依舊是尋常人,何貴於取?譬之八珍方丈而不下着,依然餓死耳。
有德之容深沉凝重,內充然有餘,外闃然無跡。若面目都是精神,即不出諸口,而漏泄已多矣,畢競是養得浮淺。譬之無量人,一杯酒便達於面目。
人人各有一句終身用之不盡者,但在存心着力耳。或問之,曰:“只是對症之藥便是。如子張只消得存誠二字,宰我只消得警惰二字,子路只消得擇善二字,子夏只消得見大二字。”
言一也,出由之口,則信且從;出跖之口,則三令五申而人且疑之矣。故有言者,有所以重其言者。素行孚人,是所以重其言者也。不然,且爲言累矣。
世人皆知笑人,笑人不妨,笑到是處便難,到可以笑人時則更難。
毀我之言可聞,毀我之人不必問也。使我有此事也,彼雖不言,必有言之者。我聞而改之,是又得一不受業之師也。使我無此事耶,我雖不辨,必有辨之者。若聞而怒之,是又多一不受言之過也。
精明世所畏也,而暴之;才能世所妒也,而市之,不沒也夫!
只一個貪愛心,第一可賤可恥。羊馬之於水革,蠅蟻之於腥羶,蜣螂之於積糞,都是這個念頭。是以君子制欲。
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冤,賴清議以明之,雖死猶生也;清議所冤,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冤之也。惟此事得罪於天甚重,報必及之。
權貴之門雖系通家知已,也須見面稀,行蹤少就好。嘗愛唐詩有“終日帝城裏,不識五侯門”之句,可爲新進之法。
聞世上有不平事,便滿腔憤懣,出激切之語,此最淺夫薄子,士君子之大戒。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行止語默,是禍福關;勤惰儉奢,是成敗關;飲食男女,是死生關。
言出諸口,身何與焉?而身亡。五味宜於口,腹何知焉?而腹病。小害大,昭昭也,而人每縱之,徇之,恣其所出,供其所入。
渾身都遮蓋得,惟有面目不可掩。面目者,公之證也。即有厚貌者,卒然難做預備,不覺心中事都發在面目上。故君子無愧心則無怍容。中心之達達以此也,肺肝之視視以此也。此修己者之所畏也。
韋弁布衣,是我生初服,不愧,此生儘可以還大造。軒冕是甚物事?將個丈夫來做壞了,有甚面目對那青天白日?是宇宙中一腐臭物也,乃揚眉吐氣,以此夸人,而世人共榮慕之,亦大異事。
多少英雄豪傑可與爲善而卒無成,只爲拔此身於習俗中不出。若不恤羣謗,斷以必行,以古人爲契友,以天地爲知己,任他千誣萬毀何妨?
爲人無復揚善者之心,無實稱惡者之口,亦可以語真修矣。
身者,道之輿也。身載道以行,道非載身以行也。故君子道行,則身從之以進;道不行,則身從之以退。道不行而求進不已,譬之大賈百貨山積不售,不載以歸,而又以空輿僱錢也;販夫笑之,貪鄙孰甚焉?故出處之分,只有工語:道行則仕, 道不行則卷而懷之。舍是皆非也。
世間至貴,莫如人品與天地參,與古人友,帝王且爲之屈,天下不易其守。而乃以聲色、財貨、富貴、利達,輕輕將個人品賣了,此之謂自賤。商賈得奇貨亦須待價,況士君子之身乎?身以不護短爲第一長進人。
能不護短,則長進至矣。
世有十態,君子免焉:無武人之態(粗豪),無婦人之態(柔懦),無兒女之態(嬌稚),無市井之態(貪鄙),無俗子之態(庸陋);無蕩子之態(儇佻),無伶優之態(滑稽);無閭閻之態(村野),無堂下人之態(局迫),無婢子之態:(卑諂),無偵諜之態(詭暗),無商賈之態(衒售)。
作本色人,說根心話,幹近情事。
君子有過不辭謗,無過不反謗,共過不推謗。謗無所損於君子也。
惟聖賢終日說話無一字差失。其餘都要擬之而後言,有餘,不敢盡,不然未有無過者。故惟寡言者寡過。
心無留言,言無擇人,雖露肺肝,君子不取也。彼固自以爲光明矣,君子何嘗不光明?自不輕言,言則心口如一耳。
保身底是德義,害身底是才能。德義中之才能,嗚呼!免矣。
恆言“疏懶勤謹”,此四字每相因。懶生疏,謹自勤。聖賢之身豈生而惡逸好勞哉?知天下皆惰慢則百務廢弛,而亂亡隨之矣。先正雲: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怠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強;曰懼;曰強而聖賢之情見矣,所謂憂勤惕勵者也。惟憂故勤,惟惕故勵。
謔非有道之言也。孔於豈不戲?竟是道理上脫灑。今之戲者,媟矣,即有滑稽之巧,亦近俳優之流。凝靜者恥之。
無責人,自修之第一要道;能體人,養量之第一要法。
予不好走貴公之門,雖情義所關,每以無謂而止。或讓予曰:“奔走貴公,得不謂其喜乎?”或曰:“懼彼以不奔走爲罪也。”
予嘆曰:“不然。貴公之門奔走如市,彼固厭苦之甚者見於顏面,但渾厚忍不發於聲耳。徒輸自己一勤勞,徒增貴公一厭惡。且入門一揖之後,賓主各無可言,此面愧郝已無發付處矣。予恐初入仕者犯於衆套而不敢獨異,故發明之。”
亡我者,我也。人不自亡,誰能亡之?
沾沾煦煦,柔潤可人,丈夫之大恥也。君於豈欲與人乖戾? 但自有正情真味故柔嘉不是軟美,自愛者不可不辨。
士大夫一身,斯世之奉弘矣。不蠶織而文繡,不耕畜而膏梁,不僱貸而本馬,不商販而積蓄,此何以故也?乃於世分毫無補,慚負兩間。‘人又以大官詫市井兒,蓋棺有餘愧矣。
且莫論身體力行,只聽隨在聚談間曾幾個說天下、國家、身心、性命正經道理?終日嘵嘵刺刺,滿口都是閒談亂談。吾輩試一猛省,士君子在天地間可否如此度日?
君子慎求人。講道問德,雖屈已折節,自是好學者事。若富貴利達向人開口,最傷士氣,寧困頓沒齒也。
言語之惡,莫大於造誣,行事之惡,莫大於苛刻;心術之惡,莫大於深險。
自家才德,自家明白的。才短德微,即卑官薄祿,已爲難稱。若已逾涘分而觖望無窮,卻是難爲了造物。孔孟身不遇,又當如何?
不善之名,每成於一事,後有諸長,不能掩也;而惟一不善傳。君子之動可不慎與?
一日與友人論身修道理,友人曰:“吾老矣。”某曰:“公無自棄。平日爲惡,即屬行時幹一好事,不失爲改過之鬼,況一息尚存乎?”
既做人在世間,便要勁爽爽、立錚錚的。若如春蚓秋蛇,風花雨絮,一生靠人作骨,恰似世上多了這個人。
有人於此,精密者病其疏,靡綺者病其陋,繁縟者病其簡,謙恭者病其倨,委曲者病其直,無能可於一世之人,奈何?曰:一身怎可得一世之人,只自點檢吾身果如所病否?若以一身就衆口,孔子不能,即能之,成個甚麼人品?放君子以中道爲從違,不以衆言爲憂喜。
夫禮非徒親人,乃君子之所以自愛也;非徒尊人,乃君子之所以敬身也。
君子之出言也,如嗇夫之用財;其見義也,如貪夫之趨利。
古之人勤勵,今之人惰慢。勤勵故精明,而德日修;惰慢故昏蔽,而欲日肆。是以聖人貴憂勤惕勵。
先王之禮文用以飾情,後世之禮文用以飾僞。飾情則三千三百,雖至繁也,不害其爲率真;飾僞則雖一揖一拜,已自多矣。後之惡飾僞者,乃一切苟簡決裂,以潰天下之防,而自謂之率真,將流於伯子之簡而不可行,又禮之賊也。
清者濁所妒也,而又激之淺之乎?其爲量矣。是故君子於已諱美,於人藏疾。若有激濁之任者,不害其爲分曉。
處世以譏訕爲第一病痛。不善在彼,我何與焉?
餘待小人不能假辭色,小人或不能堪。年友王道源危之曰:“今世居官切宜戒此。法度是朝廷的,財貨是百姓的,真借不得人情。至於辭色,卻是我的;假借些兒何害?”餘深感之,因識而改焉。
剛、明,世之礙也。剛而婉,明而晦,免禍也夫!
君子之所持循,只有兩條路:非先聖之成規,則時王之定製。此外悉邪也、俗也,君子不由。
非直之難,而善用其直之難;非用直之難,而善養其直之難。
處身不妨於薄,待人不妨於厚;責己不妨於厚,責人不妨於薄。
坐於廣衆之中,四顧而後語,不先聲,不揚聲,不獨聲。
苦處是正容謹節,樂處是手舞足蹈。這個樂又從那苦處來。
滑稽談諧,言畢而左右顧,惟恐人無笑容,此所謂巧言令色者也。小人側媚皆此態耳。小子戒之。
人之視小過也,愧作悔恨如犯大惡,夫然後能改。無傷二字,修己者之大戒也。
有過是一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都無,一不認則兩過不免。彼強辯以飾非者,果何爲也?
一友與人爭,而歷指其短。予曰,“於十分中,君有一分不是否?”友曰:“我難說沒一二分。”予曰:“且將這一二分都沒了纔好責人。”
餘二十年前曾有心跡雙清之志,十年來有四語云:“行欲清,名欲濁;道欲進,身欲退;利慾後,害欲前;人慾豐,己欲約。”
近看來,太執着,大矯激,只以無心任自然求當其可耳。名跡一任去來,不須照管。
君子之爲善也,以爲理所當爲,非要福,非幹祿;其不爲不善也,以爲理所不當爲,非懼禍,非遠罪。至於垂世教,則諄諄以禍福刑賞爲言。此天地聖王勸懲之大權,君子不敢不奉若而與衆共守也,
茂林芳樹,好鳥之媒也;污池濁渠,穢蟲之母也,氣類之自然也。善不與福期,惡不與禍招。君子見正人而合,邪人見憸夫而密。
吾觀於射,而知言行矣。夫射審而後發,有定見也;滿而後發,有定力也。夫言能審滿,則言無不中;行能審滿,則行無不得。今之言行皆亂放矢也,即中,幸耳。
蝸以涎見覓,蟬以身見黏,螢以光見獲。故愛身者,不貴赫赫之名。
大相反者大相似,此理勢之自然也。故怒極則笑,喜極則悲。
敬者,不苟之謂也,故反苟爲敬。
多門之室生風,多口之人生禍。
磨磚砌壁不塗以堊,惡掩其真也。一堊則人謂糞土之牆矣。
凡外飾者,皆內不足者。至道無言,至言無文,至文無法。
苦毒易避,甘毒難避。晉人之壁馬,齊人之女樂,越人之子女玉帛,其毒甚矣,而愚者如飴,即知之亦不復顧也。由是推之,人皆有甘毒,不必自外饋,而眈眈求之者且衆焉。豈獨虞人、魯人、吳人愚哉?知味者可以懼矣。
好逸惡勞,甘食悅色,適己害羣,擇便逞忿,雖鳥獸亦能之。靈於萬物者,當求有別,不然,類之矣。且風德麟仁,鶴清豸直,烏孝雁貞,苟擇鳥獸之有知者而效法之,且不失爲君子矣。可以人而不如乎?
萬事都要個本意;宮室之設,只爲安居;衣之設,只爲蔽體;食之設,只爲充飢;器之設,只爲利用;妻之設,只爲有後。推此類不可盡窮。苟知其本意,只在本意上求,分外的都是多了。
士大夫殃及子孫者有十:一曰優免太侈。二日侵奪太多。
三曰請託滅公。四曰恃勢凌人。五曰困累鄉黨。六曰要結權貴,損國病人。七曰盜上剝下,以實私橐。八曰簧鼓邪說,搖亂國是。九曰樹黨報復,明中善人。十曰引用邪暱,虐民病國。
兒輩問立身之道。曰:“本分之內,不欠纖微;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今也本分弗圖,而加於本分之外者,不啻千萬矣。
內外之分何處別白?況敢問纖徽毫末間耶?
智者不與命鬥,不與法鬥,不與理鬥,不與勢鬥。
學者事事要自責,慎無責人。人不可我意,自是我無量; 我不可人意,自是我無能。時時自反,才德無不進之理。
氣質之病小,心術之病大。
童心俗態,此二者士人之大恥也。二恥不服,終不可以入君子之路。
習成儀容止甚不打緊,必須是瑟僩中發出來,纔是盛德光輝。那個不嚴厲?不放肆莊重?不爲矜持戲濾?不爲媟慢?惟有道者能之,惟有德者識之。
容貌要沉雅自然,只有一些浮淺之色,作爲之狀,便是屋漏少工夫。
德不怕難積,只怕易累。千日之積不禁一日之累,是故君子防所以累者。
枕蓆之言,房闥之行,通乎四海。牆卑室淺者無論,即宮禁之深嚴,無有言而不知,動而不聞者。士君子不愛名節則已,如有一毫自好之心,幽獨盲動可不慎與?
富以能施爲德,貧以無求爲德,貴以下人爲德,賤以忘勢爲德。
入廟不期敬而自敬,入朝不期肅而自肅,是以君子慎所入也。見嚴師則收斂,見狎友則放恣,是以君子慎所接也。
《氓》之詩,悔恨之極也,可爲士君子殷鑑,當三複之。唐詩有云:“兩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又近世有名言一偶雲:“一失腳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此語足道《氓》詩心事,其曰亦已焉哉。所謂何嗟及矣,無可奈何之辭也。
平生所爲,使怨我者得以指摘,愛我者不能掩護,此省身之大懼也。士君於慎之。故我無過,而謗語滔天不足諒也,可談笑而受之;我有過,而幸不及聞,當寢不貼席、食不下咽矣。
是以君子貴無惡於志。
謹言慎動,省事清心,與世無礙,與人無求,此謂小跳脫。
身要嚴重,意要安定,色要溫雅,氣要和平,語要簡切,心要慈祥,志要果毅,機要縝密。
善養身者,飢渴、寒暑、勞役,外感屢變,而氣體若一,未嘗變也;善養德者,死生、榮辱、夷險,外感屢變,而意念若一,未嘗變也。夫藏令之身,至發揚時而解〔亻亦〕;長令之身,至收斂時而鬱閼,不得謂之定氣。宿稱鎮靜,至倉卒而色變;宿稱淡泊,至紛華而心動,不得謂之定力。斯二者皆無養之過也。
裏面要活潑於規短之中,無令怠忽;外面要溜脫於禮法之中,無今矯強。
四十以前養得定,則老而愈堅;養不定,則老而愈壞。百年實難,是以君子進德修業貴及對也。
涵養如培脆萌,省察如搜田蠹,克治如去盤根。涵養如女子坐幽閨,省察如邏卒緝奸細,克治如將軍戰勍敵。涵養用勿忘勿助工夫,省察用無怠無荒工夫,克治用是絕是忽工夫。
世上只有個道理是可貪可欲的,初不限於取數之多,何者?
所性分定原是無限量的,終身行之不盡。此外都是人慾,最不可萌一毫歆羨心。天之生人各有一定的分涯,聖人制人各有一定的品節,譬之擔夫欲肩輿,丐人慾鼎食,徒爾勞心,竟亦何益?嗟夫!篡奪之所由生,而大亂之所由起,皆恥其分內之不足安,而惟見分外者之可貪可欲故也。故學者養心先要個知分。
知分者,心常寧,欲常得,所欲得自足以安身利用。
心術以光明篤實爲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爲第一,-言語以簡重真切爲第一。
學者只把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時時留心,件件努力,便駸駸乎聖賢之域。非此二者,皆是對外物,皆是妄爲。
進德莫如不苟,不苟先要個耐煩。今人只爲有躁心而不耐煩,故一切苟且卒至破大防而不顧,棄大義而不爲,其始皆起於一念之苟也。
不能長進,只爲昏弱兩字所苦。昏宜靜以澄神,神定則漸精明;弱宜奮以養氣,氣壯則漸強健。
一切言行,只是平心易氣就好。
恣縱既成,不惟禮法所不能制,雖自家悔恨,亦制自家不得。善愛人者,無使恣縱;善自愛者,亦無使恣縱。
天理與人慾交戰時,要如百戰健兒,九死不移,百折不回,其奈我何?如何堂堂天君,卻爲人慾臣僕?內款受降,腔子中成甚世界?
有問密語者囑曰:“望以實心相告!”餘笑曰:“吾內有不可瞞之本心,上有不可欺之天日,在本人有不可掩之是非,在通國有不容泯之公論,一有不實,自負四愆矣。何暇以貌言誑門下哉?”
士君子澡心浴德,要使咳唾爲玉,便溺皆香,才見工夫圓滿。若靈臺中有一點污濁,便如瓜蒂藜蘆,入胃不嘔吐盡不止,
豈可使一刻容留此中耶?夫如是,然後圂涵廁可沉,緇泥可入。
與其抑暴戾之氣,不若養和平之心;與其裁既溢之恩,不若絕分外之望;與其爲後事之厚,不若施先事之簿;與其服延年之藥,不若守保身之方。
猥繁拂逆,生厭惡心,奮守耐之力;柔豔芳濃,生沾惹心,奮跳脫之力;推輓衝突,生隨逐心,奮執持之力;長途末路,生衰歇心,奮鼓舞之力;急遽疲勞,生苟且心,奮敬慎之力。
進道入德莫要於有恆。有恆則不必欲速,不必助長,優優漸漸自到神聖地位。故天道只是個恆,每日定準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毫不損不加,流行不緩不急,而萬古常存,萬物得所。只無恆了,萬事都成不得。餘最坐此病。古人云:“有勤心,無遠道。”只有人勝道,無道勝人之理。
士君子只求四真:真心、真口、真耳、真眼。真心,無妄念;真口,無雜語;真耳,無邪聞;真眼,無錯識。
愚者人笑之,聰明者人疑之。聰明而愚,其大智也。夫《詩》雲“靡哲不愚”,則知不愚非哲也。
以精到之識,用堅持之心,運精進之力,便是金石可穿,豚魚可格,更有甚麼難做之事功?難造之聖神?士君子碌碌一生,百事無成,只是無志。
其有善而彰者,必其有惡而掩者也。君子不彰善以損德,不掩惡以長慝。
餘日日有過,然自信過發吾心,如清水之魚,才發即見,小發即覺,所以卒不得遂其豪悍,至流浪不可收拾者。胸中是非,原先有以照之也。所以常發者何也?只是心不存,養不定。
才爲不善,怕污了名兒,此是徇外心,苟可瞞人,還是要做;才爲不善,怕污了身子,此是爲己心,即人不知,成爲人疑謗,都不照管。是故欺大庭易,欺屋漏難;欺屋漏易,欺方寸難。
吾輩終日不長進處,只是個怨尤兩字,全不反己。聖賢學問,只是個自責自盡,自責自盡之道原無邊界,亦無盡頭。若完了自家分數,還要聽其在天在人,不敢怨尤。況自家舉動又多鬼責人非底罪過,卻敢怨尤耶?以是知自責自盡底人,決不怨尤;怨尤底人,決不肯自責自盡。吾輩不可不自家一照看,才照看,便知天人待我原不薄,惡只是我多慚負處。
果是瑚璉,人不忍以盛腐殠;果是荼蓼,人不肯以薦宗祊;履也,人不肯以加諸首;冠也,人不忍以籍其足。物猶然,而況於人乎?榮辱在所自樹,無以致之,何由及之?此自修者所 當知也。
無以小事動聲色,褻大人之體。
立身行已,服人甚難,也要看甚麼人不服,若中道君子不服,當蚤夜省惕。其意見不同、性術各別、志向相反者,只要求我一個是,也不須與他別自理會。
其惡惡不嚴者,必有惡於己者也;其好善不亟者,必無善於已者也。仁人之好善也,不啻口出;其惡惡也,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則惡惡亦君子所不免者,但恐爲己私,作惡在他人,非可惡耳。若民之所惡而不惡;謂爲民之父母可乎?
世人胡塗,只是抵死沒自家不是,卻不自想,我是堯、舜乎?果是堯、舜,真是沒一毫不是?我若是湯武,未反之前也有分毫錯誤。如何盛氣拒人,巧言飾已,再不認一分過差耶?
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千德萬業,日怠廢而無成;幹罪萬惡,日橫恣而無制,皆此二字爲之。西晉仇禮法而樂豪放,病本正在此安肆日偷。安肆,懶散之謂也。此聖賢之大成也。
甚麼降伏得此之字,日勤慎。勤慎者,敬之謂也。
不難天下相忘,只怕一人竊笑。夫舉世之不聞道也久矣,而聞道者未必無人。苟爲聞道者所知,雖一世非之可也;苟爲聞道者所笑,雖天下是之,終非純正之學。故曰: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有識之君子必不以衆悅博一笑也。
以聖賢之道教人易,以聖賢之道治人難,以聖賢之道出口易,以聖賢之道躬行難;以聖賢之道奮始易,以聖賢之道克終難;以聖賢之道當人易,以聖賢之道慎獨難;以聖賢之道口耳易,以聖賢之道心得難;以聖賢之道處常易,以聖賢之道處變難。過此六難,真到聖賢地步。區區六易,豈不君子路上人?
終不得謂篤實之士也。
山西臬司書齋,餘新置一榻銘於其上左曰:“爾酣餘夢,得無有宵征露宿者乎?爾灸重衾,得無有抱肩裂膚者乎?古之人臥八埏於襁褓,置萬姓於衽席,而後突然得一夕之安。嗚呼!
古之人亦人也夫?古之民亦民也夫?“右曰:”獨室不觸欲,君子所以養精;獨處不交言,君子所以養氣;獨魂不着礙,君子所以養神;獨寢不愧衾,君子所以養德。“
慎者之有餘,足以及人;不慎者之所積,不能保身。
近世料度人意,常向不好邊說去,固是衰世人心無忠厚之意。然土君子不可不自責。若是素行孚人,便是別念頭人亦向好邊料度,何者?所以自立者,足信也。是故君子慎所以立。
人不自愛,則無所不爲;過於自愛,則一無可爲。自愛者,先佔名,實利於天下國家,而跡不足以白其心則不爲;自愛者,先佔利,有利於天下國家,而有損於富貴利達則不爲。上之者即不爲富貴利達,而有累於身家妻子則不爲。天下事待其名利兩全而後爲之,則所爲者無幾矣。
與其喜聞人之過,不若喜聞已之過;與其樂道己之善,不若樂道人之善。
要非人,先要認的自家是個甚麼人;要認的自家,先看古人是個甚麼人。
口之罪大於百體,一進去百川灌不滿,一出來萬馬追不回。
家長不能令人敬,則教令不行?不能令人愛,則心志不孚。
自心得者,尚不能必其身體力行,自耳目入者,欲其勉從而強改焉,萬萬其難矣。故三達德不恃知也,而又欲其仁;不恃仁也,而又欲其勇。
合下作人自有作人道理,不爲別個。
認得真了,便要不候終日,坐以待旦,成功而後止。
人生惟有說話是第一難事。
或問修己之道。曰:“無鮮克有終。”問治人之道。曰:“無忿疾於頑。”
人生天地間,要做有益於世底人。縱沒這心腸、這本事,也休作有損於世底人。
說話如作文字,字在心頭打點過,是心爲草稿而口謄真也,猶不能無過,而況由易之言,真是病狂喪心者。
心不堅確,志不奮揚,力不勇猛,而欲徒義改過,雖千悔萬悔,競無補於分毫。
人到自家沒奈自家何時,便可慟哭。
福莫美於安常,禍莫危於盛滿。天地間萬物萬事未有盛滿而不衰者也。而盛滿各有分量,惟智者能知之。是故卮以一勺爲盛滿,甕以數石爲盛滿;有甕之容而懷勺之懼,則慶有餘矣。
禍福是氣運,善惡是人事。理常相應,類亦相求。若執福善禍淫之說,而使之不爽,則爲善之心衰矣。大叚氣運只是偶然,故善獲福、淫獲禍者半,善獲禍、淫獲福者亦半,不善不淫而獲禍獲福者亦半,人事只是個當然。善者獲福,吾非爲福而修善;淫者獲禍,吾非爲禍而改淫。善獲禍而淫獲福,吾 寧善而處禍,不肯淫而要福。是故君子論天道不言禍福,論人事不言利害。自吾性分當爲之外,皆不庸心,其言禍福利害,爲世教發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來有無所畏而不亡者也。天子者,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於一時,畏史官於後世。百官畏君,羣吏畏長吏,百姓畏上,君子畏公議,小人畏刑,子弟畏父兄,卑幼畏家長。畏則不敢肆而德以成,無畏則從其所欲而及於禍。
非生知,安行之?聖人未有無所畏而能成其德者也。
物忌全盛,事忌全美,人忌全名。是故天地有欠缺之體,聖賢無快足之心。而況瑣屑羣氓,不安淺薄之分,而欲滿其難厭之慾,豈不安哉?是以君子見益而思損,持滿而思溢,不敢恣無涯之望。
靜定後看自家是甚麼一個人。
少年大病,第一怕是氣高。
餘參政東藩日,與年友張督糧臨碧在座。餘以朱判封筆濃字大,臨碧曰:“可惜!可惜!”餘擎筆舉手曰:“年兄此一念,天下受其福矣。判筆一字所費絲毫朱耳,積日積歲,省費不知幾萬倍。克用朱之心,萬事皆然。天下各衙門積日積歲省費又不知幾萬倍。且心不侈然自放,足以養德;財不侈然浪費,足以養福。不但天物不宜暴殄,民膏不宜慢棄而已。夫事有重於費者,過費不爲奢;省有不廢事者,過省不爲吝。”餘在撫院日,不儉於紙,而戒示吏書片紙皆使有用。比見富貴家子弟,用財貨如泥沙,長餘之惠既不及人,有用之物皆棄於地,胸中無不忍一念,口中無可惜兩字。人或勸之,則曰:“所值幾何?”餘嘗號爲溝壑之鬼,而彼方侈然自以爲大手段,不小家勢。痛哉!
兒曹志之。
言語不到千該萬該,再休開口。
今人苦不肯謙,只要拿得架子定,以爲存體。夫子告子張從政,以無小大、無衆寡、無敢慢爲不驕,而周公爲相,吐握下白屋甚者。父師有道之君,子不知損了甚體?若名分所在,自是貶損不得。
過寬殺人,過美殺身。是以君子不縱民情以全之也,不盈己欲以生之也。
閨門之事可傳,而後知君子之家法矣;近習之人起敬,而後知君子之身法矣。其作用處只是無不敬。
宋儒紛紛聚訟語且莫理會,只理會自家何等簡徑。
各自責,則天清地寧;各相責,則天翻地覆。
不逐物是大雄力量,學者第一工夫全在這裏做。
手容恭,足容重,頭容直,口容止,坐如屍,立如齋,儼若思,目無狂視,耳無傾聽,此外景也。外景是整齊嚴肅,內景是齋莊中正,未有不整齊嚴肅而能齋莊中正者。故撿束五宮百體,只爲收攝此心。此心若從容和順於禮法之中,則曲肱指掌、浴沂行歌、吟風弄月、隨柳傍花,何適不可?所謂登彼岸無所事筏也。
天地位,萬物育,幾千年有一會,幾百年有一會,幾十年有一會。故天地之中和甚難。
敬對肆而言。敬是一步一步收斂向內,收斂至無內處,發出來自然暢四肢,發事業,瀰漫六合;肆是一步一步放縱外面去,肆之流禍不言可知。所以千古聖人只一敬字爲允執的關捩子。堯欽明允恭,舜溫恭允塞,禹之安汝止,湯之聖敬日躋,文之朗恭,武之敬勝,孔於之恭而安。講學家不講這個,不知怎麼做工夫。
竊嘆近來世道,在上者積寬成柔,積柔成怯,積怯成畏,積畏成廢;在下者積慢成驕,積驕成怨,積怨成橫,積橫成敢。
吾不知此時治體當如何反也。體面二字,法度之賊也。體面重,法度輕;法度弛,紀綱壞。昔也病在法度,今也病在紀綱。名分者,紀綱之大物也。今也在朝小臣藐大臣,在邊軍士輕主帥,在家子婦蔑父母,在學校弟子慢師,後進凌先進,在鄉里卑幼軋尊長。惟貪肆是恣,不知禮法爲何物,漸不可長。今已長矣,極之必亂必亡,勢已重矣,反已難矣。無識者猶然,甚之,奈何?
禍福者,天司之;榮辱者,君司之;譭譽者,人司之;善惡者,我司之。我只理會我司,別個都莫照管。
吾人終日最不可悠悠盪盪作空軀殼。
業有不得不廢時,至於德,則自有知以至無知時,不可一息斷進修之功也。
清無事澄,濁降則自清;禮無事復,己克則自復。去了病,便是好人;去了雲,便是晴天。
七尺之軀,戴天覆地,抵死不屈於人,乃自落草,以至蓋棺降志辱身、奉承物慾,不啻奴隸,到那魂升於天之上,見那維皇上帝有何顏面?愧死!愧死!
受不得誣謗,只是無識度。除是當罪臨刑,不得含冤而死,須是辯明。若污衊名行,閒言長語,愈辨則愈加,徒自憤懣耳。
不若付之忘言,久則明也。得不明也,得自有天在耳。
作一節之士也要成章,不成章便是苗而不秀。
不患無人所共知之顯名,而患有人所不知之隱惡。顯明雖着遠邇,而隱惡獲罪神明。省躬者懼之。
蹈邪僻,則肆志抗額略無所顧忌;由義禮,則羞頭愧面若無以自容。此愚不肖之恆態,而士君子之大恥也。
物慾生於氣質。
要得富貴福澤,天主張,由不得我;要做賢人君子,我主張,由不得天。
爲惡再沒個勉強底,爲善再沒個自然底。學者勘破此念頭,寧不愧奮?
不爲三氏奴婢,便是兩間翁主。三氏者何?一曰氣質氏,生來氣稟在身,舉動皆其作使,如勇者多暴戾,懦者多退怯是已。二曰習俗氏,世態即成,賢者不能自免,只得與世浮沉,與世依違,明知之而不能獨立。三曰物慾氏,滿世皆可殢之物,每日皆殉欲之事,沉痼流連,至死不能跳脫。魁然七尺之軀,奔走三家之門,不在此則在彼。降志辱身,心安意肯,迷戀不能自知,即知亦不愧憤,大丈夫立身天地之間,與兩儀參,爲萬物靈,不能挺身自豎而倚門傍戶於三家,轟轟烈烈,以富貴利達自雄,亦可憐矣。予即非忠藏義獲,亦豪奴悍婢也,咆哮躑躅,不能解粘去縛,安得挺然脫然獨自當家爲兩間一主人翁乎!可嘆可恨。
自家作人,自家十分曉底,乃虛美薰心,而喜動顏色,是爲自欺。別人作人,自家十分曉底,乃明知其惡,而譽侈口頰,是謂欺人。二者皆可恥也。
知覺二字,奚翹天淵。致了知才覺,覺了纔算知,不覺算不得知。而今說瘡痛,人人都知,惟病瘡者謂之覺。今人爲善去惡不成,只是不覺,覺後便由不得不爲善不去惡。
順其自然,只有一毫矯強,便不是;得其本有,只有一毫增益,便不是。
度之於長短也,權之於輕重也,不爽毫髮,也要個掌尺提秤底。
四端自有分量,擴充到盡處,只滿得原來分量,再增不得些子。
見義不爲,立志無恆,只是腎氣不足。
過也,人皆見之,乃見君子。今人無過可見,豈能賢於君子哉?緣只在文飾彌縫上做工夫,費盡了無限巧迴護,成就了一個真小人。
自家身子,原是自己心去害他,取禍招尤,陷於危敗,更不幹別個事。
六經四書,君子之律令。小人犯法,原不曾讀法律。士君子讀聖賢書而一一犯之,是又在小人下矣。
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工夫便密了。
休諉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我身。
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更有長進。
理會得義命兩字,自然不肯做低人。
稠衆中一言一動,大家環向而視之,口雖不言,而是非之公自在。果善也,大家同萌愛敬之念;果不善也,大家同萌厭惡之念,雖小言動,不可不謹。
或問:“傲爲凶德,則謙爲基德矣?”曰:“謙真是吉,然謙不中禮,所損亦多。”在上者爲非禮之謙,則亂名份、紊紀網,久之法令不行。在下者爲非禮之謙,則取賤辱、喪氣節,久之廉恥掃地。君子接人未嘗不謹飭,持身未嘗不正大,有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又曰:“巧言令色足恭,某亦恥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何嘗貴傲哉?而其羞卑佞也又如此,可爲立身行己者之法戒。
凡處人不繫確然之名分,便小有謙下不妨。得爲而爲之,雖無暫辱,必有後憂。即不論利害論道理,亦云居上不驕民,可近不可下。
只人情世故熟了,甚麼大官做不到?只天理人心合了,甚麼好事做不成?
士君子常自點檢,晝思夜想,不得一時閒,郄思想個甚事?果爲天下國家乎?抑爲身家妻子乎?飛禽走獸,東鶩西奔,爭食奪巢;販夫豎子,朝出暮歸,風餐水宿,他自食其力,原爲溫飽,又不曾受人付託,享人供奉,有何不可?士君子高官重祿,上藉之以名份,下奉之以尊榮,爲汝乎?不爲汝乎?乃資權勢而營鳥哭巿井之圖,細思真是愧死。
古者鄉有縉紳,家邦受其庇廕,士民視爲準繩。今也鄉有縉紳,增家邦陵奪勞費之憂,開土民奢靡浮薄之俗。然則鄉有縉紳,鄉之殃也,風教之蠹也。吾黨可自愧自恨矣。
俗氣入膏肓,扁鵲不能治。爲人胸中無分毫道理,而庸調卑職、虛文濫套認之極真,而執之甚定,是人也,將欲救藥,知不可入。吾黨戒之。
士大夫居鄉,無論大有裨益,只不違禁出息,倚勢侵陵,受賄囑託,討佔伕役,無此四惡,也還算一分人。或曰:“家計蕭條,安得不治生?”曰:“治生有道,如此而後治生,無勢可藉者死乎?”或曰:“親族有事,安得不伸理?”曰:“官自有法,有訟必藉請謁,無力可通者死乎?”士大夫無窮餓而死之理,安用寡廉喪恥若是。
學者視人慾如寇仇,不患無攻治之力,只緣一向姑息他如驕子,所以養成猖獗之勢,無可奈何,故曰識不早,力不易也。制人慾在初發時,極易剿捕,到那橫流時,須要奮萬夫莫當之勇,才得濟事。
宇宙內事,皆備此身,即一種未完,一毫未盡,便是一分破綻;天地間生,莫非吾體,即一夫不獲,一物失所,便是一處瘡痍。
克一分、百分、千萬分,克得盡時,才見有生真我;退一步、百步、千萬步,退到極處,不愁無處安身。
事到放得心下,還慎一慎何妨?言於來向口邊,再思一步更好。
萬般好事說爲,終日不爲;百種貪心要足,何時是足?
回着頭看,年年有過差;放開腳行,日日見長進。
難消客氣衰猶壯,不盡塵心老尚童。
但持鐵石同堅志,即有金鋼不壞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