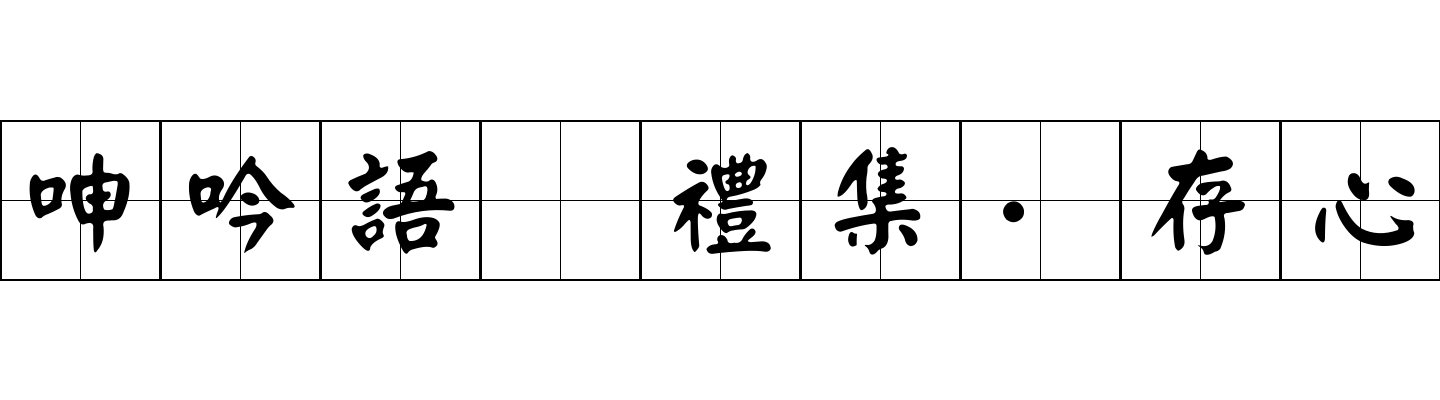呻吟語-禮集·存心-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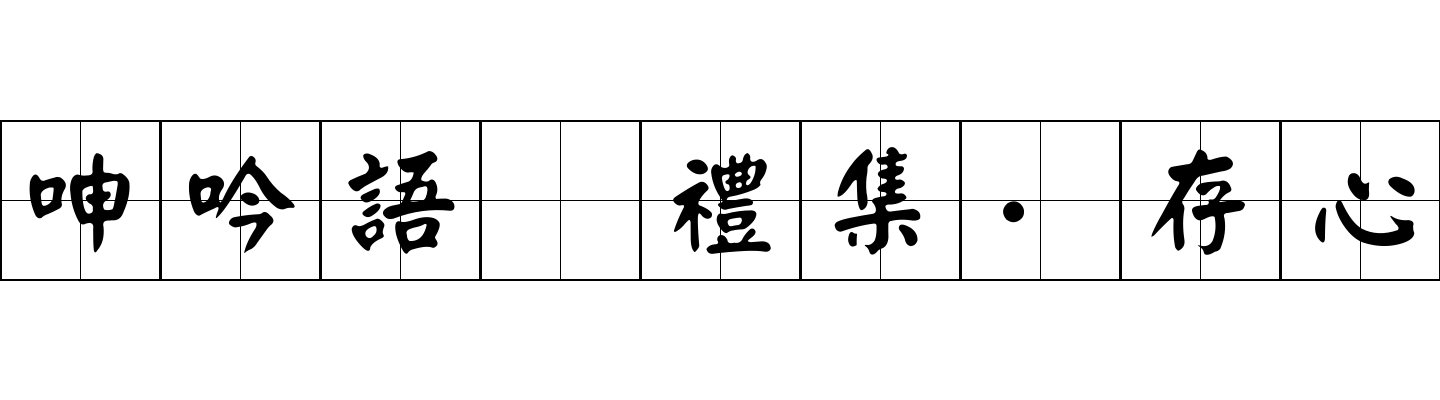
《呻吟語》是明代晚期著名學者呂坤(1536—1618)所著的語錄體、箴言體的小品文集,刊刻於1593(明萬曆二十一年),時呂坤在山西太原任巡撫。 《呻吟語》是呂坤積三十年心血寫成的著述。全書共分六卷,前三卷爲內篇;後三卷爲外篇,一共有大約數百則含意深刻、富有哲理的語錄筆記。
心要如天平,稱物時,物忙而衡不忙;物去時,即懸空在此。只恁靜虛中正,何等自在!
收放心,休要如追放豚,既入笠了,便要使他從容閒暢,無拘迫懊憹之狀。若恨他難收,一向束縛在此,與放失同,何者?同歸於無得也。故再放便奔逸不可收拾。君子之心,如習鷹馴雉,搏擊飛騰,主人略不防閒,及上臂歸庭,卻恁忘機自得,略不驚畏。
學者只事事留心,一毫不肯苟且,德業之進也,如流水矣。
不動氣,事事好。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是個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卻是禪定之學。
或問:“放心如何收?”餘曰:“只君此問,便是收了。這放收甚容易,才昏昏便出去,才惺惺便在此。”
常使精神在心目間,便有主而不眩;於客感之交,只一昏昏,便是胡亂應酬。豈無偶合?終非心上經歷過,竟無長進,譬之夢食,豈能飽哉?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才住腳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也。
一善念發,未說到擴充,且先執持住,此萬善之囤也。若隨來隨去,更不操存此心,如驛傳然,終身無主人住矣。
千日集義,禁不得一刻不慊於心,是以君子瞬存息養,無一刻不在道義上。其防不義也,如千金之子之防盜,懼餒之,故也。
無屋漏工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君子口中無慣語,存心故也。故曰:“修辭立其誠。”不誠,何以修辭?
一念收斂,則萬善來同;一念放恣,則百邪乘釁。
得罪於法,尚可逃避;得罪於理,更沒處存身。只我的心便放不過我。是故君子畏理甚於畏法。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善。”愚謂:惟聖人未接物時何思何慮?賢人以下,睡覺時,合下便動個念頭,或昨日已行事,或今日當行事,便來心上。只看這念頭如何,如一念向好處想,便是舜邊人;若一念向不好處想,便是跖邊人。若念中是善,而本意卻有所爲,這又是舜中跖,漸來漸去,還向跖邊去矣。此是務頭工夫。此時克己更覺容易,點檢更覺精明,所謂“去惡在纖微,持善在根本”也。
目中有花,則視萬物皆妄見也;耳中有聲,則聽萬物皆妄聞也;心中有物,則處萬物皆妄意也。是故此心貴虛。
忘是無心之病,助長是有心之病。心要從容自在,活潑於有無之間。
靜之一字,十二時離不了,一刻才離便亂了。門盡日開闔,樞常靜;妍蚩盡日往來,鏡常靜;人盡日應酬,心常靜。惟靜也,故能張主得動,若逐動而去,應事定不分曉。便是睡時此念不靜,作個夢兒也胡亂。
把意念沉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做?今之學者,將個浮躁心觀理,將個委靡心臨事,只模糊過了一生。
心平氣和,此四字非涵養不能做,工夫只在個定火。火定則百物兼照,萬事得理。水明而火昏。靜屬水,動屬火,故病人火動則躁擾狂越,及其蘇定,渾不能記。蘇定者,水澄清而火熄也。故人非火不生,非火不死;事非火不濟,非火不敗。惟君子善處火,故身安而德滋。
當可怨、可怒、可辯、可訴、可喜、可愕之際,其氣甚平,這是多大涵養。
天地間真滋味,惟靜者能嘗得出;天地間真機括,惟靜者能看得透;天地間真情景,惟靜者能題得破。作熱鬧人,說孟浪語,豈無一得?皆偶合也。 未有甘心快意而不殃身者。惟理義之悅我心,卻步步是安樂境。
問:“慎獨如何解?”曰:“先要認住獨字。獨字就是意字。稠人廣坐、于軍萬馬中,都有個獨,只這意念發出來是大中至正底,這不勞慎,就將這獨宇做去,便是天德王道。這意念發出來,九分九釐是,只有一釐苟且,爲人之意,便要點檢克治,:這便是慎獨了。”
用三十年心力,除一個僞字不得。或曰:“君盡尚實矣。”餘日:“所謂僞者,豈必在言行間哉?實心爲民,雜一念德我之心便是僞,實心爲善,雜一念求知之心便是僞,道理上該做十分,只爭一毫未滿足便是僞,汲汲於向義,纔有二三心便是僞,白晝所爲皆善,而夢寐有非僻之幹便是僞;心中有九分,外面做得恰象十分便是僞。此獨覺之僞也,餘皆不能去,恐漸漬防閒,延惡於言行間耳。”
自家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胸中情景,要看得春不是繁華,夏不是發暢,秋不是寥落,冬不是枯槁,方爲我境。
大丈夫不怕人,只是怕理,不恃人,只是恃道。
靜裏看物,欲如業鏡照妖。
躁心浮氣,淺衷狹量,此八字進德者之大忌也。去此八字,只用得一字,曰主靜。靜則凝重。靜中境自是寬闊。
士君子要養心氣,心氣一衰,天下萬事分毫做不得。冉有隻是個心氣不足。
主靜之力大於千牛,勇於十虎。
君子洗得此心淨,則兩間不見一塵;充得此心盡,則兩間不見一礙,養得此心定,則兩間不見一怖;持得此心堅,則兩間不見一難。
人只是心不放肆,便無過差,只是心不怠忽,便無遺忘。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斷割耳。
盜只是欺人。此心有一毫欺人,一事欺人,一語欺人,人雖不知,即未發覺之盜也。言如是而行欺之,是行者言之盜也。
心如是而口欺之,是口者心之盜也。才發一個真實心,驟發一個僞妄心,是心者心之盜也。諺雲;瞞心昧已有味哉I其言之矣。欺世盜名,其過大,瞞心昧己,其過深。
此心果有不可昧之真知,不可強之定見,雖斷舌可也,決不可從人然諾。
纔要說睡,便睡不着;才說要忘,便忘不得。
舉世都是我心。去了這我心,便是四通八達,六合內無一些界限。要去我心,須要時時省察這念頭是爲天地萬物,是爲我。
目不容一塵,齒不容一芥,非我固有也。如何靈臺內許多荊榛卻自容得?
手有手之道,足有足之道,耳目鼻口有耳目鼻口之道,但此輩皆是奴婢,都聽天君使令。使之以正也,順從,使之以邪也,順從。渠自沒罪過,若有罪過,都是天君承當。
心一鬆散,萬事不可收拾,心一疏忽,萬事不入耳目,心一執着,萬事不得自然。
當尊嚴之地、大衆之前、震怖之景,而心動氣懾,只是涵養不定。
久視則熟字不識,注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蓄疑者,亂真知,過思者,迷正應。
常使天君爲主,萬感爲客便好。只與他平交,已自褻其居尊之體。若跟他走去走來,被他愚弄綴哄,這是小兒童,這是真奴婢,有甚面目來靈臺上坐?役使四肢百骸,可羞可笑。(示多乙)
不存心,看不出自家不是。只於動靜、語默、接物、應事時,件件想一想,便見渾身都是過失。須動合天則,然後爲是。
日用間如何疏忽得一時?學者思之。
人生在天地間,無日不動念,就有個動念底道理;無日不說話,就有個說話底道理;無日不處事,就有個處事底道理;無日不接人,就有個接人底道理;無日不理物,就有個理物底道理;以至怨怒笑歌、傷悲感嘆、顧盼指示、咳唾涕洟、隱微委曲、造次顛沛、疾病危亡,莫不各有道理。只是時財體認,件件講求。細行小物尚求合,則彝倫大節豈可逾閒?故始自垂髫,終於園纊,持一個自強不息之心通乎晝夜。要之,於純一不已之地忘乎死生,此還本歸全之道,戴天履地之宜。不然,恣情縱意而各求遂其所欲,凡有知覺運動者皆然,無取於萬物之靈矣。或日:“有要乎?”曰:“有。其要只在存心。”心何以存?“
曰:“只在主靜。只靜了,千酬萬應都在道理上,事事不錯。”
迷人之迷,其覺也易;明人之迷,其覺也難。
心相信,則跡者士苴也,何煩語言?相疑,則跡者媒孽也,益生猜貳。放有害心不足自明,避嫌反成自誣者,相疑之故也。
是放心一而跡萬。故君子治心不修跡,中孚治心之至也。豚魚且信,何疑之有?
君子畏天,不畏人;畏名教,不畏刑罰;畏不義,不畏不利;畏徒生,不畏捨生。
忍、激二宇是禍福關。
殃咎之來,未有不始於快心者。故君子得意麪憂,逢喜而懼。
一念孳孳,惟善是圖,曰正思。一念孳孳,惟欲是願,曰邪思。非分之福,期望太高,曰越思。先事徘徊,後事懊恨;曰蒙思。遊心千里,岐慮百端,曰浮思。事無可疑,當斷不斷,曰惑思。事不涉已,爲他人憂,曰狂思。無可奈何,當罷不罷,曰徒思。日用職業,本分工夫,朝淮暮圖,期無曠廢,曰本思。
此九思者,日用之間不在此,則在彼。善攝心者,其惟本思乎?
身有定業,日有定務,暮則省白晝之所行,朝則計今日之所事。
念茲在茲,不肯一事苟且,不肯一時放過,庶心有着落,不得他適,而德業日有長進矣。
學者只多忻喜,心便不是凝道之器。
君子亦有坦蕩蕩處,無忌憚是已是已。君子亦有常慼慼處,終身之憂是已。
只脫盡輕薄心,便可達天德。漢唐以下儒者,脫盡此二宇不多人。
斯道這個擔子,海內必有人負荷。有能概然自任者,願以縮弱筋骨助一肩之力,雖走僵死不恨。
耳目之玩偶當於心,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此兒女子常態也世間甚物與我相關,而以得喜,以失悲耶?聖人看得此身亦不關悲喜,是吾道之一囊橐而。愛所受,如之何以囊橐棄所受也?而況耳目之玩,又囊橐之外物乎?
寐是情生景,無情而景者,兆也。寤後景生情,無景而情者,妄也。
人情有當然之願,有過分之慾。聖王者,足其當然之願,而裁其過分之慾,非以相苦也。天地間欲願止有此數,此有餘而彼不足,聖王調劑而均之,裁其過分者以益其當然。夫是之謂至平,而人無淫情無觖望。
惡惡太嚴,便是一惡。樂善甚亟,便早一善。
投佳果於便溺,濯而獻之,食乎?曰:不食。不見而食之,病乎?曰:不病。隔山而指罵之,聞乎?曰:不聞。對面而指罵之,怒乎?曰:怒。曰:此見聞障也。夫能使面而食,聞而不怒,雖入黑海、蹈白刃可也。此煉心者之所當知也。
只有一毫粗疏處,便認理不真,所以說惟精,不然衆論淆之而必疑;只有一毫二三心,便守理不定,所以說惟一,不然利害臨之而必變,
種豆,其苗必豆;種瓜,其苗必瓜。未有所存如是,而所發不如是者。心本人慾,而事欲天理;心本邪曲,而言欲正直,其將能乎?是以君子慎其所存。所存是種,種皆是;所存非種,種皆非,未有分毫爽者。
屬纊之時,般般都帶不得,惟是帶得此心,卻教壞了,是空身歸去矣。可爲萬古一恨。
吾輩所欠,只是涵養不純不定。故言則矢口所發,不當事,不循物,不宜人;事則恣意所行,或太過,或不及,或悖理。
若涵養得定,如熟視正鵠而後開弓,矢矢中的;細量分寸而後投針,處處中穴。此是真正體驗實用工夫,總來只是個沉靜。
沉靜了,發出來件件都是天則。
定靜中境界與六合一般大,裏面空空寂寂,無一個事物,才問他索時,般般足、樣樣有。
暮夜無知,此四字百惡之總根也。人之罪莫大於欺。欺者,利其無知也。大奸大盜皆自無知之心充之。天下大惡只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無知還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僞關。不畏有知是個無所忌憚心,此是死生關。猶知有畏,良心尚未死也。
天地萬物之理出於靜,入於靜;人心之理髮於靜,歸於靜。
靜者,萬理之橐[竹侖],萬化之樞紐也。動中發出來,與天則便不相似。故雖暴肆之人,平旦皆有良心,發於靜也,過後皆有悔心,歸於靜也。
動時只見發揮不盡,那裏覺錯?故君子主靜而慎動。主靜,則動者靜之枝葉也;慎動,則動者靜之約束也。又何過焉?
童心最是作人一大病,只脫了童心,便是大人君子。或問之。曰:“凡炎熱念、驕矜念、華美念、欲速念、浮薄念、聲名念,皆童心也。”
吾輩終日念頭離不了四個字,曰:得、失、毀、譽。其爲善也,先動個得與譽底念頭;其不敢爲惡也,先動個失與毀底念頭。總是欲心、僞心,與聖人天地懸隔。聖人發出善念,如飢者之必食,渴者之必飲。其必不爲不善,如烈火之不入,深淵之不投,任其自然而已。賢人念頭只認個可否,理所當爲,則自強不息;所不可爲,則堅忍不行。然則得失譭譽之念可盡去乎?曰:胡可去也?天地間惟中人最多。此四字者,聖賢籍以訓世,君子藉以檢身。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得失訓世也。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曰年四十而見惡,以譭譽訓世也。此聖人待衰世之心也。彼中人者,不畏此以檢身,將何所不至哉?故堯舜能去此四字,無爲而善,忘得失譭譽之心也。
桀紂能去此四字,敢於爲惡,不得失譭譽之恤也。
心要虛,無一點渣滓;心要實,無一毫欠缺。
只一事不留心,便有一事不得其理;一物不留心,便有一物不得其所。
只大公了,便是包涵天下氣象。
士君子作人,事事時時只要個用心。一事不從心中出,便是亂舉動;一刻心不在腔子裏,便是空軀殼。
古人也算一個人,我輩成底是甚什人?若不愧不奮,便是無志。
聖、狂之分,只在苟、不苟兩字。
餘甚愛萬籟無聲,蕭然一室之趨。或曰:“無乃大寂滅乎?”
曰:“無邊風月自在。”
無技癢心,是多大涵養!故程子見獵而癢。學者各有所癢。
便當各就癢處搔之。
欲,只是有進氣無退氣;理,只是有退氣無進氣。善學者審於進退之間而已。
聖人懸虛明以待天下之感,不先意以感天下之事。其感也,以我胸中道理順應之;其無感也,此心空空洞洞,寂然曠然。
譬之鑑光明在此,物來則照之,物去則光明自在,彼事未來而意必是持鑑覓物也。嘗謂鏡是物之聖人。鏡日照萬物而常明,無心而不勞故也。聖人日應萬事而不累,有心而不役故也。夫惟爲物役而後累心,而後應有偏着。
恕心養到極處,只看得世間人都無罪過。
物有以慢藏而失,亦有以謹藏而失者;禮有以疏忽而誤,亦有以敬畏而誤者。故用心在有無之間。
說不得真知明見,一些涵養不到,發出來便是本象,倉卒之際,自然掩護不得。
一友人沉雅從容,若溫而不理者。隨身急用之物,座客失備者三人,此友取之袖中,皆足以應之。或難以數物,呼左右取之攜中,犁然在也。餘歎服曰:“君不窮於用哉!”曰:“我無以用爲也。此第二着,偶備其萬一耳。備之心,慎之之心也。慎在備先。凡所以需吾備者,吾已先圖,無賴於備。故自有備以來,吾無萬一,故備常徐而不用。”或曰:“是無用備矣。”曰:“無萬一而猶備,此吾之所以爲慎也。若恃備而不慎,則備也者,長吾之怠者也,久之必窮於所備之外。侍慎而不備,是慎也者,限吾之用者也,久之必窮於所慎之外。故寧備而不用,不可用而無備。”餘歎服曰:“此存心之至者也。《易》曰:”藉之用茅,又何咎焉?‘其斯之謂與?“吾識之以爲疏忽者之戒。
欲理會七尺,先理會方寸;欲理會六合,先理會一腔。
靜者生門,躁者死戶。
士君子一出口無反悔之言,一動手無更改之事,誠之於思故也。
只此一念公正了,我於天地鬼神通是一個。而鬼神之有邪氣者,且跧伏退避之不暇,庶民何私何怨,而忍枉其是非,腹誹巷議者乎?
和氣平心發出來,如春風拂弱柳,細雨潤新苗,何等舒泰!
何等感通!疾風、迅雷、暴雨、酷霜,傷損必多。或日:“不似無骨力乎?”餘曰:“闢之玉,堅剛未嘗不堅剛,溫潤未嘗不溫潤。”
餘嚴毅多和平,少近梧得此。
儉則約,約則百善俱興;侈則肆,肆則百惡俱縱。
天下國家之存亡,身之生死,只系敬怠兩字。敬則慎,慎則百務修舉;怠則苟,苟則萬事隳頹。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如此。此千古聖賢之所兢兢,而亡人之所必由也。
每日點檢,要見這念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慾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
初學最要知此。
道義心胸發出來,自無暴戾氣象,怒也怒得有禮。若說聖人不怒,聖人只是六情。
過差遺忘只是昏忽,昏忽只是不敬。若小心慎密,自無過差遺忘之病。孔子曰:“敬事。”樊遲粗鄙,告之曰:“執事敬”。子張意廣,告之曰:“無小大,無敢慢。”今人只是懶散,過差遺忘安得不多?
吾初念只怕天知,久久來不怕天知,又久久來只求天知。
但末到那,何必天知地步耳?
氣盛便沒涵養。
個定靜安慮,聖人胸中無一刻不如此。或曰:“喜怒哀樂到面前何如?”曰:“只恁喜怒哀樂,定靜安慮,胸次無分毫加損。”
優世者與忘世者談,忘世者笑;忘世者與憂世者談,憂世者悲。嗟夫!六合骨肉之淚肯向一室口越之人哭哉?彼且謂我爲病狂,而又安能自知其喪心哉?
得之一字,最壞此心,—不但鄙夫患得,年老戒得爲不可。
只明其道而計功,有事而正心,先事而動得心,先難而動獲心‘便是雜霸雜夷。一念不極其純,萬善不造其極。此作聖者之大戒也。
克一個公已公人心,便是吳越一家;任一個自私自利心,便中父子仇讎。天下興亡、國家治亂、萬姓死生,只爭這個些子。
廁牏之中可以迎賓客,牀第之間可以交神明,必如此而後謂之不苟。
爲人辨冤白謗是第一天理。
無隙可乘。此謂不疏物慾,自消其窺伺之心。僩訓武毅,譬將軍按劍,見者股慄。此謂不弱物慾,自奪其猖獗之氣。而今輩,靈臺四無牆戶,如露地錢財,有手皆取;又孱弱無能,殺殘俘虜落膽。從人物慾,不須投間抵隙,都是他家產業;不須硬迫柔求,都是他家奴婢。更有那個關防?何人喘息?可哭可恨!
沉靜非緘默之謂也。意淵涵而態閒正,此謂真沉靜。雖日言語,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或稠人廣衆中應繁劇,不害其爲沉靜,神定故也。一有飛揚動擾之意,雖端坐終日,寂無一語,而色貌自浮,或意雖不飛揚動擾,而昏昏欲睡,皆不得謂沉靜。
真沉靜底自是惺忪包一段全副精神在時裏。
明者料人之所避,而狡者避人之所料,以此相與,是賊本真而長奸僞也。是以君於寧犯人之疑,而不己之女賊心。
室中之鬥,市上之爭,彼所據各有一方也。一方之見皆是己非人,而濟之以不相下之氣,故寧死而不平。嗚呼!此猶愚人也。賢臣之爭政,賢士之爭理亦然。此言語之所以日多,而後來者益莫知所決擇也。故爲下愚人作法吏易,爲士君子所折衷難。非斷之難,而服之難也。根本處在不見心而任品,恥屈人頂好勝,是室入市兒之見也。
大利不換小義,況以小利壞大義乎?貪者可以戒矣。
殺身者不是刀劍,不是寇仇,乃是自家心殺了自家。
知識,帝則之賊也。惟忘知識以任帝則,此謂天真,此謂自然。一着念便乖違,愈着念愈乖違。乍見之心,歇息一刻,別是一個光景。
爲惡惟恐人知,爲善惟恐人不知,這是一副甚心腸,安得長進?
或問:“虛靈二字如何分別?”曰:;惟虛故靈。頹金無聲,鑄爲鐘磬則有聲。鐘磬有聲,實之崒物則無聲。聖心無所不有,而一無所有,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渾身五臟六腑、百脈千絡、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毛髮甲爪,以至衣裳冠履,都無分毫罪過,都與堯舜一般,只是一點方寸之心千過萬罪,禽獸不如。千古聖賢只是治心,更不說別個。學者只是知得這個可恨,便有許大見識。
人心是個猖狂自在之物,隕身敗家之賊,如何縱容得他?
良知何處來?生於良心;良心何處來?生於天命。
心要實,又要虛。無物之謂虛,無妄之謂實。惟虛故實,惟實故虛。心要小,又要大。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小其心不僨天下之事。
要補必須補個完,要折必須折個淨。
學術以不愧於心、無惡於志爲第一,也要點檢這心志是天理、是人慾。便是天理,也要點檢是邊見、是天則。
堯眉舜目、文王之身仲尼之步,而盜跖其心,君子不貴也。
有數聖賢之心,何妨貌似盜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