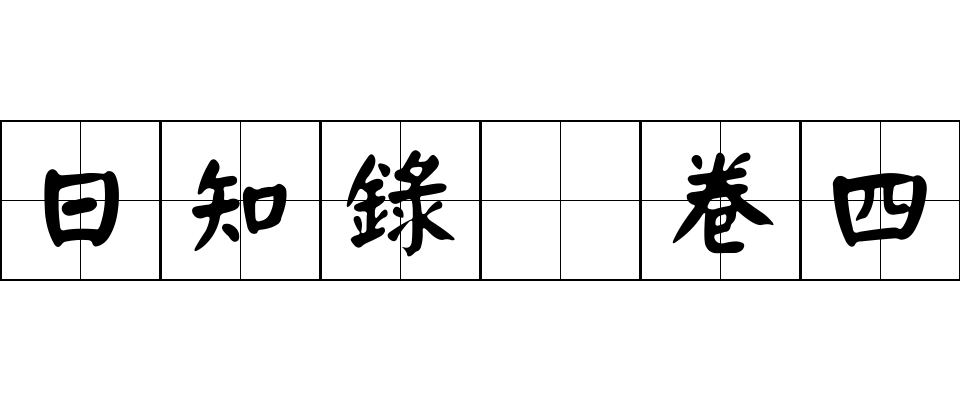日知錄-卷四-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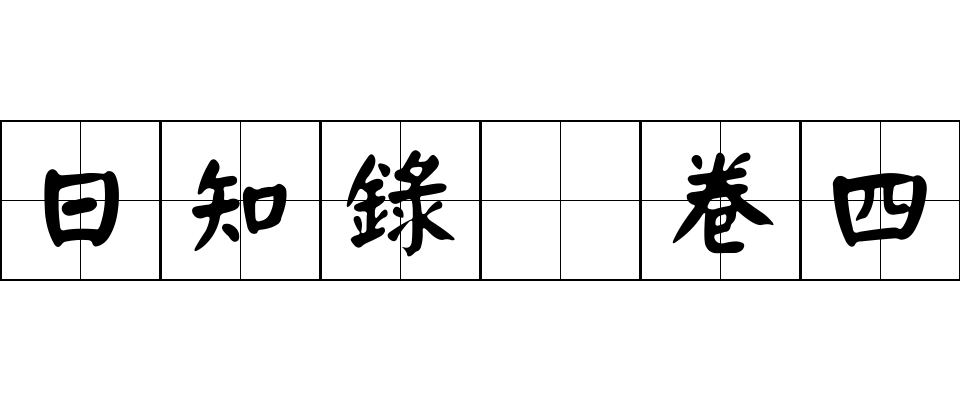
《日知錄》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大思想家顧炎武的代表作品,對後世影響巨大。該書是一經年累月、積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學術札記,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以明道、救世爲宗旨,囊括了作者全部學術、政治思想,遍佈經世、警世內涵。
○魯之春秋《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週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
○春秋闕疑之書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以聖人之明,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豈難考歷布算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況於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者乎,況於列國之事得之傳聞不登於史策者乎。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史之所不書,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魯國之史也,即使歷聘之餘,必聞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國之寶書增入本國之記注乎。若乃改葬惠公之類,不書者,舊史之所無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不名者,闕也。鄭伯髡頑、楚子麋、齊侯陽生之實弒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之文也。左氏出於獲麟之後,網羅浩博,實夫子之所未見。乃後之儒者似謂已有此書,夫子據而筆削之。即左氏之解經,於所不合者亦多曲爲之說;而經生之論遂以聖人所不知爲諱。是以新說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學《春秋》之言皆郢書燕說,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豈特告子張乎,修《春秋》之法亦不過此。《春秋》因魯史而修者也,《左氏傳》採列國之史而作者也。故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於中國,則以列國之史參之,而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間用夏正。其不出於一人明矣。其謂仲子爲子氏,未薨;平王崩,爲赴以庚戌;陳侯鮑卒,爲再赴:似皆揣摩而爲之說。
○三正三正之名,見於《甘誓》。蘇氏以爲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醜爲正者,其來尚矣。《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是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其於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獨是晉爲姬姓之國,而用夏正則不可解。
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今考《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裏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㔻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曆》推之,爲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於傳者也。
《僖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後告。”夫不告文公之入,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爲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爲舊君即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
《隱公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傳作“秋”。劉原父曰:“《左氏》日月與經不同者,丘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參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考宋用殷正,則建酉之月,周以爲冬,宋以爲秋矣。”
《桓公七年》:“夏,谷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作“春”。劉原父曰:“傳所據者以夏正紀時也。”
《文公十六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經在九月,傳作七月。
《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爲周正,則麥禾皆未熟。《四年》:“秋,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蓋芟踐之。”終是可疑。按傳中雜取三正,多有錯誤。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間有失於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閏月《左氏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並是魯歷。春秋時,各國之歷亦自有不同者,經特據魯曆書之耳。《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上年閏月。《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傳在上年閏月。皆魯失閏之證。杜以爲從告,非也。
《史記》:“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則以魯歷爲周曆,非也。平王東遷以後,周朔之不頒久矣,故《漢書·律曆志》六歷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其於左氏之言失閏,皆謂魯歷。蓋本劉歆之說。
○王正月《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也。”李夢陽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權者,亦有‘王正月’字。以是觀之,《春秋》‘王正月’,必魯史本文也。言王者,所以別於夏、殷,並無他義。劉原父以‘王’之一字爲聖人新意,非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於此見之。”
趙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
《左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此古人解經之善,後人辨之累數百千言而未明者,傳以一字盡之矣。
未爲天子,則雖建子而不敢謂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已爲天子,則謂之“正”,而復加“王”以別於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春秋時月並書《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考之《尚書》,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金滕》:“秋,大熟,未獲。”言時則不言月。《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爲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
建子之月而書春,此周人謂之春矣。《後漢書·陳寵傳》曰:“天正建子,周以爲春。”元熊朋來《五經說》曰:“陽生於子即爲春,陰生於午即爲秋,此之謂天統。”
○謂一爲元楊龜山《答胡康侯書》曰:“蒙錄示《春秋》第一段義,所謂‘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初無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鬥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爲醜。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爲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爲異。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
《五代史·漢本紀》論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爲“元”,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徐無黨注曰:“古謂歲之一月亦不雲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閒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雲‘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呂伯恭《春秋講義》曰:“命日以‘元’,《虞典》也。命祀以‘元’,《商訓》也。年紀日辰之首其謂之元,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說《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爲‘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
○改月三代改月之證,見於《白虎通》所引《尚書大傳》之言甚明。其言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爲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爲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氏引《伊訓》、《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爲商人不改月之證,與孔傳不合,亦未有明據。
胡氏又引秦人以亥爲正,不改時月爲證,則不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注,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即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
○天王《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是也。○邾儀父邾儀父之稱字者,附庸之君無爵可稱,若直書其名,又非所以待鄰國之君也,故字之。卑於子男,而進於蠻夷之國,與蕭叔朝公同一例也。《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非矣。
邾儀父稱字,附庸之君也。阝犁來來朝稱名,下矣。介葛盧來不言朝,又下矣。白狄來,略其君之名,又下矣。
○仲子《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亙來歸惠公仲子之。”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衤遂。”曰僖公成風者,僖公之母成風也。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此說得之。《左氏》以爲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之禮尊其母,又未薨而,皆遠於人情,不可信。所以然者,以魯有兩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而隱之夫人又是子氏。二傳所聞不同,故有紛紛之說。
此亦《魯史》原文,蓋魯有兩仲子,不得不稱之曰惠公仲子也。考仲子之宮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略其辭也。
《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系夫之諡,以明所屬。”如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也。妾不得體君,不得已而系之子。仲子系惠公而不得,繫於孝公;成風系僖公而不得,繫於莊公,抑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矣。
《春秋》十二公,夫人之見於經者:桓夫人文姜,莊夫人哀姜,僖夫人聲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齊姜,皆書薨書葬。文夫人出姜不書薨、葬。隱夫人子氏書薨不書葬。昭夫人孟子變薨言卒,不書葬,不稱夫人。其妾母之見於經者,僖母成風,宣母敬贏,襄母定姒,昭母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小君。惟哀母定姒變薨言卒,不稱夫人小君。其他若隱母聲子、桓母仲子、閔母叔姜,皆不見於經。定母則經傳皆闕。而所謂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傳》:“夫人者,隱公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春秋》之例,葬君則書,葬君之母則書,葬妻則不書,所以別禮之輕重也。隱見存而夫人薨,故葬不書。注謂“隱弒賊不討,故不書”者非。
○成風敬嬴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書“夫人”,書“小君”,何也?邦人稱之,舊史書之,夫子焉得而貶之。在後世則秦芊氏、漢薄氏之稱太后也,直書而失自見矣。定姒書“葬”,而不書“夫人”、“小君”,哀未君也。孟子則並不書葬,不成喪也。
○君氏卒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從《左氏》爲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系之君以爲別,猶仲子之系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
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然則去其“夫人”,即爲“君氏”矣。
夫人子氏,隱之妻,嫡也,故書薨。君氏,隱之母,惠公之繼室,妾也,故書卒。
不書葬者何?《春秋》之初,去西周未遠,嫡、妾之分尚嚴,故仲子別宮而獻六羽,所謂猶秉周禮者也。僖公以後,日以僭逾,於經可見矣。
○滕子薛伯杞伯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而子也,貶之乎?貶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也;至於名盡之矣,降其爵非情也。古之天下猶今也。崔呈秀、魏廣微,天下之人無字之者,言及之則名之,名之者惡之也,惡之則名之焉盡之矣。若降其少師而爲太子少師,降其尚書而爲侍郎、郎中、員外,雖童子亦知其不可矣。然則三國之降焉何?沙隨程氏以爲是三國者,皆微困於諸侯之政而自貶焉。春秋之世,衛稱公矣;及其末也,貶而侯,貶而君夫滕、薛、杞猶是也,故魯史因而書之也。
小國貧,則滕、薛、杞降而稱伯稱子;大國強,則齊世子光列於莒、邾、滕、薛、杞、小邾上,時爲之也。左氏謂以先至而進之,亦託辭焉爾。
○闕文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昭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而無事,皆《春秋》之闕文,後人之脫漏也。《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以爲夫子於繼隱之後而書公即位,則桓之志見矣,奚待去其王以爲貶邪”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闕文也。若曰以其錫桓而貶之,則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而書楚子,商人而書齊侯,五等之爵無所可貶,孰有貶及於天王邪?
《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言“氏”。此與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公六年仲孫忌不言“何”同,皆闕文也。聖人之經,平易正大。
邵國賢曰:“‘夏五’,《魯史》之闕文歟?《春秋》之闕文歟?如謂《魯史》之闕文者,筆則筆,削則削,何獨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乎?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推不誠伯高之心,是不誠於後世也,聖人豈爲之哉。不然,則‘甲戌’、‘己丑’、‘叔喜生’、‘仲孫忌’又何爲者?是故‘夏五’,《春秋》闕文也,非《魯史》之闕文也。”
範介儒曰:“‘紀子伯’、‘郭公’、‘夏五’之類,傳經者之脫文耳。謂爲夫子之闕疑,吾不信已。”
○夫人孫於齊《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之也。《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複稱姜氏,見魯人復以小君待之,忘父而與仇通也。先孫後會,其間復歸於魯,而《春秋》不書,爲國諱也,此夫子削之矣。
劉原父曰:“《左氏》曰:‘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爲親,乃中禮爾。然則母可絕乎?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亦不迎而致也,爲嘗試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爲宋姬不爲不慈,襄公不爲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絕不爲親,何傷於義哉!”
《詩》序《猗嗟》:刺魯莊公不能防閒其母趙氏,因之有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之說。此皆禁之於末,而不原其始者也。夫文姜之反於魯,必其與公之喪俱至。其孫於齊,爲國論所不容而去者也,於此而遂絕之,則臣子之義伸,而異日之醜行不登於史策矣。莊公年少,當國之臣不能堅持大義,使之復還於魯。憑君母之尊,挾齊之強,而恣睢淫佚,遂至於不可制。《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左氏》“絕不爲親”一言,深得聖人這意。而魯人既不能行,後儒復昧其義,所謂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豈不信夫。
○公及齊人狩於禚《莊公四年》:“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冬,公及齊人狩於禚。”夫人享齊侯,猶可書也;公與齊侯狩,不可書也。故變文而曰“齊人”,“人”之者,仇之也。杜氏以爲微者,失之矣。
○楚吳書君書大夫《春秋》之於吳、楚,斤斤焉,不欲以其名與之也。楚之見於經也,始於莊之十年,曰“荊”而已。二十三年,於其來聘而“人”之。二十八年,複稱“荊”而不與其“人”也。僖之元年,始稱“楚人”。四年,盟於召陵,始有“大夫”。二十一年,會於盂,始書“楚子”。然使宜申來獻捷者,楚子也,而不書“君”。圍宋者子玉,救衛者子玉,戰城濮者子玉也,而不書“帥”。聖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於中夏也。吳之見於經也,始於成之七年,曰“吳”而已。襄之五年,會於戚,於其來聽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複稱“吳”,殊會而不與其“人”也。二十五年,門於巢卒,始書“吳子”。二十九年,使札來聘,始有“大夫”。然滅州來,敗雞父,滅巢,滅徐,伐越,入郢,敗李,伐陳,會且,會曾阝,伐我,伐齊,救陳,戰艾陵,會橐皋,並稱“吳”,而不與其“人”。會黃池,書“晉侯及吳子”而殊其會。終《春秋》之文,無書“帥”者,使之終不得同於中夏也。是知書君、書大夫,《春秋》之不得已也,政交於中國矣。以後世之事言之,如劉、石十六國之輩,略之而已,至魏、齊、周,則不得不成之爲國,而列之於史。遼、金亦然。此夫子所以錄楚、吳也。然於備書之中而寓抑之之意,聖人之心蓋可見矣。
○亡國書葬紀已亡而書“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亡而書“葬陳哀公”,存陳也。此聖人之情而見諸行事者也。
○許男新臣卒許男新臣卒,《左傳》傳曰:“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而經不言於師,此舊史之闕,夫子不敢增也。穀梁子不得其說,而以爲內桓師,劉原父以爲去其師而歸卒於其國,鑿矣。
○於太廟用致夫人“於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於姑,至是因而致之,不稱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於夷”之文也。哀姜與弒二君,而猶以之配莊公,是亂於禮矣。明乎郊社之禮,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致夫人也,躋僖公也,皆魯道之衰,而夫子所以傷之者也。胡氏以夫人爲成風;成風尚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順也。
以成風稱小君,是亂嫡妾之分。雖然,猶愈於哀姜也。說在乎漢光武之黜呂后,而以薄氏配高廟也。
○及其大夫荀息晉獻公之立奚齊,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臣子言之,則君父之命存焉。是故息之忠同於孔父、仇牧。
○邢人狄人伐衛《春秋》之文有從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於邢。”並舉二國,而狄亦稱“人”,臨文之不得不然也。若惟狄而已,則不稱“人”,《十八年》“狄救齊”,《二十一年》“狄侵衛”是也。《穀梁傳》謂:“狄稱‘人’,進之也。”何以不進之於救齊,而進這於伐衛乎?則又爲之說曰:“善累而後進之。”夫伐衛何善之有?
《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不稱“于越”而稱“越人”,亦同此例。
○王入於王城不書襄王之復,《左氏》書“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而經不書。其文則史也,史之所無,夫子不得而益也。《路史》以爲襄王未嘗復國,而王子虎爲之居守,此鑿空之論。且惠王嘗適鄭,而處於櫟矣。其出不書,其入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未嘗出,未嘗入也。莊王、僖王、頃王崩皆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未嘗崩也,而可乎”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嘗告難於諸侯,故仲尼據策而書之。其入也,與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嘗告於諸侯,策所不載,仲尼雖得之傳聞,安得益之?乃若敬王之立,則仲尼所見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諸侯,況天王乎?策之所具蓋昭如也,故狄泉也書,成周也書。
事莫大於天王之入,而《春秋》不書,故夫子之自言也,曰:“述而不作。”○星孛《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子卒叔仲、惠伯人君而死,義張,而國史不書。夫子平日未嘗闡幽及之者,蓋所謂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讀,而莫之知者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孔寧儀、行父從靈公宣淫於國,殺忠諫之泄治,君弒不能死,從楚而入陳,《春秋》之罪人也,故書曰:“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杜預乃謂二子託楚以報君之仇,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嗚呼:使無申叔時之言,陳爲楚縣矣,二子者,楚之臣僕矣,尚何功之有?幸而楚子復封,成公反國。二子無秋毫之力,而杜氏爲之曲說,使後世詐諼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嗚呼:其亦愈於已爲他人郡縣而猶言報仇者與?
與楚子之存陳,不與楚子納二臣也。公羊子固已言之,曰:“存陳忄希矣。”○三國來媵十二公之世,魯女嫁於諸侯多矣,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蓋宣公元妃所生。
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媵,故伯姬歸於宋特書。
《衛·碩人》之詩曰:“東宮之妹。”正義曰:“東宮,太子所居也。系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女亦然矣。
○殺或不稱大夫凡書“殺其大夫”者,義繫於君,而責其專殺也。盜殺鄭公子、公子發、公孫輒,文不可曰“盜殺大夫”,故不言大夫。其義不繫於君,猶之盟會之卿,書名而已。胡氏以爲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
“閽弒吳子餘祭。”言吳子,則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吳閽弒其君”也。《穀梁子》曰:“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非也。
○邾子來會公《定公十四年》:“大搜於比蒲,邾子來會公。”《春秋》未有書來會公者,來會非朝也,會於大搜之地也。嘉事不以野成,故明年正月復來朝。
○葬用柔日《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贏,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遲而至於明日者,事之變也,非用剛日也。漢人不知此義,而長陵,以丙寅,茂陵。以甲申,平陵,以壬申,渭陵,以丙戌,義陵,以壬寅,皆用剛日。
《穆天子傳》成姬之葬以壬戌。疑其收爲後人僞作。
○諸侯在喪稱子凡繼立之君,逾年正月乃書即位,然後成之爲君;未逾年則稱子,未逾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二十八年》陳子,《定公三年》邾子是也。故有不待葬而即位,則已成之爲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十三年》衛侯,《宣公十一年》陳侯,《成公三年》宋公、衛侯定公。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此皆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傳》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逾年稱公。得之矣。
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定公四年》陳子,是也,所以從同也。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別也。
“鄭伯突出奔蔡”者,已即位之君也。“鄭世子忽復歸於鄭”者,已葬未逾年之子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聖人之抑忽而進突也。
裏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未葬居喪之子也。裏克“弒其君卓”者,逾年已即位之君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非也。
○未逾年書爵即位之禮,必於逾年之正月,即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秋之時,有先君已葬,不待逾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成公四年》:“鄭伯伐許。”稱爵者,從其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
○姒氏卒《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不書薨,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春秋》自成風以下,雖以妾母爲夫人,然必公即位而後稱之。以姒氏之不稱者,本無其事也。後世之君多於柩前即位,於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爲皇太后。及乎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貳於君,子疑於父,而先王之禮亡矣。
○卿不書族《春秋》之文,不書族者有二義。無駭卒;挾卒;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溺會齊師伐衛: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意如至自晉;至自晉:一事再見,因上文而略其辭也。
春秋隱、桓之時,卿大夫賜氏者尚少,故無駭卒,而羽父爲之請族,如挾、如柔、如溺皆未有氏族者也。莊、閔以下,則不復見於經,其時無不賜氏者矣。劉原父曰:“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其於王朝皆士也,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了。周衰禮廢,強弱相併,卿大夫之制雖不能盡如古,見於經者亦皆當時之實錄也。故隱、醒之間,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挾,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君日已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曹、秦以下悉無大夫,患其時有見者害其臆說,因復構架無端,以飾其僞,彼固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
或曰:不稱公子何與?杜氏曰:“公子者,當時之寵號。”之稱公子也,桓賜之也。其終隱之篇不稱公子者,未賜也。若專命之罪則直書而自見矣。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已賜氏也。衛州籲弒其君完,未賜氏也。胡氏以爲以國氏者國及乎上,稱公子者誅及其身,此求其說而不得,故立此論爾。
○大夫稱子周制、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以伯、仲、叔、季爲稱。三桓之先曰共仲,曰僖叔,曰成季。孟孫氏之稱子也自蔑也,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也,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晉之諸卿在文公以前無稱子者,魏氏之稱子也自也,欒氏之稱子也自枝也,趙氏之稱子也自衰也,卻氏之稱子也自缺也,知氏之稱子也自首也,範氏之稱子也自會也,韓氏之稱子也自厥也。晉、齊、魯、衛之執政稱子,他國惟鄭間一有之,餘則否,不敢與大國並也。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仲叔氏皆以伯、叔稱焉,不敢與三家並也。其生也或以伯、仲稱之,如趙孟知伯死,則諡之而後子之,猶國君之死而諡稱公也,於此可以見世之升降焉。讀《春秋》者,其可忽諸?春秋時,大夫雖僭稱子,而不敢稱於其君之前,猶之諸侯僭稱公,而不敢稱於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衛孔悝之《鼎銘》知之,曰“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成叔,孔成子鉏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君前不敢子也。猶有先王之制存焉。至戰國,則子又不足言,而封之爲君矣。
《洛誥》:“予旦以多子,越御事。”多子,猶《春秋》傳之言羣子也。唐孔氏以爲大夫皆稱子,非也。
《春秋》自僖、文以後,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則匹夫而爲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故《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亦世變之所從來矣。《論語》稱孔子爲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夫子者,“夫子矢之”,“夫子喟然嘆曰”,“夫子不答”,“夫子莞爾而笑”,“夫子憮然曰”,不直曰子,而加以“夫”避不成辭也。
○有諡則不稱字《春秋》傳,凡大夫之有諡者則不書字;外大夫若宋、若鄭、若陳、若蔡、若楚、若秦,夫諡也,而後字之。內大夫若羽父,若衆仲,若子家,無諡也,而後字之。公子亦然。楚共王之五子,其成君者皆諡,康王、靈王、平王是也,其不成君無諡而後字之,子幹、子是也。他國亦然,陳之五父,鄭之子、子儀是也。衛州籲、齊無知。賊也,則名之。作傳者於稱名之法,可謂嚴且密矣。○人君稱大夫字古者人君,於其國之卿大夫皆曰伯父,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獨諸侯然也,《曲禮》言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革,然而天子接之猶稱其字。《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季氏而弗聞乎?”《成公三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曰:“鞏伯實來。”《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後,籍談爲介。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又曰:“叔氏,而忘諸乎?”周德雖衰,辭不失舊,此其稱字,必先王之制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若侯國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並列於王官之後,蓋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成上下之交矣。
○王貳於虢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左氏之記周事曰:“王貳於虢”,“王叛王孫蘇”,以天王之尊,而日貳,日叛,若敵者之辭,其不知《春秋》之義甚矣。
○星隕如雨“星隕如雨”,言多也。《當書·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言:‘《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來至今再見。’”此爲得之。而後代之史,或曰:“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織”,或曰“四方流星,大小縱橫查餘”,皆其類也。不言“石隕”,不至地也。傳曰:“與雨偕也。”然則無雨而隕,將不爲異乎?
○築“築,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舊唐書·禮儀志》太常博士顧德章議引此,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凡城二十四邑,惟一邑書築,其二十三邑曰城,豈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又《定公十五年》:“城漆。”漆是邾邑,正義亦知其不可通,而曲爲之說。
○城小谷“城小谷,爲管仲也。”據經文,小谷不繫於齊,疑《左氏》之誤。範寧解《穀梁傳》曰:“小谷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谷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谷城,當即此地。杜氏以此小谷爲齊邑濟北谷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劉昭《郡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皆同。按《春秋》有言“谷”不言“小”者。《莊公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於谷。”《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谷。”《文公十七年》:“公及齊侯盟於谷。”《成公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谷。”四書“谷”,而一書“小谷”,別於谷也。又《昭公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谷置管仲焉,至於今賴之。”則知《春秋》四書之谷及管仲所封在濟北谷城,而此之小谷自爲魯邑爾。況其時齊桓公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見於天下,豈遽勤諸侯,以城其私邑哉。
○齊人殺哀姜哀姜通慶父,弒閔公,爲國論所不容,而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義也。而傳謂之“已甚”,非也。
○微子啓“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何孟春曰:“按《書》,殷紂無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應當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後,無復還之理。而牧野之戰,亦必不從人而伐其宗國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言,特託之古人以規楚子乎?”
徐孚遠曰:“《史記》言微子持祭器造于軍門,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夫武王既立武庚,而又復微子之位,則是微子與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後武庚之鄭,微子何以初無異同之跡?然則武王克商,微子未嘗來歸也。
○襄仲如齊納幣經書僖公之薨以“十二月”,而公子遂如齊納幣,則但書“冬”。即如杜氏之解,移公薨於十一有,而猶在二十五月之內,惡得謂之禮乎?
○子叔姬卒據《傳》,杞桓公在位七十年。其二十二年,魯文公之十二年,出一叔姬;其五十年,魯成公之四年,又出一叔姬。再娶於魯而再出之,必無此理。殆一事而左氏誤重書之爾。且文公十二年,經書曰:“二月庚子,子叔姬卒。”何以知其爲杞婦乎?趙子曰:“書卒義與僖公九年伯姬同,以其爲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其非先君之女也。”
○齊昭公《齊公十四年》:“齊侯潘卒。”傳以爲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經書“齊侯昭卒。”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爲諡。疑《左氏》之誤。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嬴生昭公。”前後文同,先儒無致疑者。
○趙盾弒其君《太史書》曰:“趙質弒其君。”此董狐之直筆也。“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此董狐之巽辭也。傳者不察其指,而妄述孔子之言,以爲越境,乃免謬矣。穿之弒,盾主之也,討穿猶不得免也。君臣之義無逃於天地之間,而可逃之境外乎?
○臨於周廟《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杜氏以爲文王廟也。《昭公十八年》:“鄭使祝史徙主於周廟。”勞動致富氏以爲厲王廟也。傳曰:“鄭祖厲王。”而《哀公二年》,蒯聵之禱亦云;“敢昭祖也。始封之君謂之祖。雖然,伯禽爲文王之孫,鄭桓爲厲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國也,將何祭哉?天下有無祖考之人乎?而況於有土者乎!意者特立一廟以祀文王、厲王,而謂之周廟歟?漢時有郡國廟,其亦仿古而爲之歟?
《竹書紀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於周公廟。”按二十一年,周文公薨於豐。周公未薨,何以有廟?蓋周廟也。是則始封之君有廟,亦可因此而知之說。
○欒懷子晉人殺欒盈,安得有諡?傳言“懷子好施,士多歸之”。豈其家臣爲之諡,而遂傳於史策邪?
○子大叔之廟《昭公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遊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即如是,子產乃使闢之。”《十八年》:“簡兵大搜,將爲搜除。子太叔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斯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此亦一事,而記者或以爲葬,或以爲搜,傳兩存之,而失刪其一耳。
○城成周《昭公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曰:‘魏子必有大咎,幹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幹位以作大事乎?’”《定公元年》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蒞政,衛彪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幹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此是一事,《左氏》兩收,而失刪其一。周之正月,晉之十一月也。其下文曰:“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斯,計徒庸,慮財用,書侯糧,以令役於諸侯。”又曰:“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庚寅即己丑之明日,而傳分爲兩年,豈有遲之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
○五伯五伯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元凱雲:“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臺卿注:“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二說不同。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爲五,亦不當繼此無伯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國語》:“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軌注:“彭祖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是所謂五伯者,亦商時也。是知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若《孟子》所稱五伯,而以桓公爲盛,則止就東周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也。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爲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越王句踐“遂報強吳,觀兵中國,稱號五伯”。子長在臺卿之前,所聞異辭。然則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之說;言春秋之五伯,當列句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闔閭、句踐爲五伯,斯得之矣。
○佔法之多以日佔事者,《史記·天宮書》:“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佔。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是也。以時佔事者,《越絕書》公孫聖:“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史記·賈誼傳》“庚子日斜,服集予舍”是也。又有以月行所在爲佔,《史記·龜策傳》:“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漢書》翼奉言:“白鶴館以月宿,亢災”,《後漢書》蘇竟言:“白虹見時,月入於畢”是也。《周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佔六夢之吉凶。”則古人之法可知矣。漢以下則其說愈多,其佔愈鑿,加以日時、風角、雲氣遲疾變動,不一其物,故有一事而合於此者或迕於彼,豈非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者邪?故士文伯對晉侯以六物不同,民心不臺;而太史公亦謂皋、唐甘、石書傳,凌雜米鹽,在人自得之於象佔之外耳。幹寶解《易》,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曰:“一卦六爻則皆雜有八卦之氣,若初九爲震爻,九二爲坎爻也。或若見辰戌言艮,己亥言兌也。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得來爲惡物,王相爲興,休廢爲衰。解爻有等,故曰物。”曰:“爻中之義,君物交集,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衆形萬類,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物也。”說《易》如此,小數詳而大道隱矣。以此卜筮亦必不驗,天文亦然。
褚先生補《史記·日者列傳》:“孝武帝時,聚會佔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兇。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
○以日同爲佔裨竈以逢公卒於戊子日,而謂今七月戊子,晉君將死。萇宏以昆吾乙卯日亡,而謂毛得殺毛伯而代之是乙卯日,以卜其亡。此以日之同於古人者爲佔,又是一法。
○天道遠春秋時,鄭裨竈、魯梓慎最明於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從,亦不復火。《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雖二子之精,亦有時而失之也。故張衡《思玄賦》曰:“慎竈顯以言天兮,佔水火而妄訊。”
○一事兩佔《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宋、鄭其飢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飢。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飢何爲?”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鄭皆飢。一事兩佔,皆驗。
○春秋言天之學天文王行之說,愈疏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而已。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佔不之及,何其簡也。而其所詳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這間及人事之治亂敬怠,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揚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佔天。”
○左氏不必盡信昔人所言興亡禍福之故不必盡驗。《左氏》但記其信而有徵者爾,而亦不盡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至於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並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爲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篡於陳氏。聞鄭風,以爲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爲最後。《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記之言亦不盡信也。
○列國官名春秋時列國官名,若晉之中行,宋之門尹,鄭之馬師,秦之不更庶長,皆他國所無。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領、左尹、右尹、連尹、針尹、寢尹、工尹、卜尹、芋尹、藍尹、沈尹、清尹、莠尹、囂尹、陵尹、郊尹、樂尹、宮廄尹、監馬尹、楊豚尹、武城尹其官名大抵異於他國。
○地名《左傳·成公元年》:“戰於鞍,入自丘輿。”注云:“齊邑。”《三年》:“鄭師御晉,敗諸丘輿。”注云:“鄭地。”《哀公十四年》:“坑氏葬諸丘輿。”注云:“坑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又是魯地。是三丘輿爲三國地也。《文公七年》:“穆伯如莒,蒞盟,及鄢陵。”注云:“莒邑。”《成公十六年》:“戰於鄢陵。”注云:“鄭地,今屬潁川郡。”是二鄢陵,爲二國地也。《襄公十四年》:“伐秦,至於或林,爲二國地也。《襄公十七年》:“衛孫蒯田於曹隧,飲馬於重丘。”注云:“曹邑。”《二十五年》:“同盟於重丘。”注云:“齊地。”是二重丘,爲二國地也。《定公十二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無注,當是魯地。《哀公十三年》:“彌庸見姑蔑之旗。”注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是二姑蔑,爲二國地也。
地名盂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盂。”宋之盂也。《定公八年》:“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周之盂也。《十四年》:“衛太子蒯聵獻盂於齊。”衛之盂也。而晉則有二盂。《昭公二十八年》:“盂丙爲盂大夫。”今太原盂縣。《哀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高阝、逆、陰人、盂、壺口。”此盂當在邢、洛之間。
州國有二。《桓公五年》:“州公如曹。”注:“州國在城陽淳于縣。”《十一年》:“鄖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
○昌[A227]《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在昌蜀、白、黑、形鹽。”注曰:“昌蜀,昌蒲菹。”而《釋文》蜀音在感反,正義曰:“齊有邴蜀,魯有公父蜀,其音爲觸。《說文》:“蜀,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蜀之音,相傳爲在感反,不知與彼爲同爲異。”今考顧氏《玉篇》有“[A227]”字:“:徂敢切,昌蒲俎也。”然則傳之昌[A227]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作“蜀”。是知南北之學陸、孔諸儒猶有不能遍通。《哀公二十五年》:“若見之君將之。”今本作“[A11M]”,《廣韻》注曰:“《說文》從口。”蓋經典之誤文不自天寶、開成始矣。
《襄公二十四年》:“日有食之。”正義曰:“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轉寫謬誤,失其本真,後儒因循莫能改易。”此通人之至論。考《魏書》江式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考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世謂之古文。”自古文以至於今,其傳寫不知幾千百矣,安得無誤?後之學者,於其所不能通,必穿鑿而曲爲之說,其爲經典之害也甚矣!
古之教人必先小學,小學之書,聲音、文字是也。《顏氏家訓》曰:“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吾有取乎其言。○文字不同《五經》中,文字不同多矣。有一經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葚”見於衛詩,而魯則爲“黮”;“鬯弓”著於鄭風,而秦則爲“”《左氏》一書,其錄楚也“氏”或爲“氏”,“箴尹”或爲“針尹”,況於鐘鼎之文乎!《記》曰“書同文”,亦言其大略耳。
○所見異辭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則所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所見以補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均勻矣。雖得之於聞,必將參互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爲異辭也。公子益師之卒,《魯史》不書其日,遠而無所考矣。以此釋經,豈不甚易而實是乎?何休見《桓公二年》會稷之傳,以恩之淺深,有“諱”與“目言”之異,而以書日不書日,詳略之分,爲同此例,則甚難而實非矣。竊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三語必有所本。而齊、魯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闕文,一也;諱惡,二也;言孫,三也。從前之一說,則略於遠而詳於近;從後之二說,則晦於近而章於遠。讀《春秋》者,可以得之矣。《漢書》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及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學。夫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曾子且聞而未達,非子游舉其事實之,亦烏得而明哉?故曰:《春秋》之失亂。○紀履糹俞來逆女“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富平李因篤曰:“此言經所以不書紀侯者,以見母雖不通,而紀侯有母,則不得自稱主人,以別於宋公之無母也。
○母弟稱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何休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爲親疏,此時人至陋之見。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禍亂萌生,鮮不由此。詩人美鳩均愛七子,豈有於父母則望之以均平,於兄弟則教之以疏外,以此爲質,是所謂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郭氏曰:“若如《公羊》之說,則異母兄弟不謂之兄弟乎?”程子曰:“《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弟爲加親也。若以同母弟爲加親,則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獸也。”
○子沈子《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闢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何後師之多歟然則此傳不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
○谷伯鄧侯書名“谷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其義甚明,而何氏乃有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之說,又有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之說。胡氏因之,遂以朝桓之貶歸之於天道矣。
○鄭忽書名“鄭忽出奔衛。”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傳文簡而難曉。李因篤曰:“《春秋》之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是則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也。故子產曰:‘鄭伯、男也。’遭喪未逾年之君,公侯皆稱子,如宋子、衛子、陳子之類是也。以其等本貴於伯、子、男,故降而稱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爲一等,下此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名非貶忽之辭,故曰‘辭無所貶。’”○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九年》:“春,紀季姜歸於京師。”從逆者而言,謂之王后;從歸者而言,謂之季姜,此自然之文也。猶《詩》之言“爲韓吉相攸”也,猶《左氏》之言“息嬀將歸過蔡”也,皆未嫁而冠以夫國之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也。而公羊以爲“王者無外,其辭成矣”,又以爲“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其說經雖巧,而非聖人之意矣。今將曰“逆季姜於紀”,則初學之士亦知其不通;又將曰“王后歸於京師”,則王后者誰之女?辭窮矣。公羊子蓋拘於在國稱女之例,而不知文固有倒之而順者也。
傳文則有不同者,《左氏·莊公十八年》:“陳嬀歸於京師。”實惠後。○爭門《公羊·閔公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注:“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據《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是也,爭門、吏門並闕。按《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從水、爭聲。士耕切。”是爭門即以此水名,省文作“爭”爾。後人以“氵靜”字省作“淨”,音才性切。而梵書用之,自南北史以下,俱爲才性之淨,而魯之爭門不復知矣。
○仲嬰齊卒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其爲仲遂後者也。《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於。”則子叔聲伯也。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故其子即以父字爲氏。生而賜氏,非禮也。以父字爲氏,亦非禮也。《春秋》從其本稱,而不沒其變氏,其生也書“公子遂”,其死也書“仲遂卒於垂”;於其子也,其生也書“公孫歸父”,其死也書“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經,爲仲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戰鞍、如晉、如莒,已屢見於經矣。
“爲人後者爲之子”,此語必有所受。然嬰齊之爲後,後仲遂,非後歸父也,以爲爲兄後則非也。傳拘於孫以王父字爲氏之說,而以嬰齊爲後歸父,則以弟後兄,亂昭穆之倫矣,非也,且三桓亦何愛于歸父而爲之立後哉。
◎隱十年無正隱十年無正者,以無其月之事而不書,非有意削之也。穀梁以爲隱不自正者,鑿矣。趙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舊史闕也。”得之矣。○戎菽《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菽也。”似據《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而爲之說。桓公以戎捷誇示諸侯,豈徒一戎菽哉。且《生民》之詩曰:“藝之荏菽,荏菽旃旃。”傳曰:“荏菽,戎菽也。”《爾雅》:“戎菽謂之荏菽。”則自後稷之生而已藝之,不待桓公而始布矣。
○隕石於宋五《公》、《谷》二傳,相傳受之子夏,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然而齊魯之間,人自爲師,窮鄉多異,曲學多辯,其穿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隕石於宋五,六退飛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雲“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雲“六”,而夫子改這“六”也。穀梁子曰:“隕石於宋五,後數,散辭也。”“六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辭乎?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未有爲之說者也。
石無知,故日之;然則梁山崩不日,何也?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則有雊鵒來巢不月,何也?夫月日之有無,其文則史也。故劉敞謂: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隕石同日,書“是月”以別之也。
○王子虎卒《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左氏以爲王叔文公者,是也。而穀梁以爲叔服。按此後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於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成公元年,劉康公伐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明叔服別是一人,非王子虎。
○穀梁日誤作曰《穀梁傳·宜公十五年》:“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疏解其迂,按傳文“曰”字誤,當作“其日,潞子嬰兒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