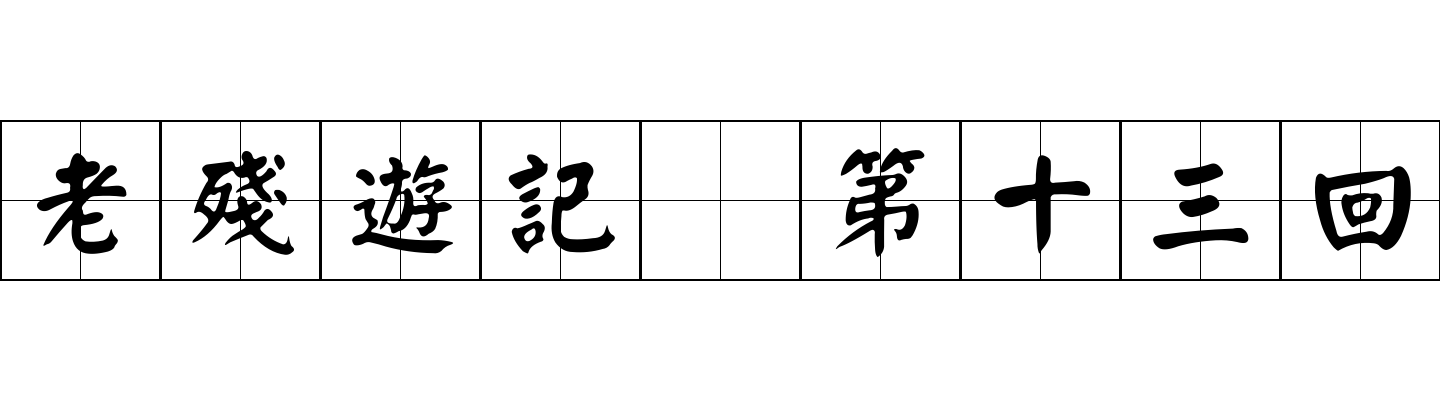老殘遊記-第十三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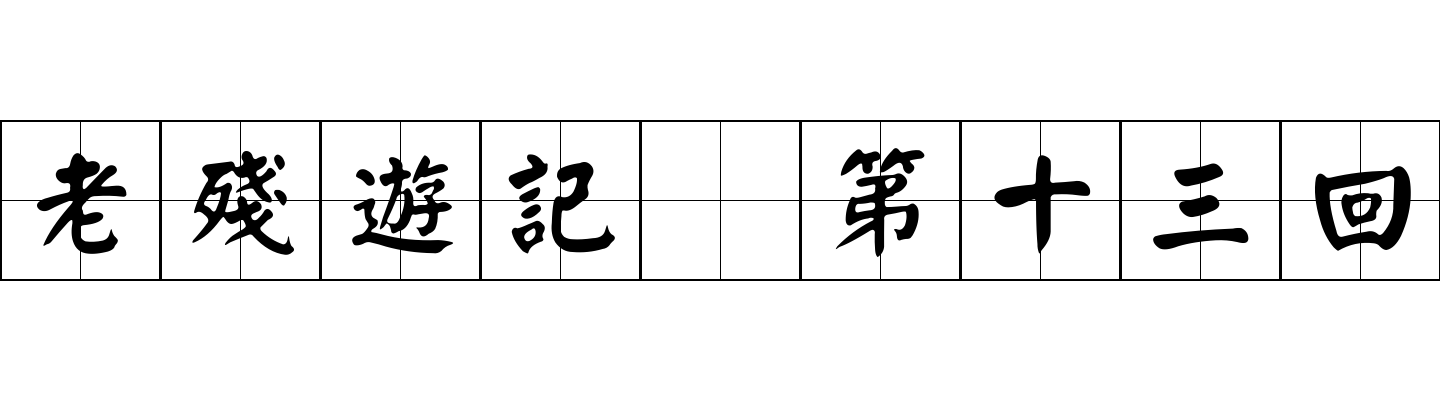
《老殘遊記》,清末中篇小說,是劉鶚 (1857年10月18日—1909年8月23日)的代表作,小說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殘的遊歷爲主線,對社會矛盾開掘很深,尤其是他在書中敢於直斥清官(清官中的酷吏)誤國,清官害民,獨具慧眼地指出清官的昏庸常常比貪官更甚。同時,小說在民族傳統文化精華提煉、生活哲學及藝術、女性審美和平等、人物心理及音樂景物描寫等多方面皆達到了極其高超的境界。
娓娓青燈女兒酸語 滔滔黃水觀察嘉謨
話說老殘復行坐下,等黃人瑞喫幾口煙,好把這驚天動地的案子說給他聽,隨便也就躺下來了。翠環此刻也相熟了些,就倚在老殘腿上,問道:“鐵老,你貴處是那裏?這詩上說的是什麼話?”老殘——告訴他聽。他便凝神想了一想道:“說的真是不錯。但是詩上也興說這些話嗎?”老殘道:“詩上不興說這些話,更說什麼話呢?”翠環道:“我在二十里鋪的時候,過往客人見的很多,也常有題詩在牆上的。我最喜歡請他們講給我聽,聽來聽去,大約不過兩個意思:體面些的人總無非說自己才氣怎麼大,天下人都不認識他;次一等的人呢,就無非說那個姐兒長的怎麼好,同他怎麼樣的恩愛。
“那老爺們的才氣大不大呢,我們是不會知道的。只是過來過去的人怎樣都是些大才,爲啥想一個沒有才的看看都看不着呢,我說一句傻話:既是沒才的這麼少,俗語說的好,‘物以稀爲貴’,豈不是沒才的倒成了寶貝了嗎。這且不去管他。
“那些說姐兒們長得好的,無非卻是我們眼面前的幾個人,有的連鼻子眼睛還沒有長的周全呢,他們不是比他西施,就是比他王嬙;不是說他沉魚落雁,就是說他閉月羞花。王嬙俺不知道他老是誰,有人說,就是昭君娘娘。我想,昭君娘娘跟那西施娘娘難道都是這種乏樣子嗎?一定靠不住了。
“至於說姐兒怎樣跟他好,恩情怎樣重,我有一回發了傻性子,去問了問,那個姐兒說:‘他住了一夜就麻煩了一夜。天明問他要討個兩數銀子的體已,他就抹下臉來,直着脖兒梗,亂嚷說:我正賬昨兒晚上就開發了,還要什麼體己錢?’那姐兒哩,再三央告着說:‘正賬的錢呢,店裏夥計扣一分,掌櫃的又扣一分,剩下的全是領家的媽拿去,一個錢也放不出來。俺們的矚脂花粉,跟身上穿的小衣裳,都是自己錢買。光聽聽曲子的老爺們,不能向他要,只有這留住的老爺們,可以開口討兩個伺侯辛苦錢。’再三央告着,他給了二百錢一個小串子,望地下一摔,還要撅着嘴說:‘你們這些強盜婊子,真不是東西!混帳王八旦!,你想有恩情沒有?因此,我想,做詩這件事是很沒有意思的,不過造些謠言罷了。你老的詩,怎麼不是這個樣子呢?”老殘笑說道:“‘各師父備傳授,各把戲各變手。’我們師父傳我們的時候,不是這個傳法,所以不同。”
黃人瑞剛纔把一筒煙喫完,放下煙槍,說道:“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做詩不過是造些謠言,這句話真被這孩子說着了呢!從今以後,我也不做詩了,免得造些謠言,被他們笑話。”翠環道:“誰敢笑話你老呢!俺們是鄉下沒見過世面的孩子,胡說亂道,你老爺可別怪着我,給你老磕個頭罷!”就側着身子,朝黃人瑞把頭點了幾點。黃人瑞道:“誰怪着你呢,實在說的不錯,倒是沒有人說過的話!可見‘當局者迷,旁觀看清’。”
老殘道:“這也罷了,只是你趕緊說你那稀奇古怪的案情罷。既是明天一黑早要覆命的,怎麼還這麼慢騰斯禮的呢?”人瑞道:“不用忙,且等我先講個道理你聽,慢慢的再說那個案子。我且問你,河裏的冰明天能開不能開?”答道:“不能開。”問:“冰不能開,冰上你敢走嗎?明日能動身嗎?”答:“不能動身。”問:“既不能動身,明天早起有甚麼要事沒有?”答:“沒有。”
黃人瑞道:“卻又來!既然如此,你慌着回屋子去幹甚麼?當此沉悶寂寥的時候,有個朋友談談,也就算苦中之樂了。況且他們姐兒兩個,雖比不上牡丹、芍藥,難道還及不上牽牛花、淡竹葉花嗎?剪燭斟茶,也就很有趣的。我對你說:在省城裏,你忙我也忙,息想暢談,總沒有個空兒。難得今天相遇,正好暢談一回。我常說:人生在世,最苦的是沒地方說話。你看,一天說到晚的話,怎麼說沒地方說話呢?大凡人肚子裏,發話有兩個所在:一個是從丹田底下出來的,那是自己的話;一個是從喉嚨底下出來的,那是應酬的話。省城裏那麼些人,不是比我強的,就是不如我的。比我強的,他瞧不起我,所以不能同他說話;那不如我的,又要妒忌我,又不能同他說話。難道沒有同我差不多的人嗎?境遇雖然差不多,心地卻就大不同了,他自以爲比我強,就瞧不起我;自以爲不如我,就妒我:所以直沒有說話的地方。像你老哥總算是圈子外的人,今日難得相逢,我又素昔佩服你的,我想你應該憐惜我,同我談談;你偏急着要走,怎麼教人不難受呢?”
老殘道:“好,好,好!我就陪你談談。我對你說罷:我回屋子也是坐着,何必矯強呢?因爲你已叫了兩個姑娘,正好同他們說說情義話,或者打兩個皮科兒,嘻笑嘻笑。我在這裏不便:其實我也不是道學先生想喫冷豬肉的人,作甚麼僞呢!”人瑞道:“我也正爲他們的事情,要同你商議呢。”站起來,把翠環的袖子抹上去,露出臂膊來,指給老殘看,說:“你瞧,這些傷痕教人可慘不可慘呢!”老殘看時,有一條一條青的,有一點一點紫的。人瑞又道:“這是膀子上如此,我想身上更可憐了。翠環,你就把身上解開來看看。”
翠環這時兩眼已擱滿了汪汪的淚,只是忍住不叫他落下來,被他手這麼一拉,卻滴滴的連滴了許多淚。翠環道:“看什麼,怪臊的!”人瑞道:“你瞧!這孩子傻不傻?看看怕甚麼呢?難道做了這項營生,你還害臊嗎?”翠環道:“怎不害臊!”翠花這時眼眶子裏也擱着淚,說道:“您別叫他脫了。”回頭朝窗外一看,低低向人瑞耳中不知說了兩句什麼話,人瑞點點頭,就不作聲了。
老殘此刻鼓在炕上,心裏想着:“這都是人家好兒女,父母養他的時候,不知費了幾多的精神,歷了無窮的辛苦,淘氣碰破了塊皮,還要撫摩的;不但撫摩,心裏還要許多不受用。倘被別家孩子打了兩下,恨得甚麼似的。那種痛愛憐借,自不待言。誰知撫養成人,或因年成飢謹,或因其父喫鴉片煙,或好賭錢,或被打官司拖累,逼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就糊里糊塗將女兒賣到這門戶人家,被鴇兒殘酷,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境界。”因此觸動自己的生平所見所聞,各處鴇兒的刻毒,真如一個師父傳授,總是一樣的手段,又是憤怒,又是傷心,不覺眼睛角里,也自有點潮絲絲的起來了。
此時大家默無一言,靜悄悄的。只見外邊有人掮了一卷行李,由黃人瑞家人帶着,送到裏間房裏去了。那家人出來向黃人瑞道:“請老爺要過鐵老爺的房門鑰匙來,好送翠環行李進去。”老殘道:“自然也掮到你們老爺屋裏去。”人瑞道:“得了,得了!別喫冷豬肉了。把鑰匙給我罷。”老殘道:“那可不行!我從來不幹這個的。”人瑞道:“我早分付過了,錢已經都給了。你這是何若呢?”老殘道:“錢給了不要緊,該多少我明兒還你就截了。既已付過了錢,他老鴇子也沒有甚麼說的,也不會難爲了他,怕什麼呢?”翠花道:“你當真的教他回去,跑不了一頓飽打,總說他是得罪了客。”老殘道:“我還有法子:今兒送他回去,告訴他,明兒仍舊叫他,這也就沒事了。況且他是黃老爺叫的人,幹我甚麼事呢?我情願出錢,豈不省事呢?”黃人瑞道:“我原是爲你叫的,我昨兒已經留了翠花,難道今兒好叫翠花回去嗎?不過大家解解悶兒,我也不是一定要你如此云云。昨晚翠花在我屋裏講了一夜,坐到天明,不過我們藉此解個悶,也讓他少挨兩頓打,那兒不是積功德呢。我先是因爲他們的規矩,不留下是不準動筷子的,倘若不黑就來,坐到半夜裏餓着肚子,碰巧還省不了一頓打。因爲老鴇兒總是說:客人既留你到這時候,自然是喜歡你的,爲甚麼還會叫你回來?一定是應酬不好,碰的不巧,就是一頓。所以我才叫他們告訴說:都已留下了,你不看見他那夥計叫翠環喫菜麼?那就是個暗號。”
說到此處,翠花向翠環道:“你自己央告央告鐵爺,可憐可憐你罷。”老殘道:“我也不爲別的,錢是照數給。讓他回去,他也安靜二我也安靜些。”翠花鼻子裏哼了一聲,說:“你安靜是實,他可安靜不了的!”翠環歪過身子,把臉兒向着老殘道:“鐵爺,我看你老的樣子,怪慈悲的,怎麼就不肯慈悲我們孩子一點嗎?你老屋裏的炕,一丈二尺長呢,你老鋪蓋不過佔三尺寬,還多着九尺地呢,就捨不得賞給我們孩子避一宿難嗎?倘若賞臉,要我孩子伺候呢,裝煙倒茶,也還會做;倘若惡嫌的很呢,求你老包涵些,賞個炕畸角混一夜,這就恩典得大了!”
老殘伸手在衣服袋裏將鑰匙取出,遞與翠花,說:“聽你們怎麼攪去罷,只是我的行李可動不得的。”翠花站起來,遞與那家人,說:“勞你駕,看他夥計送進去,就出來,請你把門就鎖上。勞駕,勞駕!”那家人接着鑰匙去了。
老殘用手撫摩着翠環的臉,說道:“你是那裏人,你鴇兒姓甚麼?你是幾歲賣給他的?”翠環道:“俺這媽姓張。”說了一句就不說了,袖子內取出一塊手中來擦眼淚,擦了又擦,只是不作聲。老殘道:“你別哭呀。我問你老底子家裏事,也是替你解悶的,你不願意說,就不說也行,何苦難受呢?”翠環道:“我原底子沒有家!”
翠花道:“你老別生氣,這孩子就是這脾氣不好,所以常捱打。其實,也怪不得他難受。二年前,他家還是個大財主呢,去年才賣到俺媽這兒來。他爲自小兒沒受過這個折蹬,所以就種種的不過好,其實,俺媽在這裏頭,算是頂善和的哩。他到了明年,恐怕要過今年這個日子也沒有了!”說到這裏,那翠環竟掩面嗚咽起來。翠花喊道:“嘿!這孩子可是不想活了!你瞧,老爺們叫你來爲開心的,你可哭開自己咧!那不得罪人嗎?快別哭咧!”
老殘道:“不必,不必!讓他哭哭很好。你想,他憋了一肚子的悶氣,到那裏去哭?難得遇見我們兩個沒有脾氣的人,讓他哭個夠,也算痛快一回。”用手拍着翠環道:“你就放聲哭也不要緊,我知道黃老爺是沒忌諱的人。只管哭,不要緊的。”黃人瑞在旁大聲嚷道:“小翠環,好孩子,你哭罷!勞你駕,把你黃老爺肚裏憋的一肚子悶氣,也替我哭出來罷!”
大家聽了這話,都不禁發了一笑,連翠環遮着臉也“撲嗤”的笑了一聲。原來翠環本來知道在客人面前萬不能哭的,只因老殘問到他老家的事,又被翠花說出他二年前還是個大財主,所以觸起他的傷心,故眼淚不由的直穿出來,要強忍也忍不住。及至聽到老殘說他受了一肚子悶氣,到那裏去哭,讓他哭個夠,也算痛快一回,心裏想道:“自從落難以來,從沒有人這樣體貼過他,可見世界上男子並不是個個人都是拿女兒家當糞土一般作踐的。只不知道像這樣的人世界上多不多,我今生還能遇見幾個?想既能遇見一個,恐怕一定總還有呢。”心裏只顧這麼盤算,倒把剛纔的傷心盤算的忘記了,反側着耳朵聽他們再說什麼。忽然被黃人瑞喊着,要託他替哭,怎樣不好笑呢?所以含着兩包眼淚,“撲嗤”的笑了一聲,並擡起頭來看了人瑞一眼,那知被他們看了這個形景,越發笑個不止。翠環此刻心裏一點主意沒有,看看他們傻笑,只好糊里糊塗,陪着他們嘻嘻的傻了一回。
老殘便道:“哭也哭過了,笑也笑過了,我還要問你:怎麼二年前他還是個大財主?翠花,你說給我聽聽。”翠花道:“他是俺這齊東縣的人。他家姓田,在這齊東縣南門外有二頃多地;在城裏,還有個雜貨鋪子。他爹媽只養活了他,還有他個小兄弟,今年才五六歲呢。他還有個老奶奶,俺們這大清河邊上的地,多半是棉花地,一畝地總要值一百多吊錢呢,他有二頃多地,不就是兩萬多吊錢嗎?連上鋪子,就夠三萬多了。俗說‘萬貫家財’,一萬貫家對就算財主,他有三萬貫錢,不算個大財主嗎?”
老殘道:“怎麼樣就會窮呢?”翠花道:“那才快呢!不消三天,就家破人亡了!這就是前年的事情。俺這黃河不是三年兩頭的倒口子嗎?莊撫臺爲這個事焦的了不得似的。聽說有個甚麼大人,是南方有名的才子,他就拿了一本甚麼書給撫臺看,說這個河的毛病是太窄了,非放寬了不能安靜,必得廢了民埝,退守大堤。這話一出來,那些候補大人個個說好。撫臺就說:‘這些堤裏百姓怎樣好呢?須得給錢叫他們搬開纔好。’誰知道這些總辦候補道王八旦大人們說:‘可不能叫百姓知道。你想,這堤埝中間五六裏寬,六百里長,總有十幾萬家,一被他們知道了,這幾十萬人守住民埝,那還廢的掉嗎?’莊撫臺沒法,點點頭,嘆了口氣,聽說還落了幾點眼淚呢。
“這年春天就趕緊修了大堤,在濟陽縣南岸,又打了一道隔堤。這兩樣東西就是殺這幾十萬人的一把大刀!可憐俺們這小百姓那裏知道呢!看看到了六月初幾裏,只聽人說:‘大汛到咧!大汛到咧!’那埝上的隊伍不斷的兩頭跑。那河裏的水一天長一尺多,一天長一尺多,不到十天工夫,那水就比埝頂低不很遠了,比着那埝裏的平地,怕不有一兩丈高!到了十三四里,只見那埝上的報馬,來來往往,一會一匹,一會一匹。到了第二天晌午時候,各營盤裏,掌號齊人,把隊伍都開到大堤上去。
“那時就有急玲人說:‘不好!恐怕要出亂子!俺們趕緊回去預備搬家罷!’誰知道那一夜裏,三更時候,又趕上大風大雨,只聽得稀里花拉,那黃河水就像山一樣的倒下去了。那些村莊上的人,大半都還睡在屋裏,呼的一聲,水就進去,驚醒過來,連忙是跑,水已經過了屋檐。天又黑,風又大,雨又急,水又猛,你老想,這時候有什麼法子呢?”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