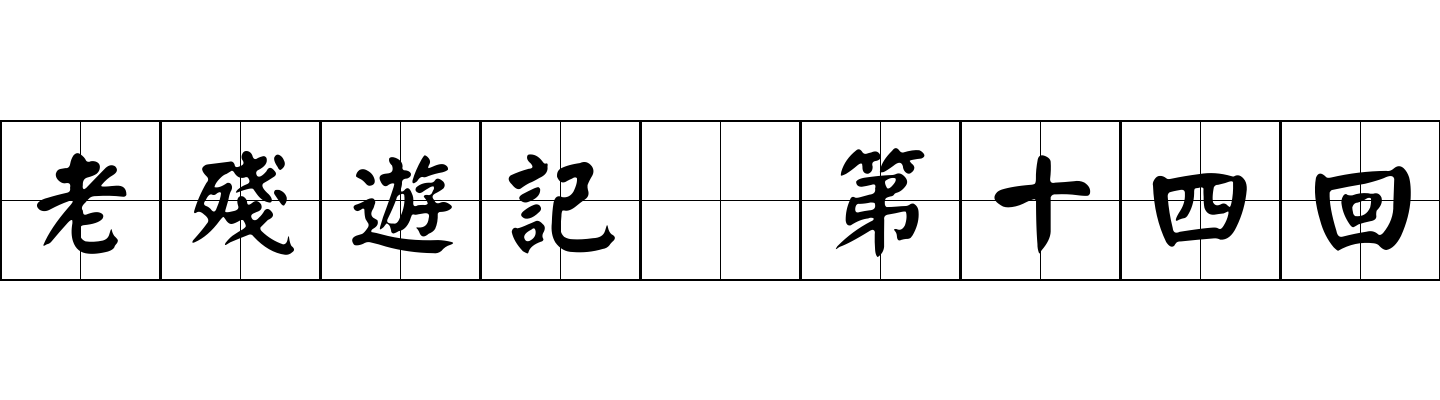老殘遊記-第十四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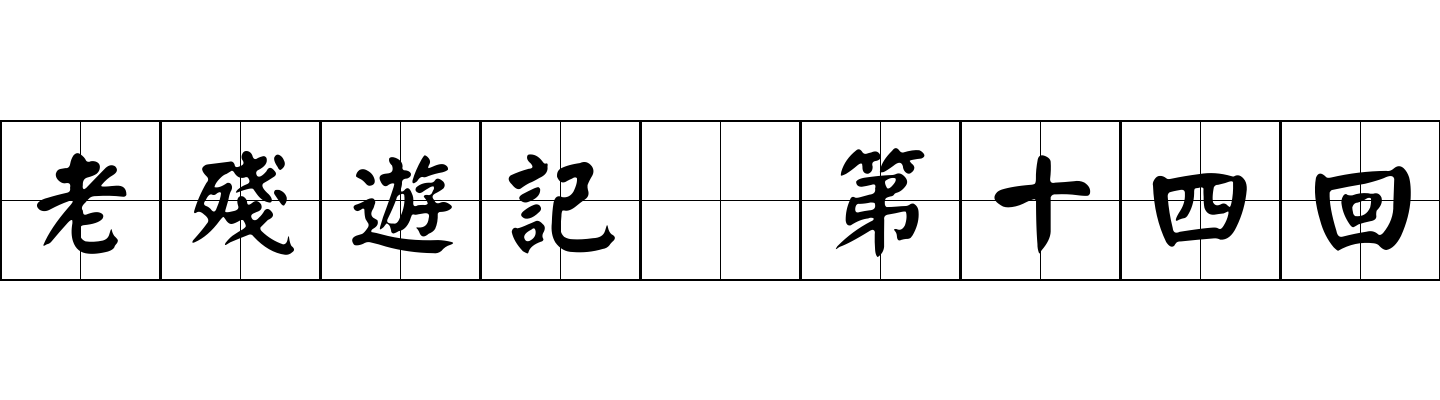
《老殘遊記》,清末中篇小說,是劉鶚 (1857年10月18日—1909年8月23日)的代表作,小說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殘的遊歷爲主線,對社會矛盾開掘很深,尤其是他在書中敢於直斥清官(清官中的酷吏)誤國,清官害民,獨具慧眼地指出清官的昏庸常常比貪官更甚。同時,小說在民族傳統文化精華提煉、生活哲學及藝術、女性審美和平等、人物心理及音樂景物描寫等多方面皆達到了極其高超的境界。
大縣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蟻分送饅頭
話說翠花接着說道:“到了四更多天,風也息了,雨也止了,雲也散了,透出一個月亮,湛明湛明。那村莊裏頭的情形是看不見的了,只有靠民埝近的,還有那抱着門板或桌椅板凳的,飄到民埝跟前,都就上了民埝。還有那民埝上住的人,拿竹竿子趕着撈人,也撈起來的不少,這些人得了性命,喘過一口氣來,想一想,一家人都沒有了,就剩了自己,沒有一個不是號啕痛哭。喊爹叫媽的,哭丈夫的,疼兒子的,一條哭聲,五百多里路長,你老看慘不慘呢!”
翠環接着道:“六月十五這一天,俺娘兒們正在南門鋪子裏,半夜裏聽見人嚷說:‘水下來了!’大家聽說,都連忙起來。這一天本來很熱,人多半是穿着褂褲,在院子裏睡的。雨來的時候,才進屋子去;剛睡了一濛濛覺,就聽外邊嚷起來了,連忙跑到街上看,城也開了,人都望城外跑。城圈子外頭,本有個小埝,每年倒口子用的,埝有五尺多高,這些人都出去守小埝。那時雨才住,天還陰着。
“一霎時,只見城外人,拼命價望城裏跑;又見縣官也不坐轎子,跑進城裏來,上了城牆。只聽一片聲嚷說:‘城外人家,不許搬東西!叫人趕緊進城,就要關城,不能等了!’俺們也都扒到城牆上去看,這裏許多人用蒲包裝泥,預備堵城門。縣大老爺在城上喊:‘人都進了城了,趕緊關城,’城廂裏頭本有預備的上包,關上城,就用土包把門後頭疊上了。
“俺有個齊二叔住在城外,也上了城牆,這時候,雲彩已經回了山,月亮很亮的。俺媽看見齊二叔,問他:‘今年怎正利害?’齊二叔說:‘可不是呢!往年倒口子,水下來,初起不過尺把高;正水頭到了,也不過二尺多高,沒有過三尺的;總不到頓把飯的工夫,水頭就過去,總不過二尺來往水,今年這水,真霸道!一來就一尺多,一霎就過了二尺!縣大老爺看勢頭不好,恐怕小埝守不住,叫人趕緊進城罷。那時水已將近有四尺的光景了。大哥這兩天沒見,敢是在莊子上麼?可擔心的很呢!’俺媽就哭了,說:‘可不是呢!’
“當時只聽城上一片嘈嚷,說:‘小埝浸咧!小埝漫咧!’城上的人呼呼價往下跑。俺媽哭着就地一坐,說:‘俺就死在這兒不回去了!’俺沒法,只好陪着在旁邊哭。只聽人說:‘城門縫裏過水!’那無數人就亂跑,也不管是人家,是店,是鋪子,抓着被褥就是被褥,抓着衣服就是衣服,全拿去塞城門縫子。一會兒把咱街上估衣鋪的衣服,布店裏的布,都拿去塞了城門縫子。漸漸聽說:‘不過水了!’又聽嚷說:‘土包單弱,恐怕擋不住!’這就看着多少人到俺店裏去搬糧食口袋,望城門洞裏去填。一會看着搬空了;又有那紙店裏的紙,棉花店裏的棉花,又是搬個乾淨。
“那時天也明瞭,俺媽也哭昏了。俺也設法,只好坐地守着。耳朵裏不住的聽人說:‘這水可真了不得!城外屋子已經過了屋檐!這水頭怕不快有一丈多深嗎!從來沒聽說有過這麼大的水!’後未還是店裏幾個夥計,上來把俺媽同俺架了回去。回到店裏,那可不像樣子了!聽見夥計說:‘店裏整布袋的糧食都填滿了城門洞,囤子裏的散糧被亂人搶了一個精光。只有潑灑在地下的,掃了掃,還有兩三擔糧食。’店裏原有兩個老媽子,他們家也在鄉下,聽說這麼大的水,想必老老小小也都是沒有命了,直哭的想死不想活。
“一直鬧到太陽大歪西,夥計們才把俺媽灌醒了。大家喝了兩口小米稀飯。俺媽醒了,睜開眼看看,說:‘老奶奶呢?’他們說:‘在屋裏睡覺呢,不敢驚動他老人家。’俺媽說:‘也得請他老人家起來喫點麼呀!’待得走到屋裏,誰知道他老人家不是睡覺,是嚇死了。摸了摸鼻子裏,已經沒有氣。俺媽看見,‘哇’的一聲,喫的兩口稀飯,跟着一口血塊子一齊嘔出來,又昏過去了。虧得個老王媽在老奶奶身上儘自摩挲,忽然嚷道:‘不要緊!心口裏滾熱的呢。’忙着嘴對嘴的吹氣,又喊快拿薑湯來。到了下午時候,奶奶也過來了,俺媽也過來了,這算是一家平安了。
“有兩個夥計,在前院說話:‘聽說城下的水有一丈四五了,這個多年的老城,恐怕守不住;倘若是進了城,怕一個活的也沒有!’又一個夥計道:‘縣大老爺還在城裏,料想是不要緊的。’”
老殘對人瑞道:“我也聽說,究竟是誰出的這個主意,拿的是什麼書,你老哥知道麼?”人瑞道:“我是庚寅年來的,這是已丑年的事,我也是聽人說,未知確否。據說是史鈞甫史觀察創的議,拿的就是賈讓的《洽河策》。他說當年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堤,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堤,去河二十五里。
“那天,司道都在院上,他將這幾句指與大家看,說:‘可見戰國時兩堤相距是五十里地了,所以沒有河患。今日兩民埝相距不過三四里,即兩大堤相距尚不足二十里,比之古人,未能及半,若不廢民埝,河患斷無已時。’宮保說:‘這個道理,我也明白。只是這夾堤裏面盡是村莊,均屬膏腴之地,豈不要破壞幾萬家的生產嗎?’
“他又指《治河策》給宮保看,說:‘請看這一段說:“難看將曰:若此敗壞城郭田廬家墓以萬數,百姓怨恨。”賈讓說:“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閥,折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尚且爲之,況此乃人工所造,何足言也?”’且又說:‘“小不忍則亂大謀”,宮保以爲夾堤裏的百姓。廬墓生產可惜,難道年年決口就不傷人命嗎,此一勞永逸之事。所以賈讓說:“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恙,故謂之上策。”漢朝方制,不過萬里,尚不當與水爭地;我國家方制數萬裏,若反與水爭地,豈不令前賢笑後生嗎?’又指儲同人批評雲:‘“三策遂成不刊之典,然自漢以來,治河者率下策也。悲夫!漢、晉、唐、宋、元、明以來,讀書人無不知賈讓《治河策》等於聖經賢傳,惜治河者無讀書人,所以大功不立也。”宮保若能行此上策,豈不是賈讓二千年後得一知己?功垂竹帛,萬世不朽!’宮保皺着眉頭道:‘但是一件要緊的事,只是我捨不得這十幾萬百姓現在的身家。’兩司道:‘如果可以一勞永逸,何不另酬一筆款項,把百姓遷徒出去呢?’宮保說:‘只有這個辦法,尚屬較妥。’後來聽說籌了三十萬銀子,預備遷民,至於爲甚麼不遷,我卻不知道了。”
人瑞對着翠環說道:“後來怎麼樣呢?你說呀。”翠環道:“後來我媽拿定主意,聽他去,水來,俺就淹死去!”翠花道:“那下一年我也在齊東縣,俺住在北門。俺三姨家北們離民埝相近,北門外大街鋪子又整齊,所以街後兩個小埝都不小,聽說是一丈三的頂。那邊地勢又高,所以北門沒有漫過來。十六那天,俺到城牆上,看見那河裏漂的東西,不知有多少呢,也有箱子,也有桌椅板凳,也有窗戶門扇。那死人,更不待說,漂的滿河都是,不遠一個,不遠一個,也沒人顧得去撈。有有錢的,打算搬家,就是僱不出船來。”
老殘道:“船呢?上那裏去了?”翠花道:“都被官裏拿了差,送饅頭去了。”老殘道:“送饅頭給誰喫?要這些船於啥?”翠花道:“饅頭功德可就大了!那莊子上的人,被水衝的有一大半,還有一少半呢,都是急玲點的人,一見水來,就上了屋頂,所以每一個莊子裏屋頂上總有百把幾十人,四面都是水,到那兒摸喫的去呢?有餓急了,重行跳到水裏自盡的。虧得有撫臺派的委員,駕着船各處去送饅頭,大人三個,小孩兩個。第二天又有委員駕着空船,把他們送到北岸。這不是好極的事嗎?誰知這些渾蛋還有許多蹲在屋頂上不肯下來呢!問他爲啥,他說在河裏有撫臺給他送饃饃,到了北岸就沒人管他喫,那就餓死了。其實撫臺送了幾天就不送了,他們還是餓死。您說這些人渾不渾呢?”
老殘向人瑞道:“這事真正荒唐!是史觀察不是,雖來可知,然創此議主人,卻也不是壞心,並無一毫爲已私見在內。只因但會讀書,不諳世故。舉手動足便錯。孟子所以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豈但河工爲然?天下大事,壞於奸臣者十之三四;壞於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又問翠環道:“後來你爹找着了沒有?還是就被水衝去了呢?”翠環收淚道:“那還不是跟水去了嗎!要是活着,能不回家來嗎?”大家吧嘆息了一會。
老殘又問翠花道:“你才說他,到了明年,只怕要過今年這個日子也沒有了,這話是個甚麼緣故?”翠花道:“俺這個爹不是死了嗎?喪事裏多花了一百幾十吊錢;前日俺媽賭錢,擲骰子又輸了二三百吊錢。共總虧空四百多吊,今年的年,是萬過不去的了。所以前兒打算把環妹賣給蒯二禿子家,這蒯二禿子出名的利害,一天沒有客。就要拿火筷子烙人。俺媽要他三百銀子,他給了六百吊錢,所以沒有說妥,你老想,現在到年,還能有多少天?這日子眼看着越過越緊,倘若到了年下,怕他不賣嗎?這一賣,翠環可就夠他難受了。”
老殘聽了,默無一言;翠環卻只揩淚。黃人瑞道:“殘哥,我才說,爲他們的事情要同你商議,正是這個緣故。我想,眼看着一個老實孩子送到鬼門關裏頭去,實在可憐。算起不過三百銀子的事情,我願意出一半,那一半找幾個朋友湊湊,你老哥也隨便出幾兩,不拘多少。但是這個名我卻不能擔,倘若你老哥能把他要回去,這事就容易辦了。你看好不好?”老殘道:“這事不難。銀子呢,既你老哥肯出一半,那一半就是我兄弟出了罷。再要跟人家化緣,就不妥當了,只是我斷不能要他,還得再想法子。”
翠環聽到這裏,慌忙跳下炕來,替黃、鐵二公磕了兩個頭,說道:“兩位老爺菩薩,救命恩人,捨得花銀子把我救出火坑,不管做甚麼,丫頭、老媽子,我都情願。只是有一件事,我得稟明在前:我所以常捱打,也不怪俺這媽,實在是俺自己的過犯。俺媽當初,因爲實在餓不過了,‘所以把我賣給俺這媽,得了二十四吊錢,謝犒中人等項,去了三四吊,只落了二十吊錢。接着去年春上,俺奶奶死了,這錢可就光了,俺媽領着俺個小兄弟討飯喫,不上半年,連餓帶苦,也就死了。只剩了俺一個小兄弟,今年六歲。虧了俺有個舊街坊李五爺,現在也住在這齊河縣,做個小生意,他把他領了去,隨便給點喫喫。只是他自顧還不足的人,那裏能管他飽呢?穿衣服是更不必說了。所以我在二十里鋪的時候,遇着好客,給個一吊八百的呢,我就一兩個月攢個三千兩吊的給他寄來。現在蒙兩位老爺救我出來,如在左近二三百里的地方呢,那就不說了,我總能省幾個錢給他寄來;倘要遠去呢,請兩位恩爺總要想法,許我把這個孩子帶着,或寄放在庵裏廟裏,或找個小戶人家養着。俺田家祖上一百世的祖宗,做鬼都感激二位爺的恩典,結草銜環,一定會報答你二位的!可憐俺田家就這一線的根苗!……”說到這裏,便又號啕痛哭起來。
人瑞道:“這又是一點難處。”老殘道:“這也沒有什麼難,我自有個辦法。”遂喊道:“田姑娘,你不用哭了,包管你姊兒兩個一輩子不離開就是了。你別哭,讓我們好替你打主意;你把我們哭昏了,就出不出好主意來了。快快別哭罷!”翠環聽罷,趕緊忍住淚,替他們每人磕了幾個響頭。老殘連忙將他攙起。誰知他磕頭的時候,用力太猛,把額頭上碰了一個大苞,苞又破了,流血呢。
老殘扶他坐下,說:“這是何苦來呢!”又替他把額上血輕輕揩了,讓他在炕上躺下,這就來向人瑞商議說:“我們辦這件事,當分個前後次第:以替他贖身爲第一步,以替他擇配爲第二步。贖身一事又分兩層:以私商爲第一步;公斷爲第二步。此刻別人出他六百吊,我們明天把他領家的叫來,也先出六百吊,隨後再添,此種人不宜過於爽快;你過爽快,他就覺得奇貨可居了。此刻銀價每兩換兩吊七百文,三百兩可換八百一十吊,連一切開銷,一定足用的了。看他領家的來,口氣何如:倘不執拗,自然私了的爲是;如懷疑刁狡呢,就託齊河縣替他當堂公斷一下,仍以私了結局,人翁以爲何如?”人瑞道:“極是,極是!”
老殘又道:“老哥固然萬無出名之理,兄弟也不能出全名,只說是替個親戚辦的就是了。等到事情辦妥,再揭明擇配的宗旨;不然,領家的是不肯放的。”人瑞道:“很好。這個辦法,一點不錯。”老殘道:“銀子是你我各出一半,無論用多少,皆是這個分法。但是我行篋中所有,頗不敷用,要請你老哥墊一墊;到了省城,我就還你。”人瑞道:“那不要緊,贖兩個翠環,我這裏的銀子都用不了呢。只要事情辦妥,老哥還不還都不要緊的。”老殘道:“一定要還的!我在有容堂還存着四百多銀子呢。你不用怕我出不起,怕害的我沒飯喫。你放心罷。”
人瑞道:“就是這麼辦,明天早起,就叫他們去喊他領家的去。”翠花道:“早起你別去喊。明天早起,我們姐兒倆一定要回去的。你老早起一喊。倘若彼他們知道這個意思,他一定把環妹妹藏到鄉下去;再講盤子,那就受他的拿捏了,況且他們抽鴉片煙的人,也起不早;不如下午,你老先着人叫我們姐兒倆來,然後去叫俺媽,那就不怕他了。只是一件:這事千萬別說我說的:環妹妹是超升了的人,不怕他,俺還得在火坑裏過活兩年呢。”人瑞道:“那自然,還要你說嗎!明天我先到縣衙門裏,順便帶個差人來。倘若你媽作怪,我先把翠環交給差人看管,那就有法制他了。”說着,大家都覺得喜歡得很。
老殘便對人瑞道:“他們事已議定,大概如此,只是你先前說的那個案子呢,我到底不放心。你究竟是真話是假話?說了我好放心。”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