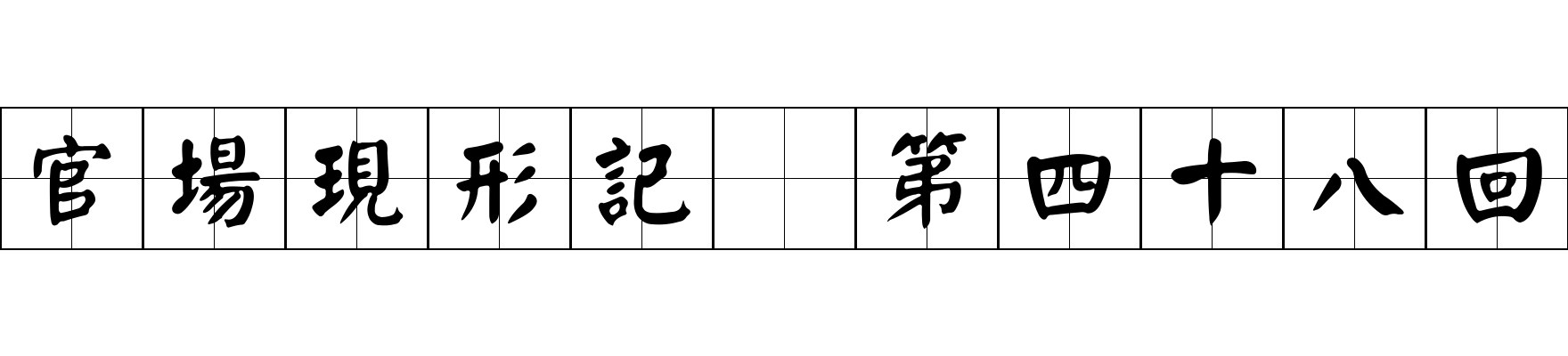官場現形記-第四十八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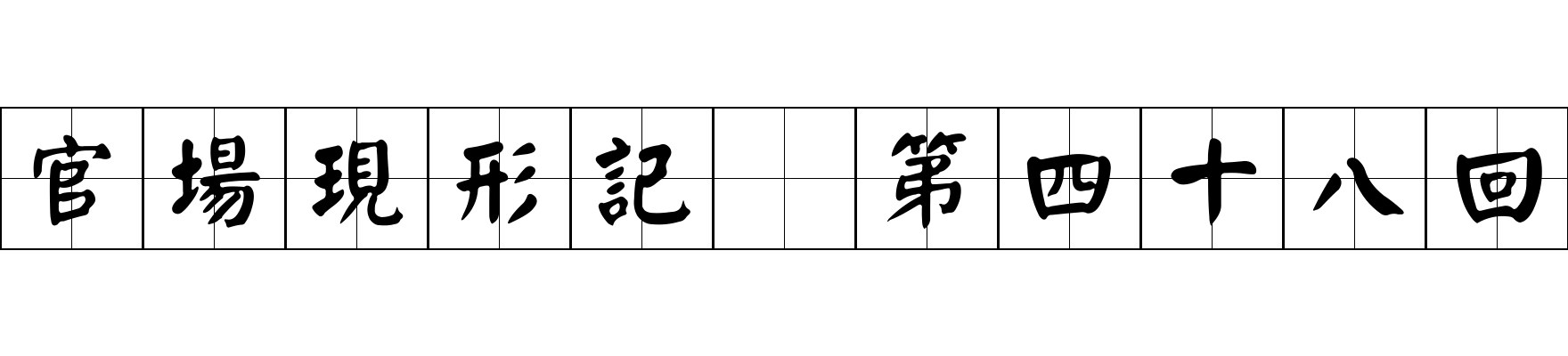
《官場現形記》是晚清文學家李伯元創作的長篇小說。小說最早在陳所發行的《世界繁華報》上連載,共五編60回,是中國近代第一部在報刊上連載並取得社會轟動效應的長篇章回小說。它由30多個相對獨立的官場故事聯綴起來,涉及清政府中上自皇帝、下至佐雜小吏等,開創了近代小說批判現實的風氣。魯迅將《官場現形記》與其他三部小說並稱之爲譴責小說,是清朝晚期文學代表作品之一。
還私債巧邀上憲歡 騙公文忍絕良朋義
卻說欽差童子良在南京養了半個月,病亦好了,公事亦查完了總共湊到將近一百萬銀子光景。因見這邊實在無可再籌,只得起身溯江上駛。未曾動身之先,就有安徽派來道員一員、知縣兩員,前來迎迓。及至動身的幾天頭裏,江寧,上元兩縣曉得欽差不坐輪船的,特地封了十幾號大江船,又由長江水師提督派了十幾號炮船沿江護衛。
在路早行夜泊,非止一日。有天到得蕪湖,欽差因爲沒甚公事,未曾登岸。及至將到安慶省城,文武大小官員一起出境迎接,照例周旋,無庸多述。因安徽省現在這位中丞亦有被參交查事件,所以欽差於盤查倉庫,提拔款項之後,只得暫時住下,查辦參案。
原來此時做安徽巡撫的,姓蔣,號愚齋,本貫四川人氏。先做過一任山東巡撫,上年春天才調過來的。由山東調安徽,乃是以繁調簡,蔣中丞心上本來不甚高興。實因其時皖北鳳、毫一帶土匪蠢動,朝廷因爲這蔣中丞是軍功出身,前年山東曹州一帶亦是土匪作亂,經蔣中丞派了兵去治服的,所以朝廷特地調他過來,以便剿辦皖北土匪,無非爲地擇人之意。蔣中丞接印之後,就派了一位營務處上的道臺,姓黃,名保信;一員副將,姓胡、名鸞仁,帶了五營人馬,前去剿辦。稟辭的時候,蔣中丞原面諭他們相機行事,及至到得那裏,他兩個辦不下來,就上了一個稟帖,說土匪如何猖狂,如何利害,請加派幾營兵,以資策應。
以繁調簡:清代的府、州、知的缺(職位)有繁有簡,分爲最要、要、中、簡四等,官員收入有差別,各省之間也有這種區分。山東爲“繁缺”,安徽爲“簡缺”。
蔣中函得稟後,就加派了一員記名總兵,姓蓋,名道運,統率了新練的什麼常備軍、續備軍,又是三四營,前去救應。此番蔣中丞因該匪等膽敢抗拒官軍,異常兇悍,實屬目無法紀,又加了一個札子給他三個,叫他們如遇土匪,迎頭痛剿。畢竟土匪是烏合之衆,那裏禁起這大隊人馬,不下二個月,土匪也平了,那一帶的村莊也沒有了。問是怎樣沒有的,說是早被他三位架起大炮,轟的沒有了。於是“得勝回朝”。蔣中丞自有一番保奏:胡副將升總兵,蓋總兵升提督,黃道臺亦得了什麼“巴圖魯”勇號。正在高興頭上,不提防被御史參上幾本,說他們並不分別良莠,一律剿殺,又說蔣中丞濫保匪上,玩視民命,所以派了童子良查辦的。
蔣中丞未曾調任之前,安徽有一個候補知府,姓刁,名邁彭,歷任三大憲都歡喜他,凡是省裏的紅差使、闊差使,不是總辦,便是提調,都有他一分。然而除掉上司之外,卻沒有一個說他好的。蔣中丞亦早已聞得他的大名。等到接印下來,同司、道談起本省公事,便道:“怎麼我們安徽一省候補道、府如此之多,連個能夠辦事的都沒有?”兩司聽了愕然,各候補道更爲失色。蔣中丞歇了一會,又說道:“但凡有個會辦事的,何至於無論什麼差使都少不了刁某人一個呢?就是他能辦事,他一個人到底有多少本事,有多大能耐?一天到晚,忙了東又忙西,就是有兼人之材,恐怕亦辦不了!”各位司、道方纔曉得中丞是專指刁某人而言,一齊把心放下。但是大衆聽撫憲如此口氣,知道不妙,就是想要替他說兩句好話也不敢說了。有些窮候補道,永遠不得差使的,心中反爲稱快。
等到下來,早有耳報神把這話傳給了刁邁彭了。刁邁彭自從到省十幾年,一直是走慣上風的,從沒有受過這種癟子。初聽這話,還是一鼓作氣的,說道:“明天就上院辭差使,決計不幹了!”親友們大家都勸他忍耐。又有人說:“中丞大約是初到這裏,誤聽人言,再過幾天,同你相處久了,曉得你的本領,自然也要傾倒的。”在外親友勸,在家太太勸,過了兩天,刁邁彭的氣也平了,也不想辭差使了,仍舊謹謹慎慎上他的局子,辦他的公事。卻不料藩臺因撫臺說他閒話,也不敢過於相信他,三四天後,忽然拿他所兼的差使委了別人兩個,大約還是些掛名不辦事的,正經差使卻沒有動。刁邁彭一見苗頭果然不對,此時一心害怕,惟恐還有甚麼下文,翻過來求藩臺,求臬臺,替他在撫憲面前說好話,保全他的差使還來不及,亦不說辭差使不幹的話了。
畢竟蔣中丞人尚忠厚,因見兩司代爲求情,亦就答應暫時留差,以觀後效。兩司下來,傳諭給刁邁彭,叫他巴結聽差。刁邁彭不但感激涕零,異常出力,並且日夜鑽謀籠絡撫憲的法子,總要叫他以後開不得口才好。心想:“凡是面子上的巴結,人人都做得到的,不必去做。總要曉得撫臺內裏的情形,或者有什麼隱事,人家不能知道的,我獨知道;或者他要辦一件事,未曾出口,我先辦到,那時候方能顯得我的本領。但是他做巡撫,我做屬員,平日內裏又無往來,如何能夠曉得他的隱事?”這天,整整躊躇了半夜。回到上房,正待睡覺,忽然有個老媽,因爲太太平時很喜歡他,他不免常在主人眼前說同伴壞話。些時忽被同伴說他做賊,並且拿到賊贓,一時賴不過去,太太只得吩咐局裏聽差的勇役,一面看守好了這個老媽,一面去追趕薦頭,說是等到薦頭到來,一齊送到首縣裏去辦。這事從喫晚飯鬧起,一直等到二更多天,薦頭纔來。太太正在上房發威,薦頭同老媽直挺挺跪在地下。這個檔口,齊巧刁邁彭踱了進去問其所以,太太又罵薦頭好大的架子,叫了這半天才來。薦頭分辨說道:“實爲着撫臺大人的三姨太太昨日添了一位小少爺,叫我僱奶媽,早晨送去一個,說是不好,剛纔晚上又送去一個,進去之後,又等了好半天,所以誤了太太這裏的差事,只求太太開恩!”
太太聽了這話,心上生氣,說他拿撫臺壓我。正待發作,誰知刁邁彭早聽的明明白白,忽然意有所觸,又見老媽年紀尚輕,甚是潔淨。刁邁彭便心生一計,連向太太搖手,叫他不要追問。太太摸不着頭腦。刁邁彭急走上前,附耳說了兩句,太太明白,果然就不響了。刁邁彭忙叫薦頭起來,向他說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們做薦頭的人也管不了這許多,薦來的人做賊,是怪不得你的。不過是你的來手,卻不能不同你言語一聲。剛纔太太因爲你來得晚了生氣,如今把話說明,就沒有你的事了。”
薦頭正爲太太說就要拿他當窩家辦,嚇得心上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如今見刁大人這番說話,不但轉愁爲喜,立刻爬在地下替大人、太太磕了幾個響頭。迴轉身來,就把那偷東西的老媽打了兩下巴掌,又着實拿他埋怨了幾句。刁邁彭又道:“這個人我本是要送他到縣裏重辦的,只爲到得縣裏,一定要追及薦頭人,於你亦有不便。我如今索性拿他交代與你帶去,只要把偷的東西拿回來,看你面上,饒他這一遭,等他以後別處好喫飯。”那老媽聽了,自然也是感激的了不得,亦磕了幾個頭,跟了薦頭,千恩萬謝而去。
第二天刁太太這裏仍舊由原薦頭薦了個人來。刁邁彭有意籠絡這薦頭,便同他問長問短,故意找些話出來搭訕着同他講。後來薦頭來得多了,刁邁彭同他熟慣了,甚至無話不談。有天刁邁彭問他:“撫臺衙門裏,你可常去?”薦頭道:“現在在院上用的老媽一大半是我薦得去的。”刁邁彭道:“有甚麼伶利點的人沒有?”薦頭道:“可是太太跟前要添人?”刁邁彭道:“不是。現在沒有這樣伶俐人,也不必說;等到有了,你告訴我,我自有用他的去處,並且於你也有好處的。”薦頭道:“可惜一個人,大人公門裏若能再叫他進來了,這個人倒是很聰明的,而且人也乾淨,模樣兒也好,心也細,有什麼事情託他,是再不會錯的。”
刁邁彭忙問:“是誰?”又問:“我這裏爲什麼不能再來?”薦頭道:“就是前個月里人家冤枉他做賊攆掉的那個王媽。大人明鑑;人家說他做賊,是冤枉的;同夥裏和他不對,所以說他做賊,無非想害他的意思。”刁邁彭道:“這個人很不錯,太太本來也很喜歡他。不過同夥當中都同他不對,因此我這裏他站不住腳,所以太太亦只好讓他走了乾淨。至於做賊的一件事,我也曉得冤枉的,所以當時我並不追問。”薦頭道:“大人、太太待他的恩典,他有什麼不知道!”刁邁彭道:“知道就好,可見得就不是個糊塗人。如今又是你的保舉,我現在就用他亦可以。”薦頭道:“他出去之後,我又薦他到南街上高道臺翁館裏去。劉道臺是一直沒有當過什麼差使的,公館裏沒有出息,聽說老媽的工錢都是付不出的。所以王媽雖然去了,並不願意在他家,鬧着要出來。既然大人要他,我回去就帶信給他,仍舊叫他到這裏來伺候大人同太太就是了。”
刁邁彭道:“錢歸我出,而且還可以多給他些好處。但是這個人並不是要他來伺候我,亦不是要他來伺候我們太太。要他去伺候一個人,伺候好了,我還重重有賞,連你都有好處的。”薦頭聽了,還當是刁大人有甚麼外室,瞞住了太太;因是熟慣了,便湊前一步,附耳問道:“可是去伺候姨太太?”刁邁彭連連搖頭道:“不是,不是。你不要亂猜。”薦頭道:“這個我可猜不着了,到底去伺候誰,請大人吩咐了罷。”刁邁彭道:“現在離年不多幾天了,我還要消停兩天,今日不同你說,等你回家猜兩天,猜不着,等我過了年再告訴你。”薦頭無奈,只得回去。
正是光陰似箭,轉眼又是新年了。這天是大年初五,那薦頭急忙忙趕到刁公館裏給大人、太太叩喜。齊巧太太被一位要好的同寅內眷邀去喫年酒去了,只有刁邁彭在家。薦頭便問:“大人去年所說的那年樁事情,可把我悶壞了。今日請大人吩咐了罷。”刁邁彭說道:“你不要着急,我本來今天就要告訴你的,總而言之,這件事你能替我辦成,我老爺的升官,連你的發財,統通都在裏頭。”薦頭聽了,直喜得眉花眼笑,嘴都合不攏來。
刁邁彭正要望下說時,恰巧管家頭戴大帽子,拿了封信進來,說是:“老爺的喜信來了。”刁邁彭聽了,不覺陡然楞了一楞,於是把話頭打住。原來上年刁邁彭曾經託京裏一個朋友謀幹一件事情。這個管家乃是刁邁彭的心腹,曉是此事,所以今天接着了這封京信,以爲必定是那件事的回信來了。及至刁邁彭拆開看過之後,才知不是,於是擱在一邊。
管家退去,刁邁彭方纔說道:“我託你不爲別的,爲的你常常薦人到撫臺衙門裏去,就是上回歇掉的那個王媽,我看這人還伶俐,我想託你拿他薦到撫臺衙門裏去。我這裏有四十兩銀子,二十兩送你喫杯茶,那二十兩你替我給了王媽。你可曉得我託你把他薦了進去,所爲何事?專爲叫他在裏頭做一個小耳朵。凡是撫臺大人有什麼事情,都來告訴我,就是沒有事情或是大人說些什麼閒話,一天到晚做些什麼事情,只要是他知道的,都可以來告訴我。我公館裏他不便來,他可送信給你,由你再傳給我。但是至多三天總得報一次。這件事情辦成,我還要重重的謝你。以後若是王媽他家裏缺什麼錢用,你告訴我,都由我這裏給他。”
那薦頭聽了刁邁彭的一番話,沉吟了一回,回說:“這人現在已不在劉公館了,另外找一個人家,聽說出息很好。等我去挖挖看。大人賞他的銀子,我帶了去。這個請大人收了回去,我們怎好無功受祿呢。”刁邁彭道:“這一點點算不得什麼。你也不必客氣,將來我還要補報你的。”薦頭見刁邁彭執意要他收,他亦樂得享用,於是千恩萬謝,揣了銀子而去。走出宅門,刁邁彭又拿他喊住,問道:“你拿他送進去給那一個?倘若送到不相干人的眼前,那是沒用的。”薦頭道:“現在是二姨太太拿權,我自然拿他送到二姨太太跟前去,大人放心就是了。”刁邁彭見他說話在行,也自放心。
果然那薦頭回去找到王媽,交代他十兩銀子,把刁邁彭的一番盛意說知,並說以後還有周濟他。王媽自然歡喜。本來他此時在劉公館裏出來,正待找主,有了這個機會,隨即一口答應。齊巧院上傳出話來,二姨太太房裏要僱個老媽,又要乾淨,又要能幹。薦頭得信,便把這王媽薦了進去。試了兩天工,居然甚合二姨太太之意。當時薦頭先把進去情形稟報過刁邁彭。過了兩天,王媽傳出話來,無非撫臺大人昨日歡喜,今天生氣的一派話,並沒有甚麼大事情。以後或三天一報,或兩天一報,都是些不要緊的,甚至撫臺大人同姨太太說笑的話也說了出來。刁邁彭聽了,不過付之一笑。只有一次是二姨太太過生日,別人都不曉得,只有他厚厚的送了一分禮。雖然撫憲大人有命譬謝,未曾賞收。然而從此以後,似乎覺得有了他這個人在心上,便不像先前那樣的犯惡他了。以後又有兩件事情被他得了風聲,都搶了先去,不用細述。
單說有天王媽又出來報說,說是撫臺大人這兩天很有些愁眉不展。聽得二姨太太講起,說他老人家前年上京陛見的時候,借了一家錢莊上一萬二千銀子,前後已還過五千,還短七千。現在這個人生意不好,店亦倒了,派了人來逼這七千銀子。這位大人一向是一清如水的。現在這個來討帳的人,就住在院東一爿客棧裏面。大人想要不還他,似乎對不住人家,而且聲名也不好聽,倘若是還他,一時又不湊手,因此甚覺爲難。刁邁彭聽在肚裏,等到王媽去後,便獨自一個踱到街上,尋到院東幾爿客棧,一家家訪問,有無北京下來的人。等到問着了,又問這人名姓;問他到此之後,可是常常到院上去的,並他來往的是些什麼人,都打聽清楚。刁邁彭是在安慶住久的,人頭既熟,便找到這人的熟人,託他請這人喫飯,他卻自己作陪。席面上故意說這位撫臺手裏如何有錢,如叫那人聽了回去,逼的更兇。過了一天,果然王媽又來報,說大人這兩天不知爲着何事,心上不快活,一天到夜罵人,飯亦喫不下去。
刁邁彭聽了歡喜,心想道:“時候到了。”便打了一張七千兩的票子,又另外打了一百兩的票子,帶在身上,去到棧房,找那個討帳的說話。幸喜幾天頭裏在臺面上同那人早已混熟了,彼此來往過多次,那人亦曾把討帳的話告訴過刁邁彭。刁邁彭立刻拍着胸脯,說道:“我們這位老憲臺是有錢的,不應如此嗇刻。你只管天天去討,將來實在討不着,等我進去同他帳房老夫子說,劃還給你就是了。”果然那人次日進去,逼的更緊。撫臺不便親自出來會他,都是官親表侄少爺出來同他支吾。有時或竟在門房裏一坐半天,弄得個撫臺難爲情的了不得,而又奈何他不得。想要同下屬商量,又難於啓齒。正在急的時候,忽然一連三天,不見那人前來。合衙門的人都爲詫異,派個人到他住的棧房裏打聽打聽,說是已經回京去了。棧房裏的人還說:“這人本是專爲取一筆銀子來的,如今人家銀子已經還了他,還住在這裏做什麼呢。”出來打聽的人回去,把這話稟報上去,弄得個撫臺更是滿腹狐疑,想不出其中緣故。
原來刁邁彭自從王媽送信之後,他袖了銀票,一直徑到棧房,找到那人,自己裝做是撫臺帳房裏托出來做說客的,起先止允還一半,那人不肯,然後講到讓去利錢,那人方纔肯了。叫他取出字據,銀契兩交,一刀割斷。然後又把那一張一百兩的票子取出,作爲撫臺送的盤川。那人自是感激。又叫他寫了一張謝帖。那人次日便動身回京而去。刁邁彭把筆據謝帖帶了回家,心上盤算:“銀子已代還了,撫臺的面子亦有了,怎麼想個法子,叫撫臺曉得是我替他還的纔好。”意思想託個人去通知他,恐怕他不認,亦屬徒然,若是自己去當面去同他講,更恐怕把他說臊了,反爲不美。而且這字據又不便公然送還他。躊躇了好兩天,纔想出一個法子。當天足足忙了半夜。
諸事停當,次日飯後上院。這幾天撫臺正爲要帳的人忽然走了,心上甚是疑惑不定。見他獨自一個來稟見,原本不想見他,後來說是有事面回,方纔見的。進去之後,敷衍了幾句,並不提及公事。等到撫臺問他,刁邁彭方纔從從容容的從袖筒管裏取出一個手摺,雙手送給撫臺,口稱;“大人上次命卑府抄的各局所的節略,凡是卑府所當過的差使,這上頭一齊有了。此外卑府沒有當過的,不曉得其中情形,不敢亂寫。”
撫臺聽了,一時記不清楚自己從前到底有過這話沒有,隨手接了過來,往茶几上一擱,道:“等兄弟慢慢的看。”刁邁彭道:“這後頭還有卑府新擬的兩條條陳,要請大人教訓。”撫臺聽說有條陳,不得不打開來,一頁一頁的翻看。大略的看了一遍:前面所敘的,無非是他歷來當的差使,如何興利,如何除弊的一派話。後頭果然又附了兩條條陳,一條用人,一條理財,卻都是老生常談,看不出什麼好處。撫臺正在看得不耐煩,忽地手摺裏面夾着兩張紙頭,上面都寫着有字,一張是八行書信紙寫的,一張是紅紙寫的,急展開一半來一看,原來那張信紙寫的不是別樣,正是他老人家自己欠人家銀子的字據,那一張就是來討銀子的那個人的謝帖。再看欠據上,卻早已寫明“收清”塗銷了。撫臺看了,當時不覺呆了一呆,隨時心上亦就明白過來,連手摺,連字據,連謝帖,捲了一卷,攢在手裏,說了聲:“兄弟都曉得了,過天再談罷。”說完,端茶送客。
且說撫臺蔣中丞送客之後,袖了那捲東西,回到簽押房裏,打開來仔仔細細的看了一回,的確是那張原據七千多銀子,連利錢足足一萬開外。”如此一筆鉅款,他竟替我還掉,可爲難得!但是思想不出,他是怎麼曉得的,真正不解!”接着又看那張謝帖,寫明白“收到一百銀子川資”的話,心想:“他這又何苦呢!正項之外,還要多帖一百銀子。”仔細一想,明白了:“這是他明明替我做臉的意思。這人真有能耐,真想得到,倒看他不出!從前這人我還要撤他的,如今看來,倒是一個真能辦事的人,以後倒要補補他的情纔好。”跟手又把他那個手摺翻出來,自頭至尾,看了一遍。雖然不多幾句話,然而簡潔老當,有條不紊,的確是個老公事。再看那兩條條陳,亦覺得語多中肯。”在候補當中,竟要算個出色人員!”盤算了一會,回到上房。
接着喫晚飯。二姨太太陪着喫飯,正議論到那個要帳的走的奇怪。蔣中丞連忙接口道:“我正要告訴你們,這銀子竟有人替我代還了。”二姨太太聽了詫異,忙問;“是誰還的?”蔣中丞便一五一十的統通告訴了他。又說:“刁某人是個候補知府”,現在當的是什麼差使。此時,齊巧王媽站在二姨太太身旁,伺候添飯,他心上是明白的,忙插嘴道:“這位老爺我伺候過他,他的光景我是知道的,雖然當了這幾年差使,還是窮的當當,手裏一個錢都沒有,那裏來的這一萬銀子呢?不要不是他罷?”蔣中丞道:“的確是他。他當的都是好差使,還怕沒錢,頭兩萬銀子,算來難不倒他。”王媽道:“這位老爺的的確確沒有錢。我伺候過他的太太一年多,還有什麼不曉得的。他的太太亦時常同我們說:‘這些差使給了我們這位老爺,真正冤枉呢!除掉幾兩薪水之外,外快一個不要,這兩年把我的嫁裝都賠完了,再過兩年就支不往了。這些差使若是委在別人身上,少說有五六萬銀子的財好發。’”
蔣中丞聽了疑惑道:“他既然沒得錢,怎麼能夠替我還帳呢?”王媽道:“這位老爺錢雖不要,然而手筆很大,一千、八百的常常幫人,自己沒有錢,外頭拖虧空。所以他身上聽說有毛五萬銀子的虧空,如今這筆錢,想來又是什麼莊上拉來的。有幾個差使在身上罩住,那裏總還拉得動,但怕將來沒了差使,不曉得拿什麼還人家呢。”蔣中丞聽了,心上盤算道:“據他這樣說來,真正是個好人了。”
毛:約計。
從此以後,蔣中丞便拿他另眼看待,又委他做了本衙門的總文案,沒有事情,都可以穿了便服一直到簽押房裏同撫臺談天的。此時刁大人的聲光竟比蔣中丞未到任之前還好。人家看了,都爲奇怪,齊說:“某人做官真有本事,無論什麼撫臺來,一個好一個。”總猜不出是個什麼決竅。
又過了一個月,童欽差要來的話早已宣佈開了,所有當銀錢差使的人,一齊捏着一把汗,刁邁彭更不必說。還算他有才具,只在暗地裏佈置,外面卻絲毫不肯矜張。等到欽差到了安慶住下,叫他們造報銷,他早已派人在南京抄到人家報銷的底子,怎樣欽差就賞識,怎樣欽差就批駁,他都瞭然於心,預備停當。等到這裏欽差才吩咐下來,他第二天就把冊子呈了上去,又快又清楚,合了欽差的心。欽差看了大喜,一連傳見過三次,所說的話,又甚對欽差的脾胃。以後通省各局所的冊子都造好送了上來,欽差看了,有好有歹,然而總不及刁邁彭的好。因此欽差很賞識他,同蔣撫臺說,要上摺子保舉他。撫臺是承過他的情的,豈有不贊成之理。這是後話不題。
且說欽差童子良因奉朝廷命查辦蔣撫臺“誤剿良民,濫保匪人”一案,案情重大,所以到了安慶之後,聲色不動,早派了兩個心腹,前往鳳、毫一帶密查。等到這裏司庫局所盤查停當,先前委去查事的人亦已回來了,徑同御史參的話絲毫不錯。欽差便行文撫臺,叫他把記名提督蓋道運、候補道黃保信、候補總兵胡鸞仁三員,先行摘去頂戴,有缺撤任,有差撤委,一齊先交首府看管,聽候嚴參,歸案審辦。這事一出,大家又嚇毛了。
先前蔣撫臺也聽見風聲不好,便有人送信給他說,爲的就是上年皖北剿匪一案。蔣撫臺說:“我有地方官奏報爲憑,所以才發兵的。至於派出去的人誤剿良民,這個我坐在省城裏,離着一千多里路,我怎麼會曉得呢。這個須問他們帶兵的,其過並不在我。”又有人把話傳給了蓋道運等三個,說:“看上去撫臺不肯幫忙。”蓋道運道:“我們是奉公差遣,他不叫我們去殺人,我們就能夠亂殺人嗎。這件事是他叫我們如此做的。欽差問起來,我有他的札子爲憑,咱不怕!”說完,便把札子取了出來,給大衆瞧了一瞧,仍舊拽在身上,又說一聲“這是咱的真憑據”!黃保信、胡鸞仁兩個聽他如此一說,亦各各把心放下。隨後又有人把蓋道運的話告訴了蔣撫臺。蔣撫臺一聽大驚,便把札子的原稿吊出查看,覺得所說得話雖然過火,尚無大礙,惟獨後頭有一句是叫他們“迎頭痛剿”。看到這裏,不覺把桌子一拍,道:“完了!這是我的指使了!”深悔當初自己沒有站定腳步,如今反被他們拿住了把柄,自己惱悔的了不得,然而又是一籌莫展。曉得刁邁彭見識廣,才情極大;況且這些屬員當中,亦只有同他知已;於是請了他來,密商這件事如何辦法。
這件事刁邁彭是早已知道的了。三人之中,黃保信黃道臺還同他是把兄弟。依理,老把兄遭了事情,現在首府看管,做把弟人就該應進去瞧瞧他,上司跟前能夠盡辦的地方,替他幫點忙纔是。無奈這位刁邁彭一聽撫臺有卸罪於他三人身上的意思,將來他三人的罪名,重則殺頭,輕則出口,斷無輕恕之理,因此就把前頭交情一筆勾消,見了撫臺,絕口不提一字,免得撫臺心上生疑,這正是他做能員的祕訣。
此時,撫臺傳見,正爲商議這件事情。他便迎合憲意,說他三有如何荒唐,“極該拿他三人重辦,一來塞御史之口,二來卸大人的干係。倘若大人再要回護他三人,將來一定兩敗俱傷,於大人反爲無益。”蔣撫臺聽了,雖甚以他話爲然,但是因爲前頭自己實實在在下過一個札子,叫他們迎頭痛剿,如今把柄落在他們手裏,欽差提審起來,他們一定要把這個札子呈上去的,豈不是一應干係都在自己身上,他們罪名反可減輕。因把詳細情節告訴了刁邁彭,問他如何是好。
刁邁彭至此也不免低頭沉吟了一回,問撫臺要了那個札子底稿,揣摹了半天,便道:“法子是有一個,但是光卑府一個人做不來,還得找一個蓋某人的朋友,肯替大帥出力的,做個連手纔好。”蔣撫臺默默無語。後來還是刁邁彭想起武巡捕當中有一個名字叫做範顏清的,這人同蓋道運本是郎舅。後來爲了借錢不遂,早已不大來往的了。“如今找他做個幫手,這事或者成功。”蔣撫臺一聽這話,連忙站起身來,朝着刁邁彭深深一揖,道:“兄弟的身家性命,一齊在老哥身上。千萬費心!一切拜託!”刁邁彭道:“卑府有一分心,盡一分力就是了。”就罷,退下。
刁邁彭也不及回公館,便去找着範顏清,先探他口氣,同他說:“想不以令親出此意外之事!”範顏清道:“我們是至親,不是我背後說,他也過於得意了。”刁邁彭一聽口音很對,便說:“你們是至親,到了這個時候,只應該幫幫他的忙纔是。你是常在老帥身邊的人,總望你替他說句好話纔好。今日連你都如此說他,他還有活命嗎?”範顏清道:“卑職的事情,瞞不過你大人的明鑑。常言道:‘至親莫如郎舅。’他是提鎮,卑職是千、把,說起來只有他提拔卑職的了,誰知倒是一點好處沾不到的。即如去年他平了土匪回來,隨折呢,本來不敢妄想,只求他大案裏頭帶個名字,就算我至親沾他這點光,也在情理之內。那曉得弄到後來竟是一場空,倒是些不三不四的一齊保舉了出來。所以如今卑職也看穿了,決計不去求他。卑職同他親雖親,究竟隔着一層。如今連他們的姑太太也不同他來往了,這可是同他一個娘肚裏爬出來的,尚且如此,更怪不得別人了。”刁邁彭一聽範顏清的話很是有隙可乘,便把他拉到裏間房裏,同他咕唧了好一會,把撫臺所託的事情,以及拉他幫忙的話,並如何擺佈他三個法子,密密的商量了半天。範顏清果然滿口答應:“情願拚着斷了這門親戚報效老帥,只求事成之後,求大人在老帥面前好言吹噓,求老帥的栽培就是了。”刁邁彭亦滿口答應。
二人計議已定。好個刁邁彭,回到公館,立刻叫廚子做了兩席酒,叫人挑着送到首府裏。一席說是自己送給黃大人的,那一席又換了兩個擡了進去,說是院上武巡捕範老爺送給他舅爺蓋大人的。隨後又見他二人不約而同,一齊來到首府,找了首府陪着他,一個看朋友,一個看親戚。首府一見他二人都是撫臺的紅人,焉有不領他進去之理。
蓋道運見了範顏清,雖然平時同他不對,如今自己是落難的人,他送了喫的,又親自來瞧,總算有情分的了,不得不拿他當做親人,同他訴了一番苦,又問姑太太的好。範顏清同他敷衍了幾句,又把刁邁彭引了過來,彼此相見。刁邁彭先見老把兄,自然另有一番替他抱屈的話,說得黃保信感激他,直拿他當做親兄弟一般看待。及至見了蓋道運,又是義形於色的說了一大泡。蓋道運是個武傢伙,更加容易哄騙,亦當他是真好人,便說撫臺如何想卸罪於他三人身上:“現在我有撫臺札子爲憑,欽差提審,我是要呈上去的。”刁邁彭亦竭力叫他把札子收好,不但保得性命,而且保得前程。蓋道運自然佩服他的話。四個人又談了半天,他二人方纔辭別而出。
第二天,範顏清說院上事忙,止有刁邁彭一個又到首府裏看他二人,說的話無非同昨天一樣。刁邁彭回到院上,同蔣撫臺說“時候到了。再不辦,欽差要提人審問,就來不及了。”當夜,刁邁彭就住在院上籤押房裏,足足忙了半夜。第三天午前,又去瞧蓋道運,說是:“剛從院上下來,聽得說你三位的風聲不好。”蓋道運道:“無論如何,我有中丞這個憑據,總不會殺頭的。”刁邁彭道:“你別這樣講,他們做文官的心眼子總比你多兩個,你那裏是他對手。你姑且把札子拿出來,等我替你看看還有什麼拿住他的把柄地方沒有。”頭兩天蓋道運聽了黃保信的話,說我們這位把弟如何能幹,如何在行,所以一聽他言,登時就要請教。齊巧黃保信這時也陪了過來,亦催道運把札子拿出來,給某人瞧瞧還有什麼可以規避的方法。”蓋道運不加思索,忙從懷裏取出那角公事,雙手送上。
刁邁清剛正接到手中,忽然範顏清又從外面進來,拿個蓋道運一把拉到對過房裏說話。大家曉得他是院上來的,一定是得了什麼風聲了,蓋道運不由得跟了過去。黃保信同胡鸞仁各各驚疑不定。刁邁彭將計就計,亦說:“範某人到這裏,一定有什麼話說,你二人姑且跟過去聽聽看。”他倆被這一句提醒,果然一齊走了過去,此時刁邁彭見房內無人,急急從袖筒管裏把昨夜所改好的一個札子取了出來,替他換上。那邊範顏清故意做得鬼鬼祟祟的,說是:“今天在院上,聽見老帥同兩司談起你老舅的事情,大約無甚要緊。老帥總得想法子出脫你們三位的罪名,可以保全自己。”
蓋道運聽了如此一講,又把心略略放下,忙說道:“果其如此,還像個人。”範顏清又故意多坐了一回,約摸刁邁彭手腳已經做好,倏地取出表來一看,說一聲:“不好了!誤了差了!”連忙起身告辭;又走過來喊了一聲:“刁大人,我們同走罷。老帥叫你起的那個稿子,今兒早上還催過兩遍,你交代上去沒有?”刁邁彭亦故作一驚道:“真的!我忘記了!我們同走,回來再來。”說完出來,便把札子連封套交代了蓋道運,彼此拱拱手,同了範顏清揚揚而去。這裏蓋道運還算細心,拉開封套瞧了一瞧,見札子依然在內,仍舊往身上一拽,行所無事。
且說童子良此番來到安徽籌款,沒有籌得什麼,安徽又是苦省分,撫臺應酬的也不能如願,所以這事既已查到實在,就想徹底究辦。先叫帶來的司員擬定折稿,請旨把蓋道運等三個先行革職,歸案審辦。這是欽差在行轅裏做的事,撫臺在外頭雖然得了風聲,然而無法彌補。偏偏又是刁邁彭因蒙欽差賞識,便天天到欽差行轅裏去獻殷勤,不但欽差歡喜他,連欽差的隨員跟人沒有一個不同他要好的,拜把子,送東西,應有盡有,所以弄得異常連絡。等到欽差參了出去,他得了風聲,又去化錢給欽差隨員,託他們把摺子的稿子抄了出來。大衆以爲折已拜發,無可挽回,落得賣他幾文。那曉得他稿子到手,立刻送到撫臺跟前。
蔣撫臺見上頭參的很兇,倘若認真的辦起來,不但自己功名不保,而且還防有餘罪,急同刁邁彭商量辦法。刁邁彭道:“只要欽差的這個底子到了我們手裏,卑府就有法子想了。”蔣撫臺急欲請教。刁邁彭道:“要大人先下手奏出去,便可無事。”蔣撫臺道:“欽差的摺子昨兒已經拜發,我們怎麼趕到他的頭裏呢?”刁邁彭道:“這有什麼難的。欽差摺子是按站走的,我們給他一個‘六百里加緊’,將來總是我們的先到。他三個的罪名橫豎是脫不掉的,如今札子已經換到,他們沒有把柄,就冤枉他們一次,還怕什麼。現在只請大人先把這事奏參出去,只把罪名卸在他三個身上,自己亦不可推得十二分乾淨,失察處分必須自行檢舉的。如此一來,我們的摺子先到京,皇上先看見,欽差的摺子隨後趕到,就是再說得利害些,也就無用了。”
六百里加緊:緊急文書,每日限定必須走六百里。
蔣撫臺聽他說話甚是有理,立刻照辦,仔仔細細擬了一個摺子,請將蓋道運三個革職嚴懲,自己亦自請議處。當天把摺子寫好拜發,由驛站六百里加緊遞到京城,果然比欽差的摺子早到得好幾天。上頭批了下來:“蓋道運三個一齊充發軍臺,效力贖罪,巡撫蔣某交部議處。”旋經部議得“降三級調用”。虧得自己軍機裏有照應,求了上頭,改了個“革職留任”,仍舊還做他的撫臺。
軍臺:設於西北邊這地方的驛站。犯罪官員如發往軍臺,每月得繳納臺費,三年期滿,得到批准,可釋放回來。
上諭下來的那天,蓋道運氣憤憤的不服,說:“我們是按照撫臺的札子辦事的,爲什麼要辦我們的罪?”一定吵着,要首府上去替他伸冤。首府問他有什麼憑據。他就把札子掏了出來,摔到首府面前,說:“老兄請看!這不是他叫我們‘迎頭痛剿’的嗎”?怎麼如今全推在我們身上呢?”首府接過來一看,只有叫他們“相機剿辦”的字眼,並沒有許他“迎頭剿痛”的字眼,便把這話告訴了他,又把字義講給他聽。蓋道運還不明白。畢竟黃保信是文官,猜出其中的原故,一定是那天被刁邁彭偷換了去。把話說明,於是一齊痛罵刁邁彭,已經來不及了。後來欽差那面見朝廷先有旨意,亦道是蔣某人自己先行出奏,卻不曉得全是刁邁彭一個人串的鬼戲。後來刁邁彭在安徽做官,因此甚爲得法。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