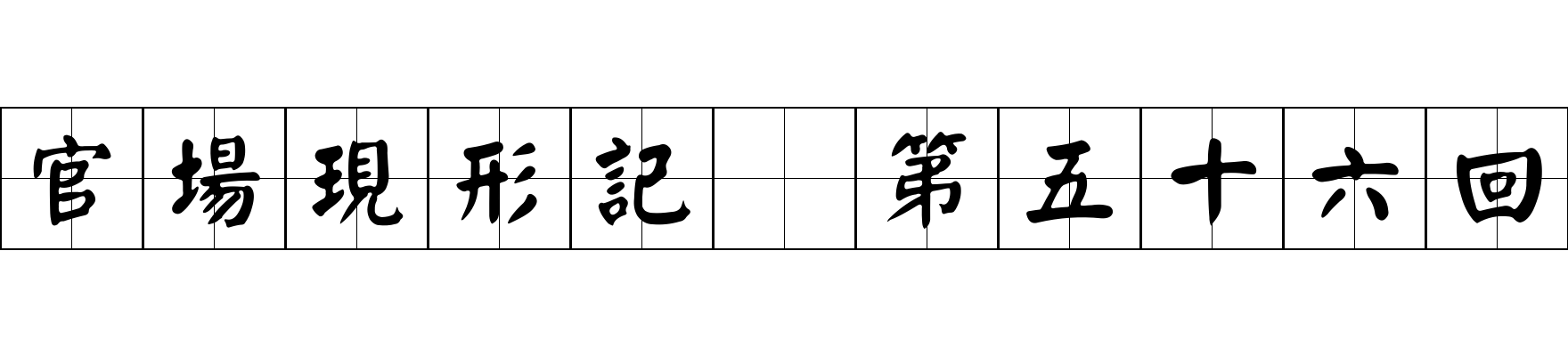官場現形記-第五十六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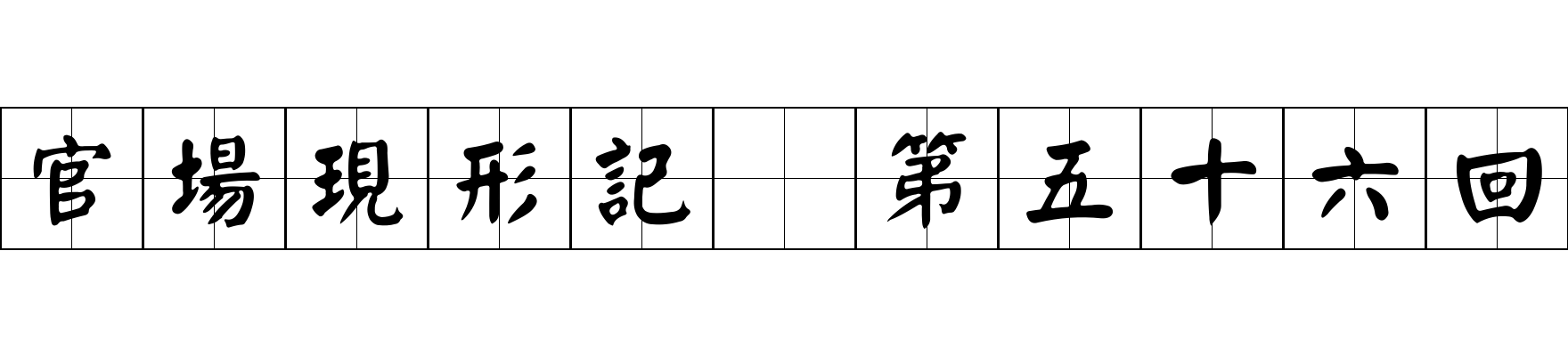
《官場現形記》是晚清文學家李伯元創作的長篇小說。小說最早在陳所發行的《世界繁華報》上連載,共五編60回,是中國近代第一部在報刊上連載並取得社會轟動效應的長篇章回小說。它由30多個相對獨立的官場故事聯綴起來,涉及清政府中上自皇帝、下至佐雜小吏等,開創了近代小說批判現實的風氣。魯迅將《官場現形記》與其他三部小說並稱之爲譴責小說,是清朝晚期文學代表作品之一。
製造廠假札賺優差 仕學院冒名作槍手
卻說海州州判同了翻譯從洋船上回到自己衙門,急於要問所遞銜條,洋提督是否允准出信。當下翻譯先說洋提督如此不肯,經他一再代爲婉商方纔應允,並且答應信上大大的替他兩人說好話。州判老爺聽了,非凡之喜。一宵易過,次日又跟了同寅同到海邊送過洋提督開船方纔回來。蕭長貴亦開船回省。
過了一日,梅颺仁果然發了一個稟帖,無非又拿他辦理交涉情形鋪張一遍,後面敘述拿獲大盜,所有出力員弁,叩求憲恩,准予獎勵。等到制臺接到梅颺仁的稟帖,那洋提督的信亦同日由郵政局遞到,立刻譯了出來。信上大致是謝制臺派人接他,又送他土儀的話,下來便敘“海州文武相待甚好,這都是貴總督的調度,我心上甚是感激”。末後方敘到“海州州判某人及翻譯某人,他二人託我求你保舉他倆一個官職;至於何等官職,諒貴總督自有權衡,未便干預。附去名條二紙,即請臺察”各等語。制臺看完,暗道:“這件事情,海州梅牧總算虧他的了。就是不拿住強盜,我亦想保舉他,給他點好處做個榜樣,如今添此一層,更有話好說了。至於州判、翻譯能夠巴結洋人寫信給我,他二人的能耐也不小,將來辦起交涉來一定是個好手。我倒要調他倆到省裏來察看察看。”當日無話。
次日司、道上院見了制臺。制臺便把海州來稟給他們瞧過,又提到該州州判同翻譯託外國官求情的話。藩司先說道:“這些人走門路竟走到外國人的門路,也算會鑽的了。所恐此風一開,將來必有些不肖官吏,拿了封洋人信來,或求差缺,或說人情,不特難於應付,勢必至是非倒置,黑白混淆,以後吏治,更不可問。依司裏的意思:海州梅牧獲盜一案,亟應照章給獎,至於州判某人,巧於鑽營,不顧廉恥,請請大帥的示,或是拿他撤任,或是大大的申斥一番,以後叫他們有點怕懼也好。”誰知一番話,制臺聽了,竟其大不爲然,馬上面孔一板道:“現在是什麼時候!朝廷正當破格用人,還好拘這個嗎?照你說法,外國人來到這裏,我們趕他出去,不去理他,就算你是第一個大忠臣!弄得後來,人家翻了臉,駕了鐵甲船殺了進來,你擋他不住,乖乖的送銀子給他,朝他求和,歸根辦起罪魁來,你始終脫不掉。到那時候,你自己想想,上算不上算?古語說得好:‘君子防患未然。’我現在就打的是這個主意。又道是:“觀人必於其微’,這兩人會託外國人遞條子,他的見解已經高人一着,兄弟就取他這個,將來一定是個外交好手。現在中國人才消乏,我們做大員的正應該捨短取長,預備國家將來任使,還好責備苛求嗎。”藩臺見制臺如此一番說話,心上雖然不願意,嘴裏不好說什麼,只得答應了幾聲“是”,退了出去。
這裏制臺便叫行文海州,調他二人上來。二人曉得外國信發作之故,自然高興的了不得,立刻裝束進省,到得南京,叩見制臺。制臺竟異常謙虛,賞了他二人一個坐位。坐着談了好半天,無非獎勵他二人很明白道理。“現在暫時不必回去,我這裏有用你們的地方。”兩人聽說,重新請安謝過。次日製臺便把海州州判委在洋務局當差,又兼製造廠提調委員。那個翻譯,因他本是海州學堂裏的教習,拿他升做南京大學堂的教習,仍兼院上洋務隨員。分撥既定,兩人各自到差。海州州判自由藩司另外委人署理。海州梅颺仁因此一案,居然得了明保,奉旨送部引見。蕭長貴回來,亦蒙制臺格外垂青,調到別營做了統領,仍兼兵輪管帶。都是後話不題。
且說海州州判因爲奉委做了製造廠提調,便忙着趕去見總辦,見會辦,拜同寅,到廠接事。你道此時做這製造廠總辦的是誰?說來話長:原來此時這位當總辦的也是才接差使未久,這人姓傅,號博萬。他父親做過一任海關道,一任皇司,兩任藩司。後首來了一位撫臺,不大同他合式,他自己估量自己手裏也着實有兩文了,便即告病不做,退歸林下。傅博萬原先有個親哥哥,可惜長到十六歲上就死了。所以老人家家當一齊都歸了他。人家叫順了嘴,都叫他爲傅百萬。其實他傢俬,老人家下來,五六十萬是有的,百萬也不過說說好聽罷了。只因他生得又矮又胖,穿了厚底靴子,站在人前也不過二尺九寸高;又因他排行第二,因此大家又贈他一個表號,叫做傅二棒錘。傅二棒錘自小才養下來沒有滿月,他父親就替他捐了一個道臺,所以他的這個道臺,人家又尊他爲“落地道臺”。但是這句話只有當時幾個在場的親友曉得,到得後來亦就沒有人提及了。後來大衆所曉得的只有這傅二棒錘一個綽號。
且說傅二棒錘先前靠着老人家的餘蔭,只在家裏納福,並不想出來做官,在家無事,終日抽大煙。幸虧他得過異人傳授,說道:“凡是抽菸的人,只要飯量好,能夠喫油膩,臉上便不會有煙氣。”他這人喫量是本來高的,於是吩咐廚房裏一天定要宰兩隻鴨子:是中飯喫一隻,夜飯喫一隻;剩下來的骨頭,第二天早上煮湯下麪。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如此。所以竟把他喫得又白又胖,竟與別的吃煙人兩樣。他抽菸一天是三頓:早上喫過點心,中飯,晚飯,都在飯後。泡子都是跟班打好的,一口氣,一抽就是三十來口,口子又大,一天便百十來口,至少也得五六錢煙。等到抽完之後,熱毛巾是預備好的,三四個跟班的,左一把,右一把,擦個不了,所以他臉上竟其沒有一些些煙氣。擦了臉,自己拿了一把鏡子,一頭照,一頭說道:“我該了這們大的傢俬,就是一天吃了一兩、八錢,有誰來管我!不過像我們世受國恩的人家,將來總要出去做官的,自己先一臉的煙氣,怎麼好管屬員呢。”有些老一輩人見他話說得冠冕,都說:“某人雖有嗜好,尚還有自愛之心。”因此大家甚是看重他,都勸他出去混混。無奈他的意思,就這樣出去做官,庸庸碌碌,跟着人家到省候補,總覺不願,總想做兩件特別事情,或是出洋,或是辦商務,或是那省督、撫奏調,或是那省督、撫明保,做一個出色人員,方爲稱意。但是在家納福,有誰來找他?誰知富貴逼人,坐在家裏也會有機會來的。
齊巧有他老太爺提拔的一個屬員,姓王,現亦保到道員,做了出使那一國的大臣參贊。這位欽差大臣姓溫,名國,因是由京官翰林放出來的,平時文墨功夫雖好,無奈都是紙上談兵,於外間的時務依然隔膜得很。而且外洋文明進步,異常迅速,他看的洋板書還是十年前編纂的,照着如今的時勢是早已不合時宜的了,他卻不曉得,拾了人家的唾餘,還當是“入時眉樣”。亦幸虧有些大老們耳朵裏從沒有聽見這些話,現在聽了他的議論,以爲通達極的了,就有兩位上摺子保舉他使才。中國朝廷向來是大臣說甚麼是甚麼,照便奉旨記名,從來不加考覈的。等到出使大臣有了缺出,外部把單子開上,又只要裏頭有人說好話,上頭亦就馬上放他。等到朝旨下來,什麼謝恩、請訓都是照例的事。就是上頭召見,問兩句話,亦不過檢可對答的回上兩句,餘下不過磕頭而已。列位看官試想:任你是誰,終年不出京城一步,一朝要叫你去到外洋,你平時看書縱雖明白,等到辦起事來,兩眼總漆黑的。
閒話少敘。且說這個溫欽差召見下來,便到各位拿權的王大臣前請安,請示機宜,以爲將來辦事的方針。這些大人們當中有關切的,便薦兩個出過洋、懂得事務的,或當參贊,或充隨員,以爲指臂之助。還有些汲引私人的,亦只顧薦人,無非爲三年之後得保起見。當下只傅二棒錘父親所提拔那位屬員王觀察,已有人把他薦到溫欽差跟前充當參贊。幸喜欽差甚是器重他。他便想到從前受過好處的傅藩臺的兒子。亦是傅二棒錘有出山的思想,預先有過信給這王觀察。王觀察才幹雖有,光景不佳,既然出洋,少不得添置行頭,籌寄家用,雖有照例應支銀兩,無奈總是不敷,所以也須張羅幾文。心上早看中這傅二棒錘是個主兒,本想朝他開口,齊巧他有信來託謀差使,便將機就計,在溫欽差前竭力拿他保薦,求欽差將他攜帶出洋。欽差應允。王觀察便打電報給他,叫他到上海會齊。等到到得上海,會面之後,傅二棒錘雖然是世家子弟,畢竟是初出茅廬,閱歷尚淺,一切都虧王觀察指教,因此便同王觀察十分親密,王觀察因之亦得遂所願。兩人遂一塊兒跟着欽差出洋。王觀察當的是頭等參贊。因爲這傅二棒錘已經是道臺,小的差使不能派,別的事又委實做不來,又虧王觀察替他出主意,教他送欽差一筆錢,拜欽差爲老師,欽差亦就奏派他一個掛名的差使。溫欽差自當窮京官當慣的,在京的時候,典質賒欠,無一不來。家裏有一個太太,兩個小姐。太太常穿的都是打補釘的衣服。光景艱難,不用老媽,都是太太自己燒茶煮飯,漿洗衣服。這會子得了這種闊差使,在別人一定登時闊綽起來,誰知道這位太太德性最好,不肯忘本,雖然做了欽差大人,依舊是一個人不用,上輪船,下輪船,倒馬桶,招呼少爺、小姐,仍舊還是太太自己做。朋友們看不過。告訴了欽差,託欽差勸勸他。他說道:“我難道不曉得現在有錢,但是有的時候總要想到沒有的時候。如今一有了錢,我們就盡着花消,倘或將來再遇着難過的日子,我們還能過麼。所以我如今決計還要同從前一樣,有了攢聚下來,豈不更好。”欽差見他說得有理,也只得聽他。好在也早已看慣的了,並不覺奇。
傅二棒錘既然拜了欽差爲老師,自然欽差太太也上去叩見過。太太說:“你是我們老爺的門生,我也不同你客氣。況且到了外洋,我們中華人在那裏的少,我們都是自己人一樣。你有什麼事情只管進來說,就是要什麼喫的、用的亦儘管上來問我要,我總拿你當我家子侄一樣看待,是用不着客氣的。”傅二棒錘道:“門生蒙老師、師母如此栽培,實在再好沒有。”說着,又談了些別的閒話,亦就退了出來。
這一幫出洋的人,從欽差起,至隨員止,只有這傅二棒錘頂財主,是匯了幾萬銀子帶出去用的。雖然不帶家眷,管家亦帶了三四個。穿的衣裳,脫套換套。他說:“外國人是講究乾淨的。”穿的襯衣衫褲,夏天一天要換兩套,冬天亦是一天一身。換下來的,拿去重洗。外國不比中國,洗衣裳的工錢極貴,照傅二棒錘這樣子,一天總得兩塊金洋錢工錢,一月統扯起起來,也就不在少處了。
欽差幸虧有太太,他一家老少的衣衫,自從到得外洋一直仍舊是太太自己漿洗。在外國的中國使館是租人家一座洋房做的的。外國地方小,一座洋房總是幾層洋樓,窗戶外頭便是街上。外國人洗衣服是有一定做工的地方,並且有空院子可以晾曬。欽差太太洗的衣服,除掉屋裏,只有窗戶外頭好晾。太太因爲房裏轉動不開,只得拿長繩子把所洗的衣服一齊拴在繩子上,兩頭釘好,晾在窗戶外面。這條繩子上,褲子也有,短衫也有、襪子也有,裹腳條子也有,還有四四方方的包腳布,色也有藍的,也有白的,同使館上面天天掛的龍旗一般的迎風招展。有些外國人在街上走過,見了不懂,說:“中國使館今日是什麼大典?龍旗之外又掛了些長旗子、方旗子,藍的,白的,形狀不一,到底是個什麼講究?”因此一傳十,十傳百,人人詫爲奇事。便有些報館訪事的回去告訴了主筆,第二天報上上了出來。幸虧欽差不懂得英文的,雖然使館裏逐日亦有洋報送來,他也懶怠叫翻譯去翻,所以這件事外頭已當着新聞,他夫婦二人還是毫無聞見,依舊是我行我素。
傅二棒錘初到之時,衣服很拿出去洗過幾次,便有些小耳朵進來告訴了欽差太太,說傅大人如何闊,如何有錢,一天單是洗衣服的錢就得好幾塊。欽差太太聽了,念一聲“阿彌陀佛”:“要是我有了錢,決計不肯如此用的。我們老爺、少爺的衣服統通是一個月換一回,我自己論不定兩三個月才換一回,那裏有他閣,天天換新鮮。他一個月有多少薪水,全不打算打算。照這樣子,只怕單是洗衣服還要去掉一半。你們去同他說:橫豎一天到晚空着沒有事情做,叫他把換下來的衣裳拿來,我替他洗。他一天要化兩塊錢的,我要他一天一塊錢就夠了。他也好省幾文。我們也樂得賺他幾文,橫豎是我氣力換來的。”
當下,果然有人把這話傳給了傅二棒錘。傅二棒錘因爲他是師母,如把褲子、襪子給他洗,終覺有些不便,一直因循未果。後來欽差太太見他不肯拿來洗,恐怕生意被人家奪了去,只得自己請傅二棒錘進來同他說。傅二棒錘無奈,只得遵命,以後凡是有換下來的衣服,總是拿進來給欽差太太替他漿洗。頭兩個月沒有話說,傅二棒錘因爲要巴結師母,工價並不減付,仍照從前給外國人的一樣。欽差太太自然歡喜。
有天有個很出名的外國人請欽差茶會,欽差自然帶了參贊、翻譯一塊兒前去。到得那裏,場子可不小,男男女女,足足容得下二三千人。多半都是那國的貴人闊人,富商巨賈,此外也是各國人公使、參贊,客官商人。凡是有名的人統通請到。傅二棒錘身穿行裝,頭戴大帽,翎頂輝煌的也跟在裏頭鑽出鑽進。無如他的人實在長得短,站在欽差身後,墊着腳指頭想看前面的熱鬧,總被欽差的身子擋住,總是看不見;夾在人堆裏,擠死擠不出,把他急的了不得,只是拿身子亂擺。
齊巧他身子旁邊站了一個外國絕色的美人。外國的禮信:凡是女人來到這茶會地方,無論你怎樣閣,那女人下身雖然拖着掃地的長裙,上半身卻是袒胸露肩,同打赤膊的無異。這是外國人的規矩如此,並不足爲奇的。傅二棒錘站在這女人的身旁,因爲要擠向前去瞧外面的熱鬧,只是把身子亂擺,一個腦袋,東張西望,賽如小孩搖的鼓一般。那女人覺得膀子底下有一件東西磕來碰去,翠森森的毛,又是涼冰冰的,不曉得是什麼東西。凡是外國人茶會,一位女客總得另請一位男客陪他。這男客接到主人的這副帖子,一定要先發封信去問這女客肯要他接待與否,必須等女客答應了肯要他接待,到期方好前來伺候。倘若這女客不要,還得主人另請高明。閒話休敘。且說這天陪伴這位女客的也是一位極有名望的外國人,聽說還是一個伯爵,是在朝中有職事的。當時那外國女客因不認得那件東西,便問陪伴他的那個伯爵,問他是什麼。幸虧那位伯爵平時同中國官員往來過幾次,曉得中國官員頭上常常戴着這翠森森、涼冰冰的東西,名字叫做“花翎”,就同外國的“寶星”一樣,有了功勞,皇上賞他準他戴他纔敢戴,若是不賞他卻是不能戴的。那位伯爵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卻把銀子可捐戴的一層沒有告訴了他。這也是那位伯爵不懂得中國內情的緣故,休要怪他。當下那外國女客明白了這個道理,便把身子退後半尺,低下頭去把傅二棒錘的翎子仔細端詳了一回,又拿手去摩弄了一番,然後同那伯爵說笑了幾句,方始罷休。
這天傅二棒錘跟了欽差辛苦了幾個時辰,人家個子高,看得清楚,倒見了許多什面;獨有他長得矮,躲在人後頭,足足悶了一天,一些些景緻多沒有瞧見。因此把他氣的了不得,回到使館,三天沒有出門。
第四天,有個出名製造廠的主人請客,請的是中國北京派來考查製造的兩位委員。這兩位委員都是旗人,一名呼裏圖,一名搭拉祥,都是部曹出身。到了外洋,自然先到欽差衙門稟到,驗過文書,卻與傅二棒錘未曾謀面。這晚廠主人請那兩位委員,卻邀他作陪。傅二棒錘接到了信,便一早的趕了去,見了外國人,寒暄幾句。接着那兩位委員亦就來了。進門之後,先同外國人拉手,又同傅二棒錘廝見,問傅二棒錘:“貴姓?臺甫?貴處?貴班?貴省?幾時到外洋來的?”傅二棒錘一一說了。他倆曉得是欽差大人的參贊,不覺肅然起敬。
傅二棒錘仔細看他二人:一個呼裏圖,滿臉的煙氣,青枝枝的一張臉;一個搭拉祥,滿臉的滑氣,汕幌幌的一張臉。年紀都在三十朝外,說的一口好京話,見了人滿拉攏,傅二棒錘亦問他二人官階一切。呼裏圖說是:“內務府員外郎,現在火器營當差。”搭拉祥是“兵部主事,現蒙本部右堂桐善桐大人在王爺跟前遞了條子,蒙王爺恩典派在練兵處報效。”‘是咱倆商量:凡是人家出過洋的回來,總是當紅差使。所以咱倆亦就稟了王爺,情願出洋遊歷,考查考查情形,將來回來報效。王爺聽了很歡喜。臨走的這一天,咱倆到王爺跟前請示。他老人家說:“好好好,你們出去考察回來,一家做一本日記,我替你們進呈,將來你倆升官發財都在這裏頭了。’傅二哥,你想,他老人家真細心!真想得到!咱倆蒙他老人家這樣栽培,說來真真也是緣分。”
傅二棒錘聽了他二人這一番說話。默默若有所悟,聽他說完,只得隨口恭維了兩句。接着便是本廠的主人同他二人說話,兩邊都是通事傳話。廠主人問他二位:“在北京做此什麼事情?想來一定忙的?”呼裏圖說是:“喫錢糧,沒有別的事情。”外國人不懂。通事又問了他,才曉得他們在旗的人,自小一養下來就有一份口糧,都是開支皇上家的。廠主人方纔明白。又問搭拉祥,搭拉祥說:“我單管畫到。”廠主人又不知甚麼叫“畫到”。搭拉祥說:“我們當司官的,天天上衙門,沒有什麼公事,又要上頭堂官曉得我們是天天來的,所以有本簿子,這天誰來過,就畫上個‘到’字。我專當這差使。除掉自己之外,還有些朋友,自己不來,託我替他代畫的。所以我天天上這一趟衙門,倒也很忙。”
廠主人又問他二人:“這遭出來到我們這裏,可要辦些什麼槍炮機械不要?”搭拉祥正待接腔,呼裏圖搶着說道:“從前咱們火器營裏用的都是鳥槍,別的槍恐怕沒有比過他的。至於炮,還是那年聯兵進城的時候,前門城樓上架着幾尊大炮,到如今還擺着,咱瞧亦就很不小了。”當下廠主人見他說的話不類不倫,也就不談這個,另外說了些閒話。等到喫完客散,傅二棒錘回到使館,心想:“現在官場只要這人出過洋,無論他曉得不曉得,總當他是見過什面的人,派他好差使。我這趟出洋總算主意沒有打錯,將來回去總得比別人佔點面子。”
一個人正在肚裏思量,不提防接到家裏一個電報,說是老太太生病,問他能否請假回去。他得到這個電報,心上好不自在。要想留下,究竟老太太天性之親,一朝有病,打了電報來,要說不回去,於名分上說不下去;如果就此請假回國,這裏的事半途而廢,將來保舉弄不到,白喫一趟辛苦,想想亦有點不合算。左思右想,不得主意。後來他這電報一個使館裏都傳開了,瞞亦難瞞。欽差打發人來問他,老太太犯的是什麼病,要電報去看。他一想不好,只得上去請假,說要回國省親。又道:“倘若門生的母親病好了,再回來報效老師。”溫欽差道:“我本想留下你幫幫我的,因爲是你老太太有病,我也不便留你,等你回去看看好放心。老弟幾時動身?大約要多少川資?我這裏來拿就是了。”
傅二棒錘一想:“這個樣子,不能不回去的了,眼望着一個保舉不能到手。至於回國之後,要說再來,那可就煩難了。”躊躇了一回,忽然想到前日呼裏圖、搭拉祥二人的說話,只要到過外洋,將來回去總要當紅差使的,於是略略把心放下。又想:“他們到這裏遊歷的人都要記本日記簿子,以爲將來自見地步。我出來這半年,一筆沒記。而且每日除掉抽大煙,陪着老師說閒話之外,此外之事一樣未曾考較,就是要記,叫我寫些什麼呢?回去之後,沒有這本東西做憑據,誰相信你有本事呢?”
亦是他福至性靈,忽又想到一個絕妙計策,仍舊上來見老師,說:“門生想在這裏報效老師,無奈門生福薄災生,門生的母親又生起病來,門生不得不回去。辜負老師這一番栽培,門生抱愧得很。”欽差道:“父母大事,這是沒法的。你回去之後,能夠你們老太太的病就此好了,你趕緊再來,也是一樣。倘或真果有點什麼事故,你老弟一時不得回來,好在愚兄三年任滿,亦就回國,我們後會有期,將來總有碰着的日子。”
傅二棒錘道:“門生蒙老師如此栽培,實在無可報答,看樣子,門生的母親未必再容門生出洋。門生的意思,亦就打算引見到省,稍謀祿養。門生這一到省,人地生疏,未必登時就有差委。門生想求老師一件事情。……”欽差不等他說完,接着問道:“可是要兩封信?老弟分發那一省?”傅二棒錘道:“門生想求老師賞兩個札子。”欽差想了想,皺着眉頭,說道:“我內地裏沒有甚麼事情可以委你去辦。”
傅二棒錘道:“不是內地,仍舊在外國。英國的商務,德國的槍炮,美國的學堂,統通求老師賞個札子,等門生去查考一遍。”欽差道:“不是你老太太有病你急於回去,還有工夫一國一國的去考查這些事情嗎?”傅二棒錘道:“門生並不真去。”欽差道:“你既不去,又要這個做甚麼?這更奇了!”
傅二棒錘又扭捏了半天,說道:“不瞞老師說;老師大遠的帶了門生到這外洋來,原想三年期滿,提拔門生得個保舉,以便將來出去做官便宜些。誰料平空裏出了這個岔子,現在保舉是沒有指望。這是門生自己沒有運氣,辜負老師栽培,亦是沒法的事。門生現在求老師賞個札子,不爲別的,爲的是將來回國之後,說起來面子好看些。雖說門生沒有一處處走到,到底老師委過門生這們一個差使,將來履歷上亦寫着好看些。”
溫欽差聽了一笑,也不置可否。你道爲何?原來溫欽差的爲人極爲誠篤,說是委了差使不去這事便不實在,所以他不甚爲然,因之沒有下文。當下但問他:“幾時動身?川資可到帳房去領。”傅二棒錘見欽差無話,只得退了下來,心上悶悶不樂。幸虧他父親提拔的那位王觀察此時正同在使館當參贊,聽得他這個消息,立刻過來探望。傅二棒錘只得又託他吹噓,王觀察一口應允。傅二棒錘又說:“只要欽差肯賞札子,情願不領川資,自行回國。”王觀察正是欽差信用之人,說的話自然比別人香些。欽差初雖不允,禁不住一再懇求,又道是:“傅某人情願不領川資,況且給他這個札子,無關出入。”欽差因他說話動聽,自然也應允了。
誰知傅二棒錘得到這個札子,卻是非凡之喜,立刻收拾行李,叩謝老師,辭別衆同事,急急忙忙,趁了公司船回國。在公司船上,足足走兩個多月方回到上海。在上海棧房裏耽擱一天,隨即徑回原籍。老太太的病乃是多年的老病,時重時輕,如今見兒子從外洋回來,心上一歡喜,病勢自然鬆減了許多,請了大夫吃了幾帖藥,居然一天好似一天。傅二棒錘於是把心放下。這趟出洋雖然化了許多冤枉錢,又白辛苦了半年多,保舉絲毫無望,然而被他弄到了這個札子,心裏卻是高興。路過上海時,請教了一位懂時務的朋友,買了幾部什麼《英軺日記》、《出使星軺筆記》等類。空了便留心觀看。凡是那一國輪船打得好,那一國學堂辦得好,那一國工藝振興得好,那一國槍炮製造得好,雖不能全記,大致記得一、半成。到了檯面上同人家談天,說的總是這些話。大衆齊說:“某人到過一趟外洋,居然增長了這多見識。”傅二棒錘聽了,心上歡喜。仍舊逐日溫習,一直等到老太太可以起牀,看看決無妨礙的了,他便起身進京引見。
到得京裏,會見幾位大老們,問他一向做得什麼。他便說:“新從外洋回來,奉出使大臣某欽差的札子,委赴各國考察一切。事完正待銷差,忽接到老母病電,一面電稟銷差,一面請假回國。現因親老,不敢出洋,所以纔來京引見的。”大老們聽了他這番說話,又問他外國的事情,他便把什麼《英軺日記》、《出使筆記》所看熟的幾句話說了出來。聽上去倒也是原原本本,有條不紊。大老們聽了,都贊他留心時事。又問他外國景緻,這是更無查對之事,除自己知道的之外,又隨口編造了許多。那些大老爺有幾位輪船都沒有坐過,聽了他話還有什麼不相信的。傅二棒錘見人家相信他的話,越發得意的了不得。
引見之後,遂即到省,指的省分是江蘇。先到南京稟見制臺,傳了上去。制臺是已經曉得他的履歷的了。一來他父親做過實缺藩司,從前曾在那裏同過事,自然有點交情;二來又曉得他從外洋回,南京候補雖多,能夠懂得外交的卻也很少,某人既到過外洋,情形一定是明白的,因此已經存了個另眼看待的心。等到見面,傅二棒錘又把溫欽差派他到某國某國查考什麼事情一一陳說一遍。說完,又從靴筒裏把溫欽差給他的札子雙手遞給制臺過目。制臺略爲看了一看,便問他所有的地方可曾自己一一親自到過。傅二棒錘索性張大其詞,說得天花亂墜,不但身到其處,並且一一都考較過,誰家的機器,誰家的章程,滔滔汩汩,說個不了。好在是沒有對證的,制臺當時已不免被他所瞞。等他下去,第二天,同司、道說:“如今我們南京正苦懂得事的少,如今傅某人從外洋回來。倒是見過什面的,有些交辦的新政很可以同他商量。他閱歷既多,總比我們見得到。”司、道都答應着。
又過了幾天,傅二棒錘稟辭,要往蘇州,說是稟見撫臺去。制臺還同他說:“這裏有許多事要同你商量,快去快來。”傅二棒錘自然高興。等到到了蘇州,又把他操演熟的一套工夫使了出來。可巧撫臺是個守舊人,有點糊里糊塗的,而且一向是謹小慎微,屬員給他一個稟帖,他要從第一行人家的官銜、名字,“謹稟大人閣下敬稟者”讀起,一直讀到“某年月日”爲止,才具只得如此,還能做得什麼事情。所以聽了他的說話,倒也隨隨便便,並不在意。傅二棒錘見蘇州局面既小,撫臺又是如此,只得仍舊回到南京。
此時制臺正想振作有爲。都說他的人是個好的,只可惜了一件,是犯了“不學無術”四個字的毛病。倘或身旁有個好人時時提醒了他,他卻也會做好官的。無奈幕府裏屬員當中,辦洋務的只仗着翻譯。要說翻譯,外國話、外國文理是好的,至於要講到國際上的事情,他沒有讀過中國書,總不免有點偏見,幫着外國。所以這位制臺靠了這班人辦理外交,只有愈辦愈壞,主權慢慢削完,地方慢慢送掉,他自己還不曾曉得。此外管軍政的,管財政的,管學務的,縱然也有一二個明白的在內,無奈好的不敵壞的多,不是藉此當作升官的捷徑,便是認做發財的根源。一省如此,省省如此,國事焉得而不壞呢!
閒話休敘。且說傅二棒錘回到南京,制臺又廖採虛聲,拿他當作了一員能員,先委了他幾個好差使。隨後他又上條陳,說省城裏這樣辦得不好,那樣辦得不對,照外國章程,應該怎樣怎樣。制臺相信了他的話,齊巧製造槍炮廠的出差,就委他做了總辦;又拔給許多款項叫他隨時整頓。不久又兼了一個銀元局的會辦,一個警察局會辦。這幾個差使都是他說大話、發空議論騙了來的。考其究竟,還虧溫欽差給了他那個考查各國的札子。他雖然一處沒有去,借了這札子的力量,居然制臺相信他,做了這廠的總辦。那海州州判調省之後,制臺拿他拔在廠裏當差。其時正當這傅二棒錘初委總辦,接手未久。亦是他倆官運亨通:傅二棒錘自從接差之後,諸事順手,從未出過一點岔子,所以制臺愈加相信。當了兩年紅差使,跟手就委署一任海關道。交卸到省,仍舊當他的紅差使。那位州判老爺因爲憲眷優隆,亦就捐升同知,做了“搖頭大老爺”,說是遇有機會就可以過班知府。後來能否如願,書中不及詳敘。
搖頭大老爺:指通判。通判是知府的輔佐官,知縣見了通判要行見上司禮節,而過後則搖頭,是瞧不起通判的,所以叫通判爲“搖頭大老爺”。
且說彼時捐例大開,各省候補人員十分擁擠,其中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做上司的人既漫無區別,專檢些有來往、有交情,或者有大帽子寫信的人,照應照應,量委差缺。有些苦的,候補了十來年永遠見不到上司面的人還有。因此京裏有位都老爺便上了一個摺子,請旨飭令各省督、撫,整頓吏治,甄別賢愚,好的留省當差,壞的諮回原籍,或是責令學習。摺子上去,上頭自然沒有不準,立刻由軍機處寄字各省督、撫照辦。各省當中,有些已有“課吏館”的,奉到這個上諭,譬如本來敷衍的,至此也要整頓起來。還有些督、撫曉得捐班當中通的人少,也不忍過於苛求。凡是捐班人員初到省,道、府大員總得給他個面子,不肯過於頂真,同、通以下以及佐雜就用不着客氣了。
這些人到省,並不要他做什麼策論,也不要扃門考試,同通、知縣只要他當面點《京報》。北京出的《京報》,上面所載的不過是“宮門抄”同日本的幾道諭旨以及幾個摺奏,並沒有什麼深文奧義,是頂容易明白的。這時候做督、撫的人隨手翻一條,或是諭旨,或是折片,只要不點“騎馬句”就算是完卷。算算是並不煩難。無奈有些候補老爺仍舊還是點不斷。
課吏館:各省設立爲候補官員學習的地方。
“宮門抄”:清代內閣發抄的關於宮廷動態等情況,同報房抄出,爲京報內容之一,或單獨印刷發售,由宮門口抄出,故名。
傳說那一省有一個候補同知到省,撫臺叫他點《京報》,點的是那一省的巡撫上的摺子。這位巡撫是姓覺羅,他當下拿筆在手,“某省巡撫”一點,“奴才”一點,“覺羅”一點。點到這裏,撫臺說:“罷了!罷了!不消再往下點了!”當下那位同知還不曉得自己點錯,等到衆一齊點過,退了下去,還要指望上司照應他,派他差使。那知道過了兩天,掛出牌來,是叫他回籍學習。他到此急了,一時摸不着頭腦。請教旁人,旁人說:“莫非你點《京報》點錯了罷?”他還不服。人家問他點的那一段,他便背給人家聽。又道:“旗人的名字一直是兩個字的,‘奴才’底下‘覺羅”兩字一定是這位撫臺的名字,我點的並不錯。”人們見他不肯認錯,也就鼻子裏冷笑一聲,不告訴他,等他糊塗一輩子。但是上司掛牌叫他回去學習是無從挽回得來的,只得收拾行李,離開此省,另作打算。此外因點破句子鬧笑話的尚不知其數,但看督撫挑剔不挑剔,憑各人的運氣去碰罷了。
至於一班佐雜,學問自然又差了一層,索性《京報》也不要他點了,只叫他各人把各人的履歷當面寫上三四行。督、撫來不及,就叫首府代爲面試。只要能夠寫得出,已算交代過排場,倘若字跡稍些清楚點就是超等。至於寫不成字的往往十居六七,要奏參革職亦參不了許多,要諮回原籍亦諮不了許多。做上司的到了此時亦只好寬宏大量,積點明騭,給他們留個飯碗罷了。
閒話少敘。目下單說湖南一省,新近換了兩任巡撫,着實文明,很辦了些維新事業,屬下各員望風承旨,極應該都開通的了。那知開者自開,閉者自閉。當時正接着這考試屬員的上諭,撫臺本是個肯做事的人,當下便傳兩司商量辦法。藩臺說:“同、通、州、縣,本有月課。現在考較他們,也不過同月課一個樣子”。臬臺說:“其實只要月課頂真些考,考得好的,拔委差缺,那不好的,自然也要巴結上進。”撫臺道:“這個我豈不知,但是現在軍機裏鄭重其事的寫出信來,總得另外考試一場,分別一個去取。我的意思不光是專考捐班人員,就是科甲出身的也應一體與試。”
齊巧藩臺是個甲班,便道:“科甲出身人員總求大帥給他一個面子,可否免其考試?”撫臺道:“這個不可。科甲人員文理雖通,但是他們從前中舉人,中進士,都是仗着八股、試帖騙得來的,於國計民生毫天關係。這番考試乃是試以政事,公事明白的方可做官;倘若公事不明白,雖是科甲出身,也只好請他回家處館。這樣人倘若將來拿了印把子,怕不誤盡蒼生嗎!”藩臺聽了無話。
當下,撫臺便叫藩臺傳諭他們:自從候補道、府起至佐雜爲止,分作三天,一體考試。如有規避,從重參處。倘有疾病,隨後補考。這個風聲一出,人人害怕,個個驚皇。不但一班候補道臺怨聲載道,自以爲已經做了監司大員,如今還要他同了一班小老爺分班考試,心上氣的了不得。至於一班科甲人員尤其不平,心想:“我們乃是正途出身,又不是銀子買來的,還要考甚麼!”但是撫臺既有這個號令,又不敢違拗,只得一個去打聽幾時才考,考些甚麼,打聽着了,以便出預先揣摩起來。
其中有位候補知府乃是一位太史公截取出來的。到省後亦委過兩趟好點的差使,無奈總是辦理不善,鬧了亂子,撤了回來,因此也就空在省裏。他雖然改官外省,卻還是積習未除。他點翰林的那年,已經四十開外,五十多歲上截取出來。目下已經六十三歲,然而精神還健,目力還好。每日清晨起來,定要臨幕《靈飛經》,寫白摺子兩開方喫早點。下午太陽還未落山的時候,又要翻出詩韻來做一首五言八韻詩。他說:“吟詩一事,最能陶寫性靈。”然而人家見他做詩卻是甚苦,或是煉字,或是煉句,往往一首詩做到二三更天還不得完。詩不做完就不睡覺。偶然得到了一句自己得意的句子,馬上把太太、少爺一齊叫了來,講給他們聽。有時太太睡了覺,還一定要叫醒了他,或爬在牀沿上高聲郎誦,念給太太聽。他自從當童生起,一直頂到如今,所有做的試帖詩稿,經他自己刪汰過五次,到如今還有二尺來高,六十幾本,自以爲在清朝當中也算得一位詩家了。後來朝廷廢去八股、試帖,改試策論,他聽了大不爲然。此時已經改外候補,因爲得了這個信息,氣的三天沒有上衙門。同寅當中有兩個關切的,還當他有病在家,都走來瞧他,問他爲什麼不出門。他嘆口氣,對人說道:“現在是雜學龐興,正學將廢!眼見得世界上讀書的種子就要絕滅了”自此以後,白摺子寫的格外勤,試帖詩做的格外多。人家問他何苦如此,他說他是爲正學綿一線之留延,所以不得不如此。大家都說他痰迷心竅,也就不再勸他。
截取:具有一定資格的官員,由吏部根據他的科分、名次、食俸年限,覈定他截止的期限,予以選用。
《靈飛經》:道教經名,唐書法家鍾紹京曾節錄經文,寫成靈飛經帖,成爲習小楷字的範本。
又過了些時,聽見撫臺有考試屬員的話,又說連正途出身的道、府亦要一體考試。他聽了更氣的什麼似的,說:“我們自從鄉、會、複試,朝、殿、散館以及考差,除掉皇上,亦沒有第二個人來考過。咱如今不該做了他的屬員,倒被他搬弄起來,這個官還好做嗎!”說着,馬上要寫稟帖給撫臺告病,說:“不幹了!我不能來受他的氣!”誰知他老人家正在鬧着告病,倒說一連接到親友兩封來信:一封是他一個至好朋友,還是那年由京裏截取出來,問他挪用過八百金,一直未曾歸還。如今那個朋友光景很難,所以寫了信來問他討。又一封乃是他的親家,現任戶部侍郎,從前定過他的小姐做兒媳,如今兒子已經長大,擬於秋間爲之完姻,以了“向平之願”。這位待郎公親家乃是他一向仰仗的。想想自己女兒也不小了,留在家裏無用,早晚總要出閣的。還帳要錢,嫁女兒亦是要錢,眼面前就有這兩宗出款,倘若不做官,更從何處張羅?因此空發了半日牢騷。
過了一夜,第二天便出門拜見首府。因首府是他同年,彼此知己,好打聽中丞這番考試屬員是個什麼宗旨,所考的是些什麼東西。首府同他說:“聽說也不過策論、告示、批判之類。”他說:“若說策論呢,對策不過翻書的工夫,鄉、會三場以及殿試,我輩尚優爲之。至於作論,越發不是難事,不過做一篇散體文章,況且朝考亦要作論,這些都是做過的。至於擬告示,擬批,擬判,我兄弟雖是一行作吏,但自問並不同於俗吏所爲,一向於這公事上頭卻也不甚留心,不甚了了。驟然拿個稟帖叫我批,說樁案子叫我判,叫我寫些什麼呢?”
首府乃是一個老滑,聽了說道:“這些事情,只要準情酌理,大致不錯,也就交代過去,沒有什麼煩難的。”他道:“總要還他格式纔好。這些格式我肚子裏一向沒有,怎麼好呢?”首府道:“就像我兄弟出來做官,何曾懂得什麼格式,也不過書辦擬了上來,老夫子改好之後,再送我過目,瞧着有不對的,斟酌換兩個字罷了。老同年如其單要講究格式,其實只要一書辦足矣。”那位截取知府聽了,喜的了不得,連忙說道:“現在我兄弟就少怎麼一個人指點指點。如此就拜託同年,可否就在貴衙門裏書辦當中檢老成練達的賞薦一位,以便兄弟朝夕領教?也免得時刻來煩老同年。”首府被他纏不過,曉得他有痰氣的,如果不答應,一定還要纏之不休,只得應允。
等他到拜客回公館,那府裏的書辦也就來了。見了而磕頭稱“大人”,自己稱“書辦”。問他那一房,回說是“刑房”。這位太守公竟其異常客氣,因爲他姓王,就稱之爲王先生。又請王先生坐,王先生執定不肯。他說:“請教的事情多,坐了好商量。”原來這位太守公從前做八股的時候單練就一種工夫,是自己抄寫類書,把什麼“四書人物串珠”、“四書典林”、“文料觸機”等類,一概自己分門別類,抄寫起來。等到用的時候,自然是有觸斯通,取之不竭。如今撫臺要考官,他想考試都是一樣,夾帶總要預備的。他的意思很想仿照款式照編一部,就題個名字,叫做《官學分類大成》。將來刻了出來,不但便己,並可便人。通天下十八省,大大小小候補官員總有好幾萬人。既然上頭要考官,這種類書,每人總得買一部。一十八省一齊銷通,就有好幾萬部的銷場,不惟得名,而又獲利。看來此事大大做得。因此便把這意告訴了王先生。
王先生聽了,楞了一楞,說道:“案卷有幾千幾百宗,一時那裏查得齊!況且書辦管的單是刑科,還有吏、戶、禮、兵、工五科的事情,再加現在的洋務、商務,一共有八九門,書辦一個人怎麼管得來呢。若是大人考較各種格式,依書辦的愚見,外面書鋪裏有一種書,叫做什麼《宦鄉要則》,買部來看看,大約亦有個六七成。”
那位截取太守公聽了甚喜,聽了一遍不懂,又問了一遍,把名字問明白了,立刻寫了個條子,叫管家去買。不到半點鐘工無,居然買了回來。翻開一看,只見各種款式都有些。他老人家翻來覆去看了一回,說道:“原來這書竟同我們做時文的所讀的《制藝聲調譜》一樣,只要把他讀熟,將來出去做官自然無往不利了。”王先生道:“這些都是個呆的,至於其中的巧妙,在乎各人學問、閱歷,書上亦載不盡許多。”截取太守公道:“這個你可辦得來?”王先生道:“辦雖辦得來,不過幾句照例的話,隨便寫了上去,仍舊要師爺改了纔好用。”截取太守公道:“我現在只要有你的本事,我就不愁了。”兩個人談了半天,就要留王先生喫飯。王先生不肯,起身告辭,特地叫他把地名寫下,以便叫人來請。
等到王先生去後,這一位太守公足足盤算一夜,想來想去,自己本事總覺有限,不可冒昧出去應考,忽然悟到:“凡是考試都可以請槍手,理的,也有商量不出道理的,冒名頂替進場。等到明天,我何不把王先生找了來,就叫他充做我的跟班,一塊兒混了進去,等到題目下來,可以同他商量,豈不省事。”主意打定,次日一早便派人把王先生找來,同他密商此事,答應送他若干銀子,如得高等,得有差缺,另外補情。
王先生聽了,若笑不笑的躊躇了一回,說道:“大人既要書辦去做這個,爲什麼昨天不說?書辦今天早上已答應了別人了。”截取太守公一聽大驚,心想:“人家倒比我還來得快!可見這事早已通行,在我今日並不算作創舉。”想罷,便問:“請你作槍的是誰?”書辦道:“是一位同知老爺,並不同大人一班。至於這位老爺的名字,書辦也不便說。橫豎到了那天,如其府、廳同一天考,只要書辦幫完了那邊,自然趕到大人這邊來效力。倘若不在一天,那話更好說了。”這位太守公聽了,默默無言,只得另打主意。
槍手:冒名頂替、代人應考的人。
原來這兩天所有的道員已經竭力運動,弄了什麼京信,撫臺答應顧全他們的面子,免其考試,府廳以下均不能免。當下已定了府、廳爲一天,州、縣人多分作三天,統通到課吏館聽候面試。至於佐雜各員則歸言道代勞。
閒話少敘。且說到了考試府、廳的那一天,撫臺因系奉旨的事,不得不格外慎重。天甫黎明,憲駕已臨課吏館。司、道大憲通同堂參與考。各官一齊翎頂輝煌,靴聲橐橐,卻個個手跨考籃,同應試的舉子一樣。當下遂一點名給卷。點完之後,司、道退出,照例封門。撫臺特留下兩員候補道作爲場中巡綽官。當下發出題目牌。衆人擠上去看時,只見上面一共寫着兩個題目:一篇史論,一道策。史論題目是大家曉得的,總出在《御批通鑑輯覽》一部書上。策題問的是“膏捐”。這膏捐一事,有些抽大煙的老爺們或者還明白一二,至於那些不抽菸的以及平時連《申報》都不看的,還不曉得是什麼事呢。一時人頭簇簇,言三語四,聚了多少人商量,也有商量出道正在聚訟紛紛之際,忽聽得一片聲喧,說是拿住了槍手。只見許多穿袍子,戴帽子的老爺,扭住一個又胖又大的一個黑漢,說:“他進來冒名頂替做槍手,如今要拿他去回撫臺。”後來那兩個監場的道臺彼此商量了一回,齊說:“這事情鬧到大帥跟前,恐怕弄僵,不好收場。”便挺身出來打圓場,勸諸位放手:“把槍手交給我們二人,我們替你們稟明中丞,查明白他那本卷子是替什麼人槍的。查明白了,一面撤去這本卷子,再把本人嚴參:一面把槍手另外一間屋子看管起來,等到開門的時候發交長沙縣嚴辦。諸位不要耽誤自己的工夫。這件事統通交給我二人便了。”一衆大人老爺們見這兩位道臺說話在理,果然把槍手交出,衆人各自散去。那兩位道臺這才進去面稟撫臺。
撫臺於此舉甚是頂真,一聽這話,忙說:“冒名頂替,照考試定章辦起來自要斬立決的。今天考試雖非鄉、會可比,然究系奉旨之事,既然拿到了槍手,兄弟今天定要懲一儆百,讓衆人當面看看,好叫他們有個怕懼。”說着,立刻叫巡捕官傳令開門,傳三大營,首府、縣伺候,說撫臺大人今天要請大令殺人。衆官不知就裏,一齊奔到課吏館。誰知等了半天,即不見撫臺出來,亦沒有別的吩咐。後來一打聽,不料拿到的那個槍手,查出那本卷子,不是別人,正是撫臺二少爺的妻舅。他因爲要仰仗太親翁的提拔,所以特地捐了一個知府,寄託宇下。正逢着撫臺考官,這位大人乃是個一竅不通的,只得請了槍手,代爲槍替。又有二少爺的內線,替他求求太親翁,料想超等總有分的。那知被人拿住了破綻。撫臺一時未及查問明白,鬧得一天星斗,一時不好收蓬。衆人來了半天,巡捕上來請示,撫臺只吩咐槍手發交首府,調三大營來,是恐怕再有人傳遞,特地叫他們來巡緝的,要殺人的話也就不提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