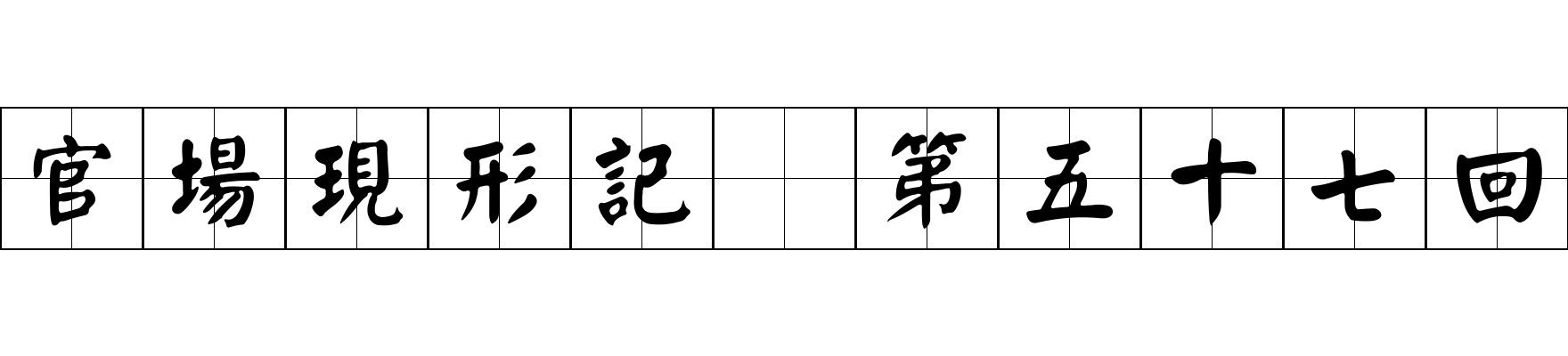官場現形記-第五十七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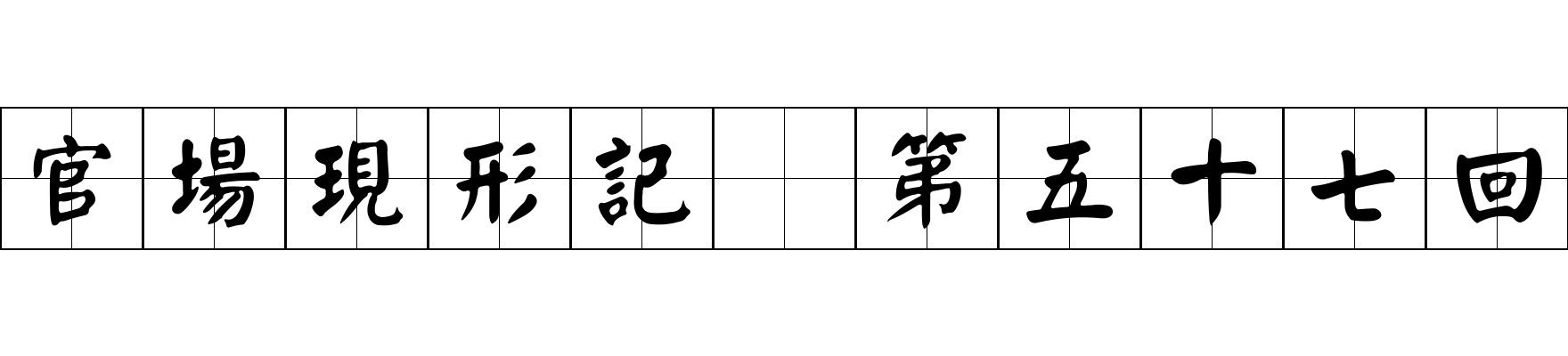
《官場現形記》是晚清文學家李伯元創作的長篇小說。小說最早在陳所發行的《世界繁華報》上連載,共五編60回,是中國近代第一部在報刊上連載並取得社會轟動效應的長篇章回小說。它由30多個相對獨立的官場故事聯綴起來,涉及清政府中上自皇帝、下至佐雜小吏等,開創了近代小說批判現實的風氣。魯迅將《官場現形記》與其他三部小說並稱之爲譴責小說,是清朝晚期文學代表作品之一。
慣逢迎片言矜祕奧 辦交涉兩面露殷勤
話說湖南撫臺本想借着這回課吏振作一番,誰知鬧來鬧去仍舊鬧到自己親戚頭上,做聲不得,只落得一個虎頭蛇尾。後來又怕別人說話,便叫人傳話給首府,叫他斟酌着辦罷。首府會意,回去叫人先把那個槍手教導了一番話,先由發審委員問過兩堂,然後自己親提審問。首府大人假裝聲勢,要打要夾,說他是個槍手。只顧言東語西,不肯承認。在堂的人都說他是個瘋子。首府又問:“這人有無家屬?”就有他一個老婆,一個兒子,趕到堂上跪下,說:“他一向有痰氣病的。這天本來穿了衣帽到親戚家拜壽,有小工王三跟去。王三回來說:‘剛剛走到課吏館,因彼處人多路擠,一轉眼就不見了。”王三尋了半天不見,只得回家報知。後來家中妻子連日在外查訪,杳無消息。今天剛剛走到府衙,聽得裏面審問重犯,又聽說是課吏館捉到的槍手,因此趕進來一看,誰知果然是他。但他實繫有病,雖然捐有頂戴,並未出來做官,亦並不會做文章,叩求青天大人開恩,放他回去。”首府聽了不理,歇了一回,才說道:“就不是槍手,是個瘋子也監禁的。”那人的妻子還是隻在下叩頭。
首府又叫人去傳問請槍手的那位候補知府。那位候補知府說是有病不能親來,拿白摺子寫了說帖,派管家當堂呈遞。首府一面看說帖,管家一面在底下回道:“家主這天原預備來考的,實因這天半夜裏得了重病,頭暈眼花,不能起牀。”首府道:“既有病,就該請假。”管家道:“回大人的話,撫臺大人點名的時候,正是家主病重的時候。小的幾個人連着公館裏上上下下,請醫生的請醫生,撮藥的撮藥,那裏忙得過來。好容易等到第二天下午,家主稍爲清爽些,想到了此事,已經來不及了。”說着,又從身邊把一卷藥方呈上,說道:“這張是某先生幾時幾日開的,那張是某先生幾時幾日開的。”又說:“家主現在還躺在牀上不能起來,大人很可以派人看的。”又道“這些醫生都可以去問的。”首府點點頭,吩咐衆人一齊退去,瘋子暫時看管,聽候稟過撫臺大人再行發落。
後來首府稟明瞭撫臺,回來就照這樣通詳上去,把槍手當做瘋子,定了一個監禁罪名。“侯補知府某人,派首具前往驗過,委繫有病,取具醫生甘結爲憑。惟該守既繫有病,亟應先期請假,迨至查出未到,始行遣下續報。雖訊無資僱槍手等弊,究不能辭玩忽之咎。應如何懲儆之處,出自憲裁”各等語。撫臺得了這個稟帖,還怕人有說話,並不就批。第二天傳發出一道手諭,帖在府廳官廳上,說:
“本部院凡事秉公辦理,從不假手旁人。此番欽奉諭旨考試屬員,原爲拔取真材,共求治理。在爾各員應如何格恭將事,爭自濯磨,以副朝廷孜孜求治之盛意。乃候補知府某人,臨期不到,已難免疏忽之愆;復經當場拿獲瘋子某某,其時衆議沸騰,僉稱槍手。是以特發首府,嚴行審訊。旋經該府訊明某守是日有病,某某確有瘋疾,取具醫生甘結,並該瘋子家屬供詞,稟請核辦前來。本部院辦事頂真,猶難憑信,爲此諭爾各守、丞、府知悉:凡是日與考各員,苟有真知灼見,確能指出槍替實據者,務各密告首府,匯稟本部院,親自提訊。一經證實,立刻按律嚴懲。飾吏治而拔真材,在此一舉,本部院有厚望焉!特諭。”
這個手諭帖了出來,就有些妒忌那位知府的,又有些當場拿人的,各人有各人的主意,有的是泄憤,有的想露臉,竟有兩個人寫了稟帖去交給首府代遞。次日衙期,一齊到了官廳。頭一個上來拿稟帖交給了首府。首府大略一看,一面讓坐,一面拿那人渾身打量一番,慢慢的講道:“事情呢,本來不錯,就是兄弟也曉得並不冤枉。但是一樣:誰不曉得他是撫臺少爺的親戚,我們何苦同他做這個冤家呢。況且就是拿他參掉,剩下來的差使未必就派到你我,而且我們的名字他老人家倒永遠記在心上,據我兄弟看來,諸君很可不必同他多此一個痕跡。果然諸君一定要兄弟代遞,兄弟原不能不遞。但是朋友有忠告之義,愚見所及,安敢祕而不宣。諸君姑且斟酌斟酌再遞何如?”大家聽了首府的話,想想不錯。有些稟帖還沒有出手的一齊縮了回來。就是已把稟帖交給首府的,到此也覺後悔,朝着首府打恭作揖,連稱“領教”,也把那稟帖抽了回來。首府又細加探聽,內中有幾個心上頂不服的,把他們的名字一齊開了單子送給撫臺。
撫臺見手諭帖出了兩天沒有說話,便按照着首府的詳文辦理,略謂:
“某守臨期因病不到,雖非有心規避,究屬玩視,着記大過三次。瘋子暫行監禁,俟其病痊,方待其家人領回。”
一面繕牌曉諭,一面已把前天所考的府、廳一班分別等第,榜示轅門。凡早首府開進來的單子,想要攻訐他兒子妻舅的幾個名字,一齊考在一等之內,三名之後。這班人得了高第,無不頌稱中丞拔取之公。次日一齊上院叩謝。其實弄到後來,前三名仍是撫臺的私人。第一名,委了一個缺出去;二三名都派了一個差使;三名之後,毫無動靜,空歡喜了一陣,始終未得一點好處。至於那位記過的雖然一面記過,一面仍有三四個差使委了下來。衆人看了他雖不免作不平之鳴,畢竟奈何他不得。
只因這一番作爲,撫臺深感首府斡旋之功,拿他器重的了不得。未久就保薦他人材,將他送部引見。引見之後,過班道臺,仍歸本省補用,並交軍機處存記。領憑到省,稟見撫臺,第二天就委了全省學務處、洋務局、營務處三個闊差使,又兼院上總文案。
且說這位觀察公,姓單,號舟泉,爲人極其漂亮,又是正途出身。俗語說得好:“一法通,百法通。”他八股做得精通,自然辦起事來亦就面面俱到了。他自從接了這四個差使之後,一天到晚真正是日無暇晷,沒有一天不上院。撫臺極其相信他固不必說,他更有一種本事,是一天到晚同撫臺在一處,凡是撫臺的說的話他總答應着,從來不作興說一句“不是”的。
有天撫臺爲了一件甚麼交涉事件牽涉法國人在內,撫臺寫錯了,寫了英國人了。撫臺自己謙虛,拿着這件公事同他商量,問他可是如此辦法。他明明曉得撫臺把法國的“法”字錯寫做英國的“英”字,他卻並不點穿,只隨着嘴說:“極是。”撫臺心上想:“某字同某人商量過,他說不錯一定是不錯的了。”便發到洋務文案上照辦。幾個洋務文案奉到了這件公事,一看是撫臺自己寫的,自然是分頭趕辦。等到仔細校對起來,法國人的事牽到英國人身上,明明是撫臺一時寫錯,然而撫臺寫的字不敢提筆改,只得捧了公事上來請教老總。單道臺道:“這個我何曾不曉得是中丞寫錯。但是在上憲跟前,我們做屬員的如何可以顯揭他的短處。兄弟亦正爲此事躊躇。”
此時單道臺一面說,一面四下一看,只見文案提調、候補知府、旗人崇志,綽號崇二馬糊的,還沒有散,便把手一招,道:“崇二哥,快過來!這事須得同你商量。”崇二馬糊忙問何事。單道臺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又道:“現在別無辦法,只有託你二哥明天拿這件公事另外寫一分,夾在別的公事當中送上去,請他老人家的示,看他怎麼批。料想鬧錯過一回,斷乎不會回回都鬧錯的。”
提調:清代在非常設的機構中負責處理內部事務的官員。
崇二馬糊雖然馬糊,此時忽然明白過來,忙說道:“回大人的話:這件公事,大帥今天才發下來,明天又送上去,不怕他老人家動氣?又該說咱們不當心了。”單道臺發急道:“我們文案上碰個釘子算什麼!差使當的越紅,釘子碰的越多,總比你當面回他說大人寫錯了字的好。況且他一省之主,肯落這個的把柄在我們手裏嗎。還是照我辦的好。”崇二馬糊拗他不過,只得依他。等到了第二天送公事上去,果然又把這件公事夾在裏面。撫臺一面翻看,一面說話。後來又翻到這件,忽然說道:“這個我昨天已經批好交代單道臺的了。”崇二馬糊不響。撫臺又說一遍。崇二馬糊回稱:“這是單道說的,還得請請大帥的示。”撫臺心上想:“難道昨兒批的那張條子,他失落掉不成?”於是又重批一條。誰知那個法國人的“法”字依舊寫成英國的“英”字。一誤再誤,他自己實實在在未曾曉得。等到下來,崇二馬糊把公事送給單道臺過目。單道臺看到這件,只是皺眉頭,也不便說什麼。爲的旁邊的人太多,他做屬員的人,如何可以指斥上憲之過,倘或被旁邊人傳到撫臺耳朵裏去,如何使得!看過之後放在一邊。
等了半天,打聽得撫臺一個人在簽押房裏,他便袖了這件公事,一個人走到撫臺跟前,一掀門簾,正見撫臺坐在那裏寫信。他進來的腳步輕,撫臺沒有聽見。他見撫臺有事,便也不敢驚動,袖了公事,站在當地,一站站了一點鐘。撫臺因爲要茶喝,喊了一聲“來”,猛然把頭擡起,纔看見了單道臺。問他幾時來的,有什麼事情。單道臺至此方纔卑躬屈節的口稱:“職道才進來,因見大帥有公事,所以不敢驚動。”撫臺一面封信,一面讓他坐。等信封完,然後慢慢的提到公事。倒是撫臺先說:昨天一件什麼事,“不是我兄弟已經同老哥商量好了,批了出去,叫他們照辦嗎?他們今天又上來問我。你看他們這些人可糊塗不糊塗!”
單道臺道:“非但他們糊塗,職道學問疏淺,實在亦糊塗得狠。就是昨天那件公事,大帥一定曉得這外國人的來歷,一定是把英國人,不是法國人。職道猜這件公事,他們底下總沒有弄清,一定是英國人寫做法國人了。大人明鑑萬里,所以替他們改正過來的。”撫臺聽了,楞了一楞,說:“那件公事你帶來沒有?”單道臺回稱:“已帶來。”就在袖筒管裏把那件公事取了出來,雙手奉上,卻又板着面孔,說道:“法國人在中國的不及英國人多,所以職道很疑心這樁事一定是英國人,大帥改的一點不錯。”
撫臺亦不答腔,接過公事,從頭至尾瞧了遍,忽然笑道:“這是我弄錯了,他們並沒有錯。”單道臺故作驚惶之色道:“倒是他們不錯?這個職道倒有點不相信了。”立刻接過公事,又仔細端詳看一遍,一面點頭,一面咂嘴弄舌的,自言自語了一回,又說道:“果真是法國人。不是大帥改過來,職道一輩子也纏他不清。職道下去立刻就吩咐他們照着大帥批的去辦。”撫臺道:“這事已耽誤了一天了,趕快催他們去辦罷。”
單道臺諾諾連聲,告退下去。回到文案上,朝着崇二馬糊一班人說道:“你們不要瞧着做官容易,伺候上司要有伺候上司的本領!照着你們剛纔的樣子,就是公事送上去十回,不但改不掉,還要碰下來!”崇二馬糊道:“依着卑府是要在那寫錯字的旁邊貼個紅籤子送上去,等他老人家自己明白。”單道臺道:“這個尤其不可!只有殿試、朝考,閱卷大臣看見卷子上有了什麼毛病,方纔貼上個籤子以做記號。我是過來人,還有什麼不曉得。如今我們做他下屬,倒反加他籤子,賽如當面罵他不是,斷斷使不得!《中庸》上有兩句話我還記得,叫做:‘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什麼叫‘獲上’?就說會巴結,會討好,不叫上司生氣。如果不是這個樣子,包你一輩子不會得缺,不能得缺那裏來的黎民管呢?這便是‘民不可得而治矣’的註解。”
單道臺正說得高興,崇二馬糊是有點馬馬糊糊,也不管什麼大人、卑府,一定要請教;“剛纔大人上去是同大帥怎麼講的,怎麼大帥肯自己認錯改正過來?求求大人指示,等卑府將來也好學點本事。”單道臺閉着眼睛,說道:“這些事可以意會,不可言傳,要說一時亦說不了許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諸公隨時留心,慢慢的學罷了。”
又過了些時,首縣稟報上來:有一個遊歷的外國人,因爲上街買東西,有些小孩子拉住他的衣服笑他。那個洋人惱了,就把手裏的棍子打那孩子,那孩子躲避不及,一下子打到太陽穴上,是個致命傷的所在,那孩子就躺在地下,過了一會就沒有氣了。那個孩子的父母自然不肯干休,一齊上來,要扭住外國人。外國人急了,舉起棍子一陣亂打,旁邊看的人很有幾個受傷的。街坊上衆人起了公憤,一齊奮勇上前,捉住了外國人,奪去他手裏棍子,拿繩子將他手腳一齊捆了起來,穿根扁擔,把他扛到首縣喊冤。首縣一聽,人命關天,這一驚非同小可!等到仔細一問,才曉得兇手是外國人,因想:“外國人不是我知縣大老爺可以管得的。”立刻吩咐一干人下去候信。當時屍也不驗,立刻親自上院請示。
撫臺見了面,問知端的,曉得是交涉重案,事情是不容易辦的,馬上傳單道臺商量辦法。單道臺問:“打死的兇手既是個外國人,到底那一國的?查明白了,可以照會他該管領事,商量辦法。”首縣見問,呆了半天,方掙扎着說道:“橫豎外國人就是了。卑職來的匆促,卻忘記問得。”撫臺又問:“打殺的是個什麼人?”首縣說:“是個小孩子。”撫臺道:“我亦曉得是個小孩子!到底他家裏是個做什麼的?”首縣道:“這個卑職忘記問他們,等卑職下去問過了他們再上來稟覆大帥。”
撫臺罵他糊塗,叫馬上去查明白了再來。首縣無奈,只得退去。回到衙門,把籤稿二爺叫上來哼兒哈兒罵了一頓,罵他糊塗:“不把那小孩子的家計同兇手是那一國的人查明白了回我,如今撫臺問了下來,叫我無言可對!真正糊塗!趕緊去查!”籤稿門下來,照樣把地保罵了一頓,地保又出去追問苦主,方纔曉得是豆腐店的兒子,是個小戶人家,沒有什麼大手面的。後來又問到外國人,大家都不懂他說話。首縣急了,曉得本城紳士龍侍郎新近亦沾染了維新習氣,請了外國回來的洋學生在家裏教兒子讀洋書,打算請了他來,充當翻譯。馬上叫人拿片子去請。等了半天,去人空身回來,說是:“龍大人那裏洋師爺半個月前頭就進京去考洋翰林去了。”首縣正在爲難,齊巧院上派人下來,說:“把外國兇手先送到洋務局裏安置。等到問明之後,照會他本國領事,再商辦法。”首縣聞言,如釋重負,趕忙前去驗屍,提問苦主、鄰右,疊成文書,申詳上憲。
閒話少敘。原來這事全是單道臺一個人的主意。他同撫臺說:“我們長沙並沒有什麼領事。這個外國人是爲遊歷來的,如今打死了人,倘若不辦他,地方上百姓一定不答應。若說是拿他來抵罪,我們又沒有這樣的治外法權,可以拿着本國的法律治別國的人。想來想去,這兇手放在縣裏總不妥當。倘或在班房裏叫他受點委曲,將來被他本國領事說起話,總是我們不好。不如把他軟禁在職道局子裏,不過多化幾個錢供應他。等到他本國領事迴文來,看是如何說法,再商量着辦,請請大帥的示,看是怎樣?”撫臺連說:“很好。……”所以單道臺下來,立刻就派人到首縣裏去提人的。當下人已提到,局子裏有的是翻譯,立刻問他是那一國的人,甚麼名字。幸虧鄰省湖北漢口就有他該管領事,可以就近照會。馬上又回明撫臺,詳詳細細由撫臺打了一個電報給湖廣總督,託他先把情節告訴他本國領事,再彼此商量辦法。
這位單道臺辦事一向是面面俱到,不肯落一點褒貶的。他說:“這事是人命關天,況且兇手又是外國人,湖南省的闊人又多,如果一個辦的不得法,他們說起話來,或是聚衆同外國人爲難起來,到這時節,拿外國人辦也不好,不辦也不好。不如先把官場上爲難情形告訴他們,請他們出來替官場幫忙。如此一來,他們一定認做官場也同他們一氣,紳士、百姓一邊就好辦了。但是一件:外國領事一定不是好纏的。外國人打死了人,雖然不要抵命,然而其勢也不能輕輕放他回去。但是如今我們說定這外國人一個什麼罪名,領事亦決計不答應。此時卻用着他們紳士、百姓了。等他們大衆動了公憤,出頭同領事硬爭,領事見動了衆,自然害怕。再由我們出去壓服百姓,叫百姓不要鬧。百姓曉得我們官場上是幫着他們的,自然風波容易平定。那時節兇手的罪名也容易定了,百姓自然也沒得說了,外國領事還要感激我們。內而外部,外而督、撫,見你有如此才幹,誰不器重,真是無上妙策!”主意打定,立刻就想坐了轎子去拜幾個有權勢的鄉紳,探探他們口氣,好借他們做個幫手。
正待上轎,已有人前來報稱:“衆紳士因爲此事,說洋務局不該不把外國兇手交給縣裏審問,如今倒反拿他留在局中,十分優待,因此衆人心上不服,一齊發了傳單,約定明日午後兩點鐘在某處會議此事。又聽說一共發了幾千張傳單,通城都已發遍。將來來的人一定不少,還恐怕愚民無知,因此鬧出事來。”
單道臺聽了,馬上三步並做兩步,上了轎,又吩咐轎伕快走。什麼葉閣學、龍祭酒、王侍郎,幾個有名望的,他都去拜過。只有龍祭酒門上回感冒未見,其餘都見着的。見了面,頭一個王侍郎先埋怨官場上太軟弱,不應該拿兇手如此優待,如今大衆不服,生怕明天鬧出事情出來,彼此不便。好個單道臺,聽了王侍郎這番說話,連說:“這件事職道很替死者呼冤!……一定要稟明上憲,照會領事,歸我們自家重辦。好替百姓出這口氣!”
王侍郎道:“既然曉得百姓死的冤枉,極該應把兇手發到縣裏,叫他先喫點苦頭,也好平平百姓的氣。”單道臺湊近一步道:“大人明鑑:我們做官的人只好按照約章辦理。無論他是那一國的人,都得交還他本國領事自辦。面子上那能說句違約的話呢?但是職道卻有一個愚見:這個兇手如今無故打死了我們中國人,倘若就此輕輕放他過去,不但百姓不服,就是撫憲同職道,亦覺於心不忍。所以職道很盼大人約會大衆幫着出力,等到領事來到此地,同他竭力的爭上一爭。倘若爭得過來,一來伸了百姓的冤,二來也是我們的面子。就是京裏曉得了,這是迫於公憤的事,也不能說什麼話。”王侍郎道:“官不幫忙,只叫我們底下出頭,這是還有用嗎?”單道臺發急道:“職道何嘗不出力!要說不出力也不趕着來同大人商量了。”一席話竟把王侍郎……一班紳士拿單道臺當作了好官,說他真能衛護百姓。登時傳遍了一個湖南省城,竟沒有一個不說他好的。
單道臺又恐怕底下聚了多少人,真要鬧點事情出來,倒反棘手。過了一天,因爲王侍郎是省城衆紳衿的領袖,於是又來同王侍郎商議。見面之後,先說:“接到領事電報,一定要我們把兇手護送到漢口,歸他們自己去辦。是職道同撫憲說明,一定不答應他。現在撫臺又追了一封電報去,就說百姓已經動了公憤,叫他趕緊到這裏,彼此商量辦法,以保兩國睦誼。如今電報已打了去,還沒有回電來,不曉得那邊怎麼樣。卑職深怕大人這邊等得心焦,所以特地過來送個信。總望大人傳諭衆紳民,叫他們少安毋躁,將來這事官場上一定替他們作主,決不叫死者含冤。所慮官場力量有時而窮,不得不借衆力以爲挾制地步;究竟到了內地,他們勢孤總可以強他就我。所以動衆一事,大人明鑑,只可有其名而無其實。倘或聚衆人多了,外國人有個一長兩短,豈不是於國際上又添了一重交涉麼?”
此時,王侍郎本系丁憂在家,剛剛服滿,頗有出山之意。一聽這話,深以爲然。但是於自己鄉親面上不能不做一副激烈的樣子,說兩句激烈的話,以顧自己面子,其實也並不是願意多事的人。當下聽了單道臺的話,連稱“是極”。等到單道臺去後,他那些鄉親前來候信,王侍郎只勸他們不可聚衆,不可多事,將來領事到來,撫臺一定要替死者伸冤。他是一鄉之望,說出來的話,衆人自然沒有不聽的,果然一連平定了三天。
等到第四天,領事也就到了。領事只因奉到了駐京本國公使的電報,叫他親赴長沙,會審此案,所以坐了小輪船來的。地方官接着,自不得不按照條約以禮相待,預備公館,請喫大菜。一切煩文不用細述。等到講到了命案,單道臺先同來的領事說:“我們中國湖南地方,百姓頂蠻,而且從前打‘長毛’全虧湖南人,都是些有本事的。他們爲了這件事情,百姓動了公憤,一定也要把兇手打死,以爲死者伸冤。兄弟聽見這個信,急的了不得,馬上稟了撫臺,調了好幾營的兵,晝夜保護,才得無事,不然,那兇手還能活到如今等貴領事來嗎!”領事道:“這個條約上有的,本應該歸我們自己懲辦;倘若兇手被百姓打死了,我只問你們貴撫臺要人。”
單道臺道:“這個自然,不特此也,百姓聽見貴領事要到此地,早已商量明白,打算一齊哄到領事公館裏,要求貴領事拿兇手當衆殺給他們看。百姓既不動蠻,不能說百姓不是。他們動了公憤,就是地方官亦無可如何。不知貴領事到了這個時候是個怎麼辦法?”領事聽了他這番話,一想:“現在我們勢孤,倘真百姓鬧起事來,也須防他一二。”但是面子上又不肯示人以弱,呆了一呆,說道:“貴道臺如此說法。兄弟馬上先打個電報給我們的駐京公使,叫他電回本國政府,趕快派幾條兵輪上來。倘若百姓真要動蠻,那時敝國卻也不能退讓。”
單道臺一聽領事如此說法。亦就正言厲色的說道:“貴領事且不要如此說法。敝國同貴國的交誼,固然要顧;然而百姓起了公憤,就是敝國政府亦不能禁壓他們,何況兄弟。以前是貴領事未到,百姓幾次三番想要鬧事,都是兄弟出去勸諭他們。又告訴他們聽:“將來領事到來,自能秉公辦理,爾等千萬不可多事。”又告訴他們,貴領事今天初到這裏,他們已聚了若干的人,想來問信,又是兄弟拿他們解散。若非兄弟出力,早已鬧出事來,貴領事那裏還能平平安安在這裏談天。就是打電報去調兵船,只怕遠水亦救不得近火。如今各事且都丟開不講,但說這個兇手,論他犯的罪名是‘故殺’,照敝國律例是要抵擬的。但不知貴領事此番前來,作何辦理?”
領事道:“是‘故殺’不是‘故殺’,總得兄弟問過犯人一次,方能作準。就是‘故殺’,敝國亦無擬抵的罪名,大約不過監禁幾個月罷了。”單道臺道:“辦的輕了,恐怕百姓不服。”領事道:“貴國的人口很多,貴國的新學家做起文章來或是演說起來,開口‘四萬萬同胞’,閉口‘四萬萬同胞’,打死一個小孩子值得什麼,還怕少了百姓嗎?”單道臺一聽領事說的話,明明奚落中國,有心還要駁他幾句,迴心一想:“彼此翻了臉,以後事情倒反難辦。我橫豎打定主意,兩面做個好人。只要他見情於我,我又何苦同他做此空頭冤家呢。”想罷,便微微一笑,暫別過領事,又回到王侍郎家裏,把他見了領事,如何辯駁,如何要求,添了無數枝葉。不曉得的人聽了都當真正是個好官,真能夠迴護百姓。後來大衆問他:“到底辦這外國人一個什麼罪名?”單道臺道:“這個還要磋磨起來看。”
單道臺此時也深曉得領事與紳士兩面的事不容合在一處的。但是面子上見了領事不能不裝出一副害怕的樣子,說百姓如何刁難,如何挾制;“如果不是我在裏頭彈壓住他們,早晚他們一定鬧點事情出來。”只要說得領事害怕,自然可望移船就岸。見了紳士,又做出一副慷慨激烈的樣子,說道:“我們中國是弱到極點的了!兄弟實在氣憤不過!如今我們還沒有同他爲難,聽說他要把諸公名字開了清單,寄給他們本國駐京公使,說是這樁命案全是諸公鼓動百姓與他爲難,拿個聚衆罪名輕輕加在諸公身上。將來設有一長兩短,百姓人多,他查不仔細,諸公是不得免的!”
幾個紳士一聽這話,起先是靠了大衆公憤,故而敢與領事抵抗;如今聽說要拿他們當作出頭的人,早已一大半都打了退堂鼓了。反有許多不懂事的人,私底下去求單道臺,求他想了個法子,不要把名字叫領事知道方好。因此幾個週轉,領事同紳士都拿單道臺當做好人。
當下拿兇手問過兩堂,定了一個監禁五年罪名。據領事說:照他本國律例,打死一個人,從來沒有監禁到五個年頭的,這是格外加重。撫臺及單道臺都沒有話說。單道臺還極力恭維領事,說他能顧大局,並不袒護自己百姓,好叫領事聽了喜歡,及至他見了紳士,依舊是義形於色的說道:“雖然兇手定了監禁五年的罪名,照我心上,似乎覺得辦的太輕,總要同他磋磨,還要加重,方足以平諸公之氣!”這番話,他自己亦明曉得已定之案,決計加重不爲,不過姑妄言之,好叫百姓說他一個“好”字。至於紳士,到了此時,一個個都想保全自己功名,倒反掉轉頭來勸自己的同鄉說:“這位領事能夠把兇手辦到這步地位,已經是十二分了。況且有單某人在內,但凡可以替我們幫忙,替百姓出氣的地方,也沒有不竭辦的。爾等千萬不可多事!”百姓見紳士如此說法,大家誰肯多事。一天大事,瓦解冰銷,竟弄成一個虎頭蛇尾!
只有單道臺卻做了一個面面俱圓:撫臺見面誇獎他,說了能辦事;領事心上也感激他彈壓百姓,沒有鬧出事來,見了撫臺亦很替他說好話;至於紳衿一面,一直當他是迴護百姓的,更不消說得了。自從出事之後,頂到如今,人人見他東奔西波,着實辛苦,官廳子上,有些同寅見了面,都恭維他“能者多勞”。單道臺得意洋洋的答道:“忙雖忙,然而並不覺得其苦。所謂‘成竹在胸’,凡事有了把握,依着條理辦去,總沒有辦不好的。”人家問他有甚麼訣竅。他笑着說道:“此是不傳之祕,諸公領悟不來,說了也屬無益。”人家見他不肯說,也就不肯往下追問了。
又過了些時,領事因事情已完,辭行回去。地方官照例送行,不用細述。誰知這回事,當時領事只認定百姓果然要鬧事,幸虧單道臺一人之力,得以壓服下來。當時在湖南雖隱忍不言,過後想想,心總不甘,於是全歸咎於湖南紳衿。又說撫臺不能鎮壓百姓,由着百姓聚衆,人太軟弱,不勝巡撫之任。至於幾個爲首的紳衿,開了單子,稟明駐京公使,請公使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詰責,定要辦這幾個人的罪名。又要把湖南巡撫換人。因此外國公使便向總理衙門又駁出一番交涉來。要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