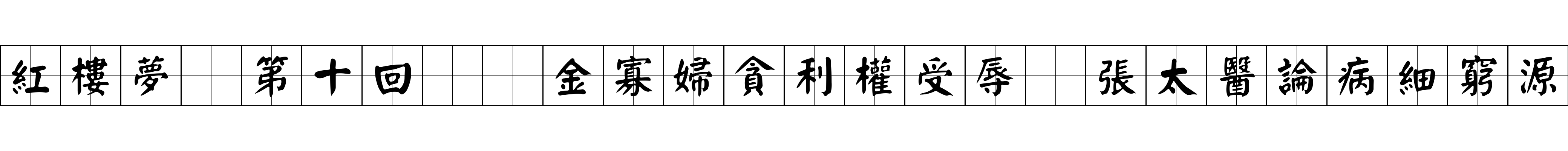紅樓夢-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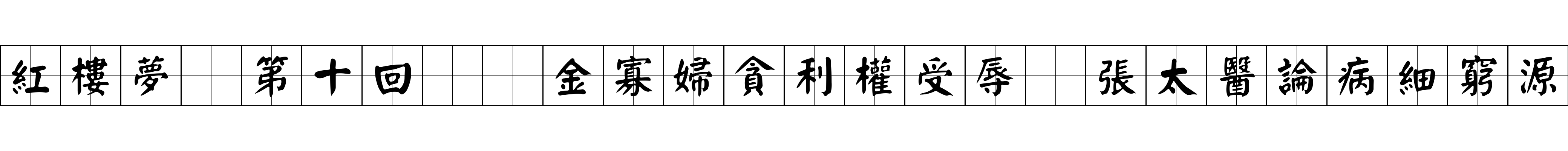
紅樓夢以錯綜複雜的清代上層貴族社會爲背景,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爲主線,通過對賈、史、王、薛四大家族榮衰的描寫,展示了18世紀上半葉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方方面面,囊括了多姿多彩的世俗人情,可謂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長篇小說。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鍾磕了頭,寶玉方纔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鐘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和他好,他就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的撞在我眼睛裏。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
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嘟嘟的說,因問道:“你又要爭什麼閒氣?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問他們西府裏的璉二奶奶跟前說了,你才得了這個唸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咱們家裏還有力量請得起先生?況且人家學裏,茶也是現成的,飯也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那裏唸書,家裏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不是因你在那裏唸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不給不給,這二年也幫了咱們有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再要找這麼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玩一會子睡你的覺去,好多着呢。”於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他自去睡了。次日仍舊上學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他姑娘,原聘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裏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着些小的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裏去請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並尤氏,所以鳳姐、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
卻說這日賈璜之妻金氏因遇天氣晴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裏走走,瞧瞧寡嫂並侄兒。閒話之間,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學房裏的那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一時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鍾小崽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都別忒勢利了,況且都做的是什麼有臉的好事!就是寶玉,也犯不上向着他到這個地。等我去到東府瞧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向秦鍾他姐姐說說,叫她評評這個理。”這金榮的母親聽了這話,急得了不得,忙說道:“這都是我的嘴快,告訴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別說去去,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起來,怎麼在那裏站得住?若是站不住,家裏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倒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聽了,說道:“那裏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她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就坐上往寧府裏來。
到了寧府,進了車門,到了東邊小角門前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之妻尤氏。也未敢氣高,殷殷勤勤敘過寒溫,說了些閒話,方問道:“今日怎麼沒見蓉大奶奶?”尤氏說道:“她這些日子不知怎麼着,經期有兩個多月沒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了下半天就懶待動,話也懶待說,眼神也發眩。我說她:‘你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好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一家兒來,有我呢。就有長輩們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掯她,不許招她生氣,叫她靜靜的養養就好了。她要想什麼喫,只管到我這裏取來。倘或我這裏沒有,只管望你璉二嬸子那裏要去。倘或她有個好歹,你再要娶這麼一個媳婦,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情的人兒,打着燈籠也沒地方找去。’她這爲人行事,哪個親戚、哪個一家的長輩不喜歡她?所以我這兩日好不煩心,焦得我了不得。偏偏今兒早晨她兄弟來瞧他,誰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大爽快,就有事也不當告訴她,別說是這麼一點子小事,就是你受了一萬分的委曲,也不該向她說纔是。誰知他們昨兒學房裏打架,不知是那裏附學來的一個人欺侮了他了。裏頭還有些不乾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嬸子,你是知道那媳婦的,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會行事兒,她可心細,心又重,不拘聽見個什麼話兒,都要度量個三日五夜才罷。這病就是打這個秉性上頭思慮出來的。今兒聽見有人欺負了她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羣混帳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調三惑四的那些個;氣的是她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裏吵鬧。她聽了這事,今日索性連早飯也沒喫。我聽見了,我方到她那邊安慰了她一會子,又勸解了她兄弟一會子。我叫她兄弟到那邊府裏找寶玉去了。我纔看着她吃了半盞燕窩湯,我纔過來了。嬸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且如今又沒個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我心裏倒像針扎似的。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
金氏聽了這半日話,把方纔在她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論理的盛氣,早嚇得都丟在爪窪國去了。聽見尤氏問她知道有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這麼聽着,實在也沒聽見人說有個好大夫。如今聽起大奶奶這個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倒別教人混治。倘或認錯了,這可是了不得的!”尤氏道:“可不是呢。”正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向尤氏問道:“這不是璜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道:“讓這大妹妹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就過那屋裏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說秦鍾欺負了她侄兒的事,聽見秦氏有病,不但不能說,亦且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又待得很好,反轉怒爲喜的,又說了一會子話兒,方家去了。
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她來,有什麼說的事情麼?”尤氏答道:“倒沒說什麼。一進來的時候,臉上倒像有些着了惱的氣色似的,及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這病,她倒漸漸的氣色平定了。你又叫讓她喫飯,她聽見媳婦這麼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了幾句閒話兒就去了,倒沒有求什麼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到哪裏尋個好大夫來給她瞧瞧要緊,可別耽誤了!現今咱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裏要得,一個個都是聽着人的口氣兒,人怎麼說,他也添幾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倒殷勤得很,三四個人一日輪流着,倒有四五遍來看脈。他們大家商量着立個方子,吃了也不見效,倒弄得一日換四五遍衣裳,坐起來見大夫,其實於病人無益。”賈珍說道:“可是。這孩子也胡塗,何必脫脫換換的,倘或了涼,更添一層病,那還了得!衣裳任憑是什麼好的,可又值什麼!孩子的身子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麼。我正進來要告訴你:方纔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才告訴他說,媳婦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因爲不得個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礙無妨礙,所以我這兩日心裏着實着急。馮紫英因說起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的,更兼醫理極深,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來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這麼看來,竟是合該媳婦的病在他手裏除災,亦未可知。我即刻差人拿我的名帖請去了。今日倘或天晚了不能來,明日想必一定來。況且馮紫英又即刻回家,親自去求他,務必叫他來瞧瞧。等這個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
尤氏聽了,心中甚喜,因說道:“後日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麼辦?”賈珍說道:“我方纔到了太爺那裏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來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願意往你們那樣是非場中去鬧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衆人些頭,莫過你把我從前注的《陰騭文》給我叫人好好的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強百倍呢。倘或後日這兩日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裏好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要來,又跟隨多少人來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又說,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來升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人叫了賈蓉來:“吩咐來升照舊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裏去請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和你璉二嬸子來逛逛。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業已打發人請去了,想必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一一的答應出去了。
正遇着方纔去馮紫英家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方纔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的名帖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纔這裏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纔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脈。’他說等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他‘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我們馮大爺和府上的大人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實不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罷。”賈蓉復轉身進去,回了賈珍、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升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升聽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
且說次日午間,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之至,小弟不勝欽仰!”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本知見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顏汗。”賈珍道:“先生何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
於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賈蓉居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說一說再看脈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的意思,竟先看過脈,再說的爲是。我是初造尊府的,本也不曉得什麼,但是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脈息,看小弟說得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脈息,可治不可治,以便使家父母放心。”於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枕來,一面給秦氏靠着,一面拉着袖口,露出手腕來。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脈上,調息了至數,寧神細診了半刻的工夫;方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脈息,說道:“我們外邊坐罷。”
賈蓉於是同先生到外邊屋裏炕上坐了,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於是陪先生吃了茶,遂問道:“先生看這脈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這脈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需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需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剋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必然肋下疼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剋制者,必然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痠軟。據我看,這脈息應當有這些症候纔對。或以這個脈爲喜脈,則小弟不敢聞命矣。”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的如神,倒不用我們告訴了。如今我們家裏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着呢,都不能說得這麼當真切。有一位說是喜,有一位說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那位說怕冬至,總沒有個準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指示。”
那先生笑道:“大奶奶這個症候,可是那幾位耽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時後就用藥治起來,不但斷無今日之患,而且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耽誤到這個地位,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來,這病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這藥看,若是夜間睡得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脈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但聰明太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的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都長過。”先生聽了道:“妙啊!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夠以養心調經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木旺的症候來。待用藥看看。”於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蔘二錢。白朮二錢,土炒。雲苓三錢。熟地四錢。歸身二錢,酒洗。白芍二錢,炒。川芎錢半。黃?三錢。香附米二錢,制醋柴胡八分。懷山藥二錢,炒。真阿膠二錢,蛤粉炒。延胡索錢半,酒炒。炙甘草八分。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紅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得很。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
於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脈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說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這麼痛快,想必用藥也不錯。”賈珍道:“人家原不是混飯喫的久慣行醫的人。因爲馮紫英與我們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來的。既有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蔘,就用前日買的那一斤好的罷。”賈蓉聽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喫。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