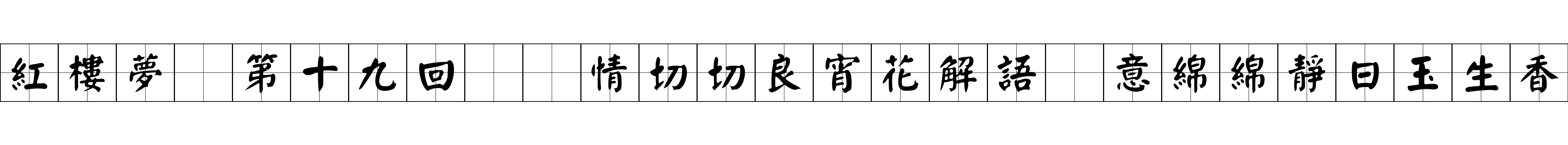紅樓夢-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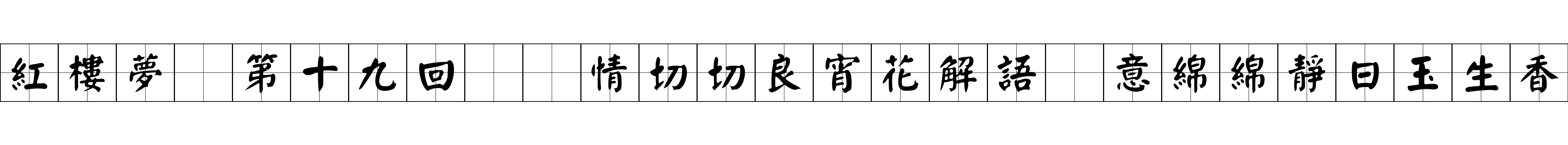
紅樓夢以錯綜複雜的清代上層貴族社會爲背景,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爲主線,通過對賈、史、王、薛四大家族榮衰的描寫,展示了18世紀上半葉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方方面面,囊括了多姿多彩的世俗人情,可謂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長篇小說。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並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綵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不必細說。
且說榮、寧二府中,因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安躲靜,獨她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掙着與無事的人一樣。第一個寶玉是極無事最閒暇的。偏這日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喫年茶,晚間才得回來。因此,寶玉只和衆丫頭們擲骰子、趕圍棋作戲。正在房內玩得沒興頭,忽見丫頭們來回說:“東府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燈。”寶玉聽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喫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自己回過賈母,過去看戲。
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子牙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甚至於揚幡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滿街之人個個都贊:“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寶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開各處閒耍。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和丫鬟、姬妾說笑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枚行令,百般作樂,也不理論,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裏邊去了,故也不問。至於跟寶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才散,因此得空也有去會賭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喫年茶的,更有或嫖或飲的,都私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些的,都鑽進戲房裏瞧熱鬧去了。
寶玉見一個人沒有,因想:這裏素日有個小書房,內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畫得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裏自然無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她一回。想着,便往書房裏來。剛到窗前,聞得房內有呻吟之韻。寶玉倒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乃乍着膽子,舔破窗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卻不曾活,卻是茗煙按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腳踹進門去,將那兩個唬開了,抖衣而顫。
茗煙見是寶玉,忙跪求不迭。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雖不標緻,倒還白淨,些微亦有動人之處,羞得臉紅耳赤,低頭無言。寶玉跺腳道:“還不快跑!”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去了。寶玉又趕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急得茗煙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因問:“那丫頭十幾歲了?”茗煙道:“大不過十六七歲了。”寶玉道:“連她的歲屬也不問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她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又問:“名字叫什麼?”茗煙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真新鮮奇文,竟是寫不出來的。據她說,她母親養她的時節做了個夢,夢見得了一匹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卍字的花樣,所以他的名字叫作卍兒。”寶玉聽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她將來有些造化。”說着,沉思一會。
茗煙因問:“二爺爲何不看這樣的好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逛逛就遇見你們了。這會子作什麼呢?”茗煙嘻嘻笑道:“這會子沒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逛逛去,一會子再往這裏來,他們就不知道了。”寶玉道:“不好,仔細花子拐了去。或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熟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來。”茗煙道:“熟近地方,誰家可去?這卻難了。”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咱們竟找你花大姐姐去,瞧她在家作什麼呢。”茗煙笑道:“好,好!倒忘了她家。”又道:“若他們知道了,說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寶玉道:“有我呢。”茗煙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
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半里路程,展眼已到門前。茗煙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彼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幾個侄女兒來家,正喫果茶。聽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唬得驚疑不止。連忙抱下寶玉來,在院內嚷道:“寶二爺來了!”別人聽見還可,襲人聽了,也不知爲何,忙跑出來迎着寶玉,一把拉着問:“你怎麼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瞧你作什麼呢。”襲人聽了,才放下心來。嗐了一聲,笑道:“你也忒胡鬧了,可作什麼來呢!”一面又問茗煙:“還有誰跟來?”茗煙笑道:“別人都不知,就只我們兩個。”襲人聽了,復又驚慌,說道:“這還了得!倘或碰見了人,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車碰,馬轎紛紛的,若有個閃失,也是玩得的!你們的膽子比鬥還大。都是茗煙調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嬤嬤們打你。”茗煙撅了嘴道:“二爺罵着打着,叫我引了來,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說別來罷,――不然我們還去罷。”花自芳忙勸:“罷了,已是來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檐草舍,又窄又髒,爺怎麼坐呢?”
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來。襲人拉了寶玉進去。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慚慚的。花自芳母子兩個百般怕寶玉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果桌,又忙倒好茶。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果子也不用擺,也不敢亂給東西喫。”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鋪在一個杌上,寶玉坐了;用自己的腳爐墊了腳;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焚上,仍蓋好,放與寶玉懷內;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彼時,她母兄已是忙另齊齊整整擺上一桌子果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喫之物,因笑道:“既來了,沒有空去之理,好歹嘗一點兒,也是來我家一趟。”說着,便拈了幾個松子瓤,吹去細皮,用手帕託着送與寶玉。
寶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因悄問襲人:“好好的哭什麼?”襲人笑道:“何嘗哭,才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當下寶玉穿著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掛。襲人道:“你特爲往這裏來又換新服,她們就不問你往哪裏去的?”寶玉笑道:“珍大爺那裏去看戲換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個地方不是你來的。”寶玉笑道:“你就家去纔好呢,我還替你留着好東西呢。”襲人悄笑道:“悄悄的,叫他們聽着什麼意思。”一面又伸手從寶玉項上將通靈玉摘了下來,向她姊妹們笑道:“你們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希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可盡力瞧了。再瞧什麼希罕物兒,也不過是這麼個東西。”說畢,遞與她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寶玉掛好。又命她哥哥去,或僱一乘小轎,或僱一輛小車,送寶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爲不妨,爲的是碰見人。”
花自芳忙去僱了一頂小轎來,衆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果子與茗煙,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教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直送寶玉至門前,看着上轎,放下轎簾。花、茗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煙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等我同二爺還到東府裏混一混,纔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聽說有理,忙將寶玉抱出轎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說:“倒難爲你了。”於是仍進後門來。俱不在話下。
卻說寶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丫鬟們都越性恣意的玩笑,也有趕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瓜子皮。偏奶母李嬤嬤拄拐進來請安,瞧瞧寶玉,見寶玉不在家,丫鬟們只顧玩鬧,十分看不過。因嘆道:“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個樣兒了,別的媽媽們越不敢說你們了。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臺――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家的。只知嫌人家髒,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們遭塌,越不成體統了。”這些丫頭們明知寶玉不講究這些,二則李嬤嬤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如今管她們不着,因此只顧玩,並不理她。那李嬤嬤還只管問“寶玉如今一頓喫多少飯”,“什麼時辰睡覺”等語。丫頭們總胡亂答應。有的說:“好一個討厭的老貨!”
李嬤嬤又問道:“這蓋碗裏是酥酪,怎不送與我去?我就吃了罷。”說畢,拿匙就喫。一個丫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着的,回來又惹氣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認,別帶累我們受氣。”李嬤嬤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壞了。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個值錢的,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我的血變的奶,喫得長這麼大,如今我喫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看怎麼樣!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裏調理出來的毛丫頭,什麼阿物兒!”一面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丫頭笑道:“她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還時常送東西孝敬你老去,豈有爲這個不自在的。”李嬤嬤道:“你們也不必妝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爲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兒有了不是,我再來領!”說着,賭氣去了。
少時,寶玉回來,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雯躺在牀上不動,寶玉因問:“敢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她倒是贏的。誰知李老太太來了,混輸了,她氣得睡去了。”寶玉笑道:“你別和她一般見識,由她去就是了。”說着,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喫飯,多早晚回來,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一時換衣卸妝。寶玉命取酥酪來,丫鬟們回說:“李奶奶吃了。”寶玉纔要說話,襲人便忙笑道:“原來是留的這個,多謝費心。前兒我喫的時候好喫,喫過了好肚子疼,疼得吐了纔好。她吃了倒好,擱在這裏倒白遭塌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喫,你替我剝栗子,我去鋪牀。”
寶玉聽了信以爲真,方把酥酪丟開,取栗子來,自向燈前檢剝。一面見衆人不在房裏,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你什麼人?”襲人道:“那是我兩姨妹子。”寶玉聽了,讚歎了兩聲。襲人道:“嘆什麼?我知道你心裏的緣故,想是說她那哪裏配穿紅的。”寶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樣的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我因爲見她實在好得很,怎麼也得她在咱們家就好了。”襲人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還要揀實在好的丫頭才往你家來!”寶玉聽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咱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道:“那也般配不上。”寶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栗子。襲人笑道:“怎麼不言語了?想是我才冒撞衝犯了你,明兒賭氣花幾兩銀子買她們進來就是了。”寶玉笑道:“你說的話,怎麼叫我答言呢?我不過是贊她好,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裏,沒的我們這種濁物倒生在這裏。”襲人道:“她雖沒這造化,倒也是嬌生慣養的呢,我姨爹、姨娘的寶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妝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
寶玉聽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嗐了兩聲。正不自在,又聽襲人嘆道:“只從我來這幾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寶玉聽這話內有文章,不覺喫一驚,忙丟下栗子,問道:“怎麼,你如今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兒聽見我媽和哥哥商議,教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的呢。”寶玉聽了這話,越發怔了,因問:“爲什麼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裏的家生子兒,一家子都在別處,獨我一個人在這裏,怎麼是個了局?”寶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難。”襲人道:“從來沒這道理。便是朝廷宮裏,也有個定例,或幾年一選,幾年一入,也沒有個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了!”
寶玉想一想,果然有理。又道:“太太,不放你也難。”襲人道:“爲什麼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老太太必不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我們家幾兩銀子,留下我,然或有之;其實我也不過是個最平常的人,比我強的有而且多。自我從小兒來了,跟着老太太,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幾年,如今又服侍了你幾年。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爲服侍得你好,不叫我去,斷然沒有的事。那服侍得好是分內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有好的來了,不是沒了我就成不得的。”寶玉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心內越發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一心只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她也不好意思接你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漫說和她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她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她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東西,因爲你喜歡,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喫虧,可以行得。如今無故憑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太太斷不肯行的。”寶玉聽了,思忖半晌,乃說道:“依你說,你是去定了?”襲人道:“去定了。”寶玉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該弄了來!臨了剩我一個孤鬼。”說着,便賭氣上牀睡去了。
原來,襲人在家聽見她母兄要贖她回去,她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喫,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喫穿和主子一樣,也不朝打暮罵。況且如今爹雖沒了,你們卻又整理得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出來再多掏澄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難了。這會子又贖我作什麼?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
她母兄見她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況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着賈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連身價銀一併賞了還是有的事呢。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衆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因此,他母子兩個也就死心不贖了。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況,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發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唸了。
如今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衆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近來仗着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蕩弛縱,任性恣情,最不喜務正。每欲勸時,料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今見他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自己原不想栗子喫的,只因怕爲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茜雪之茶等事,是以假以栗子爲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丫頭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己來推寶玉。
只見寶玉淚痕滿面,襲人便笑道:“這有什麼傷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去了。”寶玉見這話有文章,便說道︰“你倒說說,我還要怎麼留你?我自己也難說了。”襲人笑道:“咱們素日好處,再不用說。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兩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
寶玉忙笑道:“你說,哪幾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別說兩三件,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煙,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哪裏去就去了。”話未說完,急得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的,正爲勸你這些,倒更說得狠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寶玉道:“改了,再要說,你就擰嘴。還有什麼?”
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罷,假喜也罷,只是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隻管批駁誚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來,也教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裏想着:我家代代讀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不但不喜讀書,--已經他心裏又氣又愧了。--而且背前背後亂說那些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字叫作‘祿蠹’;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這些話,怎麼怨得老爺不氣,不時時打你!叫別人怎麼想你?”寶玉笑道:“再不說了,那原是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如今再不敢說了。還有什麼?”
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謗道,調脂弄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再不許喫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寶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麼?快說。”襲人笑道:“再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你若果都依了,便拿八人轎擡我,也擡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你在這裏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縱坐了,也沒甚趣。”
二人正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快三更了,該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嬤嬤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正。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
至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覺身體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扎掙得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和衣躺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診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喫一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剛服下去,命她蓋上被渥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
彼時,黛玉自在牀上歇午,丫鬟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寶玉揭起繡線軟簾,進入裏間。只見黛玉睡在那裏,忙走上來推她道:“好妹妹,才吃了飯,又睡覺!”將黛玉喚醒。黛玉見是寶玉,因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來,渾身痠疼。”寶玉道:“痠疼事小,睡出來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兒。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來。”寶玉推她道:“我往哪去呢?見了別人就怪膩的。”
黛玉聽了,“嗤”的一聲笑道:“你既要在這裏,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着,咱們說話兒。”寶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寶玉道:“沒有枕頭,咱們在一個枕頭上罷。”黛玉道:“放屁!外頭不是枕頭?拿一個來枕着。”寶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知是哪個髒婆子的。”黛玉聽了,睜開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請枕這一個。”說着,將自己枕的推與寶玉,又起身將自己的再拿了一個來,自己枕了,二人對面倒下。
黛玉因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釦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又道:“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寶玉側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纔剛替她們淘漉胭脂膏子,蹭上了一點兒。”說着,便找手帕子要揩拭。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口內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兒,吹到舅舅耳朵裏,又該大家不乾淨惹氣。”
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只聞得一股幽香,卻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籠着何物。黛玉笑道:“冬寒十月,誰帶什麼香呢!”寶玉笑道:“既然如此,這香是哪裏來的?”黛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櫃子裏頭的香氣,衣服上薰染的也未可知。”寶玉搖頭道:“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球子、香袋子的香。”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奇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朵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罷了。”
寶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麼些,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着翻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便伸手向黛玉膈肢窩內兩肋下亂撓。黛玉素性觸癢不禁,寶玉兩手伸來亂撓,便笑得喘不過氣來,口裏說:“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還說這些不說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鬢,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
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因問:“什麼‘暖香’?”黛玉點頭嘆笑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寶玉方聽出來。寶玉笑道:“方纔求饒,如今更說狠了。”說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寶玉笑道:“饒便饒你,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着,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個不住。黛玉奪了手道:“這可該去了。”寶玉笑道:“去?不能。咱們斯斯文文的躺着說話兒。”說着,復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手帕子蓋上臉。寶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黛玉只不理。寶玉問她幾歲上京,路上見何景緻古蹟,揚州有何遺蹟故事、土俗民風。黛玉只不答。
寶玉只怕她睡出病來,便哄她道:“噯喲!你們揚州衙門裏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黛玉見他說得鄭重,且又正言厲色,只當是真事,因問:“什麼事?”寶玉見問,便忍着笑,順口謅道:“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黛玉笑道:“就是扯謊,自來也沒聽見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哪裏知道這些不成?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你且說。”寶玉又謅道:“林子洞裏原來有羣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因說:‘明日乃是臘八,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果品短少,須得趁此打劫些來方妙。’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的小耗子前去打聽。一時小耗回報:‘各處察訪打聽已畢,惟有山下廟裏果米最多。’老耗問:”米有幾樣?果有幾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果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芋。‘老耗聽了大喜,實時點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了香芋一種,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芋?‘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願去偷香芋。‘老耗並衆耗見它這樣,恐不諳練,且怯懦無力,都不准它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卻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此去管比它們偷得還巧呢。’衆耗忙問:‘如何比他它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變,也變成個香芋,滾在香芋堆裏,使人看不出,聽不見,卻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衆耗聽了,都道:’妙卻妙,只是不知怎麼個變法,你先變個我們瞧瞧。‘小耗聽了,笑道:’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搖身就變,竟變了一位最標緻美貌的小姐。衆耗忙笑道:’變錯了,變錯了!原說變果子的,如何變出小姐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這果子是香芋,卻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的香玉呢。‘“
黛玉聽了,翻身爬起來,按着寶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說着,便擰,擰得寶玉連連央告說:“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爲聞你香,忽然想起這個故典來。”黛玉笑道:“饒罵了人,還說是故典呢!”
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問:“誰說故典呢?我也聽聽。”黛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還有誰!他饒罵了人,還說是故典。”寶釵笑道:“原來是寶兄弟,怨不得他,他肚子裏的故典原多。只是可惜一件,凡該用故典之時,他偏就忘了。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裏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面前的倒想不起來,別人冷得那樣,你急得只出汗。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黛玉聽了笑道:“阿彌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子了。可知一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說到這裏,只聽寶玉房中一片聲嚷,吵鬧起來。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