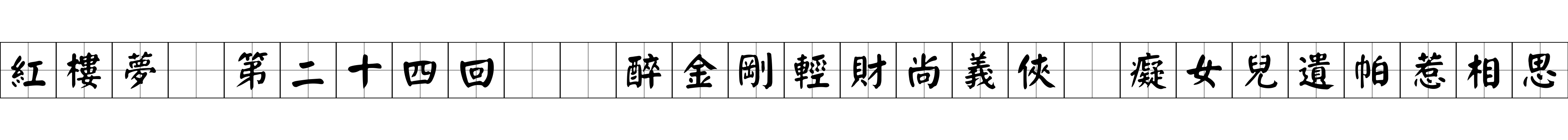紅樓夢-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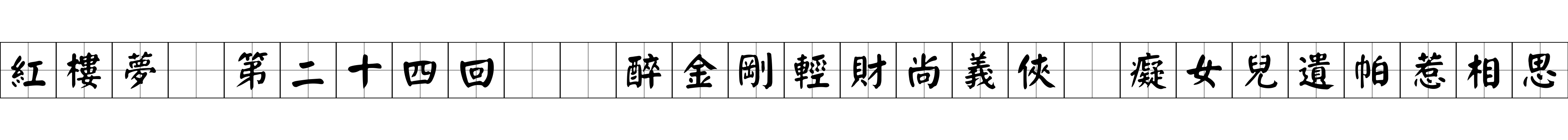
紅樓夢以錯綜複雜的清代上層貴族社會爲背景,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爲主線,通過對賈、史、王、薛四大家族榮衰的描寫,展示了18世紀上半葉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方方面面,囊括了多姿多彩的世俗人情,可謂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長篇小說。
話說林黛玉正自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她一掌,說道:“你做什麼一個人在這裏?”林黛玉倒唬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卻是香菱。林黛玉道:“你這傻丫頭,唬了我這麼一跳。你這會子打哪裏來?”香菱嘻嘻的笑道:“我來尋我們的姑娘的,找她總找不着。你們紫鵑也找你呢,說璉二奶奶送了什麼茶葉來給你的。走罷,回家去坐着。”一面說着,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瀟湘館來。果然,鳳姐兒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來。林黛玉和香菱坐了。況她們有甚正事談講,不過說些這一個繡得好,那一個刺得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
如今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果見鴛鴦歪在牀上看襲人的針線呢,見寶玉來了,便說道:“你往哪裏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爺的安去。還不快換了衣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寶玉坐在牀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著水紅綾子襖兒,青緞子背心,束着白縐綢汗巾兒,臉向內低着頭看針線,脖子上戴着花領子。寶玉便把臉湊在她脖項上,聞那粉香油氣,禁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膩不在襲人之下。寶玉便猴上身去,涎皮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一面說着,一面扭股糖似的黏在身上。鴛鴦便叫道:“襲人,你出來瞧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勸,還是這麼着。”襲人抱了衣服出來,向寶玉道:“左勸也不改,右勸也不改,你到底是怎麼樣?你再這麼着,這個地方可就難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了衣服,同了鴛鴦往前面來見賈母。
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旁邊轉出一個人來,“請寶叔安”。寶玉看時,只見這人容長臉,長挑身材,年紀只好十八九歲,生得着實斯文清秀,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哪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笑道:“你怎麼發呆,連他也不認得?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寶玉笑道:“是了,是了,我怎麼就忘了。”因問他母親好,這會子什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找二叔說句話。”寶玉笑道:“你倒比先越發出挑了,倒像是我的兒子。”賈璉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替你作兒子了?”寶玉笑道:“你今年十幾歲了?”賈芸道:“十八歲了。”
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覺,聽寶玉這樣說,便笑道:“俗語說的,‘搖車裏的爺爺,拄拐的孫孫’。雖然歲數大,山高高不過太陽。只從我父親沒了,這幾年也無人照管教導。如若寶叔不嫌侄兒蠢笨,認作兒子,就是我的造化了。”賈璉笑道:“你聽見了?認了兒子不是好開交的呢。”說着就進去了。寶玉笑道:“明兒你閒了,只管來找我,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閒兒。明兒你到書房裏來,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園裏玩耍去。”說着扳鞍上馬,衆小廝圍隨往賈赦這邊來。
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話,次後便喚人來:“帶哥兒進去太太屋裏坐着。”寶玉領命退出,來至後面,進入上房。邢夫人見了他來,先倒站起來,請過賈母安,寶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別人好,又命人倒茶來。一鍾茶未喫完,只見那賈琮來問寶玉好。邢夫人道:“哪裏找活猴兒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收拾你,弄得黑眉烏嘴的,那裏像大家子唸書的孩子!”
正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侄兩個也來了,請過安,邢夫人便叫他兩個椅子上坐了。賈環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摩挲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便和賈蘭使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要走,自己也就起身,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話呢。”寶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你們各人母親好。你們姑娘、姐姐、妹妹都在這裏呢,鬧得我頭暈,今兒不留你們喫飯了。”賈環等答應着,便出來回家去了。
寶玉笑道:“可是姐姐們都過來了,怎麼不見?”邢夫人道:“她們坐了一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裏去了。”寶玉道:“大娘方纔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邢夫人笑道:“哪裏有什麼話,不過叫你等着,同你姊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玩的東西給你帶回去玩。”孃兒兩個說話,不覺早又晚飯時節。調開桌椅,羅列杯盤,母女姐妹們喫畢了飯。寶玉辭了賈赦,同姐妹們一同回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息。不在話下。
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聽可有什麼事情。賈璉向他說:“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你嬸孃再三求了我,給了賈芹了。她許了我說,明兒園裏還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賈芸聽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着罷。叔叔也不必先在嬸子跟前提我今兒來打聽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它作什麼,我哪裏有這些工夫說閒話兒呢。明兒一個五更,還要到興邑去走一趟,需得當日趕回來纔好。你先去等着,後日起更以後你來討信,早了我不得閒。”說着便回後面換衣服去了。
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個主意來,便一徑往他母舅卜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鋪,方纔從鋪子面裏來,忽見賈芸進來,彼此見過了,因問他這早晚什麼事跑了來。賈芸笑道:“有件事求舅舅幫襯幫襯。我現有一件要緊的事,用些冰片、麝香使用,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裏按數送了銀子來。”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兒也是我們鋪子裏一個夥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至今總未還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誰要錯了這個,就要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還趕出鋪子去。況且如今這個貨也短,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種不三不四的小鋪子裏來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倒扁兒去。這是一。二則你哪裏有正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舅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兒家很不知好歹,也到底立個主見,賺幾個錢,弄得穿是穿喫是喫的,我看着也喜歡。”
賈芸笑道:“舅舅說得倒乾淨。我父親沒的時候,我年紀又小,不知事。後來聽見我母親說,都還虧舅舅們在我們家出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舅就不知道,還有一畝田、兩間房呢是我不成器,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來,叫我怎麼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別個,死皮賴臉的三日兩頭兒來纏着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沒法兒呢。”
卜世仁道:“我的兒,舅舅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說,只愁你沒算計兒。你但凡立得起來,到你大房裏,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着,便下個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嬉和嬉和,也弄個事兒管管。前日我出城去,撞見了你們三房裏的老四,騎着大黑叫驢,帶着四五輛車,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往家廟裏去了。他那不虧能幹,就有一這樣的好事兒到他手裏了!”賈芸聽他嘮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麼急得這樣,吃了飯再去罷。”一句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胡塗了。說着沒有米,這裏買了半斤面來下給你喫,這會子還裝胖呢。留下外甥捱餓不成?”卜世仁說:“再買半斤來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兒:“銀姐,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有錢借二三十個,明兒就送過來。”夫妻兩個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幾個“不用費事”,去得無影無蹤了。
不言卜家夫婦,且說賈芸賭氣離了母舅家門,一徑迴歸舊路。心下正自煩惱,一邊想,一邊低頭只管走,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把賈芸唬了一跳。聽那醉漢罵道:“肏你媽的!瞎了眼睛了,碰起我來了。”賈芸忙要躲,早被那醉漢一把抓住,對面一看,不是別人,卻是緊鄰倪二。原來這倪二是個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喫閒錢,專愛喫酒打架。如今正從欠主人家來了利錢,喫醉回來,不想被賈芸碰了一頭,正沒好氣,掄拳就要打。只聽那人叫道:“老二住手!是我衝撞了你。”倪二聽見是熟人的語音,將醉眼睜開看時,見是賈芸,忙把手鬆了,趔趄着笑道:“原來是賈二爺,我該死,我該死。這會子往那裏去?”賈芸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個沒趣兒。”倪二道:“不妨不妨,有什麼不平的事,告訴我,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憑他是誰,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坊,管叫他人離家散!”
賈芸道:“老二,你且彆氣,聽我告訴你這緣故。”說着,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道:“要不是令舅,我便罵不出好話來,真真氣死我倪二。也罷,你也不用愁煩,我這裏現有幾兩銀子,你若用什麼,只管拿去買辦。但只一件,你我作了這些年的街坊,我在外頭有名放帳的,你卻從沒有和我張過口。也不知你厭惡我是個潑皮,怕低了你的身分;也不知是你怕我難纏,利錢重。若說怕利錢重,這銀子我是不要利錢的,也不用寫文約;若說怕低了你的身分,我就不敢借給你了,各自走開。”一面說,一面果然從搭包裏掏出一卷銀子來。
賈芸心下自思:“素日倪二雖然是潑皮無賴,卻因人而使,頗頗的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臊了,倒恐生事。不如借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也倒罷了。”想畢,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我何曾不想着你,和你張口。但只是我見你所相與交結的,都是些有膽量的有作爲的人,像我們這等無能爲的你倒不理。我若和你張口,你豈肯借給我。今日既蒙高情,我怎敢不領?回家按例寫了文約過來便是了。”倪二大笑道:“好會說話的人。我卻聽不上這話。既說‘相與交結’四個字,如何又放帳給他,使他圖賺的利錢!既把銀子借與他,圖他的利錢,便不是相與交結了。閒話也不必講。既肯青目,這是十五兩三錢有零的銀子,你便拿去治買東西。你要寫什麼文契,趁早把銀子還我,讓我放給那些有指望的人使去。”賈芸聽了,一面接了銀子,一面笑道:“我便不寫罷了,有何着急的。”倪二笑道:“這纔是了。天色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還到那邊有點事情去,你竟請回去罷。我還求你帶個信兒與舍下,叫她們早些關門睡罷,我不回家去了。倘或有要緊事,叫我們女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來找我。”一面說,一面趔趄着腳兒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賈芸偶然碰了這件事,心中也十分罕希,想那倪二倒果然有些意思,只是還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的要起來,便怎麼處,心內猶豫不決。忽又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也可加倍還他。”想畢,一直走到個錢鋪裏,將那銀子稱了稱,十五兩三錢四分二釐。賈芸見倪二不撒謊,心下越發歡喜,收了銀子來至家門,先到隔壁將倪二的信捎了與他娘子知道,方回家來。見他母親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便問哪裏去了一日。賈芸恐他母親生氣,便不說起卜世仁的事來,只說在西府裏等璉二叔的來着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說:“已喫過了,給你留了飯在那裏。叫小丫頭子拿過來與他喫。那天,已是掌燈時候,賈芸吃了飯收拾歇息,一夜無話。
次日一早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大香鋪裏買了冰、麝,便往榮國府來。打聽賈璉出了門,賈芸便往後面來,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廝拿着大高笤帚在那裏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裏出來叫小廝們:“先別掃,奶奶出來了。”賈芸忙上去笑問道:“二嬸子往哪裏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麼尺頭。”
正說着,只見一羣人簇着鳳姐出來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尚排場的,忙把手逼着,恭恭敬敬搶上來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着,只問他母親好,“怎麼不來我們這裏逛逛?”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大好,倒時常記掛着嬸子,要來瞧瞧,又不能來。”鳳姐笑道:“可是會撒謊,不是我提起她來,你就不說她想我了。”賈芸笑道:“侄兒不怕雷打了,就敢在長輩前撒謊?昨兒晚上還提起嬸子來,說嬸子身子生得單弱,事情又多,虧嬸子好大精神,竟料理得週週全全。要是差一點的,早累得不知怎麼樣呢。”
鳳姐聽了滿面是笑,不由得便止了步,問道:“怎麼好好的你孃兒兩個在背地裏嚼起我來?”賈芸道:“有個原故,只因我有個極好的朋友,家裏有幾個錢,現開香鋪。只因他身上捐着個通判,前兒選了雲南不知哪一處,連家眷一齊去,他收了香鋪也在這裏不開了。便把賬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發的賤發了,像這細貴的貨,都分着送了親朋。他就一共送了我四兩冰片、四兩麝香。我就和我母親商量,若要轉買,不但賣不出原價來,而且誰家拿這些銀子買這個作什麼,便是很有錢的大家子,也不過使個幾分幾錢就挺折腰了;若說送人,也沒個人配使這些,倒叫他一文不值半文轉賣了。因此我就想起嬸子來,往年間我還見嬸子大包的銀子買這些東西呢。別說今年貴妃進了宮,就是這個端陽節下,不用說這些香料自然是比往常加上十倍的用呢。因此想來想去,只孝順嬸孃才合式,方不算遭塌這東西。”一邊說,一邊將一個錦匣舉起來。
鳳姐正是要辦端陽的節禮、採買香料藥餌的時節,忽見賈芸如此一來,聽這一篇話,心下又是得意又是喜歡,便命豐兒:“接過芸哥兒的來,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着你這樣知好歹,怪道你叔叔常提你,說你說話兒也明白,心裏有見識。”賈芸聽這話入了港,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叔也曾提我來?”鳳姐見問,纔要告訴他與他管事情的話,便忙又止住,心下想道:“我如今要告訴他那話,倒叫他看着我見不得東西似的,爲得了這點子香,就混許他管事了。今兒先別提這事。”想畢,便把派他監種花木工程的事都隱瞞得一字不提,隨口說了兩句淡話,便往賈母那裏去了。賈芸也不好提的,只得回來。
因昨日見了寶玉,叫他到外書房等着,賈芸吃了飯便又進來,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霰齋三間書房裏來。只見茗煙、鋤藥兩個小廝下象棋,爲奪“車”正拌嘴;還有引泉、掃花、挑雲、伴鶴四五個人,在房檐上掏小雀兒玩。賈芸進入院內,把腳一跺,說道:“猴頭們淘氣,我來了。”衆小廝看見賈芸進來,都才散了。賈芸進入房內,便坐在椅子上問:“寶二爺沒下來?”茗煙道:“今兒總沒下來。二爺說什麼,我替你哨探哨探去。”說着便出去了。
這裏賈芸便看字畫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來,再看看別的小廝,都玩去了。正自煩悶,只聽門前嬌聲嫩語的叫了一聲“哥哥”。賈芸往外瞧時,看是一個十六七歲的丫頭,生得倒也細巧幹淨。那丫頭見了賈芸,便抽身躲了過去。恰值茗煙走來,見那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好,正抓不着個信兒呢。”賈芸見了茗煙,也就趕了出來,問怎麼樣了。茗煙道:“等了這一日,也沒個人兒出來。這就是寶二爺房裏的。好姑娘,你進去帶個信兒,就說廊上的二爺來了。”
那丫頭聽說,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先前那等迴避了,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那賈芸說道:“什麼是廊上廊下的,你只說是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丫頭冷笑了一笑:“依我說,二爺竟請回家去罷,有什麼話明兒再來。今兒晚上得空兒我回了他。”茗煙道:“這是怎麼着?”那丫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喫得晚飯早。晚上他又不下來。難道只是耍的二爺在這裏等着捱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正經。便是回來有人帶信,那都是不中用的。他不過是口裏答應着,他那麼工夫給你帶信兒去呢!倒給帶呢!”賈芸聽這丫頭說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的名字,因是寶玉房裏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倒是,我明兒再來。”說着便往外走。茗煙道:“我倒茶去,二爺吃了茶再去。”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喫茶,我還有事呢。”口裏說話,眼睛瞧那丫頭還站在那裏呢。
那賈芸一徑回家。至次日果然又來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才上了車,見賈芸來,便命人喚住,隔窗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膽子在我的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兒你叔叔才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叔這事,嬸孃休提,我昨兒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竟一起頭兒求嬸孃,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承望叔叔竟不能的。”鳳姐笑道:“怪道你那裏沒成兒,昨兒又來尋我。”賈芸道:“嬸孃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若有這個意思,昨兒還不求嬸孃。如今嬸孃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丟下,少不得求嬸孃了,好歹疼我一點兒!”
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路兒走,叫我也難了。早告訴我一聲兒,什麼不成的,多大點子事,耽誤到這會子。那園子裏還要種樹種花呢,我只想不出一個人來,你早來不早完了?”賈芸笑道:“既是這樣,嬸孃明兒就派了我罷。”鳳姐半晌說道:“這個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裏的煙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再派你罷。”賈芸道:“好嬸孃,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個辦得好,再派我那個。”鳳姐笑道:“你倒會拉長線兒。罷了,要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不過吃了飯就過來,你到午錯的時候來領銀子,後日就進去種樹。”說畢,命人駕了香車,一徑去了。
賈芸喜不自禁,來至綺霰齋打聽寶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裏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聽鳳姐回來,便寫個領票來領對牌。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了出來,單要了領票進去,批了銀數年月,一併連對牌交與了賈芸。賈芸接了,看那批上銀數批了二百兩,心中喜不自禁,翻身走到銀庫上,交與收牌票的,領了銀子。回家告訴他母親,自是母子俱各歡喜。次日一個五鼓,賈芸先找了倪二,將前銀按數還他。那倪二見賈芸有了銀子,他便按數收回,不在話下。這裏賈芸又拿了五十兩,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裏去買樹,亦不在話下。
如今且說寶玉,自那日見了賈芸,曾說明日着他進來說話兒。如此說了之後,他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哪裏還把這個放在心上,因而便忘懷了。這日晚上,從北靜王府裏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薛寶釵煩了去打結子;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檀雲又因她母親的生日接了出去;麝月又現在家中養病;雖還有幾個作粗活聽喚的丫頭,估着叫不着她們,都出去尋夥覓伴的玩去了。不想這一刻的工夫,只剩了寶玉在房內。偏生的寶玉要喫茶,一連叫了兩三聲,方見兩三個老嬤嬤走進來。寶玉見了她們,連忙搖手兒說:“罷,罷!不用你們了。”老婆子們只得退出。
寶玉見沒丫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聽背後說道:“二爺仔細燙了手!讓我們倒。”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早接了碗過去。寶玉倒唬了一跳,問:“你在那裏的?忽然來了,唬我一跳。”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回說:“我在後院子裏,才從裏間的後門進來,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腳步響?”寶玉一面喫茶,一面仔細打量那丫頭:穿著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倒是一頭黑鬒鬒的好頭髮,挽着個簪(原字爲上髟下贊),容長臉面,細巧身材,卻十分俏麗乾淨。
寶玉看了,便笑問道:“你也是我這屋裏的人麼?”那丫頭道:“是的。”寶玉道:“既是這屋裏的,我怎麼不認得?”那丫頭聽說,便冷笑了一聲道:認不得的也多,豈止我一個?從來我又不遞茶遞水,拿東拿西,眼見的事一點兒不作,爺那裏認得呢!“寶玉道:”你爲什麼不作那眼見的事?“那丫頭道:”這話我也難說。只是有一句話回二爺:昨兒有個什麼芸兒來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便叫茗煙回他,叫他今日早起來,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裏去了。“
剛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嘻嘻哈哈的說笑着進入院來,兩個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着衣裳,趔趔趄趄,潑潑撒撒的。那丫頭便忙迎出去接。那秋紋、碧痕正對着抱怨,“你溼了我的裙子”,那個又說“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出一個人來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來是小紅。二人便都詫異,將水放下,忙進房來東瞧西望,並沒個別人,只有寶玉,便心中大不自在。只得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到那邊房內便找小紅,問她:“方纔在屋裏說什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裏?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手帕子去。不想二爺要茶喫,叫姐姐們一個沒有,是我進去了,才倒了茶,姐姐們便來了。”
秋紋聽了,兜臉啐了一口,罵道:“沒臉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去催水去,你說有事故,倒叫我們去,你可等着做這個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她們,凡要茶要水送東送西的事,咱們都別動,只叫她去便是了。”秋紋道:“這麼說,還不如我們散了,單讓她在這屋裏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着,只見有個老嬤嬤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日有人帶花兒匠來種樹,叫你們嚴禁些,衣服裙子別混曬混晾的。那土山上一溜都攔着幃幙呢,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兒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婆子道:“說什麼後廊上的芸哥兒。”秋紋、碧痕聽了,都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聽見了,心內卻明白,就知是昨兒外書房所見的那個人了。
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只因“玉”字犯了林黛玉、寶玉的名字,便都把這個字隱起來,便都叫她“小紅”。原是榮國府中世代的舊僕,她父母現在收管各處房田事務。這紅玉年方十六歲,因分人在大觀園的時節,把她便分在怡紅院中,倒也清幽雅靜。不想後來命人進來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寶玉佔了。這紅玉雖然是個不諳事的丫頭,卻因她原有三分容貌,心內着實妄想癡心的往上攀高,每每的要在寶玉面前現弄現弄。只是寶玉身邊一干人,都是伶牙利爪的,哪裏插得下手去。不想今兒纔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意,心內早灰了一半。正悶悶的,忽然聽見老嬤嬤說起賈芸來,不覺心中一動,便悶悶的回至房中,睡在牀上暗暗盤算,翻來掉去,正沒個抓尋。忽聽窗外低低的叫道:“紅玉,你的手帕子我拾在這裏呢。”紅玉聽了,忙走出來看,不是別人,正是賈芸。紅玉不覺的粉面含羞,問道:“二爺在那裏拾着的?”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她。那紅玉急回身一跑,卻被門檻絆倒。要知端的,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