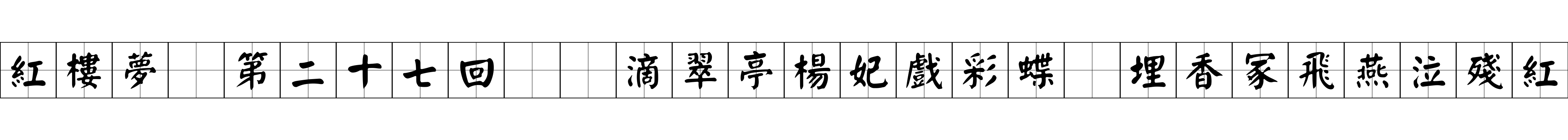紅樓夢-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冢飛燕泣殘紅-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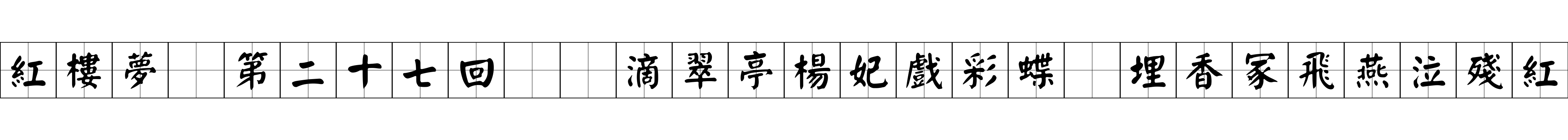
紅樓夢以錯綜複雜的清代上層貴族社會爲背景,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爲主線,通過對賈、史、王、薛四大家族榮衰的描寫,展示了18世紀上半葉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方方面面,囊括了多姿多彩的世俗人情,可謂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長篇小說。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着衆人問,羞了他倒不便,因而閃過一旁,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猶望着門灑了幾點淚。自覺無味,便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妝。
紫鵑、雪雁素日知道她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嘆,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了什麼,便常常的自淚自乾的。先時還解勸,怕她思父母,想家鄉,受了委屈,用話來寬慰解勸。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常的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沒人理,由她去悶坐,只管睡覺去了。那林黛玉倚着牀欄杆,兩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三更多天,方纔睡了。一宿無話。
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餞行。然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幹旄旌幢的,都用綵線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裏繡帶飄颻,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讓,燕妒鶯慚,一時也道不盡。
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大姐、香菱與衆丫鬟們在園內玩耍,獨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個懶丫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着,我去鬧了她來。”說着便丟下衆人,一直往瀟湘館來。正走着,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見寶釵問了好,說了一回閒話。寶釵回身指道:“她們都在那裏呢,你們找去罷。我叫林姑娘去就來。”說着便往瀟湘館來。忽然擡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和林黛玉是從小一處長大,他二人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喜怒無常;況且黛玉素習猜忌,好弄小性兒。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倒是回來的妙。想畢,抽身回來剛要尋別的姊妹去。
忽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的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雙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穿花度柳,將欲過河。倒引得寶釵躡手躡腳的,一直跟到池中的滴翠亭,香汗淋漓,嬌喘細細,也無心撲了。剛欲回來,只聽亭子裏邊嘁嘁喳喳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橋,蓋造在池中,周圍都是雕鏤隔子糊着紙。
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便煞住腳,往裏細聽,只聽說道:“你瞧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丟的那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又有一人道:“可不是我那塊!拿來給我罷。”又聽說道:“你拿了什麼謝我呢?難道白尋了來不成?”又答道:“我既許了謝你,自然不哄你。”又聽說道:“我尋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揀的人,你就不拿什麼謝他?”又回道:“你別胡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什麼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呢?況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晌,又聽答道:“也罷,拿我這個給他,就算謝他的罷。――你要告訴別人呢?須說個誓來。”又聽說道:“我要告訴一個人,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噯呀!咱們只顧說話,看有人來悄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隔子都推開了,便是有人見咱們在這裏,他們只當我們說玩話呢。若走到跟前,咱們也看得見,就別說了。”
寶釵在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喫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姦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這一開了,見我在這裏,她們豈不臊了。況才說話的語音兒,大似寶玉房裏的紅兒。她素昔眼空心大,最是個頭等刁鑽古怪的東西。今兒我聽了她的短兒,一時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趕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腳步,笑着叫道:“顰兒,我看你往哪裏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亭內的紅玉、墜兒剛一推窗,只聽寶釵如此說着往前趕,兩個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她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哪裏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纔在河那邊看着她在這裏蹲着弄水兒的。我要悄悄的唬她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她倒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這裏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又是鑽在那山子洞裏去。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她二人是怎麼樣。
誰知紅玉聽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爲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裏,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紅玉又道:“這可怎麼樣呢?”墜兒道:“便是聽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紅玉道:“若是寶姑娘聽見還倒罷了。林姑娘嘴裏又愛刻薄人,心裏又細,她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風,怎麼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待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她們玩笑。
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紅玉,紅玉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跟前,堆着笑問:“奶奶使喚作什麼?”鳳姐打量了一打量,見她生得乾淨俏麗,說話知趣,因說道:“我的丫頭今兒沒跟進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個人出去,可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得齊全不齊全?”紅玉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不齊全,誤了奶奶的事,憑奶奶責罰罷了。”鳳姐笑道:“你是哪房裏的?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答應。”紅玉道:“我是寶二爺房裏的。”鳳姐聽了笑道:“噯喲!你原來是寶玉房裏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裏桌子上汝窯盤子架兒底下放着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稱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裏頭屋裏牀上間有一個小荷包拿了來給我。”
紅玉聽說,撤身去了。回來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子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裏出來,站着系裙子,便趕上來問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哪裏去了?”司棋道:“沒理論。”紅玉聽了,又往四下裏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紅玉便走來陪笑問道:“姑娘們可看見二奶奶沒有?”探春道:“往大奶奶院裏找去。”紅玉聽了,才往稻香村來,頂頭只見晴雯、綺霰、碧痕、紫綃、麝月、待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了紅玉,便說道:“你只是瘋罷!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爐子也不爖,就在外頭逛。”紅玉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再澆罷。我喂雀兒的時侯,姐姐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爐子呢?”紅玉道:“今兒不該我爖的班兒,有茶沒茶別問我。”綺霰道:“你聽聽她的嘴!你們別說了,讓她逛去罷。”紅玉道:“你們再問問我,逛了沒有。二奶奶才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的。”說着將荷包舉給她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分路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在眼裏。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了不曾呢,就把她興得這樣!這一遭兒半遭兒的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的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得。”一面說着去了。
這裏紅玉聽說,也不便分證,只得忍着氣來找鳳姐,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在那裏和李氏說話兒呢。紅玉便上來回道:“平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才張材家的來討,當面稱了給她拿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回奶奶說: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的。平姐姐就把那話按着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她怎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紅玉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裏奶奶好。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裏的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全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裏。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
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喲喲!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着又向紅玉笑道:“好孩子,倒難爲你說得齊全。別像她們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嫂子你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幾個人之外,我就怕和她們說話。她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咬字,拿着腔兒,哼哼唧唧,急得我冒火。先時我們平兒也是這麼着,我就問着她:難道必定裝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說了幾遭,纔好些兒了。”李宮裁笑道:“都像你潑皮破落戶纔好。”鳳姐又道:“這個丫頭就好。方纔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聲就簡斷。”說着又向紅玉笑道:“你明兒服侍我去罷。我認你作女兒,我再調理調理,你就出息了。”
紅玉聽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作你的媽了?你別做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都比你大的大的,趕着我叫媽,我還不理呢!”紅玉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了。我媽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作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來不認得她?她是林之孝之女。”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笑問道:“哦!原來是他的丫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倒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雙天聾地啞。哪裏承望養出這麼個伶俐丫頭來!你十幾歲了?”紅玉道:“十七了。”又問名字,紅玉道:“原叫紅玉的,因爲重了寶二爺,如今叫紅兒了。”
鳳姐聽了,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嫌得很!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說道:“既這麼着,上月我還和她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裏誰是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丫頭我使’,她一般的答應着。她饒不挑,倒把她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氏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她進來在先,你說話在後,怎麼怨得她媽!”鳳姐道:“既這麼着,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丫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願意不願意?”紅玉笑道:“願意不願意,我們不敢說。只是跟着奶奶,我們也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見識見識。”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紅玉回怡紅院去,不在話下。
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次日起遲了,聞得衆姊妹都在園中作餞花會,恐人笑癡懶,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笑道:“好妹妹,昨兒可告我不曾?教我懸了一夜心。”林黛玉便回頭叫紫鵑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屜;看那大燕子回來,把簾子放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上。”一面說一面仍往外走。寶玉見她這樣,還認作是昨日中晌的事,哪知晚間的這段公案,還打恭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個光景來,不像是爲昨日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得晚了,又沒有見她,再沒有衝撞了她的去處了。一面想,一面走,又由不得隨後面追了來。
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見黛玉來了,三個一同站着說話兒。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笑道:“寶哥哥,身上好?整整三天沒見了。”寶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探春道:“寶哥哥,往這裏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說,便跟了她,來到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爺可叫你沒有?”寶玉道:“沒有叫。”探春說:“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沒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拿去,明兒出門逛去的時侯,或是好字畫書籍、卷冊,好輕巧玩意兒,給我帶些來。”寶玉道:“我這麼城裏城外、大廊小廟的逛,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左不過是金玉銅磁、沒處撂的古董,再就是綢緞、喫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那些!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條兒編的小籃子,整竹子根摳的香盒子,膠泥垛的風爐兒,這就好。我喜歡得什麼似的,誰知她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似的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麼,拿五百錢出去給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樸而不俗、直而不拙者,這些東西,你多多的替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做一雙你穿,比那一雙還加工夫,如何呢?”
寶玉笑道:“你提起鞋來,我想起個故事來了:那一回我穿著,可巧遇見了老爺,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哪裏敢提‘三妹妹’三個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聽了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作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襲人,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得抱怨得了不得:‘正經兄弟,鞋搭拉襪搭拉的沒人看見,且作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沉下臉來道:“你說這話胡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沒有人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丫頭、老婆一屋子,怎麼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是閒着沒有事,做一雙半雙的,愛給哪個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她氣的?”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她心裏自然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益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胡塗了!她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她只管這麼想,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兄弟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她,但她忒昏憒得不像了!還有笑話兒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玩的東西。過了兩天,她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麼難,我也不理論。誰知後來丫頭們出去了,她就抱怨起我來,說我攢了錢爲什麼給你使,倒不給環兒使呢。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屋裏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顯見得是哥哥妹妹了,丟下別人,且說梯己去。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寶玉二人方笑着來了。
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便知她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索性遲兩日,等她的氣消一消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嘆道:“這是她心裏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待我送了去,明兒再問着她。”說着,只見寶釵約着她們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來。”說畢,等她二人去遠了,便把那花兜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柳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猶未轉過山坡,只聽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一行數落着,哭得好不傷感。寶玉心中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裏的丫頭,受了委曲,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腳步,聽她哭道是:
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遊絲軟系飄春榭,落絮輕沾撲繡簾。閨中女兒惜春暮,愁緒滿懷無釋處,手把花鋤出繡閨,忍踏落花來複去。柳絲榆莢自芳菲,不管桃飄與李飛。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三月香巢已壘成,梁間燕子太無情。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傾!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花開易見落難尋,階前悶殺葬花人。獨倚花鋤淚暗灑,灑上空枝見血痕。杜鵑無語正黃昏,荷鋤歸去掩重門。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怪奴底事倍傷神,半爲憐春半惱春:憐春忽至惱忽去,至又無言去不聞。昨宵庭外悲歌發,知是花魂與鳥魂?花魂鳥魂總難留,鳥自無言花自羞。願奴脅下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天盡頭,何處有香丘?未若錦囊收豔骨,一抔淨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污淖陷渠溝。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不覺癡倒。要知端詳,且看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