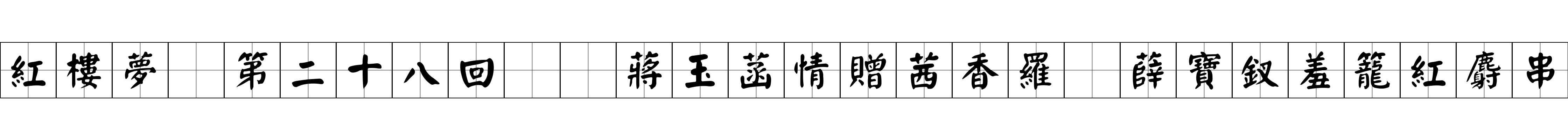紅樓夢-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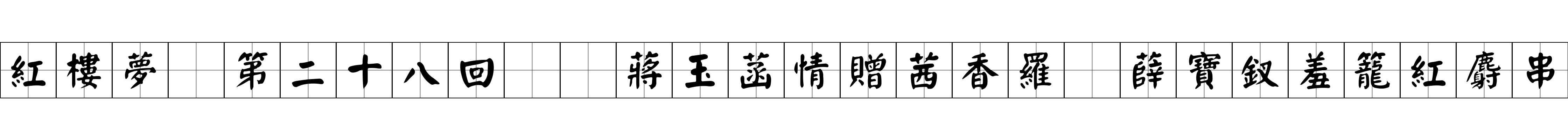
紅樓夢以錯綜複雜的清代上層貴族社會爲背景,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爲主線,通過對賈、史、王、薛四大家族榮衰的描寫,展示了18世紀上半葉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方方面面,囊括了多姿多彩的世俗人情,可謂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長篇小說。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是一腔無明正未發泄,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己,哭了幾聲,便隨口唸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是黛玉之聲,先不過點頭感嘆;次後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之上,懷裏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覆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欲爲何等蠢物,杳無所知,逃大造,出塵網,使可解釋這段悲傷。正是:
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
那黛玉正自悲傷,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些癡病,難道還有一個癡子不成?”想着,擡頭一看,見是寶玉。林黛玉看見,便道:“啐!我當是誰,原來是這個狠心短命的......”剛說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長嘆了一聲,自己抽身便走了。
這裏寶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抖土起來,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林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且站住。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後撂開手。”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從此撂開手”,這話裏有文章,少不得站住說道:“有一句話,請說來。”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後面嘆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林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寶玉嘆道:“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着玩笑?憑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喫的,聽見姑娘也愛喫,連忙乾乾淨淨收着等姑娘喫。一桌子喫飯,一牀上睡覺。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丫頭們想到了。我心裏想着: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兒,才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裏,倒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兒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姊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個心,弄得我有冤無處訴!”說着,不覺滴下眼淚來。
黛玉耳內聽了這話,眼內見了這形景,心內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來,低頭不語。寶玉見她這般形景,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憑着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倒是或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兩句,打我兩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是。就便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生,還得你申明瞭緣故,我才得託生呢!”
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麼說,昨兒爲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寶玉詫異道:“這話從哪裏說起?我要是這麼樣,立刻就死了!”林黛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實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出來了。”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想必是你的丫頭們懶怠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原故。等我回去問了是誰,教訓教訓他她們就好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兒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豈不大了!”說着抿着嘴笑。寶玉聽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只見丫頭來請喫飯,遂都往前頭來了。
王夫人見了林黛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喫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林黛玉道:“也不過這麼着,老太太還叫我喫王大夫的藥呢。”寶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內症,先天生得弱,所以禁不住一點風寒,不過喫兩劑煎藥疏散了風寒,還是喫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我也忘了。”寶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藥,不過叫她喫什麼人蔘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麥味地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得有個‘金剛’兩個字的。”寶玉扎手笑道:“從來沒聽見有個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薩散’了!”說得滿屋裏人都笑了。寶釵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笑道:“是這個名兒。如今我也胡塗了。”寶玉道:“太太倒不胡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胡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孃的臊!又欠你老子捶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爲這個捶我的。”
王夫人又道:“既有這個名兒,明日就叫人買些來。”寶玉笑道:“這些都是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麼藥就這麼貴?”寶玉笑道:“當真的呢,我這個方子比別的不同。那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還不夠,龜大何首烏、千年鬆根茯苓膽,諸如此類都不算爲奇,只在羣藥裏算那爲君的藥,說起來唬人一跳。前兒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才配成了。太太不信,只問寶姐姐。”寶釵聽說,笑着搖手兒說:“我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是寶丫頭,好孩子,不撒謊。”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倒是真話呢,倒說我撒謊。”說着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着嘴笑,用手指在臉上畫着羞他。
鳳姐因在裏間屋裏看着人放桌子,聽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這倒是有的。上日薛大哥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問他作什麼,他說是配藥。他還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裏知道這麼費事。我問他什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沒工夫聽。他說:”不然我也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你尋。“他說:”妹妹,若沒散的,花兒上也得,掐下來,過後兒我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來。“我沒法兒,把兩枝珠花兒現拆了給他。還要了一塊三尺大紅上用庫紗去,乳鉢乳了隔面子呢。”鳳姐說一句,那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裏呢!”鳳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過是將就呢。正經按那方子,這珍珠寶石定要在古墳裏的,有那古時富貴人家裝裹的頭面,拿了來纔好。如今哪裏爲這個去刨墳掘墓,所以只要活人戴過的,也可以使得。”王夫人道:“阿彌陀佛,不當家花花的!就是墳裏有這個,人家死了幾百年,如今翻屍盜骨的,作了藥也不靈!”
寶玉向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謊不成?”臉望着黛玉說,卻拿眼睛瞟着寶釵。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姐姐不替他圓謊,他直問着我。”王夫人也道:“寶玉很會欺負你妹妹。”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原故。寶姐姐先在家裏住着,那薛大哥哥的事,她就不知道,何況如今在裏頭住着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纔在背後羞我,打量是我撒謊呢。”
說着,只見賈母房裏的丫頭找寶玉、黛玉喫飯。林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拉了那丫頭就走。那丫頭說:“等着寶玉一塊兒走。”林黛玉道:“他不喫飯了,咱們走。我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着太太喫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喫齋,你正經喫你的去罷。”寶玉道:“我也跟着喫齋。”說着便叫那丫頭“去罷”,自己先跑到炕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道:“你們只管喫你們的,由他去罷。”寶釵因笑道:“你正經去罷。喫不喫,陪着林姑娘走一趟,她心裏打緊的不自在呢。”寶玉道:“理她呢,過一會子就好了。”
一時喫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掛,二則也記掛着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喫飯、喫茶也是這麼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林妹妹去罷,叫他在這裏胡羼些什麼。”寶玉吃了茶,便出來,直往西院走。可巧走到鳳姐兒院前,只見鳳姐蹬着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來個小廝們挪花盆呢。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正好。進來,進來,替我寫幾個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了房裏,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來,向寶玉道:“大紅妝緞四十匹、蟒緞四十匹、上用紗各色一百匹、金項圈四個。”寶玉道:“這算什麼?又不是賬,又不是禮物,怎麼個寫法?”鳳姐道:“你只管寫上,橫豎我自己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收起來,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你依不依?你屋裏有個丫頭叫紅玉,我和你說說,要叫了來使喚,也總沒說得,今兒見你,纔想起來。”寶玉道:“我屋裏的人也多得很,姐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鳳姐笑道:“既這麼着,我就叫人帶她去了。”寶玉道:“只管帶去。”說着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說。”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我回來罷。”說着,便來至賈母這邊,已經都喫完飯了。賈母因問他:“跟着你母親吃了什麼好的了?”寶玉笑道:“也沒什麼好的,我倒多吃了一碗飯。”因問:“林妹妹在哪裏?”賈母道:“裏頭屋裏呢。”
寶玉進來,只見地下一個丫頭吹熨斗,炕上兩個丫頭打粉線,黛玉彎着腰,拿着剪子裁什麼呢。寶玉走進來笑道:“哦,這是作什麼呢?才吃了飯,這麼空着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她的。有一個丫頭道:“這塊綢子角兒還不好呢,再熨它一熨。”黛玉便把剪子一撂,說道:“理它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聽了,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等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會話。寶釵也進來問:“林妹妹作什麼呢?”見黛玉裁剪,因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剪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你個笑話兒,纔剛爲那個藥,我說了個不知道,寶兄弟心裏不受用了。”林黛玉道:“理他呢,過會子就好了。”寶玉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抹骨牌去罷。”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爲抹骨牌纔來的?”說着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倒是去罷,這裏有老虎,看吃了你!”說着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去逛逛再裁不遲。”黛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丫頭們:“這是誰叫裁的?”黛玉見問丫頭們,便說道:“憑他誰叫裁,也不管二爺的事!”寶玉聽了,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回說“外頭有人請你呢”。寶玉聽了,忙撤身出來。黛玉向外頭說道:“阿彌陀佛!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
寶玉出來到外頭,只見茗煙說道:“馮大爺家請。”寶玉聽了,知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自己便往書房裏來。茗煙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來個老婆子,茗煙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裏等出門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道:“你孃的屄!倒好,寶二爺如今在園子裏住着,跟他的人都在園子裏,你又跑了這裏來帶信兒!”茗煙聽了笑道:“罵得是,我也胡塗了。”說着一徑往東邊二門前來。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球,茗煙將原故說了。小廝跑了進去,半日才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遞與茗煙。回到書房裏,寶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茗煙、鋤藥、雙瑞、雙壽四個小廝,一徑來到馮紫英家門口。
有人報與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裏久候,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廝並唱小旦的蔣玉菡、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喫茶。寶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晝懸夜想,今日一聞呼喚即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兄弟倒都心實。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又推託,故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即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廝過來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
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梯己新樣兒的曲子唱個我聽,我喫一罈如何?”雲兒聽說,只得拿起琵琶來唱道:
兩個冤家,都難丟下,想着你來又記掛着他。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荼縻架,一個偷情,一個尋拿,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
唱畢笑道:“你喝一罈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值一罈,再唱好的來。”
寶玉笑道:“聽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喝一大海,發一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菡等都道:“有理,有理。”寶玉拿起海來,一氣飲幹,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都要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字原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來,攔住道:“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便站起來,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麼?這還虧你天天喫酒呢,難道連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哪裏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倒喝十大海,下去給人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可治,只得坐了,聽寶玉先說,寶玉便道: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女兒喜,對鏡晨妝顏色美。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
衆人聽了都道:“說得有理。”薛蟠獨揚着臉搖頭說:“不好,該罰!”衆人問道:“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的我通不懂,怎麼不該罰?”雲兒便擰他一把,笑道:“你悄悄的想你的罷。回來說不出,纔是該罰呢。”於是拿琵琶,聽寶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咽不下玉粒金蓴噎滿喉,照不見菱花鏡裏形容瘦。展不開的眉頭,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彩,獨薛蟠說無板。寶玉飲了門杯,便拈起一片梨來,說道:“雨打梨花深閉門。”完了令。
下該馮紫英。聽馮紫英說道:
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女兒愁,大風吹倒梳妝樓。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
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個可人,你是個多情,你是個刁鑽古怪鬼靈精,你是個神仙也不靈。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地裏細打聽,才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門杯,說道:“雞聲茅店月。”令完,下該雲兒。雲兒便說道:
女兒悲,將來終身指靠誰?
薛蟠嘆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呢,你怕什麼!”衆人都道:“別混她,別混她!”
雲兒又道:
女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
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他不叫他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言者罰酒十杯。”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道:
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裏。女兒樂,住了簫管弄絃索。
說完便唱道:
荳蔻開花三月三,一個蟲兒往裏鑽。鑽了半日不得進去,爬到花兒上打鞦韆。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麼鑽?唱畢,飲了門杯,說道:“桃之夭夭。”令完了,下該薛蟠。
薛蟠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悲什麼?快說來。”薛蟠登時急得眼睛鈴鐺一般,瞪了半日,才說道:“女兒悲......”又咳嗽了兩聲,說道:
女兒悲,嫁了個男人是烏龜。
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當忘八,她怎麼不傷心呢?”衆人笑得彎腰,說道:“你說得很是,快說底下的。”薛蟠瞪了一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麼愁?”薛蟠道:
女兒愁,繡房攛出個大馬猴。
衆人呵呵笑道:“該罰,該罰!這句更不通,先還可恕。”說着便要篩酒。寶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令官都準了,你們鬧什麼!”衆人聽說,方纔罷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的我就沒好的了!聽我說罷:
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
衆人聽了都詫異道:“這句何其太韻?”薛蟠又道:
女兒樂,一根雞(原字爲左毛右幾)巴(原字爲左毛右巴)往裏戳。
衆人聽了,都回頭道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薛蟠便唱道:
一個蚊子哼哼哼。
衆人都怔了,說道:“這是個什麼曲兒?”薛蟠還唱道:
兩個蒼蠅嗡嗡嗡。
衆人都道:“罷,罷,罷!”薛蟠道:“愛聽不聽!這是新鮮曲兒,叫作哼哼韻。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了罷,免了罷,倒別耽誤了別人家。”於是蔣玉菡說道:
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女兒愁,無錢去打桂花油。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蕊。女兒樂,夫唱婦隨真和合。
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嬌,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度青春,年正小;配鸞鳳,真也着。呀!看天河正高,聽譙樓鼓敲,剔銀燈同入鴛幃悄。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見了一副對子,可巧只記得這句,幸而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飲幹了酒,拿起一朵木樨來,念道:“花氣襲人知晝暖。”
衆人倒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該罰,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寶貝,你怎麼念起寶貝來?”蔣玉菡怔了,說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念來。”蔣玉菡只得又唸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麼!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着,指着寶玉。寶玉沒好意思起來,說道:“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着拿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與蔣玉菡等不知原故,猶問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蔣玉菡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
少刻,寶玉出席外解手,蔣玉菡便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檐下,蔣玉菡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着他的手,叫他:“閒了,往我們這裏來。還有一句話借問,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的,他在哪裏?如今名馳天下,我獨無緣一見。”蔣玉菡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便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裏也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的,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着,將系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下來,遞與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進貢來的,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我的,今日才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系的給我係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琪官。二人方束好,只見一聲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來,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喫,兩個人逃席出來幹什麼?快拿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麼。”薛蟠那裏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才解開了。於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
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喫茶。襲人見扇子上的墜兒沒了,便問他:“往那裏去了?”寶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裏一條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我那條還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才是,心裏後悔,口裏說不出來,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點頭嘆道:“我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拿着我的東西給那起混帳人去。也難爲你心裏沒個算計兒。”再要說上幾句,又恐慪上他的酒來,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
至次日天明起來,只見寶玉笑道:“夜裏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系的那條汗巾子系在自己腰裏,便知是寶玉夜間換了,忙一頓把解下來,說道:“我不希罕這行子,趁早兒拿了去!”寶玉見她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襲人無法,只得繫上。過後,寶玉出去,終久解下來,擲在個空箱子裏,自己又換了一條繫着。
寶玉並不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道:“二奶奶打發人叫了紅玉去了。她原要等你來的,我想什麼要緊,我就作了主,打發她去了。”寶玉道:“很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道:“昨兒貴妃差了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着衆位爺們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着命小丫頭來,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等宮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簟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道:“別人的也都是這麼個?”襲人道:“老太太的多着一個香如意、一個瑪瑙枕。太太、老爺、姨太太的只多着一個如意。你的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單有扇子同數珠兒,別人都沒了。大奶奶、二奶奶她兩個是每人兩匹紗、兩匹羅、兩個香袋、兩個錠子藥。”寶玉聽了,笑道:“這是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樣,倒是寶姐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兒拿出來,都是一份一份的寫着籤子,怎麼就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裏來着,我去拿了來了。老太太說,明兒叫你一個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趟。”說着便叫:“紫綃,來拿了這個到林姑娘那裏去,就說是昨兒我得的,愛什麼留下什麼。”紫綃答應了,拿了去,不一時回來說:“林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着罷。”
寶玉聽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裏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來了。寶玉趕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又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禁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我們不過是草木之人!”寶玉聽她提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什麼玉,我心裏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黛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裏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麼誓!管你什麼金什麼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裏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說個誓。”黛玉道:“你也不用說誓,我很知道,你心裏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寶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黛玉道:“昨兒寶丫頭不替你圓謊,爲什麼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麼樣了。”
正說着,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裝看不見,低着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裏,坐了一會,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在這裏呢。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爲婚姻”等語,所以總遠着寶玉。昨兒見了元春所賜的東西,獨她與寶玉一樣,心裏越發沒意思起來。幸虧寶玉被一個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記掛着黛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寶玉笑問道:“寶姐姐,我瞧瞧你的紅麝串子。”可巧寶釵左腕上籠着一串,見寶玉問她,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生得肌膚豐澤,容易褪不下來。寶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要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生長在她身上。”正是恨沒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看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似水杏,脣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呆了,寶釵褪了串子來遞與他也忘了接。寶釵見他怔了,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丟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黛玉蹬着門檻子,嘴裏咬着手帕子笑呢。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兒吹,怎麼又站在那風口裏呢?”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屋裏呢。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一瞧,原來是個呆雁。”寶釵道:“呆雁在哪裏呢?我也瞧瞧。”林黛玉道:“我纔出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口裏說着,將手裏的帕子一甩,向寶玉臉上甩來。寶玉不防,正打在眼上,“噯喲”了一聲。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