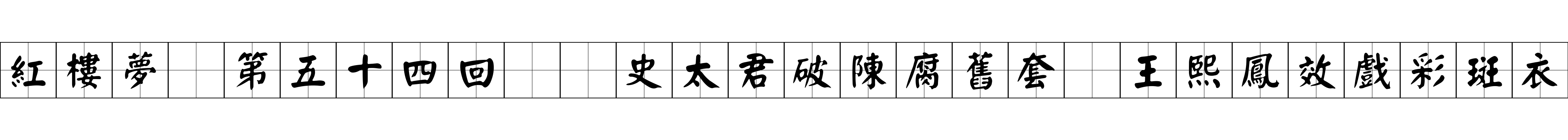紅樓夢-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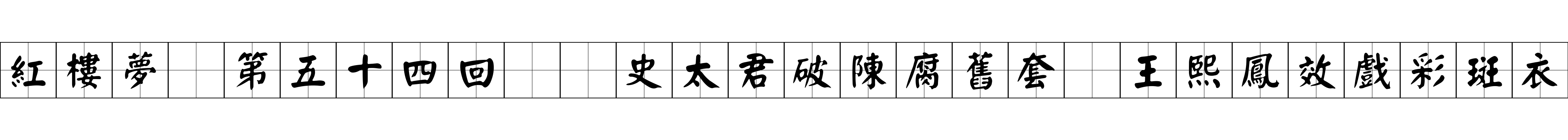
紅樓夢以錯綜複雜的清代上層貴族社會爲背景,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爲主線,通過對賈、史、王、薛四大家族榮衰的描寫,展示了18世紀上半葉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方方面面,囊括了多姿多彩的世俗人情,可謂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長篇小說。
卻說賈珍、賈璉暗暗預備下大簸籮的錢,聽見賈母說“賞”,他們也忙命小廝們快撒錢。只聽滿臺錢響,賈母大悅。
二人遂起身,小廝們忙將一把新暖銀壺遞在賈璉手內,隨了賈珍趨至裏面。賈珍先至李嬸席上,躬身取下杯來,回身,賈璉忙斟了一盞,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身笑說:“二位爺請坐着罷了,何必多禮。”於是除邢、王二夫人,滿席都離了席,俱垂手旁侍。賈珍等至賈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先捧杯,賈璉在後捧壺。雖止二人奉酒,那賈環弟兄等,卻也是排班按序,一溜隨着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也都一溜跪下。寶玉也忙跪下了。史湘雲悄推他,笑道:“你這會子又幫着跪下作什麼?有這樣,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悄笑道:“再等一會子再斟去。”說着,等他二人斟完起來,方起來。又與邢夫人、王夫人斟過來了。賈珍笑道:“妹妹們怎麼樣呢?”賈母等都說:“你們去罷,她們倒便宜些。”說了,賈珍等方退出。
當下天未二鼓,戲演的是《八義》中《觀燈》八出。正在熱鬧之際,寶玉因下席往外走。賈母因說:“你往哪裏去?外頭爆竹利害,仔細天上掉下火紙來燒了!”寶玉回說:“不往遠去,只出去就來。”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着。於是寶玉出來,只有麝月、秋紋並幾個小丫頭隨着。賈母因說:“襲人怎麼不見?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單支使小女孩子出來。”王夫人忙起身,笑回道:“她媽前日沒了,因有熱孝,不便前頭來。”賈母聽了點頭,又笑道:“跟主子,卻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若是她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裏不成?皆因我們太寬了,有人使,不查這些,竟成了例了。”鳳姐兒忙過來,笑回道:“今兒晚上她便沒孝,那園子裏也須得她看着,燈燭花炮最是耽險的。這裏一唱戲,園子裏的人誰不偷來瞧瞧。她還細心,各處照看照看。況且這一散後,寶兄弟回去睡覺,各色都是齊全的。若她再來了,衆人又不經心,散了回去,鋪蓋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齊備,各色都不便宜,所以我叫她不用來,只看屋子。散了又齊備,我們這裏也不耽心,又可以全她的禮,豈不三處有益。老祖宗要叫她,我叫她來就是了。”
賈母聽了這話,忙說:“你這話很是,比我想得周到,快別叫她了。但只她媽幾時沒了,我怎麼不知道?”鳳姐笑道:“前兒襲人去親自回老太太的,怎麼倒忘了?”賈母想了一想,笑說:“想起來了。我的記性竟平常了。”衆人都笑說:“老太太哪裏記得這些事。”賈母因又嘆道:“我想着,她從小兒服侍了我一場,又伏侍了雲兒一場,末後給了一個魔王寶玉,虧她魔了這幾年。她又不是咱們家根生土長的奴才,沒受過咱們什麼大恩典。她媽沒了,我想着要給她幾兩銀子發送,也就忘了。”鳳姐兒道:“前兒太太賞了她四十兩銀子,也就是了。”賈母聽說,點頭道:“這還罷了。正好鴛鴦的娘前兒也死了,我想她老子娘都在南邊,我也沒叫她家去走走守孝,如今叫她兩個一處作伴兒去。”又命婆子將些果子、菜饌、點心之類與她兩個喫去。琥珀笑說:“還等這會子呢,她早就去了。”說着,大家又喫酒看戲。
且說寶玉一徑來至園中,衆婆子見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園門內茶房裏烤火,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飲酒鬥牌。寶玉至院中,雖是燈光燦爛,卻無人聲。麝月道:“他們都睡了不成?咱們悄悄的進去,嚇他們一跳。”於是大家躡足潛蹤的進了鏡壁一看,只見襲人和一人對面,都歪在地炕上,那一頭有兩三個老嬤嬤打盹。寶玉只當她兩個睡着了,纔要進去,忽聽鴛鴦嘆了一聲,說道:“可知天下事難定。論理,你單身在這裏,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東去西來,沒個定準,想來你是再不能送終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裏,你倒出去送了終。”襲人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夠看父母回首。太太又賞了四十兩銀子,這倒也算養我一場,我也不敢妄想了。”寶玉聽了,忙轉身悄向麝月等道“誰知她也來了。我這一進去,她又賭氣走了,不如咱們回去罷,讓她兩個清清靜靜的說一回。襲人正一個人悶着,幸而她來得好。”說着,仍悄悄的出來。
寶玉便走過山石之後去站着撩衣,麝月、秋紋皆站住,背過臉去,口內笑說:“蹲下再解小衣,仔細風吹了肚子。”後面兩個小丫頭子知是小解,忙先出去茶房內預備水去了。這裏寶玉剛轉過來,只見兩個媳婦子迎面來了,問:“是誰?”,秋紋道:“寶玉在這裏,你大呼小叫仔細嚇着罷。”那媳婦們忙笑道:“我們不知道,大節下來惹禍了。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說着,已到了跟前。麝月等問:“手裏拿的是什麼?”媳婦們道:“是老太太賞金、花二位姑娘喫的。”秋紋笑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裏又跑出‘金花娘娘’來了。”寶玉笑命:“揭起來我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兩個媳婦忙蹲下身子,寶玉看了兩盒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果品菜饌,點了一點頭,邁步就走。麝月二人忙胡亂擲了盒蓋,跟上來。寶玉笑道:“這兩個女人倒和氣,會說話,她們天天乏了,倒說你們連日辛苦,倒不是那矜功自伐的。”麝月道:“這好的也很好,那不知禮的也太不知禮。”寶玉笑道:“你們是明白人,耽待她們是粗笨可憐的人就完了。”一面說,一面來至園門。
那幾個婆子雖喫酒鬥牌,卻不住出來打探,見寶玉來了,也都跟上了。來至花廳後廊上,只見那兩個小丫頭一個捧着小沐盆,一個搭着手巾,又拿着漚子小壺,在那裏久等。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了一試,說道:“你越大越粗心了,哪裏弄的這冷水!”小丫頭笑道:“姑娘瞧瞧這個天,我怕水冷,巴巴的倒的是滾水,這還冷了。”正說着,可巧見一個老婆子提着一壺滾水走來。小丫頭便說:“好奶奶,過來給我倒上些。”那婆子道:“哥哥兒,這是老太太泡茶的,勸你走了舀去罷,哪裏就走大了腳。”秋紋道:“憑你是誰的,你不給我?管把老太太茶吊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頭見是秋紋,忙提起壺來就倒。秋紋道:“夠了。你這麼大年紀,也沒個見識,誰不知是老太太的水!要不着的人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沒認出是姑娘來。”寶玉洗了手,那小丫頭子拿小壺倒了些漚子在他手內,寶玉漚了。秋紋、麝月也趁熱水洗了一回,漚了,跟進寶玉來。
寶玉便要了一壺暖酒,也從李嬸、薛姨媽斟起,二人也讓坐。賈母便說:“他小,讓他斟去,大家倒要幹過這杯。”說着,便自己幹了。邢、王二夫人也忙幹了,讓她二人。薛、李也只得幹了。賈母又命寶玉道:“連你姐姐妹妹一齊斟上,不許亂斟,都要叫她幹了。”寶玉聽說,答應着,一一按次斟了。至黛玉前,偏她不飲,拿起杯來,放在寶玉脣邊,寶玉一氣飲幹。黛玉笑說:“多謝。”寶玉替她斟上一杯。鳳姐兒便笑道:“寶玉,別喝冷酒,仔細手顫,明兒寫不得字,拉不得弓。”寶玉忙道:“沒有喫冷酒。”鳳姐兒笑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咐你。”然後寶玉將裏面斟完,只除賈蓉之妻是丫頭們斟的。復出至廊上,又與賈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進來,仍歸舊坐。
一時上湯後,又接獻元宵來。賈母便命:“將戲暫歇歇,小孩子們可憐見的,也給他們些滾湯滾菜的吃了再唱。”又命將各色果子、元宵等物拿些與他們喫去。一時歇了戲,便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生進來,放兩張杌子在那一邊,命她坐了,將弦子、琵琶遞過去。賈母便問李、薛:“聽何書好?”她二人都回說:“不拘什麼都好。”賈母便問:“近來可有添些什麼新書?”那兩個女先兒回說道:“倒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事。”賈母問是何名,女先兒道:“叫做《鳳求鸞》。”賈母道:“這個名字倒好,不知因什麼起的?你先大概說說原故,若好再說。”女先兒道:“這書上乃說殘唐之時,有一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曾做過兩朝宰輔。如今告老還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王熙鳳。”衆人聽了,笑將起來。賈母笑道:“這不重了我們鳳丫頭了?”媳婦忙上去推她,道:“這是二奶奶的名字,少混說!”賈母笑道:“你說,你說。”女先生忙笑着站起來說:“我們該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諱。”鳳姐兒笑道:“怕什麼!你們只管說罷,重名重姓的多着呢。”女先生又說道:“這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趕考,那日遇見大雨,進到一個莊上避雨。誰知這莊上也有個鄉紳,姓李,與王老爺是世交,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裏。這李鄉紳膝下無兒,只有一位千金小姐。這小姐芳名叫作雛鸞,琴棋書畫,無所不通。”
賈母忙道:“怪道叫作《鳳求鸞》。不用說,我已猜着了,自然是這王熙鳳要求這雛鸞小姐爲妻了。”女先兒笑道:“老祖宗原來聽過這一回書。”衆人都道:“老太太什麼沒聽過!便沒聽過,也猜着了。”賈母笑道:“這些書都是一個套子,左不過是些佳人才子,最沒趣兒。把人家女兒說得那樣壞,還說是‘佳人’,編得連影兒也沒有了。開口都是書香門第,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生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個絕代佳人。只一見了一個清俊的男人,不管是親是友,便想起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禮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兒是佳人?便是滿腹文章,做出這些事來,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男人,滿腹文章去作賊,難道那王法就說他是才子,不入賊情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再者,既說是世宦書香大家小姐,都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便是告老還家,自然這樣大家人口不少,奶母、丫鬟、服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麼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鬟?你們白想想,那些人都是管什麼的?可是前言不答後語?”
衆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一說,是謊都批出來了。”賈母笑道:“這有個原故:編這樣書的,有一等妒人家富貴,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污穢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了這些書,看魔了,他也想一個佳人,所以編了出來取樂。何嘗他知道那世宦讀書家的道理!別說他那書上那些世宦書禮大家,如今眼下真的拿我們這中等人家說起,也沒有這樣的事,別說是那些大家子。可知是謅掉了下巴的話。所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連丫頭們也不懂這些話。這幾年我老了,他們姊妹們住得遠,我偶然悶了,說幾句聽聽,她們一來,就忙叫歇了。”李、薛二人都笑說:“這正是大家的規矩,連我們家也沒這些雜話給孩子們聽見。”
鳳姐兒走上來斟酒笑道:“罷,罷!酒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潤潤嗓子再掰謊。這一回就叫作《掰謊記》,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時,老祖宗一張口難說兩家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是真是謊且不表,再整那觀燈看戲的人。老祖宗且讓這二位親戚喫一杯酒,看兩齣戲之後,再從昨朝話言掰起,如何?”她一面斟酒,一面笑說,未曾說完,衆人俱已笑倒。兩個女先生也笑個不住,都說:“奶奶好剛口。奶奶要一說書,真連我們喫飯的地方也沒了。”
薛姨媽笑道:“你少興頭些!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鳳姐兒笑道:“外頭的只有一位珍大爺。我們還是論哥哥妹妹,從小兒一處淘氣淘了這麼大。這幾年因做了親,我如今立了多少規矩了。便不是從小兒的兄妹,便以伯叔論,那《二十四孝》上‘斑衣戲彩’,他們不能來‘戲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這裏好容易引得老祖宗笑了一笑,多吃了一點東西,大家喜歡,都該謝我纔是,難道反笑話我不成?”賈母笑道:“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痛痛的笑一場,倒是虧她,才一路笑得我心裏痛快了些,我再喫一鍾酒。”喫着酒,又命寶玉:“也敬你姐姐一杯。”鳳姐兒笑道:“不用他敬,我討老祖宗的壽罷。”說着,便將賈母的杯拿起來,將半杯剩酒吃了,將杯遞與丫鬟,另將溫水浸的杯換了一個上來。於是各席上的杯都撤去,另將溫水浸着待換的杯斟了新酒上來,然後歸坐。
女先生回說:“老祖宗不聽這書,或者彈一套曲子聽聽罷。”賈母便說道:“你們兩個對一套《將軍令》罷。”二人聽說,忙和絃按調撥弄起來。賈母因問:“天有幾更了?”衆婆子忙回:“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浸起來。”早有丫鬟拿了添換的衣裳送來。王夫人起身笑說道:“老太太不如挪進暖閣裏地炕上,倒也罷了。這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我們陪着就是了。”賈母聽說,笑道:“既這樣說,不如大家都挪進去,豈不暖和?”王夫人道:“恐裏頭坐不下。”賈母笑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這些桌子,只用兩三張並起來,大家坐在一處擠着,又親香,又暖和。”衆人都道:“這纔有趣。”
說着,便起了席。衆媳婦忙撤去殘席,裏面直順並了三張大桌,另又添換了果饌擺好。賈母便說:“這都不要拘禮,只聽我分派你們就坐纔好。”說着,便讓薛、李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寶琴、黛玉、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向寶玉說:“你挨着你太太。”於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着寶玉,寶釵等姊妹在西邊,挨次下去便是婁氏帶着賈菌,尤氏、李紈夾着賈蘭,下面橫頭便是賈蓉之妻。賈母便說:“珍哥兒帶着你兄弟們去罷,我也就睡了。”
賈珍忙答應,又都進來。賈母道:“快去罷!不用進來,才坐好了,又都起來。你快歇着,明日還有大事呢。”賈珍忙答應了,又笑道:“留下蓉兒斟酒纔是。”賈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賈珍答應了一個“是”,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二人自是歡喜,便命人將賈琮賈璜各自送回家去,便邀了賈璉去追歡買笑,不在話下。
這裏賈母笑道:“我正想着,雖然這些人取樂,竟沒一對雙全的,就忘了蓉兒。這可全了,蓉兒就合你媳婦坐在一處,倒也團圓了。”因有家人媳婦回說開戲,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得興頭,又要吵起來。況且那孩子們熬夜,怪冷的。也罷,叫他們且歇歇,把咱們的女孩子們叫了來,就在這臺上唱兩出給他們瞧瞧。”媳婦們聽了,答應了出來,忙得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傳人,一面二門口去傳小廝們伺候。小廝們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的大人一概帶出,只留下小孩子們。
一時,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個人,從遊廊角門出來。婆子們?抱着幾個軟包,因不及擡箱,估量着賈母愛聽的三五齣戲的綵衣包了來。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賈母,皆手站着。賈母笑道:“大正月裏,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出來逛逛?你們唱什麼?剛纔八出《八義》鬧得我頭疼,咱們清淡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這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不知聽過多少好戲的。這些姑娘都比咱們家姑娘見過好戲,聽過好曲子。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玩戲家的班子,雖是小孩子,卻比大班還強。咱們好歹別落了褒貶!少不得弄個新樣兒的。叫芳官唱一出《尋夢》,只只需用管蕭合,笙、笛一概不用?。”文官笑道:“這也是的,我們的戲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不過聽我們一個發脫口齒,再聽一個喉嚨罷了。”賈母笑道:“正是這話了。”李嬸薛姨媽喜得都笑道:“好個靈透孩子!她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們。”賈母笑道:“我們這原是隨便的玩意兒,又不出去做買賣,所以竟不大合時。”說着,又道:“叫葵官唱一出《惠明下書》,也不用抹臉。只用這兩出,叫他們聽個疏異罷了。若省一點力,我可不依。”
文官等聽了出來,忙去扮演上臺,先是《尋夢》,次是《下書》。衆人都鴉雀無聞,薛姨媽因笑道:“實在戲也看過幾百班,從沒見用簫管的。”賈母道:“也有,只是像方纔《西樓?楚江情》一支,多有小生吹蕭合的。這合大套的實在少,這也在主人講究不講究罷了。這算什麼出奇?”指湘雲道:“我像她這麼大的時節,他爺爺有一班小戲,偏有一個彈琴的湊了來,即如《西廂記》的《聽琴》,《玉簪記》的《琴挑》,《續琵琶》的《胡茄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這個更如何?”衆人都道:“這更難得了。”賈母便命個媳婦來,吩咐文官等,叫她們吹一套《燈月圓》。媳婦領命而去。
當下賈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鳳姐兒因見賈母十分高興,便笑道:“趁着女先兒們在這裏,不如叫她們擊鼓,咱們傳梅,行一個‘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賈母笑道:“這是個好令,正對時對景。”忙命人取了一面黑漆銅釘花腔令鼓來,與女先兒們擊着,席上取了一枝紅梅。賈母笑道:“若到誰手裏住了,喫一杯,也要說個什麼纔好。”鳳姐兒笑道:“依我說,誰像老祖宗要什麼有什麼呢。我們這不會的,豈不沒意思。依我說也要雅俗共賞,不如誰輸了,誰說個笑話罷。”衆人聽了,都知道他素日善說笑話,最是她肚內有無限的新鮮趣談。今見如此說,不但在席的諸人喜歡,連地下服侍的老小人等無不喜歡。那小丫頭子們都忙出去找姐喚妹的,告訴他們:“快來聽,二奶奶又說笑話兒了。”衆丫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
於是戲完樂罷,賈母命將些湯點果菜與文官等喫去,便命響鼓。那女先兒們皆是慣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或如迸豆之疾,或如驚馬之亂馳,或如疾電之光而忽暗;其鼓聲慢,傳梅亦慢,鼓聲疾,傳梅亦疾。恰恰至賈母手中,鼓聲忽住。大家呵呵一笑,賈蓉忙上來斟了一杯。衆人都笑道:“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們才托賴些喜。”賈母笑道:“這酒也罷了,只是這笑話倒有些難說。”衆人都說:“老太太的比鳳姐兒的還好還多,賞一個,我們也笑一笑兒。”賈母笑道:“並沒什麼新鮮發笑的,少不得老臉皮子厚的說一個罷了。”因說道:“一家子養了十個兒子,娶了十房媳婦。惟有第十個媳婦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九個不孝順。這九個媳婦委屈,便商議說:‘咱們九個心裏孝順,只是不像那小蹄子嘴巧,所以公公婆婆老了,只說她好。這委屈向誰訴去?’大媳婦爲有主意,便說道:‘咱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和閻王爺說去,問他一問,叫我們託生人,爲什麼單單的給那小蹄子一張乖嘴,我們都是笨的?’衆人聽了,都喜歡,說這主意不錯。第二日,便都到閻王廟裏來燒了香,九個人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九個魂專等閻王駕到,左等不來,右等也不到。正着急,只見孫行者駕着筋斗雲來了,看見九個魂,便要拿金箍棒打,唬得九個魂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問原故,九個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孫行者聽了,把腳一跺,嘆了一口氣道:‘這原故幸虧遇見我,等着閻王來了,他也不得知道的。’九個人聽了,就求說:‘大聖發個慈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笑道:‘這卻不難。那日你們妯娌十個託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那裏去的,因爲撒了泡尿在地下,你那小嬸子便吃了。你們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吃了就是了。”
說畢,大家都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好的,幸而我們都笨嘴笨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兒尿了。”尤氏、婁氏都笑向李紈道:“咱們這裏誰是喫過猴兒尿的,別裝沒事人兒。”薛姨媽笑道:“笑話兒不在好歹,只要對景就發笑。”說着又擊起鼓來。小丫頭子們只要聽鳳姐兒的笑話,便悄悄的和女先兒說明,以咳嗽爲記。須臾傳至兩遍,剛到了鳳姐兒手裏,小丫頭子們故意咳嗽,女先兒便住了。衆人齊笑道:“這可拿住她了。快吃了酒,說一個好的,別太逗得人笑得腸子疼。”
鳳姐兒想了一想,笑道:“一家子也是過正月半,閤家賞燈喫酒,真真的熱鬧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婆婆、媳婦、孫子媳婦、重孫子媳婦、親孫子、侄孫子、重孫子、灰孫子、滴滴搭搭的孫子、孫女兒、侄孫女兒、外孫女兒、侄表孫女兒、姑表孫女兒......噯喲喲,真好熱鬧!”衆人聽她說着,已經笑了,都說:“聽數貧嘴的,又不知編派哪一個呢?”尤氏笑道:“你要招我,我可撕你的嘴!”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人家費力說,你們混,我就不說了。”賈母笑道:“你說你說,底下怎麼樣?”鳳姐兒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團團的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就散了。”
衆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別無它話,都怔怔的還等下話,只覺冰冷無味。史湘雲看了她半日。鳳姐兒笑道:“再說一個過正月半的。幾個人擡着個房子大的炮仗往城外放去,引了上萬的人跟着瞧去。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便偷着拿香點着了。只聽‘噗哧’一聲,衆人鬨然一笑都散了。這擡炮仗的人抱怨賣炮仗的捍得不結實,沒等放,就散了。”湘雲道:“難道他本人沒聽見響?”鳳姐兒道:“這本人原是聾子。”衆人聽說,一回想,不覺一齊失聲都大笑起來。又想着先前那一個沒完的,問她:“先一個怎麼樣?也該說完。”鳳姐兒將桌子一拍,說道:“好囉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節也完了,我看着人忙着收東西還鬧不清,哪裏還知道底下的事了。”衆人聽說,復又笑將起來。鳳姐兒笑道:“外頭已經四更,依我說,老祖宗也乏了,咱們也該‘聾子放炮仗――散了’罷。”尤氏等用手帕子捂着嘴,笑的前仰後合,指她說道:“這個東西真會數貧嘴。”賈母笑道:“真真這鳳丫頭越發貧嘴了。”一面說,一面吩咐道:“他提炮仗來,咱們也把煙火放了,解解酒。”
賈蓉聽了,忙出去,帶着小廝們就在院內安下屏架,將煙火設吊齊備。這煙火皆系各處進貢之物,雖不甚大,卻極精巧,各色故事俱全,夾着各色花炮。林黛玉稟氣柔弱,不禁“畢駁”之聲,賈母便摟她在懷中。薛姨媽摟着湘雲。湘雲笑道:“我不怕。”寶釵等笑道:“他專愛自己放大炮仗,還怕這個呢!”王夫人便將寶玉摟入懷內。鳳姐兒笑道:“我們是沒有人疼的了。”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摟着你。也不怕臊,你這會子又撒嬌了,聽見放炮仗,吃了蜜蜂兒屎似的,今兒又輕狂起來。”鳳姐兒笑道:“等散了,咱們園子裏放去。我比小廝們還放得好呢。”說話之間,外面一色一色的放了,又放了許多的“滿天星”、“九龍入雲”、“一聲雷”、“飛天十響”些之類的零碎小爆竹方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蓮花落”,撒了滿臺的錢,命那些孩子們滿臺搶錢取樂。又上湯時,賈母說道:“夜長,覺得有些餓了。”鳳姐兒忙回說:“有預備的鴨子肉粥。”賈母道:“我喫些清淡的罷。”鳳姐兒忙道:“也有棗兒熬的粳米粥,預備太太們喫齋的。”賈母笑道:“不是油膩膩的,就是甜的。”鳳姐兒又忙道:“還有杏仁茶,只怕也甜。”賈母道:“倒是這個還罷了。”說着,又命人撤去殘席,外面另設上各種精緻小菜。大家隨便隨意吃了些,用過漱口茶,方散。
十七日一早,又過寧府行禮,伺候掩了宗祠,收過影像,方回來。此日便是薛姨媽家請喫年酒。十八日便是賴大家,十九日便是寧府賴升家,二十日便是林之孝家,二十一日便是單大良家,二十二日便是吳新登家。這幾家,賈母也有去的,也有不去的,也有高興,直待衆人散了方回的,也有興盡,半日一時就來的。凡諸親友來請,或來赴席的,賈母一概怕拘束不會,自有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三人料理。連寶玉只除王子騰家去了,餘者亦皆不會,只說賈母留下解悶。所以倒是家下人家來請,賈母可以自便之處,方高興去逛逛,閒言不提。當下元宵已過――要知端的,下回分解。